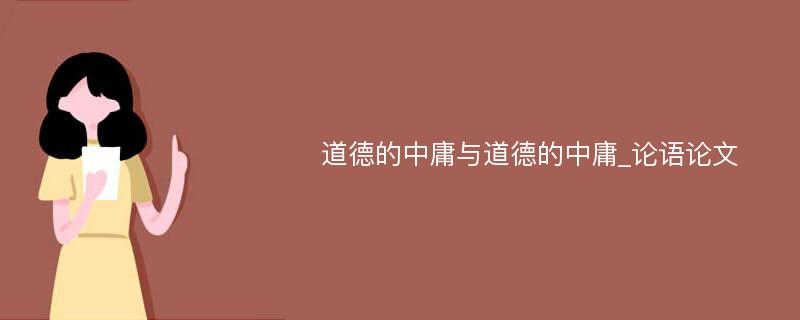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庸论文,伦理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对中庸可作哲学的诠释,也可作伦理学的诠释。在哲学的视域中,对中庸可作本体论的诠释,也可作方法论的诠释;在伦理学的视域中,对中庸可从道德的层面进行诠释,也可从伦理的层面进行诠释。尽管对于中庸不同意向的诠释之间,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从不同的视域或从不同的层面诠释中庸,对于全面了解儒家中庸理论是有益的。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对中庸从道德与伦理两个层面作一些分疏与考察,以期通过这种考察,从一个侧面论释儒学的发展与价值。
一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道德与伦理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范畴。就字义而言,道的本义为当行之路,这种本义使道演绎引申出了法则、规律之类的含义。德是“德道”。德可与得相通,“德道”即是得道,“德道”或得道也即是道德。道德与“德道”的意蕴均以《荀子》论释最为清晰。关于“德道”,《荀子·解蔽》中说:“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是以与治离走而是己不辍也。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蔽者乎!德道之人,乱国之君非之上,乱家之人非之下,岂不哀哉!”荀况这里所谓“德道”即是得道,荀况所感叹的是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时代,“德道之人”,反而要受到“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的“乱国之君”与“乱家之人”的非难。
关于道德,《荀子·劝学》中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矣。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况认定人性本恶,提倡“化性起伪”,看重后天的学习对于培植人性的作用,主张“学不可以已”。他把学习的原则理解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将学习的功能与价值,归结为提高人的德性品质,并把“学至乎礼而止”视为“道德之极”。这种“道德之极”当是“德道”的一种最高境界。应当说,荀子对道德范畴的使用,较为典型地代表了早期儒家学派对于道德的理解。这种理解吸纳了先秦各家学说中关于道的观念与德的观念:一是强调道乃“万物之所由”,道为“治国之经”;二是认定德同于得,道德即是“德道”;从而使道德成了一个表述人们外得于物、内凝于己的内在的德性与品质的范畴。在先秦学术中,荀学是“儒分为八”的产物。在儒学系统中,荀子的儒学与子思、孟轲一系的儒学理趣有别。但是,荀子的道德观念,仍然沿袭与坚持了儒学的传统,其意蕴大体上与《论语》《孟子》中出现的“德”范畴的意蕴是一致的。
历史上伦与理本来也是两个独立的范畴。伦具有类别、关系等含义;理则有条理、秩序、理则等方面的含义。在人们的社会生活范围之内,伦当是人伦,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则是指维系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外在的规范与秩序。这样的伦理,即所谓人伦之理。
但是,依据伦、理范畴的内涵,这两个范畴所指称的对象并不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除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其它自然事务的类别、关系、理则等问题同样可以用伦、理范畴来加以论释,古代典籍《礼记·乐记》中即从广义上使用伦、理范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德,德者得也。”这里所说“乐者,通伦理者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的伦、理范畴联用的实例。然而,这一论述中虽将乐与礼并提,认定“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但其所说伦理似是广义的,并非专就人伦之理立论。在《论语》《孟子》一类早期儒学著作中,作为人伦之理的伦理,常常被表述为“伦”“大伦”或“人伦”。后来,随着儒学倡导的道德观念不断强化与发展,人们才以伦理、伦常等范畴专门论释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外在的准则,与作为人们内在德性的道德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道德与伦理虽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范畴,其意蕴却是有所区别的。
道德范畴与伦理范畴在意蕴上的差别,曾经深刻地影响儒家伦理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儒家中庸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即是其表征之一。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曾从道德与伦理两个层面理解中庸,建构中庸理论,利用中庸理论。早期儒家对中庸的理解与规定即侧重于道德的范围,所提倡的中庸也主要是道德的中庸。
在儒学的系统中,主张和提倡道德的中庸,首推儒学的创立者孔丘。《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从这种论述来看,孔丘一方面肯定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同时又认定人们缺少这样的道德,且时间已经很久了。在《论语》一书中,“中”这个范畴出现的频率不低,但论及“中庸”这一范畴,仅此一处。后人对《论语》中出现的“中”及“中庸”的诠释很多。杨伯峻先生作《论语译注》,书后附有《论语词典》。据杨先生的考察,“中”字在《论语》中出现过23次,具有多层面的含义。作为哲学术语使用为一次,即《论语·尧曰》中所说的:“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这里的“中”指事物的一种至当不移的合理状态。作为伦理学范畴使用时则谓之中庸。杨先生对《论语》中仅出现一次的中庸的解释是:“中庸——这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孔子拈出这两个字,就表示他的最高道德标准,其实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1](第64页)。杨先生对《论语》中的“中”及“中庸”的诠释乃大家之言,值得我们咀嚼与借鉴。但是,如果对“中庸”的诠释,注意到其道德层面与伦理层面的差别,那么,我们对孔丘所持的中庸观念,还可作更深入的思考与解析。
我们解析孔丘的中庸观念,首先应注意到的是其内在性特征。孔丘认定“中庸”乃至上之德,这样的德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品质或德性。在西方伦理学中,德性被视为对功能完满实现的具有。这样的德性,即主要地表现为人的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同时,在解析孔丘的中庸观念时,我们还应注意古人对于作为事物理想状态的“中”与作为道德的中庸的分疏。儒家学者是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学的代表人物大都注意依据自然理则来论释人们的社会生活秩序。孔丘所持的中庸观念,即与他对于事物存在的合理状态——“中”的理解关联在一起。但是,从《论语》中对中庸的记述来看,孔丘对于事实的“中”与道德的中庸是有所区别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对于真的事物来说中间就是真实,让我们说中道就是真理”[2](第40页)。真实的“中”表明事物存在的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状态,而作为德性的“中道”,当在主体的范围之内,“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应当肯定,东方的哲人与西方的智者对于中庸的理解是相通的,孔丘所理解的“中庸”,正是一种作为“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是人们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德性。
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伦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价值取向。这样的中庸不同于作为事物存在状态的“中”。孔丘曾论及“过”“不及”与“过犹不及”。据《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从这一记述来看,孔丘所谓“过”“不及”与“过犹不及”,是评断颛孙师和卜商“孰贤”的根据。作为评断颛孙师和卜商孰贤的根据,“过”与“不及”,所涉及的是存在的、实际的、事实的“中”与不“中”,而非道德的中庸。换言之,孔丘这里所论之“中”,主要在事实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在价值的范围之内。在价值的范围内,中庸作为道德主体的德性,只是行为主体的道德意识与动机。这种意识或动机,并非一种主体行为的客观标准,无所谓“过”,也无所谓“不及”,对人们行为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能要么是道德的,要么是非道德的。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就行为的价值取向而言,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行为置于中庸的范围之内。这种作为价值取向的中庸的意蕴只能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应该”。孔丘在《论语·里仁》中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中注释“適”“莫”二字时说:“適,丁历反,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適从’,是也。莫,不肯也。比,必二反,从也。谢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学,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得罪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然则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杨伯峻先生采纳朱熹的“说法”,用现代语言把孔丘的这段话表述为:“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1](第37页)。杨先生的这种表述,颇合孔丘本意。“合理恰当”便干,当是其自以为“应该”才干。可以说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是对其“中庸”意蕴最具体的表述之一。孔丘提倡“无適”“无莫”,“义之与比”,不仅表明他主张中庸,重视道德理性,也表明他把中庸理解为“应该”,理解为人们生活行为中的一种价值取向。
“应该”意义上的“中庸”,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自身行为的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作为一种行为动机,人们对于中庸可以趋同。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生活个体的主客观条件千差万别,存在差异,个体行为中的“应该”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同一。因此,“应该”不可能成为一个客观的行为尺度,而只能表示人们自己的一种主观选择与判定。亚里士多德论及“应该”时,即曾区别对象的应该、时间的应该与方式的应该。在早期的儒家的著作中,对于“应该”意义上的中庸的这种特点也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仁”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儒门后学对“仁”的论释很多,但少有领悟孔子本义者。孟子认为“仁,人心也”,肯定“仁”为人们的道德意识,颇合孔子本意。作为人的道德意识的“仁”,实际上也可以说即是中庸,即是“应该”,即是一种价值取向。二程的弟子问“仁”,程伊川答曰:“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爱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3](卷十八)。程伊川否定对“仁”理解的片面,实际上强调了作为道德意识的“仁”,对于人们道德行为的根源性与普适性。那么怎样理解“仁”呢?程明道的主张是回到孔子思想自身:“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3](卷二)。程明道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确是对于“仁”最切当的论释。这样的“仁”正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德性,也是人自择的一种行为取向。唯有以这样的视角释“仁”,才有可能深刻理解孔子为什么要强调:“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体悟孔子对道德理性的张扬与凸显,避免对孔子“仁”学盲目的释义与无理的非难。
在孔子后学中,孟子对道德的中庸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孟子以“权”释“中”,即是因为他意识到了道德的中庸只是人们行为中的一种动机,取向、选择。《孟子·尽心上》中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即可以说是强调作为道德的中庸,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行为标准,而只是表明人们的一种行为取向。这种行为取向的表现因人而异,形式应当是多样的,而不可能是单一的。《孟子·离娄下》中所说的“汤执中,立贤无方”,强调汤“执中”,使自己选拔人才不拘泥于某种形式和原则。这里所说的“执中”,也当是指汤遵循了中庸,在自己的行为中坚持了“应该”这一取向。
由此可见,早期儒家提倡中庸,多属道德层面的中庸。把中庸理解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取向,使中庸成为一种主观的道德动机,这使得早期儒家十分看重生活行为中的道德自律与自觉,强调道德自觉对于培养人的品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特殊功用。孔子主张人们生活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都是要提倡道德理性,强调道德自觉。在孔子看来为“仁”之本与为“仁”之方,都需要人们的道德自觉,都决定于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而人们行为中正确的动机与取向,实际上即是人们在生活中对“应该”的选择,或说对中庸的践履。
二
作为人们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层面的中庸所关注的是个体的行为取向,是个体的人生价值,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外在原则的伦理的中庸,所关注的则是群体的行为标准,是社会的秩序与稳定。这种伦理层面上的中庸观念,是随着儒学自身的分化与发展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儒家学说中,从外在理则的层面规定和理解“中庸”,《中庸》的问世是其标志之一。相传《中庸》是子思的著作。现存的《中庸》则为《礼记》中的一篇。冯友兰先生曾经认为,在子思的著作中,可能确曾有一篇名为《中庸》,《礼记》中的《中庸》,发挥了子思的思想,却并非一个人的著作,也不是一个时期的著作[4](第109页)。《中庸》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难以断定,但《中庸》中的思想观念与子思、孟轲一系的儒家学说关联则是可以肯定的。
《中庸》的思想主旨,实际上在于拓展孔丘的“中庸”观念。《中庸》的作者不仅从道德品质的角度理解中庸,而且将中庸理解为世间事物的普遍法则,提出了“中和”的观念,以“大本”“达道”指称“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所说的“大本”,不仅指事物存在的理想状态与合理状态,实际上也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根据。“达道”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姐妹等5种人际关系的原则。这样的“达道”是“大本”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而作为“大本”与“达道”的’中和”,实际上也即是“中庸”。在《中庸》的作者看来,人们“择乎中庸”,能够“得一善”,把“中庸”推致于天地事物,则能够维系自然的秩序,促进万物的生长。这样的“中庸”,既是人们的道德品质,又是世间事物存在发展的理则与根据。因为,作为道德品质的“中庸”与作为事物理则的中庸是统一的。人道的中庸源于天道的中庸,或者说作为道德品质的中庸,只是作为事务理则的中庸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体现。
从儒学的发展来看,《中庸》的理趣与孟轲的儒学有别,孟轲的儒学不仅认同孔子的中庸观念,以“经权”释“中”,而且拓展了孔丘的心性理论,认定“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强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5](《尽心上》)。讲本心即性,仁义在内,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则是由肯定人的德性为天之所与,进而强调人道与天道一贯,把“中庸”这一道德原则提升为“大本”“达道”,使其升华为宇宙法则和事物生存的普遍根据。可以说这种理解,使儒家学说中的中庸观念,开始明显地从道德的层面转向伦理的层面,或者说从内在的层面转向外在的层面。因为道德层面的中庸,强调人们行为中的“应该”与自觉,伦理层面的中庸所强调的则是中庸的外在性、客观性及其对于人道与天道的根源性和普适性。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儒学由百家之说中的一家,逐步取得“独尊”的地位,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学,自觉地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更加注意以天道论释人道,从理论的层面论证封建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儒学这种从强调个人德性,注重个人生活中的道德动机,到注意社会群体的行为规范,提倡礼法名教,强调宗法等级的理论追求,促使道德的中庸进一步向伦理的中庸转化。这种转化的最显著表现,当数宋儒对于中庸的诠释与理解。
宋儒也有从道德的层面理解中庸者,程伊川所谓“如三过其门不入,在禹稷之时为中,若居陋巷,则非中也;居陋巷,在颜子之时为中,若三过其门不入,则非中也。”[3](卷十八)即是从道德的层面理解与论释中庸。但是,在宋代的儒学系统中,心学家与理学家都关注人的心性问题,心学家以为“心即理”,“心”“理”“不容有二”,强调“心”与“理”都为“我固有之”。理学家主张理本,认定“理具于心”,对于“心”“理”关系及其界限的理解,同心学家的思想路数有所不同。但心学家与理学家在理论上的共同追求都在于将儒家伦理本体化、客观化。因此,不论心学还是理学对于“中庸”的理解,都典型地体现了儒学中把“中庸”从内在的道德品质转换为外在的道德规范,把主观的道德意识视为普遍“天理”,升华为宇宙本原的思想倾向。
这种思想倾向,首先表现为宋儒认同《中庸》的思想主旨,从事物普通法则的角度来理解中庸。程颢、程颐即认定:“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种作为“天下”“正道”“定理”的中庸,已不单是人的德性,而是所有事物赖以生存的理则与根据。程颐在其学术活动中,曾同原关学门人吕大临一起深入辨析中庸。在辩论中,程颐基于理学家的立场,强调“性”“命”“道”“各有所当”;认定“中”为“大本”,“和”为“达道”,“大本”为体,“达道”为用,“体用自殊”,不同意吕氏“中即性也”,以及“不倚之谓中,不杂之谓和”等论断,明确地肯定“中即道也”。吕大临认定“中即性也”,实际上具有心学家的思想倾向。在心学家看来,“中”既可以说是道,也可以说是本性或本心。因为心性不容有二,道德原则与宇宙法则不容有二。心学家与理学家对中庸的理解虽有歧异,但在将中庸既作为道德原则又作为宇宙本体这一点上,却不无共同之点。
朱熹服膺二程之学,把理学发展到一个高峰。在朱熹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对《中庸》的理解与诠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朱熹认定《中庸》乃“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他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在《中庸章句》中,对《中庸》“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释“中”,以平常释“庸”,把《中庸》中所说的“大本”“达道”解释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这种理解中,作为“大本”的“中”成了“道之体”或说理之源,作为“达道”的“和”则成了“道之用”或说理之实现。朱熹不仅以道之体用来理解和诠释“中和”,而且强调“中和”即是“中庸”。在朱熹看来,《中庸》从第二章开始直到第十章都是以“中庸”“释首章之义”。他以游定夫“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性言之,则曰中庸”为据,解释《中庸》中何以会“变‘和’言‘庸’”。强调“‘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朱熹晚年高足陈淳曾说:“大抵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又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内外而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谓确而尽矣”[6](第48页)。对朱熹“合内外”即兼顾人的道德性为与宇宙本体论释“中庸”称道不已。
当朱熹“合内外”而言“中庸”时,“中庸”的伦理层面上的意蕴更加完备了。这种伦理层面上的“中庸”,已不单是作为道德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或者说已不是个体行为中的道德意识,而是社会群体必须遵循的一种外在的行为原则。因为,按照朱熹的理解,“中”即是“道”,而“道”乃“天理之当然”。“中庸”已是人们生话中不能不遵循的当然之理了。“择乎中庸,辨别众理”,成了人们的“成德”之途,当行之路。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曾长期受到推祟与褒扬。但是,就中庸观念而言,由于宋儒将中庸由人们的道德动机、道德情感、道德要求,一变而为人们的行为铁律,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伦常之理,成为人们生活中带强制性的行为准则,终于使早期儒家的中庸观念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可以说在宋儒的思想系统中,脱离现实的人际关系,脱离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其使儒家的中庸观念失去自身内涵与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儒家学说的特征归结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这既指明了儒家关注人伦的学理趣向,同时也指出了儒学的理论价值。但是,儒家理论自身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学的价值是应当区别解读的。从道德的中庸到伦理的中庸,表明儒家为适应中国封建统治的需要,从注意诠释个体的道德品质,转向注意论释和建构群体的道德原则规范;而中庸观念在其演变过程中,自身的内涵并不相同。可以说,中庸意蕴的转变,从一个具体的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领略儒家伦理价值的范例。
在现代伦理学中,道德原则规范被理解为一定社会或阶级对人们行为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常常表现为道德主体的行为准则。这样的准则,既是人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所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又是判断人们的道德行为或非道德行为的具体标准。道德品质则是道德原则规范在道德主体自身的体现,是通过道德主体的行为和思想意识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倾向。道德品质与道德原则规范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而言,良好的道德品质,有助于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原则规范;一定的道德原则规范,又是人们形成相应的道德品质的前提和条件。在儒家伦理中,“仁”为五常之首,既可以理解为一种道德品质或说德性,又可以说是一种规范,一种常则。在道德的系统内,道德品质与道德原则规范是统一的。但是,道德品质与道德原则规范作为道德系统中的不同要素,二者之间的差异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最为显著的即是:道德品质是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道德原则规范则表现为规范评价道德主体行为的外在标准。
儒家伦理中,有的范畴既可以理解为德性或说道德品质,又可以理解为一种常则,一种规范。例如前面所述之“仁”。“仁”作为德性,表现为道德主体“爱人”的思想倾向;“仁”作为道德规范,则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道德学说实际上即是以“仁”作为核心范畴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在儒家伦理中,也有一些范畴不宜既作为表述德性的范畴,又作为表示规范的范畴,较为典型的即是“中庸”。
如前所述,早期儒家将“中庸”作为一种德性或说道德品质,表述人们行为中的一种主观动机和价值取向,这种“应该”意义上的中庸观念,源于对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即所谓“中”的理解,使价值范围内的中道同事实上的中间区别开来,论释了人们道德行为的思想基础。这样的思想基础对于人们的道德行为而言,是带有普适性质的。当“中庸”在儒学中被逐步演变成一个表示原则和规范的范畴时,除了使“中庸”等同于“中和”,将事物真实的中间等同于价值的中道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为人们的生活行为提供一种具备可行性的准则。在伦理学的范围内,人们应当肯定善和恶实际上就是真与假,但也必须承认道德上的善恶与事实上的真假是不能绝对等同的。因为在价值的范围内,人们很难以事实上的中间,来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做到“中庸”。因此,就学理上的价值而言,在儒学所主张的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之间,我们更应该肯定道德的中庸。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以“应该”论释中道,但亚氏的中道观念晚出于孔丘的“中庸”观念。苗力田先生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在其《述要》中对中西文明有一个比较:“勇敢是相对恐惧而言的中道,过度了鲁莽,不及了是怯懦。勇敢就是中间的命中,这个中间像柏拉图的模式一样,来自射手与舵师的比喻,起着标准的作用。但在人事活动中,哪里是中间呢?那就是应该。一个应该的人怕他应该怕的,在应该的时间,以应该的方式。然而这究竟和舵之标、射之准不一样,应该是由人来断定的。亚公说,Spoudaios(真诚之人)是尺度,是准绳。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相互对照,圣人与Spoudaios对等,而Iogos最恰当的意思还是言说了。从时间上也许可以把孔丘和苏格拉底相比较,但在思想上孔子到底有一本公认的《论语》,而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的那些话,到底哪些是出自苏格拉底之口,就众说纷纭了。由此可见,就实践智慧而言,黄河文化较之爱琴海文明确实是超前200年”[2](第10页)。苗先生的论断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中,儒家文化尤其是其中庸学说的确是一种最悠久的且具世界意义的文化资源。当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思考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复兴,不应忽略儒学的传统与价值。但是,我们也不应无视儒学的片面与局限。仅从我们对儒家中庸观念演变的辨析来看,我们似可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对儒家文化总体价值的评判,应将主要目光投向儒家伦理;对儒家伦理价值的辨析,应将主要目光投向儒家的中庸学说;对儒家中庸学说的认同,则应将主要目光投向早期儒家主张的道德的中庸。因为,早期儒家的这种中庸观念,仍可作为今天人们生活的价值取向,成为今天人们道德行为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标签:论语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伦理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朱熹论文; 孔子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传记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