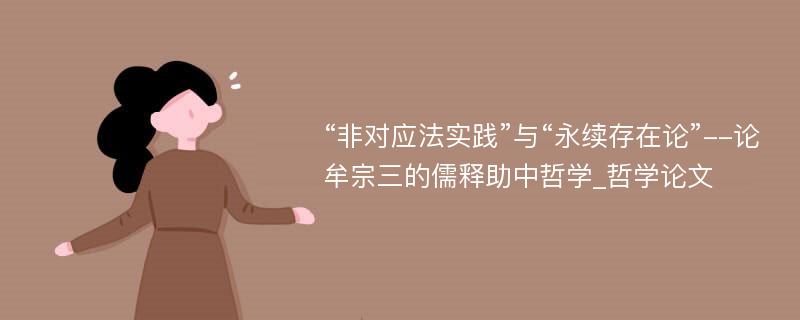
“不相应行法”与“执的存有论”——论牟宗三哲学以儒摄佛和援西入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宗三论文,援西入中论文,儒摄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5~0104~16 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 在现当代中国哲学史、儒学史和佛教史上,以“以儒摄佛”或“援佛入儒”以及“儒佛会通”的方式而建立独树一帜的“新佛学”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在经历了以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和梁漱溟等先驱人物为代表的尝试性的探索后,到熊十力终于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成功的典范。熊十力自佛学唯识论内部杀出一条血路,直奔儒学,在批判与扭转自印度传入中土的传统唯识论(即所谓“旧唯识论”)的基础上,使佛学与儒学相接榫,援佛入儒,直探心源,打通“性智”与“本心”之隔,将佛家的“寂”与儒家的“仁”会通为一,即用显体,体用如一,翕辟俱起,本心恒转,归宗《大易》之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终于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儒学和佛学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中,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典范意义的独创性的以佛学的“新唯识论”命名的哲学体系。熊十力以新佛学的形式建立的哲学体系,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无哲学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哲学原创性发展的新时代。 在熊十力哲学的直接开启与示范下,当代新儒家的健将们抛开了“忌佛”与“辟佛”的历史包袱,以开放的心态深入佛学之堂奥,平章华梵,融摄佛智,并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援西入中,把东方的儒、道、佛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尽冶一炉,以“判教”的智慧和方式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在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方东美融摄大乘佛学精神,尤其是华严宗“一真法界”“互遍相资性”的广大和谐与旁通统贯的精神,以及古希腊哲学契理的实智和欧洲近代哲学尚能的巧智,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融通互济,在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新的“判教”系统中,熔宗教、哲学与艺术为一体,建立起一个开阔的文化哲学体系。唐君毅怀抱儒家的“新宗教精神”,融摄佛教“境地论”与“般若论”的理路,汲取华严宗的“摄末归本法轮”智慧,打通由“法性”到“心性”之路,又向西方援引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辩证法精神,本于儒教“无限仁心”而“立三极、开三界与成三祭”,最后在宏大圆融的判教中融合中印西,建立“一心通九境”的庞大哲学体系。牟宗三假借康德哲学为桥梁,融摄佛学般若的妙用智慧与天台宗之圆满判教精神,引鉴《起信论》“一心开二门”之模型,又内收道家的玄智,外摄西方基督教,归宗儒学,构架“两层存有论”(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汇通融合东西哲学,分别与统一真善美,立“圆教”而说“圆善”,使源于西方的“德福一致”学说在东方哲学理论中得到应有的论证展现及更具特色和有力的解释,建立了一个尽精微而致广大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这些都是十分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典范,成为现当代东方哲学,甚至世界哲学中的一道亮丽耀眼的“风景线”,而毫不逊色于日本的京都学派。 从熊十力,旁经方东美,到唐君毅和牟宗三,他们的哲学融合儒佛,会通中西,但最终归宗儒学之大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中国哲学未来开展的重要典范和里程碑。从“以儒摄佛”和“援西入中”的双向进路,对这些“当代新儒家”大师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关乎如何消化和超越从熊十力到牟宗三的哲学,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哲学之未来走向,甚至还对未来的世界哲学,尤其是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东亚哲学之未来面貌不无影响。然而,这一课题在有关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一般皆从儒佛关系的背景中去看“当代新儒家”的哲学,也牵涉到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但若不是一带而过,就是流为泛泛之论,或干脆避重就轻。这种情形在牟宗三哲学的研究中表现最为突出。 一般地说,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东西(或中西)哲学汇通融合的“产儿”。在有关研究中,牟宗三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关系,备受青睐与瞩目,相关论著最为丰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牟宗三哲学思想深受佛学的影响,而且其本人是佛教哲学大家,具有独特而丰厚的佛学思想理论。其颇为自得的佛教哲学名著《佛性与般若》,就东西方哲学与宗教学之比较研究的原创性以及思想的精深、广度和思辨力上看,直可媲美于俄国佛学大家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可惜此书迄今没有英文本或其他外文本,未能受到世人广泛的关注与了解。对于牟宗三哲学与佛学的关系及其佛学思想,研究一直比较薄弱①,甚至没有得到专门研究牟宗三的学者的重视,更遑论把佛学与西学同牟宗三哲学连为一体,即从“以儒摄佛和援西入中”的双向进路,对牟宗三哲学思想进行剖析与论述了。这是造成对牟宗三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偏颇甚至误读,从而使研究难以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诚然,牟宗三著作等身,“清新险峻,高不可攀”②,读懂甚难和把握不易,也是公认的客观事实和原因。笔者不揣简陋,以牟宗三哲学中的“不相应行法”与“执的存有论”为题,做一初步考察。 二、执与执的存有论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套新型形上学。它以儒家的道德实践工夫为进路,引鉴并融通康德批判哲学的“现象”与“物自身”的间架和《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的模型,批判改造佛教关于“执”和“无执”以及“不相应行法”和“二谛”“三性”(《中观论》的“真俗二谛”,及唯识论的“依他起性”“遍计执性”“圆成实性”三性)等佛法趣旨,使“执”与“现象”界、或“现象”界与(心)“生灭门”融会贯通而成立“执的存有论”,借助“智的直觉”(取自康德)与“人有限而可无限”(来自儒、释、道),使“无执”与“物自身”界、或“物自身”界与(心)“真如门”融通如一而成立“无执的存有论”,最后归本乎一心即“自由无限心”,完成“两层存有论”的横向共时态的架构。同时由“自由无限心之自我坎陷”③,或以表征“自由无限心”的“良知”(心)的向下“坎陷”,做辩证的自我否定,达到“知性之辩证的开显”④,即变现出“识心”(认识心的简称)以及“识心之执”。由于“识心之执”的“执”的作用,而有“现象界”的显现与确立,以构造原则实现与完成“执的存有论”或“现象界的存有论”,这是“道德的形上学”的“无而能有”(刹那生灭中的“有”或生灭门中的“有”)。反之,则以“逆觉体证”之路向上,开显“智的直觉”,返回与亲证“自由无限心”,臻于圆融之境,在轨约原则的运用中实现与完成“无执的存有论”或物自身界的存有论,亦名本体界的形上学,这是“道德的形上学”的“有而能无”(寂静的真如之“无”或真如门中的“无”)。“自由无限心”或“良知”可上可下(上即为“无限心”或“良知”心以及“智的直觉”,下即为“识心”以及“识心之执”),实现一心双互回向之“两来往”(从“无限心”及其“智的直觉”到“识心”以及“识心之执”,复从“识心”以及“识心之执”到“无限心”及其“智的直觉”)的统一,完成“两层存有论”的纵向历时态的架构。最终“两层存有论”的纵向历时态架构与横向共时态架构的统一,就是立体分层、动静结合、圆融不二的“两层存有论”的“道德的形上学”。非常明显,在“道德的形上学”中,“心”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即“物自身”界与“现象”界开显为“无限心”与“识心”⑤。归根到底,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就像唐君毅的“心通九境”的形上学一样,乃是心的形上学。以牟宗三的话来说,它们都是分别代表中国哲学的“彻底的唯心论”型态的形上学⑥。 但就“执的存有论”这一现象架构层而论,乃是牟宗三批判与改造佛教的“执”的观念,把它从消极的意义转化为积极的意义,引入其“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而得的结果。牟宗三说: 我们这一部工作是以佛家“执”之观念来融摄康德所说的现象界,并以康德的《纯理批判》之分解部来充实这个“执”,因为佛家言识心之执是泛心理主义的,重在说烦恼,认知主体不凸显故。⑦ 显然,牟宗三很看重佛家的“执”的观念,但认为佛家所讲的“执”是泛心理主义的执心或执念,着重于“执”的结果即“烦恼”或“苦恼”,因此完全是负面意义的观念。这是佛教主张破“执”或去“执”的原因所在。佛教以为,人生中的烦恼基本上都是由“执”而生起的结果。原因在于天下有情处于无明状态,不能洞晓宇宙万物的本性是缘起的现象,皆空无自性,而误以为事物都是有自性的实在,因而夸父追日,穷追不舍,而又欲求不得,于是烦恼频生,不得片刻安宁。即使是以为得到了,也只不过是个影子,而非实在的自性本身,结果还是坠落无底的烦恼深渊。在佛教看来,无论是对于事物的实体的执著,抑或对于观念自身的执著,也就是所谓的“法执”或“我执”,都是虚妄不实的,必须破除。 然而,牟宗三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牟宗三认为,在佛教的“执”的观念中,虽然没有显现出“认知主体”,因而为消极意义的,但是透过康德哲学和中国儒家哲学,看到其中包含着积极的认识论意义,就可以透显出“认知主体”的概念。所以,“执”的观念经过牟宗三之手,就从完全消极的意义变成了完全积极的意义。牟宗三从“识心之执”凸显出佛教的“执”所具有的“知性”意义,并由此建立“现象界的存有论”。这步工作是由会通康德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与佛教的“执”的观念以及“不相应行法”“二谛”和“三性”来完成的。诚如牟宗三所说,“现象界的存有论”一方面是以佛家“执”的观念来融摄康德哲学的“现象界”,另一方面则是以康德哲学(“第一批判”)的“知性、想象以及感性所发的感触直觉”来充实“执”,使“执”成为“识心之执”,凸显出“认知主体”,“执”就获得了一种由认识论而成就“现象界的存有论”的意义与可能性。在这一条件和前提下,“现象”这一概念得到了确定无疑的规定,就是说,现象乃是由“知性之执”或“识心之执”而“执”出来的,亦即是就“物之在其自己”而“绉起”或“挑起”的。对此,牟宗三有一个具体而形象的解释⑧:“物之在其自己”本来是平静如水的,但是“春风”的“吹绉”,即“识心之执”的“执”发生作用,就吹起了“波浪”即现象。与康德的认识论所不同的是,牟宗三所讲的“现象”不是一个从感性到知性的过程,而是恰恰相反,即从知性到感性的过程。原因在于“绉起”或“挑起”现象的“识心之执”是由自由无限心的自我坎陷而成立的。当然,这是就其“道德的形上学”来说的。事实上,现象乃是感性与知性相互共同作用的结果。至于是从感性到知性,抑或是从知性到感性,皆无不可,因为这一过程本来就是双向交互的。只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各有所取罢了。从牟宗三来说,“识心之执”的本性就是对现象的执著。因此,当“识心之执”得以生成后,一执就执到底,“绉起”或“挑起”现象,便表现为从知性到感性的过程。“知性之执”或“识心之执”之“执”的全幅展露,便是现象的形成。在这个基础上,“现象界的存有论”或“执的存有论”得以成立。由此,“现象”的概念得以界定而确立。 三、不相应行法与执的存有论 “执的存有论”或“现象界的存有论”依据“执”而建立,而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不相应行法”。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学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会通康德知识论的范畴与佛教的“不相应行法”,不仅逼显出佛学中深刻的知识论思想,而且经过与儒学的融合,构建了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见的“执的存有论”。这是牟宗三哲学中的一大精彩亮点和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那么,什么是“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与康德哲学是如何会通的呢? (一)不相应行法或心不相应行法 所谓“不相应行法”,也称为“心不相应行法”(梵文Cittavipayuktasamskāe/Citta-viprayukta-dharma),简称为“不相应法”,意为与心不相应的法(现象),也就是不会随着心的生起而生起的法(现象)。它指既不属于色也不属于心,但又可名为色或心的生灭变化现象(法或法相、法象)。牟宗三指出: “不相应”可有二义:一、与色心法不相应,不是色心等法之材质的谓词,故不能说它们是色法或是心法。二、它们并无实体性,即并无一客观的实有可为其相关者,它们并无所相应的实有。⑨ 可见,所谓“不相应”,是指没有客观的实物与心相应,它仅仅显现为思想或意识中的分位假法。也就是说,它是纯粹主观的东西,没有现存的实物或实在可以与它相应;它作为一种“行法”来说,是与心不相应的“行法”。说它“不相应”、是“分位假法”,乃是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说它是“行法”,则是就其类别或归类上而言。诸如方时、离合、一异、长短乃至数目等,都属于心不相应行法。因为这种行法与心、色皆不相应,所以既不能说是心,也不能说是色,但是它们依止于色与心等法的分位而以假名的形式出现。它们虽然是以假名的形式出现的“行法”,但是这种“行法”又不能等同于(五蕴中的)行蕴,因为它们本身是无行动的,也无迁流与现起等义,它们与行蕴只能有间接的关系。再说,它们也不是无为法。说一切有部和法相唯识论把它们列为“五位法”之一。《法蕴足论》列其为十六种,《俱舍论》列其为十四种,法相宗唯识论的论典列其为二十四种(详见后文所列)。牟宗三对于“不相应行法”的了解不是一般泛泛的了解,而是借助龙树《大智度论》破时间实在论(或时间实有论)的观点,以及熊十力对于“诸行”的解释中所列出的色心分位而假立的“不相应行法”,来论述和把握的。 首先,牟宗三认为龙树破时间实有论,得出“见阴界入生灭,假名为时,无别时。所谓方时、离合、一异、长短等,名字出。凡人心着,谓是实有法”的结论,是可以承认的⑩。因为阴界入(五阴六入十八界)是具体的有生灭流转的缘起法,我们不过是就着它们的生灭流转这一特性而把它们作为“假名”来对待,并命名它们为“时”(时间),牟宗三称之为“虚假无实地姑名为时”、“克就生灭流转分位或分际而姑名为时”(11)。实际上,它们被命名为“时间”,只是一个虚假的名字,犹如数目字之为一个虚假的名字一样,并无真实性可言。牟宗三说:“时间并非是一客观的实有,除这假名的时外,并无别样的客观实有的时间。”(12)在牟宗三看来,这一假名的时间,在实质上只是刹那生灭流转的现象的“分位假法”,并无实义;它作为一种“行法”来说,不过是思行上的一个分位假法而已,在客观上并没有任何实物与时间的观念相应,它是纯主观的,佛家笼统地把它概括在“行”法之中,所以时间之为“不相应行法”,乃是确定无疑的。固然,“不相应行法”并不限于时间。除了时间以外,离合、一异、长短、数目等皆是“不相应的行法”,也就是分位假法。牟宗三指出:“这个‘行’是五蕴(五阴)中‘行蕴’那个‘行’,也就是‘诸行无常’的行。”(13)牟宗三从五蕴的“行蕴”来理解,那么它就是“诸行无常”的行了。这一理解的根据来自熊十力对于“诸行”的解释(14)。牟宗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行”的意义进行了引申和发挥,并把“行”置于四种意义上来理解:(1)行即行动义;(2)由行动义引申出迁流义,进而引申出流转、流布等义;(3)再由行动引申出现起、现行等义;(4)“修行”也是行。在这四种意义上说,一切色法无非“行”而已。牟宗三认为,这是对于“行”这一名相的最广义的理解与解释(15)。 与此同时,牟宗三指出,这一最广泛意义中的色法之为色蕴,并不表示说色法就不是行。就受、想、识三蕴来看,也并不表示说受蕴、想蕴、识蕴就不是行的意思。受、想、识三蕴作为“心法”来说,就是“心行”。然而,心法中并非仅有受、想、识三蕴而已,尚有其他种种心法。这一切的心法都以最广义的“行”来概括。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受、想、识三蕴不同于色蕴,在五蕴中是具有相对的别为一种独立意义的,从它们与“行”的关系来说,“行”的最广泛之义在五蕴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就是说,“行”既不同于色蕴,同时又与受、想、识三蕴有很大的区别。“行”的地位介乎色蕴与受、想、识三蕴之间,也就是夹在色蕴与具有独立性的三蕴受、想、识之间。它一方面受到来自于色蕴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受、想、识三蕴的限制。因为这一缘故,“行”不得不独立出来,独自成为一个“行蕴”。那么,相对于“行蕴”而存在的受、想、识三蕴也独立地成为一蕴(分别相对于三蕴来说是一个更大的独立的蕴)。于是,五蕴最终是被归为两个层面上的两蕴。如上所言,牟宗三是根据佛教“三法印”之一的“诸行无常”义,对“行”字的意涵给予厘定的,其基本要义就在于这么两点:第一,行蕴不包括色法;第二,行蕴专属于心法,但并不包括“受、想、识”。“行蕴”的这两层限制使它从五蕴中脱离出来,并获得了独立的意义,所以它一方面与色法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作为独立的一蕴的“受、想、识”区分开来,而独自为一蕴。把五蕴分为两层,类似于康德的感性和知性之分(16)。饶有趣味的是,这一独立的行蕴偏属于心法。而作为“心法”的行蕴或行具有极大的外延和概括力,它不仅轻而易举地概括了法相唯识论的五十一心所法,而且把上述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也收入囊中;在牟宗三看来,这里面似乎是有问题的,值得重新思考(详见后文)。 所谓“心所法”,简称为“心所”或“心数”,是依止于心而与心相应的心之所有的法,或说是属于心的心上所有的法(17)。一方面,五十一心所法是与心相应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与色、心诸法之间又是不相应行的。正如上文所说,它们本来就与心或“心法”不相应,不会随着心或“心法”的生起而生起或变化。因为不相应行的缘故,就不能把一切心所法,例如五十一心所法,完全归为心或色。既不能说它们是心,也不能说它们是色,但是它们是依止于色心等法的分位上而假立为种种名相的。这种假立的名相,乃是间接地通过“思”或“思蕴”摄于行蕴之中而属于行蕴的。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以假名而立的种种心所法或不相应行法本身并无行动、迁流、现起等意义。然而,也不能就因此而把这些假名视为完全消极的。所以,牟宗三强调它们也不可以称为无为法。 至此,牟宗三厘清了不相应行法与“行”或“行蕴”的关系,即以分位假法而立的“不相应行法”,究极而言,是间接地通过法相唯识论的以“思”说“行蕴”的方式摄于行蕴之中而属于行蕴的(详见后文)。 (二)删减与调整二十四法为十七法 如上所言,法相唯识论把“不相应行法”列为二十四个,传统讲“不相应行法”以此为准。熊十力在其《佛家名相通释》中解释“不相应行法”,也以这二十四个分位假法(简称二十四法)为准。它们是:得、无想定、灭尽定、无想天、命根、众同分、生、老、住、无常、名身、句身、文身、异生性、流转、定异、相应、势速、次第、时、方、数、和合性、不和合性。牟宗三则对“不相应行法”进行了创造性的批判考察。在把这“二十四法”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尤其是康德的范畴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牟宗三做了重新排序和分类。他基于开创和建立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的立场,以纯数学、逻辑和经验知识的形式科学及其形式法则的特征为标准,并从佛学的“不相应行法”内部提炼出“非色非心而隶属于思之形式法”的准则(后文详论)(18),以建立他所追求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执的存有论”为目标,删繁就简,去粗取精,新增一法(因果),新订“不相应行法”为十七法(可名为修订版“不相应行法”),把在佛教中为泛心理学主义的消极的不相应行法转化为在哲学中具有建设性积极意义的知识论之可能的形式条件,不仅为其建立“执的存有论”做了必要的准备,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天地。 牟宗三首先从名身、句身、文身的解说开始对“二十四法”进行解剖。名身与句身表示的是语言,文身表示的是文字,合在一起指的是佛教的语言文字这个层面的内容。但是,牟宗三认为,必须从语言学和佛教的思想义理两个方面及其关系中来把握和解说(19)。就是说,色、心诸法是存在的事物,属于存在的实层;语言文字则是浮在存在层的上面而自成一套语言学的工具,属于虚层。虽然可以说名、句、文三身是凭借着色法与心法的分位假法而成立的名相或假名,但是这“分位”二字也是浮泛的,严格地说,是不那么确切与谛当的。如果从诸法自体说名身,就自体的差别意义说句身,那么亦然如此。此外,文身即文字,是表示名身与句身的自性,是就着名身与句身而成立的,不是就着色心诸法而成立的。在语言文字的层面上,名、句、文三身更是远于色、心诸法,独立地自成一套语言学的工具。因此,不可以说名、句、文三身是依靠色心诸法的分位而假立的名相。根据《广五蕴论》,不相应分位假法的定义,是“依色心等分位假立,谓此与彼不可施设异不异性”。然而,在事实上,名、句、文三身可以与彼色心等法施设异性,由此可见“语言文字确与其他分位假法有独特的特殊异处”(20)。换言之,名、句、文三身与色心诸法的分位假法之间具有十分独特的相异之处。如果就语言为一种独立的共同工具而言,则不可说名、句、文三身是就着色心的分位而假立的名相。牟宗三强调:这里的所谓“分位”,意义颇为浮泛,与其他分位假法不同,因此,必须承认名、句、文三身有它们的自体性。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从它们所抒发的意义中,把名、句、文三身提出来当作独立的一套东西来对待,同时可以将它们所抒发的意义从名、句、文三身的语言文字中独立地提出来,而说此种种意义之间的差别是就着色心诸法的分位而假立的结果(21)。这就是名、句、文三身与色心诸法的分位假法之间的独特相异之处的意义所在了。 在此,牟宗三充分意识到:语言对存在(或实在)来说,既是存在之家,又是存在显现的极限。对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如果处理得不好,则两相有害或两相有碍。依据佛家“五蕴皆空”之义,一切语言文字的说法都不过是假名说而已。但说到“不可思议”之处的时候,就“心行路绝,言语道断”了,这似乎不仅是“存在”的极限,同时也是语言自身的极限。然而,佛教讲究四悉檀因缘(世界悉檀、各各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和第一义悉檀)普施众生,或依三论宗之说,佛教以四种灵活多样的“权说”方式即“四悉檀”(因缘假、随缘假、对缘假和就缘假)为众生说法。此外,《成唯识论》从说法的虚假性来理解与看待四悉檀,认为有因生假、缘成假、相待假和相续假四种虚假性。既然佛教要为众生说法,那么对于不可说者(不可说的法与不可说的众生),就需要方便地权说。故方便权说不可废,“四悉檀”亦不可废,“终日说,终日不说,时时用语言,时时超越语言”也就成为方便智慧(22)。依中观说的“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则可以“不坏语言而说诸法实相”。语言与诸法实相两不相碍。因此,名、句、文三身作为依色心的分位而假立的名相可以“不随语言生着,则亦不受其拘限”(23)。如果说“实相”之相即是“无相之相”,那么一切语言以及一切假名法皆当体即寂。所谓“空空”“涅槃”,亦如幻如化,般若亦不可得了。如此说来,岂不是一切都成了假名说了吗?但是,这只不过是“通贯地究竟说”而已(24)。在这一意义上说,不仅时间与数目是假名说,而且假名自身也是不能“着实”(即着于实有)的。不相应行法的所谓“不相应”的意义就由此得到了表彰。这里的妙趣就妙在虽然不相应,但是可以方便地权说。所以,一切方便权说皆是有原则的分位假立(25)。由此,不但二十四不相应行法是分位假立,而且名身所证的诸法自体性乃是依法之轨持义而论证与解释的,那么这里的“自体性”难道不是不相应而为了方便所假立的吗!法的自体性既然是方便权说而假立的,那么句身所诠表的自体上的种种差别之义,如“无常”“苦”“空”“无”等名相,乃至名、句、文各层次上的种种说法与解释,就没有不是方便权说而假立的了。例如科学上所造的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的名词和假说,以及学术上不可胜数的名类繁多的学术用语和理论说法,无一不是方便权说(或权设)而假立的东西。问题在于,如此一来,一切名身就都成为不相应行法了!在牟宗三看来,这一“通贯地究竟说”的权说虽然方便而不失妙趣,但弊病是说不相应行法“太宽泛”了。问题的根源出在语言上。因此,必须冲破语言的极限与限制。 其次,牟宗三对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分别进行了分析与解说。牟宗三指出,在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中,第十五“流转”、第十六“定异”、第十七“相应”、第十八“势速”和第十九“次第”五个“分位假法”的含义最为广泛。牟宗三发现,这五个分位假法与“因果”关系密切,并且皆是就着“因果”而立说的。如果把“因果”视为更根本的客观法则,那么“流转”“定异”“相应”“势速”“次第”这五个分位假法,就似乎可以说皆是由“因果”而引申出来的,同时亦可以说,它们皆可反而用以指谓与表述这一因果关系的形式特性。无疑,这些概念也是句身所诠表的差别义的分位假法。但是,“此等差别义却不能说是色法之谓词(特性),亦不能说是心法之谓词(特性)”(26)。它们与色法、心法不相应。就是说,它们既不是心所有法(心所),也不是色所有法(色所)。事实上,“它们是遍谓一切色心法的共同而虚的形式特性,不是材质的特性。这是独成一虚层的形式概念(虚概念)”(27)。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这五个名相是就色心上的分位而立的假名,那么这“分位”二字也就未免“太广泛”了,就像说一切皆是假名说,即都是分位假立的一样,是于事无补的。从“不相应”之义而言,如果一切名相都是假名说,则一切皆不相应。那么,即使是说“不相应”,也不能表示出这五个(加上“因果”是六个)“不相应行法”的特性。实际上,它们的本质特性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概念,即不能把它们当作是色法或心法的“材质的谓词”看的处于虚层的形式概念。 此外,在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中的第五“命根”、第六“众同分”、第七“生”、第八“老”、第九“住”和第十“无常”六个分位假法,与上述六个分位假法亦为同类,皆是最宽泛的形式概念。因为“命根”是“住时分限”,“众同分”是类名,也可以是“同性”,而与“异性”为相对,都不外乎为形式概念而已。至于“生、老、住、无常”也不过是“成、住、坏、空”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在牟宗三看来,它们是描述色、心等法之为“行”的共同形式特性,同时也是描述有情众生“从有到无”的共同形式特性;而并不是色法、心法等法之材质的谓词,也不是有情众生每一个体之材质的谓词。因此,它们之作为描述色心等法之为“行”的共同形式特性,以及有情众生之“从有到无”的共同形式特性,必须与作为色心等法之材质的谓词,以及有情众生个体之材质的谓词,严格地区别开来。顺便指出,牟宗三同时认为,第二十三“和合”与第二十四“不和合”这两个分位假法,是离、合两种形式概念,并且它们亦不是色心等法之材质的谓词(28)。 回到“生、老、住、无常”四个分位假法的表象上,具体地说,“本无今有”是生,“渐趋衰败”是老,“相续随转”是住,“相续谢灭”(归于虚无)是无常。这里所表象的“生、老、住、无常”的过程就是从存在到不存在、从实有到虚无之级别的过程。牟宗三把佛学中的这些分位假法与康德哲学中的范畴加以比照和会通,指出处在过程中的“生、老、住、无常”的种种表象,对于康德来说,则是由“实在”“虚无”“限制”等范畴所决定的。在这一意义上,“生、老、住、无常”四个分位假法所表示的“不相应行法”其实都是形式概念。进一步看,还可以比照康德以及罗素的哲学,就“命根”(住时分限)与“住”(相续随转的持续性)而说“常体”或“准常体”,那么这一“常体”概念就是康德所说的“常体”范畴,而这一“准常体”概念也就是罗素所说的“准常体”的设准了(29)。在把上述十四个“不相应行法”与康德哲学所代表的西方哲学的范畴进行比较研究中,牟宗三指出: 以上十三个(加上因果,是十四个)形式概念大体是属于西方哲学中所谓范畴之类的东西,不过西方哲学中尚无以“离”、“合”为范畴者。但是须知康德所系统地建立的范畴表亦只是纲领而已,尚可以引申出许多个。多点少点,存此去彼,皆无关系。然大体皆必须是形式概念,是思想上的纯粹概念,康德亦名曰“先验概念”。形式概念而谓述存在的特性,是其最普遍而共同的形式特性。此虽亦是句身所诠表之“义”,但却有一特点,即形式概念是形式概念者虚意的义也。(30) 不难看出,牟宗三始终抓住与强调佛学中的名身与句身所诠表之“义”的最大特点。以上述十三个经由牟宗三所厘定的“不相应行法”为例而言,就在于它们是类似于康德哲学中作为“先验概念”的“思想上的纯粹概念”,它们是“谓述存在的特性”的“最普遍而共同的形式特性”的概念,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描述色心等法之为“行”与有情众生之“从有到无”的共同形式特性的概念,亦即牟宗三所谓的“虚层”的“虚意的义”的形式概念。这无论对东方哲学或西方哲学来说,都足以称为一个重要的发现。 对于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中第二十“时”、第二十一“方”和第二十二“数”三个分位假法,牟宗三认为它们更具有形式性与普遍性,也就更为空洞。“它们甚至不是论谓存在物的普遍而形式的特性,即是说,它们不是义,即使是虚意的义也不是。”(31)原因在于它们不是法之自体上的差别。 如果就“数”来说,那么“数”只是标识“个”或“单位”而已,“数”既不能抒发这一“个”或“单位”的自体性,也不能抒发其差别之义。“数”“于诸行一一差别,假立为数”(32),只注意这“一一差别”中的一个的差别,而不是注意“个”之差别以外的其他差别。它的分位只是“个”而已。它不论谓色心等法的差别之义,即使是普遍的形式之义即“虚意的义”,它也无所论谓。所以,“数”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它只是就“个”而假立,反过来看,它实在只标识“个”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牟宗三把“数”与康德哲学中的范畴进行比较研究,并指出: 数是纯思想上的建立。它可于一、多、综中表示,但一多综并不是“数”。依康德,一多综是范畴。数学中也需要这些范畴,通过这些范畴而思考数,在这些范畴下而直觉地建立数。依是,数比范畴更为凸出。范畴是一般的形式概念,而数则是独个的,此其所以为直觉的综和,因而为直觉的建立(构造)也。(33) 由此可以看出两点:其一,佛学中的不相应行法的“数”与康德哲学的范畴“一、多、综”不同。“数”可在“一、多、综”范畴中表示,但“一、多、综”范畴并不是“数”。“数”比范畴“一、多、综”更为凸出。其二,范畴“一、多、综”是一般的形式概念,“数”是独立的“个”体。“数”虽然是在“一、多、综”这些范畴的前提下建立的,但是“数”是直觉的综合,只能以直觉构造的方式建立。 关于“时”(时间),前文中已有论及,但仅限于龙树批判时间实在论的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需要有进一步的论究。无疑,“时”(时间)在佛学与康德哲学中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牟宗三论“时”,也是把它与康德哲学中的“时”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与说明的。牟宗三首先指出佛家的时(时间)是“谓于因果相续流转,假立为时”而言,反过来说,其实是时(间)表象“相续流转”。事实上,“相续流转”乃是因为时(间)之表象而可能的。颇为奇妙的是,佛家与康德论“时”(时间),均与至关重要的“因果”观念相联系(尽管二者对于“因果”的理解不尽一致)。根据康德的观点,因果是形式概念,而时间则是感性的直觉摄取外物的形式条件。相比于康德的时间来说,佛家的时间只是一种“假立”,它本身不是色心等法之义,甚至不是色心等法之“虚意的义”,而是表象色心等法的形式条件。必须看到,这一时间本身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纯粹的直觉。因为它的原初表象就是一个整一,并不是由部分所构造出来的。它之为整一必然先于它的部分,而不是相反。说时间是“假立”的,以康德的术语说,就是说它是超越的想像所先验地假立的。时间之为假立,就是指它是感性的直觉摄取外物(即表象外物)的形式条件。时间作为一个整一而直觉的表象外物,这实际上就是限定外物。限定外物,就是把外物排列在时间的秩序之中。在这一意义上,牟宗三指出:“时间是整一,因其表象外物而被界划,界划成时间单位,所谓时间之部分。”(34)我们观察色心等法自从开始出现的变化,瞻前顾后,说它们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相对于这些法(法象)的“已生”或“已灭”而说过去时,这就是以时间表象法的“已生”或“已灭”;相对于这些法的“已生未灭”而确立“现在时”,这是以时间表象当前之法,而说它是“现在”;相对于这些法的“未生”而建立“未来时”,这是以时间预先表示其未来可以出现。在牟宗三看来,这些法上的事情是因时间的表象而可能的。只有法相续流转,而时间无所谓流转,也无所谓“相续流转”或变化。时间是一个虚的形式的有,即一个虚架子。它在根本上是识心的执著,是识心的凝结作用而幻化成为一个虚的形式的有。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变化的意识,才能把法的相续流转划分出“过去”“现在”和“未来”,诸法才能在时间中被表象而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现象(事情),因而才能明确地成为识心的一个现实的认识对象。如果没有时间意识,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35)。由此,可知时间对于知识论的重要。 空间与时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比照牟宗三对时间的论述,即可知道他对于空间的看法。所以,他说:“时间如此,空间亦如此,不须别论。”(36) 在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中,第二“无想定”,第三“灭尽定”,第四“无想天”。牟宗三对这三个假名进行了批判的简别,认为佛教将它们列入“不相应行法”中,显得不伦不类。这样做,一方面不足以显示单独提出二十四个假名为不相应行法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如果按“无想定”“灭尽定”“无想天”这三个假名推想下去,就必将导致不相应行法的无穷无尽,“二十四”这个数是根本定不住的。因为如此泛滥,将无严格的原则足以限制它们的扩张。那么,大乘修行上的各种位次也都可以说是不相应的分位假法了。牟宗三指出:“无想定”“灭尽定”“无想天”当然是假名,它们是就修行工夫而说的心的状态并作为描述用的抒义语(37)。这三个假名之作为描述修行工夫的抒义语,与“成佛”相关,但与“知识之如何可能”的问题无关。一是“成佛”的终极(信仰)指向,一是成就知识的“事功”(科学)指向,二者的界限不容混淆。它们虽然是假名,但是一与名身、句身、文身之为语言文字不同,二与“时、方、数”之为独立一层的“形式的有”不同,三与“流转、定异、相应、势速、次第”以及“命根、众同分、生、老、住、无常”乃至“和合、不和合”等可以概括在“形式概念”下的假名不同。所以,“无想定”“灭尽定”“无想天”不能名为“不相应行法”,必须从既定的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中剔除掉。这就是牟宗三呼吁“必须步步撤退”的结果(38)。此外,牟宗三认为“二十四法”中的第一“得”(获、成就)和第十四“异生性”是随意列入的,也必须剔除。 经过繁琐而细致的分析和论述后,牟宗三对佛家“不相应行法”的“二十四法”开膛破肚,分别剔除了八个假名:名身、句身、文身(此为一组),无想定、灭尽定、无想天(此为一组),以及得与异生性(此又是一组);保留下十六个假名:流转、定异、相应、势速、次第、和合、不和合、命根、众同分、生、老、住、无常,以及时、方、数;加上了“因果”,共计十七个。在牟宗三看来,这十七个假名保留下来,就可以保持不相应行法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这是以“时、方、数”以及“因果”为标准而定住其他各个假名的不显明性所收到的效果。其具体做法是以因果、命根、众同分别来定住生、老、住、无常,于是生、老、住、无常(取相续谢灭义)就可以概括在从实在到虚无(“空”等于“零”)的“级度”(类似于“级别”“层级”)中(39),也就可以概括在持续体(准常体)以及实在、虚无与限制这些形式概念之下,从而可以视为是这些形式概念之较为具体的表示。如此一来,就可以把它们视为形式概念。因此,当把它们列入“不相应行法”之中,便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与作用,这绝不是像普通的描述抒义语那样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依此类推,则流转、势速、次第这三个假名也可以“因果”与“准常体”来定住,而视之为形式概念。诚如上文所述,它们都不是色心等法之材质的谓词。至于“不相应行法”中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引申的,以及多或少,或存此去彼,就都没有什么关系了。牟宗三指出: 如是,我们便可说,时、方、数,为识心上所假立独成一层而有其虚层的自体义的形式的有,而其余十三个则可视为识心上所假立的形式概念而可以形式地论谓存在法之普遍的形式特性者。这样说,便可以保持不相应行法之独特性,其作用即在其为识心底认知之形式条件,即为知识以及知识之对象之认知的可能之条件。我们将随康德,说时空为感性直觉摄取外物之形式条件,说其余形式概念为知性统思直觉所摄取之现象。这统思上的纯粹概念即范畴,亦就是“形式地辨物”之概念。数学与逻辑亦是识心上所建立之独成一层的形式学问而为辨物时所必须遵守者。(40) 毋庸置疑,牟宗三这一做法的良苦用心,乃在“不相应行法”与知识论的关系。牟宗三以为由这十七个假名重新构成的新“不相应行法”足以成为识心的认知活动的形式条件,因此就可以成为知识以及知识对象的可能之条件。在这一前提下,东方或中国的哲学就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知识论系统,走出一条既有取于西方知识论而更有别于西方知识论的道路。这就是牟宗三参照以康德的认识论为代表的西方知识论的道路,尤其是以康德知识学的范畴论为津梁,把它与佛学中的“不相应行法”相会通,并将一如其《认识心之批判》一样,把数学(纯数学)、逻辑和科学这些基于识心而建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形式科学也容纳进来。这是牟宗三在自己的哲学中,立足于比较会通东西方哲学的高度,对佛学的“不相应行法”进行的一次改良“手术”,使在佛教中为“出世法”的“不相应行法”在器世界的“世间法”中获得了新的积极的现实的重大意义。 需要补充和指出的是,牟宗三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不相应行法”与康德哲学的范畴论的比较研究,而是扩展到“三性”“二谛”与知识论的研究,但又统一到“不相应行法”上。关于这一问题,牟宗三在其《中国哲学的未来拓展》一文和《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等著作中均有论述,但以《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一书所论最为丰富。他把《中观论》的“八不缘起”、华严宗的“缘起六义”与法相唯识论的“三性”相联系和贯通对比康德知识论来进行分析,又把“三性”归结为“真俗二谛”,认为不管是正面说的“六相”(总、别、同、异、成、坏)或反面说的“八不”(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常、不断)这些名相并无自性,当然就不能从“真谛”上去讲。因为就“真谛”讲,它们都是“相无自性性”,必然在般若智的观照之下被化掉,也就是说,只有对“物自身”或“无执的存有论”的“无相之相”的实相才能说“真谛”(这一问题后文中论述);但在科学知识上讲,它们就是康德所说的知识之为可能的形式条件,正相当于佛教所说的“不相应行法”。佛教所列的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杂乱无章,所以犹如上文所论,牟宗三要对它们进行“整理”,剔除其中那些不相干的名目,如此一来,就通通都在康德所说的时、空及十二范畴的范围之内,因此具有了可以独立的知识论的意义。 综上所言,牟宗三之所以破除成规,推出十七法,其目的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在于净化“不相应行法”,使“不相应行法”成为知识之可能的形式条件。换言之,牟宗三所做的工作,意在会通佛学的“不相应行法”与康德知识学的范畴论,以建立“执的存有论”。 (三)以思说行蕴 牟宗三重新整合与构建了佛学中的“不相应行法”,但是对他来说,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有所解释与阐明,这就是在佛学中佛家为什么要以“思”说行蕴。只有在回答了这一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彻底地澄清他所提出的新“不相应行法”“何以为可能”的问题。牟宗三援借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番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的考察。 上文指出,牟宗三根据佛教“三法印”之一的“诸行无常”义,对“行”字的意涵进行澄清并给予了厘定,但是行蕴作为与范畴相关联、相类同的意义并不明确。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就必须澄清两个问题:其一,行蕴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其二,行蕴包括些什么(内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规定与互相蕴含关联的。对于第一个问题,牟宗三依据法相唯识论以“思”说“行蕴”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论述,从而做出了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牟宗三从“思蕴”与“不相应行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借助于五十一心所进行论析而回答。 根据法相唯识系的论典以“思”而说“行蕴”的观点来看,牟宗三认为“行”是“思”的别名。“思”与“受、想”相同,皆是心所法之一。他引用《成唯识论》所谓“思、谓令心造作为性,于善品等役心为业”的说法来解释“思”,从而把“思”的自性(或曰本性)看成是“造作”,“思”的业用是在善恶等境中驱役心及余心所,并同时生起善恶等现象的表现。这表示“思”的造作之自性就有役使心的业用。在这一意义上说,“思”的业用即为“思业”,而思业即是“身、语、意”三业中的意业。在牟宗三看来,“意”是意识所发的意念,“思”的造作就含在“意”中。“思”在具体层面上具有心理学的意义,亦名为“行”或“业”,是心所法之一。这是佛教中有“见惑”与“思惑”之分的原因所在。思惑,亦曰修惑,是相对于见惑而言的。思惑即烦恼。“思”本身是一个心所,但由于它的造作之本性役使心及余心所,而同时引生善与恶等现象的出现,于是就使心及余心所共同为造作。“色”和“受、想、识”既然从五蕴中分出去,各自分别而独立地自成一蕴,即“色”为一蕴,“受、想、识”为一蕴,那么就可以受到两层限制的“行”或“行蕴”来命名这一个思蕴,而“思蕴”的本性则可以从“思”的造作之义得到解释与说明(41)。由此可知,行蕴即思蕴。这是行蕴的主要特征之所在。二者的区别在于:行蕴是广义的受限,即受到色蕴和“受、想、识”合为一蕴以及五蕴中的“行蕴”的限制;思蕴是直指其内容(42),即造作业用,役使心和余心所,也就是思考活动想出一个理由迫使生命不由自主地拖下去。虽然说“行蕴即思蕴”是行蕴的主要特征,但在这一命题的具体含义(内容)没有完全揭示出来以前,行蕴的特征仍然是模糊而不确定的。 至于“行蕴”的具体内容,牟宗三认为仍然需要从“思蕴”去理解与把握。“思”之作为独立的一蕴,并不限于它本身是一个心所法,它还包括了由其造作所引生的一切其他的心所法(除了“受”与“想”之外),以及属于思但又不是心所的“不相应行法”。思蕴所包括的心所,共计五十一心所,分为六类,亦称六位(43)。牟宗三对于“思蕴”所包括的五十一心所并没有像对待二十四“不相应行法”那样加以任何的改变与深研细究,而主要是紧扣那属于思但又不是心所的“不相应行法”来进行论述,以揭示其作为独立的“形式的是”(它构成“是”之为是的形式条件)的意义(44)。在牟宗三看来,思以及由思的造作役使心所引生的五十一法都是心所法。思的造作役使心,也就同时是役使这五十一个心所。在这一役使的过程中,思和五十一心所与心都是相应的,但它们为心所有,所以称为“心所”。心、思、五十一心所三者之间,叶合为一,一体而转。这当然是具体心象的表现,也就是心理学意义乃至泛心理学意义的。但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牟宗三关注与强调的是“思蕴”另外的非心理学的意义。他指出:思的造作除了役使心以外,也可以形构出一些具有独立意义而其自身却是非心非色的东西,这就是独自成为一个“虚层之形式的是”或“形式的有”(45),就像“时、方、数”以及其他的形式概念一样。这些虚层的“形式的有”是由思的造作而假立的有(实为假有),非色非心,亦非具体的心态,亦无“行”义,它们能保持恒常的形式而不变化。由于是思的造作之物,它们凸出而自有,隶属于思,而其本身并无所谓思,所以得以名为“不相应行法”。严格地说,它应该称为“非色非心而隶属于思之形式法”(46),牟宗三认为这一称谓有助于保持“不相应行法”这个词的独特性。对应于“非色非心而隶属于思之形式法”来说,“思”作为一个心所法即“思蕴”所受到的特殊限定就立即表现出来了。显然,在套用康德批判哲学的进路中,逻辑学、知识论与心理学之间的界线是非常确定地被划分开来的,这也正是牟宗三在《认识心之批判》一书中所展示的进路。对牟宗三来说,“行蕴”的具体意义或内容,只有在这“思”或“思蕴”的“虚层之形式的是”或“形式的有”之下,才能被揭晓。因此,“行蕴即思蕴”可以获得具体的确切的理解。具体地说,“思”对应“数”而言,是纯逻辑的理智思想,或纯直觉的活动;对应“时、方”来说,是纯粹的想像或超越的想像,也可能是纯粹的直觉;对应其他形式的概念说,是纯粹的辨解思想或纯粹的辨解知性。这些形式法所蕴含的知识论意义晦暗不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佛教是泛心理主义,重在说烦恼,追求解脱,而不注重论知识(47)。所以,当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到现代以来,自觉到需要开出一套独立的现代知识论型态的时候,就必须把佛学中的“不相应行法”的“形式法之意义”发掘出来(48)。 牟宗三不否认这步工作是参照康德哲学来完成的,但是他没有停留在把佛教的“不相应行法”与康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其范畴论的简单的比较之中,而是立足于现代世界哲学的制高点上,对佛教的“不相应行法”动了一次大手术,并批判佛教的泛心理主义,把笼罩在佛教泛心理主义中的识心的知识之义拯救与解放出来,以假立的“不相应行法”的“形式法之意义”去正视这识心的知识义。由此而客观地理解知识以及知识的形式条件和知识的对象是“如何可能”的,就不仅正确地理解与说明了那些假立的“不相应行法”作为“非色非心而隶属于思的形式法”的特性与作用,而且反省地透彻地明了“识心之执着”与知识的关系,即一切知识皆为识心之执著的结果。这样,才能真正地把“识心之执着”从消极的意义转化为积极的意义。当然,这就是前文中所论述的牟宗三从“识心之执”凸显出佛教的“执”所具有的“知性”意义,并由此在其“道德的形上学”中建立“执的存有论”或“现象界的存有论”的重大意义。 四、转识成智与两层存有论 “执的存有论”是牟宗三会通融合佛学与康德知识学的产儿,但是这并不足够。牟宗三进一步说: 这样正视形式法而明识心之知识义,于佛教并无妨碍,而且到从五蕴讲唯识时,更足以补充并极成识心之执着,以及转识成智后,识心智心对显,双方之丰富的鲜明性以及对显之显著性。(49) 及至转识成智,则识心转,识心所造作的形式法被拆穿,而识心所对之对象法以及此对象法之对象义亦被拆穿,而对象即不复成其为对象,如是则般若智之鲜明的意义亦充分地被朗现而亦可以通过一理路而真切地被理解——实相般若非虚言也。(50) 这两段文字都谈到“转识成智”“识心智心对显”和“般若智之鲜明的意义”问题。它既与佛教中的“成佛”及“佛性”问题相关,也与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密切相关。但是,这一问题不是“执的存有论”的问题,而是“无执的存有论”的问题。必须看到,这一问题把“两层存有论”即“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连接在一起,使“执的存有论”往上提、向上通,并一直要通到“无执的存有论”。换言之,就是要把“识心”向上超升,使它变为无限“智心”(亦名“自由无限心”),也就是“转识成智”。其中的关键在“智心”,也就是般若智或般若智心的证实与呈现。“智心”或般若智,在“无执的存有论”中更多的情形下被取自康德的“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概念来表达或称谓。牟宗三把“智心”或般若智的精神提炼并概括为“融通淘汰,荡相遣执”(51)八个字。这一智慧不是分解地说法以立教义,而是非分解地说法立教义。这是对于已有的法来说的。般若智不舍不着,荡相遣执,尽归实相,即无相之相。从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来说,“无执的存有论”即是实相的存有论,亦即一无相之相的存有论。通向“无执的存有论”的“智心”的进路,已不再是“识心”的逻辑与知识的进路,而是道德的进路了。逻辑与知识的进路一旦要进入“无执的存有论”,就会在无限“智心”的照射下被扫荡淘汰,并将“识心”以及“识心之执”化为乌有。牟宗三指出: 因为康德思想中无般若智一观念,康德不承认人类有“智的直觉”(此相当于般若智),所以他不能说人可以去掉识知,去掉范畴乃至范畴所决定之定相。可是佛教就是要讲般若智、要转识成智。讲唯识、讲八识,并不是要肯定它,而是要转化它,不转化它怎么能成佛呢?转识成智你才能成佛,否则你是在生死海中头出头没,因为那是无明。(52) 这里的范畴、定相都是“识心”以及“识心之执”“绉起”的产物,它们是成功知识的条件。但是,这些东西不可能对“无执的存有论”显现与成立。因此,一般地说,由“识心”以及“识心之执”所显现的逻辑与知识要进入“无执的存有论”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也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如果照康德的说法,这就是一种僭越或误置(两种方法论原则即构造原则与范导原则或轨约原则交错和混淆),必然导致“辩证的幻象”的出现。诚然,从无限“智心”来说,它对于“识心”的逻辑与知识的进路始终保持着不舍不着的妙用。因此,它的妙用自然可以化解“识心”以及“识心之执”。“无执的存有论”至少在表面上是以佛学的面孔出现的,但它的进路竟然不是佛家的修行实践,而是儒家道德实践的进路。这一点是颇为特别的。正因如此,牟宗三以“道德的形上学”来命名他的“两层存有论”。这当然与牟宗三在哲学上宗奉儒学以及会通融合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尤其是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有关。其中的关键是“智的直觉”。如果没有“智的直觉”,就不能证实与解释“自由无限心”;没有“自由无限心”的澄明,“无执的存有论”就失去了础石。“自由无限心”与“智的直觉”本为一体之两面,必须经由“智的直觉”才能亲证和体悟“自由无限心”。这一过程乃是“自由无限心”的反观自照,牟宗三称之为“逆觉体证”。这也是一个儒家的说法。牟宗三非常清楚地知道,儒、释、道三教的实践工夫均与“智的直觉”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均可通向“智的直觉”: 中国人的传统承认人有智的直觉,人之所以能发出智的直觉是通过道德的实践、修行的解脱,而使本有的无限心呈现。中国人承认有无限心,但不把无限心人格化而为上帝。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无限心,而通过道德的实践以及佛教、道家的修行而使它呈现。(53) 尽管如此,牟宗三独许儒家的道德实践之路为正中至大,认为由道德实践中呈现的道德意识显露自由无限心乃必经之路,所以以儒家的道德实践之路作为其“道德的形上学”的进路。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虽然融摄会通了佛、道哲学的丰富内容,但是它毫不避讳地高扬儒家哲学的旗帜,并自觉地以儒学正统相标榜。对于牟宗三来说,道德实践是进入“道德的形上学”的“无执的存有论”的必由之路,因为道德实践的进路直通到“智的直觉”。“无执的存有论”是以“智的直觉”为基础而直觉地构造的,而不是逻辑地建构的。“智的直觉”在“无执的存有论”中实在是居于中心与核心的地位。 “智的直觉”概念虽然源自康德哲学,但其具体内涵却完全是中国的,并且以儒、释、道三教所共同肯定与崇尚的最高心智为主。牟宗三指出: 心是无限心时,则中国儒、释、道三教当然都承认有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中国哲学中自无这个名词。尽管没有这个名词,然而并非无与这名词同等的理境。设若康德向陆、王或智者大师问:“人有没有智的直觉?”他们一定断然地答复“有”。(54) “智的直觉”与上文说的佛教的“智心”或般若智完全相应与相通。因此,在佛教那里,“智的直觉”无非就是般若或般若智、“性智”。但是,在“无执的存有论”中,“智的直觉”取代了佛家的“智心”或般若智,固然淡化了佛学的色彩,但更为重要的是,“智的直觉”是在中西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儒、释、道哲学与康德哲学所代表的西方哲学的比照与对显中,被牟宗三发现、移植、“改装”、充实、重塑后推出与崇奉的重要核心概念,它代表了中国以儒、释、道为主的哲学精神智慧与力量的最高活动和存在的状态。中国哲学自有传统以来一直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因而“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一般地说,西方哲学认为“智的直觉”乃是神或上帝所独有的最高心力智慧的形态,不承认人具有并可能具有“智的直觉”。因此,“智的直觉”成为中西方哲学的一大分水岭(55)。然而,在关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中,“智的直觉”却成为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与最难理解和把握的众说纷纭的概念,与此相关的“道德的形上学”也是如此。尽管牟宗三严格地区分了“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形上学)与“道德底形上学”(康德的形上学),但不幸的是,“道德的形上学”仍然未能逃脱被人严重误解和攻讦诋毁的命运。经常可以看到,“道德的形上学”被等同于“道德底形上学”,或关于“‘道德’的形上学”,“良知”被直接等同于“道德”,“良知坎陷”被说成是“道德坎陷”,“良知的自我否定”被歪曲为“道德的自我否定”,如此等等。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状况,固然有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但是通向牟宗三哲学的佛学的视野与进路不是从未进入研究者的眼帘,就是像废旧生锈的机器一样被遗忘而闲置一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如上文所指出的,尽管佛教修行实践之路,在牟宗三的哲学“判教”中,从来没有获得过与儒家的道德实践之为“圆教”哲学进路同等的地位,但是在其“道德的形上学”或“无执的存有论”中并没有否定它,而且对道家的修行实践之路也是如此。佛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从三个方向进入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可能的通道:第一,可以由“一心开二门”模型接近与把握其“道德的形上学”的“两层存有论”间架;第二,可以由“不相应行法”以及“识心之执”的观念通向其“执的存有论”;第三,可以由“转识成智”的问题将其“两层存有论”即“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联系起来,并由般若智与“智的直觉”的通贯而通入其“无执的存有论”。虽然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的方向与道路在本文中没有得到展开论述,但至少第二种可能的方向与进路已经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五、小结:以不相应行法之范例论中西哲学会通及其意义 以上所述,牟宗三对“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不是泛泛的研究,也不是孤立地从佛教的宗教性出发,而是把它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尤其是比较集中地与康德知识学的范畴论做了系统精深的比较研究,揭明与阐释了佛学“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意义,使它从佛教的泛心理学主义的笼罩中解放出来,在哲学知识论上获得了新鲜的积极的意义。这虽然仅仅是牟宗三众多的融合会通中西哲学的一个案例,但它提供了研究中西哲学会通的典范,可以用来考察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和意义。 首先,佛教的不相应行法与康德的范畴论之间本来就内在地具有心理的相通性,但二者出于各自的文化系统中,方向与目的不同:前者在佛教中是泛心理学主义的,关注人生烦恼的问题,目的是寻求解脱而成佛,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后者本来就是一套知识论理论,是为回答或解决“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出现的,目的与方向在于人类知识论理论与科学知识的发展,与心理学分界而立,与人生哲学也分属于不同的哲学领域,其意义是直接的、鲜明的、正面的、积极的。如果二者不交遇、不比较,就很难发现或看出佛教中的不相应行法所具有的知识论意义。因此,如果没有康德的范畴论是难于想像的。但是,反过来看,从佛教的不相应行法也可以理解康德的范畴论。牟宗三在为劳思光的《康德知识论要义》所写的序中,便以自己解悟康德哲学的亲身体验和思想历程做了深刻的揭示和阐述(56)。 其次,在牟宗三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康德的范畴论为参照来看不相应行法,以发现和揭示其知识论的意义。康德范畴论成为镜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标准以及范式,这是典型的援西入中。与此同时,在比较二者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和机械地移植康德的范畴论,而是加以融通与整合,“异中求同”,发现不相应行法与康德范畴论二者之间的相通相同的共理,并进一步“同中求异”,寻找不相应行法之中其自身的特性与精神,从哲学之理上进行解释与阐明,以确立不相应行法自身的框架与标准。在此基础上,以不相应行法自身的框架与标准对原有的不相应行法进行反省地批判和梳理,去粗取精,补充完善,使其具有独立的知识论形态和意义。这既是整合,同时也是创新。 由此看来,真正的融通相当艰难且不易做到,但真正的融通必有所创新或开新。因此,哲学的融通就是融合会通而有创新之义。就此而言,牟宗三对佛教不相应行法与康德范畴论的比较研究不愧为一个典范。笔者将近二十年前最初从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的未来拓展》一文读到他讲不相应行法与康德范畴论的比较会通,有振聋发聩之感,耳目为之一新,不胜惊喜之余,非常佩服与感叹他对康德哲学的精熟与通透,可谓出神入化而不为过。康德专家写的研究康德的专著,甚难使人有这般特殊的经验。牟宗三可以在佛学中讲康德,而且是在不相应行法中讲康德,如果不是对康德哲学熟透到十分的境地,那是想都不能想的事情!后来更感觉与意识到比较融合会通之不易。这必须对中西哲学皆有精深的造诣与通透的了解,才有可能;否则,就会浮在表面,隔靴搔痒,流为皮相之见。 从牟宗三在比较中会通融合佛教的不相应行法与康德的范畴论的结果和意义看,也有几点启示: 一是在佛学中发现与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以“不相应行法”与知识论问题为代表的重要课题(其实不止于此,还有“二谛”“三性”以及“色心不二”与知识论),而且这也开拓出中国哲学的一个新的领域。如果重写中国哲学史,则可以考虑把这一领域的内容即“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填补进去,这对于充实和丰富中国哲学史来说,意义重大。 二是不满足所发现的佛学中“不相应行法”与知识论的新领域,不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拘限于这一领域,而是以“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的批导为道路,走向更高的哲学追求。如从不相应行法走向“执的存有论”的建立,并在更高的哲学(“两层存有论”即“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创造中把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吸收囊括进去。这又是更高一层的复杂问题,牵涉儒释道与西学的融通问题。如在“无执的存有论”中对于不相应行法及其所显出的“识心之执”的知识论内容的摄入与整合,既是典型的援佛入儒,同时还是援西入中。 三是为佛教哲学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由牟宗三对于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形式与意义的揭示与解释,可以进一步把佛教中的不相应行法与陈那和法称等一系(包括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及上座部南传佛教)的佛教逻辑和知识论联系起来,探问与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追溯它们的历史渊源与道路,展望它们可能的未来。 这里有必要指出和强调牟宗三的一个特别看法,这就是他认为从佛教的材料来讲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与一般所说的“佛教有它的知识论”的意思是根本不同的。譬如,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在其《佛教逻辑》所讲的佛教的逻辑和知识论即佛教的“认识论逻辑的体系”(57),与牟宗三所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们两人讲的都是佛教徒的理论,而且均有东西方哲学比较的背景、内容与方法,都擅长于细密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思辨,但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与取用的材料以及学术关怀皆不同。舍尔巴茨基专门以“佛教徒创立的逻辑理论”,尤其是陈那和法称所代表的“佛教逻辑”为对象,旨在揭示与指出印度和欧洲“两种逻辑体系的相似性”(58)。牟宗三是借佛教的材料及其所蕴涵的问题来讲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并不关注陈那和法称所代表的“佛教逻辑”,甚至不注意玄奘和窥基的“佛教逻辑”包括或涉及知识的问题,其目的是要为中国哲学在现在与未来的继续发展而“开出”(亦即建立)一套知识论的存有学即“执的存有论”或“现象界的存有论”,这是哲学家的纯哲学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二人都运用比较的方法,但是舍尔巴茨基只讲求印、欧哲学之间的比较与会话,并不措意于二者的会通,牟宗三则不仅注重东西方哲学之间的比较,而且还追求二者之间的会通。 四是拓宽和丰富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和意义,对于促进中西哲学的对话与融合,影响其各自独立发展的风格与道路,会有一定的裨益。对中国哲学来说,固然需要援西入中和以西释中,但是对西方哲学来说,自然也会需要援中入西或援印入西与以中(印)释西。牟宗三说:“佛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康德,康德的说法太生硬,佛教较有黏合性。”(59)这话对西方人也可以成立。舍尔巴茨基指出:“哲学家如果熟悉梵文作品的风格,他就会试图以印度的概念术语来诠释欧洲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将印度概念译成欧洲的哲学术语。”(60)这是不能小看的。 综上所论,在中西哲学的比较融合会通中,受益的不应该只是中国哲学,也应该包括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