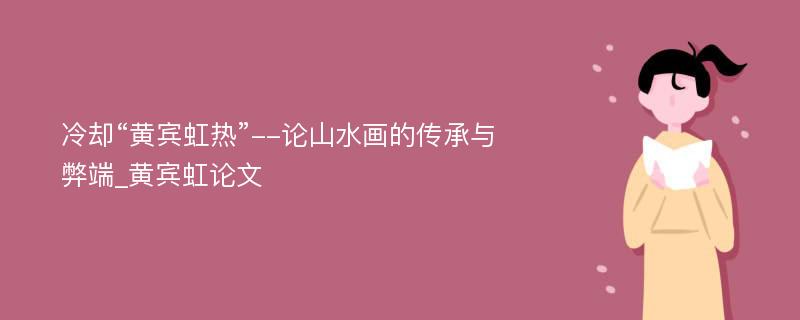
为“黄宾虹热”降温——浅谈山水画的传承与时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弊论文,山水画论文,浅谈论文,黄宾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画界的“黄宾虹热”已经有些年头了。近年来,有愈炒愈热之势。有趣的是,在全国第十届美展前,某国画界权威机构为了帮助年轻画家顺利入选参展,还特地举办了创作培训班(学费颇高)。学员们研习的山水画大多是黄宾虹风格。结果参选时纷纷落马。据说仅有一位入选,此君画的还不是尽然的“黄派”风格。看来评委们毕竟还是有眼光的。
我不知道落选的学员们当时的心境如何?他们之中有些应是地方上的高手,为什么不去深入生活写生,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创作与时俱进的新山水画呢?何必去追“黄派”之风呢?显然与时下的“黄宾虹热”和误导有关。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陈年旧事。那是1985年的秋天,我为学院的国画培训班学员上课。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有工艺美术厂的技术人员、厂长,有美术馆美术干部和中等学校的教师等。当时我带领大家在香山写生。一日,五、六个学员把我围住,其中一位学员以非常郑重的口吻对我说:“老师,我们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们大家觉得您人很直爽,希望您能认真回答我们。”当时的气氛十分严肃,我笑着说:“你们干什么呀?这么紧张,有问题就问吧,我是有问必答。”为首的学员说:“请您谈谈刘海粟、石鲁的画好不好?石鲁的画是文革前的好,还是文革后的好?”我立刻告诉他们:“刘海粟的画画得不好。石鲁在文革前画的画非常好,文革后的画和字都不好。”令我意外的是,这些三、四十岁的学员高兴地象孩子一样,几乎雀跃起来。我问他们何以这样高兴。他们告诉我:他们原来的看法与我一样,可是社会上的吹捧风之盛令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产生了疑问。学员们也曾请教过其他老师们,老师们的看法也与社会上一样,所以他们就没有自信了,开始怀疑自己的认知能力。此次我给了他们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答复,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学员们称赞我敢讲话,不怕得罪人。我告诉他们:在学术上,不存在什么得罪人不得罪人的问题,要讲学术真理,要讲艺术良心。我作为师长,要讲真话,这是我的师道尊严。
我曾多次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谈起这段往事。大家都对国画界学术问题混乱深感不安,深感为人导师责任重大。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近两年《美术》杂志开展关于美术作品艺术标准的讨论,对促进新时期美术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具体到国画山水的艺术标准的论述则鲜见(或许我没看到)。许多年来,我感觉国画山水缺少有分量的主题性作品。
前几年,我曾去中国美术馆看全国美展的获奖作品展,发现国画山水作品中缺少描绘祖国名山大川和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貌特征的作品,许多名家和年轻作者表现的题材多是些小景雅趣。或许他们画的是名山一隅,是我看画不仔细,没看明白。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大多数画家疏于造型,因此作品往往很难使观众分辨地域的差别。我想美协主办全国性大展,即使是山水画肯定也会有主题性要求的,但从大多获奖作品来看,显然是力不从心。获奖作品尚且如此,时下流行的追求笔墨情趣的空泛之作便可想而知了。
邵大箴先生说的好:“近代中国山水画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画家只在前人的作品中讨生活,只注意笔墨情趣,忽略了在描绘中与客观物象对应的真实与形似,因此,使津津称道的笔墨趣味失去具体实在的艺术感染力,也失去画面应有的视觉效果。”我想邵先生所说的,不仅指出了清末、民国年间山水画的弊病,同时也指出了近年来山水画存在的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绘画艺术属于造型艺术,而且是平面造型艺术。绘画是通过描绘出的形象来与观众交流的。不管你是西画还是国画,也不管你是什么流派,无论你用什么颜料或采用什么表现手法和技巧来画,都是要通过造型过程来完成的。国画的笔墨,西画的笔触,都是为造型服务的。造型能力为绘画第一要素,应是不言而喻。不注重造型而侈谈“笔墨”是导致山水画表现力差,路子越走越窄的主要原因。作为导师、长者理应正确引导年轻人去深人生活写生,提高用“笔墨”造型的能力。但使人遗憾的是,正是有些长者、导师、权威(起码职务上是)正在导演着“笔墨至上”的神话。时下的“黄宾虹热”便是一例。
陈瑞林先生在日前谈时下“黄宾虹热”的文章中,担心一些人通过神化黄宾虹,“确立自身的话语霸权,将‘传统’、‘笔墨’定于一尊,作为表率、典范、正宗、主流来号令四方。”
我看表率也好,典范也好,正宗不正宗,能不能成为主流,一个艺术家最终是要靠自己作品说话,而不是靠官本位,一旦下了岗,号令也就没人听了。学术问题还是需要讨论的。
我认识黄宾虹作品应是在六十年初,那是在故宫绘画馆《近百年中国绘画展览》上。齐白石和黄宾虹作品按年份陈列在最后,当时我只觉得黄氏作品与众不同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随着习画渐长,尤其是开始画山水以后,慢慢喜欢欣赏黄氏作品。但只是欣赏、品味而已,从来没有临摹过。
黄宾虹先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清末、民国年间,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美术史论家、鉴赏家和画家。人们介绍黄氏作品时,总是习惯地把他一生作品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他六、七十岁以前,这时期的作品多以临摹古人为主,但他不照搬古人,多有变化,画面造型疏疏落落,显得很灵动,不呆板。但这时期的作品,因为是以临摹为主,即使有所变化也不能称为是个人风格。六、七十岁以后,据有关专家介绍:黄老先生多了游历名山大川的机会,对大自然和生活的感悟,使画风变得浓重起来。直到晚年形成了浓重的“浑厚华滋”的风格。我比较欣赏黄氏晚年作品中,直面即是山的那种画面。画面中有树木、山、石和点缀其间的建筑物。他以“锥划沙”式的短线条和不同笔触的大小点子来塑造物象,运用笔墨则是浓、淡、干、湿并用。他淡化物象之间的轮廓线,使物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而在物象和点、线之间留的空白或是“飞白”则犹如光斑在闪烁。这类作品整体感极强,表现出一种前无古人的意境——朦胧美感,即是人们常说的《暮山图》或《夜山图》。我注意到他用笔是点、线、面相结合,即使是表现面,也不用渲染的方法,就连着色也是一笔笔点上去。因此,物象表现感觉深厚而丰富。我也曾见过黄宾虹先生用淡墨为主的作品,他先以稍重的墨色表现前景的树木、庙宇,远景大面积的山,用淡墨的短线和墨块来塑造,既深远又厚重。无论从技法或从视觉效果来看,都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黄先生的焦墨画也画的十分精彩,线条苍茫老辣且灵动,很有量感和空间感。
对于一个画家的风格和成就,美术界历来褒贬不一。对黄氏艺术持异议者大有人在。我接触过的北京老一辈画家大多已相继离世,他们中有的把黄氏艺术说的一无是处,显然有些偏激,带有门派之见。
据说宣传、推崇黄宾虹艺术从4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那时黄老已是八十高龄。傅雷、高万吹、朱金楼、王伯敏相继写评介文章,其后又有刘海粟、赖少其等人。在我看来黄宾虹先生能享有今天的盛誉,该与李可染和张仃两位先生的影响力有直接关系。李、张两位先生是中国新山水画的开拓者,在国画界举足轻重。他们的推崇不能不引起美术界的关注。
我十分有幸,年轻时就开始与他们交往,聆听教诲,学习到许多知识。我也曾向他们请教过对黄氏艺术的看法。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推崇黄氏的创造性,认为黄氏与那个时代流行泥古、因袭的画风不同。认为黄氏笔墨功力深厚,运用积墨法,浓、淡、干、湿并用,虽然墨色很重,但晶莹剔透,把物象表现得很整体,产生一种“浑厚华滋”的美感,是前无古人的。我对此表示赞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黄老疏于造型,画的黄山、雁荡山和桂林都差不多,没能表现出地貌特征。两位先生或是笑而不语,或是笑着,说我的说法要求过高。
对于一个画家成就的评价,有时的确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评价。但对于后辈学习者来说,又要站在今天的视角来认识,否则会盲目追随。毋庸置疑,黄宾虹的确是一位有创造性的画家,他有些好作品创造出的意境也是前无古人的。但我又不能不指出黄先生造型的弱势。黄先生习画从临摹入手,而且六、七十岁前大致如此。我看到他的写生作品,大多是记忆构图之类的图解式稿,没有表现出对景物深入刻画的造型能力。由于黄先生造型能力的弱势,阻碍了他把自己独到的“笔墨”优势,运用到表现丰富而具有个性的物象中去。因此他的作品地域不分,面貌单一就是必然的了。有人说他的作品还是有变化的。我看这种变化是微乎其微,视觉效果都差不多。这种地域不分,面貌单一的问题,不仅存在于黄氏作品中,同时也存在于许多过世的名家甚至被奉为大师级画家的作品中。“一套笔墨横扫祖国大江南北”的现象很常见。这不能不说是山水画的一种悲哀。
也许会有人反对我的说法:“国画讲写意,国画与西画的造型理念不一样。”
众所周知,白石老人有句名言“妙在似于不似之间”。这似乎成了侈谈“笔墨”和“写意”者的口头禅。在我看来,或许有些“写意”画家并未知晓中国画“意象”的含义。白石老人的名言并没有错,老人家深知“意象”造型的绝窍,他的“墨虾”的造型和笔墨无疑是国画“意象”造型的典范。但老人并没把问题讲透。一个“似与不似”把初学者弄糊涂了,却又给了坚持“笔墨至上”论者以口实。你说我画得不像,我则解释为“写意”,到后来还说你不懂中国艺术。在“意象”造型的解释上,李可染先生一语道破玄机。李先生曾对我说,“中国画造型要设计”。妙极了!我的理解是要在观察写生的基础上,赋予物象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它既不是原物的翻版,也不是造型不准的肆意夸张和变形;而是要求画家运用笔墨塑造出一个既能把握物象本质特征的,又能体现画家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显然,能做到这些要求,不是件轻松的事。比玩弄几下笔墨趣味要困难的多。其实那些侈谈“笔墨”的人,也未必真懂“笔墨”的含义。我不是在危言耸听,据说,在八十年代,日本画家加山又造访问某最高学府,国画系派代表与会座谈。加山先生表示对中国水墨画非常敬佩,他说自己也画,但画不好。他经常听中国画画家谈笔墨问题,想请教一下“笔墨好”的定义。在场者居然回答不出,一时成了美术界笑柄。
最近两年,我有机会参予一些主题性山水画创作,接触了一些同行。发现有许多人一接触实实在在的主题就乱了阵角。这些同行往往速写都画得很好,造型能力很强。但这种造型能力一旦转换为用“笔墨”造型时便失去了控制,笔法、墨法依然是古人、前人的,面对真山真水束手无策。画出的画依然是程式化的老样子,把握不住主题物象特征。在我看来,这是在如何继承传统上出了毛病。他们在把继承的传统“笔墨”,转换成物象现实的造型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对于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我十分赞同王仲先生的新提法:“如何传承传统”。“传承”二字对传统明确了选择性和疏导性。
李可染、张仃两位先生都十分重视传统。他们最清楚该从传统中学习什么。传统中优秀的“笔墨”被他们吸收并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运用到深入生活和写作中去。他们都十分注重造型,开创了一代新风,成为新山水画的领军人物。
他们推崇黄宾虹的艺术成就,是为了倡导黄氏的创造精神。李先生坦言从黄氏作品中汲取了“积墨法”,但他用线是“屋漏痕”而不是黄氏的“锥划沙”。他用的“散笔点”也与黄氏点法不同。张先生则是用“一波三折”的线条来塑造物象。他们是艺术上的智者。我与二位先生七十年代即相识,交往不算过密,但也不算不深。我从来没有听说两位先生要学生们去临摹黄氏作品,摹仿黄氏风格。这说明两位先生深知对“传统”应如何传承。
徐悲鸿先生对继承和创新问题有很好的见解:“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我斗胆把徐先生的名言改一下:“古法之不佳者,弃之,未足者分析之,佳者垂绝者继之而后变化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黄宾虹先生虽然有创造性,但对于五十年后的今天,用时代的眼光来看,他有“未足者”。后辈学习者应分析,哪些可学,哪些不可学。即使是“佳者、垂绝者”学了以后也应变为自己的东西。我认为这样才能传承好传统国画,开创新面貌。
明清以来,国画界对所谓“文人画”的宣传和推崇,有点儿过头,除去“文革”时期,这种宣传和推崇可以说从来没有间断过。近几年则把“文人画”捧上了天。甚至有人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画的主流,似乎是唯一值得尊重的传统。由此派生出来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追求笔墨趣味的倾向大行其道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系列展览》。几位国画爱好者看过以后对我说:“黑乎乎的,没什么好看的,分不清是谁画的。”他们不是美术专家,也不是没有文化修养的观众。他们的话,从折衷一点儿的角度讲,也应是有道理的。“黑乎乎的一片”该是“黄宾虹热”的负面影响。
引导学生,年轻画家走好艺术道路,作好对传统的传承工作是老师、长者的责任,更是身居美术界要位者的责任。 —
然而一位美术界位高权重的先生,在强调“国画”界定标准时居然说:“国画大师黄宾虹说:中国画舍笔墨而无它。”我不知道黄氏是在什么前提下说的,但我感觉这话不像出自一个“大师”之口。但我又记得黄宾虹也曾说道:“欧风东渐,心理契合,不出二十年,画当无中西之分”。黄氏的两句话哪句对呢?我看都不准确。但我从两段话中看到了两个黄宾虹,前者是保守偏执的,后者是开放豁达的。这位先生又指出:“‘构图’、‘构成’和‘色彩’都是外来语,是西方的概念,而我们中国画是有自己的概念的,它叫‘经营位置’,叫‘随类赋彩’。这种概念的混淆是不容忽视的……”多么滑稽的说法呀!看来我还要补充一句:“你们以后说‘笔墨’时,千万不要说‘线条’二字。‘线条’二字进入现代语言中不过百十来年,中国画自己从来的概念是‘描’!”我还想请教一下:“画国画是不是应该头梳长辫,身穿长袍马褂才可以动笔呢?”可笑之极!
在学术上,我不喜欢不懂装懂的人,更讨厌那些懂装不懂的人。在我眼里,那些懂装不懂的人有搞学术腐败之嫌。在美术界常有这种情况:你批评他不好,他可以说你不懂,领导过问,他说是学术流派之争,似乎学术流派之争即可掩盖真、善、美和假、恶、丑之间的区别。有位朋友说的好:“其实他们就是要借‘学术之争’来搅混水。”绘画艺术在辨别是非时,的确没有象科技那样经纬分明,但绘画是有标准的,无论是国画还是西画;无论你是人物、山水或花鸟;无论是工笔、简笔、写实、写意或装饰性的;也无论是水墨或重彩的,它总有一个好坏的标准秤。这标准秤存在于每个专门家的心中。这杆秤有时准确,有时失误,它的砣,我称之为艺术良心!陈瑞林先生在谈时下掀起“黄宾虹热”时指出:“恐怕是为了迎合某种潮流,某种时尚,是为了获取某种实际的利益。”我看此话颇有意味。不过在我看来: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国画画家,他的艺术成就基本上是大局已定(像齐白石、黄宾虹那样的老年、衰年变法者实属罕见)。这与个人天分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自己不行,就承认自己不行,好好调整一下心态。不要打着“回归传统”之类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去拉山头,造声势,最后贻误年轻人,贻误美术事业。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的“先进文化”的含义,体现在美术事业上,我理解应是“与时俱进”。我们这一代人已进入花甲之年,除了要努力创作一些“与时俱进”的好作品外,还要作好传承工作。不应引导年轻人在古人、前人的圈圈里转,更不该引导年轻人在创作时摹仿什么风格,应该大力倡导深入生活写生(写生本来就是山水画的好传统)。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千变万化的。她有许多美感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表现。传统“笔墨”只有在写生的过程中进行垂炼,改造,才能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从而创作出“与时俱进”的具有个性特征和内容丰富的新山水画。李可染先生曾说过“要为祖国山河立传”。我以为这应是山水画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