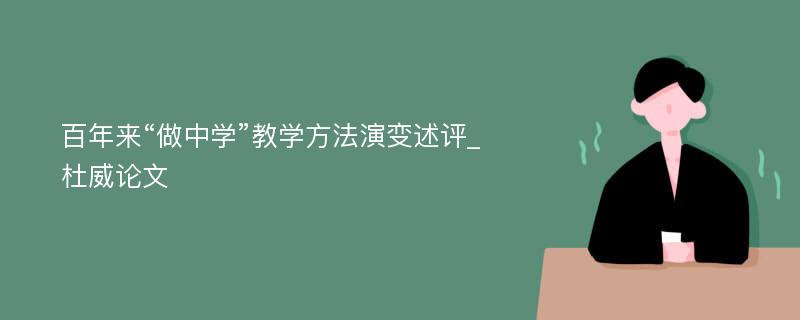
“做中学”教学法之百年演进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法论文,述评论文,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4)04-0095-08 “做中学”教学法在中国近百年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其具体的表现样态是多样的,但杜威(John Dewey)的“做中学”(或译“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教学思想可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原型”。“做中学”教学法的基本要义在于,以学生活动来架构课程,以直接经验的获得为核心旨趣,在情境化的教学场域中,通过学生的各种“做”——观察、实验、探究、劳作、游戏等来组织实施教学。“做中学”教学法既可以看作是一种教学原则,也可看作是一种教学方法。在中国近百年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做中学”教学法一直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不断冲击着教师课堂讲授、学生“静坐静听”的教学范式。 一、“做中学”教学法之百年演进历程透视 在中国近百年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做中学”教学法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其演进路线可以概括为:引介与改造→批判与异化→重估与更新,其时间跨域分别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至今。“做中学”教学法的历史命运可谓“一波三折”。 (一)引介与改造(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客观地讲,在20世纪初我国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做中学”教学法的出现与热兴,主要源于杜威。据史料记载,“五四”前夕,杜威受邀来到中国讲学,历时两年多,遍及大半个中国,主要宣传其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他的大大小小的各种讲演被陆续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有的则汇编出版,如北京晨报汇编出版的《杜威五大讲演》、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的《杜威三大演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及《教育哲学》等。[1]杜威的“做中学”教学思想便散见于这些演说中。如:“学校以儿童为中心,社会以青年为中心,所以最希望学校养成一种有生气的儿童,社会养成一种有生气的青年。要怎样养成呢?就是从自动开始。”[2]p.108“故教学儿童,当使之能自行研究、自行参考,或有问题发生之时,真可利其机会,使之研究发展能力,切不可惮烦为之讲演,为之口述,以灌输知识与儿童为能事。……教学方法之最重要者,须以儿童为教学之中心,切不可以科目为教学之中心。”[2]p.370“在小学校的儿童,可以利用他们的活泼聪明的精神,使他们自动,……教授的原理,就是使学校的教育和学校外的教育,成为一致。”[2]p.559-560“学校是为社会进步而设的,不是仅为传授知识给少数学生的,应当做成一个社会的缩影……要学游泳,除去在水中直接练习,没有更好的办法。”[2]p.604杜威的这些“做中学”教学思想是以他的基本教育哲学主张即“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为依据,强调学生能动学习、主动实践,他深信“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3]杜威的“做中学”教学思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教学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突出表现在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的广为流行。 对杜威“做中学”教学思想引介的功臣,主要是他的在华弟子以及他的一些思想“信徒”,这些人主要包括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郭秉文、蒋梦麟、张伯苓等。而对杜威的“做中学”教学思想进行本土化改造最为出色的则是陶行知。陶行知曾师从杜威,“五四”前后曾一直深信杜威的教育理念。但在回国后,他根据中国教育的实践情形,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头”,变“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创立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所谓“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学。……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4]从上述可见,“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核心在“做”上。陶行知认为,“做”就是在劳力上劳心,因为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是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是做。[5]可见,“教学做合一”,着重强调的是教育要基于社会生活实践,思想(劳心)与行动(劳力)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互补,如此获得的才是真知。与杜威的“做中学”相比,“教学做合一”不仅强调了“教”的意义,而且给予了“做”更丰富的内涵。 (二)批判与异化(新中国成立初至“文革”结束) 新中国成立初“做中学”教学法遭遇批判,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做中学”教学法受到追捧一样,也主要是缘于杜威。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以及我国的历史处境决定了对杜威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在“划清界限”的意识形态语境中进行的。较早系统性地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批判的是曹孚于1950年发表在《人民教育》上的《杜威批判引论》一文。作者把杜威教育思想认定为“反动政治立场”,据此给予了全方位的批判。之后,对杜威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多。“做中学”作为杜威整个教育思想在实践中的“方法论原则”,自然成为被批的一个重要目标。对杜威“做中学”教学思想给予批判的学者众多,如杨继本指出:“杜威的‘从做中学’的教学理论,以及服从这一理论的‘设计教学’,实际上在骨子里包藏着深沉的阴谋诡计。他要学生从事劳动活动,生产有价值的东西,而却拒绝保证获得系统的科学知识的统一的教学计划,严格的教学大纲,以及一定的教学组织、方法和手段。”[6]曾作忠指出杜威一生最强调的教学理论就是“做中学”。他认为“杜威这样厚颜夸大的儿童中心论,首先在教学过程上,失去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不过是工作的组织者,是顾问……照这个反动教育哲学家的理论去做,学生至多只能得到零星的、片断没有系统的知识,并且仅仅是一些肤浅的知识”。[7]车文博认为,杜威的“做中学”是“实用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歪曲,是反理性主义的爬行主义的反映”,是“实现帝国主义教育目的、内容的基本途径”。[8]上述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批判的主旋律。由于陶行知曾师承杜威,因此他的“教学做合一”也自然成为被批的靶子。有论者拿陶行知的“做”和毛泽东的“实践”进行比较,指出“陶先生主张的‘做’和毛主席所讲的实践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的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而生活教育的做,是放弃理论的‘做’,狭隘经验主义的‘做’”。[9]更有甚者,认为陶行知的这种思想“实在是杜威反动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再版”。[10] 新中国成立初中国教育学前苏联、批杜威,而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教育模式立即被冠以“无产阶级教条主义”之名,自然也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事实上赫尔巴特主张的“教材、课堂、教师”三中心,与我国传统的旧教育制度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契合,而这些从根本上正是新中国教育革命欲竭力破除的。毛泽东曾反思道:“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怎样交换,身体也搞垮了,真是害死人。”[11]从这里可见,当时的中国教育革命,从骨子里是趋向杜威的。新中国成立初杜威的“做中学”表面上在理论上受到了批判,但其基本思想一直如同一条暗流潜隐着,而在教学实践中却以另类的方式呈现着,这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论者评论道:“‘文革’时期,在政治层面上对杜威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后,在教育实践中并没有真正革掉杜威教育理论的命,反而早已融入中国教育中的杜威教育理论以横扫一切的姿态,又潜回了中国教育中。”[12]但问题是,这种“潜回”是非理性的,它和“文革”的“左倾”路线融合在一起,把中国的教育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文革”期间,“做中学”被彻底异化为“开门办学”“上山下乡”。譬如,有些学校竟然提出“生产在哪里,学习到哪里”“工地是学校,炉旁是课堂”,有的甚至主张去掉学校的名称,主张不再按大、中、小来划分学业阶段,而在“劳动程度上分阶段”。[13]这种被“政治化”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经彻底扭曲了“做中学”。 (三)重估与更生(改革开放后至今)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中国教育界对杜威“做中学”教学思想更多表现的是以信奉的态度推介它,新中国成立后30年对其“做中学”教学思想更多的是从政治的立场批判它,那么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界对其“做中学”教学思想则更多的是基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解读它。在重新肯定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1980年赵祥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率先发表了《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此后,学术界陆续出现了对杜威“做中学”教学思想进行重新评价的声音。譬如,夏之莲认为,杜威提出“做中学”教学思想,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培养能力的论述,在教育史的发展上,的确又提出来一个重要的思想。他不但在新的背景下提出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14]张见新指出,杜威的“做中学”教学思想反对了传统的教学思想和实践:只重知不重行,脱离学生和社会实际,满堂灌等,从而在教学思想和方法上起到了革新和创新的作用。“他这种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感性知识和‘做’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5]陈炳文则从“正确理解‘从做中学’的实质,消除各种偏见”“‘从做中学’的理论依据看其正确与否”及“‘从做中学’的历史性贡献”三个方面,较全面地对杜威“做中学”教学思想进行了中肯的重新评价。[16]这一阶段在“去政治化”语境中,学术界对杜威“做中学”教学思想的评价没有出现各种“过激”的言论,在重新认定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从这一教学思想中汲取积极的因素。学术界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决定了“做中学”教学法其命运的复兴。 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做中学”教学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于教学理论与实践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动课程”的逐步凸显与对“活动教学”的日益重视,以及21世纪新课程改革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正式确立与对“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积极倡导。20世纪80—90年代,“活动课程”在我国教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命名方式颇为多元,如“课外活动”“第二渠道”“活动课”“活动类课程”等。与此相适应,“活动教学”研究应运而生。1996年全国活动教学研讨会召开后,不仅出现了关于活动教学研究的专著,而且出现了大规模的实验研究,譬如,“活动—训练”教学实验研究、“活动教学与中小学素质发展”的实验研究等。[17]21世纪新课程改革,“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被正式提出,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并作为必修课,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各种形态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核事实上均是“活动”,其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都是“做中学”。与以往“活动课程”相比,“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加强了课程内容的统整,强调学习方式的多元性、组合化。而新课程改革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便十分契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自主学习主要强调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任务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合作学习主要强调学生能在小组或团队中基于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协商互助;探究学习则主要强调学生能独立地发现问题并能尝试着解决问题。新课程倡导的系列学习方式,赋予了“做中学”新的内涵,彰显了时代特质。 二、问题与反思 反思,常常是指向“问题”的,带有质疑的意味,但其旨趣是为了使事物、事理更加澄明。对“做中学”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认清一些问题。 (一)“做中学”教学法之命运反思 一种教学理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与时空场域中,其命运可能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一种教学理论,即使是在同一种文化环境而不同的时空场域中,其命运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做中学”教学法便是如此。自20世纪20年代杜威的作为“原型”的“做中学”教学思想被引介以来,“做中学”教学法在我国近百年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呈现着多变的命运。“做中学”教学法的命运,与杜威教育思想在我国的命运大体相同。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因“科学”“民主”受到国人信奉的杜威教育思想,在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近30年后,自新中国成立起又被中国教育批判了近30年,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的第二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杜威教育思想又逐渐得到重视。可以看到本次新课程改革的许多理念(如学生主体地位的凸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置等)均深受杜威学说的影响。反思“做中学”教学法“一波三折”的命运,可以窥见我国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存有的一些问题。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继后的“五四”运动,它荡涤了封建旧思想、旧文化,使得科学精神深入人心、民主理念广为流行,这无疑为杜威教育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而明清以来占据中国思想界主要地位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与杜威的“从做中学”有着共通之处,孙中山大力提倡的“知难行易”也加深了国人对杜威“做中学”教学思想的认识与认同。[18]这一切似乎能说明“做中学”教学法之所以兴盛确有其内因与外因。可是新中国成立初,我们对“做中学”教学法的批判,其主要缘由却因杜威的所谓“资产阶级”身份,这个“标签”致使我们的学术批判显得相当的非理性。放眼大半个20世纪,我国的教学论事实上充满了各种批判,而批判往往充斥着太多的非理性。批判不是最终目的,总得还要建构,可是建构更多的是“拿来主义”式“借鉴”,而“借鉴”更多的往往只是止于“借”而缺失“鉴”——从学赫尔巴特,到学杜威,再到学凯洛夫……那种主动的“被殖民化”消弭了中国教学理论应有的民族气质!而那弥足珍贵的一些中国本土化的可贵探索,如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也在种种非理性的批判中被漠然弃置。 新中国成立初对“做中学”的批判,除了政治的缘由,可能还有一个“本原”的内因,即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杜威、读懂他的“做中学”。思想的前提规范着人们想什么与不想什么、怎么想与不怎么想,也规范着人们做什么与不做什么、怎么做与不怎么做。而在规范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全部思想的前提中,最深层次的和最根本的思想前提,就是人们的哲学思想。[19]杜威作为一个教育哲学家,其全部的教育理念都来自他的经验自然主义哲学,而他的这个哲学观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根基。如果我们脱离其特定的“场域”,解读是很难产生“共鸣”的,批判也会显得随意乃至荒唐。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断章取义”的批判、“以讹传讹”的批判。譬如,因为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重组与改造”,所以就断定杜威是唯经验论者而否定书本知识的学习。事实上,杜威从未认为书本知识不重要,他只是在强调获取知识的方式即“做中学”是一种比“听中学”更有效的方式,强调直接经验并不代表他否定书本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层面对“做中学”教学法的重估,确实主要是缘于对学术的尊重。但对学术的尊重,不能脱离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可以看到,近30年异域的诸多教学思想几乎很少经过“审议”便极其自由地在中国教学理论与实践中流行着。“张口布卢姆,闭口布鲁纳”,俨然业已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对这种“教学文化”的非理性“入侵”,我们似乎已司空见惯乃至习以为常了。“做中学”教学思想自引进后,它在不断本土化的过程中,确实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所谓“三中心”的课堂教学范式。但在当下西方强调“学生为本”、强调“自主建构”、强调“多元智能”、强调“活动探究”等等这些“教学文化”的强势“入侵”下,“做中学”教学法似乎又逐渐偏离了其应有的运行规范,而被误用、滥用。新课程改革以来,这种“偏离”愈发明显。譬如,不管何种学科、何种课堂,总喜欢让学生合作探究一下,以显示新课改的精神。可以看到,新课程改革以来,课堂确实是“动”起来了,学生也确实是愈来愈自主了,可实际的教学效率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十年课改的深刻启示是,它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再一次说明,‘学生中心、经验课程、探究学习’(课程和教学应该主要使[是]学生直接经验),不能作为(中小)学校教育的独立或主导模式。”[20]这是王策三先生回望十年课改后给我们提出的忠告。当下“做中学”教学法在实践中被误用、滥用的命运,很能看出我国教学理论建设缺乏学术自信,且常常与教学实际相疏离、对教学实际指导乏力这一业已根深蒂固的问题。 (二)“做中学”教学法之价值反思 每一种教学法自有其适切的运用场域,均有其可为与难为之处。那么,“做中学”教学法,它的应然价值及其限度在哪?在学理上反思这一问题,是有效运用这一教学法的基本前提。 首先,从知识类型来看。信息加工心理学根据知识的性质把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两类。陈述性知识主要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程序性知识主要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陈述性知识主要以命题、命题网络或图式来表征,而程序性知识则以产生式来表征。命题、命题网络或图式的学习其主要旨趣在于记忆,而对于记忆而言,最关键的便是“意义”的理解;而产生式是一系列以“如果/则”形式表示的操作规则,其学习的关键在于实践操练。上述可见,“做中学”教学法之“活动”的特性,与程序性知识的习得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而对于程序性知识教学而言,“做中学”教学法自然是非常适切的。但对于陈述性知识而言,“做中学”教学法未必是最适宜的。陈述性知识学习的关键是理解意义,因此讲授法——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就显得更为重要。奥苏伯尔早就提醒我们,接受学习未必就是机械学习、无意义学习,[21]他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向人们揭示了讲授法事实上非常适切各种陈述性知识的教学。 其次,从学习领域来看。根据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学说,学生学习的领域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和态度。言语信息,是指能用言语(或语言)表达的知识,如人名、地名、符号以及一些基本事实,这类知识显然无须一定要“做中学”,“听中学”即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都是属于技能范畴,而技能的获得必须通过操练,这是心理学的一条基本规律,因此“做中学”教学法对上述三类学习领域就非常适切。态度,是一种对人、对事、对物、对己的反映倾向。态度的形成或改变往往需要各种内部和外部条件,内部条件主要有:对态度对象的认识、认知失调、有形成或改变态度的心向;外部条件主要有:各种强化、榜样人物的选择等。[22]由上述可见,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是颇为不易的。要让一个人形成或改变某一种态度,最重要的不是“知不知”(关涉知识),也不是“能不能”(关涉技能),而是“愿不愿”(关涉情感),实践证明,这是教学中最难的。知识可以“教”,技能可以“练”,而对于情感而言,则更多吁求“讨论—反思”与“移情—体验”,[23]可见,“做中学”教学法对于态度的习得并非特别适切。 再次,从“有效教学”来看。“效率”与“效益”,是“有效教学”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有“效率”,主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教学理想,即最“快”地实现课程与教学的价值。所谓有“效益”,主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教学旨趣,即最“好”地实现课程与教学的价值。[24]“做中学”教学法强调学生主体对学习活动的积极投入,通过主体的实践去获得经验,应该说这样的经验对学习者而言是鲜活的,因为它融入了学习主体的生命与激情,这样的学习定然是富有成效的。即从“有效教学”之“效益”来看,“做中学”教学法对于学生获取经验、形成技能确实是高效的。但如果从“有效教学”之“效率”来看,则是另一番景象。“做中学”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由“做”方能“学”,事实上这是需要以花费时间为代价的。人类获取知识事实上未必一定要从“行”到“知”。我们强调“知行结合”,起点既可以是“行”,走从“行”到“知”的道路;但也可以以“知”为起点,走从“知”到“行”的道路。学校教育情境中,面对既存的知识经验,倘若学生事事都要躬行(如神农尝百草),其教学“效率”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从学段分布来看。在学校教育情境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在活动比例大小的要求上是不一致的。年龄愈小,活动比例愈大;年龄愈大,活动比例相对减少,但活动水平相应提高。[25]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对以“活动”为主的“做中学”教学法的运用,应考虑不同学段的学生其活动的要求和水平。如在低学段,可以多多运用“做中学”教学法。幼儿园教育,就可以基本上全部运用“做中学”教学法,让儿童从玩中学。而随着学生学习层次的递升,以获取直接经验为主的“做中学”教学法可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事实上,杜威对他的“做中学”教学思想是有年龄规定的。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把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分为三个层次。其中4—8岁为通过活动而学习的阶段,所学的是怎样做,方法是从做中学。由8—12岁为自由注意学习阶段,这时可以学习间接知识,但间接知识的学习必须融合在直接知识中。12岁以后,则属于反省注意阶段,学生从此开始掌握系统性和理论性的科学知识及其事物规律。[26]上述可见,杜威的“做中学”教学思想的践行主要集中在儿童学习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并且以第一阶段为主。 (三)“做中学”教学法之实践反思 作为一种教学理论形态的“做中学”教学法,它在向教学实践的转化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会存在哪些困难?这是个颇为“现实”的问题。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较难,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即从教学实践的视角,来反思“做中学”这种教学法如何应对源于教学实践的重要诘问。这些重要的诘问主要有:其一,如果运用“做中学”教学法,教学内容如何处理?其二,如果运用“做中学”教学法,教师角色如何定位?其三,如果运用“做中学”教学法,教学环境如何设置? 基于“做中学”教学法自身的逻辑回答,理想的教学内容应该是基于学生的活动经验来组织,理想的教师角色应该是个组织者、引导者、指导者,理想的教学环境应该是趋向“生活化”、情境化的。现在需要反思的是,这些“理想”在教学实践中会遇到怎样的困境与困惑。 首先,关于教学内容组织问题。“做中学”教学法强调教学内容主要是学生的学习活动及其体验而非书本知识,它特别关注教学应当通过哪些活动展开以及怎样活动。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主要是基于学生的活动及经验来组织。应该说,这极大冲击了“知识本位”的教学取向,使学生获得知识与形成能力的过程变为同一过程,从而有效遏制了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但需要反思的是,以学生活动及经验为核心的教学内容,还要不要教科书?如果要教科书的话,这样的教科书如何编制?在杜威的“做中学”教学思想中,主要存在“去教材化”的倾向,如让学生直接通过纺织活动学纺织,通过烹饪活动学烹饪,通过饲养活动学饲养,通过木工活动学木工,等等。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存在一定弊端的。其主要弊端在于,学生习得的知识与经验往往是感性层面的居多,且缺乏系统性,可能是较为随意的、零散的,甚至可能会“误学”到一些知识与经验。如果编制教科书的话,显然不应以学科的知识逻辑顺序为主,而应以学生活动的心理认知顺序为主。但问题是,学校的课程是丰富多样的,学生面对各式各样的课程其“心理逻辑”到底是怎样的?事实上这是很难做到清晰认知的。可以断言,基于学生的活动心理来编制教科书,这是相当困难的。毕竟“学科逻辑”是显性的,而“心理逻辑”则更多是隐性的。基于学生活动心理来编制教科书,如若处理不好,则很可能什么“逻辑”都没有。 其次,关于教师角色定位问题。“做中学”教学法强调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学生自始至终都应处于中心位置,它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通过亲身实践、主动建构,以习得经验。无疑,这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现在需要反思的是,作为组织者、引导者、指导者的教师,其“教”的分量与程度到底如何把握?倘若在班级授课制的境况下,在既定的教学时间里面对庞大的学生群体教师又将如何充分地进行有效的个别指导?事实上“做中学”在非学校教育情境中是常有的事,可以没有教授者;但是在学校教育情境中,在“教学”这个特定的场域里,教师的介入是必需的。要澄清的问题是,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并非就意味着压抑学生的主体角色。在目的论意义上,“教”是为了“学”,“教是为学服务”的;但在方法论意义上,“教”绝不可处于从属地位,必须存在“教学生学”,否则,“教学”就变成了“自学”。“做中学”在学校教育情境中作为一种“教学”法,教师的介入不仅是必需的,而且对于教师而言该如何介入、介入到何种程度都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有论者指出:“‘做中学’虽然是以学生的活动为主展开的,但是教师必须提出设计计划,并随时准备解决学生遇到的各种疑难,这样不仅要求教师在知识结构上成为通才,而且还必须有高度的解疑技巧,过人的精力,客观上是不能办到的。”[27]这些言语有些偏激,但确实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最后,关于教学环境设置问题。“做中学”教学法强调教学环境与社会生活的接轨与交融,譬如,杜威认为“学校即社会”,提倡把学校当作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陶行知则认为“社会即学校”,主张社会就是一个学校。无疑,这大大拓宽了教学场域,使得教学不再囿于狭隘的课堂空间,因而将十分有助于学生活学活用、学用合一。现在需要反思的,学校教育能否提供“做中学”教学法所需的教学环境?如果能提供的话,学校教育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或者说,和校外教育相比,学校教育的边界在哪?事实上,无论是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抑或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他们在为“做中学”教学法寻求最适切的运作空间之际,都不同程度地模糊了学校教育的边界。学校的“教学世界”事实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归“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虽然是人类生存的场域,也确实为教学世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它的以经验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特征的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具有保守性和惰性。”而“教学世界通过使用以学术语言为主的语言系统,采用经过加工的教学资料,发展学生的各种思维,使学生的多种生命可能性由潜在的变为现实的,从而完成社会交给的任务。”[28]这便是“教学世界”区别于“生活世界”的独特性之所在。“教学世界”必然具有自己的独特规定性,“做中学”所吁求的“教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接轨与交融,客观上讲是不易达成的。“教学世界”可以一定程度上借鉴“生活世界”,但不应趋同和回归“生活世界”。 收稿日期:2013-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