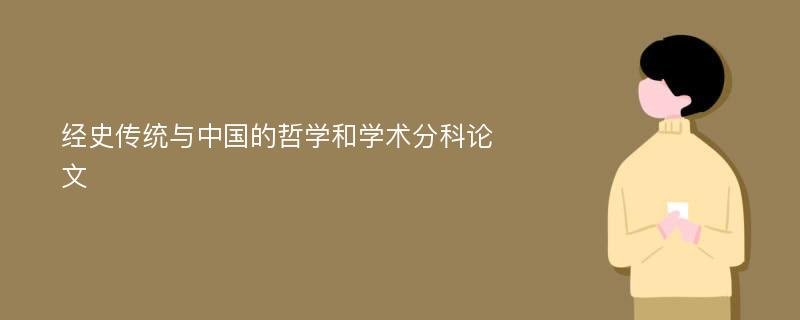
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和学术分科
文/李存山
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
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康有为等今文学家说,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所创;但经学确实可“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而并非如章学诚所说“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文史通义·原道上》)。如果这样理解,就把“经学开辟时代”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联系在一起。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这里的“史”并非后世“经史子集”意义上的“史”,而是特指作为“先王之政典”、“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作为中国上古文化之精华、“天与人参”、“官师合一”、“政典与史同科”意义上的“史”。
章学诚说:“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文史通义·书教上》)所谓“撰述无定名”,就是说三代以上之“史”并非后世一般“史部”意义上的“史书”。由此可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还不能以所谓“夷经于史”来评论之。
正是从“六经皆史”,即在中国上古“王官之学”的时代“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意义上说,经学的经书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因为“经者常也”,在经书中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常道”或核心价值观,所以亦可谓经书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
式(16)表明:协同成员pi的知识掌握程度W(pi,K)可表示为协同成员pi与其所掌握的知识点之间的边权权重之和;协同成员pi与其他成员间的关联关系强度W(pi,P)可表示为协同成员pi与其所关联的其他协同成员之间的边权权重之和。
由表3可看出,乳酸菌对SO2含量非常敏感,随着SO2浓度的增加,菌体存活率快速下降。正常苹-乳发酵时,SO2浓度调整为40 mg/L左右,而19株初筛菌的SO2耐受性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根据OD值计算),还有5株菌在SO2浓度为80 mg/L时,菌体吸光度值高于商业菌株(分别为SC-6、SC-9、SC-12、SC-13、SC-14),因此表明上述19株均可以耐受正常苹-乳发酵时的SO2浓度。
“哲学”的译名出自日本启蒙学者西周,他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philosophy”在古希腊文化中的本义是“爱智”之学,而“哲学”译名的“哲”字在中国古经书中的字义就是“智”或“大智”。孔子在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哲人”在中国古经书中释为“贤智之人”,而在“哲学”译名输入中国后即可称为“哲学家”。
正是因为孔子对中国上古文化既有继承亦有创作,在他所实现的“哲学的突破”中既有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亦有思想观念的飞跃,所以可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
《汉书·艺文志》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又有诸子“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之说。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亦云:“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这是讲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西周“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此译名的成立具有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性质。承认“哲学”具有东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方有“哲学”的译名;承认“哲学”亦有东西方文化的特殊性,方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等之名(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于1945年出版之前,西方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梯利的哲学史著作虽然被翻译为《西方哲学史》,但其英文书名却是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罗素将其哲学史著作称为“西方哲学史”,已意味着在西方之外还有东方等国家的哲学史)。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说哲学的“类称”与“特例”(张岱年先生在1930年代中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其“序论”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而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
鱼粉中的苦味物质较多,例如原料鱼在自溶、腐败变化过程,会产生苦味肽之类的物质,同时也会有麻味物质的产生。因此,鱼粉等产品中,苦味、麻味也是对新鲜度判别的指标之一。
“哲学”译名在1895年出现在中文著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十四卷修订本)中。此后,中国学人就开始了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对于“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我认为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如王国维所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就是对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是在与西方哲学的参稽比较中进行的,如王国维所说,“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另一方面也如王国维所说,“余谓不研究哲学则已,苟有研究之者,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这实际上指出了“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学“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源于这种思维方式。
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中没有“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传统的哲学思想。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原善》卷上)我认为,经书和经学中讲“天人之道”的“大训”,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不仅如此,在“子、史、集”中也有讲“天人之道”的“大训”,这些也是中国传统的哲学。
(3) 第三层时间服务:CATS A和CATS B作为NTP服务的服务器端来提供时间服务,所有工作站、LATS和连接信号子网的两个网关(即网关A和网关B)作为NTP服务的客户端来同步两台CATS服务器的时间。
孔子高扬仁学,创建儒家学派,他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述而有作”。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的删述六经,即自觉地“因革损益”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他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既有继承亦有创作。如关于《尚书》,孔子“独存其善,使人知所法”;关于《春秋》,孔子“严其褒贬之辞,使人知所惧”(许谦《读书丛说》卷一)。关于《周易》,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我观其德义耳也”(马王堆帛书《要》)。通过这样一种既有继承亦有创作的方式,孔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实现了中国文化在轴心时期的“温和”的“哲学的突破”。亚斯贝尔斯说:“假如我们关心哲学史,那么轴心期向我们提供了研究我们自己思想的最富有成果和最有收益的领域。”“那是些完成了飞跃的民族,这种飞跃是他们自己过去的直接继续。对他们来说,这一次飞跃如同是第二次诞生。”
乌有先生团团脸,酒糟鼻,胖胖的,就像庙里的弥勒佛,蓄起头发胡子,换下僧袍转行做起道士,艰难的棋局令人费神,弄得他脸上层层油汗。子虚先生清癯、瘦削,好像一只打坐的鹤似的,乌有出子慢吞吞的,他却很快,闪电似的,手指将棋子掣出来,稳稳地弹到棋盘上,棋子就放在他们身边一个荒废的鸟巢里。听到有少年提到媪妇谱,子虚转过脸,淡淡地说:“你会下棋?”
首先,在中国古代教育中,虽然以德行为统率,但也有分科教育的内容。如《周礼·地官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这里,除六德、六行外,“礼、乐、射、御、书、数”当属分科教育的内容。孔门教学,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其中的“艺”即是指“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朱熹《论语集注》)。孔门弟子中,学有成就者如“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其中的“言语”“政事”“文学”也有分科教育的性质。
章学诚又说:“《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文史通义·书教下》)《春秋左传》是以史事解释《春秋》经,而司马迁的《史记》原被归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春秋》类,此即“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在《汉志》之后,才从经部中分出了史部,以后遂有“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西晋时期荀勖、张华编《晋中经簿》始创四分法:“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此中新创的“丙部”即是史部。东晋时期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由此史部称为“乙部”。以后至《隋书·经籍志》乃正式形成“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
虽然经书源于上古,但是“经学开辟时代”则是春秋以降的后“王官之学”时代。此时,“周衰文弊”,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孔子创立民间教育,“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经过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遂形成了经学的六经系统。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六德》和《语丛一》中就有了六部经书的排列。
妻子跟我结婚二十年,我从没给她买过一件金银首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俩结婚,那个时候不兴金银首饰,没听说谁结婚买项链戒指耳环之类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里,金银首饰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应该受到鄙视和唾弃。后来时代变化,金银首饰渐渐地兴起,我们家的经济不宽裕,妻子从来没想过要一件,我就从来没给她买一件。跟妻子一块工作的女同事差不多都有一件两件的,妻子不生羡慕,回家也不跟我说。或许那个时候,在妻子心里金银首饰真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女人一身珠光宝气的,妻子认为俗气。她出门不描眉不施粉,喜欢素面朝天。妻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金银首饰的?难道从她有了皮肤病之后?皮肤病跟金银首饰有什么关联呀!
章学诚又说:“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史通义·诗教上》)这就是说,“集”乃子、史之流衍。后来刘咸炘发挥章学诚之说,亦谓“史、子皆统于经”,“经乃子、史之源”,“集乃子、史之流”。这可以说明,“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源和统率地位。
从对“哲学”的第一方面理解来说,中国的古今学术是连续性的,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就是对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研究;从对“哲学”的第二方面理解来说,这又体现了中国文化在近现代所实现的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到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的转型。
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学术分科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是经史传统,而在戊戌变法之后,在“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的学科体制。一般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学科体制是完全学习西方的,但实际上其中也有中国传统学术的因素。
(1) 本裂缝病害实质为平推式滑坡,主滑方向与临空面走向小角度相交,滑动矢量方向具有运动合成特征,使得其成因机制显得更为复杂。病害的力学机制为滑移——拉裂,运动机制为滑移——翻转。
其次,从图书分类看,《汉书·艺文志》设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中的兵书、数术、方技应属分科著录。在荀勖、张华编《晋中经簿》的四分法中,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隋书·经籍志》),此把兵书、数术、方技合入诸子,遂使分科的性质有所减弱。但在南朝宋王俭的《七志》中,“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同上),这又恢复了兵书、数术、方技的分别著录。至《隋书·经籍志》形成较稳定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与此不同者亦有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其把图书分为12大类,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等各为一类。清代孙星衍在《四库全书》编成后,也提出新图书分类,即以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分部十二”(《孙氏祠堂书目》自序)。
更应重视的是宋代胡瑗主张“明体达用之学”,“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此中的治事斋,“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即是分科教育。朱熹晚年作有《学校贡举私议》,主张“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其中,“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这也是分科教育。
在晚清的学制改革中,“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基本上容纳了西方近代的学科体制,而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曾被作为学制改革的根据。如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关于“定课程”有云:“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
在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进呈学堂章程折》有云:“自司马光有分科取士之说,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于诸经、子、史及时务皆分科限年,以齐其业;外国学堂有所谓分科、选科者,视之最重,意亦正同。”这里的司马光“分科取士”,见《宋史·选举志六》:“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由于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德行明经”一科,又以八股文取士,故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司马光的“分科取士之说”和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都未实行。但他们的思想为中国近现的学制改革提供了合理性的根据,而中国近现代的学科体制亦可视为符合他们思想逻辑进程的发展。
近年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反思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已不再把中国社会学视为完全由西方传入的“舶来品”,而认为中国本土自古就有所谓“群学”。中国近代的严复在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就把“sociology”译为“群学”,梁启超曾盛赞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在西方学者中,英国的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曾明确肯定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费孝通先生晚年多次提到并肯定他的这一论断。在1980年,中国台湾的社会学家卫惠林也指出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关于群学的基本内容,严复和梁启超都从核心概念(“群”“分”“义”)和基本命题(“人生不能无群”“明分使群”“义为能群之本原”)等方面,对荀子的群学作过概括。
主张中国自古就有社会学的学者认为,“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基础”,“才能遵照学术积累规律,使中国社会学具备实现中西会通的必要条件”,“才能明确中国社会学的基因和特色”,“有利于形成和彰显中国社会学的独特优势”。他们的这种认识,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应也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概言之,中国近现代的学制改革与中国的经史传统,也是既有文化赓续的相因连续性,也有时代发展的变革创新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摘自《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
标签:社会学论文; 六艺略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隋书·经籍志》论文; 文史通义论文; 学校贡举私议论文; 六经皆史论文; 章学诚论文; 四部分类论文; 《晋中经簿》论文; 哲学史论文; 分科教育论文; 学术分科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