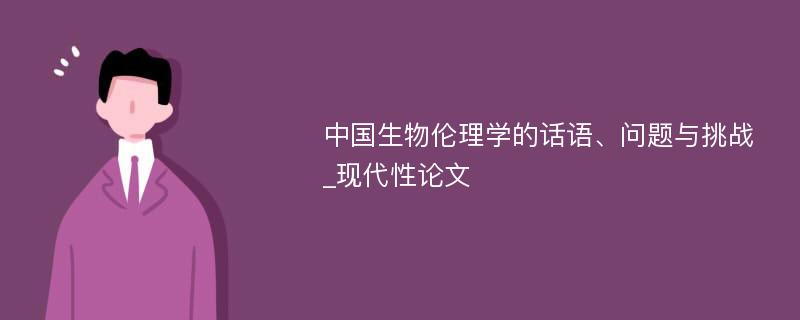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问题和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5939/j.jujsse.2016.01.015 一、话语症候:如何说“中国话” 如何看待生命伦理学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可能”的前提性反思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层面对其“话语”进行还原分析。 先从历史语境看。我们从一种历史的本土知识学的文化语境上产生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问题。一个无需赘言的明面上的事实是:我们所言说的生命伦理学必定是由“中国话语”所铺展的生命伦理学。然而,一个令人感到吊诡同时又发人深省的事实乃是,汉语文化圈中的生命伦理学却一直存在且仍然存在着一个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 一方面,不能否认,生命伦理学是在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中晚出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与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等关涉医疗、卫生保健和人类生命质素之改善的科学技术(包括医学)的最新进步密切相关的跨学科领域和前沿问题领域。它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思想触觉,既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结构,又有后现代性解构批判的锋芒,总是通过追踪最新的生物学(包括遗传学或基因工程)、神经科学、医疗技术等生命科技进步带来的重大难题和挑战以回应“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深度追问,思考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以及回应我们在此时空境域中“应该如何在一起”的前提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两大课题: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压迫?如何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叙事中真实地展开我们自己的生命伦理学话语?这要求我们在话语方式上不能仅停留在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拿来”或“借鉴”,而必须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核心价值层转出一种全球视野和国际表达。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生命伦理学不是一种与本土文化传统或具体历史语境相隔绝的知识领域。生命科技及医疗技术实践的前沿领域的进步,在不断地将我们对身体、卫生保健、生命质量、疾病的意义和死亡的威胁等问题的认知引向深入的同时,敞开了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新维度。如果仅就问题的浅表看,进步似乎给现代人带来了更多的新的选择,并带来了以往未曾遇到过的一系列道德上的两难。但就问题的深层看,它往往又是自古就有的根源性问题,与文化的核心价值、生命的信仰本质和人们理解人性、尊严、公正和健康的生活的理智形式和精神感知息息相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总是在“与己相关”的历史文化境域中产生自己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即使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向往或憧憬依然源自一种浓郁的家园之感和本土文化情结。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文化的理论框架和核心价值,才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或正视的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方面。从这里产生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另外两个至关重大的课题:生命伦理学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变迁及“传统—现代化”的断裂及延续的问题?如何在生命伦理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话语中兼容中国视野和中国表达?这要求我们所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必须立足于中国语境和中国现实。然而,当我们这样说时,前提条件是,而且只能是,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① 从理论逻辑看,生命伦理学从理论话语的逻辑层次上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问题背景是现代性道德世界观的破碎[1]19,人们从各自选取的某些道德理论的片断出发进入生命伦理学论题,带来了恩格尔哈特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领域长期存在的“文化战争”。这在理论逻辑方面,表现为多元化的道德话语之间互不相容、不可通约以及在极为不同的理论层次上相互攻讦的“诸神之争”。中国生命伦理学面对相同或者相似的“文明难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实质上是道德共识之坍塌及理论逻辑之混乱的表现。这无助于生命伦理实践问题的真正解决。比如,它在“应用论”(应用生命伦理学)、“建构论”(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和“实践论”(实践伦理学)等各种理论进路上分出纷繁复杂的理论和方法,以至每一种理论都可以找到理据驳斥其他理论为“不明所以”或“幼稚无聊”。[2]中国生命伦理学因此成为各种理论话语的试验田,且直观地呈现“大杂烩”的知识学面貌。[3]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们从事各种理论方法的创建或论证时,一种质疑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对待的。邱仁宗如是问:“现实的、实际的伦理问题能够从伦理学理论推演出解决办法吗?”[4]这一朴素的追问,指向我们在理论逻辑方面未曾深究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在理论逻辑层面如何学会“说中国话”。 第三,从实践旨趣看。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往往通过具体的生命伦理学论题使价值观得以赋形。因而,人们在解决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问题时,亦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研究表明,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主要体现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要素中。按照易于为人们理解的方式表述,就是四个环节:1)在实践中发现伦理问题;2)对相关理论进行关联分析以澄清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或原则;3)将探究结果转化为政策;4)实现生命伦理学之目的。②在上述诸环节中,实践旨趣所呈现的价值观诉求,既不能脱离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资源性支持,又不能脱离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它所蕴含的价值观赋形其实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关联、反复博弈的价值实现过程。而对于当代中国的总体实践旨趣而言,它的最大的价值实现过程就是“现代化”。明乎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内核就不能脱离“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关切及其问题症结。因此,无论具体情境中的“殊案决疑”,还是对规范和原则的理性论证,抑或是关于信仰问题的深度辩论,各种表面上看来相距甚远(甚至互不相关)的异质性的生命伦理学探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意识到还是未曾意识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轴心展开: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凸显。而与之相关的根本实践旨趣乃是:在“遭遇中国现代性”中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 二、语境难题及“语境突围”的问题 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的“话语症候”的初步分析表明:“语境突围”,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程序共识”和“中国现代性”问题,是推动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关键。循此,透过一种道德形态学的视野,管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谱系,就亟须进一步思考与之相关的紧要问题:1)我们如何寻求“语境突围”?2)我们如何达成“基本共识”?3)我们如何应对“中国现代性”问题? 这三大问题由于关联到中国形态的生命伦理学在“话语”、“理论”、“实践”三个方面碰到的“普遍性—特殊性”之两歧的难题,如何定位这些问题的性质便需要先行予以说明。该问题的详细展开有待于一种“道德形态学”的理论视野之构画。③[5~6]我们这里仅限于指出,“道德形态学”是从物质形式的结构化及其过程出发,对道德话语、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形态过程进行观察或探究。从道德形态学视野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紧要问题,就是从生活世界本身出发揭示那些影响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的改善是如何呈现为相关的话语方式、理论模式和“合理化形式”上的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是如何反作用于那些影响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之改变的。 依此而论,我们需要对中国生命伦理学在道德形态学层面遭遇的“语境难题”进行分析,以回应一个日益紧迫的与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相关的现实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总问题。这个问题的完整表述就是: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寻求“语境突围”? 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双重意义上遭遇“语境难题”。一是在一般的意义上,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本身即是建立在“语境差异”的基础之上,并以解决“语境难题”为优长。二是在相对特别的意义上,中国生命伦理学还面临自身特有的“语境难题”。 就前者而论,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关于生命伦理学的各种定义,就会明了我们遭遇的“语境难题”的症结。生命伦理学通常被理解为:“运用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为、政策等进行的系统研究。”④[7]42克劳泽(Clouser)的定义是:生命伦理学是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医疗卫生领域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8]115~127亚洲生命伦理学联合会给出的定义是:“生命伦理学是从生物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于人类社会和生物圈中提出的哲学的、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治疗的、民族的、宗教的、法律、环境的和其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⑤邱仁宗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解是: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要与其他学科一起合作进行跨学科研究,处于伦理学与科学技术、医学的交集处,是规范性的、理性的、应用性的、世俗性的、讲求证据或立足实践的学科。[3]这些定义(或理解)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相似之处,即强调“跨学科”或“跨文化”的特点,或是同时强调二者。如果从形态学视角看,我们还会发现它在某些论题的探讨或挖掘方面有“跨时代”的一面。[6]这使得生命伦理学往往在极为不同的语境层面展开,其话语的差异性分布异常广阔,涉及科学技术对人类价值之影响的诸领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道德前提、不同价值诉求的实践主体互不相容的诸理论歧见。单就学科层面的语境差异而论,就分为四个公认的研究领域:1)医者与患者间共同面对的临床生命伦理学问题;2)关于律例与指引的规范生命伦理学问题;3)关注理性基础的理论生命伦理学,它来自哲学、神学,但也包括生命科学,如生物学,尤其是在传统医学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基础;4)关注精神基础的文化生命伦理学,它把生命伦理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探讨生命伦理学如何反映主流文化、核心价值和世界观。[6][9]3语境差异从医患关系、政策法规、道德原则,再到文化根据,往往呈现出大异其趣的面貌,且各自在话语方式上也大相径庭。仅就文化根据而论,就呈现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儒家生命伦理学、伊斯兰教生命伦理学等宗教语境层面的区隔。此外,即使处在同一语境层面(例如在医患关系层面),也可再分出普遍主义话语类型和特殊主义话语类型的语境问题。生命伦理学的多重语境及其重组、重叠和分形演化,包括“大语境”或“小语境”的复杂格局,必须看成是它在跨文化条件下的沟通理解、跨学科条件下的交叉凝聚和跨时代条件下的传承转化的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语境差异的存在,才产生了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时代条件下的生命伦理学。这表明,正视语境差异,进而尊重差异,而不是无视差异或削平差异,才是解决“语境突围”的关键。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得以可能的前提。 由此,深入到语境差异发生的肌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语境突围的关键要素在道德形态学视域得到描画。按照笔者一贯的理解,将之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素。第一,通过跨学科条件下的分类方法进行“问题域还原”[10],突破单一学科语境下问题方式的话语僭越。“问题域还原”是要看清楚问题由以发生的语境以避免无谓的纷争,将各学科的话语资源调动起来融入多元视角,将道德见解或行为引向一种伟大的跨学科的智识平台。第二,通过跨文化条件下的比较方法进行“认知旨趣的拓展”[5],突破单一文化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以揭破权力的道德伪装。认知旨趣的拓展就是要突破狭隘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藩篱,真实地面对道德多样性现实,将一种互镜式道德探究和互证式伦理商谈融入伟大的跨文化理解之中,于价值图式上进行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诊断和价值扩展。第三,通过跨时代条件下物质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行道德形态过程的探究,突破单一时代语境下伦理生活的“话语盲从”以祛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话语批判”中锁定“语境突围”的根本目标:应对道德分歧;重新发现传统;通过“道德形态过程”澄清概念。⑥ 对于中国生命伦理学来说,上述一般意义上的“语境难题”同样存在,而且表现日益突出。从生命伦理学由西方发端而扩展成为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它关注的问题是那些跨越文化差异、学科差异乃至于时代差异的关乎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如“知情同意”就被视为一条全球公认的处理医患关系的医学伦理学规范。生命伦理学“四原则”(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也被视为具有标杆性的普遍原则。[11]13应该看到,生命伦理学的这种普遍主义诉求是为了建立一种特定实践的平台。我们称之为西方普遍主义模式。从这种普遍主义话语看,任何一种带限定词的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佛家生命伦理学”乃至“中国生命伦理学”都似乎是多余的。⑦[12]255由此形成了一种“普遍理论—中国应用”的探究模式。简化地表述就是:“1)从与某些社会群体或整个人群的健康、福祉或基本人权相关的伦理问题出发;2)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法律、条例或政策的缺点或不足提出挑战;3)在通过论证和辩护进行伦理学探究或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法律或政策改革的有用建议。”[3]不难看到,这是一种由“问题—挑战—建议”构成的简捷明了的“应用伦理学”范式。然而,它用来鉴定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则主要来自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这产生了从中国视野进行“语境突破”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化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压迫”。 比如说,备受公众指责的“手术签字制度”是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这问题本身就是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压迫下产生出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我国现行的“手术签字制度”具有中国特色。李恩昌等评论说:“知情同意的病人自主模式到中国演变为病人家庭决定模式是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国情的。……家庭的这种功能是西方文化所不能理解也无法给予的。”[13]78~79然而,在2007年发生了“孕妇李丽云致死事件”⑧后,面对公众对现行“手术签字制度”的指责,当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辩称:“……我们国家现行的签字制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国家目前也是实行了手术签字制度。”[13]77这里,我们把这个案例的是非曲直放到一边,单就一项在中国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的知情同意的语境探索模式(即“知情同意的家庭决定模式”)却要用“符合国际惯例”(实际上是符合欧美惯例)的辩词为之进行辩护而言,就足以表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对“中国话语”的压迫。 事实上,一种通过“传统的重新发现”以突破西方普遍主义话语霸权的学术努力,一直是中国生命伦理学为自身条件寻求语境辩护或语境突破的特有方式。它强调从传统或本土的文化视角上理解生命伦理学,遵循“中国传统—现代建构”的建构主义进路。这一进路的探究模式所示范的语境回归(即回归中国传统以开出其现代性样态)使生命伦理学直接面对中国语境中“传统与现代性”的跨时代条件下的伦理生活的根源性难题——即从传统中开出现代性的问题。然而,相对单一的文化视角,使得建构论者所诉诸的“语境突围”策略往往受制于与“语境选择”相伴生的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例如,以目前养老制度改革问题所带来的生命伦理讨论为例,建构论者认为儒家家庭主义理念再加上“孝道”伦理可以为当前中国社会开出“养老”药方——即回归儒化的“家庭养老模式”。然而,这一建议显然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脱节,它更像是从儒家学说中转化出来的一种说教,带有明显的传统话语的压迫性痕迹。 不难看到,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本身特有的语境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话语压迫,即“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特殊主义”。这种日益紧张的“话语张力”,使得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似乎充斥着“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之间无妄的纷争。但换一个视角,透过其背后的语境难题,则不能不承认,它又是一种与“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远见紧密相关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的张力”。在其深层,展现了一种世界历史观下话语展开之可能。可概括为与“语境突围”有关的两句话:一是“世界在中国”(即把世界看成在中国之中的世界);二是“中国在世界”(即把中国看成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前者是通过在语境上突破“特殊主义”的局限,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能够海纳百川,具备包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胸怀,这是我们文化生命的根系之所在。后者是通过对“西方普遍主义”进行解蔽,使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体现中国价值或“说中国话”的同时,真正成为世界或全球生命伦理学跨文化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就是要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既要以“世界在中国”的中国话语转出我们的“国际化表达”,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生命伦理学来消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暴力;另一方面,又要以“中国在世界”的国际视野开放出我们的“中国化表达”,以跨文化对话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应对各种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 三、两大挑战及其应对:基本共识和“中国现代性” 总结起来,话语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性与中国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三大紧要的问题。其中“话语与现实”在道德形态学视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属于道德话语对现实的表征,因而同样也是“理论难题”和“时代性问题”的症候之表征。在这一意义上,问题的性质得到了界划:即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紧要问题,归结起来,集中体现为一个问题,亦即最为突出的问题——“语境突围”问题。“理论/实践”、“传统/现代性”除了作为问题症候呈现在语境层面而外,它们还是用以实现“语境突围”的问题方式。也就是说,它们在更深层次上,展示了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如何实现‘语境突围’”问题上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如何达成基本共识;二是如何应对中国现代性。 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前所未有地遭遇“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挑战。出路在哪里?有各种不同的回答。笔者认为,生命伦理学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只有借助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分层方法”,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找到应对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方法。 事实上,生命伦理学对跨学科、跨文化、跨时代条件下的伦理学问题的探究,有着鲜明的以“实践”为导向(或以“问题”为导向)的特征,已经先行蕴含了求解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线索。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面向实践的学科,它优先强调从实践出发面对道德分歧。在生命伦理学视域中,伦理学问题通常被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实质伦理问题”,回答“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它旨在解决“道德朋友之间”的共识难题。第二层次是“程序伦理问题”,回答“应该怎么做”的程序问题。它旨在解决“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共识难题。两种伦理解决各自范围或各自语境中的共识难题,互不僭越,各得其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分层方法”。 如果将上述伦理分层方法运用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问题上,就会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通过伦理分层界定“大小语境”,是解决“共识难题”的关键;第二,确立“程序伦理”优先于“实质伦理”的分层原则,是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关键。 第一个结论的要点,在于区分“语境的大小”。我们之所以会面临“语境突围”的难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混淆了语境的“大小”。当人们把“小语境”范围内解决“道德朋友”之间共认或共识的理论和原则,放大到去解决大规模陌生人社会(可称之为“大语境”)的道德分歧问题,就会出现“话语压迫”。例如“儒家生命伦理学”有其基于共同理念的“小语境”预设,而当人们主张用儒家家庭主义的理念提供公共保健政策方案就属于“以小搏大”的语境不当了。另一方面,当人们把“大语境”范围内解决“道德异乡人”之间共识难题的标准当做唯一的标准,也会形成“话语压迫”。例如,从西方普遍主义范式衍生出来的应用伦理学模式就完全否认“儒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通过伦理分层方法区分“语境的大小”,正是为了匡正这两种“话语压迫”之偏,以利于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简要言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程序伦理的层面,寻找突破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压迫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从实质伦理的层面,寻找突破中国传统的文化特殊主义话语压迫的路径依赖。 第二个结论的要点,在于确立“语境排序”的原则。“传统与现代性”是中国生命伦理学无可回避的两歧困境。人们常常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说成是“古—今”之异,并混同为“中—西”之别。即,把“中国的”视同为“传统的”(古),把“西方的”视同为“现代性的”(今),再附加上一些价值评判,就很易于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这样一种思考“传统与现代性”的方式,同样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在“语境问题”上遭遇复杂的中国现代性难题。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即从伦理分层的方法视野看,就会发现,“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并非是“古—今”之异,也非是“中—西”之别,它们只不过是“实质伦理”与“程序伦理”在一种社会样态中的语境排序不同而已。所谓“传统”,是指先行预设了“实质伦理问题”优先于“程序伦理问题”的语境排序的一种社会质态或一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人们秉持这种价值理念生活,就是传统类型的人。所谓现代性,则正好与之相反,是指先行预设了“程序伦理问题”优先于“实质伦理问题”的语境排序的一种社会质态或一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同样,现代人类型的存在,亦可从此种生活样式或价值理念获得说明。如此界定“传统与现代性”的相互关系,就不会使“中国现代性”问题陷入“传统与现代性”的过度纠葛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指认,“语境排序”的原则与“语境区分”的原则是紧密相关的,二者提供了实现“语境突围”以推进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原则之指引。 行文至此,想到了孔子的两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对于反省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逻辑及其语境原则,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一句话是说,不要因为“相远之习”的阻隔,而妨碍了“相近之性”的邻近。事实上,一切理论话语上的断裂、异质和分歧,不应该成为人们孤离分隔的原因。如果人们愿意从“相远之习”的内里去理解各种异质性理论话语的背景条件和问题症候,就可能找到尊重差异的契机。第二句话是说,“同而不和”只会谋划一个“小人的国度”,“和而不同”则可成就一个“君子的国度”。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唯有理性地看待人们彼此之间的纷争、歧见和不同,才能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中面对每一种理论的真实关切及其功能展现。“和而不同”是一种君子之风,它要求从尊重差异中求“和谐”、从捍卫多样性中求“完整”。在这一意义上,“和而不同”这条儒家古训,足可以引以为我们面对分歧时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理论话语原则。如果把孔子的这两句话与生命伦理学的两类伦理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实质伦理与“我们应该如何做”的程序伦理)详加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和而不同”的理论逻辑中隐含着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洞见,即“程序伦理”要比“实质伦理”居于优先之地位。如果我们从这一视野正面看待中国现代性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理论话语的意义,那么在“我们应该如何做”的程序伦理方面寻求共认的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或“说中国话”之正题。这就要求,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之下,搁置具体内容的生命伦理学的道德争议,聚焦于一种程序合理性之共识的达成。 注释: ①这个观点受到姚新中教授在南京召开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开课论证会(2014年5月)上的发言所贡献的观点的启发。在此谨致谢忱。 ②上述“四个环节”,来自邱仁宗在2010年新加坡第10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的特邀报告中所论述的关于生命伦理学四要素的基本观点。它实际上是对一种“应用伦理学”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范式的纲领性总结。在笔者看来,这里所说的四环节或四要素,可以看作是在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方面“说中国话”不可或缺的形式构件。但真正要体现这一点,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联和互动是关键。人们很多时候借用的理论往往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一些片断,就会使政策和结论不得要领。邱仁宗在2012年发表的题为《中国发展生命伦理学之路——纪念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30周年》一文中,将四要素概括为:1)生命伦理学的第一要素是:鉴定实践中的伦理问题;2)生命伦理学的第二要素是:进行伦理学探究;3)生命伦理学的第三要素是:将探究结果转化为政策;4)生命伦理学的第四要素:实现关怀人(包括病人、受试者、医务人员)的生命、健康和权利,并善待动物、保护生态的根本目的。笔者认为,这里列举的四要素虽然体现的是一种“实践导向”或“问题导向”的生命伦理学进路,但不难看到,每一环节或每一要素实际上都离不开理论。而隐蔽于其中的理论又主要地是从西方生命伦理学那里转化而来。因此,笔者将邱仁宗开拓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道路归类在“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之下,它的重点是“应用”,但却是有其普遍主义理论之预设,是一种“普遍理论—中国应用”的研究进路。参见参考文献[4]。 ③关于“道德形态学”的讨论虽然不是本文的任务,却是笔者近年来试图开拓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学研究”的研究中,课题组围绕这一论题进行了多次讨论。笔者在《中国生命伦理学认知旨趣之拓展》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两篇论文中,对“道德形态学”都有所论及。特别是后一篇论文,进行了一些核心观点的提炼。然而,这个新视角或新方法仍然处于探索之中,许多提法还很不成熟。本文只是从核心理论原则的意义上提及这一研究方法可能开出的理解性视角,并不展开相关论述。为便于理解,本文将《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中的一个脚注援引如下:“形态学(Morphology)最初是生物学用来探究生物群落复杂性及其演化的方法。达尔文称之为‘博物学的灵魂’。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广泛用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医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形态学视角,激发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城市建筑学家、艺术学家的想象力。‘形态学’在这些领域的引入,拓展了极为不同的知识旨趣或学科发展,且在研究方法和关注方式上引发了科学性的变革及探究视角的突破。” ④这个定义是一个广被引用的关于“生命伦理学是什么”的词典定义(出自美国《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 ⑤这个定义遭到了邱仁宗的批评。在2015年发表的《理解生命伦理学》一文中,邱仁宗引述该定义后写道:“按照这样一个定义,生命伦理学不就变成了一碗杂碎汤吗?事实也果真如此:在一些号称生命伦理学的学术会议上,大家的讨论发言所涉领域杂而广,真正认真研究生命伦理学问题的实在不多”。见参考文献[3]。 ⑥生命伦理学在话语层面进行“语境突围”是其道德形态学探究的首要关切。此处对其基本要素的概述集中在三个要点上,即跨学科条件下的“问题域还原”,跨文化条件下的“认知旨趣之拓展”,跨时代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话语批判”。笔者认为,这正是生命伦理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特的学科”(邱仁宗语)的“独特”之处。它们是笔者理解“道德形态学”基本理念的进路。三个方面的比较详细的讨论分别由三篇单独的论文提供。其中,关于“问题域还原”和“认知旨趣之拓展”的论述,已有公开发表的两篇专题论文讨论(见前面两个注释)。“社会经济形态的话语批判”的讨论将在近期完成、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这些相关研究。这里笔者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道德形态学对“语境”的强调,着眼点和出发点是从“话语生产”的物质形式出发看待道德事实,因而与生命伦理学的“原则主义”进路正好相反。从对语境问题的强调,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原则主义进路的真正关切,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地批评它的比较明显的偏失。 ⑦张颖在《从墨家思想看中国的医疗改革》一文中表达了普遍主义话语隐含着的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表述的否定。国内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进路基本上持这种观点。 ⑧这一事件的概要是,因李的“丈夫”肖志军拒绝签字,医院放弃救治,导致李丽云及腹中胎儿死亡。案例的详细描述见参考文献[13]第78~79页。标签:现代性论文; 伦理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伦理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语境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