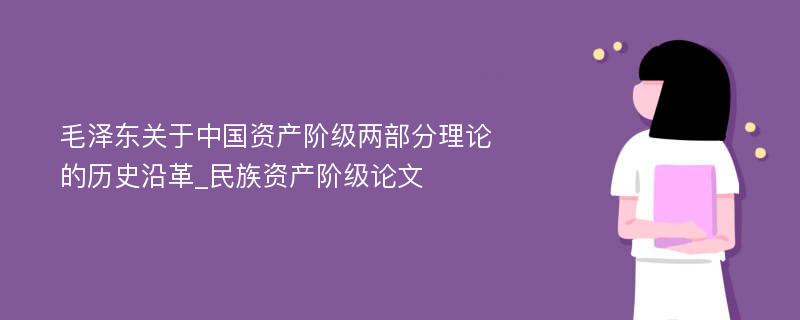
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理论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阶级论文,中国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是一个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重大变化,并因此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重要理论。因此,根据原版的毛泽东著作,认真系统地考察这一理论的演变过程,真正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对于进一步推进“毛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国共关系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都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从本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演变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六个时期。这就是:
一、初始期(1923—1928年)
1923年7月,毛泽东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 首次提出了其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最初理论。他说:“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1〕这样, 他就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初步地作出了“商人”和“官僚资本家”这种划分。在这里,他所说的“商人”,不仅包括了本来意义上的商人(买卖人),而且还包括了制造商,如上海总商会的会员等,即均在这种“商人”之列。〔2〕他认为,“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 商人是“领袖全国国民”的革命领导力量。〔3 〕他在此使用的“官僚资本家”一词,则源于陈独秀。1923年4月, 陈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曾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了三个组成部分,并首次提出:“官僚的资产阶级”“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4〕
1923年底,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首次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明确地划分为了“官僚资产阶级”和“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两个组成部分。〔5〕一年后, 中共“四大”决议案则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了“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6 〕在此背景下,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 毛泽东先后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926年2月,1926年3月,共三版)、《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 月)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1月)等文中, 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其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其中提出:
(1)“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 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7 〕“大资产阶级”还包括有:“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8〕“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国资本有关系, 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9 〕“中产阶级”则还包括有:“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10〕
(2)“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它“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11〕
(3)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 但“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以商业论,固然许多商人是洋货商土货商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有些商店的店内,是一部摆设着土货,一部分又摆设着洋货。……这类人并不是纯粹民族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乃是中产阶级右翼”。“中产阶级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如国货商等即在此列。“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去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12〕
毛泽东的这一分析,较之过去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同时,这一分析显然又是很不成熟和有严重缺陷的。譬如,简单地根据财富的多少就将地主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并将军阀、官僚、政客、大律师、一部分教授和留学生等也简单地列入大资产阶级的范畴,这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上都是错误的。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面和历史地位,也显然缺乏应有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毛泽东不久后即开始给予了部分的解决,例如,至少从1926年9月起, 毛泽东已将地主和封建军阀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中剔出,并将其完全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13〕
二、否定期(1930—1934年)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至1930年春,毛泽东在总体上依然坚持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但从1930年5 月起(以《反对本本主义》为标志)至1934年,也许是受到了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和势力的影响与压力,毛泽东却又放弃了这一理论,转而只讲一个“资产阶级”。〔14〕由此,对于1927年的事变,他也不再认为是“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领导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15〕而是认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建立了“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16〕当时,他一方面在根据地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主张“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17〕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认为资产阶级是“反革命”,主张“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对“资产阶级”实行“工农民主专政”。〔18〕当然,毛泽东对于“两个部分”的理论的否定,并不像“左”倾路线的代表者那样彻底。如1933年10月,他就曾主张“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但不没收“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19〕只是,这种比较模糊的“两个部分”的划分,在他当时的著述中,并不占居主要地位。
三、恢复和初步发展期(1935—1939年)
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再度提出和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的不同,重新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与买办阶级的反动性。这是其“两个部分”的理论得以重新恢复和初步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买办阶级的认识,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曲折演变的发展阶段。1935年底,毛泽东曾提出:买办阶级是一个反动阶级;虽然“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但是,这种明争暗斗,却不是什么“参加革命”或“革命性”的表现,而不过是一种“狗打架”的事情罢了。〔20〕然而,到了1936年底,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时,他的认识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说:“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带买办性与封建性的大资产阶级,虽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这个革命战争,然而由于他们的自私自利性与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21〕这样,虽然仍在讲买办性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却在事实上成了首要的东西了: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也都具有“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也都可以在某种历史时机“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而后到了1938年和1939年(10—12月除外),毛泽东对于“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则连提都不提了。这一点,虽然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因为他还在提“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后来对大资产阶级认识的根本改变却表明,在这种“只字不提”的状态背后,毛泽东已在考虑:是否应将以正在抗战的国民党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列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
四、重大变动与初步成熟期(1939—1943年)
这一时期,又明显地分为两个不同的重要阶段,这就是:
第一阶段: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原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初稿)》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三篇系统的理论著作。在这三篇著作中,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同前一时期相比,发生了如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变化。这就是:
第一,在长期不提买办阶级之后,又再度明确地肯定了“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22〕
第二,更重要的是,经过长期的考虑、酝酿,终于将大资产阶级从买办阶级的行列中划出,归入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23〕
第三,由于已将被认为有一定革命性的大资产阶级从买办阶级的行列中划出,所以改变了1936年12月提出的关于买办阶级也能够在某种历史时机“参加”和“领导”革命战争的观点,认为,虽然属于一定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在极小程度上与极短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由于“买办阶级决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所以,这种“参加”并不表明这个阶级还有任何的“革命性”,它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24〕
第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作了某些更充分的阐述。但由于已把大资产阶级归入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所以,一方面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现已“掌握政权”,而其“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只在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才存在;另一方面又不仅讲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而且更提出并一再讲到了它的“反动性”。而其总的估价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或两面性),虽然存在于一身之中,但其表现是有时间性的。在同一时间内,或者以发挥其革命性为主,而以发挥其反动性为辅;或者以发挥其反动性为主,但也并未消失其革命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历史行程已经把这个阶级的革命可能性完全使用枯竭之时,到了那时,它们所有的就只剩下反动的可能性了。”〔25〕这显然是严重的强调了它的“反动性”的一面。
第五,在经济方面,首次从“操纵国民生计”与“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角度,区分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两个部分,认为前者应予没收,后者则应允许其发展。〔26〕而这实际就是后来明确地从“垄断资本”与“自由资本”的角度区分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的最初原型。
第二阶段:1940年3月至1943年。 这一阶段是以将大资产阶级重新归入买办阶级的范畴,进而达到理论上的初步稳定(成熟)为其主要标志的。具体说来,主要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这就是:
第一,受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强烈影响,以1940年3月11 日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为标志,开始把大资产阶级从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划出,重新归入了买办阶级的范畴。〔27〕随后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修订本,对于这种新的理论认识,又作了着重说明,重新提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 大资产阶级历来……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28〕
第二,由于将大资产阶级重新归入买办阶级的范畴,所以,对于买办阶级的两面性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即,一方面,修正了以往关于属于一定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阶级仅仅可能“在极小程度上与极短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战线的观点,而将其改为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战线。〔29〕因为,如果说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只能在“极小程度上与极短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战线,那显然是不合乎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与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认为前者依然是一个两面性的阶级,而它的抗日与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30〕不过,这种两面性,同原来认为它所具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第三,对大资产阶级认识的改变,也直接导致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的重要改变。由于大资产阶级已被从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划出,所以,毛泽东这时转而认为:“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同时,也是由于把具有“反动性”的大资产阶级剔了出来,所以,他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含义,这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不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动性”,而只是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有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31〕
第四,由于大资产阶级是“操纵国民生计”的、垄断性的,所以,在把大资产阶级从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划出后,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只剩下了“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非垄断性的部分了。由此,1941年4 月,毛泽东便首次使用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一词,认为中国应该“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32〕这样,他就向着从“垄断资本”与“自由资本”的角度划分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五、基本成熟期(1944—1947年)
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着重从经济角度进一步区分和认识了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其主要进展包括:
第一,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虑,于1944年夏季,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官僚资本”(全称为“买办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这样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33〕1945年4月, 对此解释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而私人资本主义,则是“本国的资本主义”。〔34〕1947年底,又进一步解释说:官僚资本,就是与国家政权、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阶级紧密结合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35〕
第二,继1941年首提“自由资本主义”之后,到1945年的“七大”期间,又进一步地提出并广泛地使用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概念;同时,又首次明确地指出:“官僚资本,……垄断着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36〕当时的一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解放日报》社论,曾对此解释说:“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有垄断独占、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这两种资本主义必须严格的区分开来。”“在我国,因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种垄断的、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表现为与大地主结合的大买办大银行的官僚资本”。而与这个垄断资本相对立的,就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我们所要发展和必须发展的,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37〕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已完全自觉地把列宁关于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运用到他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理论中来了。特别是,在毛泽东说来,“垄断资本”与“自由资本”这时已明确地取代“买办”与“民族”、“大资”与“中资”、“官僚”与“私人”等等界线,而成为了划分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主要界线。
第三,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毛泽东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的不同历史地位的认识,这时也大大地发展了。他说: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同时,它又“替新民主主义革命(注意: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38〕而自由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进步性质的资本主义”。〔39〕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40〕“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41〕“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42〕因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使其“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43〕
最后,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大资产阶级的认识,还曾发生过重要的变化。例如,重庆谈判后,他即曾说过:我看,现在是有蒋(介石)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44〕政协协议签署后,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又说:“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分子”“要求”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45〕这就是说,“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政治代表,也是能够“实行民主改革”即参加革命的;而这当然是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意见的。只是,在这一时期,他的这种观点是短暂易逝的,在总体上并不占居主导地位。
六、“修正”期(1948—1957年)
1948年9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开始转变为了初级社会主义理论。〔46〕1952年9月,毛泽东又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开始从“新经济政策”式的初级社会主义转向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47〕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两个部分”的理论,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而其内容,主要就是对其关于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一再“修正”。这就是:
第一,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工业、大银行、 大商业不管是否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是要没收的。〔48〕这就是说,对于为数不多的“民族大资产阶级”〔49〕的资产,也要予以没收。这一点,是过去没有说过或没有明确说过的。但到了七届二中全会,对大资产的“没收”政策,又改为了“限制”政策,同时强调:“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50〕
第二,在1948年9月会议上提出:现在, 是有条有理地向官僚资本及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进攻,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则根本不是进攻,而是合作妥协。〔51〕这就在并不居于垄断地位的私人资本当中,又划出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这样两个部分,并对前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随后,在致刘少奇的一封信中又进一步提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52〕
第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又将限制政策的适用范围,进一步地扩大到了包括“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在内的整个私人资本。明确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都是要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的。”〔53〕显然,这同《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节制资本”政策的本意及让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主张,已经有了原则的区别。
第四,作为这一限制政策的基础与先导,还在1947年10月,即已放弃了“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的主张,转而提出可使之在政府法令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54〕这一转变,实际是导致1948年9月起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理论政策发生一系列改变的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因而,究其实质来说,它是属于1948 年9月以后的思想体系的)。基于这种认识,建国初期出版《毛选》前三卷时,更将原版的《论联合政府》中的“广大发展”的提法统统删除,而改为了“必要的发展”和“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发展”,并将“发展资本主义”改为了“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但在修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仍然保留了“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提法。
第五,在这一时期,直到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仍时常使用“自由资产阶级”一词。如在原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有三处使用了这个词。但从《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起,便不再使用这个词,而一律改用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随后,在编辑《毛选》1—3卷时,又将原文中的这个名词尽可能地改为了“民族资产阶级”。如在原版的《论联合政府》中有7处使用了“自由资产阶级”一词, 而无一处使用“民族资产阶级”一词,〔55〕但在建国初期出版的《毛选》第3卷中, 这7处中就有6处被改为了“民族资产阶级”。1960年出版的《毛选》第四卷,则更将原文中的“自由资产阶级”,一律改为了“民族资产阶级”。这样,毛泽东就大大地弱化了从“垄断”与“自由”的角度对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划分,重新强调了从“官僚买办”与“民族”的角度所作的划分。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显然与否定“广大发展”,以至最后否定私人资本有关。因为,众所周知,自由资本主义是进步的资本主义。这样,如果强调民族资本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那就必然会承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不可能去掩饰和否认这一结论。所以,尽量不提“自由资产阶级”,这实际正是在淡化民族资本的自由资本的属性和由此而来的进步性,从而为否定“广大发展”以至最后提出消灭自由资本主义,默默地开辟了道路。
第六,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中, 又将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存在和发展的时间,由原来所说的几十年到一百年,〔56〕缩减为了大约15年〔57〕。1952年9月初, 则将这一时间进一步缩减到了“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58〕
第七,由强化限制政策逐渐走向了消灭政策。如1952年3月, 明确提出要“逐步缩小私营商业”〔59〕随后,又表示现在是“削弱资产阶级”。〔60〕同年4月, 默认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的提法。〔61〕9月24日,更开始逐步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要求从现在起即开始逐步消灭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翌年6月, 明确提出:“要把资产阶级看成一个敌对阶级”。〔62〕到1956年,已将中国大陆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基本消灭。同年年底,开始发现这种做法有问题,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63〕但这一势头,很快就被中断,以至最后爆发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化大革命”。
注释:
〔1〕〔2〕〔3〕见《向导》第31、32合期。 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4〕见《向导》第22期。
〔5〕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12.1),《前锋》第2号。〔6 〕中共“四大”:《对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1925.1)。
〔7〕〔8〕〔9〕〔10〕〔11〕〔1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2.1), 《中国农民》第2期。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13〕见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1),《农民运动》第8期。
〔14 〕见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1930.5)、《寻乌调查》(1930.5)、《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1933.8.12)、《今年的选举》(1933.9.6)、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词》(1934.1.24)、 《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1934.1.24—25)等文。
〔15 〕毛泽东:《政治任务及边界党的任务》(1928.10.5)。
〔16〕〔17〕〔18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1.24—25),《红色中华》,1934年1月26日。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19〕毛泽东:《一方面军总前委来信》(1933.10.19)。
〔20〕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30、131页。
〔2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 年版第597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2〕〔23〕〔24〕〔25〕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初稿)》(1939.12)。《共产党人》第5期。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1.15 ),《解放》周刊,第98、99合期。〔27〕〔30〕详见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 见《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致肖向荣》(1940 年。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1—162页)、《中央关于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指示》(1941年5月8日。见《毛泽东选集》(下)。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
〔28〕〔29〕〔31〕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0年修订本),《毛泽东选集》(卷二)。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版,第71,71,7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32〕毛泽东:《〈农村调查〉的跋》(1941.4.19),《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172页。
〔33〕〔39〕〔49〕见1944年毛泽东与根舍·斯坦因的谈话。许之桢编译:《毛泽东印象记》,东北书店1947年版,第27,25页。并见《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1944.7.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46页。
〔34〕〔36〕〔40〕〔43〕〔44〕〔5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4.24),《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35〕〔38〕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25),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8年1月1日。
〔37〕社论:《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解放日报》,1945年6月21日。
〔41〕〔42〕1944—1945年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260页。
〔44〕〔48〕〔51〕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544,545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45 〕见《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2.1)和《中央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面转变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1946.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19、321、325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46〕〔47 〕〔56〕详见或参见拙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608,608—631,134—142页。
〔50〕〔53〕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3.5)。这些引文是原文。修改后的文字请见《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 第1322,1321—132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54 〕转引自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57 〕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58〕毛泽东:《致黄炎培》(1952.9.5),《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页。
〔5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8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60〕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67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61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第376—377页。
〔62〕转引自庞松、 王东著:《滑轨与嬗变》。第113页。
〔63〕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谈话。《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标签:民族资产阶级论文;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毛泽东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阶级划分论文; 论联合政府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