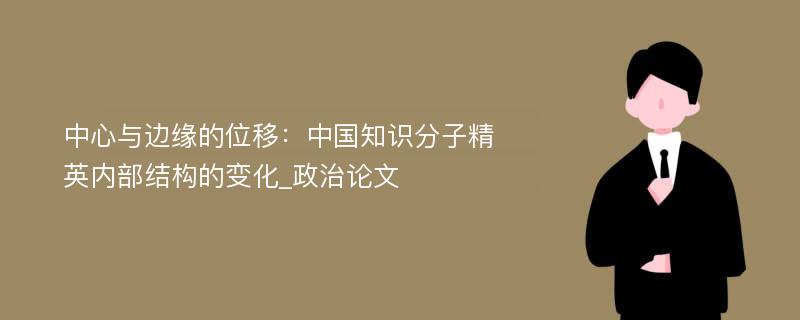
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国知识精英内部结构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位移论文,中国论文,内部结构论文,边缘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的两大系统——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以及知识主体(知识分子)的两大群体——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结构关系的变化;亦即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科技知识及科技知识分子的中心化,我认为这不只是知识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型,而且关涉到社会结构尤其是政治权力结构及其合法化机制的转换。
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及其角色蜕变
从中国历史上看,人文知识分子队伍的庞大与科技知识分子队伍的萎缩恰成鲜明对照。人文知识(文史哲)历来占据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而人文知识分子几乎垄断了知识分子精英的宝座,而且作为政治精英的“后备军”而贴近政治权力中心。科技知识则处于知识话语系统的边缘,科技知识分子大多作为手工艺人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更无望成为政治精英。他们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在知识精英结构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以至于“士大夫”这一标识知识分子阶层的名词几乎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同义语。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尤其是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机制决定的。古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伦理哲学,统治阶级以礼义治天下,社会各阶层以礼义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这一方面使得人文知识的主干——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义心性之学不仅与权力中心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而且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价值依据与身份标志;另一方面则使人文知识异化内赤裸裸的权力话语,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规范作用,它简直就是法律。由此导致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同一,人文知识(儒家礼义心性之学)成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同必修课,人文知识分子在转变为政治官僚时不必在知识结构上作相应的调整,因为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同一种东西。由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一套人文知识话语,而不是社会的经济状况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所以科技知识无法被纳入权力中心的运作系统之中,科技知识分子也就只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匠人”。
从知识及知识分子与社会一般成员的价值观念的关系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人生价值理想有一定的普及性,所以老百姓对于物质生活水平要求不高,更加上进入仕途的道路是由儒家经典铺就的,因而使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普遍的价值标准,使得普通社会成员对人文知识的需求超过了对科技知识(具有物质生活层次上的实用意义)的需求,也使得人文知识分子在他们心目中更值得崇敬。
这种状况至近现代仍无根本改变。诚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无情的事实反复证明:传统中国的礼义心性之学在面对坚甲利炮时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满腹经纶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难以承当现代化的使命。但是血淋淋的事实并没有使当时的士大夫普遍认识到传统人文基本价值的危机,以及知识精英整体结构与现代化的不适应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伦理道德、西方的科学技术”仍是士大夫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很有意思的是:五四精英们否定了洋务派和改良派的发展军工和改革体制的社会改造方案,倡言文化革命,即全盘反传统;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样,虽然五四知识精英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上与传统士大夫水火不容,但却遵循了一种共同的思维定势: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更紧密相关,因而在知识体系中地位更高。
人文知识的这种霸主地位在以下两个事实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一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表明科学在当时是作为人文科学话语而参与了文化革命,它已发生了质变,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唯科学主义就是这种质变了的人文科学话语,科学被认为是解决世界与人生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它不但可以认识世界、创造物质财富,更可以改造社会、建构价值理想和人生意义,而它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作用则是可以打倒和取代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中国人文知识。因而科学在当时是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一种新宗教(参阅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那场以科学的凯旋而告终的科玄论战中,科学话语正是以其质变为代价而大获全胜的,它实际上成了与玄学同质的话语,这种胜利不是科学话语对人文话语的胜利,而是一种人文话语对另一种人文话语的胜利,真正的科技知识在当时实际上仍处于边缘地位。同样,科技知识的变质必然伴随科技精英的质变,参加科玄论战的成员中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象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是丁文江、任鸿隽和唐钺等科学家(也许学心理学的唐钺不能算典型的科学家,因为心理学的学科归属不明)。而实际上,当丁、任、唐三位在论战中已变成人文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讲的是人文科学话语。他们三人之所以能进入当时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恰好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角色转换,这样看来,科玄之战也可以说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它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当时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巨擘陈、胡等的支持。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霸主地位在此表现得相当明显。
第二个事实是:不少留学海外的知识精英都有一个弃科技从人文的“转业”过程,如鲁迅、郭沫若、夏衍、李达等。单以创造社为例,创造社的几员大将中郭沫若原学医,张资平原学地质,成仿吾原学兵工,郁达夫原学经管。但后来都改而献身人文科学的重要分支——文学。郑伯奇对个中缘由有一个解释:“……他们所学的和以后所从事的行道为什么差距这么远呢?如果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那就会毫不奇怪了。他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他们自然不能不受这时代潮流的影响。……但是在相当长的学习时间,国内外的形势在变化,时代思潮也在不断变化,他们不能不受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是深刻而剧烈的。这就是他们对于自己以前所选择的道路不能不发生矛盾和苦闷。(《忆创选社》)郑伯奇所说的“时代思潮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短暂的实业救国思潮很快又被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所取代,创造社成员的转向与鲁迅的弃医从文从动机上说是一致的,而这种动机又反映了社会的风尚。当时的知识精英普遍认为:改造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唤起民众,即思想革命、重铸国魂,而不是发展经济,人文知识分子藉此而占居了文化的中心。
1949年,拉开了历史的新的一幕,但知识精英的内部结构尤其是其与权力中心的关系仍然没有重大调整。中国社会的性质虽然变了,但政权的合法化基础未变,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承诺,它过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革命的合法化基础,现在也仍是共产党维持其领导权的合法化基础,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是以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为标志,而它正是属于中国式的人文知识,正要靠中国式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建构。这样人文科学领域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就正好证明中央对它的重视,证明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关系的紧密,表明人文知识仍处于知识体系的核心,它实际上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而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运作。
人文知识的地位当然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表面看来,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似乎要超过对科技知识分子的批判,思想改造的对象、历次运动中受批判的靶子从来都是人文知识分子;但不要忘了,不断地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恰恰也是人文知识分子。人文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这种“同构性”不禁使人想起古代的士大夫。反观科技知识分子,他们确实没有成为思想批判的靶子,但也绝少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或成为政治精英,这表明了他们与政治权力处于相对远的关系中,表明了科技知识不象人文知识那样被直接用于政权合法化的基础。实际上,自49年到8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内,政权的合法化基础始终不是物质生活的承诺,而是意识形态承诺,所以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一直未能成为政权合法化的核心内容,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把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意识形态承诺对立起来,于是就有对“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的批判,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为的二难选择。这样,以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社会功能的科技知识自然难以进入知识体系的核心,科技精英也难以转化为政治精英。
社会转型与科技知识分子的崛起
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了深刻的转型,它对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知识的内部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一系列的相应转化。但是,由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这种知识转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当80年代初中期,转型主要表现为对作为整体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以及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就象当时拨乱反正的整个思想解放运动一样,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社会转型除了农村改革以外,还基本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地进入操作的、实践的层次。就知识的内部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内部结构而言,原先以人文知识和人文知识为中心的局面尚未发生大的变化;原因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是思想解放的口号,是社会转型的舆论准备,它作为用以转换、消解和颠覆原先的以政治为中心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由人文知识分子去建构和阐释。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扮演着比科技知识、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角色,文学、美学、哲学、史学一时成为显学,文学领域关于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的讨论、哲学中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史学领域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一时热闹非凡,它依然作为一种与政治权力中心关系紧密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担当了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多重使命,人文科学呈现少有的繁荣局面。
在文学创作领域,连续不断的轰动效应持续了四、五年之久,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重放的鲜花”、朦胧诗等等,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现在看来大多已相当平庸,但在当时却因其巨大的社会批判、历史反思的力量而频频轰动、广为传诵。它表明当时的中国人(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意识形态热情和政治热情,务实的、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尚未形成(至少是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政治的中心和老百姓生活的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所以能保持其中心地位的社会原因。
知识及知识分子内部结构的真正转换开始于社会转型的第二阶段,大约是开始于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社会转型已从思想转型、观念转型进入全方位的社会结构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成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动,科技知识不再只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生产过程和经济发展动力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已不再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而是可以计量、可以感受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当一种政权不再以关于意识形态的论争为其权力运作的主要方向和途径,不再以意识形态承诺为其合法化基础,而转向发展经济时,它就很容易地发现:经济的增长与科技知识的关系是直接而且紧密的,而与人文知识的关系则是间接的、松散的,尤其是在人文知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文学科领域的论争和探讨,常常直接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为政治服务,也可以干扰政治。这样,在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已不再成为第一需要的时候,对于意识形态和重大人文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悬置和淡化(“不争论”)。这样一来,科技知识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取代了原先人文知识与之的关系,相应地,科技精英大规模地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成为政治精英。这与传统中国社会包括解放后30年中政治精英的来源恰好成为鲜明的对比。当一个国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其中心时,管理国家所需的自然就不会再是高谈阔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了。
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还更深刻地表现在全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如果说解放后30年的中国社会是大一统的政治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活动都表现为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社会上流行的是高度政治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价值观,那么,8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价值观逐渐地由盛而衰,由衰而绝,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它是中国当今社会由政治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消费时代大众生活的杠杆是欲望,动力是金钱,而其生活方式则是赚钱。实利原则、现世原则取代了原有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消费时代的大众不关心精神、灵魂、意义或超越,他们只关心物质、欲望、现实,对意识形态以至一切人文价值的冷漠成为一代风尚。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与社会大众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任何知识活动都有广泛深厚的社会文化关联域,而不是空中之物,知识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需要的支持,才能有发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地位关系常常和它们与文化价值、大众需要的关系紧密相连。巴伯曾列举五种有利于科学知识发展的文化价值,即:合理性(理性化)、功利主义、普遍主义、个人主义、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它们基本上与我国当前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市民生活观念是吻合的,而情感主义、审美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等级制和权威主义已经并将继续失去它的信奉者,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成为时代主题。人们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乐、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收入的微薄提高却会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这就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人生哲学。
大众需要的变化引发了他们对知识与知识分子评价的改变。当他们以实用的观念和尺度来衡量知识的地位与作用时,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敌不过务实的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以其贴近现实生活、具有直接而明显的实用功能而大获大众的青睐。人们乐于从各种生活常识类的科技读物(生活小窍门)中或通过专家咨询热线向技术专家请教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法,而不再到哲学大师的格言或作家诗人的作品中寻找人生的真谛、生活的意义。在广播与电视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的听众(一种巧妙的商品推销术),足见大众的生活“导师”已不再象从前那样是人文知识分子,今日的大众导师是知道如何调节心理、合理治家、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修理冰箱、彩电、洗衣机,如何保养身体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的移位不是表明了两种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么?大众消费社会给人文知识分子留下的恐怕只有大众文化的生产和解说这一席之地了,而大众文化作为无深度的能指游戏、形象碎片,实际上已不再能回答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超越性的精神问题,它不过是供感官消遣的商品,它所满足的与其说是精神需要,还不如说是生理需要。
人文知识分子及人文知识地位的式微还来自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带来的冲击。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意味着把它们象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听凭顾客的选择和供求关系的判决。这样一来,不但谈论价值、意义、理想等虚无飘渺的话题的人文知识分子无用武之地,而且也使得没有直接应用价值、不能立即创造经济价值的理论科学知识前景不妙。由讲求实用和物质享受的大众组成的当今中国市场,不会有太多的顾客需要康德、黑格尔或哥德巴赫猜想。于是乎,作为直接的生产力、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或能直接解决大众生活问题的技术知识分子,而且也只有他们,在市场中独占鳌头、如鱼得水。人文知识分子甚至从事理论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只能是要么甘于清贫坐冷板凳,要么改行下海这么一种严峻的选择。知识的市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曾有的新生事物,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知识内部人文与科技两大分支的地位,从来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霸主地位,都不是市场给予的,而恰好是由非市场的力量保证的,而今,市场将要剥夺他们的霸主地位了。
人文知识分子的出路:走向独立而不是重返中心
在理性地检讨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带来的知识结构及精英结构的转变时,必须首先肯定这是顺应现代化需要的进步历史潮流。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以及以政治为本位的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已被历史证明难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这样,以这种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为基础形成的人文科学霸权也就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必须认识到:人文知识以及人文知识精英的中心地位是以其御用化为代价而取得的,它们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了其自身独立品格、自主精神及自身话语规则的丧失。人文知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同构、人文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界线不清在为它们(他们)赢得昔日显赫地位的同时,也埋下了它们(他们)今日尴尬处境的种子。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以及政权合法化基础的转移使得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有的与政治中心的紧密关系,市场的经济实用主义不利于没有竞争能力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没有独立品格和自身话语规则的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自然茫然无依、处境堪忧。
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今日的冷寂与其昔日的荣耀一样是不正常的。因为它昔日的政治依附性不仅使之不正常地占居了知识体系的绝对中心,同时还使之一直未能确立自己的规范、赢得自己本应赢得的地盘。人文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的知识,它回答人类生存中带根本性、超越性的精神问题,人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阐释者,这样一种学科定位与角色定位既限定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活动范围,也为之确立了自己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存在价值。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存在价值是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科技知识、科技精英的作用和存在价值同样如此。只有保持这两者在知识体系内部和精英结构内部的动态平衡,防止单方的恶性膨胀,才能使知识的推进保持最优状态。更宏观一点看,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成为相互独立、有自身游戏规则和价值轴心的互补结构,政治对经济文化的僭越(如传统中国社会)以及经济对政治文化的僭越(今天中国已露此端倪)都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中国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结构与大众生活理想不但影响了科技的发展,而且扼杀了人文学科独立生长发育的可能性,如今的社会转型合理地限制了政治话语的畸形膨胀,为科技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然而科技知识及技术专家的作用不是万能的,他们的权力也不应当是无限制的。谁来限制技术专家及技术官僚?在科技的高速发展引发大量伦理道德问题的当今西方,这已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文化哲学问题。英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在其合著的最新著作《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提到:由高科技(如生物工程)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将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重新唤醒人们对一般伦理原则的关心。世界各国不得不在学校里提高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的地位。美国的许多医院、监狱、公司甚至美国国会,都雇用了哲学家来提供决策咨询(见《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这是人文知识精英重返政治权力中心、人文关怀重新成为社会热点的重要信号。
当然,我们重提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并不是要让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再次登上中心宝座,我们只是要让人文知识及人文精英赢得自己独立的、应有的一席之地。历史已经表明:人文知识昨日的意识形态化、人文知识分子昨日的政治官僚化,使之在获得中心地位的同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实用性,使之难以在超越的、非实用的立场上,用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独立话语来阐释它应予阐释的问题、完成它本应完成的使命,这种知识话语本身的严重缺陷实际上已经造成国人精神世界的严重缺陷和价值世界的严重迷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经济实用主义、坑蒙拐骗在商品经济发轫时期的中国固然难以避免,但没有来自文化领域的有力批判,就有些不正常了。它表明伦理道德与精神文明讲了几千年的中国,实际上所缺乏的正是深切而执着的人文精神以及抵制全面商品化倾向的能力。为什么中国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雄霸知识界几千年,却没有建构起强有力的人文价值?原因即在于它的政治依附品格剥夺了其独立性和自身话语规范,以至于政治信念的危机总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人文价值危机(“礼崩乐坏”)。在此与西方的两点比较或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第一,在西方资本主义初始阶段,新教伦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商品化的批判曾极大地扼止了拜多主义与享乐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与美学更是对物质文明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它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方面。第二,西方政治制度与政治信念的改变并不引发全面的文化价值危机,除个别情况以外,政权的更替与文化传统的延续并行不悖,文化领域的转型也是在独立的轨道上进行。这两点都是得力于西方政教分离、世俗事务与文化信仰分而治之的传统。
总之,我以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除了客观的外在环境的变化之外,还有更深层的人文知识内部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推行商品经济的社会都必须伴随文化的沙漠化。这就更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标签:政治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人文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