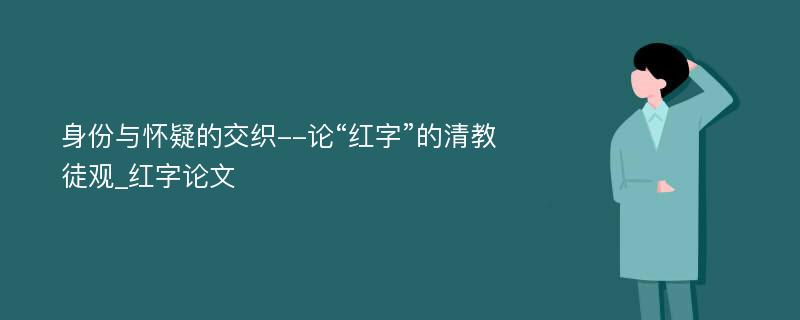
认同与怀疑的交织——论《红字》的清教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字论文,清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154(2002)04-0119-2.3
作为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关注领域是清教这方广阔而深厚的土地。由于其家族所浸透的浓郁的清 教意识,霍桑很早就潜心研究新英格兰的清教历史,深谙信奉清教的新英格兰祖先的道 德伦理观,这些成为他日后小说创作的主要源泉。由于清教自身积极与消极共存的复杂 状况,霍桑对这一特定时空的感情也是认同、接受与怀疑、超越并存,明朗与阴影共同 构成其作品画面的斑驳色彩。作为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认同:人性之恶与救赎之路
“清教”(Puritanism)一词由“清教徒”(Puritan)一词衍生而来,是人们对被称为清 教徒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概括。“清教徒”一词则源于拉丁文的Purus,意为“清洁” 、“纯净”。清教徒得名的由来是基于他们在16世纪要求对英国国教圣公会做进一步的 “净化”、“清理”的改革,其矛头指向的是天主教会的形式和礼仪。
“清教”既是一个信仰概念,也是一个伦理价值概念。就信仰层面来说,加尔文始终 是清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清教徒的神学远不止加尔文主义一种,但较之其他神学, 加尔文主义是清教徒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神学体系。其基本论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五条:彻 底的堕落、预定的拣选、有限的赎罪、奇妙的恩典以及选民的坚忍精神。清教的伦理价 值是清教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延伸,主要表现为虔敬、诚实、节俭、勤勉等。清教 徒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教人,即他们的生活是宗教化的。这种宗教化不是沉溺于冗长 繁琐的迷信礼仪,而体现为一种虔诚与艰难的灵修之旅,以祷告、研究《圣经》、布道 、听道及恪守戒律的方式,对上帝表示敬畏与忏悔、感恩与赞美,专注于灵魂的改善。
从历史的角度看,清教在生活哲学、价值规范等领域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清教的礼 仪和制度改革对后来包括英国国教会在内的教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在净化过程中 所引发出的道德力量却产生了更为久远的影响,以至于有人说:“每当西方社会发生道 德危机时,清教便向人们提供恢复道德的责任感、勇气和信心。”(注:柴惠庭:《英 国清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7月,第242页。)
在《红字》中,霍桑对清教观念的认同,一方面体现在对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另 一方面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改过是获得救赎的信仰原则上。在以《小伙子古德蒙 ·布朗》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中,霍桑已表现出挖掘人性恶的高超能力,《红字》更是层 层深入、丝丝紧扣地展示了霍桑作为心理描写大家的风采。他曾把人心比作蜿蜒曲折的 洞穴,把作家的创作比作在这莫测深浅的洞穴中探进,《红字》便是他探进的最杰出的 成果。
霍桑在《红字》中关注的焦点不是通奸这一行为本身,而是行为发生后在各相关人物 心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他们微秒的道德处境。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的通奸表面上 看来无疑是人性恶的表现,但作者并未到此止步。在他笔触的精挑细揭下,人物灵魂的 更幽深处之恶渐渐显露出来。齐灵窝斯表面上看来是通奸事件的受害者,但作者最终将 其内心的大恶真恶探究出来,令人震惊。
有论者说,海丝特是无可责难的社会牺牲品,从作品本身而言,这并非作者之本意。 从表面上来看,海丝特的确犯了当时社会所不容的通奸之罪,因为她与丈夫之外的人生 下了一个孩子。作为妻子,她背叛了丈夫。但这并不是她最关键的罪之所在,她最关键 的罪在于欺骗。在整个作品中,我们不时会听到作者的呼喊——要诚实,但海丝特却为 了爱而牺牲了真实。她在一开始与齐灵窝斯达成了一种交换,即齐灵窝斯不再追问她谁 是孩子的父亲,她也不告诉丁梅斯代尔齐灵窝斯的真实身份。海丝特的动机无疑是为了 保护丁梅斯代尔,但她采取的手段却是值得怀疑的。欺骗永远都是一种罪,即使以爱的 名义。事实上,海丝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不但没有能够保护丁梅斯代尔,反而 把他推向了一种更悲惨的境地。当她在七年之后说出事情的真相时,丁梅斯代尔已经处 于身心交瘁的边缘了。
丁梅斯代尔身为牧师,却与海丝特有了私情,这对于他的道德观念是一种背叛,但更 重要的是他没有勇气站出来承认是自己所为。相对于甘愿一人承受耻辱的海丝特而言, 他是怯懦的,也是自私的,更是虚伪的。他身处高位,害怕承认之后会失去既有的一切 。如果说海丝特欺骗了他,那他则欺骗了上帝和公众,他在“诚实”面前亦是有罪之躯 。而且,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带着这有罪之躯继续从事牧师这一本应圣洁之工作,这不 能不说是对上帝的极大冒犯和对公众的极不负责。为此,作者让他受到了长达七年、比 公开受罚更残酷的灵与肉的折磨。
齐灵窝斯表面上看来是个受害者,但作者让我们逐渐看到他是怎样由一个受害者变为 一个更大的罪人的。当他决定秘密找寻那个孩子的父亲时,复仇的种子就在他心里埋下 了。他外表沉静温和,内心却怀着深沉的恶毒。七年之中,他狡猾地与丁梅斯代尔共处 一室,解剖一颗痛苦的心并以此为乐事,疯狂的复仇念头使他堕落为一个毫无宽恕怜悯 之心的恶魔式人物。这样一个以复仇为精神支柱的人,在复仇对象死去之后,作者也让 他失掉了活着的意义,不到一年便萎缩死去。
犯罪只是清教救赎论中的一部分,还有更重要的部分即赎罪和得救。小说中这三个有 罪之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条回归之路。
作为公开受惩的罪人,海丝特以内心的忏悔和外部行为上的修行,随着岁月的流逝, 逐渐获得了一种灵魂上的安宁与平静,并逐渐赢得了周围人们的同情和尊敬,以至于在 人们的眼中,红字A具有了Able(能干)、AnSel(天使)的含义,由耻辱的代号变为德行的 徽章。
作为长期隐秘的罪人,丁梅斯代尔承受了比海丝特更为惨重的痛苦。海丝特被迫站在 耻辱台上是因为她的罪即使不说也隐瞒不了,她不必面临“隐还是显”的痛苦抉择。但 对于丁梅斯代尔来说,他的地位、职责、怯懦以及海丝特的拒不说出他的名字,都把他 置于“隐还是显”的两难境地。他是虚伪的,但他又“天生热爱真理,厌恶谎言,为旁 人所不及。因此,他厌恶不幸的自我尤胜其他!”(注:霍桑:《红字》,胡允桓译,人 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93页。)他是怯弱的,但又有谁能像他那样,在自我与身 边隐秘敌人的双重折磨下,在精神和肉体都濒于崩溃的边缘上,依然挣扎着活着,并最 终以惊人的勇气当众说出内心的秘密?尤为难得的是,他是在荣誉的顶峰,主动向世人 袒露自己的。因此,他以一种较之海丝特远为激烈的忏悔方式获得了灵魂的安宁与新生 。
即使罪恶深重如齐灵窝斯,在小说的最后也有了生命的转机。作者交待了一下齐灵窝 斯的结局:他死了,根据其遗嘱,把他的一大笔财产都留给了小珠儿。这一举动无疑包 含了一定程度的悔悟。作者通过作品流露出的一丝怜悯和同情似乎告诉人们:人类彼此 需要宽恕,这世上也没有不可救药的罪人。只要愿意,人总能获得救赎。
怀疑:神圣名义与人性压制
透过霍桑认同清教的表层,我们会发现他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潜在疑惑,而这是由清教 本身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
从历史上看,清教自身的缺陷大致有两方面:对外,清教极端主义对异己的迫害;对 内,则是以人为的神性对正当人性的压制。霍桑在其短篇小说《温柔的男孩》等作品中 ,对那些以上帝的名义迫害异己的清教徒进行了批判,并呼唤一种宽容的宗教氛围,《 红字》则主要反观了清教社会中以道德律令的形式束缚人性的社会问题。
清教的社会理想是“神圣社群”(HolyCommunity)。它要求这个社群的所有成员都应该 全然圣洁,毫无瑕疵。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关键在于使社会生活宗教化。清教徒力图使 社会宗教化的最初动机无疑是高尚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一 种极端。他们虽然取缔了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会外在的繁琐的宗教礼仪和一些迷信成分, 但又使新的细苛的宗教律条成为束缚人性的内在枷锁,从而成为对“因信称义”这一新 教基本要旨的另一种形式的背离。于是,信徒灵命的更新往往不是一种源自心灵深处、 发乎外在言谈举止的自然表现,而只是在一种极浅的外在行为层面上的强制性改变。而 且,对皈依基督的真正体验的强调会使得人们产生过度的反省,乃至不健康的内心折磨 。因此,当上帝的旨意成为某一部分人权威垄断下的社会道德律令时,有着良好初衷的 “神圣社群”就难保不笼上阴郁、沉闷的气氛,神性对人性的拯救就难保不在具体的人 为操作中丧失它的意义。
在新大陆殖民时期的日常生活中,清教徒要始终保持严谨和克制,排斥任何可能引致 道德堕落的行为。在穿着上,包括妇女都摈弃盛装艳服,大都穿用粗糙亚麻布制作的简 朴黑袍。清教徒不仅要求约束行为,也要求约束表情,据说17世纪的清教徒肖像都一脸 严肃,很难从中找出一丝微笑来。在《红字》中,我们始终都会感受到这种来自宗教精 神压力的阴郁之气,信仰本应带给人们的自由释放感,却可悲地淹没在对罪恶的忧思与 不安中了。从霍桑的笔触中,我们不难感到,一个不能被正常享受的生命是可悲的,而 一个不让人正常享受生命的社会是可怕的。
从《红字》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更形象而直观地看出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 不满。
海丝特之所以与丁梅斯代尔发生私情,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从未在年老、阴沉、畸形的 齐灵窝斯那里感受到爱情。而且,当时从欧洲去往新大陆的路途非常险恶,齐灵窝斯一 直没有音信,海丝特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已不在人世。事实上,齐灵窝斯确实曾差点丧命 。年轻美丽的海丝特在孤苦一人无依无靠的情况下,相遇德高望重的青年牧师丁梅斯代 尔,爱情的产生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海丝特因此成为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通奸者 ,公开受审,终生佩戴耻辱的红字A,且离群索居,其处境不能不令人同情。
也许读者会有疑问:既然海丝特在年老畸形的齐灵窝斯那里得不到爱情,为什么她不 能及早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重新组建自己的幸福?但问题是:在清教社会,“清教徒只 允许男人来辨别婚姻的不和谐和提出离婚,女人应当通过温顺来赢得爱情”。(注:D· L·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徐钧尧、宋立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第144页。)由此可见,一个女人在当时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即使她在她的婚姻中感 受不到爱情和幸福。而且,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视女人任何婚姻形式之外的情爱都为 “通奸”,不管某种婚姻形式是多么畸形和朽坏,因而是对正当人性的束缚和压制。齐 灵窝斯事后也对海丝特承认:“是我先委屈了你,我把你含苞的青春同我这朽木错误地 不自然地嫁接在一起,从而断送了你,”(注:霍桑:《红字》,胡允桓译,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1年6月,第27页。)“如果你早些得到强过于我的爱,这件邪恶就不会发生 了”。(注:霍桑:《红字》,胡允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20页。)为 此,他向海丝特保证,对她既不谋求报复,也不怀有邪恶,因为在他看来,天平在他们 两人之间保持了平衡。但事实上,齐灵窝斯对牧师的伤害就是对海丝特最大的伤害,因 为她爱牧师胜于一切。如果说她伤害过齐灵窝斯,那她受到来自后者的伤害要厉害得多 。但在当时的清教社会,海丝特受到了极大的惩罚,而齐灵窝斯,我们不难推测,如果 他的真实身份公诸于众,他不但不会受到当时伦理道德的谴责和制裁,反而会成为同情 和保护的对象,虽然他本人都承认这件事情的发生他首先应负有责任,更何况事后他在 感情和行为上极大地伤害了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这样一种伦理道德,怎能不引人深思 ?
珠儿这一形象也暗含了霍桑对清教的怀疑。珠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与当时的社 会有着明显的游离性。她是一朵野蔷薇,是一道阳光,是一条溪流,是跳跃在阴暗沉郁 的清教社会边缘的一个红色的小精灵,其鲜亮的衣饰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叛。在她 身上,有一种鲜活激荡的生命的特质。在丁梅斯代尔和齐灵窝斯死后,作者安排她离开 新英格兰去了欧洲,在那里她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归宿。想当年,海丝特从欧洲来到新 英格兰,在这里她有过的一段短暂的甜蜜爱情却要用漫长的耻辱、痛苦和忏悔来补偿, 严苛的清教社会扼杀了她的个性和追求,阴影缠络了她的大半生。珠儿在这片阴郁的土 地上孕育、成长,但她那种生命的特质与这种阴郁的气氛格格不入。如果她不离开,照 她的出身与性格,她绝不会有幸福可言。作者把她的幸福设置在另外一个地方,这种设 置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倾向性。
总之,《红字》是一部传达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认同与怀疑的交织之作。一方面,他 觉得罪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属性,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类似红字A的罪之印迹,每个人 也都需要靠对上帝的信仰与相应的行为来获得生命的救赎;另一方面,他又思考信仰之 于生命的应有状态,揭示了清教某些不合理的伦理制度给人造成的阴影与伤害,并间接 肯定人的合情欲望与追求。就整部作品来说,后一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