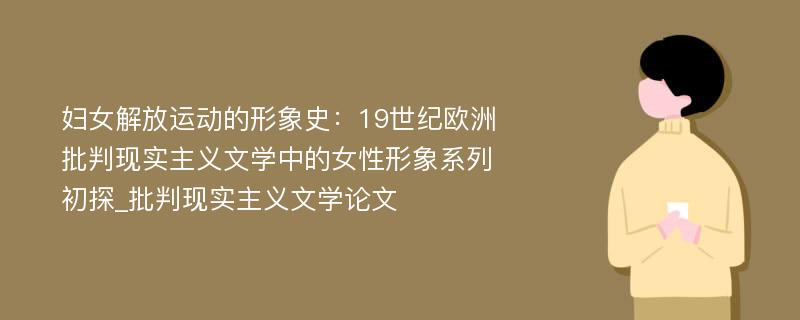
妇女解放运动的形象历史——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妇女形象系列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形象论文,欧洲论文,现实主义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精心塑造了一个个生命受着压抑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上一世纪欧洲不同阶层妇女的命运。她们的凄楚眼神、深沉叹息、奋力反抗、忘我牺牲,牵动了世世代代读者的心。她们犹如块块界石,座座路标,展示出妇女解放运动的运行轨迹、发展趋向。
厄运篇——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平民女子
女子的命运是不幸的,尤其是那些沦落在社会底层的女子。小仲马《茶花女》(1846)中的茶花女玛格丽特,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1868)中的娜司泰雅和哈代《德伯家的苔丝》(1891)中的苔丝,是这一类女子的代表。
她们的悲惨身世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层妇女的深重灾难。她们都出身低微又美丽出众,成了权势者淫逸的受害者。
玛格丽特反映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逼良为娼的黑暗现实。巴黎名妓玛格丽特不甘沉沦,与青年阿尔芒真诚相爱以后,就断然与过去决裂。她典当珍宝,出让马车,洗去铅华,过起简朴生活。可是阿尔芒之父,一个道貌岸然的绅士,视她为祸水,强行拆散他们。他利用玛格丽特善良的天性,迫使她为阿尔芒及其妹作出牺牲。他说:“你爱阿尔芒,用你剩下的唯一方式向他表示你的爱:为他的前途,牺牲你的爱情。”又说:“看在你的爱情,你的忏悔份上,把我的女儿的幸福给我吧。”冷酷的现实使玛格丽特领悟到,她在这个世界上被打入另册,是永远不配享受幸福的。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语:“我总之无非是个妓女,我过去的生活使我没有权利梦想这样的未来。”表达了成千上万玛格丽特一样的女性的痛苦绝叫,表达了她们对造成卖淫现象的罪恶社会的悲愤抗议。
娜司泰雅控诉了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金钱势力对“女性美”的残害。姿容绝世的孤女娜司泰雅十六岁遭到收养她的地主托茨基的玷污。后来,托茨基为了娶有钱的叶潘钦将军的女儿愿出七万五千卢布作她的嫁资;将军秘书笳纳贪财愿结这门亲事;将军也打算一箭双雕,既找个体面的女婿,又可利用权势逼迫下属将妻子给他作情妇;而商人罗果静贪恋娜司泰雅的姿色,拿出了十万卢布现款要笳纳出让。环绕娜司泰雅的这些贵族、资产者、暴发户、野心家,有的要出卖她,有的要收买她,有的要吞噬她。人的尊严被亵渎、蹂躏,起码的人权被剥夺干净,敏感高傲的娜司泰雅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无比激忿地跟随罗果静而去。她以这种令人震惊的自戕的方式向社会提出了控拆。罗果静是私有制黑暗势力的化身,他的私有者疯狂的占有欲最终残杀了娜司泰雅。小说深刻地揭示出“美”是怎样被一群丑怪凌辱、毁灭的,人对人同类相残达到何等丧心病狂的地步。
苔丝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法律、宗教、道德的吃人。纯洁的农家少女苔丝为生计所迫外出帮工受到雇主亚雷的奸污反被世人骂为“伤风败俗”,后来同村人竟为“风化起见”,赶走了她一家。具有自由思想并一度荒唐过的克莱在新婚之夜听苔丝说出被害经过后,竟根据传统观念认定她有罪而将她遗弃。奸淫妇女、毁坏他人一生的流氓亚雷逍遥法外,被损害的苔丝忍无可忍地反抗,就被送上绞架……。苔丝的命运展现出的就是这样一个颠倒混乱的黑暗世道。作家真诚地相信社会正义,呼吁保障人权。他把苔丝称为“纯洁的女人”,在苔丝受辱的昏黑夜晚,他写道:“哪儿是保护苔丝的天使呢?哪儿是她一心信仰、庇护世人的上帝呢?”苔丝的悲剧实在是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人权保障的莫大讽刺。
三位女性形象反映了作家对善恶的正确评判。
小仲马的私生子身世和他的当妓女的恋人的过早夭折在他的“道德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在《茶花女》中,揭露并谴责了“七月王朝”时期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淫荡堕落,怀着深深的敬意揭示出烟花女子的美德善行。玛格丽特甘愿为他人牺牲自我。她明白阿尔芒之父所要求的无非是保全他家的体面,保住他“天使般”女儿的婚姻幸福。玛格丽特竟被这个不相识的少女前途打动了,自己选择了死亡,而把幸福让给了别人,绅士阶级的自私、冷酷、伪善与被损害者的善良、慷慨、真诚,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而且,她在遵守诺言的过程中,以忘我的爱为精神支柱承受了不可名状的痛苦。阿尔芒施展各种手段残酷报复她的“背叛”,不但公开辱骂她,还炫耀新的爱情。她把忍受这一切称为“欢乐的殉难精神”,直到身心衰竭地死后,才通过日记向阿尔芒披露真情。这种为所爱的人默默牺牲自己,受尽冤屈而毫无怨尤的精神感人至深。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思想矛盾的作家。他一生都始终不渝地同情着“穷人”的苦难,又宣扬忍辱顺从的宗教思想。囿于宗教观念的局限,他企图将娜司泰雅的不幸结局归咎于她的无比骄傲,显示出被损害者最难能可贵的品格。娜司泰雅鄙视压迫者,即使拼个鱼死网破也不向权势者妥协。在生日晚会上,她言辞锋利当众揭发托茨基、叶潘钦将军之流的的阴私,使之大出其丑。她又以与罗果静同去的行动、用她的自我毁灭,向虚假、伪善的上流社会投去最大的轻蔑和抗议。她焚烧十万卢布的行为渲泄了对金钱社会的全部仇恨。熊熊火光中,她居高临下,唇枪舌箭尽情地嘲笑那帮丧魂失魄、歇斯底里的群丑,娜司泰雅高大得仿佛成了正义女神。
哈代不仅给苔丝以深切的同情、爱护,用她的美善、真诚来抨击社会的虚假、凶残,而且面对资产阶级卫道士的舆论攻击,他以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坚持了“一个心地坦白的人对于女主角的品格所下的评判”。他宣称:“如果为了真理而开罪于人,那么,宁可开罪于人,也强似埋没真理。”苔丝品格中最动人的是对平等理想的追求。苔丝杀亚雷不仅是对压迫的拼死反抗,更是对理想生活的舍命追求。她与亚雷有不共戴天之仇。是他,使她遭受蹂躏、受尽世人歧视;也是他,使她遭到丈夫遗弃;还是他,乘人之危再次将她诓骗坑害,毁了她和她丈夫的一生。克莱对于她,却是平等相待、至诚相爱的理想的化身。克莱曾把苔丝看得象诗一样美好,认为“她是一个女人,过的是人人视为至宝的生活”,“不是无足轻重的,可以随便玩耍完了就丢开了”。他多次向苔丝求婚,遭到拒绝仍一往情深。蒙羞受辱的苔丝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做人的尊严、爱情的甘美。她热切地盼望与屈辱的过去决裂,开始新生。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爱使她原谅克莱的遗弃而把他当作天神来尊重。杀死亚雷回到克莱身边,她完全不顾及严重后果,只有“称了心愿”似的快乐。
三位美好的女性的被毁灭,产生巨大的道德震撼力量。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曾向人民许诺: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存在表明它只是压迫者胡作非为的天堂,被压迫者万劫不复的地狱。“金钱代替刀剑,成为社会权利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被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①]三位女性的悲剧揭露并鞭挞了践踏生存权利的黑暗势力,残害善良无辜的罪恶制度。她们辗转于地狱深处发出的呼喊:为什么如此“博厚的大地容不下一点小土块”?长久震撼着人们的心弦,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的怀疑。
抗争篇——贵族、资产阶级的叛逆女性
开始觉酲的贵族、资产阶级妇女,奋力挣脱传统的桎梏,去争取自身的幸福。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1833)中的欧也妮,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878)中的安娜,易卜生《玩偶之家》(1879)中的娜拉和夏洛蒂·勃朗特《简·爱》(1847)中的简爱,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
她们的经历遭遇反映了贵族、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制度摧残人性。
欧也妮是法国金钱化冰冷的、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受害者。父亲爱财,泯灭了亲子之爱;情人爱财,背弃了海誓山盟;丈夫爱财,全无夫妇情分。老葛朗台至死都把财产抓在手里,绝不理会“女大当嫁”的天理人情,只以待字闺中的欧也妮为钓饵,让求婚者为之驱走效力。查理缔结了一门高攀的婚事,抛弃了为他不惜一死,等待了七年之久的欧也妮。特·蓬风不过是要通过婚姻取得鲸吞欧也妮巨大产业的合法权利,所以便有了一幕欧也妮允婚时,他“扑倒在有钱的承继人脚下,又快活又凄怆的浑身哆嗦”,连连表示“我一定做你的奴录”的丑恶表演。“天生贤妻良母”的欧也妮只能过着“在世等于出家”的生活,在“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的无限凄凉悲若中了结自己的一生。
安娜的悲剧反映出俄国贵族婚姻家庭制度是以敌视个人性爱为前提、毁灭个人幸福为特征的。安娜被“家世的利益”[②]断送了青春,十七岁便由姑母撮合,为挽救式微的奥布朗斯基家族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省长卡列宁。她的正当的离婚要求,又被虚假、阴狠,图谋报复的卡列宁以“上帝”、“神圣婚姻”的名义断然拒绝。她公开地与渥伦斯基同居,反被纵欲无度、偷情成风的上流社会骂为“堕落的女人”、“有罪的母亲”,将她逐出社交界,使她当众受辱,如同“带枷示众”的罪犯。与此同时,上流社会照旧接纳渥伦斯基并使他对安娜产生厌弃心理。安娜的心灵承受着巨大的创痛:她失去了往昔的尊荣、心爱的儿子,孤立无援地受到全上流社会的攻击,无法摆脱由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积淀所导致的梦魇般的精神折磨,又体验着从渥伦斯基对她的厌烦中预感到的被遗弃的命运。安娜太刚强了,不能苟且偷生,她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死。这是她对上流社会的抗争,也是她被逼走上了这条绝路。上流社会是摧残、扼杀这位热爱生活、向往幸福的善良、美好女性的罪魁祸首。
娜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娜拉揭露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奴隶制。与安娜不同,娜拉似乎算得上“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但一个非常事件撕去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娜拉看清了自己的“玩偶”地位。娜拉曾为救丈夫海尔茂的命冒名借了巨款。而对债主指控她犯有“伪证罪”的威胁,娜拉独自承担了全部痛苦和责任。她安排好人证,准备以死保全丈夫名誉的清白。同时,她也希望着“奇迹”出现——即丈夫实践其爱她超过一切的诺言,她将从对等的爱中得到安慰,死而无憾。可是海文茂得知详情后却恶毒咒骂她是“伪君子”、“犯罪的人”,要结束夫妇关系,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在威胁解除以后,海尔茂竟重又把自己说成是娜拉的“保护人”、“亲爱的丈夫”。娜拉从丈夫的两度变色中不仅看清了他的自私、虚伪的真面目,更痛苦地发现了自己在家庭中被役使、被玩弄的地位。婚后八年,她不过是靠给丈夫逗乐度日的“玩偶”。娜拉不能容忍这样的虚假、屈辱,毅然离家出走。恩格斯据此赞扬:“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④]
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简·爱提出了“以爱情为基础”的新婚姻观。夏洛蒂·勃朗特写作《简·爱》的时期,正是英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昂扬的时代精神使得娜拉最后达到的思想高度成了简爱最初的思想起点。娜拉为追求独立人格、平等地位走出了“玩偶之家”;简·爱来到桑费尔德就已是个具有平等思想、独立人格的新型女子。
她与罗契斯特的相爱是因为彼此间心灵的契合。受到金钱戕害而一度消沉的罗契斯特被简·爱“心境的平静、纯洁的良心和没有玷污过的记忆”所吸引,感到简·爱是他“二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而未能遇到的”“更好的自我”,他欣喜自己的“复活和再生”。这种心灵的交感在简·爱身上表现为对罗契斯特的依恋,地位卑微的她,不仅“没有受到践踏”,并且被这样一颗“独特、活跃、宽广的心灵”尊敬、信赖、热爱着,她感到幸福。简·爱的爱情表白最能表现她对社会不平等、传统婚姻制度的抗议。她误以为罗契斯特要娶富有的英格拉姆,又要留她在身边,她责问道:“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们是平等的!”订婚以后,简·爱也拒绝罗契斯特为她购置珠宝服装,而要“继续做家庭教师,用这个挣得我的膳宿费和外加的一年三十镑”。爱,只要求用爱来回报,爱情是婚姻的唯一条件——这就是简·爱的婚姻观。不管经过怎样的痛苦、磨难,简·爱对此始终不渝。所以,最后罗契斯特破产成了残废,简·爱继承叔叔遗产成了有产者,她还是回到了罗契斯特身边。而且,简·爱珍惜她的经济独立,在贫困中长大的简·爱深深懂得唯有经济独立方有人身自由。
四位女性形象表现了作家对高尚的女性人格的向往。
没有一个作家能象巴尔扎克那么淋漓尽致地描写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罪恶,那么毫不留情地活画出资产者散发出铜臭的灵魂,而拥有二千万法郎财产的欧也妮则是资产者中的特例,作家赋予她以宗教的虔诚、博爱的精神。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她的“出污泥而不染”,鄙视金钱,执着于纯真的感情。在梳妆匣的风波中,她的以死恂情的勇气慑服了贪财如命的葛朗台。在回复查理的信中,字里行间渗透了她对上流社会“名利场”、攀附权贵的负心汉的极度轻蔑:“我的确毫无上流社会的气息,那些计较与风气习惯,我都不知;您所期待的乐趣,我无法贡献。”她望着“扑倒”在脚下的特·蓬风“冷冷的”眼光也如同锋利的钢刀,直插进这个贪鄙之徒的心窝。她以保持童身为条件的婚姻,隐含着她对金钱社会的全部激忿,表现了她不同流俗的高洁人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欧也妮始终“洁身自好”,保持纯真美好的人性。“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正是这一人物强烈的美感作用所在。
托尔斯泰在塑造安娜形象时,着力于表现她的精神美。在安娜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在精神力量上——在正直、诚实、勇敢方面,能与之抗衡。安娜是一个反抗贵族家庭婚姻制度、追求个性解放的勇士,也是作家本人“对上流社会激烈的否定态度的表达者”。安娜第一次重大的行动抉择是与渥伦斯基公然同居。她挣脱传统观念束缚,论证了自己行为的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即使社交界把她关在门外,她也置之不顾。她对渥伦斯基说:“假使一切要从头再来,也还会是一样的。”对唯一相知的杜丽,她有力地申诉:“我什么都不想表白,我不过是要生活……,我有权利这样做,有没有?”正是对自身行为正义性的确信,和对上流社会堕落的了解所产生的自我道德纯净感,使她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二次重大的行动抉择是卧轨自杀。安娜的爱情是严肃的,纯洁的。不难理解,在那种特定的情境中,爱情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对渥伦斯基说:“在我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安娜的“生死恋”中蕴含着昂扬的反封建热忱,虽殒生犹不悔。可是渥伦斯基经受不住社会压力、权势诱惑,动摇了,厌倦了。安娜借着摇曳着的最后的生命烛光全面审视了上流社会,控诉道:“全是虚假,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她投身于滚滚的车轮之下,倾一腔热血,对所有虚假、伪善作出了批判和惩罚。
易卜生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在伟大的国际暴风雨咆哮声中“开始创作的。他的社会问题剧揭露了资产阶级虚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突出地表现了具有民主思想的“个人精神反叛”。娜拉便是具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叛逆女性。娜拉的魅力在于对“女人也是人”的尊严感、价值观的追求。一旦认清了自己处于依附于男子的隶属地位、被男子玩弄的卑微处境,她全然不以庸俗的家庭幸福、富裕的物质生活为念而冲出了家门。娜拉批判了统治千百年的女人“首先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最神圣的责任”是“对丈夫和儿子的责任”的男权中心思想,提出了“首先我是一个人”、“同样神圣的责任”是“我对自己的责任”的妇女独立宣言,勇敢地向传统、宗教、法律、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挑战,“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娜拉的宣言和行动,既是对夫权压迫、家庭奴隶制的反叛,也是对女子独立人格、平等地位的维护,还是对“自我”的生命意义、社会价值的追求。意识到自身独立存在的妇女本体意识已经苏醒,女人已不再是男人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工具,而是与男人一样,是个有灵性、有理智、顶天立地的社会人了。
简·爱是作家精神的产儿。夏洛蒂·勃朗特呼吸着人民广泛要求民主权利的时代气息,根据自己做家庭教师屈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经受过的感情飓风的袭击,从妇女地位问题这一独特角度塑造了简·爱的形象。虽然这一形象和作家“同样地貌不惊人和身体矮小”,但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很高的审美价值。反传统的精神贯穿了简·爱行动的始终。苦难的童年磨砺并铸造了她的叛逆性格。表现之一,是她所具有的独立人格。她不但有独立意识,即坚信“人人生而平等”,推崇自我,独立思考,不为社会偏见、传统观念所左右;而且有独立精神,即不依赖财产门第,不仰仗他人之力,独自谋生,拓展前程。表现之二,是她提出了新的婚姻观。她对罗契斯特爱情的大胆表白,表达了郁积在广大妇女心头对封建门第婚姻制度和资产阶级金钱美色婚姻制度的仇恨。她称自己是“不能给丈夫带来财产、美貌和姻亲关系的女人”,反映出她对婚姻制度本质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可以作为恩格斯关于“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⑤]的论断的有力佐证。表现之三,是她所特有的自尊、自重、自强、自立的个性特征。不管逆境、顺境,都不能使她的独立人格有损分毫。她的反叛热情、深邃思想、非凡格调,至今仍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引力,使人倾倒。
四位女性的形象,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妇女独立意识(即本性意识)的觉醒,女权运动的勃起。欧也妮不惜以死殉情。安娜理直气壮、舍生忘死地争取婚姻自由。娜拉批判夫权压迫,要做一个堂堂正正自立于社会的人。简爱提出自由婚姻的主张,并觉察到经济独立对妇女人格独立的至关重要。传统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自古已然的男权中心思想,遭到她们的批判和唾弃。她们为争取自身的民主权利,主宰自己的命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妇女解放运动的帷幕已经拉开。
求索篇——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旗帜
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社会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给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了蓬勃生机。先进的妇女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实现自身的解放。屠格涅夫《前夜》(1860)中的叶琳娜、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1863)中的薇拉,就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
她们的生活实践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叶琳娜借助爱情的力量进入了社会斗争的广阔天地。贵族少女叶琳娜从父母的婚姻悲剧中觉察到传统婚姻的不幸和贵族生活的空虚,从穷人的困苦中认识到人世间的不平。她不仅有自由思想还渴望行动,为他人解除苦难。保加利亚平民爱国者英沙罗夫的精神人格深深吸引了她。虽然父母惨死于土耳其占领者的屠刀下,英沙罗夫却认为:“现在不是报私仇的时候了;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公仇……。”“当我们中间谁是为了祖国而死,那才可以说他是热爱祖国的。”他的赤诚无私的爱国感情、不尚空谈的实干精神,使叶琳娜看出周围一切“全是个谎”,自己也生活得彷徨、茫然。这位聪慧的少女悟出了英沙罗夫纯洁的灵魂来自他“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想”。叶琳娜找到了生命意义的答案、找到了理想人物,她主动地献出自己的爱。英沙罗夫也早已爱上了她。请看他们的对话:
“‘那么,你会随着我,到任何地方?’他对她说,
‘任何地方,天边,地极!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你不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你父母永远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婚姻?’
‘我不是在欺骗自己,父母不会同意,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我已经献身给那艰苦的,不望感激的事业,我……我们不仅要经历危险,也许还要忍受贫困、屈辱?’
‘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爱你!’”
这段对话与屠格涅夫写于1878年的赞颂民粹派女革命家的散文诗《门槛》极其相似,它不只是信誓旦旦的爱情表白,也是掷地有金石声的革命誓词。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奋斗是他们爱情的基石。在奔赴保加利亚途中,英沙罗夫不幸病逝,叶琳娜只身前往战火奋飞的异国他乡。坚贞不二地忠于爱情和矢志不移地献身于亡夫未竟的事业,在她已合二为一。叶琳娜不再是为个性解放而奋斗的女子,而是为弱小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战士。
薇拉完成了从争取个性解放到争取社会解放的深刻转变。平民少女薇拉憎恨贪财的母亲、荒淫的贵族,抗拒买卖婚姻。医科大学生、民主主义者罗普霍夫用“结婚”的办法帮助薇拉逃出了牢笼。他们按照“平等原则”建立了新型的家庭关系。他们认为“该让每个人竭力保住自己的独立性,不依赖任何人”,而“女人靠男人供养的时候,她就得依赖他”。于是,薇拉婚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开办了一所社会主义性质的缝纫工场。三年后,工场兴旺发达,薇拉的家情却出现了波折。她觉察到自己对丈夫只有感激之情,而与丈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却不知不觉相爱了。她向丈夫坦诚地说出一切,并表示:“除了你我不愿意爱任何人。”她受着痛苦的煎熬竭力扑灭新的爱情火苗。罗普霍夫在“合理利己主义”指导下,伪装自杀退出了“舞台”,成全了妻子的爱情幸福。薇拉没有沉溺在新婚热恋中,她剖析了自己不能象吉尔沙诺夫那样承受得了折磨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个无法放弃、无法搁下的事业”,得出了“在妇女努力往各方面去发展以前,她们不会获得独立”的结论。她决心冲破历来男尊女卑的成见,在丈夫的帮助下学医。通过艰苦努力,薇拉终于成了当时俄国为数很少的女医生之一。最后,薇拉更以拉赫美托夫式的革命者为榜样,与丈夫相互勉励献身给人民解放事业,勇敢地投身于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
薇拉有一个执着的、向上的灵魂,她的思想不断跃向新的高度,做到与时代同步。她的奋斗最初只是为了挣脱家庭羁绊争取婚姻自主,在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她开始探索妇女解放道路,最终投身于解放斗争。她的对于妇女不幸命运追根溯源的精神,开拓解放新生活的热忱和实践的能力,使她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旗帜。
二位女性形象体现了作家进步的审美理想。
叶琳娜是当时俄国“真正的人”。叶琳娜在贵族社会中卓然不群。她独立思考,鄙视周围人夸夸其谈、无所事事,极具热情,渴望献身给正义事业。叶琳娜的爱情选择内蕴异常深刻,集中表现了这一人物的美学价值。她拒绝了三个贵族青年的追求(一个庸俗的官员,一个善良而目光短浅的学者,一个略具才华却又浅薄的画家),而转向保加利亚的平民爱国者莫沙罗夫,就是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的战士。这一选择,溶铸了作者对农奴制改革“前夜”俄国社会各阶层历史作用的独到认识和审美判断:“在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咤叱风云的时代业已结束,即使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失去了理想热情、豪迈精神和行动能力”;“自觉的英雄”须从贵族以外的平民阶级中去寻找。叶琳娜的选择,就是时代的选择。
叶琳娜的形象反映了俄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翻开新的一页:进步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已开始与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相联系,妇女解放运动将成为俄国人民解放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与英沙罗夫同样是演出俄国历史新场面所需要的“真正的人”。
薇拉是获得了解放的女性象征。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极大的热忱通过薇拉的生活经历展现出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在婚姻问题上,薇拉缔结了以爱情为基础并在婚后仍保持着爱情的真正自由的婚姻;在家庭关系上,她坚决摆脱对丈夫的依附性,坚持了经济独立;在社会生活中,她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实现了男女平等;在革命斗争中,她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使有限的生命获得了永久的价值。薇拉的生活实践表明,她不仅获得了爱情幸福,也实现了妇女作为“人”的全部价值。这便是作家所礼赞的理想人生。
集中描绘社会理想的是薇拉的第四个梦。作家用四个象征性的女王形象,展现出爱情的历史、男女关系的历史,反映了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理想社会便是最后一位女王——光明女王统治的时期。光明女王显形竟是薇拉自己。女王的姐妹解释道,由于男女权利平等得以实现,薇拉获得了真正称得上自由的爱情幸福。沐浴在爱情光辉中的薇拉如同被光轮的光辉围绕着的女王——这便是薇拉在爱人心目中的形象。当所有女性都象薇拉一样,在各自爱人的心目中都成为光明女王的时候,人类也就进入了理想社会。作家满怀激情,用诗样的语言描绘出消灭剥削、压迫以后人们的自由劳动与欢乐生活,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造福人类的伟大成果,勾画出一幅灿烂辉煌的社会主义远景。作家振奋地向人们发出号召:“未来是光明而美丽的。爱它吧,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促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吧。”
两位女性形象展示出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和发展方向。第一、二类女性的斗争都没能超越个人幸福这一狭隘内容,娜拉虽已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责任,然而也才只跨出家门。娜拉走后怎样?“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叶琳娜却从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发展到追求建立在崇高理想基础上的爱情,从个人小天地走向社会大舞台,不仅获得了纯真的爱情,更进入一个崇高的境界,对弱小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薇拉则自觉地投身于社会解放的斗争,做到了为同时代人创造幸福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幸福,为同时代人的幸福而工作的同时,自己也趋向完美,实现了自我追求幸福、发展同造福人类的统一。薇拉的奋斗,为妇女解放运动展现出光辉的前景。高尔基在《母亲》中所描写的尼洛夫娜·沙馨卡等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妇女形象,更拓展了薇拉的道路,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三组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都是优秀的作家们从不同的国度中、从时代与社会的“五脏六肺”中概括出来的,显示了他们历史的、美学的憧憬与追求。所以这些形象能够揭示一定的历史发展轨迹,为我们提供一部上一世纪欧洲妇女解放的形象历史。他们的奋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依次递升的不同目标:
第一层次是“要生存”——玛格丽特、娜司泰雅和苔丝,反映了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为捍卫起码的生存权利而拼死搏斗;
第二层次是“要享受”——欧也妮、安娜、娜拉和简·爱,表现出妇女本体意识的觉醒,为争取爱情幸福、自由平等权利而奋勇抗争;
第三层次是“要发展”——叶琳娜、薇拉展现出先进妇女在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对发展个性、发展才能,创造自身幸福和自身价值的追求。
她们的奋斗启示我们:妇女解放问题最终应归结为社会解放问题。被压迫阶级妇女的解放自不待言。妇女解放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诸如: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自由婚姻;破除现代资产阶级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实现男女平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的聪明才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等。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须以妇女成为“社会的生产劳动”、人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⑦]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最终实现,也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压迫之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⑧]妇女问题的解决和妇女解放程度的提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标志。
注释:
① ⑧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8页,第412页。
② ③ ⑤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6页,第72页,第76页,第63页。
④恩格斯:《致保·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55页。
⑥鲁迅:《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59页。
标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爱情论文; 安娜论文; 简·爱论文; 苔丝论文; 薇拉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