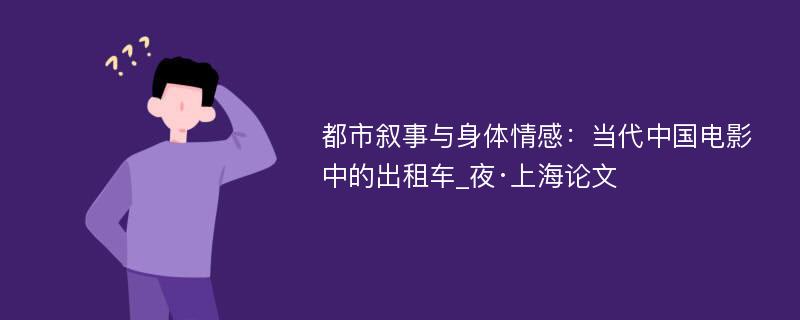
都市叙事与体感: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出租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租车论文,中国当代论文,都市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租车是都市的重要构成元素。自1907年第一辆使用计程表的出租车出现在纽约街头以来,出租车永不停息地穿行在世界各都市的大街小巷,同城市人的生活如影相随。对于城市文化研究来说,出租车的历史和再现具有“管中窥豹”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出租车及其产业的变迁是城市发展的缩影。而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19世纪末诞生的电影成为时间上同出租车并行发展的现代技术与媒介;电影和出租车都见证和参与了城市现代性的建构。也正因如此,穿街走巷的出租车成为“都市电影”(urban cinema)中常见的题材和元素。在这一方狭小的空间内外,出租司机和乘客演绎着爱恨情仇、人生百态;而这些出租车的故事和影像也成为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研究纽约出租车史的郝吉思(Graham Hodges)所说:“任何一部包含纽约街头场景的电影如果没有出现出租车都是不完整的。”①纽约如是,其他城市亦如是。 世界电影史上以出租车为表现重点或以出租车司机为主人公的电影很多,且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决定了这些作品艺术再现的不同。从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导演的新好莱坞电影代表作《出租车司机》(1976)到波兰大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十诫之杀人》(1988),从法国导演吕克·贝松(Luc Besson)的《疯狂出租车》(1998)到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十段生命的共振》(2004),众多电影借由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再现和思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语境、政治经济背景、性别意识、后殖民认同、文化建构等议题。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人公的出租车司机具有共同的性格特征,即孤独、压抑和疏离。这一方面来自于其族裔、性别、阶级等方面的身份特征以及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源自出租车司机的职业特征与工作性质。② 相对而言,中国当代出租车题材的电影乏善可陈,直至21世纪才出现了几部以出租车司机为主人公的电影:宁瀛导演的《夏日暖洋洋》(2000)、张一白导演的《夜·上海》(2007)、曹保平导演的《李米的猜想》(2008)、张江南导演的《午夜出租车》(2010)等。而在中国都市电影领域,对于这些作品的个案研究不少,却并无专门针对出租车题材或出租车司机形象的分析和论述。通过考察这些电影文本,我们不仅能够审视中国都市电影的特征与现状,而且可以借此管窥当代城市化发展在阶层、性别、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种种征候。 从研究视角上,本文试图在城市文化传统的大论述框架下(城乡对立、身份认同、都市现代性等)另辟蹊径,令电影中的出租车(及出租车司机)不再仅以主题、人物、象征符号等方式被再现(represented),而是以身体记忆和空间感知的方式被体现(embodied)。本文尤其要思考影片中出租车借由接触、漫游、穿越等方式体感城市的可能,初探交通工具、都市体感和影像再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体感”(the haptic)这一概念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同视觉、听觉等相并列与联系的身体触感,还有身体移动所带来的运动知觉以及身体和环境之间的接触。正如罗德威(Paul Rodaway)在《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ies)中所言,体感的概念不仅指涉身体的触感和身体部位的动作,还涵盖了身体在环境中的移动穿越。③而身体在空间接触、移动、穿越时,身体空间和城市空间便得以变动和交会,身体、建筑、城市之间所有感官的表面(surface)都可成为开放流动的界面(interface)。④借由此种体感的角度,本文将出租车视为城市空间机理的体感元素,同时将出租车的影像与视角看作观众的体感途径,分析和思考如下问题:电影中出租车的“穿街走巷”,如何参与影像的“穿针引线”,如何引发了人物和观众的“情生意动”(e-motion)。 一 接触:密闭空间的情欲生产 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出租车同时具有两种特征:密闭性和流动性,而这两种特征也构成了悖论关系。这两种特征同时作用于出租车司机的身上,造成了他们对于情感和人际关系的矛盾态度:既亲近又疏离,既热情又麻木。这样一种躁动不安、游移不定、若即若离的特征,是出租车司机职业病“的哥焦虑症”(cabbyitis)⑤的重要表现。这一方面源自出租车司机的职业属性(司机无法同客人建立长期的社会关系和感情,因此客人频繁的流动令他们对于社会交往越发麻木和倦怠);另一方面,即从体感的角度来说,也同出租车密闭空间的属性相关:密闭空间似乎也将身体的情欲空间关闭了,于是出租车造成了身体与外部世界的隔离。 在上述几部电影中,出租车司机都表现一种同出租车外世界相隔离的姿态,甚至都有一种都市的“倦怠”气息。诚如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言,城市是感官刺激与声色诱惑之所在,其快速变换的步调与节奏,令人时时担心被城市的不明空间和汹涌人潮淹没;于是面对城市的五光十色与声色犬马之时,必须发展出一套“倦怠”(blasé)的心理保护机制,以强化不断被感官情绪所牵动的主体认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强调理性、封闭和知识的“单一个体”(individuality)。⑥这种“倦怠”感固然主要体现在都市中产阶级男性身上,但用来分析出租车司机这一群体也十分合适。几乎每部电影都有类似的段落:快速剪辑的镜头表现了乘客更换的频繁,尤其是司机与乘客两者的特写正反打镜头,突出了司机与乘客(及外部世界)之间的格格不入,强化了出租车司机的密闭的单一个体的世界。 在这些段落中,《李米的猜想》的开头尤为精彩。镜头以内反拍、外反拍、齐轴、平行等不同角度拍摄车内的世界:边抽烟边喃喃自语的李米和车内似听非听的乘客。在诡异风格的画外音中,观众能够透过出租车窗看到外面鬼魅般的世界:车窗外的行人、摩托车和自行车的速度明显被刻意调慢,画面也被处理成模糊不清的效果,于是车外的一切都变成重重鬼影。这一段落利用电影视听手法将车内外的世界区分开,两种影像(模糊与清晰)、两种速度(正常与慢速)象征了李米的主观精神状态同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关于出租车司机与外部世界的隔离感,美国大作家菲茨杰拉尔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道: 又到了晚上八点钟,四十几号街那一带昏暗的街巷里排满了响着马达声的出租车……此时我心头感到一阵惆怅。出租车停在路口的时候,你可以依稀看到车子里人们依偎在一起,听到他们唱歌的声音,以及无法听见的说笑所引起的欢笑,还有点燃的香烟在车里吐出的一道道浑浊的烟圈。⑦ 菲茨杰拉尔德非常了解出租车司机与外部世界是如何隔离的,这段描写中的聆听、笑声、依偎、香烟等意象也出现在《李米的猜想》中,强化了这种疏离感。然而,李米这个臆想症人物设置的灵感更多来源于斯科塞斯导演的《出租车司机》(1976)——影片中的司机拉维斯患有严重的失眠和臆想症,这主要来自越南战争中的创伤(拉维斯是越战退伍军人)和存在主义思潮,导演也借此再现了当时纽约的阶级差异、政治腐败与人情冷漠。而李米的臆想症则主要来自个人爱情经历的创伤,却也从侧面隐喻了中国都市化进程中不同阶层、不同性别和不同群体人之间某种程度上的沟通障碍。 然而,一旦密闭空间被开启,便可能引发社会关系和情欲的“流动”。于是,身体空间、出租车空间、城市空间之间便产生了相互接触、摩擦的“空间接触感染”(spatial contagion)⑧。出租车空间的开启,使得内与外、公众与私密、个体与社会的区隔被打破,于是身体和城市的明确边界变得松动而模糊。上述几部电影中的出租车司机看似麻木倦怠,却都在出租车车门的开合中酝酿与生产着对于爱情与欲望的渴求,尤其是《夏日暖洋洋》中的德子更是如此。他同林芳离婚后与小雪同居,又看上了自己的乘客赵园,随后电台女主播、开朗热情的女孩也不断牵动着他对爱情的渴望。这样一种多变的、易逝的情欲渴望是同城市发展的速度,以及与城市空间的摩擦感染息息相关的。该影片中有一处细节:德子载着开朗热情的女孩穿过一片巨大的建设工地,他打开车窗令车内外的空气流动,却感到整个城市令他晕眩,于是在半路时他停车呕吐。在这一情节中,身体与城市之间并非构成隐喻性的再现关系,而是体现为一种由“空间接触感染、”而引发的与身体关联的转喻关系。⑨德子眩晕与呕吐的身体反应,正是身体空间与城市空间相互感染而引发的转喻性症状。 与德子相比,《李米的猜想》中的李米以及《夜·上海》中的林夕,作为女司机,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更为炽烈与专一。李米四年来追寻男友的踪迹,她所有的动力来自出租车的探索与寻找功能:她询问每一个乘客是否有男友的消息,在每一次车内外空间的接触感染中不断巩固和强化对于爱情的自我生产(或幻想)。离开了出租车,她的爱情故事或许就会戛然而止。林夕则总是刻意利用出租车制造小事故,从而创造与修车工东东的接触机会;于是出租车空间的开合同东东的修理相关联,出租车空间的破损与完好恰恰是林夕身体情欲打开与封闭的直接隐喻和体现。⑩可以说,两位女司机的情感追寻都发生在出租车与城市两个空间的接触感染之中,她们的情欲借由闭合或开放的出租车空间得以萌发与流动。 另外,出租车的流动性(mobility)、非目的性、随机性都是都市形态和人际关系的重要隐喻。作为城市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出租车虽然将城市的各种空间(火车站、舞场、酒店、机场等)连接起来,但它只是空间的关联,是通往目的地的手段,它本身并非目的地,这也决定了出租车司机的“过客”性质。因此,当车上的乘客不断更换之时,“空间接触感染”除了带来情欲的生产外,还造成人群与阶级的流动性。因此,出租车的流动所串联起来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日常生活空间生产。而在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日常生活的空间往往受制于资本的逻辑,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同质化的空间生产。根据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现代性的日常生活空间日益被完美无缺的现代消费体制所套牢和侵蚀,最终使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受组织和受控制的领域。日常生活空间的丰富性、差异性为资本的同质化所吞噬,变成一个被压抑的空间,一个任何元素都可以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化、均质化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将这种社会空间生产称为“日常生活空间的殖民化”。(11)在上述几部电影中,出租车上形形色色的乘客大都在为生计打拼,其中绝大部分是城市中的新兴中产阶层或白领人士。例如,《夜·上海》中很多乘客都同作为影片背景事件的“上海国际音乐节”有关,于是林夕及其出租车无形中参与了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生产。其中两名乘客的谈话内容如下: 女乘客:“师傅,您可以开快点嘛?我们赶场子。多加钱也行……糟糕,我听说这次的化妆师是日本化妆界的大腕,迟到了肯定又要火冒三丈。” 男乘客:“那是因为我们活儿接得太多了。” 女乘客:“我们只能每天向前冲,没办法。” 作为化妆助理的两名都市自领,日常生活都在“没办法”的“向前冲”中度过,而这样一种“向前冲”的要求是现代都市所召唤的,它在日常重复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中不断规训和形塑都市自领的主体性,令其成为都市社会关系空间的一分子。这背后是全球化资本的逻辑:来自于海外的“化妆的大腕”体现了人才或资本流动的全球性,这种流动性也造成了全球都市空间的日益同质化与商品化。 因此,出租车的流动性所带来的“空间接触感染”,令情欲和生产关系的流动成为可能。而都市电影则借由视听语言,将密闭空间的隐喻和转喻功能通过叙事和影像得以传达,从而实现了身体空间和城市空间、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互动关联。 二 漫游:底层游民的都市窥探 出租车的流动性不仅造成“空间接触感染”,而且引发了另一种体感城市的方式——漫游。上述几部出租车电影都具有相同的城市再现方式:出租车在都市中的“穿街走巷”,引发电影故事情节,为人物关系“穿针引线”。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观众跟随镜头一起,用身体观看、聆听和感受城市,从而完成对于城市空间的认知与体感。 罗德威将认识空间的方式分为两种:“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和“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y)。对于城市来说,“认知绘图”强调街道、建筑、名胜古迹等地标的重要性,重视认知者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是理性的认知;而“感官地理”是个人色彩的随心游走,是包含游者记忆和情感的感官经验,是感性的漫游。(12)出租车题材电影借助视听语言,表现城市空间的方式既有“认知绘图”,也有“感官地理”。 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认知绘图”是他们的基本功能之一。他们往往是最熟知某座城市地理状况的一群人,对于城市中的任何角落似乎都了如指掌。无论是本地抑或外来的乘客,都可以借由出租车司机的指引和推荐来实现对于城市的游览、旅行和认知。尤其对于城市中的地标性空间,司机更能通过自身的知识积累和职业训练,向乘客讲述其历史典故或奇闻逸事。他们每日不断地移动,目击和见证了整个城市变迁的过程,甚至熟悉每一处地理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城市地图的绘制者”。(13) 那么,在表现出租车及其司机的“认知绘图”时,电影具有怎样的功能与意义?一方面,电影能够借由俯拍或航拍来实现对于城市的俯瞰式认知。上述几部电影都包含对于城市街景的俯拍镜头,例如,《夏日暖洋洋》中的第一个镜头便是大远景俯拍,镜头中宽阔的马路、熙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为影片定下了现代化的城市空间基调。而当镜头不断拉伸,观众看到大远景中的一个十字路口,路上繁忙拥挤的车辆是北京时常出现的交通状况,而街道两旁矗立着形形色色、高耸入云的建筑。一切都在展示北京城市空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夜·上海》在主线情节的叙述中,穿插了很多上海夜色中各类摩天大楼、霓虹灯和立交桥的大远景俯拍镜头,且往往将其处理为快速流动的画面,并配以舒缓的布鲁斯或爵士乐,营造出一个既时尚慵懒又繁华多变的上海之夜。另一方面,电影镜头捕捉和再现城市中的地标性建筑空间,令观众能清楚而准确地认知故事发生的都市。《夜·上海》中屡次安排林夕驶过外滩,《夏日暖洋洋》中的德子也曾驾车经过天安门——诸如外滩、天安门等标志性建筑和空间令观众直接、明了地完成了对于上海或北京的认知。 然而,出租车对于城市空闯的认识方式,更体现在“感官地理”方面。如果说街道体现了城市的“流动性、匿名性、混乱性”(14)等特征,那么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是这些特征的直接感受者。在大街小巷中穿行的出租车,充当了“都市漫游者”(flaneur)的角色。和步行或自行车一样,出租车将街道、商店、广场、银行等都市的空间联系在一起。在电影中,借由出租车的漫游,镜头能够表现不同的城市建筑和空间,观众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感知城市的地理与脉搏。 根据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说法,“只有那些流动者和漫游者,那些不被城市法则同化的人,才能接近城市的秘密”,他们是“公共场景的经验象征”。(15)可以说,漫游其实就是一个进入城市内部结构,窥探城市秘密和体感城市功能的过程。这正如汪民安所说:“出租车参与了城市的秘密……出租车的流动,和整个城市的流动相呼应”,而且在这样的漫游过程中,“出租车司机不是目睹了结果,而是目睹了这些变化本身,他们见证了城市的生长”。(17) 在本雅明的表述中,都市漫游者往往是男性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或没落贵族,在他们眼中,女性是被观察的对象,象征着“都市的诱惑与危险”,并“引诱男性反复不断地都市探险”。(18)然而在上述几部电影中,充当“都市漫游者”的出租车司机有男有女,而且都是社会底层人士,他们漫游都市更多出于生计的需要,并非为了观察和体会城市的转瞬即逝,在此过程中,他们无意“窥探”城市的秘密。尤其在同乘客的交谈中,阴谋、隐私、辱骂甚至犯罪事件都被他们探知。如在《李米的猜想》中,李米亲历一起贩毒案件;在《午夜出租车》中,徐子见证一起谋杀案件。这些乘客的秘密刻意或无意地在他们面前暴露和敞开,而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和分享这些秘密。李米、林夕或德子这样的城市游民,在阶层上对于大多数乘客来说,并不构成威胁或压力,这也令他们对城市中人与事的“窥探”更为顺理成章。 除却“感知地理”,出租车的漫游也提供了城市空间的另一种意义:记录或保存。相对于其他几部电影,宁瀛导演的《夏日暖洋洋》有意识地记录北京变化和发展中的城市空间,并希望能够以影像的方式将其保存。正是在这样的记录过程中,电影画面不仅承担了城市空间的再现功能,而且借由“都市漫游者”完成了对城市的体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联想到她的另外两部作品——《找乐》(1992)和《民警故事》(1995),将之一并进行思考。这两部电影同《夏日暖洋洋》一起,构成了宁瀛的“北京三部曲”。“北京三部曲”从时间上横跨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十年。从城市的外观到社会内部结构以及人的价值体系,北京在这十年内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正如宁瀛自己所说:“我曾经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我爱过的人和城市正在离我远去,我们经历的是一次失恋的过程。所以我把这三部电影称作《我爱北京》三部曲。”(18) “北京三部曲”以整座城市的空间外观变化为视角,审视了这座城市的空间变化和经济发展给北京平民带来的影响;而这些城市平民是这座城市消失、变化和更新的见证人——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的“都市漫游者”。有趣的是,三部电影主人公漫游城市的工具各不相同:从《找乐》中老韩头的步行,到《民警故事》中民警们的自行车,再到《夏日暖洋洋》中穿梭于街巷中的出租车,这种交通工具的变化呈现愈来愈进步的趋势。而交通工具的发展速度,同城市建设、拆迁和发展的速度是相对应的。这种速度也是城市居民生活速度的隐喻。宁瀛自己也表达过,“《找乐》就是老头儿走路的速度”,而“《民警故事》中生活的速度就是自行车的速度”。而到了《夏日暖洋洋》中,她使用出租车来再现城市的想法来源于自身的经历:“我不爱开车老是打的,北京立交桥一架起来就变了,我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19)由此,1990年代北京城市发展之快速、变化之迅猛可见一斑。 宁瀛以影像来记录和保存城市的方式令我们思考影像体感城市空间的时间维度。如果现实中的都市漫游发生在网时同地,那电影便可以通过蒙太奇手法将不同时空的城市空间剪辑到一起,于是观众对城市空间地理的感受和认识便经历了视听语言的再创造,这凸显影像的虚拟特质。而且,无论强调客观记录的再现性影像,抑或倾向虚拟创造的表现性影像,都参与了城市文化和空间的营造,城市电影的绘图功能和意义便在这一过程中凸显出来。于是,在出租车题材的电影中,视听元素的介入令城市空间的体感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 三 穿行:主观视角的幽灵体验 地理学家多林·梅西(Doreen Massey)在谈及电影和“都市漫游者”的关系时,批评理论界过于侧重漫游者所带来的奇观凝视和都市窥探,这样一种趋势导致对电影镜头“窥视欲”(voyeuristic desire)属性的强调。(20)事实上,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能够将思维延伸,思考电影和城市关系中流动性的另一个维度:对于空间和时间中“韵律性”(rhythmicity)(21)的强调。正如拉什(Scott Lash)所说:“都市漫游者的意义,不仅在于现代性的呈现,而且在于作为火车、汽车甚至直升机的驾驶者和乘客的观感。”(22)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思考都市电影所具有的一种视角——出租车视角,包括这种视角带来的穿行特征以及穿行所带来的观感体验。出租车的漫游在电影中表现为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例如,《夏日暖洋洋》开头的视角并非出租车乘客或司机的主观视角,而是一种从不同角度和机位进行拍摄的客观视角(尤其是“认知绘图”式的俯瞰镜头);其叙事和表现的意义远大于感受和体验的意义。然而在《夜·上海》的开头段落中,为了表现出租车在深夜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拍摄视角为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虽然画面底部的“taxi”字样表明,摄影机是被置于车顶上的,然而并不影响这一镜头的主观特性。这样一种视角和拍摄方式,令观众似乎成为出租车里的乘客或司机,置身于夜晚的城市空间之中;于是出租车在城市空间的漫游,便以一种“穿街走巷”的穿行方式进行,更容易引发感官和情感的流动。 这种镜头其实早在电影发明初期便有人试用并为效果惊叹,即所谓的“幻影之旅”(phantom ride):镜头代替了眼睛,令观众感觉到自己离开地面飘浮,且随着镜头在空中穿行飞舞。英国布莱顿学派的电影大师史密斯(George Albert Smith)在1899年的电影《隧道里的吻》中,将摄影机放在向前行驶的火车头上,拍下了一个幻影般的移动镜头,这便是最早的“幻影之旅”。“幻影之旅”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都市空间属性中的流动性、变化性和情感性,于是电影本身不再是一种强调固定而又静止的空间形式,而是一种可知的、移动的、感性的环境,一种可以自由移动、旅行和漂泊的空间。 对于都市电影来说,“幻影之旅”除了完成“都市漫游者”的“感知地理”功能之外,还具有引发感官或情感变化的意义。在这方面,《夜·上海》的开头段落较为典型:画面从黑屏开始,观众先听到抒情意味浓厚的音乐,紧接着八个构图一致的“幻影之旅”镜头相互衔接,共同组成了这个段落。镜头之间以叠化的方式过渡,每个镜头中出租车的行驶速度都不同,大都远快于日常行驶的速度,因此镜头中两侧的路灯和霓虹灯缀连成串,烘托出夜色的妖娆与魅力。尤其在几个镜头的后半段,镜头的速度突然由快变慢,既在对比中增强了体感的节奏性,又能令观众短暂地审视这一刻出租车两边的建筑、灯光和其他车辆;然而又在突然加速的镜头中,一切变得模糊而转瞬即逝。这一段落在速度、叠化以及音画对位上的处理,令观众借由穿行的方式,密集而强烈地感受到上海都市的韵律性、易变性、现代性与时尚性,并短暂地拥有了一种超现实的感官体验。 与此类似,《午夜出租车》的开头段落也借由一辆出租车在北京城中的穿行,交代了故事的起点:一群人在深夜之中搭乘出租车,因为没钱付车费而一时起意杀死了女司机。影片以几个“幻影之旅”镜头开场,在诡异而恐怖的画外音乐中,镜头用不同拍摄角度(侧面、背面、正面等)的主观视角带领观众进行都市的穿行。同《夜·上海》表达的都市时尚感和韵律感不同,这一组“幻影之旅”镜头极力渲染了一种恐怖悬疑的气氛,这种气氛一方面来自画外音的烘托,另一方面来自镜头的不稳定性——由于这组镜头是手执拍摄(摄影师站在运动的汽车上进行拍摄),因此画面具有强烈的颠簸感和晃动感,这种颠簸和晃动带动了观众心理的忐忑起伏。而在画面内部,街道两旁街灯昏暗,于是出租车的尾灯便被凸显出来:画面的绝大部分由阴影和黑暗构成,具有黑色电影的诡异和压抑气氛。这一组“幻影之旅”镜头同样借由视听技巧带动了观众的感官体验,只不过这种体感是恐怖、忐忑与诡异的,一方面为接下来的谋杀案件制造悬念,另一方面确定了整部恐怖片的黑色基调。 从这两个段落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影院空间或电影银幕对“幻影之旅”镜头的体感意义。正如三维技术和全息成像技术令观众对电影的接受更为“沉浸”(immersed)一样,“幻影之旅”镜头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观赏体验的“沉浸感”(immersion)。根据德国美学家格劳(Oliver Grau)的观点,沉浸的审美享受主要来自真实与幻象(illusion)的交融,因此它是一种虚拟现实的空间营造。(23)“幻影之旅”镜头的重要意义在于,画面的内容其实已经溢出了银幕的框架,打破了影内空间和观影空间的界限,令观众将自己的身体虚拟于影片的场景中;在这种似真亦幻的体感中,无论恐怖抑或愉悦的体验,都带动了身体空间同影像空间的互动与融合。因此,在银幕上穿行的出租车,借由主观镜头能够带领观众穿越现实和表象,暂时湮没在虚拟的电影时空中。而与简单的虚拟旅行不同,电影借由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别出心裁的视听语言,令观众的审美体验更为立体和多元。 至此,本文主要从接触、漫游和穿行三个角度,分析了出租车影像对于城市空间的体感与经历。用这样一种角度,是希望能在强调“空间转向”的城市文化研究背景和框架下,从一种异于“再现”(representation)的角度重新思考、建构影像与城市的关系。其实,本文所分析的四部电影都再现了21世纪以来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征候,尤其借由出租车司机形象的塑造反思了一些社会问题。从阶层、性别或职业特征等方面来说,影片的艺术再现并非对现实的完全客观反映,而是受到类型、风格、制片等因素的制约,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尤其是从叙事和表现上来看,这几部作品的艺术创作深受国外都市电影的影响。《李米的猜想》中的出租车司机的臆想症和犯罪叙事都借鉴了《出租车司机》中的经典人物或情节设置,然而导演曹保平却将这一叙述模式以中国式底层爱情故事进行了重新书写。《夜·上海》在叙事、影像和人物等方面都借鉴了《迷失东京》中的元素,却以文字沟通(24)的方式解构了美国电影中的“迷失”,并将后现代符号帝国(25)的故事改写为媚俗化的上海版浪漫爱情喜剧。而《午夜出租车》作为一部恐怖片,在视听语言上挪用了日本、中国香港、泰国恐怖片的技法,将恐怖叙事同“北漂”青年形象及北京城市文化进行了有机结合。因此,这些中国式的出租车影像与故事,不仅同当代城市化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而且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进行了诸多艺术探索。 注释: ①[美]格雷厄姆·郝吉思:《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王旭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7页。 ②出租车司机不仅要应付交通管理行业的各种规定,而且要应付车行老板或中间商;其职业特征决定了他们需要精力过度集中、神经高度紧张;另外,他们同乘客之间很难建立长久的社会交往关系,久而久之只能在长期的孤独中持续工作。 ③Paul Rodaway,Sensuous Geographies:Body,Sense and Place,New York:Routledge,1994,pp.41-42. ④张小虹:《城市是件花衣裳》,《中外文学》2006年3月。 ⑤关于“的哥焦虑症”(cabbyitis)与“Luftmenchen”,可参见[美]格雷厄姆·郝吉思《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第12页。 ⑥Georg Simmel,"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Donald N.Levine,ed.,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p.324-339. ⑦[美]菲茨杰拉尔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姚乃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51页。 ⑧关于“空间接触感染”,可参见张小虹《城市是件花衣裳》。 ⑨从隐喻和转喻的区别来看,隐喻强调相似、认同、深度和意义达成,转喻则强调毗邻、连接、贴近的表面符号的流动和身体想象的可能性。 ⑩对于密闭空间间情欲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可参见陈涛《体感上海的方法:21世纪初中国电影叙事与城市空间》,《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 (11)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by Sacha Rabinovitch,New York:Harper & Row,pp.204-206. (12)Paul Rodaway,Sensuous Geographies:Body,Sense and Place,p.45. (13)汪民安:《城市经验、妓女与自行车》,《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32页。 (14)陈晓云:《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第45页。 (15)转引自汪民安《城市经验、妓女与自行车》,《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第131页。 (16)转引自汪民安《城市经验、妓女与自行车》,《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第134页。 (17)转引自陈晓云《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年)》,第46页。 (18)杨文杰:《导演宁瀛与〈我爱北京〉三部曲》,《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3日。 (19)宁瀛:《与城市俱进》,《北京青年报》2006年6月1日。 (20)Doreen Massey,"Politics and Space/Time," in M.Keith and S.Pile,eds.,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London:Routledge,1993,p.147. (21)关于“韵律性”(rhythmicity)的解释与论述,参见F.M.Wunderlich,"Walking and Rhythmicity:Sensing Urban Space," Journal of Urban Design,13(1),2008,pp.31-44. (22)Scott Lash and John Urry,Economies of Sign and Space,London:Sage,1994,p.252. (23)[德]奥利弗·格劳:《虚拟艺术》,陈玲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第2页。 (24)《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中的“迷失”直接来自英语和日语之间的不可转化或翻译,而《夜·上海》中男女主人公则由于文字的书写(中文和日语中都有汉字)而得以顺利沟通。 (25)《迷失东京》的重要灵感来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帝国》(Empire of Signs),中国台湾地区将此影片名译为《符号禅意东洋风》。标签:夜·上海论文; 出租车司机论文; 李米的猜想论文; 夏日暖洋洋论文; 民警故事论文; 找乐论文; 地理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喜剧片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犯罪电影论文; 恐怖电影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