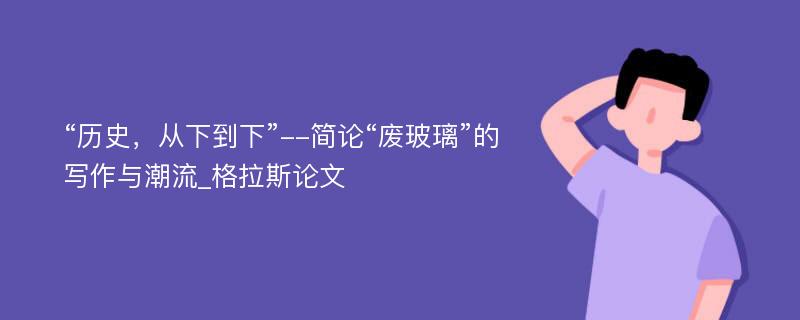
“历史,从下面看”——谈君特#183;格拉斯逆潮流的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拉斯论文,潮流论文,历史论文,谈君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58年秋,当年轻的君特·格拉斯(1927年生)在四七社(注:四七社是1947年由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召集有志文学的青年成立的文学团体,故名四七社。这是个没有会规的松散团体,参加者由里希特邀请。他们的目的是为一个新的民主自由的德国、为一个面向社会的文学而努力。这个结社在1967年解散。在它存在的二十年里,参与开会的成员约有二百人,有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在西德的文学界有决定性的影响。当初它是德国青年作家唯一的交往处所,后来参与的还有奥地利和瑞士作家。青年人在这里朗读自己未发表的作品,由同行自由评论,新人从而被发掘。格拉斯就是如此被发掘出来的。四七社还颁发四七社奖,二十年里只发了七次,得奖者后来都成了德语文学的著名作家,包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会上面对前辈和同辈作家朗读他正在写的小说的第一章时,听众就已经觉察到,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作品,当年的四七社奖颁发给他。次年,《铁皮鼓》出版,不但使格拉斯成名,也使战后德国文学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在这部小说出版四十年之后的1999年,格拉斯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晚来了数十年。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因为它“以嬉戏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在经历了十年的语言和道德的败坏后,开创了德国文学的新时代。”
要了解瑞典文学院这句评语的分量,不得不稍稍一提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德国文学面临的状况。1945年5 月随着希特勒政权的崩溃,德国人民从专制政权和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了,然而,他们面对的是物质生活的极端贫穷和精神生活的一片空白,精神上和道德上崩溃的程度不下于被轰炸成为废墟的城市,一切必须从零开始建设。文学也不例外。刚刚从战场上或从战俘营归来的年轻人,带着对战争的残酷、对俘虏营悲惨生活的回忆、带着对家人的怀念回来了,而家园破碎,个人前途和国家社会的状况令人彷徨。他们感受极深,思想和感情必须迸发出来,可是他们找不到可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十二年的纳粹统治和教育使语言公式化,纳粹僵化、腐朽的语言捆绑着青年人,他们想摈弃这种腐朽败坏了的口号语言,不愿再说假、大、空话,他们要寻找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朴实无华能够道出事实的语言,或如伯尔所说的能够让人栖身于其中的语言。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利希·伯尔(1917—1985)是战后开始写作的青年,格拉斯比他晚几年起步,他们以及同辈人在写作上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问题,要使得说出的词语不带纳粹时代的印记谈何容易,那不是避免使用某几个词就能做到的事,一定的表达模式和架构已经根深蒂固,他们需要时间转变自己的语言,需要时间慢慢学习,需要吸吮外国文学的精华,并与切断了的德国文学传统接上头。伯尔后来回顾这一段时期的写作时,认为德国战后文学从整体看来是寻找语言的文学。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青年作家,对这种寻找语言的艰辛过程,当然也是深有体会的。除了语言问题,战后的德国青年作家还需要时间思考伦理道德问题,思考历史问题,对此,文革后的中国作家自然也不陌生。
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大多数青年作家以最平实的语言揭露战争的残酷、战争带给人的恐惧、描写战后的困苦,题材全部来自现实生活,重点在于描写现实情况,生离死别、悲愤、抗议以及对法西斯的挞伐、对历史的疑问是主要内容,而内容是唯一重要的方面。进入50年代,对文学的理解逐渐深入,对语言的处理逐渐成熟,借助语言透视事物的方法得以发挥,语言表达的潜力得到重视,文学的形式试验从各方面表现出来,蒙太奇、内心独白、倒叙法、象征、比喻、隐喻等等手法使用很多。青年作家已经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语言,也有能力以文字对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自己的反应,对原有的问题作出反思,虽然理论界一再讨论叙述的不可能性,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危机,但是50年代已经出了不少重要作家和作品,写实派与现代派并存,不过,要到了格拉斯的《铁皮鼓》出来之后,德国文学才真正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那么《铁皮鼓》之倍受瞩目,原因何在呢?
二
《铁皮鼓》之成功最主要的该归功于格拉斯别出心裁塑造出的主人公奥斯卡·马采拉特,一个在娘胎里智力已经完成、三岁时决定不再成长而从地窖楼梯摔下去的侏儒,并由他在精神病院里叙述自己的故事。借助这个机警聪明的侏儒的视角、借用他作为叙述人,作者简直达到进退自如为所欲为的地步。奥斯卡拒绝长高,他的身高使他可以看到常人见不到或注意不到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视角在下面。他拒绝适应成人社会,使他可以不受任何伦理道德和礼教的约束,他生长于下层社会,又因为身体的缺陷,就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只能是个边缘人。以边缘人的地位看小市民的社会,在这一层意义上他的视角又在下面。因此,他能够看到小市民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需要和冲动,他们的饮食男女、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作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命运以及他们如何孕育了纳粹。格拉斯所想展示的就是:“历史,从下面看”。他毫无顾忌地把他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叙述出来,详尽的细节描写中,既不忌讳一般人不说出口的细节,特别是性方面的描写,又不忌讳粗俗鄙陋的语言。文字的力度和语言的丰富以及语言的驾驭能力,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另一大原因。中肯精确的词句、不断变换的语调、不同的语言层面和不同的语言形式、节奏活泼的片断、冗长的喃喃细诉或随口而出的方言俚语以及自由自在的嬉笑怒骂调侃讽刺,还有语言的双重性、比喻性以及物的拟人化的运用,是这部小说的语言特色。读过《铁皮鼓》的人会知道,格拉斯被誉为语言最丰富的德语作家不是没有道理的。丰富的语言和想象力以及别具一格的视角,加上从下面来的视角又分别由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夹杂叙述出来,使这部小说充满动力、张力和活力。格拉斯就这样让他的奥斯卡·马采拉特带着读者一起回顾他三十年的生命历程,并回溯到世纪初他的姥姥年轻的时代,同时将但泽市(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也是格拉斯的出生地)世纪初到50年代初的社会和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也就是这段时期德国历史的缩影。这一写作手法和风格贯穿着格拉斯几乎全部的作品。
格拉斯为他的奥斯卡配备了一个儿童玩的铁皮鼓,还赋予他一副尖嗓子,敲起铁皮鼓,他想召唤的往事就历历在目,尖嗓子一唱或一叫,玻璃就被震破。奥斯卡用《铁皮鼓》唤出被人遗忘的历史,因为在奥斯卡叙述生平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浸没在经济奇迹的欢乐中,生活富裕起来了,刚刚结束的噩梦般的历史有被忘记的可能;因为许多人,特别是当权者,不愿再谈这段历史了,而这是一段不能不面对的历史,历史的教训不能不记住,历史的罪责谁来负?奥斯卡用尖嗓子和鼓声代替正常的语言交流,因为语言已经败坏,而且当暴力起作用的时候,弱者的语言就苍白无力。
奥斯卡入学第一天,貌似和蔼的老师用好言好语没有能够让他暂时放下鼓,于是露出狰狞面目,她挥动教鞭,教鞭打在课桌上,但当孩子不肯伸出手被打时,老师狠狠地把教鞭打在鼓上,被触怒的小奥斯卡尖声叫起,老师的眼镜立刻碎裂,一幅荒诞怪异的景象。不过从这段故事已可看出鼓声的反抗作用了。孩童时代奥斯卡多次使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因而成为有名的坏孩子。反抗的先决条件是怀疑、不信任、不被假象所蒙蔽。奥斯卡五岁的时候,在诊所把大夫的玻璃瓶叫碎后,大夫用奥斯卡的材料写了二十页的报告,登载专业杂志上,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妈妈大为骄傲,而奥斯卡嗤之以鼻,看穿大夫所写完全不着边际,因为“我当时已经具备十分敏锐的怀疑精神”(第58页)。(注:G ünterGrass, Danziger Trilogie.Die Blechtrommel,Katz und maus,Hundejahre.Darmstadt:Luchterhand Verlag,1980.下文中引自同书的引文只在文中括号内注明页码,不另加注。)这种怀疑精神和识破假象的能力以及对假象的嘲讽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小的时候怀疑老师的教育方法、医生的论文,后来对天主教堂、对伦理道德、对战争、对疯狂的爱国主义、对迫害犹太人、对盲目的服从和尽义务都充满怀疑。可以说反抗和怀疑是《铁皮鼓》的主要精神,它传递出的是振聋发聩的声音。
政治主题很明显,批判意识非常强烈,而叙述中却看似随意道来。看似偶然观察到的细节描写,却具有重要的批判意义。奥斯卡亲眼看见1938年11月9日犹太教堂被烧的大灾难, 那是因为父亲听说城里发生事情,带他去看热闹,火光中,奥斯卡偷偷溜到附近的玩具商店,他担心城火殃及池鱼,因为他的鼓都是在这家店买的,他看到的是一群狂热分子正在店里打砸抢,一个洋娃娃正遭破腹之灾,而“他们不喜欢我的鼓,我的鼓经受不住这愤怒,它们不敢做声,它们膝盖发软,瘫倒在地”(第174页),这时,犹太店主已喝下毒药。
小说的另一主题是性。奥斯卡的叙述从他姥姥的裙子开始,小说开篇第一章“宽大的裙子”中,他不厌其烦地描写姥姥年轻时穿在身上的五条宽大的裙子,描写被追捕的纵火犯如何在两个警察的眼皮下,躲进姥姥的大裙子里,描写姥姥与这陌生男人肌肤亲近的表情,据说,其结晶就是奥斯卡的母亲,于是引出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和无关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插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也就被呈现出来了。如此这般,一年年过去,奥斯卡三岁时,已经是1929年了,纳粹在小市民和资产阶级有意和无意的支持下逐渐壮大,形形色色的人物跃然纸上,有活跃分子,有跟着走的人,也有默默认可的人,各式各样的场景铺张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群众的狂热、阅兵的场面、烧犹太教堂、抄犹太人的家、前线、战后货币改革、经济复苏等等,市民生活的描写占主要地位,而其中处处离不开食和色,性的描写特别多,以畸形扭曲的角度描写,这其中自有人性真实的一面,然而挑衅的意味十分明显。格拉斯这么做,显然有突破禁忌的用意,是反抗的体现。
作者的挑衅也针对天主教堂。对教堂的大不敬和讽刺从奥斯卡做婴儿受洗礼那天就开始,幼年时他又认为母亲因为有了情夫,才更加勤于去教堂忏悔,到了他做画室模特时,描写艺术学院的一位画家,看够了裸体女模特,有了性冲动后才能大笔一挥,画出圣母像,清楚显示作者有意把性同天主教堂联系起来。为他生了个孩子的继母,也就是他的情妇,名字就叫玛丽亚,这也不会是偶然的,对教会的亵渎又表现在奥斯卡让手下的一批希特勒童子军,锯下圣母玛丽亚怀中的耶稣像。这也是对教会抗议的表现。当我们在“信、望、爱”那一章读到城里一边在烧犹太教堂、另一边却有虔诚的妇女举着“信、望、爱”的标语在请人做慈善捐款(第175页), 在读到奥斯卡小时候在教堂看到十字架时联想到的各式各样的十字,其中也有纳粹的带钩的十字时(第119页), 就能够了解这种讽刺、愤怒和反抗了。
不过,奥斯卡与天主教的关系并不完全对立,他从小就不让自己的叫声把教堂的玻璃震碎,另外,他把鼓挂在小耶稣塑像手上,要教他敲鼓,居然听见鼓敲起来,并且听到耶稣说:“你是奥斯卡,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堂建在这磐石上。跟随我吧!”(第315页), 这样的幻觉,是不是显示奥斯卡潜意识里有救赎世人的意愿?奥斯卡三十岁生日时将被释放,而“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开始收门徒”(第513页),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耶稣用他的血为世人赎罪,而奥斯卡的三岁是“费尽力气并且做了最大的舍弃维持住的”(第314页), 我们可以把奥斯卡自我认定的牺牲理解为赎罪的表现,他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公诸于世,让自己也让他人面对和认识这既充满苦难又不光彩的历史,这样,他就既为自己也为他人赎了罪。
铁皮鼓是乐器,表示奥斯卡与艺术有缘,他的职业都与艺术有关,他曾在“前线剧团”表演,在艺术学院当裸体模特儿,做过爵士乐队的鼓手。鼓是他的谋生工具,又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慰藉,是他的栖身之地,他与鼓不能须臾分离,从小他就知道,没有鼓他不能也不愿意活,鼓声为他营造了一方自己的天地,使他得以无视外在生存环境的险恶而生存。在小说中,他多次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而艺术的确是这个侏儒的避风港和自由活动的处所,作者在此显然十分强调艺术的重要性,虽然他在谈艺术时,用的是十分调侃的语气。
最初,奥斯卡出于游戏的冲动,为艺术而艺术(第59页),后来,鼓声除了抗议还产生了其他效用。“洋葱窖”一章里,经济起飞后的一些生意人、医生、律师、演艺界人士、艺术家、记者、名运动员,还有法官和市政府官员,带着夫人、女友来到“洋葱窖”酒店,虽然他们很想把内心的苦闷和自己真正的问题一吐为快,很想显示出真正的、赤裸裸的自己,却表达不了真正的感情,他们失却了哭泣的能力。在酒店里大家同时切起洋葱时,被熏得泪眼朦胧,这时真正的泪水也就跟着出来了。后来,奥斯卡的鼓声取代了洋葱,他能用鼓声把他们带回孩童时代,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哭和笑,恢复成为能够表达真实感情的人。鼓声还救了一个在50年代被追杀的人,杀手出示1939年军事法庭的死刑状,他们自认所作只是尽可恶的职责而已,奥斯卡的鼓声把他们带到当初波兰骑兵队冲杀的状况中,让他们清醒过来。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艺术如何召唤历史和人性。艺术,也是《铁皮鼓》主题之一。
小说结束时,奥斯卡正过三十岁生日,他的谋杀嫌疑被澄清,势必走出精神病院的他,思考着将来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他想到了许多可能,不过他说:“一切的可能性都得检验,如果不是用我的鼓,用什么去检验呢。”(第522页)所以他决定敲出儿时常唱的儿歌“黑女厨”,借问前程,因为奥斯卡知道,他将在“越来越黑暗的儿时恐怖的阴影下”过日子。小说以“黑女厨”儿歌结尾,儿歌中出现的黑女厨、黑话语、黑钱,与此前提起的恐怖的阴影相呼应,特别是黑女厨,她从前就一直追踪他,如今她将迎面而来,奥斯卡将如何应付即将面对的社会的恐怖和黑暗呢?这个开放式的结尾,给这本看似充满嬉戏和黑色幽默的小说,添上一份伤感和沉重的气氛。
对个人的命运和整体社会的历史面貌,小说并没有顾此失彼,刺耳的声音和刺目的景象并没有减低读者心灵被触动的程度。作家的历史和社会使命感和小说的艺术性如何兼顾,一向是写作上的大难题,这个难题,格拉斯非常难能可贵地解决了。
格拉斯的早期作品有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6)、《轨道三叉口》(1960),剧本《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还有十分钟到水牛城》(1959)、《可恶的厨子》,写法近似法国荒诞派戏剧。小说则继《铁皮鼓》(1959)之后发表了《猫与鼠》(1961)和《狗的岁月》(1963),一般称为“但泽三部曲”。《狗的岁月》的故事和《铁皮鼓》一样,也发生在20年代到50年代的但泽市,反映的也是希特勒时代和德国战后至经济奇迹时代的历史面貌,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相近。不过叙述者有三个人,视角不一,语言形式更加多样化。马特恩和阿姆塞尔幼年时代是好友,在法西斯时代马特恩出卖了有犹太血统的好友,将他全口牙打掉,让他躺在雪地上,然而他自己受到良心的责备而沉沦,政治上得不到信任,战争中受了伤。战后两人言归于好,如今满口金牙的阿姆塞尔,以他的艺术天才,借稻草人的样子做出各种人物和景象,呈现出令人难堪的残酷往事,马特恩因而被迫正视历史。在这部小说里,艺术再次实现了召唤历史的功能而起了启蒙的作用。小说材料丰富,故事铺张,写作过程中,《猫与鼠》逐渐从《狗的岁月》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中篇。这叙述二次大战期间,少年马尔克因为生有特大的喉结而遭受同学取笑,因此他格外努力表现,虽然得到不少掌声,内心却很孤独,他得到了勋章,却丧失了生命。外界就像猫,马尔克就像老鼠。把环境置于希特勒时代,个人的遭遇就显得更加严峻了。这两部小说的批判精神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格拉斯的主要作品有戏剧《平民排练造反》(1966》、《之前》(1969),诗集《盘问》(1967),小说《局部麻醉》(1969),随想录《蜗牛日记》(1972),这些都是以当时的政治时间和政治环境为主题的作品,写作上表现出极端的政治化倾向。这期间格拉斯身体力行参与政治,他在1965、1969和1972的竞选活动中,积极为社民党出力,他的政治理想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不赞成激进的革命手段,认为蜗牛式的渐进改良是比较可行的社会发展方式。
到了长篇小说《比目鱼》(1977),格拉斯恢复了《铁皮鼓》的写作风格。他在这部集童话和历史于一身的长篇巨著里,以诗歌、散文以及大量的食谱描写了人类饮食的历史及女权被取代的经过,故事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一个长生不老的渔夫和他抓到的一条长生不老的比目鱼,对渔夫怀孕的妻子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帝王将相的历史成为格拉斯取笑的对象,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是故事的主要组成部分,男人是战争祸害的罪魁祸首,对环境的危机也要负绝大责任,妇女虽然一直是受压迫者,可是人类社会还是靠着妇女才保留着人性。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想象力、随意道来的嬉笑怒骂、毫无忌讳的详尽细节描写,仍然是格拉斯写作的特点,表现的自然是从下面看到的历史。这次特别强调了女性意识。
《特尔格特的聚会》(1979)是献给“四七社”创始人维尔纳·里希特的中篇小说。这是格拉斯虚构的一次德国巴洛克诗人聚会,时间在1647年,影射三百年后“四七社”的作家聚会。格拉斯对德国巴洛克文学颇有研究,《铁皮鼓》继续欧洲流浪汉小说的传统,有德国巴洛克小说《痴儿西木传》的痕迹,他的写作语言也有巴洛克语言膨胀的风格,他对巴洛克作家相当了解,聚会中,赋予他们每个人恰如其分的言谈举止。就他们的理解,文学和作家的社会责任应该直指世界的苦难,唤醒世人的良知。小说里,一边是诗人风趣的高谈阔论,离他们聚会不远的另一地方则有政治人物和军事领袖严肃的洽谈。诗人代表时代的精神,政界人物代表实权,或许格拉斯有意借着同步进行的会议,强调精神界的参与意识,并强调实权政治必须有精神界的参与,二者同样重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诗人散会之时,也是结束三十年宗教战争的和平条约将要签订之日,我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知识分子尽管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但是左右世界现状的是实权人物。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家在现实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格拉斯十分关注的问题。格拉斯认为二者可以兼顾,从小说的结局看来,则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拳拳赤子心可敬可佩亦复可悲。知识分子之可爱处或许正在于此吧。
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而世界人口爆炸,各国军备竞赛停止无期,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对于人口、生态及和平这几大问题格拉斯倍加关怀,1980年出版的小说《头脑的产物》描写的就是个人在这种环境中的困惑,提出到底要不要后代的问题。他在停笔多年之后,于1986年推出又一巨著《母鼠》,就此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次,他的矛头不止指向德国,而是人类总体,他又一次用荒诞虚构的景象,指出人类自我践踏必定引出的严重后果。叙述者梦中与一只母老鼠的对话占全书主要的篇幅,谈话内容包括人类整个历史,从诺亚的方舟救出人类到人类在一次核爆炸后消灭,以及人类之后的世界景象,那时将是个老鼠的世界,鼠说:“如果那时没有我们,那么就没有东西会谈到人类。人类遗留下的,就我们记忆所及……就是垃圾。”(第14页)(注:Günter Grass,Die Rattin,Darmstadt:LuchterhandVerlag,1986.)人说:“不!老鼠,不!我们还在活动。比如, 已经和牙科大夫约好日期。”(注: G ü nter Grass, Die
Rattin,Darmstadt:Luchterhand Verlag,1986.第15页)最后,在群鼠的取笑声中,人说:“只是假设一下,我们人类还存在。”“……那么这次我们会相互关怀,并且要和平相处,以爱心和谦让,我们的天性原是如此。”(注:Günter Grass,Die Rattin,Darmstadt:Luchterhand Verlag,1986.第505页。)与人鼠谈话交织在一起的有好几个同时进行的情节,《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马采拉特如今已六十岁,是影片公司的大老板。他的姥姥正要庆祝107岁生日。五位妇女乘船出发, 研究波罗的海水母的状况,小说中,关心海域的生态平衡、关心树木死亡的是妇女。女性意识和在《比目鱼》中一样强烈。此书写作风格没有改变,以生动流畅老成诙谐的文字,轻松自如地从一个叙述角度转换到另一角度,比如,叙述者需要奥斯卡出现,“于是,我叫一声,喂,奥斯卡,他就出现了,坐着一辆豪华奔驰车来了。”(注:Günter Grass, Die Rattin,Darmstadt:Luchterhand Verlag,1986.第30页。)书中充满忧心忡忡的警告,奥斯卡的电影剧本《十二点前的五分钟》就是一部警示片,是人类末日前最后的挣扎,而人类的希望也正在这里。
格拉斯多才多艺,对环境的关注还以其他艺术形式表达出来,1990年的版画集《死木》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作品凡有配画皆出自自己手笔。格拉斯以小说著名,而他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小说中常夹杂着诗。也出版诗集,1997年的诗和水彩画集《寻找失物》隐含的意义是寻找被历史忽略的事物。
善于写宏篇巨著的格拉斯,本世纪最后一年出版的著作却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我的世纪》由一百篇短篇组成,从1900年到1999年,逐年以一篇故事为代表,由不同的叙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以此带出德国的历史。格拉斯想通过故事引导人们认识历史、进入历史,面对历史,如他在获知得奖消息当天对采访的记者所说那样,从《铁皮鼓》(1959)到《我的世纪》(1999)他所做的工作是一致的,就是“从下面看历史”,也就是以普通人的角度看历史。从小事情看历史,如同他的长篇小说,他在《我的世纪》里叙述的都不是历史舞台上的重大事件,而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个人经历。不过一百个德国人的经历或对话和思考合起来,德国人经历的历史真实也就显示出来了。这一百个人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男女老少以及左中右各派人士都有,其中自然也不乏格拉斯的化身。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德国士兵写回家的信,讲述他1900年在八国联军的行列中攻打北京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战争中残酷的烧杀掳掠使人想到其他的战争,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人类世界的互相残杀不知何时得以完结。从个人经历谈到人类大事,是这本书里多数故事的写作方式,涉及的题材有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一次大战后的通货膨胀、失业大军、希特勒掌权、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二次大战后德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妇女、1953年东德的工人暴动、1962对纳粹头子艾希曼的审判、1964年关于奥斯威辛的审判,还有左派运动、恐怖分子、核事故、两德统一及有关的事件等等。1972年的故事叙述一对德国左派夫妇向警察举报乌丽克·麦霍夫,导致麦霍夫被捕,她后来死于监狱。麦霍夫事件在当时的德国是件大事,不过格拉斯在此描述的重点是告发者的心理状态,是他们意识形态上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在当年也是很典型的。《我的世纪》里有不少诸如此类可以成为时代的典型的故事。曾经身历其境的人,读来一定感到亲切。格拉斯并不谦虚,1959年的故事写的就是《铁皮鼓》出版大获成功的情况,似乎他自己当时已认为这部小说是划时代的作品。《我的世纪》中,一百个故事都不长,许多故事是带着距离感写出的,较少慷慨激昂刺耳的语调,几乎没有道德教条,但是其中都浸着格拉斯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他的讽刺和幽默也处处可见。这本书和格拉斯所有其他著作的命运相同,评论界的反应不一,反对它的人,不会因为作者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而改变意见。
四
格拉斯执著地关注政治、人权、环境,对公众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他的写作和画册,以他的演讲和谈话,以他的作品和他的实际行动,都是那么样地强烈,批评起来直指痛处,他的意见又常独树一帜,无不在舆论界引起极大争议。最早的《铁皮鼓》虽然得到广泛的赞赏,亦惹来强烈的批评,不来梅文学奖的评委会把奖评给格拉斯,却被市议会否决掉,1965年的毕希纳奖颁发给格拉斯,而抗议者举着标语责问:纳税人的钱是奖励艺术还是奖励黄色小说?然而,格拉斯引起的轩然大波无过于他对两德统一的看法,1989年全国上下为之欢欣鼓舞的统一,他极力反对,觉得统一需要时间,应有妥善的计划,目前匆忙的统一,不过是以西德强大的经济力量并吞东德,他也唯恐德国的民族主义因此再次抬头。以一人之力,抗众人之意,逆时代潮流,招惹来的猛烈抨击可想而知。但是他不屈不挠,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广阔田野》,在这部长达784页的小说里, 格拉斯借统一后托管局一个年纪已老的办事员之口,大谈德国历史和德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冯丹纳的作品,因为这位办事员是一个冯丹纳迷,他批评现状,并认为原先的东德也未必就那么糟糕,他已经不愿再居住在德国了。又叙述一位犹太教授统一后的遭遇,他认为犹太人在此没有安身之处,因此而自杀。小说遭到恶评不在话下,国内外的报刊杂志、电视、广播充斥有关评论、谈话、辩论、演说以及批评的评论。对于小说本身的美学批评集中在:人物似影,没有血肉,过于冗长,无法卒读,结构松散,内容单薄。事实上,反对统一才是受到如此恶评的主要原因。舆论和论坛上激烈的交战,引发出一个问题,文学对政治到底可以介入到什么程度?文学批评是美学批评还是道德批评?
1997年德国书商和平奖颁给土耳其作家亚萨尔·凯末尔,格拉斯在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褒奖词称赞凯末尔为人权的守护者,他介绍了凯末尔的作品后,话锋一转,批评起德国的难民法不顾人权,又批评德国已经沦落为仅仅是经济场所,他为他的国家感到羞耻。这一来,格拉斯又成为众矢之的。
格拉斯中学尚未毕业就被抽去当兵,战后从美国俘虏营回到德国,开始反思纳粹意识形态导致的恶果、反思意识形态的危险性,自己能够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就有责任做历史的见证人,寻找纳粹能够在德国社会找到温床的原因,以为告诫。这种责任心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没有丝毫改变,他的实际行动和他的写作从来都是一致的。历史,从下面看,写作,为弱者言,逆潮流而行,时刻批判,时刻怀疑,怀疑冠冕堂皇的大话,怀疑轰轰烈烈的壮举,这就是君特·格拉斯,当代德国的堂·吉诃德。在自己的国家争议极大,在国际社会却为德国带来声誉,因为,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知道自我反省的民族。人类社会中,巨大的风车不停转动,它虽然貌似无敌,心里真正害怕却又需要的,还是堂·吉诃德的长矛。
标签:格拉斯论文; 文学论文; 铁皮鼓论文; 奥斯卡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我的世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