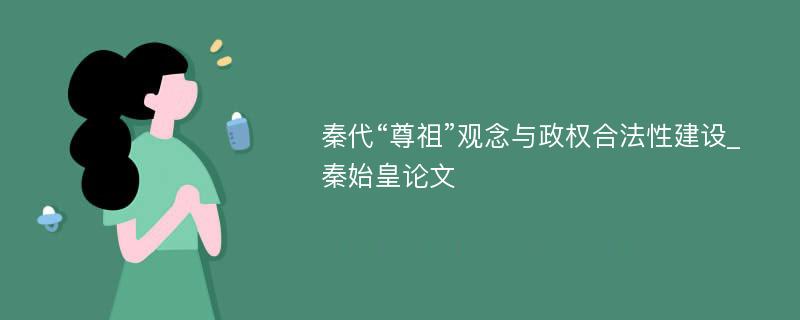
秦朝“敬祖”观念与政权合法性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朝论文,政权论文,合法性论文,观念论文,敬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6)03-0024-07 秦统一之后,继承秦国“敬天”、“敬祖”的思想并加以改造,形成具有秦朝特色的官方意识形态。其中关于“敬天”的问题,学界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①而对于秦人的“敬祖”行为则关注不多,本文试从秦人“敬祖”的具体措施入手,进一步讨论秦始皇通过“敬祖”手段对皇权的强化过程。 一、“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统一六国,令群臣商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提出: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制曰:“可。” 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 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② 秦始皇“议帝号”诏,主要完成了两件事。一是决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二是追尊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并以“子议父”、“臣议君”不合理为理由,废除谥法。对于秦始皇称“皇帝”一事,学界不乏讨论,③总的来说,“始皇帝”之名,是受三皇、五帝、星宿崇拜、凤鸟崇拜等多种因素影响,是集先秦圣君名号的大成,秦始皇以“始皇帝”自称,一方面是强调权力承自先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兼有“功过五帝,地广三王”④的超越之势,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而与之同时提出的追尊太上皇一事,虽学界讨论较少⑤,但据提出的时机来看,显然也有其深刻的政治用意。 秦始皇追尊生父为太上皇,这种做法在先秦时代便有迹可循。《史记·周本纪》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又张守节《正义》载:“《易纬》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郑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称王,已改正朔布王号矣。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岂殷纣尚存而周称王哉?若文王自称王改正朔,则是功业成矣,武王何复得云大勋未集,欲卒父业也?《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据此文乃是追王为王,何得文王自称王改正朔也?”⑥这段概括周文王政绩的记载中,司马迁和张守节对文王之号持不同意见。司马迁认为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是文王的政绩,而张守节根据武王的政绩和《礼记大传》的记载推论武王才是追尊先祖之人,甚至文王之王号也是死后追尊而来。对此,晁福林、王晖、刘国忠等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已经证明文王当为生时称王,并非是死后追谥,⑦所以古公和公季的王号均为文王追尊,具体实施办法是将先祖的爵位提高一级,即由公尊为王,这便是秦始皇追尊太上皇的雏形。战国时,秦国也存在追尊之事。周平王即位之初,西戎来扰,秦襄公出兵讨西戎,解平王之困,又武装保护平王东迁洛邑,功劳显著,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史称秦襄公,赐其岐山以西的地区,秦才有了封国。⑧而他的父亲秦庄公之所以成为第一位称“公”之人,便是襄公在其死后追尊的。⑨秦国的追尊之事还存在于女性中。史载:“(秦昭襄王)五十六年秋(前251),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⑩唐八子,姓唐,是昭襄王的妾,孝文王的母亲,其在孝文王即位时已经去世,故死后被追尊为太后。(11)八子在内宫的地位并不高,秦孝文王将母亲由八子直接尊为太后,追尊的等级远不止一级。总之,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依照周制,(12)一直存在着统治者即位后追尊逝去先祖的做法。(13) 秦始皇统一之后,依然保留了这一做法,其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除亲缘关系外,更是对庄襄王过去功绩的肯定。(14)究其原因,主要与秦国的建国方式有关。战国时期,秦一直被冠以“虎狼之国”的称号。秦惠王时,游腾向楚王献策时就说过:“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15),苏秦也有“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16)的言论。秦昭王时,虞卿谏赵王不要向秦求割地求和时,同样指出“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17),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汉代。贾山就曾提出:“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18)这种对秦国的认知,从客观上说明了秦国武力征伐的建国方式,但也正是这种“虎狼之势”,最终成就了秦的统一大业。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指出:“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19)桑弘羊和司马迁也有类似的观点。(20)不难看出,秦完成统一是经过秦国历代君王的不断积累,逐渐壮大,才最终成就的。被尊为太上皇的秦庄襄王,在位三年期间,一方面颂扬先王,施德厚民,另一方面大力征伐,灭东周,使蒙骜破三晋,置三川郡、太原郡,文治武功均有成绩,这从其谥号“庄襄”(21),即兴兵征伐、开疆拓土之意也能够体现出来。秦始皇追尊秦庄襄王就是借对先祖功绩的肯定来证明权力的正统性。同时,由于谥法开始出现美恶之分(22),秦始皇最终选择废除谥法,摒弃了后人评论先王的做法,最大程度上维护皇权的尊严。 汉承秦制,生而追尊太上皇(23),但相较秦代“续六世之馀烈”建立起来的帝国,汉的建国方式则截然不同。陆贾在授尉佗南越王印的时候曾说过:“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24)汉高祖刘邦以亭长身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建立汉政权,这使得其在利用先祖解释权力传递的正当性时,无法选择标榜先祖功绩的做法,只能转向另一道路,即强调以“孝”治国。于是,汉高祖刘邦在效法秦制追尊太上皇时,更突出对太上皇的“孝”,其在太上皇在世时便因其喜好,建新丰,迁故人充实。(25)在太上皇崩后,令诸侯王在郡国国都内立太上皇庙,并在太上皇庙举行立太子仪式,(26)借“孝治”完成了太上皇及太上皇庙在权力合理性建构中的载体作用。 二、“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 《礼记·祭法》郑玄注曰:“庙之言貌也,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27)宗庙象征着祖先,是祖先在礼仪中的物化形式,具有皇帝继位、受斋、告庙等政治功用。同时,皇帝的个人礼仪,如冠礼、婚礼等也在宗庙举行。(28)可以说,宗庙礼仪同时兼具国家礼仪与皇帝个人礼仪两种性质,历代皇帝都是通过祭祀创业者及其继承者的宗庙祭祀,才能确认自己的权力渊源。(29)这使得宗庙成为从亲缘解释皇权合理传递的重要来源,也是“敬祖”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先秦时代,秦人就表现出对宗庙的重视。《吕氏春秋》载:“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30)规定宗庙要位于城市中心的位置,从宫城布局上明确了宗庙的中心地位。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建筑群地处秦故都雍城的中部偏南,东西长160多米,南北宽90多米,其位于宫城中心的位置与文献记载吻合。遗址先后发现牛、羊、空、人、车、牛羊、人羊等七类祭祀坑181个,出土各类陶瓦、陶、金、铜、铁、玉等器物,其从规模和出土器物来说,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保存最好的宗庙建筑群。(31)足见秦人对宗庙的重视。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继承了先祖对宗庙尊崇的传统,不断强调宗庙的重要性。在“议帝号”之前,便有“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32)的言论。在群臣提出分封诸王的时候,秦始皇再次强调祖先对秦统一的重要性。(33)邢义田认为:“秦王政相信秦之所以能兴起、兼并六国是赖祖先神灵的护佑……秦并六国,置祖庙于天下之中,似乎有意以此证明他们得以王天下的根据和凭借。”(34)实际上,不仅是秦始皇本人,群臣对于宗庙的政治象征意义也有共识。丞相王绾、卿李斯、王戊等劝始皇琅琊刻石时就说道:“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35)将宗庙制度的明晰作为始皇的政治功绩之一。李斯临死前在狱中上书,也提到“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36)所谓七宗罪说的是反语,而这之中提出修宗庙一事,也是宗庙重要性的一个旁证。 秦二世也很重视宗庙祭祀,曾私下对赵高说:“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37)将安宗庙作为国家兴盛的标志之一。二世皇帝元年(前209),下诏增益秦始皇寝庙的祭祀牺牲,令群臣商议如何才能崇显始皇之庙,群臣认为: 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38) 关于先王庙的位置,刘庆柱指出:“孝公以后的诸秦王陵墓,分为两大陵区:一在秦咸阳城西北部,距城不远,一在秦咸阳城东南的郦山西麓,距城较远,后者因在都城之东,故又称‘东陵’。”(39)滕铭予在研究关中秦墓的时候指出,宝鸡地区北部的凤翔一带已发现的墓地年代多在春秋中期以后,多属第一级别,应与秦都雍城有关。西安地区只在咸阳一带发现了第一级别的墓地和少量零散的A类墓,应与秦都咸阳有关。(40)考古发掘出的凤翔和咸阳高规格秦墓的广泛分布,或许可以成为秦二世所谓“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的一个间接证据。 关于秦的庙制,二世之前并不明确。秦二世即位后,群臣提出据《礼记》改革庙制,试图规范宗庙制度,具体仪制为: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41)这种宗庙制度规定了不同等级立庙的数量,借此区别各阶层的等级性,此举无疑是想通过宗庙礼制的确立进一步强调秦二世的天子地位。其中,对于秦始皇的极庙更是推崇,改始皇庙为帝者祖庙,要求全国都要进献贡品、增加祭品;天子则按照仪注单独奉酒祭祀始皇庙;群臣祭祀时需按照礼仪顺序进入,以突出其“帝者之祖”的地位,这也是二世对于秦始皇奉自己为“帝者之祖”观念的继承。 事实上,秦二世是否施用天子七庙制度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中均没有明确的证据,这之后的庙制也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直到汉元帝时,根据韦玄成的意见定立新的庙制,罢郡国宗庙、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不毁;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42)至此,以天子七庙为主体,实行合祭制和昭穆制度的天子庙制才有了雏形。 三、“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秦始皇称“始皇帝”,将自己置于帝祖之列,并通过标榜“敬祖”观念,进而要求后世帝王尊崇自己“帝者之祖”的身份,借以达到其皇权“二世三世传之无穷”的目的,形成了秦朝新的“敬祖”观念,这种观念在秦始皇营建陵墓和历次官方刻石中均有体现。史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43)秦始皇在生前,便开创性的按照自然景观营建陵墓,开帝者陵墓的先河。巫鸿从宗庙建筑的纪念碑性讨论了秦始皇的宗庙制度由宗庙到陵墓的转变过程,认为宗庙代表祖宗,而墓陵则代表家庭和个人的权势,东周之后,个人的权势、财富及野心不断膨胀,墓陵建筑也随之膨胀,最终导致秦始皇骊山陵的出现(44),揭示了秦始皇营建陵墓的政治意图。二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在渭南建信宫,后又更名为极庙,效法天极,与咸阳宫室相对应,由极庙筑路直通郦山陵墓。(45)秦始皇将骊山陵墓与渭南极庙相连,以衣冠道连接两者,奠定了后世帝王陵寝,宗庙合一的基础。三十五年(前212),又营建阿房宫,仿照天极,做阁道抵达咸阳宫室。田天认为,极庙是始皇生前为自己所建宗庙,其与阿房宫同为渭南宫殿群的核心建筑。始皇修造的咸阳城有两条通路,一条自渭北至渭南阿房,一条自骊山到极庙。两条通途分明生死,其终点都对应帝星。换言之,始皇是使自己所在的位置,永远与帝星相呼应。(46)史载咸阳宫城“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47)。按照星象布局,咸阳城象征天之中心,而陵墓正通向中心咸阳,从当时宫城的布局与方位来看,田天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总之,秦始皇大力营建陵墓、极庙等具有宗庙性质的礼制建筑,无疑是在强调自己“帝者之祖”的身份,并在封禅和巡狩的多次官方刻石中不断重申此观点以昭告天下: 二十八年(前219)峄山刻石: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48) 二十八年(前219)泰山刻石: 皇帝临位……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49) 二十八年(前219)琅琊刻石: 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50) 二十九年(前218)之罘刻石: 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51) 二十九年(前218)东观刻石: 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52) 三十二年(前215)碣石刻石: 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53) 三十七年(前210),南海刻石: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後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54) 巡狩和封禅本为祀天礼中的非常祭,以天为主要祭祀对象,以歌颂上天为主要内容,而秦始皇各地的刻石内容并非如此,其碑文一是颂扬自己首创之功,如“皇帝立国”、“皇帝临位”、“皇帝作始”等;二是要求后世继承自己的事业,如“永承重戒”、“垂于常式”、“长承圣治”、“垂著仪矩”、“光垂休铭”等。这些表式性文字的大量使用,就是要通过官方舆论,宣扬始皇“帝者之祖”,皇权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观念。 秦二世即位后,继续强化秦始皇帝祖的形象,上文提到的抬高始皇极庙的礼仪规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二世还重巡始皇巡狩之地,并在始皇刻石处刻石,用以“章先帝成功盛德”,并下诏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55)后在丞相李斯等人的劝说下,才决定将二世诏书刻于始皇诏书之左,以突显始皇独尊的地位。现出土的秦代度量衡中就不乏两诏铜椭量、两诏权的现象,(56)足证二世对始皇的尊崇。 有趣的是,刘向《说苑》中记载了一段秦始皇与鲍白令之关于禅让的讨论,大意为:秦始皇召群臣讨论皇位的继承是选用五帝的禅贤之法,还是三王的世继之法,鲍白令之一番引经据典,甚至不惜冲撞秦始皇,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效法五帝禅贤之法,秦始皇于是放弃禅让之意。(57)关于此段文字的时间渡辺信一郎推测当为西汉后期。(58)这则史料中秦始皇的形象显然与《史记》中的秦始皇形象有所出入,再加之这则史料只见于《说苑》,此事是真实发生,还是西汉末年刘向受“天下为公”思潮影响编造的故事,尚无定论,但故事的结局无疑是后人为秦始皇皇权“传之无穷”寻找的借口,或许可以作为秦始皇宣扬“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一个旁证。 总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承秦国的“敬祖”观念,追尊庄襄王。一方面强调自己对先祖功业的继承,解释皇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秦始皇不断标榜“敬祖”观念,并通过营建极庙、陵墓、刻碑等措施反复强调其“始皇”的身份,将自己置于“帝者之祖”的位置,形成新的“敬祖”观念,要求后世帝王尊崇自己,从而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注释: ①杨天宇:《秦汉郊礼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田静、史党社:《论秦人对天或上帝的崇拜》,《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236页。另参见曾磊:《秦始皇“议帝号”诏评议》(未刊稿)。 ③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李俊芳:《秦朝最高统治者称号问题试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刘泽华:《秦始皇神圣之上的皇帝观念:先秦诸子政治文化的集成》,《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周新芳:《“皇帝”称号与先秦信仰崇拜》,《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先秦帝王称号及其演变》,《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6页。 ⑤王子今、李禹阶:《秦汉时期的“太上皇”》,《河北学刊》,2009年第11期。林燕:《“太上皇帝”与“太上皇”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辨异》,《兰台世界》,2015年第21期。 ⑥《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19页。 ⑦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王晖:《周文王称王史事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刘国忠:《〈保训〉与周文王称王》,《光明日报》2009年4月27日。 ⑧《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9页。 ⑨《诗经·秦风》孔颖达疏曰:“襄公始为诸侯,庄公已称公者,盖追谥之也。”(《毛诗正义》卷六《秦谱》,《十三经注疏》,北京: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18页。 (11)《史记》卷一〇《孝文帝本纪》裴骃《集解》引应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第435页。 (12)《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十三经注疏》,第219页。 (13)追尊是追封谥号的一种形式,这也是秦始皇将追尊太上皇与废除谥法作为同一事件提出的原因。 (14)王子今、李禹阶:《秦汉时期的“太上皇”》,《河北学刊》,2009年第11期。 (15)何建章:《战国策注释·西周策》,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页。 (16)何建章:《战国策注释·楚策一》,第508页。 (17)何建章:《战国策注释·赵策三》,第726页。 (18)《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2328页。 (1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8-280页。 (20)(汉)桑弘羊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八《结和》:“伯翳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穆公开霸,孝公广业。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孙成之。”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80页。《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秦起襄公,章於文、缪,献、孝之後,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第759页。 (21)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彙校集注》卷六《谥法解》:“兵甲亟作曰庄,叡通克服曰庄,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714页,第690-691页。 (22)楚共王就有主动请恶谥的例子,其在弥留之际就说道:“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00、1001页。 (23)(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羣、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一四“太上皇”条:“《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号,尤周曰‘太王’也。汉则以为生号,而后代并因之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4页。 (24)《汉书》卷四三《陆贾传》,第2111页。 (2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第387页。 (26)《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92页。 (27)《礼记正义》卷四六《祭法》,第1300页。 (28)参见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台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00页。 (29)参见[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0页。 (30)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七《慎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0页。 (31)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3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3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第239页。 (34)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 (3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7页。 (36)《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2页。 (37)《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2页。 (3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6页。 (39)刘庆柱:《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5期。 (40)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41)《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第382页。 (42)《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第3118页。 (4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5页。 (44)参见[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4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1页。 (46)参见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3页。 (47)史念海主编,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一《咸阳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48)《金石萃编》卷四《峄山刻石》,《历代碑志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4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3页。 (5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5页。 (5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9页。 (5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0页。 (5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2页。 (5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1、262页。 (5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7页。 (56)参见邱光明编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8页,第350-354页。 (57)(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释》卷一四《至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7、348页。 (58)参见[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第131页。标签:秦始皇论文; 史记论文; 秦始皇本纪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秦朝论文; 礼记正义论文; 咸阳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