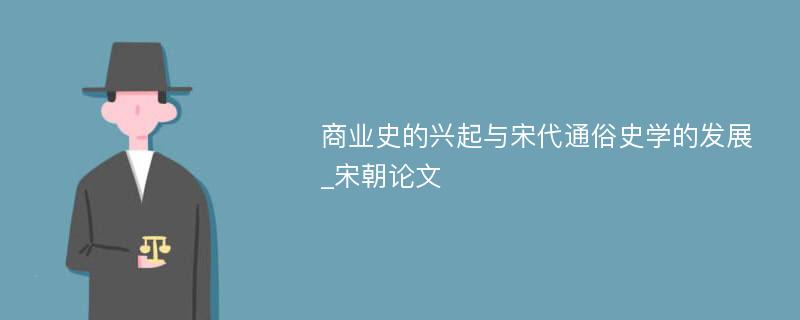
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商业性论文,宋代论文,通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092;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0583—0214(2000)01—116—07
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颇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中国史学的长河至宋代而波澜壮阔,中国史学的画卷至宋代而绚丽多彩。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兴起于这一时期的商业性讲史。它为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中国的讲史活动起源极早。在宋代以前,它们包括以追述民族或家族历史为内容的述祖性讲史;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而进行的政治性讲史;在各类学校中以传授历史知识为目的的传授性讲史;以及以“街谈巷语”为主要特征的民间通俗性讲史。(注:参见拙文:《先秦两汉讲史活动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到宋代, 在这些类型之外,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讲史活动——商业性讲史开始出现并日趋兴盛,在宋人的著作中,将其称为“讲史”、“讲史书”、“演史”、“说史书”等等。这种讲史与此前诸类讲史活动相比较,具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商业性特征,它与此前诸类讲史的非商业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宋代这种讲史的内容和形式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也将宋代兴起的这种讲史称为“宋代讲史”,以区别于由前代延续下来的其它类型的讲史活动。宋代讲史的商业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讲者身份与讲述目的的商业性。在宋代以前的各类讲史中,作为讲述主体的讲史人,其身份是非商业性的。他们或为教育者,或为政治活动的咨询者,或为历史知识的传播者,不以讲史作为商品换钱谋生。而宋代讲史则不同,讲述者是以一种精神产品的出售者的身份来从事讲史活动的,被宋人归入“售艺者”之列,是一种商业性的身份。因为具有这种身份,宋人对他们的称谓也与“市”这一作为商业性标志的措辞联系在一起,称其为“市优”、“市人”。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的《田舍即事》诗(之九)即云:“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将讲说楚汉战争史的讲史艺人称为“市优”。北宋学者高承在《事物纪原》卷九中记载说:“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将讲说三国历史的讲史者称为“市人”。“市优”、“市人”的称谓,生动地表明了讲史者的商业性身份。讲史者的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从事讲史活动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换取听众的钱币,即商业性目的,从而使宋代讲史成为一种商业性活动。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九十二转录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志》支丁卷第三《班固入梦》中的记载说:“乾道六年(1170年)冬,吕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嵎)、魏子正(羔如)、上官公禄(仁)往临安观南郊,舍于黄氏客邸……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其尾云:‘今晚讲说《汉书》。’”在这里,讲史者使用了较为显眼的带有商业广告性质的“招子”,通告将要讲述的内容。这种招子是中国传统集市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一种“民俗标志”,它们“事实上已有商业广告的性质”(注:乌丙安:《中国民俗学》第六章《市、商的民俗标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它是此前讲史活动中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的现象,是宋代讲史者对其商业性目的的毫不隐讳的表白,也是宋代讲史作为一种商业行为的确凿无疑的证据。
其二,讲史听众与讲听关系的商业性。宋代以前各类讲史的听众,无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在听讲时,其身份都是受教育者,而不是讲史这一精神产品的购买者与消费者,是一种非商业性身份。而在宋代讲史中,听讲者首先是作为一名精神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进入听讲人这一角色的,是具有商业性身份的听讲者。宋代讲史中讲述者身份、讲史目的与讲史听众的商业性,决定了在讲史过程中讲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换关系,即讲述者收钱讲史,听讲者付钱而听。每讲一次,收付行为便重复一次,二者之间的商业性关系由此形成。《东坡志林》卷一《塗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记载说:“王彭尝云:‘塗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显然,在这里,“塗巷”中的儿童须从家里拿钱付与讲史者,才能取得听讲“三国事”等“古话”的权利。而讲史人则要在收取包括“塗巷小儿”在内的听讲者支付的钱币的情况下,才讲给他们听,双方完全是一种商业性的交换关系。
其三,讲述场所的商业性。在宋代以前,无论何种讲史,都是在非商业性场所中进行的。述祖性讲史通常是在宗庙、祠堂等祭祀祖先之处或在举行节日庆典的地方进行;政治性讲史的场所则是宫廷、朝堂或官署;传授性讲史或在学校,或在家中;民间通俗性讲史被称作“街谈巷语,道听塗说”(注:《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生动而又形象地指出了它在讲述场地和讲述时间上的随意性。田间地旁、闾里小巷常常是它的讲述场所。而宋代兴起的商业性讲史则完全不同,它是在从事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商业性场所中进行的,其中又以“瓦市”为主。瓦市北宋时又称为“瓦肆”(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二,《酒楼》;卷之五,《京瓦伎艺》。),南宋时称为“瓦舍”、“瓦市”,或直接称“瓦”(注: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 123页。)。又通称为“瓦子”。宋人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解释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即聚合容易,分散方便之意。“市”、“肆”则是专供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正如当时的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布市、酒肆、茶肆等等皆为商业活动场所一样。(注: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95页。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市》,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440页。)这种瓦市, 在北宋时已十分热闹繁华。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北宋首都汴京的瓦市中,包括“讲史”在内的各种伎艺“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在汴京东角楼街巷中的诸多瓦市内,有分别用于从事“货药、卖卦”等买卖和各种伎艺表演的大大小小的“棚”,其中最大的棚“可容数千人”(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二,《东角楼街巷》。)。在南宋首都临安,瓦市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数量还是繁华程度都超过了北宋汴京,有的一个瓦市内,就容纳了“勾栏十三座”。到元代,瓦市仍旧十分兴盛。元人郭罗洛纳在《河朔访古记》中记载说:真定路(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的南门外,“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娼门,酒炉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可见,至元代,瓦市仍旧是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场所。除瓦市之外,宋代商业性讲史也在茶肆、酒楼等商业消费场所中进行,前面所引洪迈《夷坚志》中所载吕德卿等人在茶肆中“见幅纸用绯帖其尾云:‘今晚讲说《汉书》’”即为明证。在宋代,瓦市、茶肆、酒楼是从事商业性讲史活动的一种固定场所。如南宋临安北瓦的十三座勾栏中,便“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注:《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至于在寺庙、乡村、闾巷、路旁等非固定场所中进行的讲史则要临时围起一个空地用于讲述。尽管它们已不是宋代讲史的主要场所,但在商业性这一特征上,与固定的讲史场所是完全相同的。
由上可见,宋代讲史从讲述者身份与讲述目的、讲史听众与讲听关系以及讲述场所等方面,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其商业性的特征。它不同于前代出现过的诸类讲史,它是讲史活动的一种全新的类型——商业性讲史。可以说,商业性是宋代讲史的本质特征,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失去商业性,宋代的这种讲史将难以生存。
二
商业性讲史之所以兴起于宋代,是和当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时代发展在史学中的一种反映。北宋建立后,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削平了南北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战乱的局面,完成了统一。此后的三百余年,尽管先后有来自辽、西夏和金王朝的威胁和侵扰,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与唐末五代相较,宋王朝内部相对安宁。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记述北宋时的情形是:“太平日久……班白之老,不识干戈。”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序》中说,南宋至理宗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在这种较为安定的环境中,经过广大劳动者的辛勤努力,宋代的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并推动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都市商业,日益走向繁荣。以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为例,北宋时的汴京,“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注:《东京梦华录序》。)。除城中随处可见的小店小贩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大型交易场所。参加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有的地方,“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二,《东角楼街巷》。)。宋代以前城市中那种坊与市即市民居住区与交易场所绝然分离、限时开闭的传统制度,也由于商业的发展而被打破。汴京城内店铺林立,与民居交错杂处。商店的营业,小贩的叫卖,不受时间、区域的限制,出现了通宵营业的“鬼市子”。不少交易场所的“夜市”,自暮及晓,始终十分热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说:“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二,《酒楼》;卷之三《马行街铺席》。)
南宋首都临安的商业,其繁荣程度又超过了北宋的汴京。宋人灌园耐得翁感叹说,当时的临安“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临安城内,“人物繁盛,风俗绳厚,市井骈集”(注: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序》。)。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道:“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注: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塌房》。)又说:“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宁和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茶市酒楼及各种店铺遍布城中,“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注:《梦梁录》卷十三,《团行》、《铺席》。)夜市之热闹,也超过了北宋汴京,所谓“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注:《梦梁录》卷十三,《夜市》。)
商品种类的增多和交易数量的庞大,市场特别是都市市场的兴盛,商品交易在空间与时间范围上人为限制的被打破等等,使宋代商业特别是都市商业走向了空前的繁荣,使它由此前的古代型商业“转向于近代型,具备了近代都市商业的各种色调”(注: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五章《唐以后的历代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同时也使一些此前并不用于交换的生产品转变为商品。 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里所列举的南宋临安街市上经常买卖的近三百种商品中,相当一部分在宋代以前并不用于交易。与此同时,许多原本不具有交换性质的非商业活动也进入了商业领域。如此前作为民间日常娱乐活动和文人文字游戏的猜谜,到宋代进入集市,成为一种商业交易活动。一些在制谜和猜谜方面具有特长的人,出于谋生的需要,以猜谜这种娱乐形式在市场上换取“来客”的钱币。这种进入商业领域的猜谜活动,在当时被称为“商迷”,从事商谜活动的人被称为“商者”。他们“先用鼓儿贺之”,作为开场来吸引观众,“然后聚人猜诗迷、字迷、戾迷、社迷”,且有“道迷、正猜、下套、贴套、走智、横下、问因、调爽”等形式供“来客”挑选。(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都城纪胜·瓦舍从伎》。)此前只用于教育后代、传授历史知识、总结统治经验的讲史活动即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进入商业领域,在集市或临时的“场子”中进行交易,成为讲史活动中一个新的类别——商业性讲史。如“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从事政治性讲史的“王六大夫”,在离开宫廷之后,为了谋生,利用自己“讲诸史俱通”的特长,进入瓦市中讲史(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把原来的非商业性讲史转变为商业性讲史。可见,宋代商业特别是都市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为商业性讲史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
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其最直接的作用是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职业通俗讲史者的出现。我国的民间通俗性讲史活动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它是下层民众了解历史发展、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途径。但是,在宋代以前,它是一种被称为“街谈巷语,道听塗说”的随意性很大的讲史活动,讲述者是那些所谓“闾里小知者”(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即普通民众中对历史传统和历史知识了解较多的人。他们并不以此为职业,不用讲史换钱,不靠讲史谋生,而只是利用劳动的间隙或其它空闲时间,向街坊乡邻特别是青少年讲述前辈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以满足这些人对历史的兴趣和了解历史的愿望。他们都是非职业的民间通俗讲史者。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在民间,以讲史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通俗讲史者开始出现。这些职业通俗讲史者,在北宋时期,可考者有汴京瓦市中的讲史人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霍四究、尹常卖等。(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在南宋,仅周密《武林旧事》中载录的临安瓦市中的讲史者便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陈进士、陈一飞等23人。(注:周密:《武林旧事》卷第六,《诸色伎艺人》。)他们不计春夏,不分秋冬,从早至晚长年累月地在瓦市中讲说史书。《东京梦华录》中“不以风雨寒暑……日日如是”,《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说的便是这种情况。(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这是仅限于汴京和临安两地见于记载的职业通俗讲史人,其他城市中以及游走于小镇乡村间的职业通俗讲史者,当不在少数。职业通俗讲史者的出现,使此前只是偶尔进行、三五人随意围坐听讲的民间通俗性讲史,成为拥有大量听众的规模可观的经常性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发展。
其二,通俗史著的产生。我国史学发达,史籍之多,浩如烟海。但是,在宋代以前,所有史著,无论官修还是私撰,也无论是出于政治的还是学术的需要,其修撰目的都是供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阅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班固《汉书》问世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注:《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固传》。),便是这种情况的很好说明。传统史著的这一特点,使它们在内容、形式和文字表述上都远离大众,无法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发展,听众日益增多,职业讲史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讲述内容也日渐丰富、多样,单靠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已经无法满足通俗讲史活动发展的需要,作为讲述依据的讲史底本的出现和逐步完善成为必然结果。由于商业性讲史所面对的是普通市民和广大下层民众,而传统史籍在内容、形式、文字表述上的“庙堂”特征,使它们不符合商业性讲史对讲述底本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创作新的底本,以满足客观的需求。于是,一种与传统史著不同的面向广大民众的新的史著随之产生。从保留至今的这类著作看,作为商业性讲史的底本,这种史著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文字表述上,都以能够吸引广大民众为原则,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特征。在内容安排上,它十分注意选择诸如下层人物发迹史、奇谋异略取胜史、英雄美人生活史等民众感兴趣的史实作为讲述内容。在情节描述上,它常常采录野史杂传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使事件发展迭宕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命运曲折多变,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给听众造成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普通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记述形式上,它以通俗生动的诗歌评史论人,状物写景,使讲史过程摆脱单调枯燥的平铺直叙而变得生动活泼。在语言文字上,它摒弃古奥之语、生僻之词,采用当时流行于广大民众中的习语白话,使讲史对广大民众来说,显得既易懂,又亲切。很明显,它是一种通俗化的史著,与传统史著相较,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它的出现,是通俗史学发展和逐步成熟的标志。
其三,通俗讲史内容的系统与丰富。中国的通俗性讲史尽管起源很早且广泛存在于民间,但在宋代以前,作为业余的随意性很大的讲史活动,由于受讲述时间和讲述者历史知识的局限,使它在内容上显得零碎而又简略。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零碎简略的内容已经无法长久地吸引听众,从而对职业通俗讲史人和商业性讲史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直接的威胁。为了适应商业性讲史在固定场所进行长期讲述的需要,必须将此前对一人一事的零碎叙说和简略讲述转变为对一个时代众多人物、事件以及整个历史进程的自始至终的详细叙述,使一代风云,历历在目。宋代商业性讲史的这一变化,其结果是使通俗性讲史在内容上趋于系统和丰富。北宋汴京瓦市中霍四究的“说三分”、尹常卖的“五代史”(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南宋临安瓦市中职业通俗讲史人的“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无不显示出宋代通俗讲史的这一特点。
其四,通俗史学传播范围的扩大。宋代商业性讲史兴起之后,作为一种职业的讲史活动,它不再是空闲时间里的偶尔讲说,而是每日皆有的长期性活动。它不仅长年进行,从不间断,且听者众多。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说,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讲史艺人王六大夫在瓦市中讲述《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由于“讲得字真不俗,记闻渊源甚广”,结果“听者纷纷”,吸引了大量的听众。(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那些来往于小镇和乡村间的讲史者,同样拥有众多听讲者。南宋诗人刘克庄在《田舍即事》诗(之九)中描述的“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所记“满村听说蔡中郎”,都生动地记述了这种情况。宋代商业性讲史人与讲小说、讲经者一样,长年不断地将讲述的内容“说与东西南北人”(注: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小说引子(演史讲经并可通用)》,见《宋元平话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05页。),使当时无论市民村夫、男女老幼,只要有兴趣, 都能听讲秦汉鼎革、三国历史、五代史事,使通俗史学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
四
随着通俗史学的发展,宋代商业性讲史兴起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使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商业性讲史兴起之后,通俗史学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许多原本对历史知之甚少的普通民众,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甚至熟悉历史。而且,他们通过商业性讲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不再是零散细碎的轶闻趣事,而是较为系统丰富的历史发展状况。正如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所说,当时所谓“小说者流”,“或名演史……皆有所据,不敢谬言”。他们讲述的历史,从“鸿荒判古初,羲农黄帝立规模”起,中间叙及少昊、颛顼、高辛、尧、舜、夏商周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唐世末年称五代,宋承周禅握乾符”,简直是一部从上古到五代的完整的中国通史。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商业性讲史者,有不少是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南宋著名学者周密在《武林旧事》卷第六《诸色伎艺人》中列举临安瓦市中的各种伎艺55类,从艺者共514人,其中,唯有“演史”一类大量使用了诸如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陈进士、武书生、刘进士、穆书生、戴书生、王贡士、陆进士等带有文人称谓的名号;其余五十四类,包括讲“小说”者在内,只有“商迷”一类中出现了一名“东吴秀才”,余皆与文人称谓无关。这种称谓不是随意使用的,它与从艺者本人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它说明商业性讲史者与其他艺人相比,具有知识丰富、文化素养高的特点,他们中的很多人,极有可能是曾经长期苦读经史的落魄文人。宋代商业性讲史系统丰富的内容和讲史者较高的文化素养,对作为听众的广大普通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无疑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二,强化了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宋代商业性讲史在内容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宣扬爱国主义,赞颂民族英雄及其爱国行为,对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者痛加斥责。《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中记载说,南宋著名讲史艺人王六大夫,其讲述内容为“《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复华篇》倡导爱国自不必说,“中兴名将传”显然是宣扬抗金将领们的爱国事迹的。而对后晋高祖石敬瑭那样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割地纳贡甘当儿皇帝的人,宋代讲史艺人痛斥其为“甘臣胡虏灭天常”,是“妖狐假虎威”(注:《宋元平话集·五代晋史平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9、140页。)。由于宋代商业性讲史在传播上的广泛性,这种对抵御外侮的颂扬和对卖国行径的痛斥,强化了对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爱国将领们的事迹在民众中广为流传。正如北宋著名学者欧阳修所说,宋初爱国将领杨业、杨延昭父子的事迹,“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注: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九。)。这是宋代商业性讲史在扩大通俗史学传播范围的同时所产生的明显的社会效应。此外,宋代商业性讲史中所大力提倡的忠君、孝亲、仁爱、节俭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加强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宋代商业性讲史底本的写作者和一部分讲史人是长期受封建文化熏陶的下层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封建史学的组成部分,宋代商业性讲史所宣扬的伦理道德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落后甚至反动的内容。同时,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在讲述过程中,也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迎合市民阶层的一些低级趣味,从而难以完全摆脱尽管是很少量的庸俗性描述。此外,包括商业性讲史在内的宋代瓦市中的活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处于封建官府的监督之下。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九的记载,南宋时,临安城外的瓦市“多隶殿前司”,城内瓦市“隶修内司”。在这种情况下,讲史者为了生存,即便有反封建的思想,也是不敢表露的。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从整体上看,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内容和基本精神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因而其道德教化的主流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有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的。
【收稿日期】1998—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