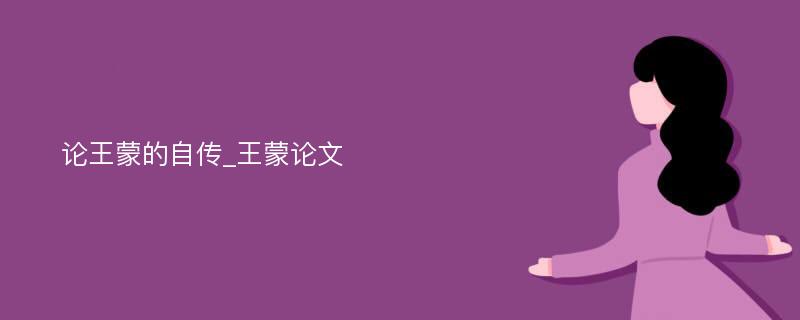
论王蒙“自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自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独特的个体性存在,或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学“符码”,由何而来?《王蒙自传》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感性地体现了王蒙的个性以及精神特征的形成历程,向我们展示了王蒙如何从一个“北方农村的土孩子”①、“一个落后的野蛮的角落里的宠儿”②,成长为共和国文学的一代大家,如何由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成为了经验主义者,以及这种思想转变的现实合理性和实践根据;从王蒙思想的形成、衍变过程,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以及思想形成衍变的过程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历史主义的角色”③,王蒙生活在20世纪这个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其生活和思想上的许多“拐点”④,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某种思想变化息息相关。共和国文学的这段变动频仍的历史,王蒙都是亲历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反刍者”和“忏悔者”⑤。因此,《王蒙自传》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特定的时代而言,同样带有某种“镜像”意义。
一
王蒙是个复杂的存在。然而,自传中的王蒙更显复杂。“自传”其实就是“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⑥。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传主对“历史境遇”的兴趣超越了对“自我”关注的程度。“以《史记》为开端,中国传记的写作实际上形成了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写人的宏大叙事传统,后继的传记作者所关注的大多是与历史有关的大局、大事、人物大节,而对于个人的身边琐屑,传主的内心世界一般都不给予过多的关注”⑦。自传当然离不开“大局、大事、人物大节”之类的“宏大叙事”,但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人物的“内心世界”。《王蒙自传》也写了诸如“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当代中国的“大局、大事”,甚至不无总结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思考人与历史关系的宏大意味。“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⑧,几乎是一切自传作者的“初衷”,但是,在这部自传中,王蒙对自我“内心世界”即个性精神的关注和表现,超越了对外部事件即时代风云的兴趣。由此,使这部自传不但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真实的品格,同时展示了王蒙自我心灵的多维真相,王蒙为自己画了一幅真实的“肖像”——一幅多维的复杂甚至矛盾的精神和心灵的肖像。
那么,自传中王蒙的“自我”是如何形成和“定义”的呢?王蒙是通过“审父”来“定义”自我的,这是王蒙呈现给读者的第一副“面孔”。新时期以来,王蒙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王蒙引发“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即是“过于聪明”、“世故”等。在《王蒙自传》中,我们却看到了王蒙的另一面,一个决绝的王蒙,这是与王蒙通常留给人们的“印象”所不同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史传传统,司马迁《史记》所体现出来的“实录”品格,一直是中国史传自觉追求的楷模,但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想性境界,事实上,“虚美隐恶”,为亲者、尊者、逝者讳,对传主的“理想化”,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似乎也已经成为传记的“自然”伦理,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对历史深怀敬畏又具有某种文字崇拜的民族,尤显突出。“坦白事实是自传叙事的最高叙事伦理”⑨,自传中的王蒙,将无可避免地面对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某种道德甚至审美定势。王蒙已经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传统的对立面。
英国传记作家李顿·斯特拉屈认为“不偏不倚地追求真实”⑩是传记的“三大信条”之一。王蒙称张洁小说《无字》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白得不能再坦白,真诚得不能再真诚,大胆得不能再大胆”的书写为“极限写作”(11),在这个意义上,王蒙已经逼近了这种“极限写作”。王蒙说自传是他在年逾古稀后写下的一个“留言”,“想说出实话的愿望像火焰一样烧毁着樊篱”(12),面对历史的真相,虽然王蒙也表现出了某种游移和不自信,如他自问道:“你能够做到完全的就是说百分之百的真实吗?不,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但是我做到了,在我的自传里完全没有不真实”(13)。这种逼近真相的“火焰”,最终还是“烧毁”了王蒙的“理性”防线,那个“聪明”的王蒙开始走向反面,王蒙开始“审父”。如果说《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在文学的意义上“审父”的话,那么,在他的自传中,王蒙却是站在更高的层面,“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14)。
王蒙的决绝甚至达到了残酷的程度。虽然王蒙深知“对于先人,逝者,保持一点敬意,不是不必要的”(15),但王蒙更清醒地知道“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德,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16)。王蒙对那个“受了启蒙主义自由恋爱全盘西化的害”、“从来没得到过幸福,没有给过别人以幸福”的父亲——王锦第的“审判”,成为王蒙自传中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特别是对某些隐私如“外遇”(17)的描写、“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18)日记的披露,以及父亲与母亲、姨妈、姥姥的家庭纷争,直到大打出手以至“脱裤子”的细节等,这在通常的伦理的意义上,确实“是忤逆,是弥天的罪,是胡作非为”(19),这不但形成了对世俗伦理的挑战,而且也形成了对传统传记伦理的挑战。“审父”已经成为王蒙的一种庄严的使命:“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我愿承担一切此岸的与彼岸的,人间的与道义的,阴间的与历史的责任。如果说出这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20)。这是王蒙内心最激荡的声音,也是迄今我们在自传中所能见到的最坦诚最光明的文字。王蒙多次谈到自己的“不忍之心”(21),然而,无论是在他的《活动变人形》还是自传中,他却“起诉了每一个人”(22)。王蒙的“审父”甚至超出了读者通常的心理承受能力(23)。这是一个超越了世俗伦理的、决绝的、义无反顾的王蒙。
自传作为一种“最富有刺激性”的文学形式,其魅力恰恰来自作家“毫无遮掩地对待他的一生”(24)。然而,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克服一些人性的弱点例如不自觉的自我美化、自我掩藏等,还能够有勇气和力量面对道德的责问,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在文学作品特别是传记中,与那些表现个体性隐私相比,人们更愿意表现那些“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25),这就形成了“中国文人写自传,归根到底都是强调自己的正确”(26)的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性格的缺陷。王蒙在努力超越这种文化的力量。与传统自传中的“圣徒”意识不同,王蒙在自传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自己某种并不光明的思想和做法:王蒙被打成“右派”在京郊劳动时,夫人崔瑞芳“精神奕奕、仪态从容”来到劳动农场看他,王蒙则“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并告诫崔不可对“右派”们“太热情”(27);“文革”一开始,王蒙害怕“祸从笔出”,烧掉了所有的字纸,“不论接到什么尊长的信,我都立即用来如厕,很少在家中保存超过三个小时的”(28)。这也反映了王蒙在“文革”之中的某种真实心态。
同时,自传还表现了一种严肃的反思精神——一种真正的历史理性精神,即对自我的审视和拷问。“反右”、“文革”之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特殊年代的无辜“受害者”、“被冤枉者”,一味地控诉、批判时代的罪愆,忽略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不敢正视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世界,王蒙在回顾、反思自己被划为“右派”时,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并非由于思想上的“右”,实与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的“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式”有极大关系,“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29)。王蒙“反躬自问”,“文革”中,“如蒙上峰赏识,如果被召被宣,冷宫里耗得透心凉的我会不会叩头如捣蒜做出不得体的事情,丢人的事情,我实无把握”(30)。王蒙的这种自我忏悔,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真诚,还需要真正的敢于面对自我的勇气和力量。
王蒙的反思并非仅仅面对自己,还说出了一种至今我们还不能正视的文化或人性的真相。《半生多事》中记述一位老导演,本来在“文革”中平安无事,但是他不甘寂寞,不甘被“忘却”,“不甘置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外”,自己跳出来给自己贴大字报,终于被关入牛棚的故事(31)。王蒙认为“反右”运动中“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于右,而是由于太左才找了倒霉”(32),这是王蒙的一个发现。王蒙在回忆“反右”期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坦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确实具有某种“原罪心理”,对工农“欠着账”,“必须通过自我批判改造,通过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赎自己的灵魂”,真诚地认为自己“应该晾晒灵魂”(33),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右派”的思想真相以及“反右”运动的某种深层的心理动因。再如,王蒙认为“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至少是习惯于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粗暴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施于人。不欲己受,必授他人。不欲,则授受最亲”(34)。王蒙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苦主,而把有关的人装扮成魔鬼”(35),在那个特殊年代之中,“右派”的“受害者”身份中也同时流露出某些更为复杂的人性内容: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和施虐者。这个发现其实是相当残酷的。在这里王蒙所表现出来的执拗和“傻劲”超越了一般“书生”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对自己颇为决绝的王蒙。
二
评论家王干说王蒙是“新中国的一面镜子”(36)。王蒙并非是一个单向度的存在,而是一个文学家、政治家、思想者等多种精神质素的混合体,这是王蒙的独特之处。作家的革命化、政治化甚至组织化,是建国后中国作家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不独王蒙。然而,这种革命化,政治化无疑在王蒙身上表现得更执著、更强烈,这是王蒙独特的生活、政治阅历所塑就的品格。
在自传中王蒙对自己有一个独特的定位:“桥梁”和“橡皮垫”,要“充当中央与作家同行之间的桥梁”(37),“充当一个减震减压的橡皮垫”(38)。王蒙的这种定位深刻地影响了他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形态。王蒙谈到自己的创作倾向时说:“让我写民俗?大概也就能说说新疆,因为我在那里生活工作过。让我写遗老遗少?我没研究过清史。让我写性爱脱衣?别说裤衩了,就是让我脱上衣光着脊梁,我也扛不住。……我也想书卷气,如兰似菊,可我气韵不对!你让我学富五车?那就是让我裤腰上缠死耗子,假充猎人。我只能写政治生活下的人们,因为我的特点就是革命”(39)。王蒙曾不止一次地感叹自己的经历“太历史了”,“虽然我主张作家写得可以个人一点,也可以写得花样多一些,但实际上我做不到,我的作品里,除了历史事件,还是事件的历史”(40),王蒙曾羡慕贾平凹《废都》“把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给你洗得干干净净”(41),自己却永远做不到,“我无法淡化掉我的社会政治身份社会政治义务”(42)。
那么,王蒙这种“桥梁意识”或者说“桥梁心态”,是由何而串呢?我认为这源于王蒙的“独一无二的少年革命生涯”(43)所塑就的“干部的心理和习惯”(44)。少年时期的革命经历及其所带来的建国初期的革命者心态,塑就了王蒙的某种远比一般作家更为强烈的主人意识和政治意识。革命是王蒙的“起点”(45)。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少年王蒙曾“怀着一种隐秘的与众不同和与众相悖的信仰,怀里揣着那么多成套的叛逆的理论、命题、思想、名词”(46),积极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之中。王蒙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大量革命文艺作品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理论书籍,革命成了王蒙的“童子功”。王蒙的这种早年的地下斗争经历特别是后来的共青团“背景”,构成了王蒙的第一个政治“身份”,也几乎是影响王蒙一生的最重要的精神“徽记”。王蒙后来在回答某些诸如对历史和现状不够决绝的责备时说:“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47),王蒙的“起点、出发点”就在这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蒙的精神走向,也决定了王蒙的价值观念甚至思维方式。
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审父”为王蒙“自我”的形成和发展规定了方向。王蒙在父亲的身上,已经找到了后来“走向革命”的依据。父亲(其实就是《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原型”)的“清谈”、“大而无当”,“树立高而又高的标杆”、“绝不考虑条件和能力”的“理想主义”(48),父亲对所谓诸如“喝咖啡”、“讲哲学”等新潮和“西洋文明”的“痴迷”、以至被讥为“外国六”(49)的做派,以及最终“一事无成”的命运,都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王蒙的“反面教材”。“父亲”的形象,成为王蒙内心深处的一种永久的自我提醒,也促使王蒙走出那种互为“石碾子”(50)的生活轨迹,寻找“别样”的人生。这是王蒙最终走向革命的原初的动力。
青少年时期的革命经历,在王蒙身上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多方面的。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之所以是“相信的一代”(51),在于他们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那个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的时代,王蒙曾深受这种理想主义的影响,并使之成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然而,还有另一方面。王蒙作为一名地下革命工作者,除了地下革命所带来的隐秘的兴奋,更面对着许多实际的、复杂的、甚至是危险的斗争。建国前夕,为迎接解放军进入北平,年轻的王蒙曾经佩戴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和袖标,配备左轮手枪值夜班(52)、散发传单、发动学生参加“护民护城”运动,后来参加开国大典……这种经历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这一方面强化了王蒙的作为革命者的心态,另一方面也使之变得清醒与冷静,理性与务实,不可能简单地从教条出发,从书本出发,而会更注重实践的矛盾性、复杂性。许多学者都充分注意并论及了王蒙创作中的“革命情结”或“政治意识”(53),其实这是与王蒙这种独特的政治身份紧密相连的。在当代作家中,像王蒙这样与革命和政治发生如此密切关系的并不多见。革命或政治,对于王蒙而言,绝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叙事对象或叙事策略,王蒙对革命或政治的兴趣,是一种“宿命”:“我不能够做出一副‘我不喜欢政治’的样子,那是虚假的。我从小就热衷于救国救民”(5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从来就没有是身外之物”(55)。因此,王蒙拒绝对现实和历史采取默然的态度,拒绝成为“对立面”,甚至拒绝“横站”(56)式或成为索尔仁尼琴式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这才是革命者意义上“桥梁”式的王蒙。
除此之外,王蒙的前后十年的“中委”身份和三年的部长生涯,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种“桥梁”心态。政治经历之于一个作家并非必需,但有无这种经历却并不一样。王蒙的这种政治经历,其实是他青少年革命经历的一种延续,这不但极大地拓展了王蒙的“生活经验面”,构成了王蒙“重要的政治经历、政治资源、理论资源、生活资源与文学资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治生活实践“可以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它使我对许多事不再感觉那样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魔化、夸张化、恶意化”(57),使王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观察社会和看待问题的立场、心态或角度,使王蒙获得了一种使命意识、全局意识,能够更为宏观地、建设性地看待问题。“要当个和谐的因素而不是生事的因素,要当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搅乱的因素”(58),“起一些沟通的作用,健康的作用,照顾大局的作用,缓解矛盾增进团结的作用而不是相反”(59)。王蒙的这种独特革命经历,赋予了他“革命者的一种骄傲与特殊身份感”(60),王蒙曾不止一次说过:“我轻视那种哩哩哕哕,抱残守缺,耍丑售陋,自足循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脑筋”(61);同时王蒙对那些“抓住头发就想上天”的“书呆子”(62),脱离实际如坐云端的大言欺世者,也表达了他的不苟同。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社会实践塑造了作家的思想。王蒙精神个性、思想性格以及价值取向的形成,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王蒙独特的实践经历分不开的。
然而,这仅仅是王蒙的一个方面。王蒙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除了这种“桥梁”的角色,同时还拥有另一个“身份”——“界碑”。也即是说,王蒙除了“左右逢源,前后通透”的一面,也面临着“不完全入榫”、“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63)的一面:“我好像一个界碑,……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64),这其实就是王蒙所说的“相差一厘米”(65)。20世纪中国社会始终激荡着两种声音,那就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这两种思潮激荡中,王蒙确实有“左右逢源”的时候,但同样也有“左右夹击”的窘迫,“左派把他当右派,右派把他当左派”(66),其实是王蒙必须面对的处境。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坦言,他比一些同志多了一厘米的艺术气质与包容肚量和随和,比作家同行们多了一厘米政治上的考量和成熟,比书斋学院派精英们多了也许多于一厘米的实践。王蒙的这种“界碑”式的不被理解不被认同的尴尬和窘境,其实正源于他的这种“相差一厘米”。王蒙说“我不是索尔仁尼琴,我不是米兰·昆德拉,我不是法捷耶夫也不是西蒙诺夫,我不是(告密的)巴甫连柯,不是(怀念斯大林的)柯切托大,不是(参与匈牙利事件的)卢卡契,也不是胡乔木、周扬、张光年、冯牧、贺敬之,我同样不是巴金或者冰心、沈从文或者施蛰存的真传弟子,我不是也不可能是莫言或宗璞、汪曾祺或者贾平凹、老李锐或者小李锐……我只是,只能是,只配是,只够得上是王蒙”(67)。王蒙之所以不是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于他的这种思想和精神的独特性。
同时,王蒙的这种“界碑”感,也反映了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某种思想现实。新时期“复出”后的王蒙与“青春万岁”时代的王蒙甚至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似乎变得复杂了、游移了,甚至欲言又止了,不再那么“纯粹”了,不再那么理想主义了,实际上王蒙开始了思想转型。王蒙的某种政治上的主流感和“本质是文人”(68)的特性,使他容易陷于某种思潮的漩涡之中。对于生活和文学的敏锐,使他不满足于当时文学的主流说教,迅速超越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阶段,率先进行了文学上的一些探索和实验。王蒙事实上一度成为80年代中国文坛的“风向标”和“现代派”在中国的代言人,这引起了文坛的某种忧虑,甚至连文学上十分内行的“贵族马克思主义者”(69)胡乔木也“教育”王蒙“不要在意识流上走得太远太偏太各色”(70)、“少来点现代派”(71)。对当时文坛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言,那个“党性特强”(72)的王蒙,无疑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坛和思想界的“远行的叛徒”(73);而对于某些“简单而又片面的人”(74)来说,王蒙反复强调的又是“我已经懂得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75)。到了90年代王蒙更是开始讲“理性”,讲“理解”,讲“躲避崇高”,王蒙确实成为了他们“前进脚步的羁绊”(76),王蒙正好站在思想上这“两个不能对话的世界”(77)的中间。虽然王蒙反复告诫自己“做一个健康、理性、平衡与和谐的因子”(78),事实上,就王蒙思想的特点和80年代以来当时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意识形态价值动荡的现状而言,王蒙具备“界碑”心态似乎不可避免。
三
就王蒙的思想和精神完成性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王蒙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成了“经验主义者”(79),从50年代的青少年革命者转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80),从一个革命者转变成了“后革命时期的建设者”。王蒙虽有建国前后的参加地下学生运动以及共青团工作的经历,对那种天真的乌托邦思想具有某种“免疫力”,但就王蒙的精神个性而言,那种文人的伤感和理想的一面,要明显于理性和务实的一面。那么,王蒙是如何从那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中走出来,最终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疏离者、审视者、甚至质疑者?王蒙是如何完成了这种转变的呢?《王蒙自传》在展现王蒙个性的形成即精神的自我成长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法国学者菲力蒲·勒居恩称自传是“人格的故事”(81)。王蒙的转变源于“反右”特别是“文革”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既是王蒙思想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拐点”,也是王蒙后革命时期思想的真正来源和逻辑起点。王蒙说:“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不但有清明的、真实的、可以理解乃至可以掌握的过程,也有许多含糊的、不可思议的、毫无根据的、乃至骇人听闻的体验”(82)。王蒙的“右派”生涯和“文革”记忆无疑主要是后者的“体验”。这十年的“生聚”和“教训”,成为了王蒙思想转变的某种契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已经不那么年轻,我已经不那么相信概念的区分,命题的转换必定能够决定一切。我知道了一个与方针政策理论同样同时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常识,这就是现实”(83)。十年“生聚”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王蒙,使他走向了人生和思想的另一境界,也成为了王蒙的某种心理和思想另样的出发点和参照系。
对于一个经过了“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理想主义已经成为乌托邦的代名词,起码当人们回过头来再看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时候,虽然在情感上可能仍旧难以忘怀(这一点王蒙同样如此,甚至更强烈。《恋爱的季节》即是这一情感的产物和明证),但在理性上已经增加了某种警惕性和反思性的成分。“反右”和“文革”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轨迹,更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走向。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已经明白了“单纯的理想易于通向假大空的自欺欺人”(84)的道理,明白了“激情常常是和思想的贫乏而不是智慧的丰富联系在一起”(85),更洞彻了“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们驱赶到地狱里”(86)。王蒙迎来了一个新的思想转型——向经验主义的转型。
王蒙说:“经验塑造着不同的人”(87)。王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和内心的经验都很丰富的人。从历史经验层面而言,王蒙可谓“半生多事”,经历丰富,阅世极深,是个深味中国国情、世态、人心的知识分子。王蒙后来的很多思想,特别是例如不要太“形而上”,要认同生活的世俗性、此岸性的一面;不要走向教条主义,不要大言欺世,要认同常识、常情、常理;不要走极端,不要相信简单化,要认同事物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等,既与他早年经历有关,更与他十年的“生聚”和“教训”有关,“王蒙思想上的成熟,应当说是从新疆那里开始的。他从底层人的苦难中,意识到了什么,感悟到了什么,他的理想主义,用世的儒家情感,开始饱受着风雨的侵袭”(88)。王蒙曾说新疆生活是他的“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89),其实,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不仅是他创作的“本钱”,而且是他思想的新的“出发点”,“是他返观革命的一个新的角度,新的价值参照,新的智慧的援助”(90)。50年代的“右派”生涯和60年代的中年赴疆使王蒙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行万里路,识万种人,做百样事,懂百样道理千样行当万种风物”(91),从一种更为开阔的价值坐标和更为实践性意义上重新看取和审视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
同时,王蒙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经验,使他真切地感受到现实的力量、实践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16年的新疆生活,特别是在伊犁同底层各族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使王蒙“完全改换了视角”(92),从那种极左政治的虚妄中解脱出来,从那种凌空蹈虚的意识形态的“亢奋性”(93)中解脱出来,认识到生活和存在的“坚实性”,认识到“活着的力量”才是“天下最顽强最不变的力量”(94)。王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劳动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要关注生存问题,关注粮食、蔬菜、居室、燃料、工具、医药、交通、照明、取暖、婚姻、生育、丧葬、环境……诸种问题”(95)。王蒙洞见了“理论”大话、空话的极端虚妄性(96),曾多次劝告并希望理论家,要多多注意和联系“中国革命运动的背景”和“特别的中国”。王蒙这种更具世俗和实践理性思想的形成,是与这近二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王蒙曾说:“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包括老庄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革命导师的辩证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97)。这种“生活本身的辩证法”使王蒙远离那种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避免了凌空蹈虚、偏执乖张,而是注重生存、现实和实践,对现实始终保持了一种务实的理解性的建设姿态。王蒙意识到在一个建设时期,人们更需要的是务实和理性的点滴建设,而不是理论的豪华化、空洞化和悲情主义。
“反右”和“文革”的痛苦经历和建立在这一痛苦经历基础上的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彻悟,是促使王蒙走向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思想资源。曾有一位美国人问王蒙:“50年代的王蒙和70年代的王蒙,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王蒙回答说:“50年代我叫王蒙,70年代我还叫王蒙,这是相同的地方;50年代我20岁,70年代我40岁,这是不同的地方”(98)。王蒙的“回答”,似乎在开玩笑,其实,在这种“玩笑”的后面,蕴含了诸多的人生体味。“反右”和新疆生活使王蒙沉于生活最底层,懂得了生活的辩证法,也赋予王蒙某种真正“王蒙式”的精神“徽记”:“将近20年过去了,王蒙还是王蒙,依旧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一个清醒的、经过各种磨炼的布尔什维克。依旧是一个赤子,但是一个成熟的赤子。依旧心头热血奔流,但他不会再为生活中美丽而晃眼的假象所迷惑,单纯又傻气地冲动起来。依旧充满社会责任心,但他更懂得这种责任的严峻性和怎样去尽自己的职责”(99)。新时期“复出”后的王蒙,曾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二十岁的时候,生活和文学对于我像是天真烂漫、美好纯洁的少女,我的作品可以说是献给这个少女的初恋情诗。初恋的情诗可能是动人的,然而它毕竟是太不够太不够了啊!”(100)。王蒙的这种“清醒”,其实是源于现实的经验,特别是源于十年的“生聚和教训”。
王蒙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局限”(101)。那么王蒙的“机遇”特别是“局限”又在哪里呢?王蒙坦言“我不是书斋型的知识分子”(102),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王蒙的“机遇”,也是王蒙的“局限”。“右派”生涯和“文革”记忆,一方面为他后来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极富辩证色彩和实践理性的文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和可能,但也强化了王蒙的“局限”性一面。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王蒙后革命时期对极左充满“警惕性”的思想,源于他的“恐惧性思维”:“内心的恐惧使王蒙总把恶梦一般的岁月时时加以警惕,时间长了,这种警惕就不再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自觉支配”(103)。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王蒙说:“历史扮演着人,人表演着历史”(104)。王蒙作为一个独特的精神个体,其复杂性、矛盾性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历史的“回音”;同时,又是他独特的生活阅历和个性禀赋的产物。王蒙曾以“蝴蝶”自喻:“你抓住我的头,却抓不住腰,你抓住腿,却抓不住翅膀”(105)。王蒙这只“蝴蝶”,其实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从王蒙身上,我们的确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个独特的文学时代、一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特定的历史时期。
注释:
①(12)(13)(15)(22)(37)(38)(42)(45)(55)(57)(58)(59)(60)(62)(63)(64)(65)(67)(70)(71)(72)(74)(76)(78)(83)(89)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第204、141、141、323、225、335、165、79、187、24、186、266、165、43、61、175、175、175、230、152、162、156、70、70、215、190、50页,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②(16)(17)(18)(19)(20)(21)(27)(28)(29)(30)(31)(32)(33)(34)(35)(43)(46)(48)(49)(50)(51)(52)(85)(91)(92)(93)(94)(101)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26、25-26、12、18、14、14、350、187、319、173、350、353、179-180、173、180、25、122、61、10、16、12、246、69、272、224、231、216、256、75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③王蒙:《共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与陈建功、李辉的对话》,《王蒙文存》第17卷第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版本同,不再注出处。
④“拐点”的说法,是2006年9月在“王蒙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王万森教授提出的。王蒙在《大块文章》中认同了这一说法。
⑤(68)王蒙回答陈德宏访谈时所言。此资料复印件保存于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
⑥[法]萨特:《词语》第310页,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⑦(25)辜也平:《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民族特色》,《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⑧郭沫若:《〈我的童年〉前言》,《郭沫若全集》第11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1992年版。
⑨王成军:《“事实正义论”:自传〈传记〉文学的叙事伦理》,《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⑩转引自朱文华:《传记通论》第9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王蒙:《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王蒙文存》第22卷第186页。
(14)[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第1页,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3)在《王蒙自传》第二部中,王蒙说:“我以充满阳光的坦诚,回顾旧事,却碰到了阴暗乖戾的一些小痞子”——《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第174页。
(24)Stephen Spender,"Confessions and Biography",Auto biography: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ed.James Ol-ne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16.
(26)[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第206页,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6)王干:《关于王蒙的八个问题》,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第100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9)(54)《杨澜访谈录》第九辑第77、6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0)王蒙:《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海南作家》1986年5月8日。
(41)夏冠洲:《生活·创作·艺术观——王蒙访谈录》,夏冠洲著《用笔思考的作家》第245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4)(47)(56)(61)(80)(86)(95)(96)(97)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第22、9、83、236、9、269、3、3、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53)对王蒙的“革命情结”论述,可参阅吴三冬著《解不开的革命情结——王蒙小说的思想轨迹》一书,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
(66)董健:《简论王蒙的人生哲学》,温奉桥编《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第一届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9)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王蒙文存》第17卷第211页。
(73)(77)(88)孙郁:《王蒙:从纯粹到杂色》,《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
(75)(100)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存》第21卷第26、25页。
(79)王蒙:《沪上思絮录》,《王蒙文存》第23卷第220页。
(81)Philippe Le Jeune:On Autobiograph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6.
(82)王蒙:《〈王蒙荒诞小说自选集〉序》,《王蒙文存》第21卷第123页。
(84)王蒙:《理想与务实》,《王蒙文存》第15卷第362页。
(87)王蒙:《纽约诗草(三首)》之《致A·W——并答〈纽约时报〉》,《王蒙文存》第16卷第19页。
(90)郜元宝:《当蝴蝶飞舞时——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和方面》,《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98)(99)冯骥才:《话说王蒙》,李扬编《走近王蒙》第56-57页、57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2)王蒙:《我只是只文化蚯蚓》,《羊城晚报》2000年7月1日。
(103)谢泳:《内心恐惧:王蒙的思维特征》,《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0日。
(104)王蒙:《梁有志他》,《王蒙文存》第21卷第92页。
(105)王蒙:《蝴蝶为什么得意》,《王蒙文存》第21卷第97页。
标签:王蒙论文; 自传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王蒙自传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活动变人形论文; 理想主义论文; 父亲论文; 右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