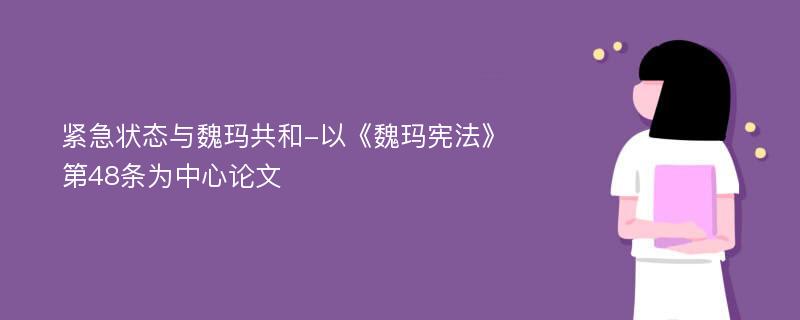
紧急状态与魏玛共和
——以《魏玛宪法》第48条为中心
方 旭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1)
[摘 要] 从立法实践来看《,魏玛宪法》是全世界第一部内置紧急条款的宪法,魏玛共和国也是德国历史上首次议会民主制度的“政治试验”。后世对这部宪法的评价毁誉参半:一方面,《魏玛宪法》是德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从宪法字面上看,它可谓是最符合当代西方法学家口味的宪法,也被称之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另一方面,由于魏玛宪法中设置了一个保留君主权力的紧急条款(《魏玛宪法》第48条),德国宪法学界对之一直聚讼纷纭。
[关键词] 《魏玛宪法》第48条;紧急状态;马克斯·韦伯;卡尔·施米特
紧急状态(emergency)向当代法治国家抛出了一个问题:一旦代表国家最高权威的宪法遭遇危机时刻,如何捍卫国家宪制秩序的稳定?对于自由主义法治国而言,除了在规范性的宪法大厦中镶嵌一个紧急条款(emergency provisions),似乎别无选择。如今联合国193个国家中已经有179个国家(占比92.7%)在宪法中明文制定了紧急条款,而其余14个国家(占比7.3%)则通过特别立法方式予以调整① 滕宏庆《:紧急宪法:自由与安全的紧急正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页。 。可见,在宪法中设置一个紧急条款已经成为当代法治国家的共识所在。然而,在国家遭遇危机关头,由紧急条款衍生出的紧急权力却具有某种双重性:一方面,面对国家生死存亡之时,需要国家凭借强力捍卫国家生存,可宪制秩序建立的本质却在于限制权力;另一方面,宪法内部运行紧急权力时并不能确保不伤害到公民基本权利,造成的人权克减违背了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立宪初衷——何况,紧急条款滥用的覆车之辙至今还引人深思。
(2)基于潜在语义分析的概率主题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比较典型的有基于LSA(Latent Semantic Analysis)[10]、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11]的文本语义相似度计算模型。主要思想是利用词语中的共同信息对文本进行主题建模,挖掘出文本中潜在的语义信息,从而计算出文本之间的语义相似度。这类方法的优点是考虑到了词语的深层语义信息,准确率高于第1类方法,缺点是没有考虑到词与词之间的位置关系,受样本种类限制较大。
《魏玛宪法》第48条的第1款、第2款是《魏玛宪法》第48条的核心要件,第1款调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2款则是第48条的内容实质,本条款规定:
如果德意志联邦内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严重的扰乱或危害,联邦总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公共安全和秩序,必要时得以武装力量干预。为达到这一目的,总统可以暂时中止规定在第114条(个人不可侵犯)、115条(住宅不可侵犯)、117条(通信秘密)、118条(言论及其表达自由)、123条(集会自由)、124条(结社自由)、153条(财产不可侵犯)中的全部基本权利或部分基本权利。② 《魏玛宪法》全文采用肖蔚云等:《宪法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宪法学说》一书附录中的中文译文可参考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页;黄卉《:德国魏玛时期国家法政文献选编》,黄卉,晏韬等编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页。
数据管理、预警管理与预警发布管理3个模块安装在服务器端,由于交互性较强,采用B/S架构,基于ASP.NET的MVC模式设计。预警分析引擎也安装在服务器端,由于不需要进行详细的配置,采用C/S架构。服务器端实现远程数据管理、预警规则设定、预警分析处理等功能,在接收到实时数据后,进行分析计算,判别是否超警,同时生成预警消息,推送至客户端。
韦伯强调的是一个诉诸民意产生的领袖。1919年2月25日,在向民国大会提交帝国宪法草案之际,韦伯在《柏林交易所报》上发表《帝国总统》的文章,猛烈抨击德国议会制度,宣称“今天所有的宪法提案都要屈服于对议会的多数,而不是人民的多数”④ 蒙森《: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65页。 ,要求直选帝国总统,破除最高决断力与民众之间存在的官僚阶层的隔阂,克服比例代表制导致议会庸碌无为等困境,从而应对战后的国内外危机。最终普罗伊斯在宪法最终稿中调和了各方意见,也技术性处理了韦伯的直选总统的意见。在他的方案中,公民直接选举总统,规定总统的任期有七年,还可以连选连任。在他们看来,公民进行投票是实现人民意志同质性的唯一途径,并且通过这种投票实现国家意志统一。魏玛的总统职位设计还存在对议会制衡的作用。《魏玛宪法》第25条规定“总统有权力解散国会”,尤其是针对将来在议会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者多数派⑤ 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米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3页。 。
德国法学家们认为,这一宪法设计要为希特勒合法上台致使魏玛共和国早夭负责任,尤其本条第1、2款起了巨大作用,谁能料想,共和国成立短短十四年后,1933年3月24日希特勒即借助国会批准的授权法案登上德国最高政治舞台。吊诡的是,宪法秩序需要依靠其反对的集权力量维护自身稳定,而恰恰是这道强力成为了导致宪制破裂的缝隙,让民主的敌人切入宪法内部动摇宪法秩序本身。本文依据魏玛共和国建国立宪的思想史脉络,对《魏玛宪法》第48条历史背景、内容及其影响展开讨论① 国内研究相关成果如下:高媛《:紧急状态与法治:从〈魏玛宪法〉第48条说起》,见姜明安编《:行政法论丛》(第18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刘士文《:权威善治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现代西方权威理论及其借鉴价值》《,探索》2018年第5期,第182-192页;王晓玲《:桀骜难驯的权力:德国立宪艰难之因》,见陈景良,郑祝君编《中西法律传统》(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页;陈伟:《施米特与魏玛德国宪政危机》,见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编:《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田飞龙《:施米特对魏玛宪制的反思及其政治宪法理论的建构》,见张仁善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陈新民《:宪法的维护者:从卡尔·史密特对魏玛宪法的回顾与反省谈起》,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28页。 。
一、内外危机:《魏玛宪法》第48条的历史背景
此外,随着《凡尔赛条约》的签订,魏玛共和国遭受外辱,同时又受到国内政治动荡之影响,工人罢工、街头冲突、政治暗杀和军事政变等暴力盛行,这些都冲击着整个国内政治生态,共和国内部已难以依靠议会民主方式协调各党派之间的纷争,魏玛共和国内已有部分政治精英采取“非传统民主”方式来实现政治诉求。例如在《魏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法学家们甚至建议设立“全民直选总统”,赋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废止民主权利的大权,以此与进展缓慢、迟疑不决的民主议会相抗衡。
德意志第二帝国最高军事统帅已意识到无力继续战争,他们明白德国若要保存自身,就要在美国与英法之间做一个政治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都需要以政治改革和德皇退位为代价来换取缔结较宽大的对德和约。他们深知,基于地缘和历史因素,作为战胜国的英法两国定会制定一个想方设法削弱德意志国力的协议,故而德国将政治赌注压在威尔逊身上,希望凭借他的力量使德国在巴黎和会上占据一个较为合宜的谈判空间。可巴黎和会上的明争暗斗远远超出了德国政治精英们的想象,为迎合欧洲大陆高涨的反德情绪,威尔逊不得不牺牲德国利益。
其中,v(h)为交叉项.中出现周期性三角脉冲,其脉冲中心位置为h=kTs和h=kTw,k=0,±1,±2,….当扩频码周期采用方案Tw=mTs,m=2,3,4…时,发现中三角脉冲的间隔恒为Ts,与大信号的参数特征相同,未发现机密信号的参数特征.因此,采用所提方案设计的机密信号可以抵抗基于功率谱二次处理的盲检测.
社会服务能力是指教师在学校以外的环境中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进行社会活动的能力。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在工作之外,还应具备利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但目前这方面能力被许多教师所忽视。
为了羞辱德国人,法国政府将签约地点定在了当年德皇威廉一世登基的凡尔赛宫镜厅。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损失了十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煤矿产地,以及半数的钢铁工业,甚至包括其多年苦心经营的海外殖民地。美国在这一条约上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德国曾希望通过“十四点计划”在威尔逊那里获取较为宽大的和约,而这一希望随之完全破灭。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认为,尽管《凡尔赛条约》表面上做到了条款上的“公正”,但其本质却成为了“压制、剥削和永远羞辱德国人的庞大工具”② 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佘江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在接受《凡尔赛条约》后,德国被迫启动内部政治改革,一方面要满足列强停战协议的要求,建立一个议会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若不建立新的宪制秩序,德国政局很可能会走向四分五裂、暴力动乱的漩涡。
可以说,魏玛的民主化进程是直接受到战争逼迫而推动的,不过从国家内部看,旧帝国政体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1919年曾有小册子在魏玛坊间流传,书名便叫《皇帝走了,将军们留下了》。同时,各大政党之间的党争十分激烈,大家内心皆知民意如散沙,谁能争夺民意,谁就能获得新宪制秩序的决断权力。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1月19日艾伯特主持国民议会选举,采用世界较为先进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了421位代表参加国家立宪会议,政府将投票权开放给所有25周岁以上的成年公民。社会民主党获得最多选票(1 150万张),但他们在议会中并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在421个代表中只获得了163个席位,占37.9%的选票,不得不与代表天主教的中央党以及代表自由党左翼的德国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这一阵营史称“魏玛联盟”。可见,魏玛政府是各方势力让步妥协的结果,但毕竟在形式上又是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这标志着德国历史从帝制迈入了共和。
艾伯特担任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他的主导下,1919年2月6日立宪会议在小镇魏玛召开,成立了以普罗伊斯,马克斯·韦伯,以及恩斯特·特洛尔奇等精英为代表的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委员会,他们仔细研究了瑞士、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宪法,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立宪经验,在形式上制作出了一部“周全宪法”。这部宪法结构之雄浑、条文之细密,连英、美、法等国一流法学家都大为称道,将之视为“最为完善的宪法,几乎可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运行”,1919年民国张君劢读《魏玛宪法》后兴奋不已,在《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上号召“吾国民将德国第一期之共和建设史书万遍,读万遍也”① 张嘉森:《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0页。注:张君劢原名张嘉森,此书出版时用的是原名。 。
在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物资装备部和专业分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渤海装备按照物资采购建立区域集中储备中心的工作要求,在国内最大烟气轮机制造企业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建立了中石油烟气轮机集中备件储备库,集中储备了中石油集团所属各大炼厂的烟气轮机轮盘、动叶片、主轴等十大类近700件/套的关键备件。
如果抛开《魏玛宪法》的外在形式不谈,转而考察宪法本身,同样会发现诸多矛盾。第一个让人感到刺眼的是新政权的国号“Das Duetsche Reich”,这个宪法名称与旧帝国并没有什么不同,但《魏玛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德意志联邦是共和政体,国权出自人民”,无疑明确正式宣告废除帝制,政府实行民主选举。若真要表达德意志共和国的含义,国号应该是“Das Duetsche Republik”。一个号称人民主权产生的共和国的国号竟然仍是“帝国”,无疑让人感到大惑不解。即便是德国知识分子仍然持有德意志帝国共同体情节,可威廉二世被赶走之后,以普鲁士王国为中心,各地方依附普鲁士央地传统帝国的结构俨然被肢解,新共和国的联邦由中央和地方组成,地方政府地位从“德意志邦国”降为“州”。这个模仿美国和瑞士的空洞联邦制根本无力凝聚起整个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意志。
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失败的产物。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十四点计划”,称它是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唯一方案”,并提出要以这一计划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纲领”,以此描绘战后世界蓝图。经多次磋商,协约国勉强同意以十四点计划作为议和的指导纲领。德国在这场谈判中所拥有的筹码并不多,虽然十四点计划没有直接要求德国的政治体制做出改变,可该计划核心要义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此时的魏玛共和国而言,这就涉及如何将一个君主制国家改造成一个民主制国家。
可是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并不认同宪法的设计。在他看来,《魏玛宪法》在形式上模仿各国先进宪法,显得像一个宪法怪物(这几乎是当时魏玛学界的共识)。宪法生效之后,魏玛国内流行过一幅漫画:《1919年的宪法连衣裙》,嘲笑的是普罗伊斯制定的这部宪法不过是“全盘西化”,是英、法、美等国宪政制度的舶来品拼凑之物。宪法内部条文的制定几乎是党争利益争夺的体现,《魏玛宪法》成为各个党派的政治妥协之物,这造成了宪法本身纷繁复杂,体例庞大。宪法制定者普罗伊斯何尝不知?他评价自己的作品道:“这部宪法并非在阳光之下诞生,而是身负国家战败深渊,整个民族不幸之下。”② 考威尔:《人民主权与德国宪法危机:魏玛宪政的理论与实践》,曹晗蓉,虞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与其说妥协中道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不如说在国内外复杂环境下产生的《魏玛宪法》先天羸弱,不堪一击。
根据图4所示的不同围压下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可以得到不同砂粒含量下的砂质黄土的摩尔-库仑抗剪强度包线如图5所示。由不同砂粒含量下砂质黄土的摩尔-库仑抗剪强度包线可以得到其抗剪强度强度参数如表2所示。
二、美国宪制的想象:《魏玛宪法》第48条的理论来源
这便是魏玛宪法紧急条款(第48条)产生的时代背景。跳出那个时代,从整个德国宪法历史看,在宪法框架内设置一个“兜底”性质的紧急状态法律条款是德国法传统的特征。从1848年《普鲁士宪法》第111条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第68条都规定,皇帝拥有调动军队作战的唯一权力,则《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的总统紧急权力是遗留在民主议会政制中的最后“帝王痕迹”。故而,我们说《魏玛宪法》第48条,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总统紧急权力。不过,总统制度是美国人的发明,威尔逊对《魏玛宪法》制定时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我们要探讨魏玛的总统紧急权力制度,需要反过来考察美国的总统制。
在1878年费城制宪时,摆在美国国父面前的立宪难题并不比1918年的魏玛国父们小。制宪会议对美国政治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探讨,涉及新政府性质、分权、众议院、参议院、总统、司法等内容。这个依靠战争塑型的国家在建国会议上,必须回应的首要问题是:新建国家如何保障自我安全?美国的国父们非常清楚,历史上的宪制与理论表明,要保障自我安全首先应该从制度上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应对内外的军事威胁。那么,如何使得这个强力政府与国会协调呢?美国的经验是设立一个功能强大的总统,统摄委任军官、统帅和指挥武装力量的权力。1878年费城宪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并在各州民团奉召为合众国执行任务时担任统帅。”总统拥有如此强大权力,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总统就是国王① 姜峰,毕竞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中的辩论,1787—1788》,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为了制衡总统权力,宪法在第一条第八款中将宣战权赋予了国会,十二到十四项赋予国会“招募军队、提供给养,装备海军并维持补给,制定统辖陆、海军的条例”。如此,在宪法设计上,美国宪制中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保持某种形式的制衡:总统拥有指挥作战的军事行动权,国会则拥有组织和管理军队的军事政务权。不过,宣战权只是表达对敌对国家战争的宣示,并不是一种战争行动,而真正的战争权应该是对敌军开战部署,或者发动战争进攻的权力。故而应对军事紧急状态的决断权到底是国会还是总统,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晦暗不明的中间地带。在美国历经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的战争决策权达到了顶峰。
在魏玛的国父们看来,魏玛共和国产生于云谲波诡的历史时代,若总统不具有强势并灵活的紧急权力,行政效率则难以得到保证,更不用说要应付对国家宪制造成冲击的紧急状态。
美国在设计宪法时可以把关于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的争论,转变为共和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职能划分② 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魏玛共和国不同,1848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中都指明国家的力量需牢牢掌握在国王手中,新宪法中总统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如何确定议会对总统制约的权力呢?这个问题摆在了新的立法者的面前。
施米特质疑:第2款的第1句所列举的条款是否意味着对第2款第1句的限制?第48条会有怎样的限制和可能性?他对这两个疑问持有否定观点。按照魏玛宪法之父们设置第48条的初衷,这个条款应对的是魏玛共和国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严重的扰乱或危害,国家遭受巨大动荡冲击,在这一大前提下,总统动用第48条时应该不受到任何限制。此时此刻,总统可以采取任何措施来处置当前的情形。无疑将第48条的实际执行者的总统变为紧急状态下的“立法者”。
同时,作为一部现代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是其基本特质。比如《魏玛宪法》第73条对共和国通过法律有严格规定:第一,议会要审议通过一项立法,首先要由总统提前一个月将立法议案交由人民公决;第二,法律之由联邦国会三分之一之动议、展期公布者,如得有投票权之人民1/20提议,应交付国民表决;第三,有选举权之人民十分之一请愿提出法律案时,亦当交国民公决之。如此看来,只有“帝国总统有提交国民表决之权”。韦伯欲将总统视为受人民所托而制衡议会的力量,在议会之外行使独立决策权的设想得以基本实现。不过魏玛的著名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继承了韦伯的“直选总统”概念,却将之具有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因素剔除。接下来,我们考察施米特对第48条的解读。
第3款、第4款、第5款是紧急条款限制条件。其中第3款是要求总统把依据第1、2款动用的措施告知参议院,国会也可要求废除这些措施。第4款规定:“如果拖延会引发危险,州政府可以在其领土内采取符合第2款规定的临时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应联邦总统或国会的要求而废除。”
1918年11月马克斯·韦伯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勾勒出德国未来政体的基本轮廓。他质疑从德国历史宪法传统如何走出一条既民主(人民)又自由(议会)的宪法。在他看来,新的宪法势必不能完全照搬欧美,要根据德国实际来构建。而这个德国宪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削弱普鲁士邦。若继续延续原有法统,便会引起诸协约国的猜忌,从而强加给德国更苛刻的和平条件。普罗伊斯强调“创制一部宪法不仅仅意味着改变统治模式”,而是意味着全新的共同体意志的构塑与表达③ 李强《:宪政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另参见房宁,涂锋《:当前西方民粹主义辨析兴起、影响与实质》《,探索》2018年第6期,第66-71页。 。普罗伊斯追随的是卢梭“公意”的概念,通过强调“人民”基于同质性的政治共同体从而形成“公意”。但卢梭的困境是,作为公意前提的政治共同体如何形成?也就是说,谁来共同签订社会契约,形成公意?这是韦伯与胡果·普罗伊斯对待新宪法的最大分歧。
三、强力是安全的保证:卡尔·施米特对《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解读
正如上节所述,《魏玛宪法》是多种理论与实践混合妥协的产物,其中的这个“强力条款”第48条,自然成为了诸多法学家评述的对象。1922年葛劳发表的《总统和各州政府依靠〈魏玛宪法〉第48条实行专政》中认为,《魏玛宪法》第48条几乎是一项毫无限制的条款,在危机情况下,所谓的限制条款几乎无法起到任何作用。1924年,托马在《控制独裁权》一文中重点研究了第48条第1款即有关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条款,还讨论了公民在紧急状态下如何保障个人的人权。同年,雅各比发表《关于〈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的总统紧急权的报告》,不仅辩证地看待第48条对宪法的破坏作用,还考察了其对魏玛宪制的维护作用,这篇文章提出了“作为宪法敌人的专政,如何在宪制危机时刻保卫宪法”的观点。1925年拉维尔斯基发表《解释〉魏玛宪法〉第48条》,与雅各比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尽管第48条具有维护魏玛宪法制度之功用,但仍应该强调宪法的其他条款对第48条的限制,如此才能合法地捍卫宪法秩序① 方旭《:民主政制中的专政法权:魏玛宪法第48条总统紧急权的法理学研究》,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2-13页。 。
魏玛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论专政》的附录《论〈魏玛宪法〉第48条的总统专政权》中专门对《魏玛宪法》第48条的第1、2款进行分析。他认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动用第48条的前提有二。一是用来调节央地关系,即地方某邦不服从中央宪法或者联邦法律规定义务时。这在1932年普鲁士诉联邦政府的案件中便有所体现:兴登堡总统动用第48条赋予的紧急权力,中止普鲁士州行政职能,由中央政府直管该邦事务。二是当总统认为有“扰乱或者危害公共安宁及秩序”情况存在时。可是,谁来界定“扰乱或者危害”的程度如何呢?同样在1932年的案件中,当兴登堡总统认定纳粹的冲锋队扰乱公共秩序,向普鲁士派驻联邦特派专员时,遭到了普鲁士当地政府的强烈反弹,不惜向宪法法院提请对中央政府的诉讼。通过阅读魏玛的历史可以知晓,所谓紧急状态首先指的是对外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内的政治不安定的状态。这点不言自明。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10月12日艾伯特总统动用宪法第48条禁止投机炒作外币,从而认定第48条中“扰乱或者危害公共安宁及秩序”既包括政治动乱,也包括经济危机。总的说来,《魏玛宪法》对总统在何种情形下动用紧急权力界定不清,比如宪法中并没有说明地方应对中央尽到何等义务、扰乱或者危害秩序之内涵以及总统采取“必要处置”的幅度等。这些都要依靠总统紧急权力的自由裁量。施米特认为在非常时期,总统具有某种普遍的权威“中止公民的基本权利”② 施瓦布《:例外的挑战:1921年至1936年间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李培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
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魏玛临时政府宪制改革有好几套方案,改革的关键在于是否废除普鲁士邦的强势地位。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肢解普鲁士,他力主延续俾斯麦宪法模式,可以削减普鲁士的实力,但仍要保存必要的优势地位,以此凝聚各邦国的力量。不过鉴于内外压力,1918年11月15日,魏玛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委任胡果·普罗伊斯主持起草宪法,他提出的是“散权化单一制国家”的方案,即:一方面未来德国要服从协约国的意愿,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央要保证对地方具有实际控制权力。这个方案将普鲁士肢解为10个州,从而使得整个国家分为16个州,但如何既平衡各方势力,又保证中央的权威?这是普罗伊斯起草宪法遭遇到的难题。
1.QQ天天在线,说明你害怕孤独;2.QQ天天隐身,说明你承认孤独;3.QQ天天忙碌,说明你装不孤独;4.QQ天天离开,说明你暗示孤独。
选取鼻腔优势菌种为表葡菌者进行BF培养。治疗前鼻腔优势表葡菌BF阳性率为73.6%,治疗后鼻腔优势表葡菌BF阳性率降低为33%。正常人中鼻腔优势表葡菌BF阳性率10%。
从第48条的法理内涵上看,这个紧急条款终究是一种临时性的权力,尽管何为“紧急”的法律界限晦暗不明,但仍然要将之称作是“临时授权条款”。施米特主张的“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并不意味着将切换成“主权决断常规状态”。施米特对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解读几乎是古罗马专政官制度的现代翻版,《魏玛宪法》第48条就是典型的“委托专政”。按照其《论专政》一书中对“委托专政”的论述:委托专政者只是在国家危机时受到最高权威之任命,至于这个权威是“君主”还是“人民”,将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只要受托者完成了这项任务,其委托专政的权力也将交托给最高统治者。
不过,按照现代民主制的说法,人民通过行使制宪权,从而创制宪法,现代民主共和国据此得以建立。当“公共秩序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总统作为最高制宪权威的人民之意志的代表者悬置“宪法基本权利”,拥有暂时不受约束的权力重建共和秩序。从面上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专政”,但若究其本质,则这是一种“主权专政”的结果。人民作为一种普遍意志的承载者,通过政治的同质性形成统一的主权意志,由此,总统作为共和国的意志的体现,代表人民意志出场。尽管如此,对总统紧急权力的限制条件却不得忽视:第一,第48条第3款规定总统有向国会告知动用条款之义务,否则国会可以中止条款的运行。第二,第43条规定,国会可以以三分之二的动议罢免任期未满的总统。第三,副署制度要求总统和内阁在采取行动前必须达成一致。第四,根据第59条规定,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可以控告总统“违反宪法或者其他共和国法律”,最后在众议院的支持下,可以向最高宪法法院弹劾总统① 罗斯托:《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孟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但是《魏玛宪法》内部仍然设置了对国会权力的反制条款,比如第25条赋予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以及第53条总统有选择和撤除部长的权力,这些权力在一些特定情形之下可以帮助总统摆脱国会或者部长副署制度的制约。
四、《魏玛宪法》第48条的实践与影响
《魏玛宪法》本身与《魏玛宪法》第48条之间的内在张力体现出魏玛宪法“双头政治”特性:日常政治秩序以人民主权代表的国会行使,一旦出现紧急状态,全民选举的总统则呈现出帝王面相。这样的独裁权力超越国会之上,可以动用强大军事力量维持国内秩序。考虑到魏玛共和国诞生时动荡混乱的境地,设立强权总统也并无过错,然而,总统在危急时刻拥有的强大自由裁量权真的能够为宪制秩序本身带来安全吗?还是给德意志传统的君主意识和集权意识冲击薄弱的魏玛民主提供了正当理由?
从历史上看,在魏玛共和国艰难诞生之后的最初几年内,为了应对国内政治混乱,经济萧条等危机,《魏玛宪法》第48条的使用超过130次,如果没有这个紧急条款的维护,魏玛共和国不可能充分实现其宪法设计者的民主-自由的期望。到了魏玛共和国晚期,德国政府运行几乎完全依赖《魏玛宪法》第48条,本条款在魏玛共和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该条款援用次数达到了令人吃惊的250余次② 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假借“国会大厦纵火案”说服总统签署动用第48条紧急命令。按照《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规定,这条法案可以中止公民基本权利,紧接着就是“合法的恐怖主义”登堂入室,终于成为压垮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架空国会的《授权法》出台后,政府可以不经国会同意颁布任何法律。实际上,这从法理上实现了希特勒拥有至高无上独裁权力的野心。这个号称人类历史上最自由、民主的《魏玛宪法》名存实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三帝国被摧毁之后,鉴于《魏玛宪法》第48条被滥用的惨痛教训,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省,联邦政府在设计《联邦德国基本法》之初,便号称以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作为宪法的基础和最高价值,从而取消了紧急条款,采取由议会宣告紧急状态的方式应对危机。反讽的是,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1968年6月24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所合组的“大联合政府”颁布了《基本法第17次修改法》,重新请回了“紧急条款”。
正如施米特发现了自由主义法治国中存在的“法与非法”相互依存的法理悖论,本雅明也发现,代表“法中非法”的“紧急状态”同样会成为国家暴力入侵法治国秩序的合法依据,主权者为维护宪制秩序寻找动用暴力的正当性基础。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的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③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见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69页。 。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和哈特延续本雅明的思考,将法律规范对紧急状态的驯化推向另一种极致。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作为数字化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帝国”,凭借着技术将规训之术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操纵着所有社会的秩序。“在一个规训性的社会中,随着所有生产与再生产的有机系统的发展,整个社会都处在资本与国家的规训之下,而且整个社会会逐渐和带着不可抑制的持续性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所单独规训。一个规训性的社会因而是一个工厂式的社会。”① 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一旦新帝国所辖秩序发生混乱、暴力和战争之时,“例外状态”就如约而至。“新帝国”的推行者借着维护公共秩序之名,通过类似颁发“紧急状态令”的合法途径,用暴力维护秩序。在法律之幕的掩盖下,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群已经无力认识到新帝国的暴力真相。帝国主权为实现真正全面的统治,用“例外状态”抽空了人作为法律的主体性,公民社会与国家主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此走向终结。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清晰地认识到,自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之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不再被视为一种“例外状态”,而是“危机就是一种不能浪费的坏消息”② 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但他并未消极地看待法律规范对紧急状态的控制,2006年他将《不要恐慌》《这不是一场战争》等讨论紧急状态宪法的主题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下一次袭击之前:恐怖主义时代捍卫公民自由》。本书宣称“要设计一种宪法框架,允许某种暂时的紧急状态存在,从而既能够让政府负责重新恢复秩序的功能,同时对个人权利不至于受到长期的侵害”③ Bruce Ackerman,Before the Next Attack.Preserving Civil Liberties in an Age of Terrorism,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80. 。阿克曼的紧急宪法设计能否吸取魏玛共和国的教训,从而探索出一条危机状态下的新宪制秩序?这还需要美国宪法制度在实践中进一步回应。
An Emergency State and the Weimar Republic:A Focus on Article 48 of The Weimar Constitution
FANG X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The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Committee of CPC,Chongqing 400042,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egislative practice,The Weimar Constitution is the first constitution with built-in emergency clauses in the world.The Weimar Republic is also the first“political test”of the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n German history.The evaluation of this constitu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is mixed.On the one hand,The Weimar Constitution is the first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in German history.Literally,it can be the constitution that best meets the taste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jurists,and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freest and most democratic in the world.On the other hand,an urgent clause that preserves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Article 48 of The Weimar Constitution)also incurs controversy among the constitutional community in Germany.
Key words: Article 48 of The Weimar Constitution;state of emergency;Marx Weber;Carl Schmitt;
[图书分类号] D 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9)05-0018-07
[收稿日期] 2019-02-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XKS0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9M650953)
[作者简介] 方旭(1984-),男,湖南衡阳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严孟春]
标签:《魏玛宪法》第48条论文; 紧急状态论文; 马克斯·韦伯论文; 卡尔·施米特论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