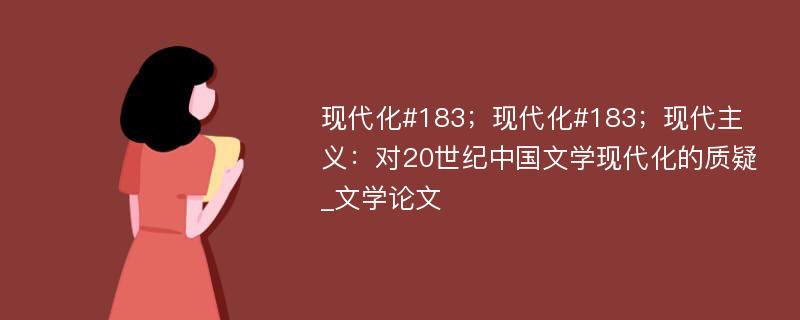
现代性#183;近代性#183;现代主义——对《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现代性论文,现代主义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虽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形态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赓续,是自本世纪初文学改良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确立的与中国古代文学完全异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继。以上我所说的几近于常识,然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这也是我最近读了杨春时、宋剑华两先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①a](以下简称《近代性》)一文之后引起的一点想法。
对于《近代性》一文有两点质疑,陈述如下,希就教于杨、宋两先生。
一、关于“现代性”和“近代性”
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不具备现代性,只具备近代性,这是《近代性》一文立论的基点,而这种提法是否成立本身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近代性”与“现代性”两个名词本身存在相当程度的概念内涵的模糊性,不宜用作选言判断的不相容选言肢。应当指出,《近代性》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字重新定性的愿望是有其合理背景和出发点的。即在中国文学巨变百年的时候,借用范伯群先生的话说,“我们的学科虽然不再年轻,但我们还没有为自己‘取名’。至少我们只有‘乳名’而没有‘学名’,也即是说,我们的学科的名称的科学性尚待科学鉴定。”[②a]然而《近代性》一文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定名为“近代文学”,事实上并未恰切地科学地鉴定了我们学科的名称,只能说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对文学史的又一次不成功的“取名”。《近代性》误入的圈套仍然是数代学者中了无数次的那个圆套,即,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它们原本是一个术语。为什么“我们只有‘乳名’而没有‘学名’?”就像樊骏先生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近代”“现代”“当代”的段落划分,从一开始就存在了相当的临时性、相对性和模糊性:“无论在汉语还是外文,‘近代’和‘现代’都没有什么区别(比如都相当于英文的modern,所以夏志清的那部小说史,就有《中国近代小说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两种译名),‘现代’和‘当代’也没有什么差异(比如都相当于英文的today、nowaday、contemporary)。”[③a]正由于这种名词的不确定性,《近代性》一文在英文目录中也被毫不客气地译作“On the Modernit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就是说,如果根据这个题目再转译成中文,完全可以是“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同样,假如把这篇论文译作英语,则会出现通篇的“modernity”,这恐怕是作者所始料不到的。
其次,“现代性”本身是一个随时代变动而外延不断改变的概念,《近代性》却忽略了这个事实。企鹅书店《现代主义》的两位主编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指出:“在通常用法上,现代性意味着某种以年代推移的速度、与年代一同前进的东西,就像船头浪一样;去年的现代就不是今年的现代”,因而,“当人们超越历史的范围时,或者用G.S.弗雷泽或《现代传统》编者们的话来说,当人们称卡图卢斯(而不是维吉尔)、维庸(而不是龙沙),多恩(而不是斯宾塞)、克拉夫(而不是丁民生)、康拉德(而不是高尔斯华绥)为自己那个时代的‘现代’作家时,这个词语在意义上的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①b]正由于此,陈子展1929年4月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从戊戌维新讲起,而钱基博1933年9月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从辛亥革命讲起,任访秋1944年5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则从清末直贯抗战。可见,所谓“现代”或“近代”在不同学者眼里有着不同的所指,而不论众人的观点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即“现代”总是指著史人当时所在的这个时代[②b]。有鉴于此,我们在对“现代性”的概念的模糊性与变动性有所了解之后,再说我们现在的文学不是现代文学显然就有些欠通了。
再次,《近代性》用以界定现代性的所谓“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视角”,也有一定的盲目性。歌德在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从此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并引发了比较文学的发生。这诚然是由于国际文学的互动日益鲜明,但同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离开本土,离开民族,一个人、一个作家群、一代文学工作者的作品是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范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然应当放在世界文学中进行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定性与定名也一定要套合欧美文学的历史进程。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的现代性是相对于二十世纪之前欧美文学的异质而定性的,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则是相对于文学革命之前的中国文学的异质而定性的。中国没有经历过欧美(确切地说,美国与欧洲也很难并提)经历过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应地,也就不存在与欧洲古典文学相对应的中国古典文学,与欧洲近代文学同质的中国近代文学,自然,虽同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欧美的现代文学却决不是一回事。“机械地套用西方文学史的分期于中国文学”,无论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等同于欧美现代文学,还是欧美近代文学,都是不可取的。
复次,《近代性》认为,按一般的文学史分期,“好像中国的古代文学一跃便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而中国的古代文学一下子就获得了现代性”,文章以此作为本世纪中国文学尚无现代性的一个依据也有失考虑。不可否认,作者指出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几乎取消了中国近代文学史,只是把它限定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前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而且也很少有创作实绩给予支撑”的问题确实存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的薄弱也是实情。然而,研究工作的欠缺并不意味着文学发展史上渐变过程的不存在。周作人就曾将明末的文学视作五四文学运动的渊源,这是在中国文学史内部矛盾运动中寻找现代文学之发生根源的第一次尝试。如今这样的尝试日渐增多[③b],这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变异过程的。晚明时期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相应地,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带有西方近代性色彩的主张与作品,如果没有有清一代的打断,说不定中国近代文学就如《近代性》的作者所设想的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因此中国近代文学应该说从晚明的变异,到清代的蛰伏,到晚清的渐成风气,它以其独特的面貌存在着,虽然它不像欧美近代文学那样,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别名,然而却同样是一种现代文学的先声,那就是单单属于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
以上从辨析概念入手就《近代性》五论的两个依据提问,下文将涉及《近代性》一文的另一关节:现代主义。
二、关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
由于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其实已经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之谓是个有特定定义范围的概念。80年代后期,学界曾就其定义达成了一点较宽松的共识,表述为:“文学的现代化,包括了从文学语言到艺术形式、表现方法、审美情趣,到思想内容的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革和创新。”[①c]王瑶先生特别指出,由于“‘现代’既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时代概念,它最主要的内涵就是时代精神”,这个定义“就自然包孕了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观察角度,也不致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生混淆。”[②c]而《近代性》一文之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发生疑问,就是因为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与“欧美现代主义文字”的“现代”混为一谈了。
对此,《近代性》一文有这样几个主要观点:
1.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不属于现代文学的主题;
2.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排斥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所以不是现代文学;
3.中国文学“苏化”之后走入新古典主义,近代文学过程被延长;
4.九十年代中国文学非理性倾向加强,这预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将出现现代文学。
这四个问题根源于同一个逻辑前提,即衡量一种文学是不是“现代文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本世纪初勃兴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作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具备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所以不是现代文学,我们虽已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范围,但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姑且退一步,先同意《近代性》所论,以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尺来衡度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第一个问题——《近代性》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是对国家、民族、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注,它以自己的方式作为近代意识形态的载体参与了社会的变革,而不属于关注个体精神归宿的现代文学主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是什么,这是个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当然,“对国家、民族、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注”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但能不能说它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呢?李泽厚先生曾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归纳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③c],这应当是对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史特征的一个更到位的概括。从这个命题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则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分别应和思想史的两大主题。那么,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至少有两个,即启蒙与救亡,《近代性》显然忽略了前者[①d],而恰恰是前者关心着个体精神的归宿。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三位学者则概括道:“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规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②d],这是切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质的。对精神的高度重视决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对话的可能性,启蒙的艰难使得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心灵满贮焦灼与苦闷,这不用说更是与同时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特征直接相通了。
第二个问题——《近代性》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近代性的表现之一是“它排斥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不大,几乎未能进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广大作家的视野之内”。这一判断当然是不准确的。世纪初的译介热浪中,与世界文学长期隔膜的中国作家对来自异域的各种主义和思潮采取的是一种兼容并取的宽容态度,现代主义就是在这时与各种近代文学思想一同进入中国文学的。与其说“中国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化,不是它独立运动的结果,而是西方近代文学冲击的产物”(《近代性》),不如说,中国古代文学,由于它自身的独立运动遭受过历史的挫折,新文学的因素作为某种潜流,在海禁开放之后,受西方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共同冲击,终于被激发为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不是排斥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文学运动,相反,现代主义文学从本世纪初即被传入中国,在五四更是掀起波澜,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纷纷得到译介,它们直接参与了“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反传统热潮,成为变革文学形态的一大武器。胡适对美国意象主义文学主张的借用,鲁迅本人对尼采哲学的阐发,作品中充斥的荒诞感、孤独感和虚无感,都是著名的例证。随着一代作家的成熟和客观情势的日趋复杂,中国文学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与引进呈现了日益理智化的特色。正如《近代性》所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遭到了文坛主流的一定程度的排斥,这是中国以救亡压倒启蒙的时势使然,是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使然,但同时亦是中国作家自觉选择的结果。历史决定了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的土壤中不可能不加任何改造地存活。而事实上,以现代主义为创作手段之一,与现实主义等创作手法相结合,共同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学,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已经做了并仍在继续进行的一项伟大功业。《近代性》只是列举了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曹禺式的表现主义戏剧这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其实只要再深入一步,即可发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接受现代主义影响远远不止这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象异彩斑斓,却总是很难脱开时代的哀感,作家入世的企图每每将这种哀感冲淡,却也总无法掩饰那现代人才有的不安心境:以现实主义著称的作家,冷静客观的外衣包裹着更接近于现代主义的时而孤寂,时而躁动的焦灼心灵;以浪漫主义名世的作家,与西方浪漫主义者的形似之中,隐隐传递出只有二十世纪现代人类才有的绝望与无奈;被后世认为更赋有现代主义品格的作家,却又总有一重永难释怀的济世拯民的抱负藏裹胸中。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泾渭分明地画出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鼎足而治的三国地图可能是一种自缚之举,真正出色的中国现代作家是难以用西方的某“一种”创作流派归类的。中国诚然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诚如《近代性》指出),然而也没有出现过一件纯粹的人文主义文学或古典主义文学或启蒙主义文学或浪漫主义文学或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外界综合影响与中国文学自身努力双重作用后形成的,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特征,表现现代中国人心灵的文学形态,是中国的现代文学。
第三个问题——《近代性》认为,“革命文学”之后直至“文革”,中国文学走上“苏化”的道路,从而“不但没有进入现代阶段,反而退到新古典主义,与世界现代文学拉大了原来的距离。”这是《近代性》一文颇为精采的论点,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触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不可违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古典化的加强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里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澄清。首先,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勃兴只是当时文坛发生的“一件”大事。当时的文坛尚不存在主导话语,故而也谈不上是“五四的‘西化’”就这样“演变成为‘苏化’”了。就在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时候(1928年2月),茅盾正在创作他的细致描摹知识女性虚妄感受的《蚀》三部曲,沈从文正在连载他的颇具荒诞意味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丁玲恰巧发表了她的深怀绝望与恐惧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巴金还在为无政府主义奔忙,老舍则在万里之外的伦敦大学图书馆读他的康拉德……而正当左翼文学运动蓬蓬勃勃地展开的同时,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以及继起的京派),新感觉派,论语派,象征诗派等文学社团和流派同样如火如荼,并有着骄人的创作实绩。在这样的文坛景象中,把中国文学描绘成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就“开始全面接受苏联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显然是过于夸张了。其次,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和政治原因,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入了那一段岑寂期,然而,却不能说这就是文学史的“倒退”,因为只有历史的发展过程已有规定模式,一旦不符合这个模式才有“倒退”之谓。王富仁先生在论述近现代文化史与现当代文学史时也曾以西方历史作参照系观照过中国的情况,他当时是审慎地使用了东西方“互为逆向发展”这样的表述[①e],而《近代性》的作者,由于是先入为主地以西方近代文学的发展史为参照模式来反观中国文学,就必然地失去了一份史家的公允心态。再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确有一段对现代主义视作洪水猛兽的历史时期[②e],但即使这样,五四传统作为一种潜流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当然,我们已经论述过,五四传统就是真正具备现代特质的中国文学新传统,其中自然也包括某种与西方非常相近的现代主义情绪的凝聚。因而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它也没有真正绝灭过。以现代主义为主力军的现代文学在新时期的爆发,就证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顽强生存。
第四个问题——《近代性》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进到了‘后新时期’阶段,现实主义的势头大为减弱,而现代主义的因素则迅速增强”,这表明中国文学正“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学冲刺”。这里,作者立论的前提是中国现在的文学尚无现代性可言。本文是不同意《近代性》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的,而且刚刚已经证明了即便以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仍具备着相当强的现代性。然而,为了看得再清楚一些,不妨再退一步,承认中国文学尚无“现代性”,看一看能推出什么结论。作者说,“文学的理性精神和理想性消歇,非理性、非理想倾向加强”,“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言下之意,中国文学要想具备现代性,必须走非理性化的道路。这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命题。中国文学的非理性化倾向近年来确有加强,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新现象。先锋小说对形式的狂热追求显然根源于某种对内容与主题的躲避,然而既空且玄的语言游戏,不但令读者腻味,而且使作者们也渐渐显出底气不足来。中国文学应当是有中国个性的文学,跟着欧美亦步亦趋决不是办法。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不但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经验,而且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现代体验。新时期,尤其是市场经济环境里中国文学如果说具备了某种欧美现代性,那也只是近似而已。同时,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学。我认为二战后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枝)的非理性是得自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那就是两次大战对整个人群价值信仰的无情摧毁和继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对人类的全方位围困,这些因素加上非理性主义哲学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催生,才产生了总名为“现代主义”的二十世纪各种非理性主义文学流派。现代主义文学当然是文学在新的时代考验面前的一次成功的突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有不少属于文学的畸变。未来主义的随心所欲的对凌乱感的过分追求,新小说派对小说基本要素(情节人物等)的不成功消解,“垮掉的一代”对人的原始欲望的放纵和粗糙表现,等等,与其说是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毋宁说应当是引起我们警觉的前车之鉴。最后,《近代性》的作者还忽略了这样一点,欧美现代文学本身并不完全等于现代主义文学,它应当是现代主义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合体。以英国文学为例。一个世纪以来,正如戴·洛奇教授指出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品不仅贯穿于整个现代时期,我们还可以勾画出这两者交替出现、轮流支配的各个阶段”[①f]。约翰·高尔斯华绥、托马斯·哈代、乔治·奥威尔、约翰·普里斯特利等名字的存在证明了菲尔丁、狄更斯传统的绵延不绝。而在意识流小说、南方文学派、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小说的策源地美国,一战后尚有以德莱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群,二战后则有以索尔·贝娄为代表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队伍的存在;即使是公认的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如南方文学派的福克纳,“迷惘的一代”的海明威,同样不是纯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要想取得恒久的生命力,对现实主义的合理化利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手段,正如现实主义在现在的时代要想站住脚跟,也必须借鉴现代主义的成功经验。文学的解放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向,但即使是欧美现代文学也并没有迹象表明文学的最终目标是弃绝理性的文学或者说弃绝现实主义的文学。《近代性》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文学”,进而得出结论,中国文学正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学”即告别现实主义传统,以非理性化为标志的现代主义文学冲刺,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综上所述,《近代性》一文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只具备近代性、不具备现代性的结论是以欧美近代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为参照标准得出的一个很可质疑的命题。虽然《近代性》的作者认为非理性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但我们还是愿意治史的现代人能够理智些,再理智些。
注释:
①a 《学术月刊》1996年12月号,下简称《近代性》。
②a 范伯群:《危机主要不在于“人满为患”和“空间狭小”》,《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应当说明的是,范先生文中提出的弃“现代文学”而使用“新文学”的名称的设想还是可以讨论的。
③a 樊骏:《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探讨——关于讨论近一百多年文学历史分期的几点理解》,《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12期。
①b 〔英〕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名称和性质》,《现代主义》6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
②b 参阅《现代汉语词典》。
③b 如吴中杰:《现代文学研究要破关而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3期),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骆玉明《向新文学的推进》(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章培恒、谈蓓芳:《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科版)》1996年4期)等。
①c 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②c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王瑶、李何林《中国现代文学及〈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知识出版社1990年6月版。
③c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①d 应当说,《近代性》一文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但几乎每一次都存着向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靠的企图,故而并未从本义上理解同样是单:属于现代中国的“启蒙”——以国民性改革为最终趋赴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它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目的紧密结合,难分畛域,但毕竟是属于精神领域的,与救亡主题各有分工。
②d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①e 王富仁:《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4月。
②e 参看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第4章第4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①f 〔英〕戴·洛奇《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侯维瑞译自英国《新评论》1977年5月号,沈恒炎、吴安迪主编《外国文艺思潮》第4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