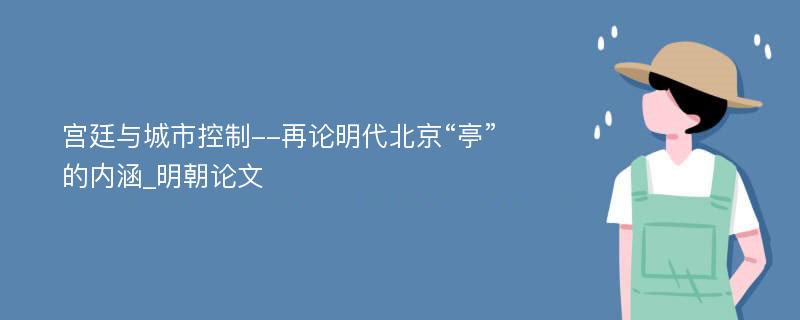
徭役与城市控制:明代北京“铺户”内涵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铺户论文,徭役论文,明代论文,北京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11-0120-09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北京城市史呈现出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民族史等多视角综合研究的取向,这不仅拓宽了北京城市史研究的领域,也凸显了北京城市史的特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1]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如明清时期北京“铺户”的内涵及其实质方面,学者们之间尚存在不少分歧。 对于明代“铺户”的诸多研究涉及其概念、来源、分布及性质等方面,以往学界已经进行了许多深入讨论,并且积累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立足于“铺户”的职业类别及其主体的角度来把握“铺户”的内涵,即认为明清时期“铺户”应为兼坐贾和手工业者双重身份的城镇工商业者,①是除官员(及其家人、为之服务人员)、卫所军士及其家属外的城市居民主体。[2]部分学者注重结合赋役制度解析“铺户”,如许敏的相关研究认为“铺户”与军、民、匠等户一样,是注以某一籍的人户,“铺户”占商籍及民、军、匠的分化是其转变为“铺籍”的原因;[3]基于对铺户须注籍的认识,她还对明清史籍中所记载的“商籍”进行了研究。[4]高寿仙探究了明代前中期的“铺户买办”和“召商买办”,以及明末买办成为强制性的“商役”的演变过程。[5]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铺户”的演变过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是,深究明代“铺户”的性质,其最初为负担买办之役而设,作为国家徭役的一种具体形式,买办一开始就是城市居民的徭役,而不是官民之间的市场交易。另一方面,明代北京“铺户”的涵义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铺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何出现、出现后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关心的问题。因此,笔者结合明代北京城市城厢控制体系与买办制度变迁,再次探讨“铺户”的内涵。 二、明代北京的城市坊铺体制与铺行之役 以往关于明代铺户的研究多提到明万历年间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宛署杂记》的一段文字:“铺行之起,不知所始。盖铺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曰当行,然实未有征银之例。”[6]这段文字描述的应该是明初北京的情况。从引文我们可以看出,要明白铺行/铺户的内涵的前提是要准确把握“铺居之民”和其所负担的徭役——当行。如沈榜所说,明初北京城市居民按居住区域来编排、按行业注籍来负担徭役,起初城内外居民负担徭役时被称为“行户”。这段文字清楚说明,铺行是为在北京城市占籍、并被编入某种管理体制下的城市居民负担官府的徭役而设的,而铺户服役主要是为官府采购物料。 (一)铺居之民与明代北京城市控制:从坊厢制到坊铺制 明初洪武朝在全国乡村建立了里甲黄册制度,在重要城市中则建立了坊厢体制。明初南京城中立坊、郭外为厢,郊外为乡。其中,上元9坊5厢18乡,江宁15坊12厢21乡。[7]明初降元大都为北平府治,在废元大都城市警巡院的同时将城市划为33坊。永乐改元后的北京依南京例强化了坊厢体制。 关于“坊、厢”的涵义,余清良的研究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其实类似乡村的基层乡治组织。入明后,同“坊”一样,“厢”主要是黄册里甲制度在城市中的编制单位名称,主要在城邑附郭地区实施,其性质、功能都等于黄册里甲组织中的“里”。②坊厢长作为一种职役,最主要的职责是与里甲长一样负担杂泛差役,如张罗酒席等。万历时顾起元称,“而坊厢应付,则各上司祠祭香烛祭物,各上司本县到任、下程酒席、纸札饭食、刑具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门应取杂支,与考试供给,致贺举人、进士、贡士等项之费,此其大略也。”[8]明初陈奂上任上元知县,奉命料理郊天燎火,即招来各坊长,规定“在城不问大小户,各要典一章门庶,并香灯迎驾,不备者罚米一石”。[9] 宣德元年(1426年),因京城治安形势严峻,巡警铺开始进入明代北京坊厢体制中。[10]建立巡警铺的初衷是组织军民防盗防火,并让邻里间互相监督。巡警铺有铺舍,铺设总甲,按照制度要求是“不分官吏、军民、旗校、匠役之家”,都要负担“轮流守望”的夫役。[11] 成化六年(1470年)兵部题本中提到:“本部为火夫之设,所以巡警盗贼,至为紧要,已经议奏,行移五城兵马司,从公查勘。勇士、将军、厨匠等项之家,除有例优免正身外,其一家有三丁或四五丁者,或一户而分二三门者,逐一清出,编入牌甲,令其坐铺巡夜。”[12]这里的“牌甲”即牌铺中的“火甲”,为城市居民巡夜时的夫役。同年还规定每铺设总甲一人,“以丁多者充之,率三月一更”。[13]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材料显示:巡警铺还设有铺长,因为铺舍为总甲巡警所用,亦称总舍,总甲负担巡警任务,故称甲役。总甲以铺舍为定,铺舍以人户为准。因为甲役的负担因每铺承担该役的人户多寡而不同,故有大臣建议“今宜定每铺宜若干人户为则,其人稀者听其彼此通融,或以人户拨补,或以铺分并一”。[14]万历年间沈榜称明代北京“城内地方以坊为纲”,“见在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立铺头、火夫三五人,而统之以总甲”,[15]这里的“铺”就是巡警铺。巡警铺的火夫、总甲是在兵马司的督率下巡警京师,提防火盗。[16]成化朝以五十人为一班次巡夜,[17]直至明末。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详细记载了当时北京城坊/厢—牌—铺—巷、街或胡同的行政、地域管理体制——此时的北京城有40坊厢、110牌、720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左右的宛平县五城有13坊、133铺,并详细记载了宛平县所属坊及其下的牌、铺的数目及名称。[18]随着巡警铺的职能扩展,政府逐渐将其当做基层社会组织,坊铺制取代了坊厢制。 可见,“铺居之民”即为北京宛平、大兴二京县的坊/厢—牌—铺管理体制下的城市居民,但应排除皇室、官僚及为之服务的人口、军人。 (二)铺户与铺行之役 把握明代北京铺户和铺行的内涵,应该上溯到宋元时期的团与行。宋人对此的记载有:“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医尅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内亦有不当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饭行是也。又有名为团者,如城南之花团、泥路之青果团、江下之鲝团、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其他工伎之人,或名为作,如蓖刃作、腰带作、金银镀作、鈒作是也。又有异名者,如七宝谓之骨董行、浴堂谓之香水行是也。”[19]可见,宋代城市各行业的组织是在外在压力下出现的:一是工商业者面对官府的科索和祗应官差,不得不组织起来与官府打交道;二是官府为了便于征调工商业者负担徭役,强制性要求工商业者按照行业组织起来,从而使得每一个在城市谋生的经营者,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投行”,否则便没有合法营业的资格。[20] 宋代史籍中已有“铺户”名词出现,如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户部言:“商旅贩矾,旧听其便。乃者发运司请用河东例,令染肆铺户连保豫买,颇致抑扰。”[21]这里的“铺户”是指城市中负担官府物料供应的商贾。可见,为官府负担徭役的团、行之下的具体工商业者即为“行户”,亦称“铺户”。行户负担的徭役主要为官府提供本铺物料,或提供劳动力。这样的情形在元代同样存在,甚至将官府控制的行的范围扩大,如教书的儒生、乞丐都要编行,负担官府的徭役,即当行和祗应。已有的研究证实宋元时期的团、行本质上是官府将城市中的工商业者编入册籍,保证政府对民间工商业者财货和劳动力征调的需要。[22] 明代的行户(铺户)编为“排甲”(或称“牌甲”)来服役,如“(正德)四年,定行户等第,分为上中下三等,编作牌甲协力奏办”。[23]“(嘉靖)六年正月丙申,户部应诏条上恤民未尽事宜……六、均铺户。言佥报铺户,贫富不均,任意网利,请稽牌甲旧藉,以次征纳,纳完予价,毋令久稽……奏可。”[24]可见,明代行户(铺户)按一定原则编作牌甲来负担徭役。因此,要把握铺户的内涵,还需关注其与所负担的徭役之间的关系。 (三)铺户是铺居之民承担铺行之役的特别称谓 根据前文,明代北京“铺户”是城市坊/厢—牌—铺之下的城市居民承担徭役时的特别称谓。铺行之役,亦称铺役,后又称商役,故有“铺户之设,以待官府征收供亿之用”。[25]铺户商役制度与坊厢(坊铺)制度的结合,便是城市的里甲黄册赋役制度。同样的情况在南京也存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南京礼科给事中游震得称“南京城坊居民自里甲正徭之外,复有各项铺户办纳”,[26]可见南京城坊居民除里甲正役外,还要被编为铺户,为官府办纳物料,而南京的铺户正是城坊居民负担买办物料之徭役时的别名。 嘉靖六年(1527年)的一份材料称:“京城铺户各有本行,如酒醋局、织染局及轿夫,三行多取中产开铺之家应当差役,优免本户。”[27]可见,北京铺行中的酒醋局、织染局及轿夫三行主要是为了方便官府征派徭役、佥定京师中产居民而成立的。 宣德朝之前,北京城中还是坊厢体制,城市居民以“所业所货”的行业划分来注籍,其负担徭役时类似乡村的里甲户一样轮流排年服役,即当行;而服役的人户即称行户。宣德朝后,坊厢体制变为坊铺体制,且铺在京城社会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故宣德朝后史籍中多出现“铺户”,但史籍中也会出现“行户”。万历七年(1579年)吏科给事中郑秉厚奏称:“臣等查得铺行清审,十年一次,自成祖皇帝以来,则已然矣。但排甲卖物,当行而已,未有征银之例。后因行户赔貱不资,苦不堪命,乃议九则征银。官司召商买办,此盖征其银,不复用其力,法之变而通者也。若今之买物,仍责铺户领价,则其赔貱之苦,犹夫故也。”[28]这里郑秉厚将先前因当行而卖物给官府的行户与时下为官府买物服役之铺户等同起来,看来二者是一回事情;细细深究,二者的区别还可能在于时间的先后及服役形式的不同——行户在前,主要是以己之物提供给官府;铺户在后,则是为官府采购物料。 这里提到铺户的徭役——为官府采买、置办所需物料,即“买办”。铺户买办就是官府强迫铺户按照官定价格向其提供或为其采办所需物品。明代北京铺户的买办之役大致先后经历了当行买办、召商买办和佥商买办三个阶段,下面略做介绍。③ 三、明代北京铺户买办的历史变迁 明代政府消费的物料,除来自夏税秋粮及各地土贡外,就是承继宋元的和买、买办。关于明代的买办,《明史》对此有记载:“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于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29]这段话粗略地描述了有明一代买办之役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变化:起初,各地仍需上供本地特产——“任土作贡”,即“岁办”;后来有“采办”——官府出钱,在市场上采购物料,铺户当行买办;其后,又实行召商买办物料。 根据明代买办所呈现出的特点,北京铺户买办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买办制度的建立时期 在目前所见明代的材料中,“铺户”一词最早出现在洪武二年(1369年):“又定时估,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或客商到来,中买物货,并仰随即给价……毋致亏损于民,及纵令吏胥、里甲、铺户人等,因而克落作弊。”[30]这段材料清楚表明,虽受到法律的禁止,但明初“铺户”的确存在,其职责是为上司收买物料。真正建立铺户买办制度则要到永乐朝。 永乐十三年(1415年)二月二十三日,是日“早,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于奉天门钦奉圣旨:那军家每既在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料,他怎么不肯买办,恁户部行文书,去着应天府知道,若有买办,但是开张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等,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31]仔细阅读上引材料,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永乐十三年前民籍铺户已承担买办,而军籍铺户却推避不当,④而永乐十三年的诏书很明确地说明永乐朝的南京城的居民(不分军民)凡开张铺面,必须以铺中物料提供给官府。可见铺户不是一种户籍,不然就不能解释铺户中有军民等籍人户,后文另有论述。 早在永乐六年(1408年)就有关于豁免北京军民买办徭役的规定:“(永乐)六年六月庚辰,诏谕北京诸司文武大臣曰:北京军民数年之前或效力戎行,或供亿师旅,备历艰难,平定以来,劳悴未苏。比以营建北京,国之大计,有不得已重劳下事之人,然隐于朕怀,不忘夙夜……自今北京诸郡不急之务及诸买办悉行停止。”[32]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追忆北京铺行的文字所指应该是永乐迁都北京后的情况。[33]铺户的买办之役首先是当行买办——卖物当行,即沈榜所称“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曰当行”,[34]与顾起元所说“铺行之役,不论军民,但卖物则当行……初令各行自以物输于官”[35]是同一个意思。卖物当行的承担者主要是城市的坐贾及兼手工业、买卖于一身之人,也包括媒人行、挑担行、轿子行等脚夫苦力。 宣德元年(1426年)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戈谦揭露“朝廷买办诸色物料,有司给价十不及一,况展转克减,上下糜费,至于物主所得几何,名称买办,无异白取”。[36] 总的来说,明初洪武至宣德,这一时期铺户及买办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又与当时的实物财政有很大关系;即使是采办物料,也强调在出产地收买,或许出于减轻京师铺户的采办负担的考虑。 (二)买办制度的发展时期 《明史》认为官府物料之采办在英宗时开始兴盛,成化以来“天下常贡不足于用,乃责买于京师铺户”。[37]正统九年(1444年),下令“岁用果品厨料,照旧支领官钱派买,不许于存留粮内折征。又令凡遇造作等项急用物料,止于官库关用,有不敷者方许具奏,先给官价派买”。[38]这一规定,将“岁用果品厨料”限定在必须买办的范围内;同时又留下伏笔,急用物料而官库不敷,仍可以买办。 明代中央各官署岁用物料中纸的需求一直很大,时人称京师宛、大二县铺户不能按时上纳钦天监造历所用黄白榜纸、书籍纸,故景泰四年(1453年)朝廷一度停罢纸的买办。[39]成化十年(1474年)十月,针对宛、大二县铺户买办不能立即获得物料价值,而要等待很久才能领钞于内府;其买办日多,长期积累起来的物料总价越来越多,而价钞自此寝乏,[40]宪宗下令“给内帑钞三百三十一万贯有奇,偿大兴、宛平二县铺户买办物料之直”。[41]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至成化末仍有拖欠给价的事情发生。[42]成化十二年顺天府尹邢简揭露了宛、大二县及通州铺户在承担买办时,铺户先垫资,待上纳物料后再估价给钞,“虽称给与官钱,实民间出钱买纳”,铺户之贫者不得不向富家贷钞垫付料价;领钞时往往又受到内库管事人役的刁难勒索,故建议在外司府每年用所属户口、商税等项钱钞采买物料上供,若数不足,再令户部从所管仓库中拨补。但凡遇有买办,邢简建议能随时给价,以防侵欺。户部同意所奏。[43]此外,成化十二年始有诏令对北京宛、大二县及通州的铺户按十年一次,进行清理。[44] 正统至成化,铺户所承担的买办较之前几朝已经制度化了,虽然在某些时候还有回复到各地岁办物料的倾向;[45]同时买办中的种种弊端也大量出现,已有材料显示导致京城中下层铺户“无所经营,多至失所”,[46]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破坏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故此时期虽有大量游民在京师游荡,却未见大规模的城市居民的逃亡现象。 (三)当行买办向召商买办的过渡时期 弘治、正德两朝时间不长,只34年,却是当行买办向召商买办过渡的重要时期。 弘治十五年(1502年)兵部尚书刘大夏奏请裁减光禄寺岁办物料,[47]但弘治十七年(1504)闰四月间仍有官员反映“光禄寺供应猪羊等料,比旧加至数倍”,建议裁革。[48]20多天后,光禄寺卿艾璞对此辩称:“本寺磨户多投充酒醋者等户,避重就轻。先年虽经清查,旋复废格,以致数少,贻累铺行,乞遂一清查,应当前役为便”,孝宗同意其请求。[49]正德朝光禄寺买办中的弊端依旧:“近者供应大繁,自正德七年十二月至八年正月,两月之间牲果等价费至二万一千五百余两,遇有缺乏,多于铺行赊贷,又不得以时给直,役重累深”,虽然皇帝下令光禄寺撙节用度,但仍不能杜绝铺户因此而逃亡。[50] 这一时期买办的特点有:铺户出银代役,官府收到铺行银后召商买办以及随之出现的铺行编审。 弘治十五年之前,因通州距京路途遥远,铺行赴京买办不便,科道官奏请将通州铺行分为三等九则,出银代役。弘治十五年通州张家湾铺户蒋松建议,经巡抚同意,依照门面房屋间架,将通州铺户分为四等出银代役。依给事中汪应轸所言,从正德四年(1509年)编审上溯十年,即上一次铺行编审应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51] 自正德四年始,京师各行按照资产多少,不分军民人等,编为三等九则,编作牌甲——服役的官府的册籍。铺行编审时,科道官、顺天府佐贰官、宛、大二县委官及五城兵马司参与其事。此处所称“牌甲”,印证其应与坊厢—牌—铺的制度有关;具体而言,铺户的清审所编牌甲文册即为火夫坐铺之役的清审所编牌甲册籍。[52] 万历初吏科给事中郑秉厚回顾铺户纳银代役的原因时称“后因行户赔貱不资,苦不堪命,乃议九则征银,官司召商买办。此盖征其银,不复用其力,法之变而通者也”。[53]在他看来,铺户的当行买办转变到召商买办,是当行买办时铺户的“赔貱不资”所导致的制度变革。 由铺户纳银代役,自然就导致买办服役形式上的变化,即召商买办出现:“(正德)二年闰正月己巳,户部主事张文锦往顺天府招商纳草,众商拥门争入,有蹂贱死者,为校尉所发,下镇抚司考问,坐文锦不能预为处置,令褫职为民。”[54]“(正德)八年,召商买纳粮草,量减草场租税。”[55]但大规模的粮草召商买办要到嘉靖八年(1529年)才出现。[56] (四)买办的鼎盛时期与佥商买办的出现 《明史》称“采造之事,累超侈俭不同。大约糜于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57]可见,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是买办的鼎盛时期。 《钦定续文献通考》在回顾明朝的买办时总结道:“自岁办改为采办,不免加派,累及铺户。然嘉靖末年岁用止十七万两,隆庆时裁为十五万两,万历初年,减至十三四万,中年渐增几三十万两,而铺户之累滋甚。时中官进纳索贿,名铺垫钱,费不赀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佥京师富户为商,令下,被佥者如赴死,重贿营免,官司密钩,若缉奸盗。至天启时而商累益重,乃有不得一钱者矣。”[58]据此可知嘉、万时期是明代买办最盛时期,因为中官的索要铺垫钱而使得铺户赔累不堪,不得不逃亡,便有官府强制性地“佥富户为商”的事情发生。 嘉靖初的一些物料买办如草料、柴炭等已经成为商人的“专利”,包括坐贾与行商都可以应召买办,但户部收到折银后,能否成功“召商”主要取决于价格高低。京师草场的买办是有利可图的,如景泰五年(1454年),“户部以各场急缺草,奏准召商纳草,然所定价少,全无纳者”,最后不得已而“增召商纳草价”;[59]又正德二年(1507年)户部主事张文锦往顺天府召商纳草,“众商拥门争入,有蹂践死者”。[60]而嘉靖八年(1529年)秋天却出现了“京师谷价翔贵,召商无应者”的情形。[61]为了及时得到所需物料,有关部门便只能强迫商人买纳。于是“召买”演变为“佥商”。到嘉靖后期,在京各仓场纳草铺商,因“给价不敷,亏累为甚”,[62]“率多逃窜,不得已审编铺户”,即粮草买办中出现佥商买办。 召商买办按照铺户等则征银在官,则涉及铺行编审。在嘉靖朝初期,关于铺户的编审,顺天府府尹万镗建议仍如正德四年例——十年一清——来进行。[63]但该建议应该没有得到采纳,故嘉靖二年(1523年)又有编审铺户的请求:“(嘉靖二年四月)顺天府各行铺户自清理后,已过十年之期,应合取勘查编……该科及咨都察院照例行委给事中、御史各一员,督同顺天府佐贰官,并通行宛、大二县及五城兵马指挥司,将各行铺户,查照节年事例,无分军民官舍之家逐一挨门查出,不拘有无免帖,俱令当行买办。其行户等第仍照正德四年题准事例,分为上中下三等,编作牌甲,协力奏办。中间若系正德年间投托滥免,今已革退例该应役者,亦就逐一查出,与见在行户均编,一体当行……事完将清理过铺户及审编过等第,造册奏缴,青册送部查考等因,准此。”[64]这里所提到的“牌甲(册籍)”,就是沈榜在《宛署杂记》中提到的“以所业所货注之籍”的“籍”。此种册籍的编订是在铺行清审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次编审,将“中间有父子兄弟各开铺面者并当一户,及将通州铺户再行查审,住居偏僻、家业消乏及老疾逃故者革免开除,其相应当行人户分别为上中下三等则,编定牌甲”,最终编审结果是:大兴县段子等行铺户黄叙等14939户,宛平县牛羊等铺户林政等7733户,通州布绢等行铺户沈贯等2495户。[65]此时的铺行清审与编定册籍工作中,科道官(给事中和御史)、顺天府、宛、大二县、五城兵马司共同参与,依照铺户资产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则,按审行时所编定的册籍佥派相应铺行的铺户买办。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给事中赵格议将在京宛、大二县铺商分为三等九则,上上、上中二则免征银,听有司轮次佥差,领价供办;其余七则令其照户出银,上下户七钱,以下每则各递减一钱,以代力差。[66]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嘉靖四十五年四月,朝廷命有司清理京师铺行,引发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锦衣卫是否应该与其他铺户一体当差,即锦衣卫的优免及逃役问题。结果是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的意见占上风,铺户九则都应征银免役;免行银由兵马司征收,解户部转顺天府待用,两县官府再召商买办;通州铺行等银协济京师;锦衣卫铺户不属两县管理,而归各卫官管理,征银送顺天府。[67] 嘉靖末北京城中的铺户逃亡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是编审铺户的一个动机——控制铺户,为官府负担徭役。在铺户交纳免役银后,因为买办中的众多弊病,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铺户应召为官府买办物料,故在召商买办取代当行买办不久,就有官府强制性佥派铺户买办之现象出现。据万历七年(1579年)给事中郑秉厚所奏,自嘉靖四十五年始,北京铺户分为三等九则,开始征银代役。免役银交顺天府后,宛、大二县负责召商买办,这里的“商”,本意可为外地商人,也可为在京铺户,前提是彼此情愿;“不得定以铺行之名,以致重累”表明实际情况是仍主要靠佥派京师铺户买办物料,“若今之买物,仍责铺户领价,则其赔铺之苦,犹夫故也,征银又何名哉”。[68]故召商买办有名无实,“佥商买办”出现。 “佥”同“签”字,意谓抽签。所谓佥商买办,应是通过抽签方式来决定哪些人负担买办之役。买办发展到佥商买办阶段时,“商”即铺商;被佥报为铺商所依据的是资产丰裕,并非一定从事商业。佥商买办与当行买办、召商买办不同,它没有法律上应限定负担买办的铺户的范围。当行买办自然是在京师占籍、纳入北京坊厢体制下的京师居民;召商买办下的交纳免行银的铺户也如此,只不过召商买办下具体应召买办的铺户可能不限于京师居民,因为负担买办的徭役是有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而不像当行买办中的铺户要自备工食与脚力费用。因此,佥商买办有可能派及京师外的铺户。前引材料中,郑秉厚认为北京铺户既纳免役银,而又用其力的做法不妥,[69]据此可以判断:佥商买办之初,被强制性负担买办者仍限于京师铺户,直到明末才有材料显示负担买办的铺商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京师宛、大二县居民之外,累及流寓商贾。 万历七年(1579年),因给事中郑秉厚的奏请,在南京铺行五年一审实行四年后,朝廷明确北京铺行也实行五年一编审。[70]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1522-1620年)近百年时间是明代历史上急剧变化的时期,既是买办发展史上的高峰,同时也是对明初所建立的铺行制度破坏最大的阶段。综观这三朝的铺户买办可以发现:召商买办取代当行买办后,不久就出现佥商买办——在交纳免役银后京师铺户仍被佥充负担买办。召商买办与佥商买办在明后期几乎并行不悖,对于京师铺户而言,行银成为京师铺户的新增的经济负担;而对于宛、大二县来说,行银则成为地方财政的重大收入来源。[71] (五)明末危机下佥商买办的盛行与铺行制度的瓦解 天启至崇祯的20余年是明朝各类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佥商买办呈现新的特点。 首先,在京仓场粮草买办任务繁重,无不凸显明末战事频仍的时代特点。其次,相比前代买办出现了新的变化:佥商买办之初,注籍于京师坊厢—牌—铺体制之下的铺户成为佥派的重点对象,明末则扩及无货可居的殷实市民。崇祯元年(1628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黄忠烨鉴于“富商巨贾,乃一经佥报,遂以流寓为辞,而土著穷民、伶仃下户,偏受佥报之苦累”的情况,建议佥报流商,因不合旧制,未得批准。但实际情况是已经佥及流寓,才有崇祯二年思宗下旨豁免流寓的商役。不仅如此,崇祯四年十二月巡青科院复都御使傅宗龙称,明代原有“内商不外佥”之例,但明末“辇下不足,而浸及于附近之州县”,通州、良乡、昌平、固安、东安、漷县、武清等州县皆有人被佥为商,并辩称“佥商及外州县,非自今日始也”。[72]第三,在明末的佥商买办中的承担者完全可以不是商人。崇祯四年曾有一案例:家住阜财坊的中都留守司署正留守宋嘉宾的年方四岁的弟弟宋二被佥充铺商,家中用事之人央求其家住金城坊的同名族叔宋二代役,一应钱粮均由阜财坊的宋二供应。该案例中侄宋二才四岁,不可能亲身服役。可见佥商买办中的商是“商役”,与其职业、年龄无关,只要家资稍殷,即可被佥报为商。从铺户到铺商名称的变化反映出明代买办制度的变迁。第四,因为佥商不过是强迫被佥者替官府垫付买办的价银,故官府将经纪立为官牙,代官府收购粮草,故明末开始实施官买法。如崇祯五年,“顺天府五城、宛、大二县居民翟谦等,奏称佥商苦累畿民,乞敕各衙门设法变通,务祈必免佥商之令,必行官买之法”,户部重提崇祯二年所拟官买办法,崇祯皇帝遂令“自五年秋月为始,着通行官买”,[73]“自是永除其例,民困大苏,富民始得安枕而卧”。[74] (六)关于明代北京铺户买办的小结 纵观有明一代的北京铺户买办,我们可以发现:北京的铺行一开始就是在官府强制性的编派下建立的,承继了宋代团行的特质——官府强制性佥派服役的组织。明代北京铺户的买办,无论是买办负担的轮派还是免役银的征收,都依赖于铺户之等则,所以铺行编审也是官府管理铺户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考虑到城市铺户的资产情况编为不同等级,从而承担轻重不同的徭役,或将没有入籍京师的各色人等纳入坊厢体制下,编入不同的铺行中。嘉靖以后两京的审行是在科道官、顺天府或应天府委官、宛大二县或上江二县派员等共同参与下进行的,事后造册查验。[75] 明朝中叶以前,召商买办并没有成为铺户的经常性的、普遍的、大规模的徭役。明太祖立国所确立的财政体制,建立在实物主义基础之上。皇室和官府需要的物品,主要依靠贡赋途径获取,即使少部分需要通过市场采购,也是由官府直接向商人或生产者“和买”,无需烦扰铺户或商人。但到永乐朝,内府和中央各衙门的物料需求大为增加,于是出现了强令京师铺户为其“买办”物品的现象,这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北京铺户的“买办”的开始。毫无疑问,因为铺户为官府办纳物料时自行负担脚价等人力、物力费用,且不得拒绝,故明确成为京师居民的一项徭役负担。 从当行买办到召商买办,除了顺应全国性的徭役折银化的趋势外,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⑤官府在收到折色后召商买办,召买本应是政府与商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但由于存在估价偏低、拖欠价款等弊端,商人不但难以从中谋利,还经常蒙受重大损失,导致铺商不愿应召买办。不得已,官府在征收免行银之后,依恃国家权力,仍将买办之役强加于铺户身上,强迫商人买纳物料,以致铺户不但未能从徭役中解脱出来,反而在交纳免役银之外,又成为召买的主要承担者,可谓役上加税。 嘉万以来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京城体现在城市经济的凋敝,铺户为躲避买办之役,逃离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铺行制也随之受到破坏。随着明末国家财政日益捉襟见肘,佥报铺商买办不再是为了其服役,更主要的是要被佥报的铺商垫资采购国家所需物料,尤其是军需粮草。崇祯朝经官员们一再请求,朝廷同意停罢“佥商”而改行官买,铺行制度走向了瓦解。 可见,铺户作为明代北京城市居民的主体,必须将其与王朝对城市居民的管理体制——坊铺制和铺行之役——联系起来,方可完整理解其内涵,即铺户是城市坊厢牌铺体制下的居民承担为官府采购物料时的专门称谓。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铺户”等同于城市中开张店铺的工商业者,因为铺户制度的本质是官府控制城市劳动力和财物的制度。只有清楚了解这个事实,我们才能理解铺户的赋税负担不只是商人所承担的商税,同时徭役中的买办也并非专门针对商人。要成为生活在北京坊厢体制下的铺户,户籍登记是前提,而定居在京城并有一定产业是入籍京师的关键。在史籍中很多地方都有有关铺户的记载,只有结合具体的材料,并在具体的时空下讨论,我们方能对明代城市的铺户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城市赋役制度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认识。 ①如彭雨新:《明清时期的铺户作坊和资本主义萌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5-219页;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9-449页;傅筑夫:《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387-492页;唐文基:《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赵毅:《铺户、商役和明代城市经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②详情参见余清良:《明代“乡”、“区”、“坊”、“厢”、“隅”含义考析——以福建地区为例》,《明史研究》第11辑,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③笔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参见胡海峰:《明代北京铺户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高寿仙也考察过明代买办历时性变化,参见高寿仙:《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④高寿仙认为是军户的优免杂役权利成为其拒绝买办的理由,参见高寿仙:《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⑤这种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首都的地位以及16世纪国内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参见吴承明:《16至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