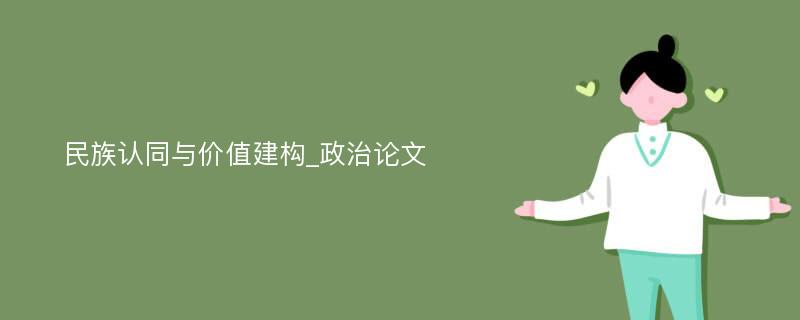
民族认同与价值观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世纪,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独立战争,新兴民族国家在世界各大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入21世纪,民族主义的势头不仅没有消减,反而以更为强劲的姿态挺立时代潮头。21世纪迄今为止的重大国际性事件,从伊拉克战争、“911”事件、阿拉伯之春、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外交争端、缅甸民主化运动,到目的乌克兰危机,都可从中发现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 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体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在一个国度里,族体的疆界不得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开”,①根据这一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致力于谋求政治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又需要以建构成熟稳定的民族认同为前提。事实上,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现实的政治运动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式成型之时,它就是以民族认同作为思想基础和情感归属的。21世纪民族主义浪潮的复兴和进一步发展,把如何理解和对待民族认同的问题再一次推上了时代前台。 自民族认同作为一个概念于18世纪启蒙运用时期形成以来,它就不是一个单一而稳定的封闭体系。“‘民族认同’始终是被每一代人重新解释和重新塑造的”,②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民族认同新的内涵。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和世界秩序,两次作为战后新秩序之主要缔造者的美国,从自身的立国经验和谋求全球霸权的现实利益诉求出发,通过操纵联合国的表决权,在世界各地大力推销其“民族自决”主张,声称: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在没有外部压迫或干扰的情况下,人民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③这一主张大大强化了民族认同中的政治诉求,并集中表现为追求建立本民族独立国家的强烈意志。在民族自决原则的主导下,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在整个20世纪风起云涌,解放了很多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并永久性地终结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制度,使英、法沦为听命于美国的二流国家,重构了世界秩序;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浪潮又大大强化了全球范围内的不稳定因素,制造了诸多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和地区关系的紧张。进入21世纪,民族认同与民族自决之间的关联被进一步内化和强化,并更多地表现出其副作用和危害性,不仅危及到一些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使有的主权国家爆发内战并长久陷入分裂状态。但美国此时已作茧自缚,不仅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控制其负面影响,而且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行动的受害者。理论和现实的发展都需要重新建构民族认同的当代形态,强化民族认同的积极因素、克服其消极因素,引导民族认同向促进自由、稳定、和平、和谐的方向发展。 当代著名民族理论家安东尼·D.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包括“共同的神话和记忆,有共同的大众公共文化,有既定的祖国,具有经济统一性,所有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力和义务”,④其中既包括了一个民族对内的自强与整合,又包括了对外的诉求与争取。建构民族认同的当代形态,就是一个使上述基本特征具体化的过程,所以,需要着重解决民族认同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即“对内应当认同什么”和“对外应当认同什么”两大基本问题。 一、民族认同的内涵:对内应当认同什么 从原初意义上来讲,民族是血统与文化的共同体。⑤民族认同是在血统与文化的共性及其相互强化中形成的,相同的血统和共有的文化构成了传统意义上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但是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两个基本要素的构成及作用今天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首先,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徙极大地改变了民族作为血统共同体的稳定性:一方面,有同一血统关系的人们居住得越来越分散,而且居住地变得不再固定,导致人们在精神上、情感上的联系日趋松懈和疏远;另一方面,特定民族个体成员的择偶范围又得到了极大的拓宽,本民族原先得以稳定传承的血统谱系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性因素,“共有的血统关系”对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被不断地稀释,尤其是少数民族族群中的青年一代,他(她)们已经很少从血统的意义上来体认和表达对本民族的归属感、责任感,也不认为自己在婚姻选择中有责任去保护本民族血统的纯正性。 与此同时,民族认同中文化的因素及其作用却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序幕即将开启之际,有为数不少的各界人士曾预测说,经济活动的全球一体化,将导致文化的差异性在世界范围内被抹平。但事实上,自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晚期成为现实以来,文化的差异性不仅没有被消解,反倒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首先,在全球性的经济交往及利益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在实现了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之后,商品在文化含量上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往往是消费者在货比三家后,最终决定购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保留并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成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有效手段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非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内的壁垒,而且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⑥全球性的经济合作与竞争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的,国家为了强化自身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不仅日益强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且充分意识到文化对经济行为的渗透和影响作用,加强了对国内文化活动的控制,并且在国际上以本国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自居,通过以各种方式展示及渲染本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2014年初发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尓巴耶夫提议为国家改名事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解读为:国家为加强经济竞争力而在不断强化本民族的文化差异性。 正是由于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差异性更多地以民族或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获得呈现,民族认同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来体认和接纳自己身上的“民族性”,并将文化的差异性作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基本标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在他们对民族认同的理解中加大了文化因素的分量。例如,美国学者迈尔威利·斯徒沃德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⑦安德森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分子对其共有文化在心理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依恋”;⑧弗里德曼强调“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关键意义所在”。⑨文化因素在民族认同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在相当程度上,现代意义的民族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来建立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民族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⑩因此,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更应当注重通过文化建设来巩固民族认同。 文化因素在现代民族认同建构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上升,使得各民族对自身文化差异性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首先体现为对本民族语言的抢救和再造,另外还广泛表现在对民族文化典籍的发掘和修缮、对民族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过程当中,经由这些工作,本民族的内聚力因为文化的纽带功能而得以强化;而另一方面,原先不甚明显的民族之间的差别也可能由于文化异质性的彰显而拉大、加深,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松懈族际认同的巨大离心力,这种现象如果出现在两个民族国家之间,则会埋下外交关系失和甚至国际关系紧张的隐患。 二、民族认同的外延:对外应当认同什么 我们置身于一个开放时代,对于每个民族来说,民族认同都不可能仅仅是本民族内部的事情,而必然会涉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共融。并且,本民族对于自身的认同感能否稳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能否与其他民族之间建立起的良性互动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获得安全、承认、尊重。因此,民族认同的当代建构既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外化的过程,在后者意义上,势必要求解决“对外应当认同什么”的问题。 (一)将对主权国家的政治认同置于认同结构体系中的最高层次 现代意义的民族认同在欧洲萌芽之际,就与建立国家的政治诉求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民族认同的问题必然性地关联着国家认同的问题。在民族认同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过程中,政治诉求的分量及重要性愈益彰显,并且更为集中地指向建立和维护民族国家,因此,在当今世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并构成了在民族认同的外延界定中不容回避的首要问题。 在18、19世纪,第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催生的都是单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在最初意义上指的是由单一民族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但时至今日,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目前世界上单一的民族国家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极少数,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已经日薄西山。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等同关系趋于消失的情况下,民族认同如果主要表现为对单一民族国家的认同,或者是脱离目前的政治共同体而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诉求,就会导致认同危机,遭到国家强制力量的遏制和打击,此种意义上的民族认同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民族认同,成为了地区和区域冲突、国家政权不稳、世界形势动荡的重要原因。反之,所谓积极的民族认同,就是要超越本民族共同体狭隘的文化与政治边界,表达出对多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政治认同,并自觉将这种认同置于认同体系的最高层次,集中体现为本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二)强化正向族际交往态度,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国家建构(nation-construction)的问题,就实际实施情况来看,国家建构通常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在前者意义上,主要是建立维护多民族统一的制度体系,而在后者意义上,则主要是建构一种“国家民族”(即“国族”)意识,将不同族群的民族认同融为一个整体。当前,“国族”还是一个尚存争议的概念,而产生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存在疑虑,认为在国族意识的建构中,会出现主体民族将自己的文化形态、观念系统借由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加给各个非主体民族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导致非主体民族强烈的排斥情绪,不仅无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而且还会强化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背离倾向。例如,前南斯拉夫在铁托时代,曾通过政治强制性力量在广大国民心目中培植起了后天的“南斯拉夫人”即“国族”观念,“大家都只说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说是哪个共和国的人”,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南共长期的政治教育抵不过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11)南斯拉夫的国族建构之所以失败,并且最终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南斯拉夫的解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南斯拉夫人”这一观念的形成,是以各非主体民族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向主体民族交出自己的文化独立性、淡化和模糊对自身的民族认同为代价的。所以,虽然国族的概念在政治意义上看似被培植起来了,但前南斯拉夫内部民族之间的裂痕却不仅没有得到愈合,反而在一种引而不发的压抑状态下被不断地发酵、扩大,并最终以反国家、反政府的极端民族主义形态骤然爆发。即便在通过实施“熔炉”政策而较好地解决了民族认同问题的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仍旧根深蒂固,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只是在形式上保留了印第安人不相连贯的部分居留地,但却在文化上推行干预和同化政策,对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贡献缺乏尊重和保护,使印第安人整体性的文化特征不断消失、政治地位长期失落,导致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被排斥感,并由此生发出对国家和政府的不满和激愤情绪。长期以来,印第安人的反抗政府政策、要求索回土地的维权运动始终没有平息,一些上层人士特别强调恢复自己的文化,他们通过开办学校,举办传统节日等方式进行着努力,但为了赢回自己的生存空间,印第安人还要走过漫漫长路。(12) 上述例证表明:国族意识的培育是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建构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把主体民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简单地转化为文化上的主导权甚至于垄断权,而是应当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性、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不同民族以平等的政治权力,通过建构多元和谐的民族关系而形成各民族对于国家的信赖感、尊重感和归属感,在此过程中逐步凝练造就国族意识,涵养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三、以价值观建设塑造积极的民族认同 在民族认同的时代变迁中,通过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考量,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因素——文化的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当代走向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文化认同构成了民族认同的前提和基础。(13)因此,必须充分重视文化的因素,建构与积极意义上的民族认同相适应的文化认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尤其是民族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在本质上更是取决于价值观的状况。建构具有强大适应能力和整合能力的文化认同,在民族主义的时代大潮中维护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亟须我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重视和推进价值观的建设。 (一)有效的认同教育是价值观建设的基础 通过价值观建设塑造积极的民族认同,教育是基础,应当强化价值观教育作为一种认同教育的重要特征,价值观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认同教育。(14)虽然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但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却很重要,如果简单地将价值观教育作为一种政治需要而进行强制性的灌输,就很容易造成教育对象的反感和排斥,使目的和手段背道而驰。在教育心理学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对价值观教育的实施是非常注重方法和技巧的。例如,英国高校将价值观教育与其闻名世界的“绅士教育”巧妙地熔为一炉,使教育对象在追求个人成功、“成为绅士”的过程中也成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拥护者;美国高校通过政治、历史、文化、法律等领域广泛的课程设置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把高尚的道德色彩赋予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美国国家价值观,从情感上打动受教育者;另一方面却通过扭曲、夸张、变形的方式极度贬抑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令人心生反感和排斥,通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正反对比方式,成功地从意识形态意义上实施了对教育对象的价值观塑造。 一个民族尤其是多民族共同体最深刻的认同感来自于共同珍视的文化传统。要强化价值观教育作为认同教育的特征,就应当把优秀文化传统作为价值观教育的活水源头。事实上,前述英、美成功实施价值观教育的方法,正是在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英国的“乡绅文化”具有调和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矛盾的特征,构成了英国资本主义模式的文化基础;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反压迫、反殖民的自由精神深植于美利坚民族的血脉当中,构成了美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从19世纪开始,美国就以全世界“自由的守望塔”自居。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表述就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与重和合可谓一脉相承。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内蕴,并从中提炼出能引发受教育者普遍情感共鸣和理性共识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就能够有效克服单纯意识形态说教的“假大空”色彩。当前,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价值观教育中呈现出越来越多富于时代感的积极因素。亦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15) (二)社会精英要成为价值观建设的引领者和示范者 民主化和精英化是现代社会并行不悖的两个特征。一方面,广大民众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日益增强,而另一方面,对社会话语体系的把控权越来越集中在社会精英手中。精英阶层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其中,政治精英由于控制国家机器,对社会资源具有最强的整合能力,也最能够主导整个社会的话语权。价值观建设由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非常需要政治精英的引领与示范。这首先表现在:政治精英要积极引导和组织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宣传,并通过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构来保障核心价值观在国家上下的推广。而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精英尤其是上层政治精英要以具体言行说话,塑造并积极展示自身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与模范践行者的形象,获得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可与接纳。现代社会,政治精英往往是公众瞩目的焦点,也是各种媒体追逐和监督的重要对象,在众目睽睽所形成的放大效应当中,政治精英一旦对其倡导的价值观表现出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致,立刻就会导致社会公众对这种价值观之合理性、正当性的强烈质疑,并可能最终导致价值观建设工作的无所建树,甚至走向反面。事实上,在当今百姓心目中,政府官员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当然的践行者、垂范者,相当一部分民众之所以对核心价值观缺乏认同感和践行的驱动力,是由于他们对政府官员的形象、作为的不认可。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从重塑政治精英的理想信念入手,切实转变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革新官员形象、革除官场积弊。在此过程中,文化精英和企业精英应协同政治精英,在价值观建设中共同发挥引领者和示范者的作用。 (三)营造有利于价值观践行的良好社会氛围 价值观建设的落脚点在于践行。要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自觉成为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离不开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 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度进行,社会风气中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色彩,不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因此首先要通过积极有效、讲求宣传艺术的舆论引导,逐步扭转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树立有序、和谐、长远的个人与社会发展理念,使目前由于过度逐利而导致的喧哗、浮躁的社会氛围一步步沉淀下来。其次,要着力改变各种社会组织“泛行政化”及由此导致的对社会事务不作为的现状。放松政府的管控和束缚,让社会组织相对自洽、比较充分地发挥其服务社会、造福民间、齐聚民心的作用。通过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增强社会运行的平稳性、有序性,并以此增强人民的主体责任感、相互信赖感及归属感,逐步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心态和社会氛围,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践行。再次,针对目前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怀疑心理,如:“老人摔倒该不该扶”、“好人会不会有好报”等,通过各种社会渠道大胆地、有针对性地塑造社会心理、引导社会舆论,使民众形成正确、积极的是非判断标准并敢于大胆实践。 四、结语 以史为鉴乃后事之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尤其是价值观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值得反思的教训。苏联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就出现了意识形态阵地松动的信号。赫鲁晓夫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受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邀访问美国后,就多次在不同场合对美国的自由精神及生活方式赞赏有加,无意中充当了美国价值观的代言人和贩卖者。一方面,苏联开动各种宣传工具向民众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另一方面,上自最高领袖的统治阶层却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越来越亲西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深度割裂,使广大民众对苏共的虚假意识形态日趋反感,社会价值取向呈现出迷失状态。以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反共老手”,正是看准了前苏联国家安全中的这个巨大漏洞,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发动反共攻势,借助舆论渗透、以各类基金项目培养亲西方的政界、学界精英等方式,从内部瓦解了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进而再利用经济问题、民族问题等最终摧垮苏联。前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也有近似之处。对此,基辛格曾评价说,共产主义从来未能把它对政府和媒体的掌握,转化成使得民众接纳它。(16)这句话值得我们在批判的意义上深刻反思。准确把握价值观建设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价值观建设需要切实有效的政策方略,惟此,方能塑造积极的民族认同,维护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家庭的持续稳定与繁荣。 注释: ①参见[英]埃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er)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转引自[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②陈茂荣:《“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研究述评》,《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4期。 ③参见维基百科,“民族自决”,http://zh.wikipedia.org/。 ④[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⑤[英]斯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⑥[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序言。 ⑦[美]迈尔威利·斯徒沃德:《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周伟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93页。 ⑧[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⑨[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0页。 ⑩参见栗志刚《民族认同的精神文化内涵》,《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 (11)张维为:《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12)参见舒泥《美国印第安人一瞥》,《中国民族》2012年第4期。 (13)参见万明纲等《近年来国内民族认同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8期。 (14)蒋红:《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云南日报》2014年3月14日。 (15)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5日。 (16)[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52页。标签:政治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价值观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