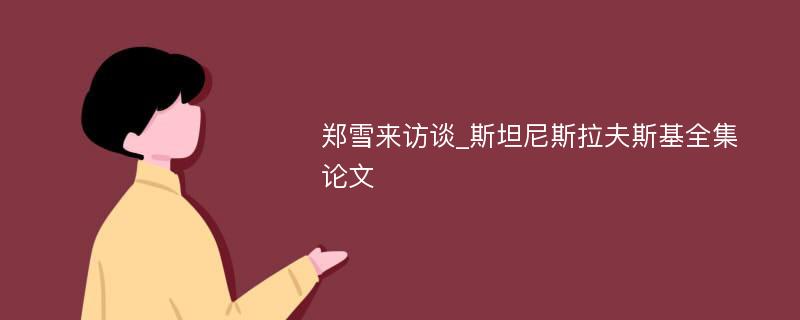
郑雪来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谈录论文,郑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2009年3月24日—4月16日 地点:北京郑雪来家中
采访:陈墨 文字整理:赵晶
受访者简历:
郑雪来,1925年生,福建长乐人。暨南大学外文系肄业。“二战”期间在印缅战区美军第475步兵团任翻译官,参加对日作战,后从事英文教学、编译工作。建国后入电影界,从事电影理论及“斯坦尼”体系的翻译、编辑及出版工作。“文革”后,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曾主持外国文艺研究所工作,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世界电影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发表有《电影美学问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艺术学卷)等论著、译著、编著共三个余部。
翻译编辑出版
陈: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您还有什么印象吗?
郑:10月1日那天,我还在浙江省绍兴中学教书。当时是学校通知的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虽然不是听广播,但我仍然很兴奋、很激动。中国人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终于建立自己的新中国了。
陈:1951年初,您是因为什么机缘进入电影界的?
郑:我还是比较想自己翻译东西,听说表演艺术研究所,就是后来的电影学院招人我就去了。当时所长叫白大方,他刚好需要俄文翻译人员,介绍一些苏联的材料。好像当时也经过考试,但我很快就被聘用了。我还参加过表演艺术研究所1951年的开学典礼,当时,袁牧之和我并排坐在主席台上。过了没多久,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程季华听说我做过一些工作,而且俄文、英文、法文都懂得一些,他就把我调去了,那是在1951年八九月间。
陈:1951年,您被抽调到电影局艺委会研究室编译组工作,当时从事电影翻译工作的共有多少人?您是主修英语的,为何会被分配去做俄语,从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译介?
郑:那个时候我刚到编译组,还没有几个人,有徐谷明、戴彭荫、富澜、沈善,邵牧君夫妇是后来才到的。语种包括俄语、日语、英语,但主要是以俄语为主。我的第一外语是英语,也做俄语翻译,就是因为建国初期,我们各个战线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主要介绍苏联各方面的经验,包括电影经验,所以,没有让我去搞英文翻译。后来有三十多个人,各种语种都有了。英文和日文计算内部稿费的时候要打20%的折扣,就是因为懂英文、日文的人太多,懂俄文的人少,这个做法现在看来很荒唐。
陈:您翻译的第一篇电影文章是尤列涅夫的《评〈幸福的生活〉》,翻译的选择权是在译者,还是在刊物的编辑?刊物的选题如何决定?为选题而争论的情况多吗?
郑:我翻译的《评〈幸福的生活〉》1952年初在《电影艺术丛刊》第一期上发表,作者是苏联著名电影评论家尤列涅夫,这部影片把苏联社会矛盾描绘成“好与更好的斗争”,文章把它吹得天花乱坠。直到1953年以后,奥维奇金写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写的《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才开始揭露苏联经济的很多矛盾。我当时也不知道,只是照翻不误。1987年,我在莫斯科电影节当评委的时候遇见了尤列涅夫还提起这段往事。那时候除了订苏联刊物,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刊物,我们有些搞资料的人就制作目录索引,由程季华、丽尼根据文章的内容和作者情况来圈定译哪一篇文章。重要的理论文章都是他们根据索引来确定的,而小文章、报道之类的就由编辑部定。关于“斯坦尼”专栏的文章由我来选。至于选题,《电影艺术译丛》时代不是我管,后来从《国际电影》开始,选题我说了算。程季华是总编辑,忙于写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很多事情,他不看稿子,也没什么争论。他召集掌握材料的同志提供一些稿子,最后由我来决定选题。当时《电影艺术译丛》上所有的稿子都是由我们内部人来翻译,这样才能赶时间,保证质量。
陈:195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成立,电影艺术编译社并入出版社改为外国电影编辑室,您继续担任丛书编辑组长,策划了《苏联电影剧本选集》,组织翻译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三大师的文集,以及其他电影理论专题论文集等,这些选题计划是否都如期完成了?1962年初,您曾提出一个总字数达到两千万字的外国电影史论选题计划,其中包括哪些重要选题构想?
郑:当时我兼任业务秘书策划选题。《苏联电影剧本选集》连续编了三本,把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剧本都收录其中。三大师的选题也是我策划于60年代初出版的。1962年,我担任外编室业务副主任的时候,搞了一个很大的选题计划,一个是史,一个是论。史包括通史和国别史。我做的选题中通史方面主要有萨杜尔的《电影通史》和《世界电影史》。此外还有英国保罗·罗莎写的电影史,原名叫做The Film Till Now,和波兰电影史家托埃普里兹用波兰文写的《电影艺术史》。国别史的选题计划主要有《苏联电影史纲》、《美国电影之兴起》、《日本电影史》、《意大利电影》、《法国电影史》。论的部分很多,既有像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尤德凯维奇、罗姆等大师的著作,也有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马尔丹的《电影语言》,雷纳·克莱尔的《电影随想录》,英国曼威尔的《论电影》和苏联几本谈论技巧的书,如《电影剧作家的技巧》、《银幕的剧作》等。另外还有评传,即玛丽·西顿写的《爱森斯坦评传》和两本《卓别林评传》。这个选题我初步算一下有两千万字左右。在1962年出版社选题会议上,袁文殊、程季华和各编辑室负责人都参加了并一致通过。我当时建议大量向外约稿,我们就搞一些校编工作,有必要的写一些前言后记,而把更多时间用在研究问题上。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内部工作人员要用业余时间翻译这些书稿,比如邵牧君翻译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就是这样约的。1962-1965年这段时间,我大致估计已出版的书有一千万字左右。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二十部左右的书稿,已经校订编辑好,有一些甚至打了纸型,因为“文革”就要来了,根本不能出版。这些书包括《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美国电影之兴起》、《日本电影史》、《爱森斯坦评传》等。80年代初,中国电影出版社能一下子出那么多书,也是因为有这么多校编好的译稿。
陈:您翻译过《乡村女教师》、《舍甫琴珂》、《海之歌》等多部译作。您为何说《海之歌》是您的得意译作?为什么有人说当时翻译电影剧本算是一个“美差”?
郑:《海之歌》是杜甫仁科的遗作。1956年末,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破天荒地以头版半版的篇幅刊载了剧本的精彩片段。紧接着在1957年第一期苏联《电影艺术》上全文发表了这个剧本,并登了杜甫仁科亲自绘制的几十幅场面设计图。我看到《真理报》登这个片段以后,就深深为其中革命浪漫主义的段落所吸引。比如说,这个剧本一开篇就引用舍甫琴珂的诗句:“辽阔的德聂泊河在呼号,狂怒的风暴在咆哮,高高的柳枝吹垂拂地,波浪与群山比量高低”;以及后面引用的“这时候,苍白的月亮从乌云后面向外张望,像一叶孤舟漂泊在海洋”。整个剧本非常充满诗意。1955年我曾经翻译过《舍甫琴珂》这个诗人的电影剧本,里面好多舍甫琴珂的诗句,剧本出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约我翻《舍甫琴珂文集》,但我后来工作太忙没有答应,所以看到《海之歌》在苏联《电影艺术》登出来之后,我非常激动,也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就翻译了。那时,我常常彻夜不眠,俄文程度也相当可以了,再加上我又比较喜欢诗歌,所以整个翻译下来也不觉得累,大概用了三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就把这十万字的稿子翻译出来了。1957年《中国电影》杂志11、12月合刊《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专辑,就把我这个剧本全文登载,包括所有的场面设计图。1958年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单行本也印出来了,1959年又再版,这个剧本对电影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作为译者就收到很多读者来信,畅谈他们的读后感。这个剧本充满诗情画意,我的翻译也能准确表达杜甫仁科的风格。
关于“美差”这个事,那是当然。我开始翻译剧本的时候都是组织上的照顾,50年代初期我的家庭负担很重。程季华看到我家庭比较困难,就让我在工作时间改稿子、业余时间翻译剧本,补贴家用。剧本一般都在五六万字左右,我往往在两三个月时间就翻译出来了,稿费有二三百块钱,比两个月工资还高。有些人也想翻译剧本,因为剧本比较容易译,不像理论文章那么枯燥,叫它为“美差”也是有道理的。但是那个时候,内部人员业余翻译剧本的就是我,其他都是外稿,因为电影剧本比较容易,许多搞文学的人都能翻。
陈:请您谈谈您主编的《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丛书的策划缘起和出版过程。您开始准备出版多少册?后来为何延续下来?这套丛书的经济收益如何?
郑:1989年,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何强跟我提出要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的想法,目的是成为电影工作者案头必备参考书和电影爱好者欣赏各国影片的“电影院”,我就痛快答应了。我的选片标准是:在电影史上和当代电影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知名影片、电影史上各种思潮流派的代表作、世界级电影大师的作品、国际电影界有争议的影片,包括禁映的影片,以及一些虽非世界名片但比较受国内观众欢迎的影片。我召集研究各国电影的专家开会,由于他们对这些影片很熟悉,不到一年时间第一卷稿子就齐了,并于1991年出版。当时很多电影界的头面人物参加此书的出版讨论会,大家一致提出应该再编下去,迎接世界电影100周年。福建教育出版社与我再签合同,争取在1995年前再出版两卷。第二、三卷不光动员了国内有关研究人员,还找了一些港台、旅外电影学者,请他们写了好多条目。第二卷在1993年出版,第三卷在1995年出版。1995年,趁北京举行世界电影10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们院和出版社又组织召开了更大规模的出版座谈会。大家提出各种意见建议。有人觉得有些中国影片选得不具备代表性,有人觉得介绍一些关注社会现实的中国影片也无可厚非;也有人提出三卷本对第三世界国家介绍不够,题材范围可更宽广些;还有的作者提出选片时间只截止到1993年,而此后两年还有很多影片质量很高。最终大多数人强烈建议再出一卷。1995年,筹备第四卷,主要写入了阿拉伯电影,德国从表现主义时期到希特勒上台以前的电影,1994-1995年期间法、英、意、俄等国家的一些新出品的影片。我唯一遗憾的就是东欧、拉美国家的某些重要影片没有写入第四卷,因为我选作者的原则是必须亲眼看过这些电影,并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比较了解,但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就没有写成。
福建教育出版社除了教材赚钱以外,只有这个辞典不仅保本还赚了钱。90年代末还出了三卷本的光盘。去年清华同方、北大方正跟我签合同制作电子版,网上读者的数量也不少。特别是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把此书作为考生主要参考书,但现在几乎都买不到了。我今年3月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希望能再出精编版,把四卷压缩为两卷,把800部压缩到400部,因为根据市场调查,读者对一些小国家的影片、枯燥乏味的影片不大感兴趣。
不再编下去有两方面理由:一方面,虽然我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外电影看得很少,但是一般情况我还是了解的。首先,从世界范围来讲,电影方面没有值得注意的思潮和流派,只是某些国家有个别导演的部分影片不错。据我了解,欧洲电影普遍不景气,好多美国科幻片也只有幻想没有科学,现在奥斯卡获奖的影片也很难找到哪一部或哪几部影片可以和20世纪各个时期美国著名影片相提并论,所以没法儿编。另一方面,我岁数太大了,眼睛耳朵都不太好,好多新片情况不了解,如果有别的同志有兴趣把这个工作负担起来,那是很好的。
陈:您曾为《电影艺术词典》撰写过哪些词条?撰写这些词条与您的理论文章写作有怎样的不同?后来《电影艺术词典》出了修订版,您对其中某些词条是否有所修订?
郑:《电影艺术词典》初版我主编电影学分科,后来修订版的时候改成电影理论分科。编这个电影词典的时候,也是我给《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写大条目的时候,所以关于电影学的想法已经比较成熟了。1985年,张骏祥同志约我写“电影学”这个条目,我写了差不多有一万字。他看完之后还跟我说:“老郑,我们国内恐怕也只有你能写这样的条目。”我是把各国关于电影学的看法介绍一下,然后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我提出除传统的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三类外,还应该把电影美学、电影哲学、电影艺术学、电影社会学、电影心理学、电影符号学、电影社会心理学等等作为电影学的分科。我当时觉得“电影学”的范围应该比较广。后来我当电影学分科主编,让崔君衍也一起当分科主编,因为他对法国符号学、心理学熟悉,很多术语我就请他写。其他方面比较主要的条目就是由我来写,大概四五十条。到修订版开会的时候,富澜是主编之一,他提出《电影艺术词典》也可以叫做“电影学词典”,分科也叫“电影学”不是矛盾吗?他就主张把电影学分科改叫电影理论分科,而电影、电影艺术、电影学三大条目收编在总论中,我就同意了。后来在修订版中,我把电影学和原来词典中的方法论并在一起,作为“电影学”的内容,共一万多字,很长的一个条目。有些条目还需要做一些轻微的修改,使它比较完整,但主要还是介绍性质的,因为条目跟文章不一样,条目要客观,资料要丰富,让读者了解到各种各样的说法。
陈:您与美国俄亥俄大学的沃特曼教授共同主编了《比较艺术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请谈谈这部著作的出版过程,以及您对美国的观感。
郑:1989年,我和话剧所所长田本相去美国俄亥俄大学回访,我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俄亥俄大学签订意向书,准备两边各出十个学者合写这本书。意向书一签订,双方就动手写了。1990-1991年,沃特曼教授和海格内教授再访中国,签订具体出版协议,商定出《比较艺术的理论与方法》的中英文版。中文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英文版由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委托文化艺术出版社代印,他们出12000美元经费,相当于十万元人民币,两本书出版就都够了。1992年初,我带中国学者写的所有英文译稿到俄亥俄大学,住在沃特曼教授家,我俩交叉审稿。我审美国部分,他审中国部分。对于英文译稿翻译不完美的地方,他和海格内教授做英文文字加工。这本书最终于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代印出版,但没有把样书寄去美国。我自己花钱把样书邮寄给沃特曼和海格内教授和中方作者,我自己只留了一两本。美方对不寄样书非常不满。出版社说第二个6000美元没有收到,所以中文版就没有出。
关于美国的观感,我想说美国人情报资料工作做得非常完善,而且他们很念旧。第二次我一个人到美国之前在美国使馆办理签证,美国使馆接待人员一看我的名字,就对院外事处人员陈双说:“郑先生是我们的人啊,他在1945年在缅甸我们第475步兵团里当翻译官。不仅如此,美军总部还通过团长给他颁发西南太平洋战役纪念绶。”所以,在我办签证的时候,还要帮我把原定的两个月延期到半年内自由往返。在旧金山入美国国境,所有乘客要下飞机检查行李,结果那次我的行李免检,而且请我走外交人员通道。
关于“斯坦尼”
陈:从1951年开始,您主持翻译或改译、校订、出版了多部关于“斯坦尼”的学术文集。您与“斯坦尼”的因缘绵延数十年之久,其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
郑:我刚到“艺委会”,程季华就给我一本厚厚的《回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文集》让我挑选几篇进行翻译,因为当时已经开始办《电影艺术参考资料》,介绍苏联电影报刊中的理论和评论文章,我忙于这个工作就没有翻译这本书。1952年初,程季华又给我《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我就参照英文节译本开始翻译了。1956年,以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本书以后,开始筹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八卷集,一共500万字,程季华任命我负责翻译校订工作。第一卷《我的艺术生活》是“斯坦尼”艺术自传,有很长的前言,“斯坦尼”全集的序言对整套书也做了非常全面的评价。以前的译本翻译得不完全,缺少俄文本的好几百条注解,我们两位同事重新按照俄文本进行翻译,由我进行校订。第二卷是《演员自我修养》的第一部,前七八章是姜椿芳根据俄文翻译,曾在1939年《演剧艺术》发表过的,我做了文字加工,使其符合“斯坦尼”文风。后八九章是出版社懂俄文的同事一人一章翻译,由我进行校订。当时提倡集体攻关,但是改稿非常辛苦,因为原作者风格比较独特,他们不了解“斯坦尼”的术语和文风,翻完了我都要改。1962年第一二卷再版时,丽尼参照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做法,要写明译文主要负责人,所以分别署上郑雪来校,之前第一版是没有的。第三卷和第四卷是我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第三卷基本部分是《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另外还有“斯坦尼”的其他一些文稿,是编者有根有据整理出来的、首次发表的文章。第四卷是《演员创造角色》,两本书100万字,于1963、1964年出版。1980年初,中国电影出版社邀我继续主持第五、六卷的翻译校订工作,第五、六卷是论文讲演集,印数只有一两千册,相比第三、四卷的五万多册差得很多。第七、八卷两本都是书信集,一个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一个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加起来一百多万字,注解非常多。那已经是80年代后半期了,我负责外国文艺研究所,要到处讲学,写那么多论文,办了两个刊物,还要替好多人改稿子、校订文章,实在没有时间搞那么浩大的工程。其实,我已经组织人翻译了好几十万字,并把译稿交给出版社总编辑让他们酌情处理。但很遗憾,第七、八卷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可能也有商业方面的考虑吧。我在回忆录中说,我做了半个多世纪介绍和研究“斯坦尼”体系的工作,最后文化部授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唯一一部译著一等奖,等于是对我做过的工作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肯定。这样我也可以无愧于这位慈祥的老人了。因为我翻译斯氏体系,后来又研究斯氏体系,自己得益是很多的。一方面通过翻译,我的俄文程度逐步提高。另一方面,虽然我为翻译和研究吃了很多苦头,但一点也不后悔,毕竟除了电影理论工作外,在中国,我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翻译这么多“斯坦尼”体系的文章、写那么多研究文章的人。
外国电影
陈:您的《漫谈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向及一些理论问题》、《对现代电影美学思潮的一些看法》、《现代派与现代电影》、《当前世界电影发展趋势》等论文以及关于意、英、法、美、苏等国家电影的研究论文,不仅具有知识信息,更有理论思考。在这些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对这些文章,您现在怎样看?
郑:1978-1979年,我开始在电影学院各个系做讲座。从1980年开始,我讲课的地点包括三十几所综合性大学、艺术院校、各地影协分会、电影制片厂、话剧单位、戏曲单位,甚至一些军事单位,我粗略估计,80年代上半期做过一百多场讲学活动。这些文章有些就是我讲课的时候人家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或者是选片、参加国际电影会议,或者是带代表团到外国去、当电影节评委,都是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影后才写的论文,特别是关于英国、法国、瑞典电影。我比较系统地看到各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又通过所掌握的各种学术资料,所以我对这些国家的电影有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任何外国理论家的看法。我所谈所写的内容是对这几个国家电影看法的归纳和到世界各国去了解的最新的电影信息。在这些文章的发表过程中没有任何的阻碍,因为80年代上半期,很少有懂电影理论的人出国,更不用说像我懂得这么多种语言,看过这么多电影,刊物、出版社都欢迎之至。《中国电影时报》、《电影艺术》、《电影评介》、《电影文学》、《电影世界》都登了我很多关于外国电影的文章,一些重要的论文还收在我主编的《世界艺术与美学》、《当代外国艺术》上,可以说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虽然不记得细节,但我觉得那些看法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陈:2008年,您在《电影评介》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外看外国电影”文章。您如何能够在一年内写那么多篇文章?若您的身体还允许的话,还有多少个题目要写?
郑:从去年到今年2月,《电影评介》一共登载了我的25篇文章,总标题为“银海遐思录”。我的这些文章中,有谈一部影片的,比如《悔悟》、《猎鹿人》、《海之歌》、《生活万岁》等;也有很多文章不只谈一部影片,如联系伯格曼、戈达尔整个创作道路谈他们的作品,也有联系一些思潮来谈影片,比如我用一部影片为例谈新左派运动的兴起及衰亡,它的社会政治影响等;还有文章谈国际电影会议观感,联想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现状;还有从影片看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现象等等。我写的这些内容都是过去的一些研究对象,特别是新左派问题。因为戈达尔也可以说是新左派,我比较关注,过去写的一些文章、给《电影艺术词典》写的一些条目也涉及新左派,我的印象都比较深。我在写作前翻翻过去有关的一些东西,参考一下,但更多是用今天一些新的思路把当时没有想到的部分补充进去。
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有几个题目想写,比如,关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代表作我几乎都看过;我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比较问题也很感兴趣。另外,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后,电影方面比较有艺术价值的作品那么少?根据电影史上各个时期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电影思潮和社会思潮相联系,而新世纪能够提得上社会思潮的、值得关注的东西比较少。我还要谈国际评奖问题,因为评奖虽然对艺术价值的肯定比较准确,但是对思想政治价值的评断很不一样;还有关于新世纪电影的展望。
电影美学
陈:请谈谈您的三部重要论文集即《电影美学问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论集》、《电影学论稿》的出版过程。您曾想要写《电影理论概论》和《电影思潮概论》这两本专著, 当时的主要想法是什么?
郑:《电影美学问题》是1981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社科院文学所做几次报告的整理,内容是关于电影美学研究对象、方法论等问题及对电影美学的一些设想,198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论集》是198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1980年,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地做过关于“斯坦尼”体系的系列讲座,讲座报告加上我另外写的文章,不到20万字结集出版,销路很好,但没有再印。这本论集出版后,我还写了二十多篇有关“斯坦尼”体系的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还来不及结集。《电影学论稿》是1986年出版的。当时关于电影学我有个设想,觉得应该建立电影学学科。书中的文章就比较多,内容比较庞杂,有些不一定是关于学科建设的内容,包括电影研究各个方面的文章也都收进书中。《电影学论稿》不到50万字。我后来在《电影文学》上发的六七篇关于电影学的文章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关于电影学的长条目也都没来得及收进去,所以这是不完全的论稿。
关于《电影理论概论》和《电影思潮概论》,我的主要想法是要写专著,绝不能去搞什么“汇编”,必须有个人明确的、独到的见解,在这个领域里面别人没有说过。也可以谈别人的说法,但必须要有自己的说法。钱钟书说的“我不轻易写概论之类的东西,因为很难避免流于陈言和空话”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自己考虑得不十分成熟,应该构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见解、理论体系,这时候写专著才比较有意义。1983-1984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对当时电影创作影响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当时一方面电影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不够重视,对巴赞理论过于热衷,另一方面,很多比较年轻的导演追求一些西方的花招儿,实际上拍出来的一些影片不怎么样。他们缺乏文艺理论,电影理论方面的知识,当然更缺乏哲学、美学方面的素养,所以应该多写一些文章来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写书的事可以晚一点儿。等到1986年,我已经考虑得比较成熟,可以着手写这两本书了,结果因为任命我当所长、主编两个刊物,还搞好多项目,写书的事没能继续下去了。
陈:您在80年代初就曾在《中国电影时报》和《艺术世界》上撰文倡导电影学研究,后来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写过《电影学》词条,还发表过关于电影学的系列研究文章,您的电影学主要构想是什么?
郑:电影学这个问题,我很早就注意了。1980年我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在此以前中国没有人提过电影学这个名词,我写的这两篇短文,提出中国应该建设电影学,使得电影研究系统化的设想。此后,我就写了很多电影学的文章,并在1983年第一期高校电影学会上做了报告,提出电影学及其方法论问题。很多人研究问题多半都是采用历史主义方法,没有注意到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有两种概念,一种作为哲学思想,强调理性,后来取代非理性的存在主义;一种作为方法论,20年代苏联叫构成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普等,电影方面是爱森斯坦,苏联人称“形式学派”。作为方法论的结构主义传到匈牙利后成为布拉格学派,最后又传到法国成为法国的结构主义,比如结构语言学、语义学等。既然是一种艺术,就不能只讲内容,如何表达这个内容,形式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历史主义作为纵向分析,结构主义作为横向分析,必须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纵横交错分析一部作品才比较完整。
80年代我一直不断地在提要把电影学作为学科来论述,要建立电影学学科,代替过去的电影理论和电影史学科。1998、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艺术学为一级学科,电影学、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等属二级学科。当时沈嵩生院长作为学位委员会委员代表电影项目参加该大会。不过,电影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国际电影学术界尚有争议,只有中国、德国、苏联认同,英、美并不如此认为,法国则有自己特殊的概念。
陈:您是中国较早进行电影美学问题思考和研究的学者之一,您认为电影理论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何在?
郑:关于电影美学有一段故事。中国电影出版社在50年代出了一本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的著作,译名为《电影美学》,但本书的原名是The Theory of Film,不是“电影美学”。巴拉兹这本书是他到苏联以后于1949年写的,谈了一般的电影理论问题,很多是电影技巧问题,而并没有把电影理论作为学科来提。尽管美国有些学者把电影理论分成两大类是一种误解,是对巴赞理论的一种误读,但至少是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巴拉兹这本书还上升不到理论的层次。但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在电影界很有影响,很多人以为电影美学就是这样,而书中所谈实际上就是一般的电影理论和技巧问题。在50年代,我还谈不上研究电影,但在“文革”以后我正式研究电影问题的时候,我就感到把《电影理论》的书名翻译成《电影美学》是不妥的。我1980、1981年开始研究电影美学问题,比电影学的研究还早。那时候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办一个美学研究班,请我去做报告,我的第一篇电影美学文章就是《电影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提出电影美学跟电影理论还是不同的,电影美学应该是层次更高一些。后来,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讲座的时候进一步提出,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有三点:第一是电影作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第二是电影思维作为形象思维的特点;第三是电影有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我所说的这个电影思维的特点,后来在1984年访问法国高等电影学院,跟院长科斯特罗·敏内交谈时得到证实。他告诉我这个学院就两个系,导演系和剪辑系,招收的多半是大学毕业生,入学考试就只考命题的电影剧本,限两天内写出,用以考察考生的电影思维能力。我认为电影特性当然要研究,但不是电影美学的全部。因为电影跟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电影美学的首要问题,电影艺术必须反映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而电影要创造形象,电影的形象思维与文学、音乐、绘画等的形象思维都不一样,主要是蒙太奇思维。
标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论文; 演员自我修养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大百科全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美学论文; 电影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