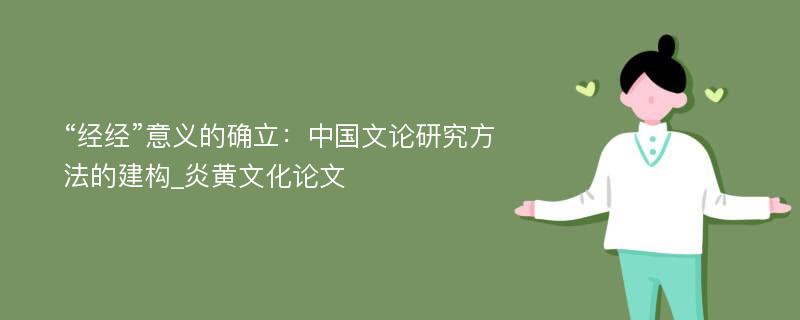
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方法论文,依经立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依经立义”首次见于王逸《楚辞章句序》:“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后来,刘勰将其简化,《文心雕龙·辨骚》云:“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前者旨在评论屈骚,后者意在辨述骚评。汉代士人曾掀起了一股研究屈骚的热潮,淮南王刘安开其端,士大夫王逸集大成。然而,在这一研究潮流中,尽管他们由于各自的生存与文化经验不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态度有褒有贬,但几乎所有人都把儒学经义作为屈骚评判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谓“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无一例外地把“依经立义”作为屈骚解读的首选方法。无论是褒扬派的刘安、司马迁、王逸,还是贬抑派的扬雄、班固,他们在看似截然不同的意见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所谓“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王充《论衡·程材》),都以经义作为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经义在他们那里都具有至高无上不可违背的权威性。究其实,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是随着汉代经学的产生与兴盛而出现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中国文化圣人孔子所删、定、著的典籍——《诗》、《书》、《礼》、《春秋》、《易》确立为法定的经典,遂出现经学。诚如朱熹所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①“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②这就分别从创作和接受两个层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圣—文”的密切关系,即“圣人”通过“文”(经)让人们懂得“道”,而人们通过对经典的阐释,在获得“道”的同时还可以依经典产生新的意义,这样便形成了中国“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因为经学的兴起,是为了适应“大一统”政治统一思想的需要,所以当时的意识形态权威对“经”有着不同以往的解释,从而形成了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从汉代经学注重对经典“本义”的发掘,到宋学提倡以“六经注我”,再到清代“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朴学,今古文之争此消彼长,直至经学衰亡。
综观自汉迄清中国两千余年的释经活动,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古今文学派释经的方法不同,但其释经的目的却无异:一是通过“释”来确立经典;二是通过“释”来彰显经义。不过,无论是确立经典还是彰显经义,其最终目的都是树立经典的权威,因为“圣言至尊,圣言中的歧义不仅关涉到生存的理解,也关涉到生存的方式;圣言失去了确定性,信仰者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依托”。③通过对经典的确立和经义的解释,人们可以获取圣人的旨意,从而有了行动的指南和方向。而这也正是中国经学“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形成的根本原因。不过,这种“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在方法论上也有其固有的缺陷。
首先,“依经立义”所依之经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所有经典,而是仅限于儒家传统的经典。换言之,经学之所以会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主要是从孔子开始,就奠定了经典文本的解读模式,即“述而不作”,“以读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普遍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④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儒家学派前后绵延两千余年,其所以能够基本上维系于一个大致相同(或相通)的思想体系之中,除去以‘宗师仲尼’为其主要旗帜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一批贯通古今的基本典籍,就是孔子所整理编纂删订的《六经》。”⑤而所依之经的局促却导致了严重后果,尤其是清代朴学主张“无征不信”、“孤证不立”、强调用证据说话,反对望文生义,这固然具有实证的科学精神;但宗儒轻子、墨守经籍的用证规则,使朴学把观察对象拘泥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导致学问道路愈走愈狭隘,最后转入歧途,渐呈偏枯之象。
其次,“依经立义”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以尊奉经典、效法古人为圭臬,以对儒家经典的整理解释为意义生成的基点,虽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人对古代经典的师承传统以及‘序’、‘传’、‘笺’、‘注’、‘正义’、‘疏正’、‘经解’等等名目繁多的注解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一大奇观,是中国文化一个极有特色的、非常重要的基本解读方式”,⑥但其唯古是崇,唯经典是崇的读解倾向,仅是一种满腹经纶的“博学”,而不是追问原因的“创新”。则这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尊经”复古保守传统。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与文论历代都存在复古与革新的斗争,且复古派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过了革新派,而革新派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第三,崇奉文化经典,主要就是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鉴和运用文化经典,但要根据现实要求借鉴和运用文化经典,又必须遵循一定的观念,运用一定的方法理解和解释文化经典,从中阐发出新的思想理论。诚如成中英先生所说:“‘阐释’是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作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它可以面对历史、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作出陈述与发言,表现阐释者心灵的创造力,并启发他人的想象力,体会新义,此即为理解。事实上,阐释自身即可被看为宇宙不息创造的实现。”⑦作为一种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就是一种阐释。但是这种阐释方式发展到清代朴学,由于其考据繁复,规矩森严,使得学问不易普及,丢失了广泛的民间基础,最终导致了经学的衰落。
近现代以来,随着经学的衰落,关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渐渐只在学术的范围内展开,但是“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并未随着经学在现当代的消失而消失,它仍然有着生命与活力,是完全可以进行现代转换,并进而发扬光大的。我们认为,要让“依经立义”这一意义生成方式发挥现代方法论作用,就应该立足于当代,并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寻求发展动力。所谓纵向寻求,就是内求传统经典,在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层面,重新解读儒道释文化元典和历代文论经典,重新阐释中国文化和文论经典的范畴术语和理论命题,进而揭示其当代价值。而横向寻求,则是外求他国理论,通过对西方、印度等他国文化、文论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二
文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论的发生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而中国文论本身又是中国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因此,让文论经典向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敞开,并结合当下新语境进行重新理解、认知与评价,进而揭示其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而这也是“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的学理依据。具体而言,作为中国文论的研究方法之一,主要应从三个层面对“依经立义”的解读方式进行整体把握。
首先,将“中国古代文论”改称为“中国文论”。之所以不叫“中国古代文论”,是基于当前学界对中国文论的一种基本判断。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伯海先生曾指出:“尽管目前高校的有关专业多设有古文论的课程,学术领域里的古文论研究亦仿佛搞得火旺,而究其实质,基本未越出清理历史遗产的层面,也就是不被或很少应用于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不仅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评论中罕见古文论应用的痕迹,就是今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亦未必常沿袭古文论的学理,反倒要时时参用现代文论乃至西方文论的理念。……要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必须增强理论自身的活力,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一条明显的出路便是变古文论为中国文论。”⑧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曹顺庆先生则更将其视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曾经失落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今天为什么又开始受到当代文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种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和‘重建’的学术讨论和学术论战,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理论另外一个转折的开始。……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一厢情愿,或者某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⑨由此可见,用“中国文论”代替“中国古代文论”不是个人臆想,而是学界的一个信号!中国文化又一次转折的信号!这种转折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意愿,而是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是一个学术前沿问题,也是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好,认识得清楚、深刻,那就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机遇;处理得不好,就很可能会困扰我们的文化发展,困扰我们的学术研究。
其次,在关注中国文论“说什么”的同时,重视“怎么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的言说过程及其结果大体上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即“说什么”与“怎么说”。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言说”这一存在方式的基本立场就为此奠定了基调: “儒家主‘言’,认为一切可以言说,并且通过言说的内容(‘说什么’)施行教化,完成‘自然的人化’;道家由‘道’出发,认为‘言而无言’、‘不可言说’,但又必须得说,道家这种‘不可言说之说’使道家在‘怎么说’上形成了自己的言说方法——立意,并最终指向了审美。”⑩直到近代,梁启超们的“三界革命”和王国维们“词以境界为最上”亦不例外。他们或标举“说什么”,或重视“怎么说”,抑或兼收并蓄。因此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论应同时注重“说什么”和“怎么说”,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性地承续已被中断近一个世纪的文论传统。具体而言,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解决“说什么”的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史”(或曰“中国文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伊始,就一直格外关注“说什么”,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意义上的教材从1927年陈中凡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到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册丛书即是明证。当前,我们应从两方面去思考中国文论“说什么”的问题。一方面,思考我们说的是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另一方面,思考我们要说什么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前者强调的是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后者强调的是处理材料取舍问题,两者直接构成了中国文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传统。第二步,解决“怎么说”的问题。关于中国文论“怎么说”,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点,而当前中国文论研究应如何揭示、分析,笔者在这一领域做了一点尝试性的研究,除了系列论文之外,专著《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中国文论“怎么说”的悠久历史为基础,分析其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等方面表现出的鲜明诗性特征,并结合其言说的具象性、直觉性和整体性,揭示出中国文论在思维方式上的诗性特质。诚然,“说什么”是有限的,但是“怎么说”却是无穷的。中国文论研究秉持此二端,必将焕发其永久的诗性生命力!
第三,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的序言中曾说:“虽然作者是以古代作为出发点来写作,但是,他的写作毕竟不是古代,而是在现代并且为了现代而写作的,从而在他研究鬼怪的原始本质时,就不会丢掉现代的鬼怪。”(11)诚然,任何时代的学术研究,单纯地为古而古,都是无用的。因此,对本土经验和当下生态的关注,也是“依经立论”研究方法的题中之义。古代文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其中仍包含大量富于生命力的成分。诚然,特定的理论思维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会有其独一无二的个性。但任何一种思想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又必然会具备某种普适性的功能,个性中亦寓有共性。将传统诗文评里(小说、戏曲等批评同样)蕴藏着的普遍性意义发掘出来,给予合理的阐发,使之与现代人的文学活动、审美经验乃至生存智慧相连结,一句话,使传统面向现代而开放其自身,这便是古文论向着中国文论的转换生成,亦即众说纷纭的‘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要达成的中心目标”。(12)现在我们有不少学人正从事这种工作,让我们以宏观的视野、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态度投入其中,使古代文论像中医一样,逐渐走进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园地,融到现代的文学理论中,变古代文论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论。
三
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尚没有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融全世界文论为一体的文化或文论专著,建设总体文学理论或曰一般的文学理论(General Literary Theory)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中国文论作为世界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也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而“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之一,其意义生成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也具有了坚不可摧的学理依据,既扩大了所依之经的范围,又加强了所立之义的效用。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借鉴他国文化、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手段,“阐发研究”早在1976年就由台湾学者古添洪、陈鹏翔(陈慧桦)正式提出过,也早已出现在大陆学者(如王国维、吴宓、朱光潜等)的学术实践之中,并由港、台及海外学者和留学生发扬光大。正如余国藩先生所言:“过去20年来,运用西方批评观念与范畴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潮流愈来愈有劲。”(13)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阐发研究的单向维度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但用以研究中国文论,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其不仅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文论的丰富内涵。我们许多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中国文论中的许多概念、术语(如“文气”、“风骨”等)常常不易说清楚,已经到了《文心雕龙·序志》所言“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的程度,而借鉴异域的眼光、他者的视界却往往具有“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意义。因为各国的文化、文论不但具有共同的规律,同时也必然具有各自特殊的规律,通过借鉴、阐释,中国文化、文论的魅力才能更准确地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借鉴应在准确理解中国文化、文论的基础上进行,尽量避免牵强附会。
第二,以他国文化、文学现象印证中国文化、文学理论。笔者曾指出:“当你认认真真地借石攻玉的时候,你最终发现,在你自己的国土上并不缺少良玉,缺少的是艰辛的挖掘和精细的打磨。而在众多的良玉之中,最有历史和现实价值的自然是各个领域的经典。”(14)这些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仅能跨越时间长度,而且能缩短空间距离。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曾一度出现了“读经热”。有很多学者,包括在西方呆了很久的学者,他们当年提出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现在却都开始倡导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如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重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认为不能完全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不能有什么“贾桂”思想。而以研究西方后现代理论为主要方向的王岳川先生也提出重新“发现东方”,倡导将中国文化“输出东方”。相较以前那种“言必称希腊”的错误导向,中国文化、文论研究已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而以他国文化、文学现象印证中国文化、文学理论的方法不仅能激发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文论的信心和热情,而且能变被动为主动,立足于我,兼收并蓄,丰富、完善中国文论。
第三,中外文化、文学理论比较研究。唯有比较,我们才能用雄辩的事实证实中国文论的巨大理论价值及其在世界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过,严格地说,将中外文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是比较诗学或曰比较文艺学的基本内容。但在中国文化与文论的研究中运用此方法,则能凸现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当代价值和学术意义。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既源远流长,又独具特色,在概念术语以及入思方式等方面,都与西方、印度有很大的差别。这使得处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他国学者难以进入其中,彼此相互印证也十分困难。而中国学者如能摆脱过去那种比较封闭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以西方、印度文化与文论为参照,打通中外文化与文论,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则一方面能寻找本民族文化与文论在世界文化与文论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能发现本民族文化与文论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与文论之间的会通点,这对中国文论与文论走向世界和世界性文化与文论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7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页。
③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④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3页。
⑤谢祥皓,刘宗贤:《中国儒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⑥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
⑦成中英:《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6页。
⑧陈伯海:《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⑨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⑩蔡安延:《儒道两家的言意冲突:立言与立意——浅析儒家的“说什么”与道家的“怎么说”》,《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1)[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页。
(12)陈伯海:《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13)Anthony Yu,'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hinese-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s',YCGL.Vol23,p.50.
(14)李建中:《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 国学论文; 曹顺庆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