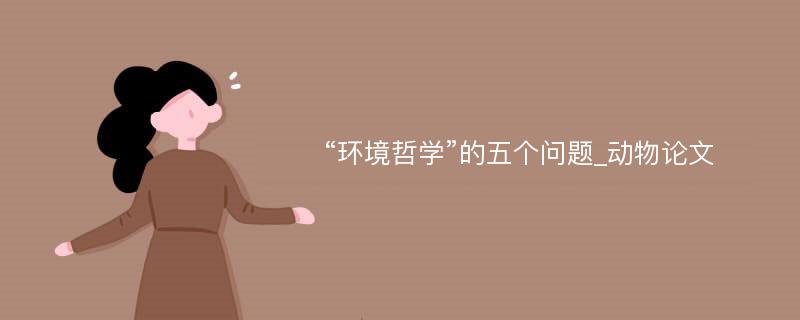
“环境哲学”的五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1 生态与环境:环境概念哲学的分析
一般说来,环境概念是指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自然条件的总体。但具体说,这一概念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环境概念包括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资料来源的自然资源,而狭义的环境概念则不包括资源的含义,而仅仅是指人类生活的“家园”的意义。人也是一个生命体,他从自然界来,他也要在自然界中生活。人的生活需要有适合于人这一哺乳动物的自然条件:他得以立足的大地,清洁的水,由各种不同气体按一定比例构成的空气、适当的温度、一定的必要的动植物伙伴、适量的紫外线的照射和温度等等。由这些自然物构成的稳定的动态的自然体系就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作为人类生存须臾不可离开的必要条件的整体,是人类的“家园”,是人类的“生活基地”。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就是指狭义的环境。如“环境污染”概念中的环境,就是狭义的环境。
我们研究环境价值,还必须把环境概念同生态概念区别开来。人们总是把“生态”和“环境”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认为讲“生态问题”就是讲“环境问题”。其实,“生态”和“环境”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尽管二者就其外延来说都是指自然界,但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却是人们在应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解释自然界时所形成的,因而它们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所谓生态学的方法,即“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的方法,“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1]。因此,用生态学的方法看待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只能把人看作自然界整体的普通“一员”,看作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物。而“环境”概念则是立足于把人作为“主体”来看待人同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时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外在性”;外部的自然物是构成人类生活的“环境”。可见,生态学的方法是立足于“自然整体的尺度”理解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的,而把自然作为环境的研究方法则是立足于“人的尺度”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很显然,如果仅仅把人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一个普通的部分,那么,自然界的整体系统就不是人的环境,也就是说,从生态学的方法中产生不出环境概念。从逻辑上说,局部(人)是不能把整体(自然系统)作为环境的。如果把整体作为局部的环境,那么,局部本身因为也是整体的部分,因而也成了自身的环境,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实际上,当我们说“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时,我们所说的“自然界”并非自然界“整体”,而只是人类以外的局部自然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质上是人同外部局部自然界(与人的生存相关的自然界)的关系。只有立足于人的尺度,把人看成主体,人以外的自然界才成为人的环境。
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环境的存在论意义。工业时代的哲学思维正是把主体绝对化而造成了对存在的遗忘。自然界成了人类实现功利的目的对象,人则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欲的上帝。当人们为了效用的目的任意处置自然界的时候,自然界的存在本性便遭到了无情的破坏,造成了环境危机。因此,环境概念又不是与生态概念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服从生态学的规律。生态学是环境哲学的科学基础。我们当代出现的生存危机归根到底是因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解决环境问题也必须从解决生态问题入手。生态问题是环境问题中的主要问题。
2 哲学人类学:人的环境与动物的环境
人与环境的关系同一般动物同它生存环境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按照哲学人类学的观点,动物的生物学结构是“专门化”的。动物的专门化是指动物的生物学器官的专门化。动物的器官是在长期适应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因而它们的器官的生物学功能具有特定的指向性。鱼的器官的功能是专门指向水的,鸟的器官的功能是专门指向天空的。因此,物种的器官功能都是只适应某种特定环境的。如果它生活在它的器官所指向的环境中,它凭借着器官的生物学功能就能对环境应对自如;而当它的活动超越了专门归属于它的天地时,它就会因失去了应对新环境的生物学手段而灭亡(例如当鱼失去水的时候)。物种器官的专门应对某种特定环境的生物学功能就是生物的本能。这种生物学本能是物种维持生存的惟一手段。本能是先天的,是物种在长期适应某种特定环境的条件下形成的,是通过物种的生物学遗传机制得到传递的。由于物种内部的个体得到了相同的遗传信息,因而从属于某一特定物种的个体都具有相同的本能。老鼠甲与老鼠乙的生存能力基本上是相同的。同时,由于这种遗传机制的固定性,也使得不同世代的物种个体具有大体相同的本能(“现代老鼠”同它们的祖先——数千年前的“古代老鼠”没有显著不同的本能)。
因此,动物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封闭的。动物都只能在它的本能指向的狭小的环境中生存。黑格尔说:“每一动物都以一个有限的范围为它自己的无机自然界,这个无机自然界完全是它自己支配的领域。”[2]因此,“环境”概念对于动物来说也是相对的。一般动物正是靠有限的、特定的本能同某种固定的、外部自然发生关系来维持生存的。人们往往是从人的观点去看动物的环境,因而把动物的环境人化了,把动物的环境等同于人的环境。通常看来,似乎处于同一空间中的不同的物种或人面对的是同一个环境,而实际上它们面对的生存环境却是极为不同的。“雌性的蝙虱对光、气味、温度都具有感觉能力。它用对光的感觉,发现它爬行的路线,用对气味和温度的感觉,使它当热血动物穿过树枝时能跳过去喝他们的血。”[3]它没有眼睛、耳朵和味觉,因为它不需要这些器官。“环绕蝙虱的丰富的整体世界因而蜷缩在一起,转化为一个贫乏可怜的结构。此世界包括了三种特质和三种刺激,即只是蝙虱的环境。”[4]
人的器官的生物学结构和功能却是非专门化的,它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环境。相对于动物的狭隘有限的、固定的环境来说,人的环境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没有哪种特定的环境是专门属于人的。因此,人是惟一能够在全球的任何地方生活的动物。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仅仅是说,人只要依靠后天的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才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生存。如果离开后天的实践活动,那么,人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都不能生存,因为人没有维持生存的生物学本能。从生物学上说,人并不具有动物的那种专门应付某种特定环境的绝招。因此,人没有生物学上的维持生存的本能。“人不是受本能制导的生物,不仅如此,人类根本没有本能,只有本能的残余。这些本能残余只表现在很少一些需要最低限度的智力的协调动作中;并且像达尔文早就说过的那样,这些残余也处于遭到毁灭的过程中。”[5]
人与环境的关系同动物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动物与它的环境是直接同一的。它并不能把自己同环境区分开来。它与环境的关系不是主客体的关系,不是对象化的关系。物种的特定的器官与它的特定的环境一起构成了它的本能结构,服从着同一的规律。动物感知的东西“作为一般的内在形式已经载于动物自身。”因此,“动物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它先天就知道的”[6],它本能地知道它可能知道和必须知道的东西,它的知识早已先天地存在于它的生命规律中。动物对这个世界的印象不是作为感知结果的知识,而只是释放事先决定行动机制的信号。这种感知内容并没有把世界传达给动物。
可见,人不能仅仅依靠天然的自然环境生存。人没有应对天然环境的生物学器官,没有生存的自然本能。因此,人必须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制造“人造器官”。这就形成了人类特有的“第二环境”,即人化的环境或文化环境。人化环境同自然环境既有区别,又有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在这两种环境中,“第一环境”始终具有终极性的决定意义。
3 环境与价值:人类生存的一个悖论
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人的生存可以摆脱自然环境的作用。只是表明了人对环境的依赖同动物对环境的依赖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罢了。
从广义上说,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就具有两种价值:第一,作为“人类家园”的价值;第二,作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资源)的价值。
这两种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价值。但是,它们却具有相反的性质:作为人类的生产活动的原料的价值是一种“消费性价值”。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消费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资料被消费的,而且是因为它的价值只有在被人类消费时才能实现出来。而(狭义的)环境价值则是一种“非消费性价值”,即“存在性价值”。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存在性价值”,是因为它是只有在保持其存在时才具有和能够实现其价值。如河边的树木同时具有两种价值:当它得到保存(不被砍伐)时,它具有调节空气成分的比例、保持土壤水分、保护堤岸等价值。这是一种环境价值;而当这些树作为消费资料被砍伐时,它就具有制作工具、家具等价值,这是一种“消费性价值”。我们不能同时使自然物实现这两种价值:要使树木具有环境价值,就不能把它砍掉(消费),也就是说,必须保持它的存在;而要使它具有消费性价值,就必须砍掉它,这时,它就不再具有环境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悖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消费自然,就必然对人类的另一个生存条件(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而要保持原有的人类生存环境,人类就不能消费自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改造自然,就会因为生活资料的危机而无法生存;而如果改造自然,又必然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这同样也会危及人类生存。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都是人类生存的危机。
现代发展观(即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只看到了自然界的消费性价值,而没有看到自然界的环境价值。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把获得最大利润作为最高目的。在金钱的驱使下,无限制地改造自然界,从而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因为人并不能依靠像普通动物那样同环境发生关系来维持生存。
人与环境关系的自然科学基础是生态学规律。尽管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间接的,是通过文化的中介发生的,但人既然仍然是一个生物体,它最终离开自然环境也是不能生存的。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是保证狭义上的环境价值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
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观应当是生存论的价值观,把人类的生存价值作为终极关怀,才能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既改造,又适应),也才能合理地对待自然界的消费性价值同环境价值的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危机,正是这一矛盾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结果。如果把人类的生存作为评价人类行为的终极尺度,那么,我们就既不能无限制地改造和掠夺自然界,也不能完全否定人类消费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必要性。要做到二者的统一,关键在于要找到它们的最佳结合点。
4 环境与伦理: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
环境伦理学是在出现了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新伦理学。人类生存危机的出现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类无限制地改造自然界的结果。因此,环境伦理学首先要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我们“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传统发展观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人是主体,自然界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实践行为都是天然合理的。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行为都是天然合理的,那么,只要我们有能力做的,就一定是应当做的。例如,我们把生产、生产力(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作为评价社会关系和实践行为合理性的终极的和惟一的尺度。既然它是终极尺度,它本身就是天然合理的,就是无须评价、也不能评价的。因为在它的后面再也没有比它更基本的尺度了。这就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约束、无规范的改造。环境伦理学,就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对人类的实践行为的评价、约束和规范。实践并不是人类行为的目的,而只是实现生存与发展的手段。因此它不能成为评价社会关系、社会发展合理性的终极尺度;我们“能够做”(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环境伦理学正是以此来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
环境哲学既是关于环境的哲学,也是一种新的人学,或曰“环境人学”。即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阈对人本身的重新反思、对人类行为的重新评价和规范、对人类生存的新的终极关怀。我们应当在更广阔的视阈来理解环境哲学。
5 生存论:环境哲学的终极关怀
环境哲学的理论性质是人道主义。但它并不是传统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人的生存论和生态科学基础上的新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提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发展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而形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传统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尊严和权利,以反对神权;尊重科学,崇尚理性,以反对蒙昧主义;重视现实生活,主张个性解放,以反对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歌颂友爱,提倡平等,以反对王权和等级制度。这种人道主义对于封建社会的“神道主义”和“王道主义”确实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却走向了极端,引发了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当代人类遭遇的各种困境和危机,都同这种人道主义的极端发展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这种人道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就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伦理学的终极根据也是人道主义。但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人道主义的“新人道主义”。它在以下方面同传统的人道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1)从个人本位到类本位的转变 传统人道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私有制,道德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合理的利己主义”。它所追求的人的权利、尊严、自由、平等以及伦理学讲的幸福、快乐等都是以个人为基点的。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也只不过是“不损害他人利己行为”的个人利己行为而已。“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是对这种人道主义的形象描述。这种人道主义为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其个性和追逐最大的利润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和自由竞争,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资源的掠夺开发和对环境的极大破坏,从而使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在当今世界,我们人类面临的危机已经具有全人类的性质。第一,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任何局部破坏,都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第二,任何个人的生存都必然依赖于“类”的生存,如果失去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生存下去。第三,解决目前困境的出路也只能是全人类的统一行动,任何局部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一全局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需要实现从个人本位向类本位的转变。只有如此,才能解决时代提出来的新问题。
(2)从绝对主体意识到“有限主体”意识的转变 传统的人道主义消灭了虚幻的上帝,却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帝,即人类自己。在处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时,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欲”、“无所不可”、“无所不做”的绝对主体,这是一个“疯狂主体”。它消灭了人的理性、价值追求和实践行为的绝对界限,使人失去了任何限制和约束。它忘记了,无论人的能力怎样发展,人都仍然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作为部分存在的人类,始终都只有依赖于自然界整体的存在才能生存。自然界整体的生态系统遭到彻底破坏之时,也就是作为自然整体之局部的人类的灭亡之日。因此,作为自然界整体一部分的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超越自然界整体对它的限制。它始终是一个“有限主体”。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的保持,是人类的欲望、行为的绝对限度(底线)。所谓发展伦理学就是评价、约束和规范人的欲望和实践行为的伦理学。对有限主体的确认,是这种伦理学的终极原理之一。
(3)从享乐意识到生存意识的转变 从生存论看,消费本来是对人的健康生存需要的满足。但是,传统的人道主义在实现了把人生的意义从天堂转向尘世、从禁欲主义转向物欲主义之后,人的消费也从对生存需要的追求转向了对挥霍、奢侈、享乐的追求。我们把这种追求叫做“欲求”。“欲求”不是“需要”,而是“想要”,它产生于人们追求对他人在地位上优越感的心理竞争。丹尼尔·贝尔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7]什么是幸福?只有当我们的消费超越了进入我们视线的其他人们的消费时,我们才会感到幸福;只有当我们今天的消费超越了我们昨天的消费时我们也才会感到幸福。这种心理上的竞争使消费的增长成为一个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无底黑洞,其后果就是人均消耗资源量的无限度增长。在当今世界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的困境下,这无疑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敌。新人道主义立足于生存论来看待消费问题,把保证人的健康生存需要看作是满足消费的终极尺度,提倡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发展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行为被看成是人类的美德,是在当今世界使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惟一出路。
(4)从现世主义意识向未来意识的转变 当传统的人道主义赶走了“神道主义”的虚幻的“来世崇拜”之后,合理的“未来意识”也被判处“退场”。商品经济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只注重实惠和实效,只注重有限的、实际的东西,不关心无限的、神圣的、终极的东西,即只要现在,不要未来。“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过把瘾就死”是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表现。这种现世主义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孪生姐妹,都是在“用今天赌明天”,“用现在赌未来”的“赌棍”人生观。作为可持续发展观和发展伦理学根基的新人道主义的人生观则是面向未来的人生观。当今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告诉我们:人类生死存亡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这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是不容“试错”的。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在,更应当关注未来;我们不仅自己要生存,而且也要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整个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持续生存下去。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可持续性)的需要来约束和规范我们现在的发展与实践。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自觉的发展。我们需要一种关注人类未来的新人道主义,也需要一种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新伦理学,即发展伦理学。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系统。它具有一定的自我生长、自我组织、自我修复能力。因此,只要人类对自然界的消费和改造的实践活动保持在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以内,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消费和改造活动就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致命的破坏,因而就不会危及人类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只有一个:我们需要改造自然,但必须对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进行评价、约束和规范,以便把人类的生产活动限制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的限度以内。这样才能使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两种价值都得到满足。因此,只有立足于生存论,才能合理地处理环境价值与消费性价值的关系,找到隐藏在消费价值与环境价值背后的更深层的人类的生存价值。生存价值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也是评价、约束、规范人类实践行为的终极尺度。
收稿日期:2003-06-20
标签:动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