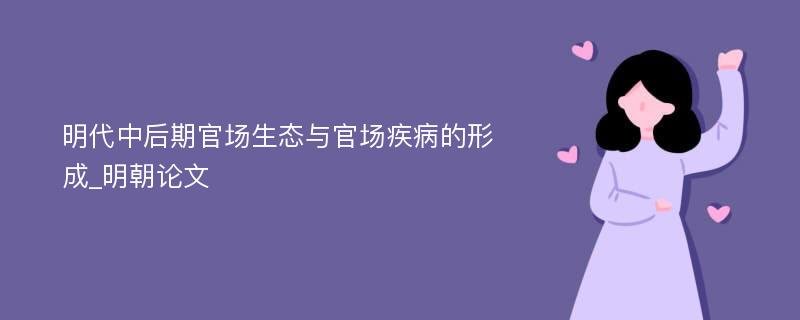
明代中后期的官场生态与官场病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场论文,明代论文,后期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5-0126-11 引论:从“五瘴”说起 追溯“五瘴”之论,理应从宋人梅挚所写《瘴说》一文说起。自唐宋以后,岭南以瘴气闻名,成为仕路的一大难途,官员避之犹恐不及,深怕自己在官路上为瘴气所染,客死他乡。故岭南之地,多为京官贬窜之处。宋景祐初年,梅挚出知昭州,专门撰写《瘴说》一文,镌刻在崖石之上,并以“瘴气”为喻,对当时官场中的五种瘴气之病一一加以揭示。梅挚所言宋代官场的五种瘴病,即“急征暴敛,剥下奉上”的“租赋之瘴”,“深文以逞,良恶不白”的“刑狱之瘴”,“昏晨醉宴,弛废王事”的“饮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实私储”的“货财之瘴”,以及“盛拣姬妾,以娱声色”的“帷簿之瘴”。①细绎梅氏之意,“五瘴”之病,并非像岭南这样的边远官场所独有,即使在辇毂之下,亦在所难免,只是仕者或不自知,于是将其归咎于“土瘴”。梅氏“五瘴”之说,堪称切中官场膏肓。在明人汪天锡所辑《官箴集要》中,亦收录了梅挚的《瘴说》,旨在说明瘴气的危害,不仅仅限于“地瘴”,而是另有一种“仕瘴”。地瘴未必能死人,反而是“仕瘴”,更容易死人。[1] 此外,对仕宦之地的看法也表明明代中后期官场文化已偏离儒家政治文化之本义。由于自然环境的优劣之异,再加之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一,必然导致仕宦之地的苦乐不均。随之,在明代的官场上开始流行“命运低,得三西”的谚语。[2]所谓的“三西”,即山西、江西与陕西,或因处于边地,或因经济落后,或因民风刁讼,为官甚难,且无多少油水,百官视为仕路畏途,避之犹恐不及。这固然不能遽断为一种官场病态,但至少说明官场生态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为官者弃“事君”“惠民”于不顾,更多地考虑“事亲”甚至是一己之私,与儒家所倡导的为官本义渐行渐远。此即自宋以后儒家士大夫所常言的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 一、官场生态与吏治变迁 官场生态的形成乃至变化,其最为关键的一点,则牵涉到如何理解为官的本义。换言之,为官本义上的“为人”与“为己”之辨,甚或“致君泽民”与“营私肥家”之别,确实关乎士大夫内在的精神世界。假若出仕者抛弃久已信奉的儒家为官准则,那么必然会引发官场生态的异变,乃至士风的堕落,进而导致吏治的变迁。 1.为官本义及其沦丧 就为官本义而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实已经发生了两大转向:一是从设官“为民”转向设官“为君”;二是从设官“为君”转向设官“为贵人”。由此而来者,则是从“忘己”向“树己”的转变,进而沦为“固己”,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则是为官不再“为国”,而是仅仅为了“中饱”私囊。[3] 这就需要从儒家政治文化的视角重新对为官本义加以审视。按照儒家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为官的本义理应是“事君”“惠民”与“事亲”。所谓“事君”,就是官员“上罄其诚以报其主”。所谓“惠民”,就是官员“下竭其力以惠其民”。换言之,士人做官,并非以享爵禄、操利势,使人奔走承奉为荣,而是必须惠泽及于百姓,使百姓爱戴自己犹如“父母”,令名垂于无穷。所谓“养亲”,则指官员通过出仕而获取廪禄与华贵,以廪禄“养亲”,以华贵“敬亲”,进而使双亲“尊而且荣,安而且寿”。[4] 真正能将儒家理想乃至精神人格付诸实施者,做官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致君泽民”。儒家学者所秉持的是义利之辨,在出仕为官方面,人人必须过得“义利”之关。他们所崇尚的是“义”,而不是“利”,即使“大利”,亦“不换小义”,更遑论“以小利坏大义”。[5]换言之,士人之“廉”,犹如处女之“洁”,“一朝玷污,终身玷缺”[6]。 反观明代官场,儒家政治文化中的为官本义已经丧失殆尽,很多人将出仕做官当作一桩“买卖”或者“生意”。在这单生意中,所有前期诸如参加科举考试之类的付出,必须在出仕以后获得相应的回报,甚至有利可赚。于是,世人更重“官荣”,致使“仕路丧天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7]至于其具体的表现,则可析为以下三点:一是仕宦追逐名利,不再有实惠及于百姓,“卑者泪利,高者骛名”[8]。二是仕宦有“市井之心”、“盗贼之行”,上焉者只是“务名以干上司之知,其弊徒受虚文,无恻怛之实”;下焉者,则“惟知渔利,人面而鬼心”[9]。三是为官不再为国,而是仅仅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谋国事似甚拙,而谋富贵又甚巧;为朝廷干办似甚疏,而为身家私图又甚密”[10]。 为了保持一己的富贵之欲,在明代官员中普遍流行恋官之风。按照儒家的政治观念,士大夫居官,常要思量此官朝廷今日要回就回,明日要回就回,有如此见识、度量,方不失为官本义。然揆诸明代官场,官员恋栈之例,俯拾即是。即使是尊官大吏,一听说自己被罢职,就茫然自失,甚至“哭泣嗟咨继之”[11]。有的官员尽管已经外补、左迁、革职,但还是书写以前的官衔,足证他们对美官的眷恋不舍之情。[12] 何以如此恋官?正如明代介丘和尚所言,还是因为这些官员的心中,存有一个“得失”的念头。作为富贵人的官员,一旦享用了服食起居方面的荣华富贵,就“淡薄不得”;在任时的热闹场面,经历过了,就“冷落不得”。得不到,就称之为“失”。得失的念头,常转于胸次,所以在学道之时,不能做到“悬崖撒手”[13]。更有甚者,为了保持富贵荣华,有些官员不惜做出“抢官”之举。冯惟敏所著散曲《八不用》八首,其中一首云:“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14]所言即此。 做官初意一差,其后的行政必然一塌糊涂,吏治之坏,由此而致。流风所及,明代官员仅仅满足于“当官”,而不再“做官”,或仅知“做官”,不晓“做人”的道理。正如明人徐学谟所言:“六卿但知从政,不知执政,是以题覆屡至变更;有司但肯当官,不肯做官,是以施为一切苟且。”[15]尽管只有一字之别,然当官者只是满足于一己之私,以苟且两字加以应付;而做官者则需为朝廷、百姓做事。照理说来,真正的做官,既得小民之欢心,何暇计上官之谩骂?既树居官之气节,何须畏当路之厌薄?若能如此,虽然会遭遇世路风波,但“做人”两字还是绰绰有余。但事实并非如此。明代官场的官员,不免工于欺世之“小术”,甚至假托“时中”两字,一开口,一举足,不问自己“慊不慊”,但问别人“喜不喜”[16],官场已无真实做官之人。 2.官场生态的变化 为官本义一旦沦丧,必然殃及官场生态。细加概括,明代官场生态的变化,大抵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假借养病,规避营私。按照明代吏部所行事例,凡是京官养病,到家调理,痊愈之后,必须按期赴部听用。若有托故延住三年之外者,照例革职。[17]嘉靖八年(1529)十一月,明世宗更是下诏:“这御史但有养病三年以上的,都革了职,着冠带闲住。”[18]然假借养病,既可文饰迁延之罪,又可藉此获取“恬退”的高名,难免官场仿效成风。[19]在此风气的影响下,凡是公家之事,只要不关系到个人的身家利益,官员莫不替自己算计,有时甚至将人、己合在一起通算妥帖,才做决定,朝野皆然。如六科官员出使琉球之差,因渡海有风波之险,躯命所关,无人愿意承担此差,只好轮流充任。万历年间,有一位官员轮当此差,就“先期告病归,自谓得计”[20]。 其二,因循苟且,“善宦”成风。明代官场,能臣颇乏,很多不过是因循苟且的庸吏。流风所及,则形成两大官场病态:一是“善宦”。所谓善宦,通俗言之,即为善于或巧于做官,譬如当官者“率务裂纲纪,以市私恩,纵奸慝以为盛德”[21]。二是“痞政”。所谓痞政,显是政治缺乏清明的典型症候,且丧失了设官的本义。[22] 其三,官员入幕,给事私门。自隆庆末年、万历初年以后,随着内阁首辅权力的更替,很多政府官员均入执政大臣之幕,给事私门,导致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堂官,对下属官员难以约束。这些属官,“恣其胸臆,旁若无人,自称风采焉。习以成风,彼此相效”。至于外省,巡按御史见到那些进士出身的推官、知县有科道之望,就曲加护庇,引为“私人”,甚至委托他们查访布政、按察二司官员的贤否,“悉出唇吻,有所不悦,遂以萋菲而祸终不免”。于是,二司官员反而畏惧推官、知县,遇到他们前来谒见,“每每留饮幕中,亲陪谈笑,以结其欢心”[23]。 其四,官员撒泼,骂座打架。在明代官场,一些官员为了官位升迁一类的个人私利,不惜置士大夫的身份于不顾,互相詈骂,一如街头泼皮。如傅策,字元汉,上海县人。曾为刑部主事,因上疏论劾严嵩,谪戍广西,为此声望日重。穆宗登极,补任吏部,后历转南京礼部侍郎。同里人兵部主事张明化,拿三百两银子前去谒见傅策,希望能居间谋得升迁之职。傅策听后,不免勃怒,大骂明化。明化遭此奇辱,亦攘臂大诟,甚至历数傅策的过失。傅策更是怒甚,骂道:“竖臭子,我为若推星运,不过十年官,今宜尽矣。”明化反唇相讥,骂道:“若论星运,汝不久且丧元。”说完拂衣取去。[24]更有甚者,明代官场中人,一语不合,诉诸武力者亦有其例。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广东乡试,无锡人巡按御史顾某,在试院堂上,与绍兴人布政使王泮,议论不协,顾氏以手掌打王泮,王泮不让,反手击打,顾氏披发倒地,身且去服。王泮疾行出院,衣冠体面,丧失殆尽。[25] 其五,士气衰落,趋名趋利。士气云云,乃国家之元气。而揆诸明代官场,人心士习,日趋颓靡。在明代官场,官员不知有公道是非,袭套献谀,虚美熏心,互相效仿,靡然成风。大官皆然,尤以相门为甚。当时的官员,尤其崇尚“老成”与“善处”。所谓老成,就是不喜言人,见人俯首深揖,口中讷讷,不吐一词。所谓善处,就是不喜人直,遇事圆融委曲。[26]时风所至,则无不将立节之人视为“好异”,将守正之人视为“矫情”,只是取模棱软媚之人。于是,巧猾无耻之徒,“乘间斗进,天下靡然顾化”,而所谓真气节者,则“折北而远避”[27]。 3.吏治变迁 究明代官场吏治变迁,实有“清平之世”与“否塞之世”的区别。明人陈第有《二疏咏》诗,其中有句云:“君不见清平之世吏多廉,归居卑室耕薄田;子孙刻砺谋树立,青云接踵称英贤。又不见否塞之世吏多贪,满堂金玉堆琅玕;子孙骄侈旋破败,冬或衣葛朝无餐。奈何荐绅弗明觉,一入膴仕忘旧学。公然剥削殖资财,泾水侵淫渭亦浊。”[28]细绎诗句之意,两者之别,在于一为“吏多廉”,一为“吏多贪”。 世道的变迁,实关乎士风的兴衰。考明代士风的衰落,显然始于弘治以后。按照丘濬的说法,在正统、景泰以前,气化隆洽,人心淳朴,士风尚未至于浇漓。当时的士大夫,制行立言,“类以质直忠厚、明白正大为尚,而不为睢盱侧媚之态、浮诞奇诡之辞”[29]。至弘治年间,士风趋于转变。弘治十二年(1499),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宁在上疏中,直言士风之邪正,关系到天下之安危,且至弘治年间,士风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最终导致贤否混淆,是非倒置,甚至天下不治,民生不安。[30] 与士风变迁相应,明代的吏治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根据清代史家赵翼的观察,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起自闾右,熟悉墨吏对民生吏治的危害,尝以极刑处之。然太祖施政,并非专任刑法,尚通过旌举贤良,以示奖劝。故自洪武以来,吏治澄清,长达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即使内外多故,而民心尚无土崩之虞。究厥其由,还是因为吏鲜贪残之故。自嘉靖、隆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人不自顾惜,且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官员均凭贪墨奉承上司,于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明朝随之覆亡。[31] 二、官场病的形成与症状 明代官场病的形成,起源于弘治年间,至嘉靖、隆庆以后更是病入膏肓。至于官场病的症状,因观察者的视角不同,其概括亦稍有差异。最为简单的概括,当数李三才,他在上奏中,用“泄泄沓沓,以社稷为戏”九字加以论断[32],可谓切中时弊。嘉靖元年(1522),羽林卫指挥使刘永昌在上奏中,将“人臣之恶”亦即官场病症概括为下面六种,分别为“贪赃”“嘱托”“私意”“苟延”“骄纵”“淫滥”。[33]高拱更是将官场病概括为“八弊”,即“坏法之习”“赎货之习”“刻薄之习”“争妒之习”“推委之习”“党比之习”“苟且之习”“浮言之习”[34]。下面顺着高拱之论,再参之明代诸家之说,将明代官场病症厘定为下面六种症状。 1.官场病症之一:为己徇私 一个“私”字,已经明确道出明代官场病态实况。所谓“私”,又可析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做官为己,不为百姓谋福利,只是打自己心中的小算盘;二是在官员选拔上,亦多徇私情。 按照明制,官员考察乃至选拔,事权均集中于吏部,故吏部有“铨部”之称。然自嘉靖年间孙丕扬创为“掣签”之法,于是吏部又有“签部”之号。当时一位山人赋有一诗加以讥刺,云:“冢卿无计定铨衡,枯竹拈来知有灵。若使要津关节到,依然好缺作人情。”[35]可见,掣签之制,貌似公平,实则还是徇私,关节人情,满目皆是。如史载选官掣签之日,官员“多以银一锭及历日扎于右手腕,流俗相传,莫知所谓”[36],足证掣签时还是必须以银子开路。 各级官员之综核、考察乃至选擢,公则明,私则阍。这是公认的道理。此外,各级地方官员的劝惩,系于黜陟之法,而黜陟所凭,则在于巡抚、巡按之举劾。揆诸明代的官场,巡抚、巡按并非时时体访、务在的确并将殃民不职的官员拿问、参奏,而是徇私市恩,讲私情,顾体面,听嘱托,最终导致“法为情骫”[37]。 2.官场病症之二:虚文矫饰 明代官场虚文矫饰之病,实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习尚繁文,将精力专注于趋谒、酬酢之类的官场应酬,无暇甚至无心处理公务;二是工于虚伪,托诸空言,讲求声称,不再实心做事。 承平既久,明代官场习尚繁文,已成一时风气。当官者不再专心于自己的职守,而是好为趋谒,酬酢多端。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官员相见之礼,即使是属官拜见堂官,亦不过是行两拜之礼。只有上朝参见皇帝,才行五拜三叩头之礼。而明代的官场交际,尤其崇尚繁文缛节,将朝参之礼用于官场交际。如“三让已多,务以百数;一揖既足,务相回旋;甚者动辄四拜,而叩头在无算之数”。每日时刻有限,一人精力有限。假如官员整日应付繁缛的官场交际,势必影响到处理公务,其结果则是“始入衙门,办理公务,苟了前件,又复出应人事。每见人无遗力,日无暇时,而公家之事曾无一二”[38]。 明代官场不但习尚繁文,而且工于虚伪。在追求虚名的风气影响下,官员率多务名,而人亦徒徇其名,不责其实。于是,“机警辩捷者,目之为有才;狡伪熟猾者,目之为有智”。至于那些悃愊无华,不肯与世浮沉的官员,反而“不见称于人”[39]。吏习趋巧、工于虚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事多而官事少,官事多而民事少。风气所至,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的官员,实不多见。更多的官员,不过是“剥下奉上,以希声誉;奔走趋承,以求荐举;征发期会,以完簿书;苟且草率,以逭罪责”[40]。官场上下,矫饰成风。 3.官场病症之三:软熟谄佞 明代官场软熟谄佞之病,一则软熟,讲究“养态”;二则谄佞,阿谀逢迎。所谓“软熟”之症,实为“软美”之态。儒家讲究“无欲则刚”。人一有了欲望,就难免显得“软熟”了。很多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贵,对朝廷的弊政就不闻不问,表面上是通过谦卑逊顺之态,维持自己的一种“体面”,并藉此博取一种好的名声,实际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富贵。这在内阁大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按照明代的惯例,内阁大臣一般多起家翰林,这些人做官确实是一路“淡薄”,才能最后“进步黄扉”。但一旦进入“黄扉”,就不再变得淡薄,而是一条“膻路”,功名一日到手,便有无数好处。为了保持这条“膻路”,他们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不再敢于直言相谏,甚至面对下属官员也保持一种“谦卑逊顺”之态。于是,当时北京的官场专门嘲讽这些翰林官入阁是“吃蔗头”。何以言此?这是因为甘蔗多带有甜味。翰林一入阁,就犹如“既思其甘,又思其苦,故富贵功名,愈咀嚼,愈有味”[41]。 软熟养态的极端,势必导致“佞风谀俗”,弥漫官场。通观明代官场,已是“谄佞盈朝”,并将不阿谀逢迎他人者视为“迟货”[42],即时代的落伍者。明代官场阿谀逢迎之风,大抵与权监、权臣擅权同步而生,其例更是俯拾即是。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擅权,大臣王文,附和王振,“见必长跪鼠伏,奔走甚欢,尤为士论所薄”[43]。成化年间,明宪宗信任太监汪直,朝绅谄附,无所不至。当汪直巡边之时,经过地方的巡抚大臣,无不铠甲戎装,迎至二三百里之外,“望尘跪伏,候马过乃起”。等到汪直驻扎于宾馆,则换成小帽曳散,“趁走唯诺,叩头半跪,一如仆隶”。于是,当时有谚语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奔竞之甚,一至于此。[44] 嘉靖、万历年间,首辅严嵩、张居正擅权,士风、士气尤为低落。为了巴结严嵩、张居正,甚至一些大臣亦纷纷自认“干儿”。为此,杨时乔专赋《干儿谣》一诗加以揭示,其序有云: 予从缙绅后,则闻所谓干儿于分宜、江陵者。盖司空某妇入省分宜妪,至袒韝蔽自上食。已裒金豆散诸傔,亡不啧啧司空妇矣。妪榇过武陵,制使太保某跣齐衰舁入哭。而江陵方炙手可热也,按楚某御史某语三司:“老父顷书至。”有窃哂者,噫吁,至是哉!谣之,志秽尔。[45]“志秽”云云,确乎堪称当时官场士人秽迹的实录。 设官本义,原为朝廷、百姓做事,事实上却成为权门的看门狗。明末清初人钮易庵《贞白楼诗稿》中有《今乐府》多首,其中一首为《权门犬》,专门揭示依附权门官员的谄态。其中有云:“权门犬,吠权门。好官我自为,笑骂谁复论。嗥以南,嗥以北,权门有窦恣出入。卤簿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空叹息。一朝权门冷落车马稀,群犬狺狺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摇尾权门空尔为。”[46] 4.官场病症之四:苟且推诿 明代官场之病,吕坤用一个“苟”字加以概括,云:“而今只一个‘苟’字支吾世界,万事安得不废弛?”[47]此即明代官场的苟且推诿之病。此病之状虽多,却可以从下面三点观之: 一是官员互相推诿责任,不再实心任事。换言之,明代的地方官员,往往不尽其心,只要稍微涉及利害疑难,就观望推诿,不肯身任其责。事不关己,虽“偾事殃民”,亦不加顾惜。[48]在明代的官场,官员虽身在局中,反而漠然视之,将自己置身局外。“明不足也,而文之曰‘浑厚’;赡不足也,而文之曰‘镇静’。”[49]究其目的,无非是避免“生事”之名,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毁无誉”的境界,只要能安然得到自己所欲,就可以离官而去,将官署视为传舍。简言之,就是拙于任事,巧于避事。 二是媕婀雷同,圆融已极。明代官场陋习,其弊已久。当时的官场士大夫,无不以“媕婀雷同”为尚,碰倒难为之事,通常持一种“无所可否”的态度,并以此自诩“识时达变”。若有官员稍自激励,想“举其职事”,干出一番事业,反而“世共訾笑之”[50]。可见,所谓的媕婀雷同,不过是处事圆融的另一种表述方法而已,甚至流于圆滑。 三是怠缓悦从,虚应故事。明代官场,怠缓悦从,蔚成风气。怠缓悦从,所包甚广,未易指数,仅就新官初任、官员入觐、赍捧表文三件事论之。照理说来,新官初任,是人臣事君之始,然当时官场,新官通常优游在家,并不急于赴任。地方官员入觐,属于国家大典。按照制度规定,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较为僻远之外,通常二月辞朝,八月即可抵原任。至于赍捧表文,九月辞朝,第二年正月、二月可抵原任。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入觐、赍捧表文官员,十个月过去,尚多在家料理家事,而不急于回任,且恬不为异。此即“怠缓”之病。面对官场如此“怠缓”之风,无论是中央衙门的吏科,还是地方上的巡抚、巡按,无不采用一种“悦从”之态。譬如吏科原本有限凭之制,限期官员抵任,但事实上并不按照规定实施,而是“俱务宽纵,不照旧规”。至于巡抚、巡按,因恐得罪下官,官员抵任来迟,亦“绝不问故”[51]。 5.官场病症之五:奔竞钻营 明代官场奔竞之风的盛行,显然导源于良心的沦丧。良心一旦丧失,势必导致“干之则力为推毂,不干则任其淹滞”,所谓的奖恬抑竞,也就流于空言而已。[52]官场躁竞之风,又源于名利之争。然相比之下,过去的争名夺利,尚有所顾惜自己的声名,只好在昏夜偷偷摸摸地干;而明代官场的争名夺利,则已是在白昼大张旗鼓地做。宋人苏轼在论及宋代官场弊病时,曾说当时官场一官出缺,有三人争夺,即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者又一人。明代官场,一官出缺,伺者不止一人。如巡抚缺出,至拟更定三四人,而犹不定,其他善地美官,莫不皆然。更有甚者,有些官员坐席未温,又图他迁。虽说官场不乏恬淡无营的君子,然在“十人竞而一人恬”的大势下,势必导致“恬者亦不能自立”[53]。 明代官场的奔竞之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之说。譬如明代吏部文选司,掌管官员的考核升黜,每次退朝之后,就会被群臣遮留,或讲升调,或讲地方,或讲起用,“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回到公署,尚不得清静,公书私书,阗户盈几,应对不暇。假如不从,则又写信切责,以为有违公论,“必欲如所求而后已”,于是时有“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之说[54]。寥寥数语,可谓切中时弊。“面皮”云云,是说官场讲人情成风;“书帕”云云,则是说官场行贿成习。二是“讲抢嚷”之嘲。明代官场士大夫的风气,显已“官邪风坏”。恬退者众诮其拙,奔竞者咸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志,“或以谄谀舐,或以贿赂求,或以奉承得”。如一官出缺,官员就各自奔趋权势之门,讲论年资体例应得之故。此即所谓的“讲”。先讲之人既已得官,那么后讲之人势必不能得缺,于是官员无不“争先趋走,抢而论之,往来频数”。此即所谓的“抢”。讲而不得,则只好“喧嚷腾谤”,即使吏部亦深感难于措处,此即所谓的“嚷”。[55] 随官场奔竞之风而来者,则是官场钻营之习。为了求得好官美差,明代官员的钻营之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随之也就有了“佛钻”的说法。如陆五台任吏部尚书时,好佛教,于是朝士无不“起而佞佛”。为此,有人作诗加以揭示,云:“谈经不为天花坠,说法惟求太宰知。”此即所谓的“佛钻”[56]。更有甚者,在明代的官场,形成了一股“攫”之风,其实就是抢官成习。如明人赵时春撰有《攫说》一文,其中有云:“子不闻士之处世,如群羽之翔丛林,丛林无適主,则唯攫之,攫之力则获之多,不力则少获,不攫则不获。”[57]这是以主客设问的寓言形式,借丛林中猛禽的弱肉强食,讽刺当时官员为了攫取一己之利而不择手段。 6.官场病症之六:贪贿黩货 明代官场,纳贿受赂,公行无忌,最终导致士风大坏。明代流行一句俗语,即“无饿死进士”。其意时说,书生一旦做官,便有一种为官的气势。一旦履任,“望见便如堆积金银”[58]。为此,明人徐学谟云:“世以不要钱为痴人,故苞苴塞路。”[59]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亦说:“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60]王廷相更是直言,明代朝野,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便为营利之计;贿赂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61]。 当然,明代官场贪贿之风的形成,实与借债做官的现状大有关系。科举制度的相对公平性,使得出身贫寒的子弟得以进入仕途。然贫士做官,官俸微薄,有时甚至谒选的路费都需要向人称贷。关于此,有一则典型的事例可以证明。如张三崖谒选之时,向人称贷路费,自嘲道:“样样借人的,如贫汉种田,工本都出富翁,比及秋成,还却工本,只落得掀盘帚。我们借债做官,他日还了债,只落得一副纱帽角带。”[62]闻者均信其然。在明代官场,“京债”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足见在京谒选官员借债成风。且京债利息甚高,按照惯例,京城借贷,“利半其本”[63]。如此的高利贷,那么官员得官之后,其中的清官,当然还债之后,只是落得一副乌纱角带而已。至于其中的贪者,为了还债且享受奢华的生活,只能贪贿黩货。 明代官场贪贿之病,亦有以下两大转向:一是从偷偷纳贿受赂,到公开纳贿受赂。关于此,王廷相有所揭示,称原先的纳贿受赂,尚是“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其后纳贿受赂,则已是“公行无忌”[64]。二是纳贿受赂之数,由少至多。正如王廷相所言,起初官场亦有纳贿受赂之事,然只要“馈及百两”,人已“骇其多矣”,其后则“动称数千,或及万数矣”[65]。 三、官场病的病根与病因 究明代官场病的病根乃至病因,大抵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科举导致学仕分离,士风不振;二是用人制度的弊端,导致官员行同盗跖,心劣商贾,士风益偷;三是考察、监察制度的缺失,导致进贤、退不肖之制完全失衡;四是官俸微薄且追求享受,导致官员别开径窦。 1.科举导致学仕两分 科举选士制度的出现,固然使人才登进趋于相对的公平,但亦不免使读书士子陷入俗学的境地,读书治学目的不再端正。自宋以后,民间流行《劝学文》,以俗诗劝世,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言越发俚俗,见识更趋鄙陋。于是,士子自束发读书之时,所接受的教诲,不过所谓的“千钟粟、黄金屋”一类话头,所以一旦服官,即以追求个人的欲望为目的,“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66]。换言之,科举导致明代士子读书治学,仅仅是“为利而已”[67]。 自科举之学兴盛之后,导致治学与出仕歧为两橛。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学与仕可以合为一体。反观科举风气下的士子,无不以“得第”作为“士之终”,而以“服官”作为“学之始”。科举士子,无论贤者还是不肖,一旦由科目登进,那么终身可以无营,而显荣可以立望,士子亦称“吾事毕矣”,此即所谓的“士之终”。然佔毕之事,不可以莅官;偶俪之词,不可以临民。士子高中科举,出仕做官,犹如刚刚入学,此即所谓的“学之始”。由于没有预养学术根柢,且乏道德修养,一旦进入官场,其结果则是“柔者巽懦而不立,而刚者又好愎而自用;佞者淟涊以自谋,而直者矫激而忘物;宽者废弛而自纵,而严者凌谇尽察而无所容”[68]。 2.用人制度的弊端 明初人才登进之制,其途非一,其中最为重要者,即所谓的“三途并用”。当然,明初所谓的三途并用,亦有一个主次之分,即“荐举为重,贡举次之,科举为轻”。即使在科举一途中,进士、举人之分,尚未明显。举人出身之人,同样可以登八座甚至成为名臣。 然自明代中期以后,人才登进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亦即转而变为“科举为重,贡举次之,荐举不行”。这是从不拘资格向专求资格的转变。于是,世俗之情,无不以中进士为荣。即使中了举人,只要“未第于南宫”,“儽然犹诸生也”[69]。随后,官场开始流行“选贡瘟、举人瘴”之说,其意是说选贡出身的官员,其前途如同得了瘟病,没有不死之理;至于举人出身的官员,其前途则犹如得了瘴病,尚有死与不死之别。[70]事实确乎如此。那些选贡出身之人,只能出任“末职”。这些微末之职,在京城候选尚颇费时日,限于财力,其中很多候选者只能从事裁缝这一职业度日。[71] 照理说来,无论是委任官员,还是责成官员,理当论其才能与政绩,不当问其是否进士出身。然在明代的官场,无论是官员选拔,还是官员考成,重甲科、轻贡举已成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以官员荐举为例,甲科进士出身的地方官员,固然不乏砥砺名节、志期远大之人,然贪肆不检之人,亦往往有之,“率以过小见宥”。反观举人、贡生出身的地方官员,固然多为日暮穷途、甘心丧气之辈,然奋励自立之人,并不仅见,却“每以限数见遗”[72]。且不说贡途,即使同为科目出身,进士、举人亦大有差别。凡是进士出身的官员,则“众向之,甚至以罪为功”;而举人出身的官员,则“众薄之,甚至以功为罪”。至如像京城堂官一类的要职,几乎已经成为进士出身官员的专职,举人出身者再也很难觊觎。[73] 此外,明代中期以后纳粟入监制度的实施,非但难以对用人制度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更使明代官场盛行“商贾之道”。有一则记载,颇能说明问题。如有一位纳粟监生,出身富家,曾官拜余姚县县丞。因事罢归,居常怏怏不乐。叶权劝慰道:“公,白丁,以赀官八品,与明府分庭,一旦解官,家又不贫,身计已了,何不乐也?”不料这位县丞听后,以实情相告,道:“自吾营入泮宫,至上纳费金千两,意为官当得数倍。今归不勾本,虽妻子亦怨矣。”[74]以“勾本获赢”之心,出而为百姓的父母官,势必会以“商贾之道”治理政事。卖爵之弊,何所底止。 3.考察与监察制度的缺失 尽管明代具有一整套颇为完备的考察与监察之制,藉此考察并监管各级官员,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这套制度已陷入流于形式的尴尬境地。譬如明代设立巡抚、巡按之官,均以“巡”为名,其意是说天子巡狩之礼难以恢复,于是设立巡抚、巡按之官,代替自己巡行天下。而巡抚、巡按的职责,以“举刺”地方为大。然御史所至,并非尽心尽职,而是“汲汲于问其官之所自”。只要是进士出身,即使官员如何不肖,巡按御史亦必改容加以优待,甚至加以荐举,吏部则根据巡按御史的推荐而加以陟升。反之,若不是进士出身的官员,即使如何贤能,巡按御史亦并不改容加以优待,并将他们列入荐牍,吏部则根据巡按御史的考语而加以黜退。其结果则是进士出身的官员,不论如何恣睢于民上,亦难以惩治;而豪杰之士,因为不出于进士之途,只能终身俛首,再无自奋之志。[75]又如分守道、分巡道一类的官员,一般被称为“守巡道官”,同样难以担当起巡视的职责,而是苟且塞责,或者屑屑较计于传厨之间。地方官员“少不当心,辱官笞吏,口出恶声,以致极意供应,所费不赀”,甚至还接受地方官员的馈谢。[76] 明初立法,综合吏治,对于枉法受贿的官员,往往处以重治。其后稍为姑息,人心怠玩,以致廉隅磨缺,名检堕失,寝以成风,不可禁制。明代的地方巡抚、巡按大僚,仅仅将耳目委诸下属官员,且多被欺蒙。即使赃官有所败露,又以“宽纾容隐为良,曲意回护以树私恩”。所以,在巡抚、巡按对地方官员的考语或奏劾疏文中,所劾贪官不到十分之一。吏部根据这些考语或奏劾,加以惩创,轻者改调,或升王府官属;重者褫其职任,如此而已。唯有赃私狼藉,众所共愤的官员,才请旨提问,其结局最多不过是一个罢官为民。其实赃吏之愿,原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所以,即使罢官为民,他们尚能在家乡觅取良田美宅,扬扬自谓得计,而旁人也反而认为他们能居官致富,以“雄杰”目之。如此轻松的惩罚惯例,最终必然导致“效尤者,恬不为异”[77]。 4.官俸微薄且奢靡成风 无论是《明史·食货志》,还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无不认为明代官俸最薄。导致明代官俸微薄的原因,主要在于官员俸禄不是实支俸米,而是采用折色之法,先是以钞折米,后来又以布折钞,甚至还定有折银之例。官员俸禄微薄,且官场又奢靡成风,其恶果就是导致官员贪贿成风。 明初百官的俸禄,均取给于江南官田。其后令还田给禄。洪武十三年(1380),大抵已经确立了文武官禄米俸钞之数。洪武年间,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一般为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部支米。后来施行折钞,凡是一石米折钞十贯。又凡是折色俸禄,上半年给钞,下半年则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1471),户部因缺钞,于是将官俸折布,每布一匹,折钞二百贯。当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已,那么米一石折钞十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文钱。布一匹亦仅仅值钱二三百文,那么折米二十石,一石米仅值十四五文钱。 明代官俸包括两部分,即“本色”与“折色”。其中本色又分为三部分,分别为“月米”“折绢米”与“折银米”。凡是月米,不问官之大小,都是一石。折绢之俸,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之俸,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这显然比原先以布折钞稍优。其折色亦有两种,分别为“本色钞”与“绢布折钞”。本色钞,二十贯折米一石。绢布钞,绢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官员,本色仅占俸禄总数的十分之三,递增之从九品,本色占俸禄总数的十分之七。[78] 尽管官员俸禄微薄,官场却是奢靡成风。这种官场崇尚奢靡之风,尽管源自那些“贵公子”,然其影响已经及于普通家庭出身的士子,以致一中进士,便学奢侈。如隆庆二年(1568)科的进士,大抵还只是一人雇佣一个皂隶,间有巨室贵介公子,则雇二三个皂隶。至隆庆五年、万历二年(1574)两科,则新科进士无不两位皂隶带马跟随,且底下家人众多。有一位进士,好制衣服,甚至不惜花费三四百两银子。[79] 那么,如何维持富贵荣华的生活?其结果则不能不“别开径窦”[80]。所谓别开径窦,其实就是另找维持奢靡生活的路子,对于官员而言,就是贪污受贿。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法教不施而风俗苟简”所致。[81]就人心而言,原本至公至明,尘埃不滓。一旦为利欲所诱,就会蒙蔽昏昧。对于那些贪官来说,当然知道民冤当雪的道理,但一旦念及“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御服之华,玩好之饰,广仆从以耀闾里,置阡陌以子孙”,就不免“浚民肝脑,剥民脂膏,朝通百镒,则夕蒙百镒之利,夜纳千金,则且受千金之赐,百计诛求,多方鞭扑,惟恐私橐之不克,民财之不罄”[82]。 四、官场病的应对与治疗 面对积弊日深的官场病态,明代的士大夫群体出现了以下两分的应对之法:一则消极逃避,视官场为“活地狱”。出仕做官,为官清廉固然值得称道,且是士人的美节,而为官“耐烦”看似平平之语,却更显重要。耐烦既是做官的第一要务,也是众善之所集。正是因为不耐于烦,一些官员才将官场视为“活地狱”,面对官场的诸多病态,采取一种消极应对的态度。二则积极应对,且提出诸多的治疗之方。治疗官场积弊,犹如治病。在积极应对官场疾病的同时,明代的一些士大夫纷纷提出治疗官场病态之方。细加罗列,大抵有以下几种: 1.心理治疗:正心诚意 正心诚意之说,原本是儒家古老的话语。在明代的士大夫看来,官场病的形成乃至流行,实则源于内心之病,即多了自私自利之心,少了公己公人之心;多了富贵好欲之心,少了清心寡欲之心。 首先,若欲正心诚意,需要去除心中之“伪”。所谓“伪”,并非限于言行之间。即使实心为民,中间搀杂一丝让人感恩戴德之心,便是“伪”;实心为善,中间羼杂一念求知之心,便是“伪”;从道理上讲该做十分,只争一毫未满足,便是“伪”;汲汲于向义,才有二三之心,便是“伪”;白昼所为皆善,而梦寐中尚有非僻之干,便是“伪”;心中仅有九分,外面做得恰像十分,便是“伪”。[83] 其次,若欲正心,必先养心,调理元气。养心之说,来源于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之说。明代的士大夫认为,君子“以讲学为先,以主敬为要,以克己为功,以自得为期”[84]。当然,养心之法,在于善于调理元气。譬如人之一身,荣卫自足,假如能“亟除其大蠹,而徐调其元气,则不惟弱可使强,而调之既久,延长之道固在斯矣”[85]。治理官场之病亦然。 2.立志修身:行为实践 若是落实到行为实践上,明代士大夫治疗官场病之方,大多将视点集中于个人的立志修身之上。做官与读书并不矛盾。商辂云:“此生不学,此日闲过;此身一败,君子之三惜。”[86]何乔新云:“一日不读书,便觉于政事有碍。”[87]当然,读书为学,其目的在于“自检”,即检束自己之心,更是为了“容人”,即容得下他人的不同意见;反之,“检人则隘”,“自容则拙”[88]。 在明代的官署中,通常设有戒石与座右铭,既是对为官者的警醒,同时亦督促官员立志修身。在明代府州县衙门的甬道上,大多立有一石,用亭子覆盖,并在亭前镌刻“戒石”两个大字。石头背面,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按照通行的说法,戒石之文,始由蜀主孟昶所作,且其文尚多,共有二十四句。入宋以后,宋太宗删繁取简,摘取其中的十六字,颁行天下。至宋高宗绍兴年间,又以黄庭坚所书铭文,命州县长吏刻铭座右。至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浙西廉司移治钱塘县,参政徐容斋将其铭文修改,定为“天有昭鉴,国有民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十六字。②此外,明代浙江温州府的官署中,尚保留着十六字的座右铭,其铭文为:“净洗眼睛,紧缚肚皮,硬竖脊梁,牢立脚跟。”据史载,此铭文是由元代浙江廉访副使臧氏所作。其后,董师谦对这十六字座右铭每句加了赞语,进而发明其中的刚介特立之意。[89] 由此可见,通过戒石、座右铭等形式强调官德,进而促使官员立身修己,这是自五代以后惩治官场病的重要方式,有些铭文甚至沿袭至明而不改。在继承前代戒石、座右铭的同时,明代士大夫尚通过衙署对联、榻铭等形式,强调官德,纠正官场病态。如胡世宁曾自署云:“瞒人之事勿为,害人之心勿存,有利于国之事,虽死不避。”[90]嘉靖年间,布政司参议钱蝶可写下一副署联,下令所属衙门张贴,其联云:“宽一分,民受一分,见祐鬼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91]吕坤在任职山西按察司的时候,新置一榻,并在榻上刻下铭文,左边云:“尔酣余梦,得无有宵征露宿者乎?尔炙重衾,得无有抱肩裂肤者乎?古之人卧八埏于襁褓,置万姓于衽席,而后爽然得一夕之安。呜呼!古之人亦人也夫?古之民亦民也夫!”右边云:“独室不触欲,君子所以养精;独处不交言,君子所以养气;独魂不着碍,君子所以养神;独寝不愧衾,君子所以养德。”[92]通过“养精”“养气”“养神”“养德”之类的个人修养,其终极的目的在于关注民生。 3.名教匡正:礼制约束 明代官场病的盛行,究其病因,还是因为风衰义缺之故。如何扭转官场病态之风,明末清初诸如顾炎武、张履祥之类的学者,痛定思痛,深感必须借助名教加以匡正,进而以礼制约束官员的行为。 “名教”云云,或称“名节”,或称“功名”。顾炎武认为,纠正官场弊风,使天下趋于大治,唯有“名可以胜之”。在崇尚名教的风气之下,尽管不无一二矫伪之徒,但还是胜过“肆然而为利者”。换言之,名教即使不能让天下之人都“以义为利”,但还是可以让他们“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但终究可以挽救“积湾之俗”[93]。张履祥亦认为,古人行己有耻,能有所不为,所以不必看重名节,也能做到“大德多不逾闲”。时至明代,廉耻道丧,士人无所不为,就“不得不重名节”[94]。 进而言之,礼义是治人的大法,廉耻是立人的大节。若是不廉,则会无所不取;若是不耻,则会无所不为。顾炎武认为,在礼义廉耻四维之中,“耻”最为重要。究其原因,人之不廉,而后至于悖礼犯义,均源出于“无耻”。所以,士大夫之“无耻”,自然就是一种“国耻”[95]。可见,唯有行己有耻,方可扭转官场风气。 4.神道威慑:宗教警示 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通常是“人治”与“神治”趋于合一。譬如自古以来的循吏名宦,在上任之日,通常有一道“矢诸天日,盟诸鬼神”的程序,并在誓言中,立志让自己“不惑于奸吏,不夺于妻子,不沮于权贵”,而且能够守之终身,以成就正大高明的事业。[96]这种官员莅任时的矢盟之举,其实就是神治意识。官场病态一旦形成,为了治疗其病,除了制度建设之外,尚须借助神道的力量,通过神道之威慑,因果之恫吓,进而让“公门好修行”之说成为官场的一种共识。 在神道设教的过程中,明代官场最为流行的就是《当官功过格》的流行及其对官员的警示。所谓的《当官功过格》,其实就是在晚明官场风行一时的《为官功过格》,由袁黄编纂而成。在此之前,功过格一类的善书,比较有名的是《太微仙君功过格》。名僧莲池大师在此基础上加以增定,编成《自知录》一书,流传甚广。而袁黄《为官功过格》的编成乃至流行于官场,其最大的功效在于让为官者明白如下的道理,即一笔可以立判生死,一言可召来灾祥,一念可分出寒暖。俗语云:“当官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所言亦是相同的道理。换言之,“以之种德,则进贤即九品莲台之阶级;以之酿恶,则进贤即三途苦趣之津梁”[97]。 明人陈继儒云:“当官若不行方便,做甚么?公门里面好修行,凶甚么?”[98]此语前半句,就是演绎功过格之义,后半句则倡导公门修行的理念,即藉因果之说而恫吓官员不再为恶。那么,公门中好修行之说,其义究竟如何?这可以从明末较为流行的善书即颜茂猷所著《迪吉录》一书中得到很好的解释。[99]所谓的公门中好修行之说,就是通过因果报应之说,让官员在衙门中行善积德。 5.制度建设:修举实政 任何制度性的建设,大多均有针对性,且多为有的放矢。细加罗列,大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修举实政,综合名实,进而使“巧宦者罔售其诈,而举职者莫掩其真”[100]。这就需要重振衙门纪纲。若是官员因循苟且,萎靡不振,那么“吏胥将纵其奸,小民均受其害”。反之,纪纲一定,则衙门严肃,吏卒敬畏,公事容易办集。[101]针对官员规避边方任职之弊,则通过确立“减俸”“优擢”之例加以解决。[102]一旦出任边地官员有“减俸之例”与“考选优擢之荣”,那么官员就会争思奋厉于功名之路,不再择地而蹈,规避不前。 二是通过立法解决官员贪污问题。明代姑息之政,甚至超过宋世。譬如败军之将,尚可免死;赃吏贪赃巨万,仅被处于罢官。有鉴于赃吏仅处罢官,而不追赃,最终导致贪官污吏“掉臂而乐去”。陈以勤主张,对于那些贪赃官员,不但要处以罢官,而且要将赃私如数追出助边,“轻者追完放归,重者仍依律间断,即撄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103]。换言之,通过法律重典或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而澄清士风。 结束语 明代官场生态的变化乃至官场病的形成,固然其病根不一,然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人心趋变所致。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念,一家仁,则一国兴仁;一家让,则一国兴让;人人亲长,则天下太平。可见,明代“世界之坏”,乃至官场病态的形成,不过是“人心为之”。明代中期以后的人心,一向不良于行且不听父兄教诲者固不必言,即使那些号称礼义之家、诗书之子,也是不亲不逊之极,满腔恣睢,百事乖谬,比比皆是。人心一坏,势必导致为官本义的沦丧,官员不再讲究风节。可见,士人风节,关乎居官之德,只有保守名节,将此言铭记在心,且付诸实践,方可不易官守,更不会趋炎附势。 为官之要,在于克终善后。如何克终善后,则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名实、忧乐、义利、进退、己人之间的关系。为官的名实之辨,其要在于官员不可自鬻。为官一任,造福地方,令百姓享受实惠,才是本分之义,而不在虚誉美名。忧乐之辨,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先忧后乐。士人出仕做官,有了职位,自然也有相应的责任;有了责任,自然会操心忧虑。可见,任重则责重,责重则忧深。官员应以责为忧,且在忧虑之中包含着官位之乐。若是专以官位为乐,则不过苟窃其位而已。义利二者,势不并处。义亲则利疏,利近则义远。为官一方,自当成为百姓的表率。若是专务于利,必然会聚怨纳侮,反而不若市井小人。换言之区分公私,这是最为重要的为官准则。义命之辨,关乎进退。按照儒家的观点,君子必须以义处命,而不是以命害义。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乐则行之,忧则违之,根本不为命所左右。官员一旦致仕,多见其怏怏不乐,反而为识者所笑。其实,宦途犹如筵席,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可见,知退比知进为愈。己人之辨,则又关系到官德。为官者当求进于己,而不可求进于人。为官之人,不当以富贵利达为心,而应以行道为职责。若是道不行,即使富贵利达,亦是士人之耻,不以为荣。 注释: ①钮琇:《觚賸》卷7《粤觚》上《五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按:此文亦为清人陈宏谋所辑《从政遗规》卷上《常言》所引,仅个别文字稍异。参见《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册,第233页。本文后引《官箴书集成》均为此版本,不另标注。 ②关于戒铭的记载及其考证,可分别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18《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14页;梁章钜:《浪迹续谈》卷1《戒石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4-255页;郑端:《政学录》卷3《戒石铭》,《官箴书集成》第2册,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