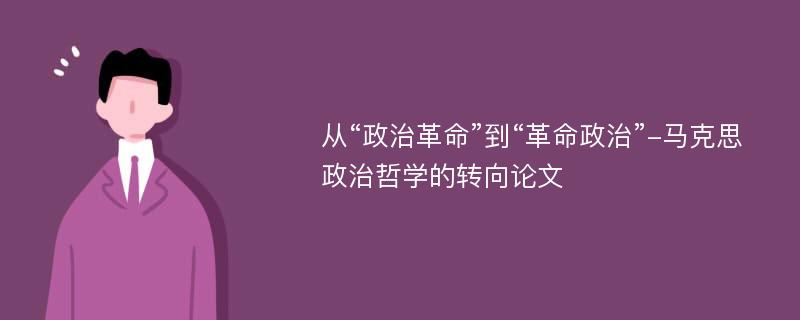
从“政治革命”到“革命政治”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转向
白 刚
摘 要 近代资产阶级以“自由”和“平等”为旗帜而发动的“政治革命”,虽然推翻了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神圣形象”的统治,但它只是使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治的”解放和“形式的”自由,广大无产阶级依然受“抽象”——“非神圣形象”的统治,它还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只是市民社会暂时的“政治平衡器”。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挖掘和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背后深刻的经济学根源,实现了对政治革命之“政治经济学根基”的解剖和批判。在此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张从“政治革命”转向“革命政治”,通过无产阶级的联合劳动,消灭私有制而解放资产阶级旧社会所孕育的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因素,最终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和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实体性自由”,从而完成“最高级自由革命”。
关键词 政治革命;革命政治;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转向
马克思作为骨子里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且在漫长的政治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提出的政治哲学虽然表现为“政治性”“规范性”和“革命性”等不同进路[1],但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还是一种“革命性”进路。马克思既很好地继承了近代启蒙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追求自由解放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传统,又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和转变——从单纯的“政治解放”转向了普遍的“人的解放”,即实现了政治哲学从“政治革命”到“革命政治”的根本转向,从而开辟了一条政治哲学发展的“革命政治”新道路。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太阳报》的记者约翰·斯温顿早在马克思生前就采访他并撰文指出:马克思“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强大的作用”[2](P685)。
一、政治革命:市民社会的“政治平衡器”
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的最为标志性事件,就是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这一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却是由启蒙思想家们提供的。如卢梭提出的“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康德强调的“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主张的自由是绝对理性的“自我实现”等。为此,马克思甚至称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法国大革命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为理论武器和进军旗帜,实际地推翻了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作为一种由资产阶级政权从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革命”,“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3](P441)。由此可见,专治特权被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取消了,它消灭了市民社会所属的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统治的单纯的“专制性质”和“宗教灵光”,使资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权和政治自由。所以,政治革命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甚至是从一切普遍内容的假象中获得解放。在此意义上,政治革命也就是市民社会的革命,这一革命虽不是普遍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却使资产阶级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他并没有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财产自由。他并没有从行业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行业自由。”[3](P442)也就是说,政治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消灭宗教信仰和财产权,却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宗教自由和财产自由。“根本而言,政治革命是已经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政治权力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财产关系的法律改造。”[4](P50)所以说,在政治解放的意义上,这一革命确实确立了卢梭所谓的“人生而自由”的相关政治权利。对此,黑格尔曾为之欢呼,称法国大革命为“壮丽的日出”,甚至种下一棵自由树来作纪念。而对这一政治革命的巨大解放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P402-403)可以说,正是在自由、平等等政治思想的宣传和鼓动下,以启蒙思想引导的“政治革命”团结和组织了市民社会的各个阶层,一起反抗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从而成为市民社会的“政治平衡器”——“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P402)。
作为市民社会的“政治平衡器”,政治革命对于突破封建王权、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来说,毫无疑问是人类解放迈出的一大步:“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3](P429)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虽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但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它却是资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最高和“最后形式”。当然,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所实现和获得的解放,实际上只是市民社会自身的解放,或者说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还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更不是普遍的人类解放。也就是说,政治革命只是部分的或“纯政治的”市民社会的革命,它只是解放了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造成普遍的“人的”实际解放。在政治革命的意义上,市民社会仍然是普遍利己主义的领域。因此说,政治革命所推动的人类解放事业,在资产阶级时代,或者说在市民社会中达到了其最高阶段和最现实的表达。但这一市民社会的最高阶段和最现实的表达,根本上仍然囿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的自我运动中。也就是说,政治革命还只是一种观念的解放,或者说是一种观念的革命,它使人们摆脱了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统治,获得了一定的形式的自由和平等。说到底,政治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发出的“哲学通告”,它只是实现了人从人身的依附关系向对绝对性观念的普遍依附的过渡,而黑格尔却把这一过渡看作是人的“最后解放和自由的最终体现”[6](P185)。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黑格尔是想以“概念的革命”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以便使现实政治生活趋向于其普遍的理性观念,从而实现理性与现实的真正和解。但黑格尔这种极力想“通过概念超越概念”的思想革命,也只是达到了政治和自由的概念,仍然保持着政治革命的“概念的自我驯服”。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要做的“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特定的观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同抽象观念建立关系,把政治制度列为它的(观念的)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7](P19)。在此基础上,作为黑格尔的余脉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满口喊的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实际上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仍然是在追求观念的解放和精神的革命,仍然难以真正改变现实世界本身,而这也正是逐渐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不得不与之分手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革命之所以是不彻底或半截子的“革命”,主要是因为政治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是建立在市民社会普遍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基础上的。对此,马克思以小资产者和工人联合的“社会民主派”的政治主张为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5](P698)。由此可见,政治革命虽然自身涂上了迷惑人的革命色彩,但仍局限于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来缓和与协调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而不要求彻底改造和变革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两极对立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政治权力通过政治领域凌驾于市民社会(经济领域)之上,试图根据政治权力的原则组织和安排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臣服于政治权力统治之下。在此意义上,单纯的政治革命无非就是特殊东西与普遍东西之间的对立二分的最终极端化,它最终证明单纯的政治革命追求的所谓自由和平等的普遍性是虚假的,因为它表明,国家只有通过无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内容和脱离市民社会,才能实现自己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政治革命以单纯的“政治性”取代了市民社会的“丰富性”,以形式的普遍性掩盖了实质的特殊性。因此政治革命必然走向虚假性和不彻底性。
在实质性意义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也都是停留在“政治革命”的“纯政治的”意义上来面对市民社会及其改造。“空想社会主义者绞尽脑汁设计政治统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要抛弃一切政治形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接受议会制的形式。”[8](P78)在此意义上,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不自觉的合伙人,都是“政治的”自由和平等范畴的继承人,而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不仅是被封建王权剥夺的政治世界和政治关系,还有被资本权力剥夺的经济世界和经济关系。所以,只有当现实的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3](P443)。因此,政治革命绝“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9](P103),而是在对现代社会——市民社会的细致分析和解剖中,揭开政治革命的秘密和实质:政治革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5](P498)。所以,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彻底解放,人要想真正摆脱异化——“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双重统治,仅仅作为公民获得政治解放是不够的,还必须消灭政治领域与经济生活领域之间的矛盾。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了马克思解开和超越政治革命之奥秘的钥匙和关键。
作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革命政治”,它既不是康德和黑格尔所谓的“理性自由”,也不是法国大革命所谓的“政治自由”,更不是阿伦特所谓的“自由言说和行动”,而是马克思自己强调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说,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所有的范畴都终止于存在着的社会秩序,那么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的范畴则是触及这些存在着的社会秩序的否定[16](P223)。在一定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通过发现所谓的“政治自由”而达到历史的终结,马克思则是通过革命政治终结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而发现真正的“实体性自由”,也即马克思是通过否定资本主义政治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如果说,政治革命追求的是“财产的自由”,那么,革命政治追求的就是“摆脱财产的自由”。但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7](P347)。而这一共产主义行动,就是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政治”——它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7](P861)。在马克思的革命政治这里,共产主义不是推倒旧社会的一切重来,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为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革命政治之主体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9](P103)。在革命政治的意义上,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倾其一生的巨著《资本论》,就不再仅仅是“非批判的”经济学著作,而是“批判的”哲学和革命著作。《资本论》通过揭示剩余价值之谜,论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然要为争夺剩余价值而进行“阶级斗争”。正如柯尔施所言:“《资本论》整个的、贯穿于三卷中理论的论述与批判,以同样的方式最后归结为鼓动革命的阶级斗争。”[14](P109)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本论》之所以不同于和高于《国富论》《纯粹理性批判》和《法哲学原理》,就在于“这部书远离了一切超然的解释和抽象的说教,而是仅仅在具体的斗争总体性中把握概念”[18](P4)。《资本论》就是资产阶级发展与灭亡的“革命政治的辩证法”。革命政治的激情在《资本论》中一再喷薄而出——《资本论》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和共产主义的“助产婆”。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
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所有革命都仅仅转换了生产关系的内部分配,它们把生产方式与财产的控制权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但没有改变这种控制权的性质,因而没有改变生产关系本身。“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5](P170-171)。所以,马克思主张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以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活动方式代替另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活动方式,正如资产阶级革命是以雇佣劳动代替农奴劳动,共产主义革命将为一种彻底新的生产方式铺平道路。这种彻底新的生产方式消灭和超越了分工以及人类所总是了解意义上的“劳动”——异化劳动自身。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一切人都能自由自觉地联合劳动——“劳动解放”的革命政治。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一切人都将成为自由创造的个人,自由创造力才能变成人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劳动才能变成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在这个时候,“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9](P68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分析,绝不仅仅是关于劳动者的恶劣境况的悲惨故事,而是马克思革命政治的具体化。革命政治要废除的“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9](P138-139)。所以说,革命政治的最终目的与政治革命相反,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形式和口号,而是“阶级”和“政治”的根本终结和废除,这才是革命政治作为“最高级自由革命”(塔克语)的真实意义。
在马克思之前,政治革命的实质都是把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手中,但是它们却未触及它的根本弊端,即统治和剥削的权力。与基督教一样,政治革命也给人们留下了双重生命:想象的自由与现实的奴役[19](P449)。但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遭受奴役的根源并不在于政治,而在于一种允许一个阶级占有和垄断生产资料的生产制度以及私有制所引发的劳动分工。因此,除了政治革命以外,还必须有革命政治,它将通过生产社会化——无产者的联合生产而把人与公民完全联合成一体,并一劳永逸地铲除剥削和社会不平等的各种根源。也就是说,所有政治革命都是肤浅的,因为它并未触及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任何实质性的变革;而且通过这种变革,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也将立即得到变革。在此意义上,革命政治的实质不在于劳动产品怎么分配——分配权的问题,而在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所有权的问题。这其实也正是黑格尔为什么强调“财产是自由的最初.定.在”[11](P54)的原因所在。革命政治就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夺剥夺者”的行动。“剥夺剥夺者”的行动就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争夺财产权的斗争,也就是消灭私有制——“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9](P818)。可以说,马克思通过革命政治——“剥夺剥夺者”,把黑格尔的政治革命——“自由的定在”实现出来了。如果说,政治革命只是实现“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那么,革命政治的本质和存在的秘密就是瓦解“政治革命的经济基础”,宣告迄今为止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解体。为此,马克思强调:革命政治就是人民群众“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9](P140)。所以,革命政治不是“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而是“人”和“劳动”的解放——人之自由个性的实现,其最高目的是通过推翻经济生活里的支配和奴役关系而实现人之“自由的联合劳动”。在马克思的革命政治这里,自由的联合劳动最终要代替强制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9](P9)。要真正实现人之劳动的“自由联合”和解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根本。
马克思终生的政治理想,就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创造一个更高级的、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世界——共产主义。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不满意单纯的“政治革命”,而必然转向“革命政治”——“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实质所在。对此,作为马克思一生最亲密、最伟大的战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盖棺定论地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其实,早在回答小女儿爱琳娜的提问“什么是幸福”时,马克思就回答:斗争!而到了晚年,在回答太阳报记者约翰·斯温顿的提问“什么是存在”时,马克思依然深沉而庄重地回答:斗争!对此,太阳报记者感叹:斗争是马克思“生活的规律”[2](P688)。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一生就是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革命和斗争的一生,“政治革命”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序幕”和“开场”,“革命政治”才是其“高潮”和本质。在此意义上,美国学者塔克强调:革命观是马克思理论结构的基本原理[15](P26)。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说,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革命政治”,就是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主题和“理论轴心”。
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理论解剖和分析,无疑就是马克思最卓越的“革命实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资本运动的科学,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科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科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既是人类活动的哲学,又是工人以阶级斗争实现自身解放和自我发展的革命:通过把工人作为“劳动力”引入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8](P87),也即把政治经济学由关于物的静态科学转变成了关于人类解放的动态科学。在本质而重要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马克思的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也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就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卡尔·洛维特语),它既是解开市民社会中人的奴役与救赎之谜的钥匙,也是从“政治革命”通向“革命政治”的桥梁。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发展不均衡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阶段,城乡发展不均衡是由生产力发展不足所造成的。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采取适当的方法是能够实现城乡融合和同步发展的。
三、革命政治:无产阶级的“最高级自由革命”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既明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政治革命之后个人现在依然受“抽象”(资本)统治的现实,又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交换过程中所体现的自由和平等的“形式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性”:“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12](P362)在马克思看来,奠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政治革命所获得的自由和平等——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天生的平等派”,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义。也就是说,政治革命只是实现了“平等地对待不平等”,这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平等。纯粹的或单一的政治革命并没有也不能消除实际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都无法在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正确理解资本与劳动的不等价交换关系,也即无法解释“不平等是如何在市场的平等之外产生的”。也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者之所以寸步难行,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的“囚徒”。在无产阶级第一次专政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修订的“共同章程”中就明确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资产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和一切精神沉沦、社会贫困以及政治依附的基础;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因而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经济解放”这一“伟大的目标”[9](P171)。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只有揭示和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所制约的“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揭示出剩余价值的实质和秘密,克服拜物教而实现“经济解放”,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对此,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后的几乎所有著作中,运用经济术语来重新定义他年轻时赤诚的革命激情”[13](P51)是合适的。所以说,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的自我毁灭条件的“经济学考察”,《资本论》就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柯尔施也明确强调:“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4](P94)
本书讲述了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一个小女孩女扮男装,出外谋生以养活家人的故事。作者长久致力于女权和反战运动,作品真实、震撼又温暖。“请告诉世人我们的遭遇吧!别让世人忘记我们。”带着这样的使命,她一次次走进阿富汗,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本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先后被翻译成25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发行。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虽然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其最终结果却是“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5](P403)。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政治革命中所获得的不实际的“政治自由”被实际的“贸易自由”所取代了,也即“由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资产阶级平等和自由观,被还原成了交换关系的意识形态表达”[10](P339)。因此,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和平等,在政治经济学这里转换成了商品交换的自由和平等,也即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通过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实现出来了。这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得以可能的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P364)而恩格斯也认为:“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门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这种与物质有关的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2](P488)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高于古典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高明之处,他们都深刻看到和揭示了政治革命背后的经济根源或政治革命的经济表达。对此,恩格斯后来又特别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9](P797-798)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为什么主张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解剖市民社会的根本原因。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言:“市民社会才是惊人的权力,它把人扯到它自身一边来,要求他替它工作,要求他的一切都通过它,并依赖它而活动。”[11](P241)在此意义上,政治革命既有其鲜明的“政治权力”,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市民社会,而这一基础正是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承认而斗争”的基本前提。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经济学(物质)赋形”。由此决定,革命政治必胜的信心,不是取决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关于自由、平等的观念,而是不可抗拒的可以感触到的人与物(商品、货币、资本)之间颠倒关系的“经济事实”。在这一意义上,阿伦特批评马克思的革命政治因关注“生存”(幸福)而忽视了“政治”(自由),实际上是非常短视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革命,并不仅仅是在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和纠正错误论断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在更广泛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上的批判,即辩证地扬弃一门实质上是市民社会理论的科学,而基本意图则是克服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身——将自由落到实处。马克思的革命政治抓住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话柄”:自由和平等不应当仅是形式地在政治(国家)领域中实行,它应当还是具体的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实行。也因此,马克思才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5](P140)。
如果说,政治革命的最大成就和最大进步意义在于突破了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统治,即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使人——主要是资产阶级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但在做完这一步之后,“革命”并没有万事大吉,而是刚刚开始,它还要深入政治革命的背后,挖掘政治革命的世俗基础——市民社会,进一步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对此,马克思以批评费尔巴哈仅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为例进行了深刻揭示:费尔巴哈“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5](P138)。而费尔巴哈(包括一切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不能和无法完成的任务,正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完成的。
Spatial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earch on a New Foundation Structure of Offshore Wind Power WANG Tingting,SU Liyuan,LU Shengjun(1)
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形式性的政治自由”,马克思只是“批判的承认”。他认为,只有在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治中,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实体性的自由”。“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5](P862-863)由此可见,通过“剥夺剥夺者”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17](P872),其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也即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实际展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通过“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政治,在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的政治革命所造成的实践和理论解释盲区的地方,开辟了一条人之自由解放的新道路。
2018年,《草原与草坪》承蒙以下审稿专家认真审阅稿件,付出辛勤工作,使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此,编辑部向为我刊审理稿件的专家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您愿意挤出宝贵的时间,对我们的稿件给予悉心指导! 祝各位审稿专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说到底,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虽然都具有“政治革命”的思想倾向和理论诉求,他们的倾向和诉求甚至在形式上使“政治革命”显得光彩而成了时髦的东西,并因此而深刻影响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马克思。但由于他们共同的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和泛逻辑主义,致使在他们的“政治革命”主张中,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观念”变换成了革命的主体,“政治革命”变成了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最终,他们也都变成了资产阶级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和同盟军。而马克思却通过深入“政治经济学”中对市民社会釜底抽薪式的解剖,彻底瓦解了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的“政治革命”的世俗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打破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平衡器”,既终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历史性现实,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超历史性神话,因而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双重自我异化。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突破了“政治革命”的“观念论牢笼”,才真正成为超越“政治革命”的“革命政治”,走上了“通向自由之途”。所以,革命政治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新革命的开始——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参考文献
[1]李佃来.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三种进路.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张东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4]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5]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张英魁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9]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From “Political Revolution”to “Revolutionary Politics”A Transition of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Bai Gang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political revolution”launched by the modern bourgeoisie with the banner of“freedom”and “equality”did not bring about universal“human”liberation and freedom,but was a temporary “political balancer”of civil society.It only made the bourgeoisie possessing property acquire “political”liberation and“formal”freedom,but the majority of the proletariat was still ruled by the “abstract”-“non-sacred image”,although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overthrew the rule of“sacred image”which represented religious theocracy and feudal monarchy.Through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arx deeply explored and revealed the profound economic roots behind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revolution,and successfully analyzed and criticized the“political economic foundation”of“political revolution”.In this sense,“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s the“history of redemption”in the language of national economics.It is on the basis of“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that Marx advocated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tical revolution”to “revolutionary politics”,to liberate the factor of communist new society originating from old bourgeois society,through the joint labor of the proletariat,and the elimina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In the end,“political revolution”could complete the “most advanced freedom revolution”,through the liberation of universal“human”and the“physical freedom”of full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dom and personality.
Key words political revolution;revolutionary politics;civil society;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 D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5-006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ZX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20003)
DOI: 10.14086/j.cnki.wujss.2019.05.007
收稿日期 2018-12-28
作者简介 白 刚,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吉林 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 涂文迁
标签:政治革命论文; 革命政治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政治哲学转向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