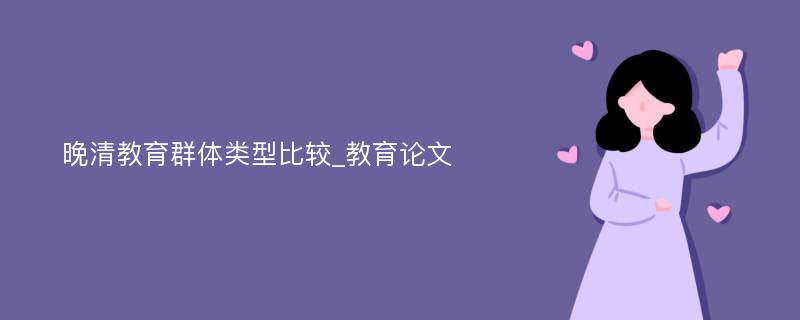
清末教育团体类型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团体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22(2004)01-0049-05
清末内忧外患的不断深重,迫使清政府加快了变革步伐。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创新在保持原有社会秩序连续性的基础之上,逐渐推动了社会变迁与政治格局的更新。新式学堂的推广与留学热潮的涌动,促使知识阶层觉醒与分化。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使了各种社会团体的出现,教育团体便是其典型。根据有关教育会的两个部颁章程,清末教育团体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1906年定章颁布以前成立的民间教育团体;定章颁布以后的地方教育会和1911年的中央教育会。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清末教育团体类型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具有代表性的著述主要有:文[1]对教育会的发展状况作过统计,文[2]对发展过程作了详尽的论述,文[3]对清末中央教育会成立的前后经过及其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的作用与影响作了详尽论述。有关清末教育会的发展概况见文[4]。本文力图管见所及,对清末教育团体类型作一初步比较,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各种类型教育团体的成立缘起
清朝前期,朝廷实行严厉的党禁政策。公开的社会团体特别是政治团体很难有立足之地,更不用说开展活动了。戊戌维新时期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全国曾出现一些社会团体,但在短暂的维新活动之后大都消于无形。1901年以后,随着清末新政的不断深入,对结社的限制逐渐放松,各种民间教育团体应运而生。
各地教育团体的出现,与新式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及日益高涨的留学热潮密不可分,是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新式学堂的建立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研究教育得失,介绍教育经验,各地热心教育者组织学会成为学界热点。中国教育会与江苏学务总会便是1906年定章颁布以前成立的民间教育团体中影响较大的两个。
中国教育会1902年春成立于上海。是年4月15日,由蔡元培、叶翰、蒋智由、王慕陶等人倡议发起,27日开会,举蔡元培为事务长,王慕陶、蒋智由等人为干事。参加者总共一百多人(注:《文明介绍》,载《中国白话报》第7期(1904年3月17日)。)。该会成立以后,一方面编辑教科书,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以《苏报》与《警钟日报》为中心,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从而隐然成为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心。据中国教育会重要骨干蒋维乔回忆,该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5](P.84)。在其影响下,浙江、江苏、江西、四川、湖南、广东等地先后成立教育会或教育研究会。
1905年10月8日,江苏一批热心教育之士汇集上海,在沪北愚园开会,商议成立江苏学会之事,是日到会者共110余人。会议决议选举张謇为会长,恽祖祁为副会长。规定凡入会者需为“发明教育或推广教育者”和“有关系学务上经济问题之能力者”(注:《纪议立江苏学会情形》,载1905年10月9日《申报》。)。12月14日,学会再次集会,会期5天,通过了《江苏学会暂定简章》,定名为“江苏学务总会”,学会宗旨为“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包括“注重师范、考求实业,提倡尚武精神,预备地方自治,联合本省学界等”(注:《江苏学会暂定简章》,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期333-336页,1905年2月。)。江苏学务总会虽非禀承官宪之意成立,但成立之后与官方的联系并不见少。学会实际上禀承官宪之意对新式学堂进行有效的指导与监督,如推广教育、争取办学经费、调解学界纠纷等。
各地教育团体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然而由于1905年学部刚刚成立,各地学务机构尚未完善,学务职责也尚未明确,“或有学务公所而无学会,或有学会而未立学务公所”。学会的成立在地方官而言则“惧其侵占官权”,在地方绅董而言则“怒其夺利”(注:《论官绅仇视学务公所学会之原因》,载1906年5月11日《申报》。),再加上归国的留学生(特别是1905年底因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后归国的大批留日学生)大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与革命学说,教员中不堪师表和不胜教职的亦大有人在,致使各地毁学风潮时有所闻(关于清末新政期间的毁学风潮将另文详述)。为规范全国各地教育会的活动,1906年7月学部颁行了《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折》,规定各地教育会只成立或保留一所,地方教育会取得了法定地位。自此以后,各地原来教育社团纷纷遵照定章,在省城的改称教育总会,在各府、厅、州、县的改称教育会。同时为规范各地僧侣开办学堂和成立僧教育团体,同年底,学部核议要求各地佛教学务公所改称为僧教育会,并对“有藉学堂经营别项事业或援引外国僧徒依托保护妨害国权者,由督学局及各处提学司查办,以杜弊端”(注:《宗教各省教务汇志》,载《东方杂志》第3年第12期57页,1907年2月。)。
早在学部成立之初就曾有仿照日本政制设立高等教育会议的构想(注:《奏定学部官制暨归并国子监改定事宜折》,载《学部奏咨辑要》卷一,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编,宣统元年(1909年)。)
,只因学部各部丞反对,此事一直拖延下来。1911年6月,面对全国各地教育会日益活跃的局面,再加上宪政期限日益临近,而要达到1916年全国识字率达总人口5%的任务非常艰巨,迅速普及中小学教育已成迫在眉睫之势。学部召集全国教育界名流共同研究解决困挠宪政的教育普及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11年6月,学部向清廷奏请设立中央教育会,其目的便是在于解决与宪政紧密相连的教育普及与发展问题。1911年7月15日,中央教育会在学部编订名词馆正式开幕,出席会议者有学部各司厅官员和来自全国各地教育界代表共150多人。中央教育会作为晚清惟一一次官方举办的教育会议,对于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与教育、官府与民间意见起了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决策的民主性。会议期间通过了呈请学部施行议案9件,特别是停止毕业奖励案的通过如时评所说“实教育上一大关键。此案实行,则教育上种种窒碍,可消灭其大半矣”[6]。虽然由于清廷不久以后垮台而议案大多未能得以实施,但其社会影响却甚为深远。
二、人员组成与研究范围
在1906年定章颁布以前各地组织和参加教育团体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从参与的人员构成来看,此一阶段的教育团体多由地方上热心学务之人组织发起,虽然与官方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多为商界或教育界人士。民间教育团体在其发展初期还吸收一部分学生入会。中国教育会成立之初人数甚少,只是到了1903年因南洋公学学生退学引发全国性的学潮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为安置退学学生,中国教育会创办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学生皆入会为会员”[5]。江苏学务总会成立之初章程便规定了会员入会资格除了与学务有关和扶助学务的绅士外,兴办工商实业著有成效者亦准入会,这明显反映了新兴工商阶层人士要求积极推进学务的愿望,同时吸纳他们入会也可使总会在经济上无多少后顾之忧。
1906年定章颁布以后,对各地教育会会员的资格要求作了一些限制,如“现为学堂之学生不得为会员”。另外,章程中还规定了“凡学堂曾经黜退之学生及游学外国因事开除之学生均不得为会员,尤不得自与发起之列”(注:《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载《学部奏咨辑要》卷一,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编,宣统元年(1909年)。),则明显有限制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开除回籍的学生入会的意图。地方教育会会员中人数最多的当为各级学堂教员,但在其中起影响作用的则是各类学堂监督与各界社会名流。社会名流在教育会中的作用尤其活跃,传统功名取得者与新式学堂毕业生及回国留学生占据了社会名流的相当比重,江苏教育总会中的张謇、王同愈、唐文治等人是前一类型的代表,而雷奋、孟森、黄炎培等人则是后一类人物的典型。新旧两派人物关系的是否协调影响着教育会的发展。一般看来,传统功名取得者多能利用其本身的声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而新派人物则利用对学务的精通来推进教育原理的研究与学务规划的进步。江苏教育总会是新旧两派合作非常出色的典型。
中央教育会会员多出于学部指派。从部颁章程中可以看出,职官类占据了绝对比重,而真正属于教育家者只有各省教育总会会长、副会长,各省两级师范及中学堂之监督教员、两等小学堂长以及学部酌派著有学识或富于教育经验者30人(注:《学部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并拟具章程折并章程》,载《教育杂志》第3年第6期67-69页,1911年8月。),即便上述会员中亦有一些职官充斥其中。
三种类型的教育会在研究学理的范围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教育会成立之初,人员稀少,经费困难,于是决定“暂从文字方面鼓吹,实行办学,尚未有具体计划”。1903年南洋公学会退学引发退学潮后,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收留退学学生,成为其走向全盛时期的一个契机。此后中国教育会除继续办理教育和研究学理外,更注重于从事革命舆论的宣传工作。至《苏报》案发,中国教育会虽未遭查禁,但会员大部分已经散去,“虽不能如上半年之公开鼓吹革命,然内地之运动革命者皆以教育会及爱国女校为秘密接洽之机关”[5]。从此会中的激进派与温和派显成两途。中国教育会未能公开活动必然会大大影响其对学理研究的力度与从事教育活动的广度。
在1906年定章颁布之前,各地教育团体的研究范围可谓是五花八门。虽然成立教育团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推进本地学务,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地方事务,如1903年由黄炎培、李叔同等人发起成立的沪学会则以集议地方自治为重点,在1905年9月的年会上除了集议有关地方学务事项外,还包括了本省铁路、清查户口以及招集游民创设工院等有关地方事务(注:《沪学会提议要件》,载1905年9月4日《申报》。)。
江苏学务总会成立以后,纯以研究学务得失,办理地方学务规划为目的。1906年定章规定地方教育会具有补助教育行政的职能,其中心内容仍围绕地方学务进行。教育方法的改进、教育宗旨的确立、本地学务规划的制定等均为地方教育会研究的范围。由于地方教育会的补助教育行政的功能,故能将其学务研究的成果很快地推行下去,江苏教育总会在1909-1910年举办的单级教授练习所便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和地方教育会相比略有不同的是,1906年之后成立的僧教育会以规划地方僧办教育为主要任务。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主要有释觉先在北京和湖南,释敬安在宁波与杭州,释谛闲等在江苏,释佛源在四川,释月霞在安徽与湖北先后建立了僧教育会以及僧俗学堂。亲身参与其事的释太虚说,“那时僧教育会会长有二:出家长老、地方士绅。惟长老多无能,士绅多土劣,僧寺虽负担经费以兴学,办理多难完善”[7]。这些僧教育会的创立虽然在当时影响不大,但是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各寺僧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开始建立一种僧界的联系体制,为民国以后佛教改革的先声。
与地方教育会相比,中央教育会研究范围明显狭窄得多。早在章程制定之初,学部便将其会议范围限定在中学以下各事宜。就学部而言,召开此次大会的主旨在于解决宪政进程中的教育普及问题,特别是小学教育普及以提高居民识字率。会议中虽有些会员提出了一些希图解决教育宗旨等一系列困挠教育发展的问题议案,由于时间有限,未能引起大会的足够重视,但在会议期间各地教育家汇聚一堂,商讨新式教育振兴方法,取得的成绩也不容忽视。
三、从经费来源看与官方的关系
1906年定章颁布以前,各地教育团体组织的成立无须经过官方的同意,经费也必然由会自行解决,因此与官方的联系并不密切,甚至于有些与官方没有任何联系。中国教育会成立之初影响不大,“会员人数稀少,会费尤为竭蹶”。至1903年的春季大会上吴稚晖提议推举乌目山僧黄宗仰为会长,乃是希图通过宗仰与罗迦陵(罗迦陵女士为犹太富商哈同在上海之妾,“上年冬中国教育会发起爱国女校之时,经常费由宗仰介绍罗迦陵女士独任之”)的关系寻求经费捐助。会员中对之多不以为然,“以为宗仰为方外之人,以长教育会,不甚适当”,最终在吴稚晖的坚持下仍得以通过[5]。然而此次效果并不明显,经费支绌大大限制了中国教育会初期的发展。
江苏学务总会由民间一批热心学务之人组织成立,资金亦由民间自行筹集。不过由于会长张謇等一大批知名的民族资本家和社会名流发起,无论是在会员的招集还是在经费的筹措方面均远远优于其他一般的教育团体。总会成立之后办事机构设在上海大生纱厂帐房内(大生纱厂为会长张謇在上海大东门外创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就可以看出总会浓厚的民间色彩。
1906年地方教育会定章颁布以后,各地方教育会的设立与运作均纳入了官方的指导管理体系。与此前的教育团体相比,地方教育会的官方化色彩开始加深。首先表现在各地教育会的成立均须报请官府批准;其次便是大多数的地方教育会须从官方领取一定数额的经费。教育会虽按定章补助教育行政,然并非完全的官方机构。按照定章各会员每年缴纳6元的会费,因此官方能否给予资助或者资助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教育会能否正常开展工作。江苏教育总会改制之初虽仍按江苏学务总会旧制由务会员募集经费,但到了1907年以后,也不得不沿门托钵向各位在籍大吏乞请资助。1907年,江苏教育总会致书两江总督端方,请求官方予以补助。书中谓“总会支持两年,不轻对官场作寒酸语,盖欲使社会知自待之宜重,亦谅官场之为难也”,然经费支拙,“故謇意宜使全体感公补助教育之雅意”(注:《江苏教育总会张会长致端午帅书》,载1908年1月1日《申报》。)。1908年初,奉天提学使张鹤龄答应每季予以江苏教育总会200元补助(注:《奉天张提学使致江苏教育总会函》载1908年2月21日《申报》。)。同年6月,江督端方答应了总会的请求于江南财政局每季拨款1000元以资补助(注:《江督等奏拨江苏教育总会经费片》,载1908年5月24日《申报》。)。这些补助拨款的到位使总会经费紧张状况得到了一定的程序上的缓解。湖南教育总会成立于1907年冬,但成立后既无经费来源又无场地,只好临时赁屋办公。1908年5月会长谭延闿领衔呈文,请求官方补助。官方批准每月补助100元,另外拨出贡院余地数亩以作总会建筑会场之用(注:《教育总会迁移长沙》,载1908年6月5日《申报》。)。
总的看来,各省教育总会作为一省教育会的总枢,官方多能予以经费上的支持。相对而言各地府厅州县教育会的处境则艰难得多,由于有些地方官方并不热心新式教育,在各地教育会员成立之初便受到官方的种种刁难。即便是成立之后,在涉及到经费补助问题上,官方多不予支持。为此,江苏教育总会于1907年上书学部,指陈各地教育会成立之后不仅不能获得官方补助,甚至有些“地方官不晓会费为表明入公之志愿,且系会章所定,竟指为结会敛钱”,再加上各地执掌学务与执掌地方公款亡人或于学务毫无经验,至因隔阂而屡生冲突,地方教育会举步维艰,要求学部明定办法以补助各地方州县教育会经费(《江苏教育总会呈学部文》,载1907年11月23日《申报》)。
另外,各地的僧教育会与官方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通过选派地方士绅参与僧教育会的运作来实现。根据部颁章程,僧教育会会长有二,一为绅会长,一为僧会长。僧教育会的经费来源于各寺的认捐数目,如1907年浙江僧教育会成立之后规定浙江全省僧教育会预算款项为15000余元,由各寺分别认捐。认捐数额分为六等,第一等为500元,第二等为300元,第三等为150元,第四等为70元,第五等为30元,第六等为15元,各寺捐款分四季认缴(《僧教育会会议详情》,载1907年5月7日《申报》)。
与地方教育会不同,中央教育会从会议的筹备到最终召开纳入了学部的管理体系。考虑到此时学部亏空太多无法作正开销,于是便规定各地方会员旅费均由地方承担,会议经费则来源于进士馆的津贴余款14000余两,并商定此次会议举办之后所余款项留至下次中央教育会开会之用(《紧要新闻》,载1911年7月24日《申报》)。会议期间学部把持会议进程,且会议之后议案采择之权完全在学部,这一切说明中央教育会至多算是学部的一个决策咨询机构,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清末教育团体的蓬勃发展表明,随着清末新政的不断发展新型社会团体开始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由于科举制度的变革与废除,传统士大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逐渐由新型的近代士绅取代(也有一部分传统士大夫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发生蜕变)。近代士绅组织教育团体的目的,既是为了促进教育的快速发展,也是为了使自己能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不可否认,清末新政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预备立宪的颁布,使新型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振兴与富强的希望,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而社团组织就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作为官方而言,为维护其统治,限制与规范这些社团组织也是必然。官绅双方虽然在有些方面存在矛盾,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力合作,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余论
总的看来,1906年学部定章颁布前各地教育团体为民间自发成立,以研究学理与引导学生运动为主旨,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与官方的联系并不密切。1906年定章颁布后改制的教育会因其补助教育行政的职能,与官方的联系日益频繁,且官府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地方教育会的命运(特别是在请求补助拨款这一点上)。地方教育会补助教育行政的职能表明学部希图将之纳入官方管理轨道,因此它基本上是一种半官方的教育团体。中央教育会经费来源于学部指拨,会员亦多由学部指派(除地方会员外,即便是地方会员亦已确定了入选范围),会议内容更是会前就已明定范围,很显然其基本上是一个官方机构。由于中央教育会议案最终采择权在学部,虽与地方教育会同具补助教育行政的职能,但只是学部的一个决策咨询机制,这也是后来中央教育会通过议案未能得到学部的最终完全采择通过的原因。
收稿日期:2003-04-11 修回日期:2003-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