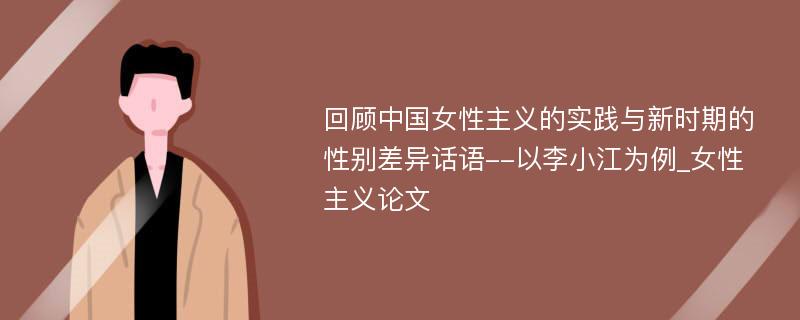
重审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和性/别差异话语——以李小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妇女(女性)学和性别研究在中美两国都开拓出了新的空间和方向。虽然中美女性主义实践处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而且双方的发展总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中美女性主义在向新领域的转向中还是表现出值得回味和需要重视的相似性,对这种相似性的探求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20世纪70~80年代经济、政治、知识和理论走向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的直接参与以及协助作用①。同时,这种相似性还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世界各地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无法完全超越各自所生成的经济、社会体系——这些体系有时具有全球性有时具有地域特征。具体地说,中美女性主义实践(feminist practices)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总体领域的转向上。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实践都开始侧重并转向文化层面、学术研究和话语领域,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别体系的独立性,逐渐同经济体系、政治国家管理和社会运动产生距离。而这种转向本身,又是同西方霸权国家(美国、英国等)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上转向新自由主义,同中国的经济开放和资本的世界流通直接相关。 综观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与西方,冷战的二度深化,左翼阵营中女性主义者同左翼男性的分歧,以及新自由主义政府管理在英美的形成,导致了本质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的产生和发展并使得女性主义在总体上从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政治运动转向文化批评,强调性别范畴的独立性。女性的压迫被本质女性主义认为是性差异特别是男性本能造成的,是跨历史的、普遍性的,不以经济生产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提高女性意识并加强女性文化生产,而非批判或推翻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等级社会体系和扩张霸权政治,被认为是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具体手段。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和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美国再次升温,主导了社会文化潮流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文革”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势力的带动下,全国上下出现经济改革浪潮,而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又亟须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构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以批判“文革”极左政治化发声,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同政治、社会和文化间的整体关系缺乏深度研究和了解,在不经意间从批判“文革”的“唯意识形态论”转向了同西方现代性接轨的意识形态的追求和建构,在突破中国传统体制的种种局限,在追求向西方看齐的一统价值观和个体主体性的过程中,规避了体制的根本差异,规避了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国际化可能带来的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并忽略了社会主义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维护社会平等(包括阶级和性别)关系和价值的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的“民间”的“妇女研究运动”③正是在这种主导社会转型潮流中创建的。具体地说,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体制性实践④,新时期的女性主义实践具有很强的文化学术特性,这是同当时政经体制的转变,同中国政府逐渐从极左政治转向市场经济,同知识界追求同西方文化思潮接轨而避开其资本主义政经体制基础直接相关。 中美在20世纪70~80年代在多重领域变革中体现出来的相似性、重叠性以及这些相似性的根源(有影响、有共生、有异质,也就是说有霸权、有同谋、有分裂)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为这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当代全球化生成的复杂性。限于篇幅和本文不同的侧重点,笔者在这里只想特别强调在重新审视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女性主义实践(本文以“民间”女性主义研究运动为主)时,我们必须首先将其置放于当时的市场、资本、政治和文化理论再次形成全球化走向的过程中,以凸显其跨国资源和影响,以及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角色和作用。可是,本文的重点是强调全球化的另一面,即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批评实践在历史上生成的复杂多质性,因为当时的带有多元并相互矛盾的观念和立场并不是全球化能简单涵盖或抹灭的,因而特别值得再梳理再研究。 尽管中美知识界在20世纪70和80年代都经历了从左翼和激进“左倾”社会运动到跨国普适(universal)理念的(再)确认的总体走向,并且知识精英开始转向文化主体和话语建构,避开批判性审视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可是这两个年代在中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历史上又同时是比较多元发展的阶段。在美国,本质女性主义和自由女性主义的走向激发了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后者质疑西方主流女性主义强调性别的单一取向并挑战现存女性主义用跨国普适视点同化世界妇女经验时体现出的中产阶级白人霸权。她们提倡运用一种交叉的方法去研究女性问题,将种族、阶级和族裔等类别直接纳入性别研究⑤。20世纪70年代受欧洲大陆批评理论影响而兴起的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亦对当时主流女性主义话语有很大冲击,尽管它们在其他方面亦有联手。后结构女性主义将性别重新界定为社会与话语的建构,直接挑战性/性别差异的自然观并质疑女性(人)是一统、跨国普适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这种后结构性别理论为考察性别在建构与具体呈现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提供了分析方法⑥。80年代还出现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它进一步拓展黑人女性主义思潮,将地缘政治等范畴引入性别与女性的研究。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深受后殖民理论的启发,对性别与权力的全球历史别有洞见,揭示了在殖民和后殖民世界里,西方帝国主义对于知识生产和身份认同所扮演的角色⑦。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政府经济改革、开放国门的方针加上文化政策的宽松,共同推动了其后十年蓬勃发展的文化与知识分子运动。这场运动在当时包含着不同背景的成员、不同历史资源和不少异质成分,但由于这场运动所体现出的一些强势共同性,特别是对“文革”的批判和对启蒙现代性和国家现代化的追求/回归,使得当时不尽相同的声音、视点和立场在主流的重建和整合下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消减甚至消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女性主义运动,从整体发展上来看具有多元性质,它的历史根源、理论资源以及发展走向都比较复杂。它不仅仅是中国各地知识女性(学者)的单方开拓,也是当时仍具官方地位的妇联的努力,更是国家经济政治总体走向转变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了西方主流(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的影响。从纵向历史角度看,即使在学者发起的“妇女研究运动”内部,虽然启蒙现代性和知识女性个体主体意识的主题比较强劲,但是社会主义性别化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阶级性别平等体制给这场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理论基础。 这也就是说,虽然20世纪70~80年代初见证了新一轮市场、资本全球化,西方价值跨国普适化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文化化,但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理论批评实践在不同场景中具有一定的多元异质性,这种历史复杂性特别要求我们重返当年的场景,重新梳理并分析女性主义实践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复杂角色,检索话语多元异质性生成的资源及其消解的原因,关注那些本来带有别样立场和别样想象的女性主义的特定实践,并批判地重估不同女性主义实践在具体地域历史中产生的具体意义和局限。 一、女性个体话语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性别差异 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正式推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由此标志了新时期的开始。在文化领域,“解放思想”极大地激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并同各种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和理论一道拉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文化知识运动。总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绝大多数是认同并拥护中国政府重新确立现代和经济发展的价值观的,所以人文知识分子于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文化以及学术空间,尽管表现出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治和后来的市场力量⑧的形态,却为政府的政治经济转型和后来的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的意识形态基础。 人道主义在新时期早期再度兴起,构成了文化知识和实践蓬勃发展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集中展现“文革”中个人和家庭,特别是亲情间的“异化”,开启了有关人性话题的思考并推进了有关人道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和哲学讨论。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不仅用以批判、否定“文革”中激进的(被定义为非人道的)、乌托邦的和过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它将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讨论和建构导向有关启蒙现代性、个人主体性、理性、科学主义与跨国普适主义(universalism)的方向。不过,在新时期初期,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包含着不同走向:一方面,人本观念开始出/复现,强调早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类自然(超验)本性、人性的普遍性价值和阶级的特殊阶段性,凸显“文革”的人性“异化”⑨;可另一方面,质疑“抽象”人性论的观点也同时存在,后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的历史社会性,认为人没有脱离或超越社会政经关系的统一本性,并指出“人道主义”普遍性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披上一件全人类的外衣⑩。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以及异化问题成为这一时期辩论的中心问题(11)。那也就是说,虽然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第一次讨论最后以一篇官方立场的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命题的文章暂时作结(12),但当时的改革开放探索本身具有一定多元异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关于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表现出对未来走向不尽相同的构想和理念基础。可是当80年代中期以后第二次有关人道主义辩论再次兴起的时候,虽然不同意见仍然存在并以学术对垒姿态出现,可是人的自然属性(包括性别)、文学/文化主体性、独立主体/启蒙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成为文化和理论领域的强劲话语(13),不仅对后来的文化和学术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也反映或者配合了当时政经改革的主流倾向的形成。 个体独立意识、文学艺术主体论和科学精神的讨论进一步加强了跨历史的普遍性价值的追寻,并同当时盛行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化心理学和文化热一道,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认知理论和文艺实践方面的文化、学术转向。80年代中后期主流知识阶层话语,包括当时对学术精神和科学治学方法的提倡,开始同当下的“经济社会”体制实践疏远,而同跨历史的深层民族意识、民族文化、跨地区的普遍性现代文明以及科学的学科建设相连,并在文化学术反思中推动新的精英、启蒙主体的形成。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性别的自然差异(跨历史和普遍性的一种人类自然性)作为一种文化认知在不同领域得到迅速发展(详见后文),而发展的结果却远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对自然的回归,而是新一轮的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性别重构。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人道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多元异质阶段并于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一个普遍性主流文化走向,新时期女性主义运动亦经历了类似的轨迹。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有关人性和人道主义以及主体性(14)的讨论构成中国知识女性进入新文化实践和新学科创建的具体话语环境。虽然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并不是个一体化的整体,各自的反思和体验并非完全一致(15),但是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主流思潮的形成并借助其冲击力拓展出一个具有个人化特征的性别话语领域:女作家为传达个体的声音和知识女性的经验开辟了新的文学空间,女导演为电影语言的个体化和主体性开创了实验性电影先河,而女学者则发起了“妇女研究运动”,第一次在社会主义中国创立了妇女学学科并建立了妇女学术主体,相对独立于官方以及官方妇女机构(中国妇联)。这个个人化的话语领域在新时期初期带有多元异质性并具有双刃剑的特色,它不仅仅体现了新时期个人主体性作为一种对“文革”批判话语的兴起,它还同时侧面质疑了新时期普遍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的性别盲点以及20世纪80年代对传统女性气质的呼唤。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化的女性文化实践在新时期初期揭示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体制实践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艺术和理论设想。中国知识女性在新时期初期建构的个体化的性别叙述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们个体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经验。张洁、张辛欣和李小江等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学者,在她们自传和个人化著述中,表述了她们作为女性在“文革”时期以及新时期的一系列带有矛盾和错位的经历。这些矛盾和错位主要表现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婚姻、家庭)之间,特别是官方妇女解放话语和日常生活中对妇女的一些固有偏见之间的差异,以及社会主义公共/官方空间里为男女平等设立的统一的革命阳刚模式(masculine model)同家庭空间里男人对女人传统职责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些相互不吻合的错位对女性提出了矛盾的要求,使她们肩负双重责任和负担,而对知识女性来说,她们除了体能上的疲惫和透支还在情感和精神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当然,现代社会男女平等过程中所遇到的社会和家庭两个空间滋生出来的矛盾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强调社会经济生产时对人类再生产不够重视,在强调经济体制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时,对家庭机制特别是脱离了传统经济模式的家庭机制所产生的性别等级作用缺乏理论洞见,这对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性别平等复杂性的认知上造成了明显的局限。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中国,因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体制化(16),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巨大变化。在文化再现领域里,中国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的主人公而且成为全国模范和榜样(17)。此外,传统父权夫权在主流文化中亦受到各种批判和讨伐。所以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包括20世纪30年后期)和50年代的女性是在世界上高度性别平等体制和公共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她们的自我认知、平等的主体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都达到历史的空前高度。但是她们(包括当时的政府)未能预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迅速有效地推翻了传统体制和性别固有等级却并没能够彻底地根除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家庭男性中心的一些理念和习俗。冷战期间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局限也变相地增加了中国妇女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双重压力。另外,社会主义制度对(女性)情感生活和需求的忽视和简单化亦造成知识女性的很大失落。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的态度,认为中国男女已经平等了,主要看的是制度保障下公共/官方空间中女性地位的变化以及公共场所中传统观念受到的抑制,没有认识到固有的传统“父权”“夫权”意识和习俗需要长时间不懈怠的制度性(经济和社会)和文化性的清肃,没有意识到持续的新习俗和多元审美建构的必要性。“文革”期间在具体政策方面对性别问题的放松和忽视,包括解散中国妇联,都反映了对性别问题的持久性缺乏深度了解。这种放松也无形中助长了一些传统习俗在家庭中以及社会上的回归。所以当成长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在社会上享有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平等的年轻知识女性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步入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时,特别是当她们当中的一部分必须面对世俗和家庭生活中对女性的传统审美和责任要求时,她们体验到了很大的冲突和落差。而新时期带有等级性自然性别差异的显现更扩展了原有的错位并加深了女性的失落。虽然这种不同空间的性别标准的错位或时差并非社会主义时期各个阶层妇女都感受到的,但它有足够的代表性,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一种独特的性别差异。 张洁最早在新时期表达了事业成功的知识女性对于传统婚姻的失望,对社会伦理压抑爱情的质疑,和对女大当嫁的社会压力的抵抗。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18)(1979)将女性对个人情感和理想爱情的需求和追求提到日程上,不仅大胆正面地描写了婚外爱情,它的最后结论,即年轻女性找不到真爱就不应结婚,对新时期乃至当今的中国社会观念和结构提出了巨大挑战。从某种角度上看,小说是从个体“自然情感”角度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对妇女解放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议题。 在她轰动一时也饱受争议的中篇小说《方舟》(19)(1982)里,张洁讲述了三位离异的单身知识女性的故事,凸显她们事业上的追求与情感婚姻生活的不幸。在这篇小说中,张洁用“性沟”这个词阐发男女两性之间种种无法超越的差异并表达了女性对历史积淀而成的男性中心的性沟(性别歧视)的批判和反抗。一方面小说扩展了马克思妇女解放观点,强调主体意识:“妇女要争得真正的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解放,还需要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中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20)。另一方面,小说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的性别阳刚模式和审美,三位女性都具有阳刚气质和对精神独立的追求,质疑新时期以来女性的“性化”或“女人化”(21)。这篇小说提出了妇女解放在体制实践之上的新的方向,但它同时又表达了对“性沟”弥合的悲观态度,预示了妇女解放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的艰难性。 张辛欣在她的短篇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22)(1980)同样集中表现了社会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女主人公所面临的事业和爱情的矛盾以及困境。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出生于50年代初期,是一位精神独立、富有才华和事业心的年轻女性,但随着阅历加深,她发现那个真正懂得、欣赏她文学作品的男人却渴望找一位气质阴柔和温存本分的女子相伴。感情上的挫折迫使女主人公反思社会上推崇的阳刚化模式,以及中国男性在私下里所坚持的传统审美标准。其间的错位和差距揭示了中国知识女性在情感上的失落和困惑。在小说结尾,女主人公别无选择地继续着自己生活方式,因为她清楚“阳刚面具”一旦戴上,就已成为了让她之所以是她的精髓。另外,她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事业。尽管如此,她仍然渴望自己能有“女人味”,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爱情和幸福。虽然独立并才华横溢,社会主义时期胸怀大志的知识女青年却常常像女主人公一样,在情感之路上遭遇种种矛盾和坎坷。《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一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性别建构的单一阳刚模式,一方面又质疑了新时期回归的“女性气质”,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里成长起来的城市女性面对事业、情感和家庭所感到的极度困惑。 李小江极其认同这些女作家在作品中再现出的女性特有的挣扎和困惑。在李小江看来,当时的女性文学关注的问题就是妇女研究和妇女学所需要探讨的问题(23)。她直接借用张洁的“性沟”来探讨人类历史上更广泛的性别问题。当被问到“你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去不断开拓当代中国的妇女学?”之类的问题时,李小江的回答特别强调来自于她身为社会主义中国女性的个人生活经历(24)。“将我逼上妇女研究道路的,不是社会,不是十年浩劫,也不是职业,而是女性的生活道路,它几乎可以看做是一件自己的私事。”(25)李小江之所以转向妇女研究,最初主要是给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寻找答案。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认同的是世界上成功人士(多为男人),看重的是独立的生活方式。但为人妻母的经历瓦解了她从前对女性和自我的认知,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她认识到女性在人类繁衍中的不同角色,体会到爱的伟大力量,特别是母子(孩子)纽带和母性奉献;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缺乏对母子情感纽带的价值确认,她又强烈感到自己被女性家庭角色所困,因为这些角色侵占了她的事业和独立人格。她努力去维持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平衡却最终发现自己身心濒于崩溃。她不禁要问为什么女性要承担双重负担(26)。“我想知道”,她说,“女人为什么活得这样艰难这样屈辱?在男女平等的时代,女人为什么仍然这样劳累这样压抑?”她还想知道,“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为什么导致‘男强女弱’的价值定格延续至今?”(27)现实的问题促使她探索“女性”,一个她当时感到一无所知的话题。 正是在这样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即中国知识女性通过她们在“文革”以及新时期阶段的个人经历和身体体验来表述传统体制下特殊的性别差异——官方男女平等制度实践和非官方空间中持续的传统习俗和性别分工,以及新时期性别等级的重新浮现——李小江开始了她作为一名妇女研究者和学者的职业生涯。20世纪80年代知识女性文化学术运动发展的这种特殊个体经验根基,对于如何审视后新时期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以及怎样理解它在具体历史中的社会意义和后来的走向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这种个体经验,虽然因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体性思潮的兴起而得以呈现,但它不同于新时期初期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普遍抽象,而是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经体制下的性别化体验。这种具体的历史、社会体验具有质疑和抗衡抽象、跨体制、跨历史的普遍性价值的潜质,是我们重审李小江20世纪80年代从本体论、科学观以及学术理论角度对女性及妇女解放所作论述时必不可少的历史观照点。 二、李小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女性文化主义 李小江是20世纪80年代妇女学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她是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位(1)修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并在此基础上发表自己女性主义理论观点的作者(1983);(2)发起官方组织以外的妇女学会(1985),提倡用一种理论框架来推动妇女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妇女学,1986)的学者;(3)创立妇女学研究中心(1987)并主编出版一套妇女研究丛书(1988)的女性主义学界带头人。80年代末,李小江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妇女研究专著,《夏娃的探索》(1988)、《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1989)、《女性审美意识探微》(1989)和《性沟》(1989),集结了她于80年代的种种思考和探索。尽管这些著作探求极为广阔的领域和不同主题,但它们的中心论述都围绕着性/性别差异。李小江因此被不少学者看做是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者(28)。此外,在90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带动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性差异成为了盈利的资本,而女性性征尤其被商品化,因此白露等学者又将李小江的立场同中国市场对性与性别差异的重构以及市场女性主义相联系(29)。 李小江所论述的性/性别差异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难道她仅仅是简单地呼吁人们去认知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别?抑或是对市场经济的性别建构太具乐观和肯定?在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文化和妇女研究中,性/性别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这些差异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李小江是怎样给自己女性主义立场做历史定位的?对未来的妇女解放她又持怎样的观念?她的著述采用了何种理论框架,她的成果为将来的性别与妇女研究创建了什么新的理论基础? (一)矛盾的理论突围:《人类进步和妇女解放》(1983) 李小江是位多产作家,因写作风格多元、融合多种体裁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但她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人类进步和妇女解放》(30)(1983)却没有在日后的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受到足够重视。其实这篇文章当年一发表就引发了论争,因为李小江在文章中批判性地修正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篇文章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妇女学的理论根基和起始脉络,对中国妇女学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李小江在其后发表的其他著作里,一再回到她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的主要观点。这篇文章不仅给上面提到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答案,帮助我们了解李小江的女性主义立场,它还为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批评,诸如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本质女性主义,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这篇文章所讨论的核心话题包括女性压迫和解放的物质、经济基础,物质生产与人类生产(生育)之间的关系,劳动的两性分工,妇女在历史上同自然、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母子关系,以及社会化。这篇文章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修正主要有三点:第一,相对于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观,李小江将妇女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勾勒和归纳出三段人类妇女历史——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和解放时代。这三个时代同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的历史既有关联又有差别:妇女的奴隶时代涵盖了马克思的奴隶和封建社会;妇女的解放时代指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三个妇女时代呼应着女性在历史上演变的三种类型:自然类型、家庭类型和社会类型。这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中,两性的发展和进化并非完全同步的。第二,李小江认为马克思的人类历史是围绕经济发展、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男性价值观来发展的,它同时是自然和女性的异化历史。虽然妇女解放必须要经过这几个阶段的历史才有可能取得,但妇女的最终的解放不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两性在社会生产中平等的实现就顺理成章的到来。妇女的最终解放需要进一步摧毁夫权中心的价值体系并建立新的文化伦理秩序。第三,家庭才是妇女进步道路上的最顽固阻力的来源。新的价值体系需要建立在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的规律性合作上:一方面实现家庭义务的社会化;另一方面明确妇女对儿童的社会义务。女性的最终解放同人类自身解放不可分割,妇女解放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社会伦理对母子关系和母性责任的认可和宣扬。 李小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主要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语境中产生的,其中新时期知识文化界关于自然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无疑对她的思考和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她还受到了西方女权运动史的影响(31),在理论的关注点上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有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论争相契合,并同70年代兴起的本质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有着一定的相似性(32)。本质女性主义在70年代初期通过批判左翼女性主义观点迅速发展成为主流,其主要观点集中并散见在当时的各种女性主义研究著作中,包括在一批80年代初中期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的著作中(33)。本质女性主义广为流传的观念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后“文革”时期的女性主义实践的具体影响还有待进一步仔细考察,但西方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历史的影响是显然的。不容忽视的是,本质女性主义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左翼男性中心实践发展出来的,但它的理念基础却同西方自由女性主义有着渊源关系(34),而在具体实践中,本质女性主义后来又同自由女性主义有着不同程度上的结合或结盟(35)。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妇女“研究运动”来说,美国70年代女性主义实践从社会、政治运动转向学院的学科建设,所谓的“妇女科学化、学科化”亦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36)。 具体地说,李小江理论同本质女性主义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她们都一定程度质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即阶级革命的成功和社会大生产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第二,她们都将性/性别或女性主义实践看做是相对独立的体系或范畴,应该同政治(国家)、经济和其他社会运动(阶级)分离(37);第三,她们挑战传统的机械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提出女性的最后解放必须建立在反男性中心的“女性文化”建设上。从历史的角度看,本质女性主义和李小江的理论在中美两个地区作为批判话语产生的时候都具有重要进步意义,因为它们都是对具体历史场景中所产生的女性主义实践问题的反思,特别是针对美国左翼阵营和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的性别问题的一种理论再思考。这种理论再思考,即使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实践中也依然存在着必要性和重要性(38)。理论上,它们都从性别文化角度挑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社会发展模式,显示性别压迫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当然,从今天的视点回顾,美国本质女性主义亦受制于或参与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知识学界的保守转向,具体体现在它从批评左翼阵营里的男性活动家的性别歧视到退出批判资本主义的整个左翼阵营,最后发展成本质(文化)女性主义,同自由女性主义形成同盟,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求生存。如此发展起来的本质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强调的独立性最终却丧失了其早先的批评锋芒,演变成一种依赖于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中产白人的跨国普适价值观的话语力量。正如继本质女性主义之后兴起的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批评的,本质女性主义对父权的单一批判,完全无视资本主义同父权制之间的互助互靠关系,从而丧失了批判资本主义性质的父权制(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各种性别分工等)的能力(39)。 李小江文章以及李小江所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运动的局限也同当时中国主流政治走向和经济文化实践相关。通观李小江的这篇文章,她对妇女历史的重构和对妇女解放的最终目的的再定义,即定义为不仅仅是社会生产中的男女平等,而必须同时是人类再生产(繁衍)中男女关系的一种基于自然分工的社会伦理,都体现了她试图从理论上开辟一条探求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的妇女问题的道路,但她的论文构架和整体论述的视点却呈现出同原来具体的语境、体验和动机相矛盾的倾向。究其成因,似乎同中国当时迫切认同西方(正常)模式,希冀同世界(西方)接轨,搁置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实践和经验直接相关。这些矛盾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文章的出发点,根据上文对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的分析,是基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部分知识女性的历史情感经历,所以本来的目的是挖掘现存理论在理解和分析公有制社会主义性别平等体制下性别关系的局限并进一步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而并不是否认或否定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体制。可是,文章的视点和结构却在现代性、个人主体意识和(社会)科学性的历史抽象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西方历史和妇女史作为了底版,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性别平等体制公正性和必要性的坚持。文章不仅没有对不同体制,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制度、性别建构和伦理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有所分析,反而让社会主义体制在文章中完全缺失。文章的历史综述都截止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社会大生产中男女的基本平等还是女权运动,似乎在无意间暗示当代世界女性主义实践走向应该回到资本主义时期并从那里开始进入新的女性文化和家庭伦理建立的新历史阶段。在别处,李小江也直接提出中国妇女解放具有“立法超前”性质,因而需要弥补西方女权所倡导并经历过的女性主体意识(40),即所谓回归到一种“正常”的轨道上。可是,这种“正常”轨道同资本主义体系间的关联性,虽然在李小江的文章中没有直接界定,却难免会引起疑问。总而言之,现存的社会主义政经体系及其男女平等制度的意义和价值被完全搁置起来。换一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中的缺失给文化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给中国同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实践接轨提供了文本条件。正是这种带有矛盾性的对所谓“正常”现代性的追寻在很大程度上妥协掉了中国历史以及后“文革”时期女性主义实践的异质性和别样构建的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逐渐强势发展起来的以西方为标准的启蒙现代性和学科科学化直接消减甚至遮蔽了当时新兴话语自身所包含的复杂的历史多元异质性,而其中被遮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作为一个制度实践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它为8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运动兴起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上文提到,李小江文章的一个重要贡献,即对人类妇女历史的不同勾勒,但这个勾勒也因现代性以及社会科学性(正常)的走向(或筛选)而演变成以西方妇女历史为底版的论述。李小江在90年代和以后的文章中都对跨国普适价值和西方女权的霸权地位有许多深刻的反省并积极提倡本土化。她曾非常尖锐地指出,作为运动的“妇女研究运动”,它的终结恰恰是因为西方女权主义全面进入中国(41)。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妇女研究运动”当初包含的中国历史特定性和异质性到90年代中期当西方性别研究全球化并全面系统进入中国以后完全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市场经济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全面发展也是另外一个,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但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妇女研究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所追寻的人道主义主体性和启蒙现代性就已经构建了一个排他的框架,开始遮蔽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并消减了“妇女研究运动”起始阶段的多元异质性。如果说美国本质女性主义在批评左翼男性的性别歧视时放弃了左翼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从而导致了本质女性主义实践上最大的历史局限,那么中国“民间”女性主义实践的局限则体现在它在揭示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解放存在的问题时不经意间放弃了对社会主义性别平等体制实践的固守和坚持。“自上而下”的“恩赐”论(42)强调女性主体意识在妇女解放中的重要性,但它遮蔽了个人主义主体性和女性主义独立性同资本主义体制和主流自由主义话语间的密切关系,从而遮蔽了任何有效的女性主义运动在历史实践中体制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当然,不同政经体制中的女性主义实践与主导政经系统的整合关系又并不相同(43)。西方个体女性意识本身并不是独立于资本主义体制和主流话语的,而是精英自由主义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极度经济私有化和社会“原子化”的组织原则,因为它们同主流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一道,极大地消解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集体运动(阶级和妇女运动)(44)。所以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用超越体制的理想主义化的女性个体主体意识来架空或否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体制化实践的重要历史意义导致了中国民间女性主义运动不仅逐渐脱离了其起始的历史动因,而且在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和一些西方中心女性主义涌入中国的现状时失去了有效的体制性和集体性的抗拒。 第二,文章中关于人类历史和女性历史发展的分析,直到资本主义时期,都基本采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视点,可在谈及当代女性主义和未来妇女解放运动的走向时,文章转向了文化伦理。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历史是由生产力向前推动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其后的社会进步则需要依靠文化伦理的作用(人为创建)。这种从历史唯物论转向文化建设论的结构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段论,这两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怎样连接,文章缺乏有效说明。文章揭示了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物质文明高度发达阶段也是自然和女性的异化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又是妇女解放的必经历程。那么,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准后,怎样才能在不需要生产力带动下开始一场性别文化革命?如果女性在人类物质发展历史中一直被深刻地异化和物化,而男性则占有主导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那么没有男性的认同和合作,女性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才能获得性别文化革命的胜利?如果男性合作或人类共同努力是妇女最终解放的前提,那么占据各种权力中心的男性在没有任何外力胁迫下,为什么会/要合作并认同女性/母性的价值观? 当然,李小江在矛盾中展现出的一种普遍意义的理论构架同西方本质女性主义历史实践还是有着本质差别。其中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于她坚持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妇女解放的历史观的一个必然部分,而不是像本质女性主义那样全盘否定和彻底放弃。在《人类进步和妇女解放》文章中,李小江强调妇女解放必须经历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历史的几个社会阶段,因而消灭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虽然不是足够的条件。换句话说,美国本质女性主义追求的是理念上回归到资本主义体系内发展文化女性主义;而李小江则试图解决的还是侧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后)体系中存在的性别文化问题,虽然跨国普适话语框架使得社会主义部分遭到很大程度的遮蔽。另外在具体分析妇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运动时,李小江非常明确地强调不同的阶级妇女——上层贵族、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妇女——面对的不同问题以及她们各自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的不同目的和起到的不同作用。虽然她注重女性主义和妇女历史的独立性,但她对阶级的关注以及她对妇女解放同人类总体解放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强调显示她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分明得益于她身处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经验。这不仅给她带来了探索问题的历史制高点和优势,也为她“修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供了物质、历史和理论基础。 (二)非异化的文化伦理突破点:性/性别差异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控诉”“文革”时期的“非人性”,在国家拨乱反正,重建秩序并且重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自然性/性别差异,作为自然人性的重要一部分,代表性地预示了以“去政治化”“科学化”和“人道主义”为标志的新启蒙时代的到来。一时间,性/性别差异话语成为开冰破土、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走向的先锋之一。 第一,性/性别差异成为政府规范新的社会角色和新的劳动分工,以及重新划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一种重要途径(45),可是对科学真理性的膜拜使得一些打着科学旗号的有关男女在生理、心理和智商等方面差异性的著述在80年代得以盛行。根据韩起澜(Emily Honic)和贺萧(Gail Hershatter)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些科学话语(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帮助建构了很多领域中的新法则,即女性弱/次/劣于男性。生物学决定一切,而更严重的是,女性的最终命运是根据男性的生理来衡量的(46)。性/性别差异成为重新规范性别等级的标准并直接同公共/私人空间、职业性别化以及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挂钩。 第二,当时的经济市场虽然还处于“无形的”的阶段,但也已开始通过“恢复”女性“天生”或“自然”性差异和性态来重构和消费性别。 第三,性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为建立精英男性中心的阳刚气质和民族振兴起到重要作用。70年代末,在中国推行贯彻了30年的性别平等之后,“阴盛阳衰”被用来描述当时的性别关系,而“阴盛阳衰”这个词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常常以自然阴阳失衡来暗示着社会和政权的秩序紊乱。男性作家和学者开始反思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由此导致公众对“真正的”男子汉——那种有独立意志,能够抵制政治不公并捍卫人民权益的男人——的缺失而悲叹。但是这种对理想化的男子汉缺失的反省,在男性知识分子的陈述和再现中常常是通过对“文革”中“异化”的批判,对自然的男性阳刚本性的呼唤来呈现的。沙叶新在剧本《寻找男子汉》(1986)里借女主角之口总结了中国当代男子汉缺失的原因:“男人的懦弱,也许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又来的一次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寻找男子汉》)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男人们”其实只是指涉中国男人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概念排除了以革命名义发起运动的(男)人和在“文革”中没有被整的(男)人。这段话还明显地暗示了“文革”等运动对“女人们”并没有造成类似的影响。的确,女人在《寻找男子汉》中不仅具有一定主动力而且是社会道德的化身,可也正是在这个作品中,女性角色被再现为一个辅助性的呼唤者,她的主要功用是要呼唤出新时期所需要的(男性)历史主体。沙叶新在《我寻找什么》中这样强调“男子汉”的历史意义:“寻找的是那本应该在我们民族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阳刚之气……为的是民族精神的更新。”(47)仿佛在浑然不觉间,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话语建构中不仅将“中国男子汉”重新定义在知识阶层(相对于以前的工农兵),而且还将男子汉的缺失归于“文革”等系列政治运动,并将“文革”后的自我重塑演绎成普遍性自然的阳刚回归,理性坚持(相对于政治运动)和民族精神的振兴。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精神的更新并不是对传统的回归,而是为了走向世界,进入一个现代化文明,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虽然80年代的各种思潮都秉承着世界化、中立的立场,可是寻求男性阳刚/理性主体、民族振兴和世界公民权是一条重要引/隐线贯穿于80年代的人道主义、启蒙主义、文学主体性、现代主义和文化寻根等运动之中。它暗示了希求通过恢复性别差异或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阳刚和阴柔——来恢复男性知识阶层地位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正当”秩序的强烈欲望。它其实揭示出新时期主流话语的性别化以及阶层化的根基。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化运动更直接体现了男性“自然”阳刚和理性反思同民族文化振兴间的隐喻关系(48)。 因为性/性别差异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多重建构中的不同出发点和目的,所以这里特别有必要将李小江的女性主义立场同其他关于性/性别差异的实践区别开来,尽管这些话语实践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也都无形间起着相互合作的作用。如上所述,以李小江为代表的80年代知识女性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性别差异,在政治和理论上至少包含如下三层意义。第一,知识女性特有的历史个体经历和反思在社会主义历史上首次得到集中的再现和表述。第二,它揭示了社会主义中国(大)部分妇女承担的双重职责:一方面在社会上无私地履行她们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的使命,一方面在家庭内部继续维持着传统角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表述了社会主义中国与性别相关的一系列历史矛盾和错位。这些矛盾错位揭示了一个在当时常被忽视的事实,即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内,在实现了公有制,在官方绝对性别平等的体制实践下和对传统价值观的激烈批判和变革中,有些历史上构成的性别差异,某些传统道德规范和日常习惯,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可以存留下来并同性别平等一起构成了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性别差异。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传统家庭中的男性中心结构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确受到了历史上最大程度的打击和制约,但并没有被根除。鉴于当时男女社会平等在理念和制度上的基本建立,这种矛盾错位推动了李小江这样的女学者开始在理论层面上批判性地重审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 《人类进步和妇女解放》,如上所述,就是李小江在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探索。在这篇文章中,李小江提出社会或历史性/性别差异(等级)和自然性/性别差异(无等级)的概念。在分析马克思历史阶段(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李小江揭示了“性沟”是怎样基于自然差异而在历史上和社会中一步步建立成等级差异并巩固下来的。她强调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是建立在自然和女性异化历史上的,是以男性为标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性别等级。她进一步指出,虽然社会性别平等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但没有转变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因此这不是妇女解放的最终目标,而只是向这个目标更迈进了一步而已。自然性差异作为一种同人类历史上被异化的、同社会性别等级相对立的概念进入了李小江的论述,成为她重构真正平等性别关系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的关于自然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对李小江的性差异理论有直接影响。当时的人本主义者就提出人类发展应该从阶级性向自然人性的回归。在80年代,李小江加入其他知识女性,探讨了女性生理差异、女性的健康以及她们特殊的心理需求和欲望。她强烈指出社会不应有意忽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因为这种忽视造成了女性的“双重负担”并损害了她们的身心健康(49)。但是李小江提出的自然性差异并不停留在自然物质范围内,它同时还包含着特定的伦理和隐喻维度,因而在政治和理论层面上表达了她对未来的女性主义的憧憬和构想。 在中国新时期阶段,李小江同屈指可数的几位女学者一道,第一次将人类文明的历史和发展认定为男性统治自然和控制女性的过程(50)。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女性先被压制成弱/次/劣于男性的性别(这种社会决定的性别差异却声称是自然差异所然),然后又被要求变成和男性一样(性别平等又要求女性克服自然性差异)(51)。同法国女性主义学者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不无相似之处,李小江在重申自然性差异的重要性时,她的目的是消除异化、消除等级秩序(夫权中心)并建构新的伦理价值(非男性中心,互相支持、和谐共处)。因为中国后“文革”时期女性主义迫切需要树立一种独立的女性主体,这种基于自然的身份似乎比传统的和现代的女性概念更有前景,因为李小江认为无论传统和现代女性身份都充斥了太多男性价值观(52)。 在自然性差异中,李小江身为母亲的个人经历使她更加看重并反思生育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这里,不同于现代早期“进步女性主义”(53),后者对生育以及女性自然性欲和性选择的强调是为了改善种族、增强国力。李小江认定自然性差异可以帮助建立一种新的情感和伦理体系,而母子关系和母亲的责任是代表和体现这个新体系价值的取向。李小江认为以男性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把等级性别秩序自然化,这种自然化的结果是通过双重异化(劳动力和妇女的客体化)过程不断巩固下来的。女性主义的目的是要“回归”真正的自然性差异(既批判社会等级性别差异自然化又质疑男女什么都一样),建构非等级的男女关系和差异,提倡互相支持、和谐共处。从另一个角度看,李小江的自然性差异也是对人类身份的物质性(拒绝彻底社会化的可能性)的一种坚持,从而也是对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性别建构理论的一种挑战。鉴于李小江对自然性差异以及女性生理的执著、对一种女性/母性天然情感及其内在平等伦理的坚持,有学者把她称之为本质主义可能也并非言过其实,但她的本质主义却来自她对人类历史和自身经历的多层次的深刻思考。她的自然性差异意图带来极端不同的新的社会伦理想象。她的自然本质主义质疑并批判企图维护男性统治(性别等级)的社会决定论。 李小江的自然性差异在政治和理论层面上产生的意义,从根本上异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和市场对性别和女性角色的重构,后者是同新的性别劳动分工、私人空间的建构以及女性的商品化密切相连的。同时,李小江的自然差还异质疑了新时期主流话语,诸如自然人性和个体主体性等的性别盲点。最后,它的母性伦理理想直接挑战8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男性阳刚气质和理性反思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李小江的自然性别差异当然也有它的局限。同自然人性一样,自然性别差异具有非历史唯物的先验性,而且其自身发展有特定的历史含义和阶级属性。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母子的理想伦理构想明显带有一定精英特色。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李小江最初是针对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问题而转向女性主义研究的。根据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体制当然是比市场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历史阶段。她关于未来的构想是以消除男女之间的权力等级(尤其是女性的客体化)的真实性差异为前提的。可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同李小江设想的新一轮女性主义运动的起点其实是有错位的。在社会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并没有注重巩固原有社会关系,而是一切以发展经济为重,因而导致在体制层面上社会性别平等的倒退。政府在社会职责方面的“撤身”从某种程度上鼓励并促进了民间社会和学术团体的兴起,也就是说民间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本身并非完全“独立”的、自下而上的,而是整个体制转向的效果之一。“女性主义运动或妇女解放的独立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神话或误区,因为它遮蔽了不同历史语境中女性主义实践同具体政治经济体系的关系,遮蔽了它所代表的特定群体的社会和政治利益。20世纪80年代所强调的民间或学术运动的独立性和责任性以及女性个体的主体意识都在无意间迎合了政府管理上减弱社会职责的走向并配合了中国体制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经济改革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露等学者将李小江的“自然性别差异”同市场商业主义以及市场女性主义挂钩就不是全然没有道理了。 中国当代的知识阶层,无论男女,在新时期初期都一致拥护政府倡导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蕴含着一定的多元异质性,所以很少有人在当时能够深刻意识到他们所积极投入的人道主义、现代化、主体性和科学真理同市场经济之间的错综关系。在他们以理想主义的姿态从跨国普适文化角度拥抱启蒙现代性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表面上同政府和市场保持着一定独立性,结果却逐渐失去了洞察自身在整体经济社会变革中的位置和作用的能力,也失掉了对快速增长的经济所造成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的清醒理解。正如一些学者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化运动后所得出的结论,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将“文革”灾难归于当时激进的理想主义,认为它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可他们自身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同样侧重文化主义的途径,直接削减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立场(54)。这也就是说,80年代的文化精英尽管否认、谴责“文革”,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背离“文革”时期文化理想主义的影响,因而对他们支持、拥护的经济改革的实际经济和社会后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新时期努力追求跨(政经)体制的跨国普适文化价值时都有意无意避开了不同体制系统的社会伦理差异。因此,指认李小江等8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主义发展以及中国女性商品化过程中无意之中起到同谋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全无道理。 的确,李小江以及其代表的新时期的女性主义研究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了一个矛盾重重的位置。一方面,她尖锐揭示了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存在性别问题,试图寻求新的理论途径重新界定和思考妇女解放,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时期的性别伦理关系。通过对历史夫权中心的社会性差异的批判,通过对在人类历史上非异化的自然性差异的坚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框架的修正,李小江为未来构想出一种无性别等级差序的基于母子关系的社会伦理。可另一方面,她又信奉启蒙现代性、科学真理性、个人主体性和经济现代化,而这些话语和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中(特别在没有坚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体制实践的状况下)都更多地用来发展市场和建立男性中心的社会等级(这也正是她在《人类进步和妇女解放》中所批判的异化女性的人类历史和价值体系),结果是更多地降低了而不是改善了中国妇女的地位,致使中国妇女整体在社会主义阶段享有的制度性男女平等以及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享有的权益,在中国全面投入市场发展之后开始迅速滑坡。 另外,李小江侧重的自然性/性别差异中的母亲和孩子的纽带性的伦理关系同她在其他场合所强调的女性的独立自我意识和个体的主体性在本体论和伦理范畴中也存在着很大矛盾:一个强调非异化的自然连带性的情感关系,一个强调异化社会中自治的理性主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定历史及其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经济上的问题)又加剧了新时期女性主义运动在时空方面的矛盾走向:是解决性别平等社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主义主体性、发展“自然”(平等)女性文化,还是回归到一种所谓正常的经济轨道上,弥补西方女权所倡导并经历过的女性个体主体性和“异化”的中产阶级女性文化?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发挥了解放思想的潜力,也行使了抑制不同地域多元异质女性主义实践的跨国普适霸权。在新时期阶段,如果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奠定了女性的跨国普适范畴的基础,如果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的“新女权”运动成为后“文革”时期女性主义实践文化化和科学化的参照,那么当中国女性主义者在下个十年内更深入地接触到各种西方(中心)女性主义理论之后,她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她们早前确认的跨国普适范畴,并且开始对她们在本土和全球语境中的作用和立场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55)。 自从《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问世以来,李小江不断努力调整自己的位置,一方面应对中国快速的、“意想不到的”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另一方面对应关于妇女解放、启蒙现代性、社会主义遗产、本土化、性别发展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多种多样且具有潜在冲突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具有特殊历史和理论意义的女性主义运动在中国主流启蒙现代性话语和经济发展的同步实践中彰显出了一段充满矛盾、悖论和纠结的历程。其早期所蕴含的多元异质性和潜在的基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基础上的另类想象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政经结构转变中被支离化和边缘化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和解放运动的历程再次显示了女性主义实践在历史上不可能独立于其所置身的政经体制(国家、全球和地区)。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主义实践在新时期所历经的种种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深刻揭示了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中所面对的复杂情境,为深入解读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女性主义实践的意义、作用和局限,为跨国女性主义实践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可贵的物质、政治和理论资源。 收稿日期:2015-09-15 注释: ①Harvey,David,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②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③这一术语是由林春在1994年提出的。见李小江:《公共空间的创造》,载《身临其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④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⑤Crenshaw,Kimberlé,"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89,1989,pp.139-167; Collins,Patricia Hill,"Gender,Black Feminism,and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88,2000,pp.41-53。 ⑥Scott,Joan W.,"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1(5),1986,pp.1055-1075。 ⑦Mohanty,Chandra Talpade,"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Ed.C.T.Mohanty,A.Russo,and L.Torres,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⑧Liu,Kang(刘康),"Subjectivity,Marxism,and Cultural Theory in China," Third World and Post-Colonial Issues,Spec.issue of Social Text,(31/32),1992,pp.114-140; Zhang,Xudong(张旭东),"On Some Motif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Fever' of the Late 1980s:Social Change,Ideology,and Theory," Social Text,39(Summer),1994,pp.129-156。 ⑨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⑩邢贲思:《怎样识别人道主义》,《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 (11)庹祖海:《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综述》,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证辑要》下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475-1477页。 (12)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 (13)庹祖海:《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综述》,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证辑要》下册,第1478-1479页。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1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5)笔者在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女性作家和导演的研究中,发现具体文化生产模式和媒体对从事不同职业的女性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影响。 (16)关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概念及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体制化实践,见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17)Chen,Tina Mai(陈庭梅),"Female Icons,Feminist Iconography? 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 Gender and History,15(2),2003,pp.268-295。 (18)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19)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 (20)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 (21)李小江在《夏娃的探索》(李小江:《夏娃的探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对张洁《方舟》的探讨。 (22)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收获》1980年第5期。 (23)李小江:《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最初发表于1986年),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302-311页。 (24)李小江:《家国女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25)李小江:《家国女人》,第8页。 (26)李小江:《家国女人》,第9页。 (27)李小江:《家国女人》,第8页。李小江在她的作品中多次重复了相似的问题,见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3页。 (28)Yang,Mayfair Mei-Hui(杨美惠),"From Gender Erasure to Gender Difference:State Feminism,Consumer Sexuality,and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China," Ed.Mayfair Mei-Hui Yang,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p.35-67; Wang,Zheng(王政),"Maoism,Feminism,and the UN Conference on Women:Women's Studies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8(4),1997,pp.126-152。 (29)Barlow,Tani,"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Market Feminism of Li XiaoJiang,"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New Directions in Women's Studies,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53-301。 (30)李小江:《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第4期。 (31)李小江于1986年编了《西方女权运动文选》,她自己认为她在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学术资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见李小江:《对话Tani Barlow:关于1980s“妇女研究运动”:由〈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说开去》,Other Genders Other Sextualities:Chinese Differences,Ed.Lingzhen Wang,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32)Kuhn,A.,and A.Wolpe,eds.,Feminism and Materialism,London:Routledge,1978; Sargent,Lydia,ed.,Women and Revolution: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Boston:South End,1981。 (33)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34)Eisenstein,Zillah,"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Critical Sociology,25(2/3),1978,p.201。 (35)Willis,Ellen,"Radical Feminist and Feminist Radicalism," Social Text,(9/10),1984,pp.91-118。 (36)李小江:《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304页。 (37)李小江在20世纪90年代总结新时期妇女运动时强调“新时期妇女运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种)分离”。在同篇文章的结尾处,她特别对这种“分离”做出了新反思,认为新时期已经过去,在20世纪90年代“主导趋势不再是‘分离’而是重新‘合入’社会,与过去的原则告别”。见李小江:《新时期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之我见》(最初发表于1993年),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8-399页、第402、406页。 (38)Kaplan,Caren and Inderpal Grewal,"Transnational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Beyond the Marxism/Poststructuralism/Feminism Divide," Between Women and Nation:Nationalisms,Transnational Feminisms,and the State,Eds.Kaplan,Caren,Norma Alarccon,and Minoo Moalle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49-363。 (39)Eisenstein,Zillah,"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Capiti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Critical Sociology,25(2/3),1978,p.201; Ehrenreich,Barbar,"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s?" Win,June 3,1976。 (40)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165-170页。 (41)李小江:《对话Tani Barlow:关于1980s“妇女研究运动”:由〈中国女性主义思史中的妇女问题〉说开去》,Other Genders Other Sexualities:Chinese Differences,Ed.Lingzhen Wang,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 (42)李小江在《论中国妇女解放的特点和道路》中指出:“解放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每一个措施,都是自上而下的,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妇女自己的努力,‘恩赐’本身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此文收在《女性问题在当代的思考》,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29页。 (43)王玲珍:《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 (44)Ehrenreich,Barbara,"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s?" Win,June 3,1976。 (45)Wang,Lingzhen(王玲珍),"A Chinese Gender Morality Tale:Politics,Personal Voice,and Public Space in the Early Post-Mao Era," Personal Matters: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51-153。 (46)Honig,Emily,and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47)李晓主编:《上海话剧志》,上海:百家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48)Honig,Emily,and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50-170。 (49)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31页。 (50)见李小江在《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中的论点。另参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1)李小江:《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第4期。 (52)李小江:《女性启蒙与政治代价》,《女人:跨文化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2页。 (53)Barlow,Tani,"Foundations of Progressive Chinese Feminism,"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New Directions in Women's Studies,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p.64-126。 (54)Barlow,Tani,"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Market Feminism of Li XiaoJiang,"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New Directions in Women's Studies,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53-301.Liu,Kang(刘康),"Subjectivity,Marxism,and Cultural Theory in China," Third World and Post-Colonial Issues,Spec.issue of Social Text,(31/32),1992,p.122,p.19。 (55)李小江在20世纪90年代对80年代女性主义实践有不少反思,并转向本土资源和女性研究的本土化。参见李小江:《关于本土化的访谈》(收于李小江:《女人:跨文化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156页)中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李小江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性知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家庭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