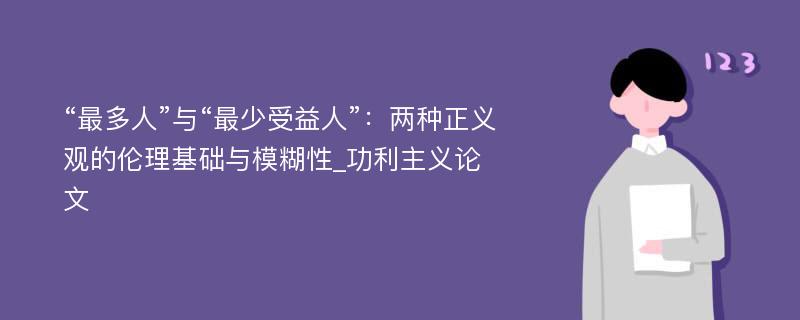
“最大多数人”与“最少受惠者”——两种正义观的伦理基础及其模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多数人论文,伦理论文,正义论文,模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0-0051-08
在边沁(Jeremy Bentham)、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义”与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两种立场迥异的分配正义观中,两个社会群体分别成为各自伦理判断的社会基础,即“最大多数人”与“最少受惠者”;这两个群体也是两种分配正义观的逻辑起点。在功利主义原则中,分配正义惠及的范围是社会成员中的“最大多数人”,公正就是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为他们谋取最大利益;而罗尔斯分配正义的目标群体是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公正就是为“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利益,政府的责任首先是为该群体带来“最大利益”。然而,不论是“最大多数人”还是“最少受惠者”,两个概念都具模糊性,都无法得出清晰的公正观,进而导致两种分配伦理原则在实践中出现有效性危机。遗憾的是,当今的正义论研究很少从这个视角探讨两种正义观的伦理基础存在怎样的问题,而是主要集中于两个维度:一是对功利主义效率导向及其缺陷的批评,二是对罗尔斯正义论进行肯定性论述。两种研究通常都是运用两种正义观的常识性知识解释分配正义问题,而对两种正义观本身的理论逻辑缺乏深入探讨,尤其对两者的伦理基础更是少有深入的学理思考,以至于两种正义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范围与对象始终是模糊不清的。本文尝试从学理层面研讨两种正义观的伦理基础,探查两者具有何种不确定性,借此理解两种分配正义观对公正的不同理解及其实践阈限。
在功利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中,利益最大化是其正义观的终极目标。该理论的逻辑假设是:分配正义的最终目标维系于无差别的个人或“公民”权利,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同样重要,并且是平等自由的。用密尔的话说,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①。这种公民平等的自由权利也是“社会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②。据此,功利主义原则本应得出惠及“每一个公民”或“全体社会成员”的伦理原则,然而事实上,功利主义者推论出的却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者说“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③。该原则实际指涉的范围是“最大多数人”或行为相关者。从“每一个人”或“全体社会成员”到“最大多数人”,这一逻辑上的跳跃导致该原则的应用范围不可能是“全体社会成员”,而只是作为大多数人的行为相关者。但谁是行为相关者或“最大多数人”,却没有清楚的规定。这样一来,功利主义作为公正分配目标的“最大幸福”就变得无法预测而模糊不清。
那么,满足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功利主义的分配正义标准呢?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认为,“在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解决政治问题的社会规章或解决方案中,能够对最大多数人产生最大幸福的便是最好的标准”④。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它要求行为的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地为行为相关者(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福利余额。然而,在实际运用中,以最大余额为公正分配的依据却使该原则的含义语焉不详。在具体的分配方案决策中,决策者如何测量受惠者及其期望获得幸福的总量呢?这样的表述并不能真正指导行为的选择,也无法准确预测行为产生的余额是多少。
这可以通过下述两个方案的比较得以理解:
假设有甲、乙两个方案涉及的对象有100人,将功利按照0~10个单位分级。甲方案的分配结构中,有70个人每人可以得到7个单位的功利,20个人每人可以得5个单位,另外10个人每人得1;而乙方案的分配结构中,有50人每人得7,另外50人每人得6。那么,根据产生幸福的倾向计算,乙方案必定取胜,因为它可以产生650个单位的功利总量,而甲方案只能产生600个单位的功利总量。但是,如果进一步考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情形就会变得复杂。如果我们忽略“最大多数人”,就有可能坚持认为乙方案更好,就福利或幸福的总量而言,乙方案仍然优于甲方案。但有人也可能会认为甲方案更好,毕竟甲方案中有70人能得到7,满足“最大多数人”的要求,而乙方案只有50人能得到同样数量的功利,甲方案明显不符合功利主义的初衷——增进最大的福利总量。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者往往会忽略不计“最大多数人”的要求,偏离其伦理基础,这样做可以降低预测结果的难度。因为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政治决策的目的“通常也不过是关注福利的最大化而已”⑤。
问题是,缺乏明确界定的“最大多数人”直接导致了“最大幸福”或者说“最大余额”的含糊性。什么是“最大幸福”?它是指积极地、无限止地增加的“福利”呢,还是消极地避免“不幸”的增加呢?功利主义者无视个人之间福利的差异,专注于“福利”的持续增长和“痛苦”的不断减少,那么,“最大幸福”到底是指社会福利的最大总量呢,还是最大的平均量?全社会福利的总量是否等于社会总人口(N)中每一个人的福利之和?平均福利是否等于福利总量除以总人口(N)?实际上,功利主义通过否认福利差异的重要性以模糊“总量”与“平均量”的差异。因此可以说,在“总量”与“平均量”的问题上,功利主义理论家其实并没有给出实质性的规定,除非把特定分配对象的人数考虑在内,以确定一个明确的分配范围,否则,无法真正得出什么是“最大幸福”的内涵。在很多情形下,当人们在涉及自身福利的情况下,往往愿意考虑福利的平均量,而不是全社会的总量。可是,功利主义要求的恰恰是社会福利的总量,而不是个人的平均量,尽管这种计算是基于个人福利的。
对此,可以从边沁的论述中得以理解:“……(5)把所有快乐之值相加,同时把所有痛苦之值相加。如果快乐的余额大于痛苦之值,那么,该行为对于个人利益来说总体上具有好的倾向;如果痛苦的余额大于快乐之值,则该行为总体上具有坏的倾向。(6)确定利益相关者的人数,对每个人都按照上述程序估算一遍,就可以出现两类人:第一类是,对他们来说,行为的倾向总体是好的;第二类是,对他们来说,行为的倾向总体是坏的。把行为涉及第一类人的好倾向程度相加,再把行为涉及第二类人的坏倾向程度相加,如果快乐的总量大于痛苦,则表示该行为总体上对全体当事人或个人共同体具有善的倾向;如果痛苦的总量大于快乐,则表示该行为总体上对该共同体成员具有恶的倾向。”⑥
但是,上述两类人的总体幸福和痛苦的数量是否具有真实的代表性,在幸福和痛苦的性质有差异的情况下又如何计算?边沁并没有具体论述,他只是笼统地将当事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余额的计算,而这种笼统的方法其实并不能对分配正义提供有效的指导,也无法为个人提供行为准则。事实上,边沁本人也承认这个看似准确的计算“公式”不可能被严格执行。他明确说过,不要指望在每个道德判断之前,或者在每项立法或司法行动之前,“上述程序都会被严格地得到遵守”。他意识到,这一计算方法只能在预测行为结果时考虑到它,“实际遵从的程度与之越接近,就将越准确”。⑦正因此,阿玛蒂亚·森(A.K.Sen)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计算基础是不同人之间的得失比较,即只要甲得到的福利比乙失去的更多,该行为便是善的。可是,这无法真正指导现实的行为选择。所以,他认为,如果说这种证明具有某种合理性或者有效性的话,那也是不全面的。⑧边沁论证中的漏洞十分明显。
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密尔的论证中。他在证明功利主义原则普遍有效性时也说过,既然“每一个人的幸福对他自己是善的……因此,普遍的幸福就是对全体人都是善的”⑨。这种推理在逻辑上仍然存在着跳跃,“全体人”是怎样从“每一个人”中推导出来的,密尔也没有清楚阐释,尽管他试图这样做。他在回复一位批评者的信时,就明确地解释过他使用的“general happiness”与“the aggregate of all persons”两个概念,以避免边沁面临的质疑。他说:“我在《功利主义》中提到‘普遍幸福’(general happiness)是指对作为‘整体的全体人’(the aggregate of all persons)是善的东西,这并不意指每一个人的幸福对每一个其他人来说就是善的,尽管我认为在一个良善的社会与好的教育环境下,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一特定的词句中,我仅仅是指既然甲的幸福是善的,乙的幸福是善的,丙的幸福也是善的,以此类推,那么,所有善事物的总量也一定是善的。”⑩
的确,密尔承认“每一个人的幸福”对“每一个其他人”来说并不一定就是善的,但是,他坚持只要作为个体人甲、乙、丙的幸福是善的,其整体的幸福必定也是善的。这里,其论证的思路仍然摆脱不了数量累计的框架。事实上,上述论证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功利主义原则中的“最大多数人”和“最大幸福”究竟是什么。他在证明功利主义原则时,更多地证明的是幸福为什么是可欲求的,而没有证明为什么其分配正义惠及的范围是“最大多数人”。密尔的解释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而是以“全体人”概念代替“最大多数人”或“利益相关者”,而对整体幸福的理解则依然是个人幸福的相加。正因此,拉斐尔(David D.Raphael)认为,密尔论证中的谬误在于用“普遍幸福”解释所有人集体欲求的目的,“甲的幸福对甲是值得欲求的,乙的幸福对乙是值得欲求的,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甲的幸福加上乙的幸福就是对甲和乙都是值得欲求的,而密尔却以为他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11)
功利主义对上述基本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必然导致其分配正义惠及的范围含糊不清,而这种不稳定的伦理基础,进一步导致其分配正义理论中对公平界定的不确定性。一旦用这样的原则指导社会财富的分配,政策惠及的范围必定是似是而非的,以至于无法清晰地确定政策的受惠对象,于是,公共政策所要达到的公正目标也难以实现。波普斯(Gerald M.Pops)认为,功利主义分配正义的逻辑要求计算相对“最大多数人”的净利益,而论证的却是社会的全体成员,即使这样,这个全体成员仍然是不清晰的概念。例如,它是指当今世代的全体成员还是包括未来不同世代的人?(12)鲁克(J.S.Luke)则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当前决策涉及的对象范围已经不可能仅限于当今世代的“最大多数人”或全体社会成员,而是必须涉及未来几代人,政府决策一般都是根据具体情境解决具体问题,当具体情境中的利益与国家的长期利益发生冲突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该作何理解?当具体决策与后世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又如何理解“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这些情况下,很难在实践中将功利主义的分配正义观贯彻到底。实际上,分配正义的执行者通常只能照顾到部分人的“最大利益”,或是本国内的“公民”,或是当前时代的“全社会”,也或者只是部分人的利益。更何况,在全球化背景下,具体分配政策会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最大多数人”是一个永恒的变量,功利主义分配正义论追求的目的需要在动态的综合与协调中才能实现,或者说,只能获得不完整的结果(13),以此指导现实社会的利益分配,很容易导致不公正的分配结果。正因此,功利主义分配正义原则的伦理基础遭到诸多质疑与批评。
在诸多批评功利主义分配正义伦理基础的观点中,最具颠覆性的批评来自罗尔斯的“最少受惠者”理论。他抨击功利主义导致社会分配不公,是因其只关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忽视了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的差异,尤其是对“最少受惠者”群体的忽视。他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无法补偿利益牺牲者的损失,这种缺失了补偿的正义观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只有确定一个“基本地位”,即“某一代表人的地位”(14),才能为公正分配社会财富提供一个“合适的观察点”(15),以便为判断社会体系提供一个“恰当的立场”(16),这就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基点可以使分配目标明确向弱势群体的地位倾斜,以避免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模糊性。
那么,什么样的人符合“最少受惠者”的基本地位并与“最大多数人”相抗衡呢?罗尔斯分三个层面进行界定:
其一,将基本地位的“代表人”限定在毕生参与社会合作的人。罗尔斯认为,“正义的首要问题是关注那些特定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全身心地、积极地参与日常各项工作的合作,即正义的首要问题只关注社会合作者之间的关系”(17)。这就直接排除了社会合作体系之外的人。进而,他又假定这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合作的人“都有各种正常的生理需要和心理能力,既无健康忧虑,也无智力问题,所以不必提及健康问题”(18)。在罗尔斯看来,“如果过早地引入这些问题,就可能使我们越出正义理论的范围,考虑这些困难的情况,会引导我们总是去想那些远离我们正常状态的、由于命运不佳导致的不幸和焦虑,这将会困扰我们的道德观”(19)。
之所以将分配正义原则置于这一有限的社会基础之上,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是罗尔斯所处的时代已经实施福利经济原则,福利原则为解决无保障者的基本生活问题提供了有效支持,几乎惠及社会的每一个人,且福利原则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并不能创造财富与效率。严格地说,这不是《正义论》所要论证的问题,所以,分配正义原则维系的“基本地位”不再是“全体社会成员”或者是“每一个人”,更不是语焉不详的“最大多数人”。正因此,罗尔斯审慎推敲正义原则的受惠者地位,通过修正差别原则的表述,确认分配伦理的社会基础。他先是这样表述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20);随后又修正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1)。不难看出,从“每一个人的利益”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受惠者的范围逐渐明确,从而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确定的伦理导向。
其二,根据特定阶层的经济地位。罗尔斯从两个方面衡量社会合作者中的“最少受惠者”地位:一是“选择一个特殊的社会地位,比如说,非熟练工人,然后把同处于这一地位、具有相似或更少收入和财富的人,算作最少受益者”;二是“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只根据相关的收入和财富,比如,所有达不到中等收入者均可作为最少受惠者。这一标准只根据收入和财富分配中较低的一半群体,其优点在于,便于人们关注最少受益者和中等群体之间的社会差距”(22)。罗尔斯相信,“这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都涵盖了(因各种偶然因素导致的)所有最不利者,为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社会(财富的)最小量提供了基础”(23)。从这个角度看,凡是达不到中等收入的人被当做一个无差别的整体看待,它不考虑特殊个人和特殊群体的差异,而是把处于同一经济地位的群体看作一个“代表人”。这里,“最少受惠者”地位是对同一经济地位的人的理论抽象,抽去了具体个人的各种特殊性质,留下的是共同或相似的收入水平。在这个层面上,单个人的特殊地位不见了,它们融入在作为“一个代表人”的群体地位中,融合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基本地位”。
根据经济地位确定“最少受惠者”,把“最少受惠者”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社会地位区别开来,是为了使社会分配制度的设计有利于该地位的“代表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关注。它有别于功利主义的“全体人”或者“最大多数人”,“最少受惠者”具有明确的收入指标依据,且遵循“最大最小原则”的分配程序(24)。把分配正义置于“最少受惠者”的社会阶层之上,可以将社会中最不利群体的利益清晰地凸显出来,而不是缺乏具体指向的模糊概念,有利于矫正功利主义原则导致的弊端,以确保最低的公正要求。
其三,依据个人的某些重要特征。如果转换视角,考察特定社会背景下哪些个人真正属于“最少受惠者”地位,或者说,除了经济收入标准之外,个人进入“最少受惠者”地位是源于什么缘由,那么,上述经济标准无法提供足够详细的信息。例如,某人的工资收入的确处于中等收入之下,但是他是因为好逸恶劳、不求上进而沦为收入最少者,差别原则是否应该照顾这样的低收入者呢?为了寻找真正应该保护的最不利地位,罗尔斯在其修订版《正义论》中进一步从个人角度提出三条具体的微观标准。他把它们概括为:“第一,他们的家庭和阶级出身比其他人更不利;第二,他们的自然资质(实际的)使他们的生活比别人更差;第三,他们一生的命运和机遇确实使他们只享有很少的幸福。所有这些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考虑以及与社会基本财富相关的衡量标准。”(25)
这三条标准提供了另一个划分“最少受惠者”的参照系,也是个人成为“最少受惠者”的重要原因。现实社会中,一部分人处于“最少受惠者”地位,往往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收入和财富的差异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的成因极其复杂。个体标准要回答的是:人们在社会合作中收入和财富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个人具有怎样的特质才会成为“最少受惠者”?经济标准所包含的特征并非抽象的,某些人之所以处于“最少受惠者”地位,往往是由个人自然的偶然因素和社会的随机事件导致的,如愚笨、残疾、种族歧视等。社会的“最少受惠者”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上述三方面影响。他们或者出身在贫穷家庭;或者天生智障低能;或者虽然勤奋工作,但命运和机遇特别差。这些方面(或某一方面)条件较差、起点较低者,都有可能使他们在参与社会合作过程中处于更不利的社会地位。
至此,罗尔斯对“最少受惠者”的界定是具体而明确的。首先,将分配正义原则惠及的对象限定在“参与社会合作的人”,排除了社会合作体系之外的人;其次,这些合作者属于经济收入处于中等或中等以下者,排除了参与社会合作者中收入高于中等以上的人;再次,是由于个人特殊的先天与后天境遇不利而导致收入低下者,排除了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贫困者。与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相比,这一界定为确认谁是“最少受惠者”提供了可衡量的指标。在这一意义上,分配正义惠及的范围具有明确的对象,公正的依据是清晰可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局限。
然而,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运用契约论方法推论的结果。这种思维方法的最初表现形式是通过对假设性前提的追问,即“假若我们处于适当的条件下而要一个选择,那么,我将会选择何种安排。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一种安排在适宜性(eligibility)这一标准方面胜过了其他安排,就是各种可行的选择方案中最值得想望的”(26)。这一传统的价值在于,它适宜于构建理想的理论和普遍原则,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出发,层层推论出具体原则和标准,以构筑自我完满的理论大厦。不过,正如从现实中无法找到真正自我完满的事物一样,契约论方法推演出来的理论和标准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当理想的理论和标准运用于现实社会时,往往会出现难以贯彻或无法实施的问题。这也是契约论无法克服的困难。深入思考罗尔斯“最少受惠者”标准的内在逻辑,同样可以发现它们并非无懈可击,其“最少受惠者”的标准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致使正义原则的应用面临新的困境。
在“最少受惠者”的各种规定中,虽然经济标准的确立为公正的伦理标准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以便明确地将社会中最不利地位的群体作为公平正义原则的伦理基础,然而,当罗尔斯试图寻找谁会成为“最少受惠者”的答案时,其三条个体标准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明确而便于应用。探寻三条微观标准,同样可见其内在理论逻辑的不一致。
如前所述,三条标准涉及的是个人在一生参与社会合作和分配中可能遇到的偶然因素,个人“由于其中任何一种因素导致获利最少,便是最少受惠者”(27)。以家庭出身为例,某人天生聪明、勤奋并努力工作,只因出身贫穷,父母无力承担其接受良好教育的费用,使他无法从事智力劳动和复杂的技术劳动,尽管他工作勤奋努力,但低智力的简单劳动使他不可能得到理想的高报酬,他就会处于社会最低阶层。相反,一个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人,优裕的生活条件和优良的教育使他从一开始就处于很高的起点。这意味着,这类人从出生之时就拥有日后社会生活中的好机会。他们参与社会合作获得高利益的潜力更大,即使他们在工作中不像前者那样努力勤奋,也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他们像前者那样勤奋,则可能得到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获。对这种差异,不同的分配制度有不同的道德态度。作为公平的正义观认为这种差异“从道德的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断的”(28),也是正义社会不能容忍的。正义原则的使命就是通过公正的分配制度,确保“最少受惠者”阶层的利益。
然而问题在于,当罗尔斯将“最少受惠者”定位于自愿参与社会合作的群体时,是从原初状态的“代表人”特征出发的,即假设他们自愿积极地参与社会合作。事实上,三条个人标准却来自特定的现实社会,而任何现实社会中的人比原初状态下的“代表人”要复杂得多。有些“最少受惠者”确实因为某些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所致;有的却由于懒惰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酗酒、吸毒等所致。他们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最少受惠者”。那么,在分配社会财富时,如何区别对待两者呢?罗尔斯对此未作区分,这导致差别原则的实施带来困难。
关于自然资质(天赋)的定义也是似是而非的。罗尔斯所说的“自然资质”(endowments)主要是指天资和才能,或智力和能力,但他没有说明天资和才能具体指的是什么。从罗尔斯的定义看,弱智和低能显然是自然天赋之不足,此类特征可以作为判断“最少受惠者”的依据,差别原则应该保护这类对象。但与此相似的丑陋、疾病、悲伤、早夭和衰老等却不属于自然资质,因为这些因素似乎是非常特殊的,因此不必考虑,由此导致这些人在参与社会合作中的不利地位,就不能作为相关代表人的特征,他们似乎不能成为差别原则惠及的对象。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把“自然资质”作为确定“最少受惠者”的参照是否确定无误?的确,智障与低能是不利的自然资质,会直接影响他们在社会合作中的地位,阻碍其从社会合作的利益分配中获取应得的平均利益。按照罗尔斯的观点,“从一种道德的观点来看,自然天赋的最初资质和早期生活中发展和教养的偶然性是任意的。……一个人愿意作出的努力是受到他的天赋才能和技艺以及他可选择的对象影响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天赋较好的人更可能作出认真的努力……”(29)这里,罗尔斯似乎把契约论假设中的抽象状态当作了现实存在的情景,他假定只要天赋较好,就会作出认真的努力。他没有考虑到可能面临的风险,即将一种分配正义制度建立于个人选择基础之上,该推断本身具有某种任意性的风险。正如诺齐克批评的:“对于一个其原则如此依赖于人们的选择建立起来的理论”是“一件冒险的事情”(30)。
此外,罗尔斯的推论还蕴涵另一个风险:那些天赋较差的人,即使不如天赋较好者那样认真而努力,只要他们的收入达不到中等收入水平,差别原则也应该给予关照。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差别原则惠及的对象不仅包括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包括那些对社会参与抱消极态度的人,因为这是由于他们天赋较差造成的,正义的分配理应考虑他们的情况。如此,差别原则的分配对象范围就值得怀疑。为此,诺齐克主张的政府“守夜人”角色有理由拒绝罗尔斯的政府干预论,且批评其认定“最少受惠者”的标准具有任意性。
的确,罗尔斯对自然天赋能力的理解是笼统的,他没有区分“拥有的能力”与“运用的能力”之间的差异。在《正义论》中,他没有区分先天决定的“自然资质”与社会环境决定的“能力”。他在论述人的自然资质是“不应得”时就蕴涵这一逻辑,他认为既然自然资质是“不应得的”,那就不是属于某一个人,也就无所谓运用与否。正如其批评者指出的,自然资质既然无所谓正义与否,因此没有人是应得的,也没有人是不应得的。(31)罗尔斯显然同意这一观点,他用几乎两页的篇幅论述自然资质,提到“自然资质”无所谓正义,也无所谓不正义,它仅仅是一种自然事实。(32)但是,正如约翰·沙尔(Jone Schaar)所说,罗尔斯花如此大的篇幅论证“自然资质”是不应得的,并不会简单地满足于区分“自然资质”与“努力”(33)。蕴涵在罗尔斯论证中的真实逻辑是:既然自然资质不是个人应得的,而是一种共同资产(34),那么,个人无法对其真正地“拥有”与“运用”。依此类推,社会中地位较好者是由于他们具有较好的自然和社会资质,但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些不是他们应得的,因此,从他们的较高收入中纳更多的税用于提高“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就成为社会分配制度的责任,而差别原则的使命正是保护这一最不利群体的利益。
这一论证导致的结果是,罗尔斯为差别原则确立了特定的应得标准,即当某些人处于上述三种不利地位而导致低收入时,差别原则认为他们的处境是“不应得”的,需要加以保护,至于他们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则可以不作考虑。但另一些人,如资本家因“努力”运用他们的自然资质而获得高收入,差别原则认为也是“不应得”的,社会应该征以更多的税,以补偿那些自然资质更不利的人。这里,差别原则对“应得”的标准具有双重性,即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的,“应得似乎是永无定论和多样化的”(35)。正如某年轻人值得去爱,但说他值得某个特定女性去爱却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他爱她,而她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则只能说是他的不幸,人们无法用外力加以纠正,更不能通过政府的力量加以干预。当然,沃尔泽赞同国家和政府可以做这样的分配,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分配的是人们需要的东西,如医疗保健,而不是人们应得的东西”(36)。因为,按照“应得”分配财富的话,则未必就是某人“需要”的,也不一定是某人通过努力后得不到的东西。那么,按照罗尔斯的标准划定谁是差别原则应该照顾的“最少受惠者”,会对现实的分配公正带来困难,甚至导致人们对公正含义的模糊理解。
进一步思考原初状态下界定“最少受惠者”阶层的“弱理论”,罗尔斯论证中的矛盾也是明显的。一方面,当他论述原初状态下作为代表人的“最少受惠者”地位时,其理论倾向是义务论的。他认为,在原初状态下,没有人会受“基本善”之外的原因所驱动,尽管“各方代表”知道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其他善观念,其中有的是不能容忍的,但“原初状态”中的“代表人”不会接受功利主义的善观念,这种“弱理论”的规定有助于确认各方的代表人地位,包括“最少受惠者”。这是其契约论假设的重要目的之一。但另一方面,当罗尔斯论证两个正义原则形成时,其采用的却是目的论的途径,接受了结果最大化的思路。按照义务论伦理,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正当”应该优先于“善”,基本善优先于并生成两个正义原则,杰克逊(M.W.Jackson)认为,“更准确地说,我们对基本善的欲望使得我们需要为正义而设定最低程度的限制,但在无偏私的原初状态议程中,这种不可容忍的善与其他善具有同等的地位”(37)。杰克逊的意思是说,在运用最大最小原则推论两个正义原则过程中,对结果最大化的追求依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受益主体的身份是“最少受惠者”而不是“最大多数人”或“每一个人”。这种理论矛盾使得“最少受惠者”的特征很难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确切的对应,从而为差别原则的实施增加了难度。
至此不难看出,罗尔斯将正义原则置于“最少受惠者”的基本利益之上,这种原初状态下确立的伦理基础具有明显的理想色彩,因而适合于达到普遍正义的目标。但是,对政府制定分配政策而言,它只可作为公平正义的普遍价值导向,却不能提供具体的分配比例与定量标准。因此,由契约论方法确立的公正伦理基础,在现实中依然需要借助具体的情境加以确认,正如“最少受惠者”的三条个人标准无法明确甄别谁是特定公共政策必须照顾对象,义务论的正义推论在现实中同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伦理冲突。差别原则坚持“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最大化,虽然颠覆了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导向,却无法令人满意地消除受惠对象的模糊性,为制定公正的分配政策留下遗憾。
综上,两种正义原则分别以“最大多数人”和“最少受惠者”为社会基础,从不同的方向为公共决策提供现实的伦理依据。但是,由于两者的内涵都存在模糊性,以此为基础确立的分配正义原则也很难为现实的分配决策提供确定无疑的指导。区别只在于,两种正义观的公正内涵不一,追求的正义目标不尽相同。功利主义注重的是财富总量的增加,而对不同阶层之间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关注,“最大多数人”往往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代名词,进而掩盖实际的分配不公。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向“最少受惠者”利益倾斜,注重的不是福利数量的计算,而是福利水平提高,强调不同阶层之间福利水平的改善,但由于现实中的“最少受惠者”群体存在争议,致使追求普遍福利的愿望可能偏离公正分配的宗旨,从而使分配政策在实施中难以达成公正的目标。当然,两种正义观在实践中面临的障碍很难通过各自的理论修正得以克服,而是需要经由各种正义理论之间的冲突与竞争,相互吸收与融合才能得以完善。正因此,在功利主义与罗尔斯正义论之后,出现了更多相互竞争的正义观,每一种正义观的提出,同样基于对“受惠者”的重新界定与确认,以至于分配正义的范围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决的议题。
注释:
①②[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第13、1页,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③[英]约翰·穆勒(密尔):《功利主义》,第12页,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④⑤Philip Pettit,Judging Justice: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Rougledge,1980,p.108,p.109.
⑥⑦Jeremy 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Methuen & Co.Ltd,1982,pp.39-40.
⑧A.K.Sen,"Rawls versus Bentham:An Axionatic Examination of the Pure Distribution Problem",in Norman Daniels ed.Reading Rawls:Critical Studies o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284.
⑨Plamenatz ed.,Mill's Utilitarianism,Backwell,1949,p.198.
⑩Hugh S.R.Elliot ed.,The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10,Vol.Ⅱ,p.116.
(11)David D.Raphael,"Fallacies in and about Mill's Utilitarianism",in G.W.Smith ed.,John Stuart Mill'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Vol.1),Routledge,1998,p.53.
(12)Gerald M.Pops,"A Teleological Approach to Administrative Ethics",in Terry L.Cooper ed.,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Marcel Dekker,Inc.,1994,p.159.
(13)J.S.Luke,"New leadership requirement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s:from managerial to policy ethics",in J.S.Bowman,ed.,Ethical Frontiers in Public Management,Jossey-Bass,1991,p.158.
(14)(15)(16)(17)(18)(19)(20)(21)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81,p.82,p.82,p.84,p.83,p.84,p.53,p.72.
(22)(23)(25)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84,p.84,p.83.
(24)罗尔斯的《正义论》假设原初状态下的代表人运用“最大最小原则”选择两个正义原则。在“无知之幕”下,各方代表按照选择对象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进行取舍,即在最坏结果中选择最好的对象。它可以保证“最少受惠者”这一最低阶层的获利最大化。这与差别原则的取向具有一致性。
(26)[澳]乔德兰·库卡塔斯、菲利普·佩迪特:《罗尔斯》,第19页,姚建宗、高申春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7)(28)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83,p.39.
(29)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79—280.
(30)Robert Nozick,ANARCH,STATE AND UNTOPIA,Basic Books Inc.,1974,p.214.
(31)G.Gaothier,"Justice and Natural Endorsement",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Vol.47,(Jan.1974),p.15.
(32)(34)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87,p.164.
(33)J.Schaar,"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the Just Society",in H.Gene Blacker and Elizabeth H.Smith(eds.),John Rawls'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0,p.170.
(35)(36)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Basic Books,1983,p.22,p.24.
(37)M.W.Jachson,Matters of Justice,Sydney:Croom Helm Ltd.,1986,p.136.
标签:功利主义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福利人论文; 个人努力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合作原则论文; 经济学论文; 正义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