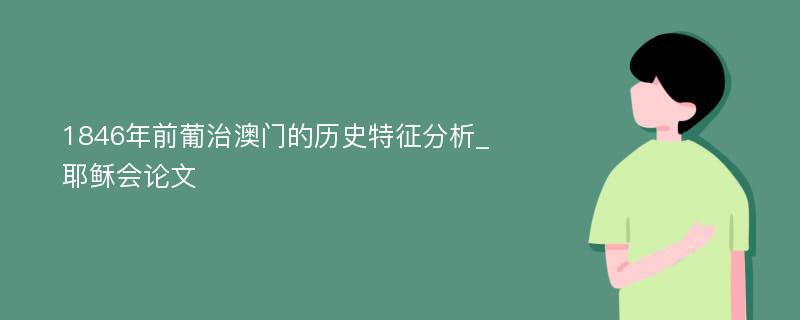
试析1846年以前葡萄牙管理澳门的历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葡萄牙论文,澳门论文,历史论文,试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557年到1846年的近三百年中,葡萄牙人在他们以租借形式盘踞的澳门半岛上,曾力图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管治。尽管这种殖民管治受到了当时中国明、清两朝当局的抑制,但它却体现了中世纪欧洲大陆社会形态的遗风。关于它的历史特点,目前尚未有比较明晰的评价;然而对此加以了解,有助于认识该时期传教士通过澳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澳门作为贸易港的兴衰,葡萄牙人在1840年以后追随英国人对中国进行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等基本问题。
一、再现欧洲中世纪城邦管理的传统色彩
葡萄牙人获得居住澳门半岛的许可之后,逐步建立起对澳门半岛居住地的社会管理,他们的管理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体现着欧洲中世纪城邦管理的传统色彩。其表现在:
1.建筑城堡。这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及发展其管理方式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之一。澳门半岛上颇具规模的葡萄牙城堡体系,从开始筹措到基本建成,前后持续了大约一百多年。耶稣会传教士在城堡体系的设计和施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522年,马丁·阿丰索率领的葡国船队到达珠江口,他此行的使命之一,是在屯门或寻找其它适合的地点修筑城堡。1586年,西班牙的菲利蒲国王赐名澳门为:“中国的上帝圣名之城”,享有与葡萄牙埃武拉和科英布拉同等的城市权力。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统治之后,新国王唐·若奥四世于1642年授予澳门“天主圣名之城,无比忠贞”的称号,同时认可澳门继续享有已获得的城市权力。约在明朝末年,葡萄牙人已按照“城市”的设计构思,在澳门半岛上建起了城堡体系。大英博物馆藏彼得罗著《东印度》(1646年出版)所载的澳门平面图上,可以见到澳门半岛城堡体系的完整轮廓。此外,在《澳门记略》(1751年出版)所载的正面及侧面澳门图上亦可以见到,此时的城堡体系已分别建有西望洋、娘妈角、南环、伽思兰、东望洋和大三巴六座炮台,以及连接炮台的城墙;在城墙上,分别开有大三巴、小三巴、沙梨头和花三庙四道城门。明、清两朝官府对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上修筑城堡体系的计划和工程,曾屡次予以干涉。田明曜《香山县志》(卷八)记载:“澳夷旧有城垣,为明总制何士晋所坠”。1636年,澳门议事会讨论修缮受损严重的城市围墙和城堡的事宜,与会者都说自己负债累累,最后商定给广州的海道衙门赠送礼品,先表示了葡萄牙人的尊敬和良好合作愿望之后再作打算(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43页。)。满清朝廷对葡萄牙修筑城堡体系的干涉,在满清海关设置澳门“关部”后才略有缓和。
2.建立和巩固议事会自主政治制度。澳门议事会成立于1583年,是作为葡萄牙人讨论和处理有关澳门半岛居住地事务的管理机构。有三个因素促成澳门议事会的成立。首先,1580年起,葡萄牙被置于西班牙王朝的统治之下。其次,随着澳门半岛上的人口增长,为了抵御海盗、保持澳门半岛的社会秩序,以及应付中国朝廷的有关事务和海上贸易开展的需要;在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有一个葡萄牙兵头和两个辅助他的好心商人,还有葡萄牙官营贸易船队的队长,于1565年左右联合起来。再次,葡萄牙耶稣会的神职人员已开始行使罗马教庭的宗教庇护权,在澳门半岛上修筑教堂、划定教区,开展基督教传播;由于唐·贝尔希奥主教的积极推动,议事会得以成立。
1584年,葡萄牙印度总督唐·杜阿尔特向澳门议事会授予了行政和司法方面的权力,但规定有关澳门半岛的特殊事项,得事先召开市民大会才能作出决定。澳门议事会最初只有六名议员,包括两名法官、一名管理金库的财政监事和一名负责对外事务的总务长;议事会设有主席,由全体议员逐月推选议员担任;通常都是由澳门主教或市民选定的元老级议员当选,以及主持议事会日常事务。每当议事会的表决出现平局,便得请文人或宗教界的元老们出面解决。议事会设有中文翻译官,除了负责撰写公文及翻译收到的公文之外,还得负责中文课程的教授;担任翻译职务的人,一直是从澳门教会的神甫中临时任命;自1814年起,才改由澳门的土生葡人担任该项职务。葡萄牙国王或葡印总督以国王名义委任的王室大法官、总督、王室财政监事及官营贸易船队队长,有参与和辅助议事会的义务,但没有投票表决权。议事会可任命行政官员、普通法官及检察官。1586年,经过以澳门市民的名义提出要求,葡印总督授予议事会享有与葡萄牙埃武拉及科英布拉同等的城市管理权限;在此之后,议事会还通过不同途径多次要求葡萄牙王室,对上述城市管理权限的自治性质予以追认。1638年,意大利人阿瓦罗在其《澳门城的描述》中提到:该城市在最初建成时,是按共和国方式治理,即由最年长的顾问管辖。到十七世纪末,议事会议员人数已增至九名。
削弱王室大法官和澳门总督的实权,一直是议事会提高和巩固其澳门自治管理地位的重要手段。葡萄牙于1580年开始从里斯本向澳门派遣王室大法官。1588年,王室大法官规章颁布,但澳门却一直没有设立皇家法院。1596年,西班牙国王菲利蒲二世应澳门市民的请求,指示葡印总督转告他的决定:王室大法官不再兼任影响重大的孤儿法官,改由被澳门当地各方面了解的“已婚并称职之市民”担任该项职务。在1587~1600年期间,先后有六名王室大法官被更换,不称职是当时更换该职务人选的主要缘故。1626年,澳门市民贡萨罗被推选担任王室大法官,该项任职资格得到了葡印总督认可。耶稣会在澳门设立宗教裁判所之后,王室大法官之职便形同虚设。西班牙王室统治葡萄牙以后,直至1607年才授予葡印总督任命长期驻澳门的兵头以总督的权力。1615年,葡印总督委任弗朗西斯科为第一任澳门总督,兼任王室大法官及官营贸易船队队长。这项任命不仅反映了以往议事会与总督和王室大法官之间的对立,而且反映了葡印总督企图建立起新的权力制衡关系。然而,在1783年以前,葡印总督通过澳门总督去抑制议事会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在此期间,议事会对澳门总督人选的决定仍起着重要影响;担任或代理总督职务的人可以是王室贵族、主教和市民,亦可以是葡萄牙人、印度或澳门的土生葡人;总督到澳门就任的日期是综合了新任总督自己的意见,以及议事会的意见之后才确定和宣布;如果总督去世令该职务空缺,在确定总督的死亡后,由议事会取出当年的册封单,宣布单上所记载的继任人名字;总督继任人得在澳门参加由指定议员授予总督权力手杖的仪式;议事会秘书立公文记载上述发生的一切,这些公文最后得由秘密和新总督本人签字。1622年,澳门市民曾选出由安东尼奥署理主教与市民彼得罗和阿戈斯蒂纽组成的执政委员会,该执政委员会不仅行使兵头职务,而且不受当时官营贸易船队队长的管辖。在澳门的防务方面,议事会有权指派分别负责炮台、要塞和海上守备的军官,在澳门制造火炮及火药的工匠亦受议事会控制,令总督在弹药不足时得向他们求助。1685年,担任过马尼拉贸易船队队长及议事会议员的澳门土生葡人梅斯吉达被推任总督;但议事会不久便对该总督不愿执行授予议事会的权力产生不满。不受议事会欢迎的总督常常被改派到蒂汶任职。另外,教会的神职人员亦利用议事会与总督针锋相对。因此,总督与议事会之间一直存在着深刻的敌对情绪;1643年,唐·塞巴斯蒂奥总督曾企图取消当年进行的议事会议员选举。到十八世纪初,这种敌对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732年,澳门总督梅内塞斯对他与议事会之间的深刻矛盾作出过这样的评论:葡萄牙国王将澳门的政治及经济管辖权授予了议事会,在解决这些管辖权涉及的有关问题上,总督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所作为,因为议事会太自行其是,自己决定是否征求总督的意见,不把总督放在眼里(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19页。)。虽然议事会内部也有严重的派别争斗,但它总能以葡萄牙王室敕令的权威压制住对手。1784年,葡萄牙王室授权澳门总督得参与有关澳门福祉的各项事务,并对议事会的任何动议有一票否决权,议事会对澳门行政权的控制终于被打破。然而,议事会却不愿善罢甘休,不仅耗费巨资在1784年建成堂皇的新会所,而且顽固地阻挠行政权力的转移。一方面以很多理由不断向果阿或里斯本提出申诉,要求恢复往日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则在澳门行政及司法事务上继续制肘总督。这种状况反映了当时澳门议事会包括教会的神职人员,尚未意识到此项权力转移对重整葡萄牙海外殖民地扩张残局的意义。
3.维持市民大会的传统地位和作用。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列入澳门市民的人士可分成三等。第一等级的市民由教会神职人员、王室贵族人员和公认是元老的人士及其家属组成。第二等级的市民由富人、船主和担任公职的人士及其家属组成。第三等级的市民由辅助或替第一、二等级市民服务的人及其家属组成。第一、二等级的市民主要是白种人和葡萄牙人,普通的印度和澳门土生葡人属第三等级市民。奴隶和没有入教的中国人不被列入澳门市民。显然,澳门市民的等级划分与欧洲大陆传统的国民等级划分有所不同,来到澳门的葡萄牙人尚缺乏形成封建领主的土地条件,只能在等级划分上保持传统的形式。但是,第一、二等级市民由充满冒险精神及不甘约束的船主、商人,以及蔑视世俗权力的传教士占了多数,则提供了市民大会能在澳门半岛上出现的社会基础。在当时的澳门,市民大会并不是一个具备组织功能及形式的权力机构,只是市民们共同商议和决定某些重要事项的场合。市民大会由议事会不定期举行。神职人员和元老的意见对市民大会的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强化基督教会的神权统治地位
议事会成立之前,传教士已在澳门半岛建立起教会组织及其教区管理。1522~1557年,在中国沿海尤其珠江口、广州一带进行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逐渐增加。1555年,努内斯神甫已在浪白澳向大约三百名葡萄牙人传教。该年,浪白澳有近四百名葡萄牙人、五位弥撒神甫及数位川走广州之间的传教士。1557年,教皇保罗四世敕令澳门划归马六甲教区,隶属果阿,受葡萄牙教区保护;制定教士规程。到1568年唐·贝尔希奥担任澳门署理主教时,已有多批耶稣会传教士和神甫来到澳门居住。1576年,教皇格雷戈利奥十三世成立了葡萄牙澳门教区,辖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所有毗邻岛屿。从唐·贝尔希奥起,历届澳门主教都由教皇直接任命。1581年,第一任主教唐·莱奥纳尔多抵达澳门,此时澳门教区已先后落成圣·安东尼奥堂、仁慈堂、主教堂、圣母堂及第一所耶稣会学校。1584年,澳门获得与科英布拉和埃武拉同等的城市管理权限。在宗教方面,科英布拉是葡萄牙传教士的摇篮,第一所耶稣会学校于1547年创办。1559年成立的埃武拉圣·思大学是当时培养神职人员的最高学府。
传教士强化教会神权统治地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通过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的影响,促使葡萄牙市民皈依和虔信基督教义。在澳门第一部采用活字印刷的书籍,即博尼法西奥编著的《基督教义问答》(1588年版)的封面素描构图上,描绘了两位高高坐在众多教民头上,正在解答圣经的长老。这部著作的出版及其封面构图的内容,反映出教会掌握着当时澳门半岛上的教育及文化活动,市民及其他人接受的主要是基督教义,并且以入教作为信仰归宿。1594年,耶稣会圣·保禄学院设立,有学生60人,学习葡文、拉丁文、艺术和神学。1623年起,该院附设圣·依纳希奥神学院。1657年,耶稣会圣·约瑟学院设立。1672年圣·方济各修道院开设药房行医以后,各教会团体亦陆续开办提供慈善服务的药房、医院及收养院。1640~1846年,澳门的基督教徒人数一般都保持在五、六千人上下。但有史料记载曾达到一万九千多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八十。1723年,澳门半岛已被耶稣会划分成三个教区。从唐·伊拉里奥主教时起,神职人员便对普通市民的衣着服饰不断提出指责。1777年,议员中的非神职人士被检察官命令,在参加公众活动时得披斗蓬和穿黑色衣服,不得穿礼服。1779年,唐·亚历山大主教在他的《牧师论》中亦指责教徒们的服饰;并且不顾教徒的抗议,要求他们改穿符合传教士观感的衣着服饰。
2.通过宗教裁判,影响行政、司法及市民的社会生活。耶稣会在澳门教区设有宗教裁判所,其成员是当然的教区法官;该职务通常是在耶稣会传教士当中选任。由于教会对议事会及市民大会有着深刻影响,教区法官便得以透过议员选举,公职的任命或推选等途径,从事行政、民事或刑事等方面的司法。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实际上亦削弱了王室大法官的职能。1710年,狄奥戈总督解散议事会之后,召集市民大会推选空缺的法官,但选定的人却陆续站到了圣·保禄学院的耶稣会神甫一边,法官的职务仍然空着。1711年,王室大法官托马斯因执行职责逮捕了宗教裁判所的雇员,便被教皇特使铎罗下令扣押和送往果阿。1727年,热苏斯修士对国王使臣唐·亚历山大平息该年的司法界冲突有如下记述:国王使臣说他们不懂什么法律,不受法律的约束,只是凭意愿和按贿赂行事,歪曲法律,为所欲为(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13~114页。)。耶稣会的宗教裁判所设有监狱。1754年,葡印总督向议事会征求搬迁该监狱的意见,但遭到拒绝;直到1777年该监狱才由耶稣会转移给议事会管辖。宗教裁判所的意见对主教及议事会的决定常常起着重要影响。1758年,该所主判官佩雷拉神甫提议,在当年举行的主佑葡萄牙国王免遭地震之灾的圣像游行中,不准中国人参加,议事会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该项提议。
3.与葡印总督保持松散的行政联系,以利提高教会在澳门的影响力。传教士要在澳门半岛上牢固树立教会组织的权威,必然面对如何处理与罗马教廷、葡印总督及中国朝廷之间的权利关系问题。澳门教区在教会组织的隶属关系上,以及为了宗教传播的最高目的,不可避免得以教皇作为权力轴心。但他们作为葡萄牙的传教士,以及为了达到通过议事会对澳门半岛自治管理的目的,又必须妥善对待与葡印总督的关系。葡印总督作为葡萄牙国王的代表,是东印度葡萄牙殖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传教士一直力求澳门教区与葡印总督之间,保持既不完全脱离,也不过分密切的松散关系,以便为提高和稳定教会神权的地位创造条件。澳门教区成立前,在浪白澳传教的神甫与果阿教会学院保持着直接联系(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3页。)。1573年,教皇开始派遣视察及指导东印度各教区的巡视主教。1583年,第一任巡视主教范礼安神甫(1606年在澳门去世)在果阿设立主教府。此后,历届巡视神甫都由果阿派出,果阿实际上成为教皇管辖东印度各教区的教权中心。
4.通过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论战,削弱对立教派和世俗权力,巩固教会组织在澳门的地位。“中国礼仪”问题是当时澳门教会在不敢得罪中国朝廷,又必须维护其教权地位及文化控制的产物。问题的焦点是传教士如何看待中国教徒祭祖,以及在澳门及中国遵守中国朝廷的觐见礼仪和其它有关传教士活动的规定。随着中国教徒人数增加,以及传教士进入中国受到限制,“中国礼仪”问题愈来愈受到传教士关注,不同的教派对祭祖各持己见,对祭祖在基督教皈依者生活中的地位亦众说纷纭,并且在1700年向康熙皇帝求得有关“中国礼仪”是礼节性的和政治性的解释。处事谨慎的耶稣会传教士最初对“中国礼仪”的辩论有所提防,不想介入与中国朝廷政治及其社会息息相关的宗法礼教的明显对立。然而,1703~1704年,教皇认可了禁止东印度各教区的教徒继续奉守当地礼仪的命令。不久,澳门教区便在“中国礼仪”奉守与否问题上发生耶稣会与其它教派、主教与总督之间的冲突。耶稣会会士是最早登上澳门半岛的传教士。到十七世纪末,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定会的传教士亦来到了澳门半岛。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对基督教义的理解或解释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但耶稣会会士认为自己的是最正统的教派。1705年,教皇派遣觐见康熙皇帝的特使、安蒂奥基亚宗主教铎罗抵达澳门,他此行目的旨在解决耶稣会会士与其他教派传教士之间有关“中国礼仪”的辩论。最早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神甫主张尊重“中国礼仪”,明朝政府规定只向赞同利玛窦神甫观点的传教士发给进入中国的特许证。康熙皇帝对前来觐见的铎罗主教重复了此项规定。但铎罗主教仅以朝廷觐见礼仪的角度片面解释这项规定,并且在1707年禁止中国教徒遵循儒道及祭祀祖先。澳门教区的卡萨尔主教反对这项禁令,先后关押了支持此项禁令的多明我会及奥古斯定会的会员,并且革除了与他们有来往教徒的教藉。1711年,卡萨尔主教创立澳门司铎团,认同有条件奉守“中国礼仪”的观点。1719年,教皇又派遣里斯本的卡洛斯神甫觐见康熙皇帝,希望扭转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僵局,但徒劳而返。不得不于1721年在澳门宣布:允许中国教徒和传教士在奉行教皇命令的前提下遵循“中国礼仪”。1742年,教皇接受了唐·埃乌热尼奥主教的建议,再次对“中国礼仪”提出谴责,并敕令澳门和中国的传教士宣誓服从教廷。随后,澳门的耶稣会传教士及其在中国各个教区的主教,逐步表示了完全服从敕令的态度,这场围绕“中国礼仪”的论战才得以结束。这场论战除有利于巩固教会组织在澳门的地位之外,亦暂时统一了各个教派在澳门和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旨。
三、商业贸易活动以服从和资助教会福音传播为导向
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半岛定居后,很快便形成以澳门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网络。这种海上贸易网络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是背靠中国市场面向海洋,直到十八世纪末此特征才略有改变。其次,以澳门——长崎,澳门——马六甲——果阿/加尔各答为主要海上贸易航道。其三,从澳门开出的商船基本上是采取沿途贩运的贸易形式,没有固定目的地市场。从澳门运出的货物以瓷器、布匹和土产为主,运回澳门的货物则以白银“黄金”以及印度支那半岛或南洋群岛出产的木材为主。其四,从事航运和贸易的商船分官营及私营两类,马六甲被荷兰人占领后,官营船队逐渐瓦解。最后,这些贸易航道同时亦是运送传教士,以及澳门的教会组织与其它教区的教会团体互相联系的通道。葡萄牙人曾试图在该贸易网络内建立贸易垄断,但在当时中国朝廷的贸易制度限制下,以及在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接踵而来的对贸易航线争夺的排斥下,这项打算始终难以得手;贸易垄断的建立或由此偶尔形成的贸易繁荣景象都非常短暂。
在澳门,葡萄牙商人通过对外贸易赚回的财富除私人及其家庭的开支和储蓄外,有三条主要使用去向:第一,缴交议事会财政官征收的税款和其它临时性的公务费用。第二,向教会施舍捐献。第三,其它公共用途的集资(如船舶保险金,以及为了抵御海盗和其它海上侵扰得由私人出资的项目,包括供养城市护卫队队员及修造战船)。
议事会征收的税款按照其用途主要分成两类:一类为王室财政用途的税收,另一类为议事会本身财政用途的税收。税收采用抽盘形式,议事会司库的监秤官负责税收管理。在官营贸易船队趋于瓦解时,葡印总督曾要求澳门议事会实行单一税率,即所有货物包括白银及药材都以百分之五抽盘,但遭到反对。1719年议事会对若干货物规定的税率分别为:粗布百分之八、细布百分之四、白银百分之二。议事会在财政紧绌时,得适当提高税率予以弥补。1783年,葡萄牙国王玛丽亚一世敕令在澳门征收缴交王室的百分之四转运税,使议事会的实际税收税率超过了百分之五。从税率的变化上反映出议事会在税收方面的两个特点:其一,鼓励船主和商人在从事对外贸易时尽量赚取白银、黄金回澳门;其二,官营贸易船队瓦解之后,其担负的王室财政责任被转移给普通的船主和商人,并且王室财政负担在税收中占较大比重。
议事会本身财政收入的开支主要有以下几项:a.向中国朝廷缴纳的澳门半岛借居年租(俗称地租银),以及向中国朝廷申领出海贸易准照的费用。b.议事会行政运作开支。c.有关防务方面的开支。d.对教会的资助。除d.项外,其它几项亦不同程度与教会有关。议事会在财政开支安排的优先次序上得先考虑教会方面的态度。此外,议事会透过传教士要求免缴地租银的活动从来没有终断过;1714年,卡多索神甫由广州致信议事会,答复议事会询问的免交地租银之说是虚假的。议事会从成立时起,一直受教会尤其是耶稣会神职人员的控制,有关议事会行政运作的开支,基本上亦是教会头面人物的活动费用。在防务支出方面,议事会发给的兵饷相当微簿;但教会神职人员不仅是民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炮台、火炮设计及修造的主要参与者或承担者。但是,严格分别教会方面占议事会财政支出的比重,既不可能亦没必要。议事会财源匮乏时,借款和拍卖资产是常用的筹款方式。借款对象包括澳门市民、教会团体及神职人员,乃至邻近国家的首领。除基本的抵押形式外,在澳门通过对市民大会的承诺,在澳门以外凭友好关系亦是重要的借款条件。
议事会对教会的直接财政资助包括几个方面:a.神职人员的薪俸。1633-1634年,有几批圣·方济各会修女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托莱多来到澳门,每月享有五十两白银津贴;1777年,议事会出资建造的新主教府落成。b.教堂及教会团体的传教活动及其本身管理费用的不足部分。1685年起,每年出资在教堂举办感激守护神圣·若奥·巴蒂斯达保佑澳门的九日祭;1703年起,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得到以每年税收百分之一发给的财政补贴;1710年,议事会去信葡印总督,赞同其有关改变主教供款的决定;1721年起,每年拨给圣·奥古斯定修道院八十两白银;1757年,拨款帮助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唱诗班;1784年,商定有关圣·约瑟学院修缮、神甫薪俸、及其神学院费用补贴等事宜;1795年,分别对主教座堂、圣·老楞左堂、圣·安东尼奥堂进行修缮。c.教会开办的慈痒机构及其活动。1789年,议事会与仁慈堂已合办了一所孤女教养院及两所慈善医院。d.教皇使臣、使团途经澳门时的路费补充。1751年,议事会司库费尔南德斯携带布匹,陪同教皇的传教使团前往日本,作了一次在贸易及宗教上均无收获的航行;议事会特此记载:神甫们指望议事会负担使团、贡品的费用,为的却是传教团的利益,但最后还得由神甫们自己及一些私人出资,因为运去日本的布匹又运回了澳门,神甫当中除有一位返回澳门外,都在日本躲藏起来。
据《澳门城的描述》记载:约在1635年,澳门半岛上有八百五十位已婚葡萄牙人,他们的子女很健壮,都有几个奴仆;另外还有一百五十位未婚葡萄牙船员,部分是拥有五万多葡印金币的富豪;富商都不愿迁往果阿或将财富献给国王。然而,葡萄牙船主、商人和船员却对澳门教会非常恭顺虔诚。具有这种心态的根源,除对基督教义的虔信外;一是入教可以得到教会的恩惠,二是祈望上帝保佑海上航行安全及通商贸易好运。1570年教皇敕令,凡在中国、日本和马鲁古入教者免除十五年抽盘(估计澳门没有采用什一税制,仅订定比什一税制优惠得多的贸易抽盘税制)。1620年,从澳门开出的圣·巴尔托罗梅乌号,在前往日本途中遭荷兰人袭击,船上的商人们保证,只要他们能生还,一定在澳门建造一座圣母小教堂,他们履行了诺言,将捐款委托给了奥古斯定修道院;1622年,该小教堂举行了首次弥撒。向教会施舍捐献的形式是多方面的:1712年,市民罗得里格斯留给仁慈堂二百两白银遗产,其中一百两用于孤儿和寡妇,五十两用作弥撒。1713年,市民法瓦肖向教会捐献三千枚葡印银币,其中一千枚每年给某个葡国人或修士名下的仁慈堂孤女提供嫁妆:另二千枚捐给仁慈堂和望德圣母堂,其中用于白银库存、孤儿和寡妇的分别为一千枚和五百枚。1716年,取稣会神职人员接管了议事会的慈善机构孤儿金库,该金库负责接受和发放死者的遗产。1718年,市民法瓦肖死后捐给教会的遗产包括:二十个孤女的嫁妆,澳门圣母堂作弥撒用的四百枚葡印金币,以及让耶稣会管理澳门与交趾支那贸易的权力。1737年,船主弗乌梅斯死后交给教会两类遗产:一是让仁慈堂收取几项债务,二是给司铎团白银一千两。
澳门教会得到的财政收入及教徒的施舍捐献,大部分是拨给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不仅如此,1729年,澳门教会还从马尼拉抽运大量的教徒施舍捐献,拨给在中国的传教士,以支持他们的传教活动(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15页。)。与澳门普通市民一样,教会神职人员亦盛行讲排场风气,这在弥撒活动方面尤其突出。由于缺乏严格的财务管理,各教派团体及教堂的财力浪费现象很严重。这些因素促使当时澳门教会的神职人员非常重视关系到教会财富来源的海外贸易。传教士不仅关注澳门葡萄牙船主和商人的贸易状况,而且直接参与贸易活动,或为船主和商人尽可能提供必要条件(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72页。)。在1630~1645年尝试恢复澳门与日本通商贸易关系的时期,传教士不仅支持议事会的要求,即葡萄牙船主和商人恪守对日贸易信誉,归还欠日本商人的债务,暂时不能归还,须取得延期支付的准可;惩罚在对日贸易中令日本商人及澳门商人遭受损失的船主和商人,没收故意拖欠日本商人货款者的白银;而且支持议事会摈弃西班牙王室禁令,扩大对马尼拉的贸易规模;告诫马尼拉教会方面不得再向日本派遣传教士,以避免澳门的贸易船只及财物在日本遭焚烧,另外还派团赴日本谈判;当谈判使团在日本被害后,其家属得到以储存在神学院的货物支付的赔偿。1674年,教会神职人员提醒议事会注意檀香木贸易对澳门财政收入的重要性。1685年,借护送在澳门翻船落海的日本船员返回日本的机会,再次尝试恢复对日通商贸易。澳门主教、官员及元老们商定,用葡萄牙船护送日本船员有希望感动日本解除贸易禁令。曾任日本教区总务长的菲埃切神甫等几位市民提出愿为购买所需船舶出资,但仍以国王赴马尼拉使臣塞格依拉的圣·保罗战舰担负此次使命;通过耶稣会托马斯神甫在广州取得满清朝廷的出航准照;出航前澳门主教特意在圣·保禄学院举行九日祭,各教派的传教士亦与教民们举行祈祷,祈求上帝保佑此次航行能恢复澳门与日本的通商;但此次航行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为了能让财力不足的普通市民参与澳门对南洋群岛的通商贸易,尤其是对帝汶的檀香木贸易,澳门教会的慈善机构仁慈堂、主教堂司铎团司库分别提供借款,利息约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1710年,议事会有条件地接受了葡印总督将部分对主教的供款转移到印度使用的决定。这些条件包括:总督不介入议事会管理,澳门船只享有帝汶檀香木贸易优先权,去果阿贸易的澳门船只免于抽税。1712年,阿尔内多神甫作为交趾支那国王的通商贸易使臣抵达澳门。1719年,议事会在两位重要商人沙勿略和克依罗斯神甫的反对下,放弃葡印总督有关每年只派四艘船往雅加达贸易的决定,改让船主们自由前往,因为雅加达港口不仅租船收入大,而且澳门与雅加达的海上贸易可给议事会创造约三万两白银的税收。澳门的传教士还是最早注意及参与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商人之一。约从雍正年间时起,已有不法商人通过澳门向中国走私鸦片。当时,满清朝廷上下官吏热衷于吸鼻烟,以及向澳门索取鼻烟的消息,不断由传教士传到澳门。1770年,荷兰人布朗·胡克吉斯特说:在澳门赚钱最多的是印度鸦片。1775年,澳门主教唐·亚历山大向议事会提议关注鸦片贸易。翌年,他又向葡印总督提出允许外国商人租用澳门船只,把鸦片和想运来的其它货物运进澳门的建议。1792年,议事会以投票决定,反对满清官府在澳门设立鸦片稽查的做法。
教会神职人员在以高利息借出白银的同时,对帮助议事会摆脱财政困境,常常显得迫不得已。1713年,议事会数次筹款以摆脱财政困境;其中一次,教会团体及其神职人员只答应借给所需款项的三分之一;议事会寄以厚望的圣·保禄学院神甫说:议事会应该公布税收支出项目及筹款用途,如果需要很紧迫,议员、总督及官员都得出资,议事会要将得款尽量存储备用;从议事会没有建立严格的财务账目,及其本身是受教会神职人员影响和控制的角度可以说明,当时澳门教会对白银等财富的需求非常迫切;这种状况亦是教会必须满足其传教扩张需要的反映。然而,1714年,若泽和克利安两位神甫却促使议事会作出决定,为庆贺康熙皇帝执掌朝政五十三年敬献贡品;耶稣会的会员们也加入了敬献贡品的行列。
传教士对海上贸易的关注及参与尽管充满了早期重商主义的色彩,但他们当中一直占上风的态度却是:不鼓励在澳门实行自由贸易,甚至阻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季节暂停期间在澳门从事贸易活动,以排斥异教徒势力可能对传统教权地位带来的损害。(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19~120页。>%1732~1733年,议事会讨论澳门实行开放贸易问题;对此,议员及教会内部都有分歧;结果以澳门主教卡萨尔为首的,担心澳门的宗教风俗会被外国人改变的意见,迫使议事会放弃开放贸易的打算。1773年,议事会讨论外国商人定居澳门问题;结果议事会仍决定奉行已采用多年的办法,即外国商人居住澳门得有条件:a.不准建立住宅,得携同家眷乘坐澳门船只抵达澳门;b.绝对不允许在澳门从事贸易活动,只可投资经营普通的零售店铺;c.外国贸易公司头目本人得接受议事会规定的贸易活动范围。但澳门方面亦不敢执行葡印总督驱逐外国商人的命令。1776~1777年,吉马良斯主教对议事会说:外国商人的竞争使澳门损失严重,但在澳门这块土地上驱逐外国商人是毫无意义的。葡萄牙人的这些规定,不是奉守当时中国朝廷的市舶、公行贸易管理制度的反应。按照中国朝廷的政策,澳门是有条件保持仅次于广州的贸易港地位的。中国朝廷除禁止澳门传教及走私鸦片外,没有禁止过澳门的对外贸易,满清海关在澳门设有负责税务的“关部”,澳门一直与香山、广州保持着民间贸易。进入十八世纪以后,部分葡萄牙商人逐渐接受了荷兰人、英国人的自由贸易经营方式,如1753年在里斯本成立专营印度、澳门贸易的葡萄牙亚洲航运公司。但是,澳门教会却不支持澳门和其他欧洲商人实行贸易开放,米格尔神甫在1730年以前已提出的,在澳门创建贸易公司的建议一直得不到响应。这种状况除说明当时葡萄牙人与其他欧洲商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外,还说明澳门教会的传教士担心开放澳门的贸易对广州可能构成竞争,最终仍会导致中国朝廷对澳门贸易地位的干预,以至进一步威胁教会组织在澳门的存在。但这种状况亦必然会令澳门的贸易逐渐衰弱。
葡萄牙传教士以澳门作为大本营向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与后来英国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倾销鸦片,掠夺资源一样,本质都是殖民主义侵略。但彼此的殖民主义性质的经济贸易活动目的,特别在贸易盈余的用途方面是不尽相同的。教会组织的传教士对澳门海上贸易活动的关注及参与,目的是开辟财源以巩固教会在澳门的统治地位,支持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然而,葡萄牙人推行的这种殖民主义方式,在当时只能向葡萄牙殖民帝国本土提供极其有限的物质利益,其在澳门和中国的传教活动发展及收获亦不稳固。这是葡萄牙人在1840年以后,追随英国人对中国进行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根源。葡萄牙人似乎此时已意识到以武力作后盾,依靠其它殖民主义列强,将无形的与有形的鸦片结合在一起的殖民主义方式,将会是最能获得效果的殖民主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