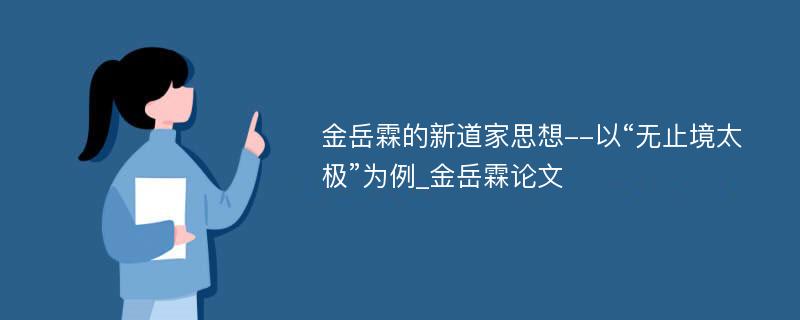
金岳霖的新道家思想——以“无极而太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极论文,太极论文,道家论文,为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3)01-0031-07
任何时代哲学思想的创造,都离不开对以往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资源的利用和借鉴。这种对传统哲学资源的利用借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实质性继承,却采取了某一时代流行的话语和言说方式;另是对传统哲学概念和术语的“租借”,却将其实质性的内容予以“剥落”或“剥离”。前者,可称之为“新瓶装旧酒”;后者,可称之为“旧瓶装新酒”。金岳霖在《论道》一书的“绪论”中说:“我在这本书里的用字方法就是普通所谓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向来不赞成旧瓶装新酒,如果名目可以假借,则货不真,价不实,而思想底混乱是难免的结果。我深知道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底毛病,尤其是所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其所以明知而故犯之者就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的情感转移到这本书一部分的概念上去。”[1](P17)金岳霖的《论道》一书是“旧瓶装新酒”的典型形式。书中许许多多重要的范畴和概念,都取自传统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但《论道》一书之主旨,与其说是对宋明理学思想的继承,毋宁说是对道家思想的发挥。然而,处于20世纪中西哲学交汇之点的金岳霖,其哲学思想又不是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简单重演,而有对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怀特海哲学的重要吸收。下面,将围绕《论道》一书中“无极而太极”这一命题,对金岳霖的新道家思想加以分析。
一、“无极”:道之根
《论道》顾名思义,是论“道”的著作。“道”是道家思想的最上位概念,亦是《论道》一书的核心观念。《论道》中对“道”有各种各样的解说,如说“道是式一能”,“道不一”,“道无量”,“居式由能莫不为道”……等等。最后,金岳霖在书的结尾写道:“无极而太极是为道。”这可说得上是关于道的一个总结性的定义。
问题在于:“无极而太极”本是宋明理学的术语,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以人道服从天道,视包括人类生活在内的整个宇宙世界为一“天演”的洪流,其对“道”的理解属于道家思想范畴殆无疑义,可是,他为什么不采取“接着”道家思想讲的形式,却偏偏要采用宋明理学的范畴和命题来表达他关于“道”的思想呢?依我看来,这大概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因为先秦时代的原始道家,无论老子或庄子,其哲学思想的表达都用“诗意”的语言出之,富有形象性和象征性,而经过西方近代哲学洗礼,尤其是以逻辑分析见长的金岳霖,觉得运用老庄式的语言和运思方式,不易传达出他本人的哲学思想;比较而言,倒是宋明理学的许多术语和范畴,却更适合于他用来进行语义分析。其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作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对“无极而太极”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而由于中国语言的多义性和歧义性,一旦改变了语境,它完全可以被瑛予一种新的意义。这就为金岳霖运用传统的术语名词概念来阐发他的新道家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我们看到,金岳霖的天道观,正是从区分“无极”和“太极”开始的。
与宋明儒普遍将“无级”等同于“太极”不同,金岳霖认为,“无极”与“太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宋明儒将“无极而太极”中的“而”理解为修饰词,从而可以在“无极”和“太极”之间划等号。金岳霖则不然,他说,“无极而太极”中的“而”是一个动词,故“无极而太极”表明的是整个宇宙洪流的天演过程。在《论道》中,金岳霖赋予“无级”一词如下几重含义。
第一,“道无始,无始底极为无极。”[1](P178)在金岳霖哲学中,道是宇宙的别名,而道或宇宙是没有始终的。这里所谓无始终,简单的理解就是不占有时间的意思。下面这段话,金岳霖将占有时间与不占有时间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从前的人已经说过道无终始,物有死生。这两句话在本书里也很有道理。用本书底语言说道无终始就是说式与能无终始,说它们无终始,就是说它们无所谓终,无所谓始。物大概就是所谓东西或事体。果然如此,则物占时间,所谓物占时间,就是说物有死生。也许物之中有很特殊的物如天文学家底‘宇宙’;这样的‘宇宙’既然是占时间的物,当然不是真正的宇宙,当然有终始,当然有死生。总而言之,道为道,物为物,物有生死而道无终始。”[1](P27-28)从这里可以引出如下意思:道无始,是说无论把任何有量时间以为道的始,总有在此时刻以前的道。或者说,从任何现在算起,把有量的时间往前推,推得无论如何的久远,总推不到最初有道的时候。看来,说道无始,其意思并不太难理解,问题在于:既然说道无始,为什么又要说“无始底极”,这“极”字岂不与道无始的说法相矛盾?金岳霖的解释是:这极是极限的极,是达不到的极。他说:“它虽然是达不到的,然而如果我们用某种方法推上去,无量地推上去,它就是在理论上推无可再推的极限,道虽无有量的始,而有无量地推上去的极限。我们把这个极限叫做无极。”[1](178)可见,金岳霖理解的无极与朱熹所说的无极或太极并不是一个意思。在朱熹那里,太极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活动之理。他说:“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是则所谓太极也。”[2]关于无极就是太极,朱熹是这样说的:“原极之所以得名,盖取枢极之义。圣人谓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谓之无极者,所以大无声无臭之妙也。”[2]而在金岳霖看来,无极并无万事万物活动之理的意思,它只不过是不断上溯宇宙起源或发生时所达不到的一种极限状态而已。
第二,“无极为无,就其为无而言之,无极为混沌,万物之所从生。”[1](P179)金岳霖认为,我们现在的世界是“有”,这所谓的“有”是有分别的有,有这个那个的“有”。每一个“有”从前都有“无”的时候,现在所有的“有”从前都有“无”的时候。现实没有开始的时候,所以在事实上我们不能从现在的“有”追根到“无”,可是,这样的“有”的极限总是这样的“无”。要注意的是,金岳霖所说的“有”是有这个有那个的“有”,所说的“无”也是无这个无那个的“无”。无这个无那个就是无分别。在这种意义上,无极是混沌一片,是万物之所由生。对于金岳霖来说,说无极是无,并不是说它是绝对的“无”或空无所有的“无”;能生“有”的“无”仍是道有——“有”中的一种,所谓无者不过是无任何分别而已。在这方面,金岳霖所说的“无”与《老子》中“‘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中的“无”的意思相当。
第三,“无极为极,就其为极而言之,无极非能而近乎能。”[1](P180)无极是混沌,这混沌到底是什么呢?首先,这混沌不是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那时候天地未分,还没有占据时空的物质形式的存在。但这混沌又不是虚无。金岳霖认为,无极表示的是老是现实的可能还没有现实。他说:“无极是极限,从极限之不能达这一方面着想,无极仍是无始;从极限之为极限这一方面着想,虽在无始中有些可能老是现实,而在此极限中它们还没有现实。”[1](P197)可见,说无极表示老是现实的可能还没有现实,这当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它是现实的,表示它不是单独的能,所以非能。其二是说这些老是现实的可能还未现实,所以是近乎能。无极非能而近乎能,假如换一种说法,可以理解为无极表示的是一个先验的世界。所谓先验的世界是说经验可以没有,我们这样的世界可以没有,而式不能没有,能不能没有,现实不能没有。
第四,“无极为理之未显势之未发”。[1](P184)在金岳霖哲学中,“理”可以理解为共相的关联,势则是殊相的生灭。无极是混沌,它不是能而近乎能;它是现实,可是,它虽是现实,而它是混沌的现实。在这混沌的状态中,当然有共相的关联,当然还是有理。这当然的理的根据就是那不能不现实的现实。但金岳霖接着指出,无极所有的理虽然一方面近于纯理,可另一方面,就此理与彼理的分别而言,它又非常晦涩,此所以说无极为理之未显。所谓无极为势之未发,是说在无极能还没有出入,能既没有出入,则无殊相的生灭。所以说无极为势之未发,其实是说无极无势。不过,在金岳霖看来,因为无极是无始的极限,事实上它是达不到的,如果说无极无势,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势是从无到有的,所以他宁可说无极为势之未显。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金岳霖的“无极”一词虽采自宋明理学,却与宋明儒的理解有相当大的距离。金岳霖关于无极的思想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中得到启发是殆无疑义的。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提出,现实的存在是由其生成的历程构成的;离开生成的历程,绝不可能有任何的存在。为了进一步说明事物变动,尤其是新事物出现的原因,怀特海还提出了“创造”这一终极范畴。他说:“创造没有它自己的特性,正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matter)亦不具有自己的特性。……它不能被特性化,因为所有的特性都比它本身更为特殊。但是创造总是在诸条件下被发现到,而以条件加以描写。”[3]这里,怀特海把创造视为终极的,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创造构成一切实际存在体的普遍的形上特性,因此,它是终极的;其次,现实事物是创造的个体化,它是终极的。看来,正是从怀特海的“创造”中,金岳霖悟出了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一语包含的丰富意蕴,并将它提升为宇宙的根本原理,如果说“无极而太极”是一不息的活动的话,那末,无极无疑是创造之源,它本身包含着一切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同时还应注意到,金岳霖哲学中的“无极”一词又并非怀特海的“创造”一词所可以完全置换,对于怀特海来说,创造的历程是由繁多创生一体的过程,而对于金岳霖来说,创造的历程,或“无极而太极”的过程却是由一到多,由混沌到清楚明晰演化的过程。此外,金岳霖与怀特海之间更重要的一点区别是:怀特海在进一步解释“创造”这一终极原理时,还同时提出“上帝”的概念来加以补充。怀特海在解释“创造”时之所以引入“上帝”的范畴,说明他脱离不开西方的传统。而金岳霖在解释“无极”一词的意思时,则明确表示无须再借助于“上帝”。他说:“如果我是欧洲人,谈无极之后,也许我就要提出上帝,那是欧洲思想底背景使然。这里的无极不是推动者,所以它不能做欧洲式的上帝。能没有开始出入的时候,也不能有欧洲式的上帝开始去推动它。”[1](P185)从金岳霖拒斥引入“上帝”概念来对“无极”加以解说可以看到,金岳霖虽然从怀特海哲学中得到启发,并且接受了怀特海的不少说法,归根结底,他的本体论思想却是据于中国传统的。
二、“无极而太极是为道”
在谈论宇宙洪流中个体的变动时,金岳霖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变动之极,势归于理;势归于理,则尽顺绝逆。”[1](P193)这段话对于理解金岳霖的天道思想十分重要。它表明:在金岳霖眼里,个体的变动尽管是生灭无终的过程,但这过程的发展依然有个方向。这方向,金岳霖称之为“势有所依归”。势有所依归是归于理;势归于理是不可达的,但它是个体变动的方向。一旦果真是势归于理,则“尽顺绝逆”。
对于金岳霖来说,这“尽顺绝逆”的状态是不可达的,而只是个体的变动的历程的一种极限状态,这种极限状态,称之为太极。太极是与无极相对应的概念。金岳霖说:“道无终始。无论以什么有量时间为道底始,在那时间之前已经有道;无论以什么有量时间为道底终,在那时间之后,道仍自在。道虽无始,而无始有它底极限,道虽无终,而无终也有它底极限。无始底极,我们叫做无极。无终底极我本来想叫做至极。可是,既有太极这名称与无极相对峙,我们似乎可以利用旧名称把无终底极叫做太极。无极既不是道底始,太极也不是道底终。追怀既往,我们追不到无极,瞻望将来,我们也达不到太极。”[1](P194)
前面说过,金岳霖所说的“无极”不同于宋明儒所说的“无极”。他所谓的“太极”与宋明儒所说的“太极”也是两码事。在《论道》中,金岳霖着重阐发了太极的如下几方面的含义:
第一,“太极非式而近乎式”。[1](P198)金岳霖在讨论中指出,在现实的历程中,各种各类的可能或者同时地或者相继地或者相隔地现实;不能不现实的固然现实,老是现实的可能仍然是老是现实的,不可能当然是不可以现实,老不现实的可能也仍然是老不现实。可是到了太极情形就不相同。虽然一可能即在太极仍为不可能,而老不现实的可能即在太极也就现实。所谓老不现实的可能包括像空无所有的“无”、“将来”、“空线”、“时面”等等,这些可能在太极都现实。太极是与无极相对称的概念。在无极老是现实的可能还没有现实,在太极老不现实的可能却已现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无极不可以不现实的仍不可以不现实,在太极不可以现实的仍不可以现实。金岳霖特别强调,在太极不可以不现实的,老不现实的,及其他许许多多未淘汰的可能都现实。太极是充满现实的境界。从充实这一方面着想,太极最充实不过,所以它不是那仅是可能的式。再从可能的数目来看,太极与式的分别也很清楚:式是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而太极不是无所不包的可能。以上强调的,是太极非式的一面,为什么又说太极近乎式呢?这是因为在太极势归于理。所谓势归于理就是势理合一。金岳霖说,在现实的历程中,势虽依于理而不完全达于理,而在太极势归于理的情形下,理势都纯。势归于理的理是纯净清洁的理,此所以说太极非式而近乎式。
第二,“太极至真,至善,至美,至如”。[1](P196)在日常生活中,真、善、美的分别非常之大,它们是分开来说的。而在太极就不同,即以真而论,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命题欠关联,真与一致是两件事,在太极因为势归于理,所有的命题都四通八达地呈现共相的关联,所以只要真就是一致,只要一致也就是真,真与一致是合一的。可是,就真本身说真只是分别地说真,还不是综合地说太极。果然综合地说太极,太极的真就是太极本身,太极的善与美也是太极本身,所以它们没有分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论道》中,金岳霖一直没有正面涉及到善与美的问题,在讨论太极的时候,也没有对善与美下一明确定义;他提出太极是至真、至善、至美,就因为太极是绝对,在这种情况下真就是美,美就是真,而它们也就是至善。这样看来,金岳霖与其说是注重对太极是至善、至美作逻辑式的推理,毋宁说是在表达他对太极应为真、善、美合一境界的一种追求。也许正因为太极是真、善、美的合一,所以金岳霖称太极为至如。他解释“至如”说:“虽然道莫不如如,而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情不尽性用不尽体,万事万物各就其本身而言都不完全地自如。在现实底历程中任何一阶段,万事万物都在那不均衡的状态中,无时可以安宁,无时可以休息,所以无时不在相当紧张状态中,这就是说它们都不完全自在,不完全自在,当然也就是不完全自如。在太极情尽性,用得体,万事万物莫不完全自在,完全自如。……太极不是不舒服的境界,它不仅如如,而且至如。本书底道本来是如如,可是,最低限度是如如,最高很度是至如如,简单地说是至如。”[1](P197-198)这是一段极富于哲理而又极富于抒情的文字。其所以富于哲理是因为其中融入了作者丰富的人生体会与体验,其所以富于抒情,是由于其中饱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执著追求与热情。这里,作者一洗其在《论道》的其它地方刻意追求语义分析的风格,借“至如”一词直抒他追求人生美好境界的情怀。作者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崇尚道家崇尚自然,以及将人融化入自然的“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但无论老子还是庄子,其道家思想又流露出逃避现实,认为理想人生已成远古过去的那么一种消极的情绪,而金岳霖的天道观则是建立在近代进化论的基础上的。他尽管承认现实不如人意的东西实在太多,也就是他所说的“情不尽性,用不得体”,但他认为,天道毕竟是自无极而太极的过程,社会与人生既然为宇宙洪流中的一部分,自然也就融入了这一过程。也正因为如此,金岳霖在谈论天道观时,不满足于“如如”,而要确立一“至如如”的太极。
第三,“自有意志的个体而言之,太极为综合的绝对的目标”。[1](P195)对太极的这一看法,反映出金岳霖的“道论”不同于中国原始道家思想,而有接受了西方人类中心观思想影响的一面。金岳霖认为,“无极而太极”固然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演”过程,但是,人却又是有意志的动物。那么,人的意志在“道演”过程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呢?金岳霖从两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一方面,在现实的历程中,会有有意志、有知识、有心灵的个体出现,“自道而言之,万事万物莫不如如,这样的个体未出现,道固然是道,这样的个体出现,道仍然是道”。[1](P195)另一方面,“自现实底历程而言之,这样的个体出现,而天下中分;有这样的个体本身的现实,有相对于这样的个体而非这样的个体本身的现实。前一方面的现实可以修改后一方面的现实,后一方面的性可以为前一方面所了解,后一方面的尽性能力可以因前一方面的意志而减少或增加,在这样的个体出现后,现实底历程增加一种主动力。”[1](P195)可见,金岳霖是不仅承认人的意志,而且承认这种意志是有修改现实和改变现实的能力的;换言之,人在现实的历程面前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完全被动地适应现实或环境。不同于西方人类中心观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无论有意志的个体出现与否,道仍然是道;有意志的个体参与和改变现实的历程,归根结底依然属于“道演”。但是,正因为出现了个体的意志,故这种“道演”在有意志的个体的眼里,似乎不再是一种盲目的过程,而是奔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太极”。金岳霖解释说:“有意志的变动出现,目标也出现。目标底现实虽在未来,而目标之所以为目标至少是因为它在现在已经是思考底对象。这就是说我们可以讨论,可以想像,可以思议未现实的目标。未现实的目标当其未现实总是理想的。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以往不知即不能言,可是,对于将来,虽不知而亦能言,因为对于将来,主动的个体有盼望,有追逐,有理想,有要求,对于将来,如果我们是主动的,我们所言的不过表现其在自我而已。关于一个体底自我,该个体总有发言权。”[1](P195)这话的意思是说,太极之作为目标,是对于有意志的个体而言的;离开了有意志的个体,太极虽然至真,至善,至美,但无极而太极只是一个不断地“情求尽性”的过程,它无所谓目标不目标。金岳霖关于“自有意志的个体而言之,太极为综合的绝对的目标”的提法,实际上已深入到关于人类活动的历史哲学的领域,是在为历史哲学中人类活动的自由与必然这对范畴的关系作本体论的论证。他说:“太极是变动之极,是势归于理;在那势归于理底状态中,各个体情都尽性用都得体。可是,有些个体是有意志的个体,有意志的个体底意志与它们底意志也是顺顺逆逆中或范围较小的冲突与调和中的情求尽性用求得体而已。它们一时一地的目标是它们一时一地的求尽性。性不会尽,它们底目标不会完全地绝对地达。老有求尽性,老有目标,而尽性也就是它们底总目标。……自有意志的个体而言之,太极是它们自我底极限,虽未达而亦能言。”[1](P196)人类历史活动潮流中的自由与必然就这样被解释为“情求尽性”的过程。而且在金岳霖看来,只有在“太极”那里,自由与必然才会合一,它是人类活动的极限,也是有意志的个体自我实现的极限。
总括起来,金岳霖的“太极”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蕴。尽管在金岳霖看来,“道演”是无终点可言的,但他还是为“道演”定了一个发展的极限处,称之为“太极”。有了“太极”,“道演”方才有方向可言;作为有意志的个体或人类,也才有既定的目标与理想。金岳霖认为,尽管“太极”是不可达的,作为理想,它永远是理想,但这理想却不是在遥远的过去,却是在将来。这是金岳霖与追求“返朴归真”的中国原始道家的区别所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从金岳霖对有意志的个体的肯定来看,他并不像原始道家那样摈斥理性与知识,而是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只不过,他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的进步与进化离理想的状态还相差实在太远。这里所谓人类的进步与进化,主要不是指技术、物质方面的进步,而是指人性的进化与进步。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金岳霖对“道演”的看法就不像原始道家的淡泊和自如,而似乎多了中国儒家的那么一份悲悯之情。他一方面对“道演”的过程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现实底历程是有意义的程序。这就是说现实底历程不是毫无目的,毫无宗旨的,它不仅是历程而且是程序。……即以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而论,人类本身我们不能不说有进步,虽然以道观之我们不免沧海一粟之感,而小可以喻大,这点子成绩也可以表示现实底历程不是毫无意义的历程。这历程既是有意义,同时也是一种程序。”[1](P203)另一方面,他却又对人类未来的发展表示深深的关切,他写道:“在太极有好些现实总是要淘汰的,历史上的野兽免不了已经淘汰。切己的问题当然是人。……我个人对于人类颇觉悲观。这问题似乎不是人类以后会进步不会底问题。人之所以为人似乎太不纯净。最近人性的人大都是孤独的人,在个人是悲剧,在社会是多余。所谓‘至人’,或‘圣人’或‘真人’不是我们敬而不敢近的人,就是喜怒哀乐爱恶……等等各方面都冲淡因此而淡到毫无意味的人。这是从个体的人方面着想,若从人类着想,不满意的地方太多,简直无从说起。人类恐怕是会被淘汰的。”[1](P203)但是,综观《论道》全书,却毕竟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的。金岳霖认为无论人类会淘汰与否,绝不会影响到“道演”的进行。因为从究竟义来看,人道只是分开来说的道,而只有“无极而太极”才是合起来说的道。所以,《论道》一书最后以如下一段话作结:“无极是道,太极是道,无极而太极也是道;宇宙是道,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也莫不是道。……道可以分开来说,也可以合起来说;宇宙则仅是就道之全而说话的一个名词,此所以我们可以说天道,说人道,说任何其他的道,而不能说天宇宙、说人宇宙……等等。”
收稿日期:2002-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