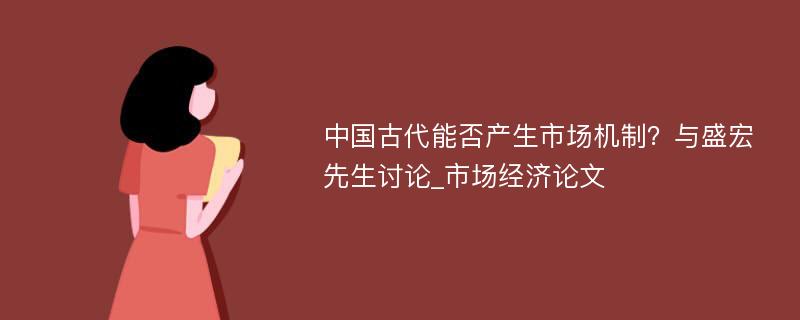
中国古代能产生市场机制吗?——兼与盛洪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市场机制论文,洪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中,盛洪的文章比较富有历史感,这与他曾经从事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有关,但他对中国经济史的几点结论,我认为值得商榷。如他断言:“受儒道两家自然秩序哲学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是一个(非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因而在经济领域引入西方的市场制度,并无大的冲突。”(盛洪:《治大国若烹小鲜:关于政府的制度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又说:“中国经济在产权制度上的进步领先欧洲达十五六个世纪。”(盛洪:《经济学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6页)判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过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仅仅依据古书上对市场行为或现象的文字记载还不够,因为“市场古已有之”,“只有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肺腑内脏’,以及它所运行的社会环境进行双重解剖,才有可能理解中国古代特殊的‘市场经济’,特殊的市场‘生理’机制。”(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产权制度也是这样。为了揭示这种特殊性,厘清中国古代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应该是有益的。
改革开放初期,吴慧先生写过《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把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北宋的王安石和明代的张居正称为古代的经济改革家大致没错,因为他们设计并实施的经济政策或者明显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或者有效地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前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后者维持了封建政权的延续。那么,他们的改革举措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管仲的改革措施包括税收上的“相地而衰征”、农业上的“无夺民时”等,但最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并主张定四民之居,“勿使杂处”。他采取的办法是“参(三)其国而伍其鄙”,即把国都分为士、工、商三部分共21乡,其中士居15乡,工、商各3乡,其余的农村分为五属,全部安置农业人口。与这种凝固的人口管理相一致,4种社会职业是世袭的,照管仲的说法,此举能使未来的就业者“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显然,这样一种约束型的人口政策,从根本上杜绝了劳动力的地区流动,也堵塞了人们自由择业的途径。
商鞅的变法以统一度量衡、废除井田制、推行重农抑商、实行法制、奖励军功、建立郡县制等为主要内容,其中准许土地自由买卖最受后人的褒贬。贬之者说中国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土地兼并顽疾即缘于此;褒之者则把它誉为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如盛洪便依据“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认定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建立了“准现代”的经济制度(《经济学精神》,第106页)。其实,细加考察不难发现,商鞅变法后中国的土地状况与现代意义上的产权绝不可同日而语,王家范先生曾从两个角度论证了这种土地产权的残缺性:1.农民从占田制、均田制等政府法令中获得农业生产资料,表明他们本质上是封建国家的佃农;2.西汉以后朝廷经常实施抑兼并政策,这说明即使是大地主也不拥有稳固的土地占有权。(《中国历史通论》,第126~139页)另一方面,商鞅变法对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限定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众所周知,商鞅对人的求利本性是承认的,但他强调统治者必须对此加以规制,所谓“利出一孔”,就是让人们只能从农业中获得他们所追求的名和利。为了“令民归心于农”(《商君书·农战》),商鞅制定了许多优惠激励措施,如减轻农业税,增产粟帛的农民可以免除徭役,有余粮上交者可以得到官爵,提高粮食的价格,官吏不得违法而害农,等等。与此同时,对其他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社会活动则给予抑制,如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提高酒肉的征税以使其价格上升从而限制经营商牟取厚利,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商人及其奴隶都要服徭役,至于奢侈品的生产和销售,更是遭到严令封杀。在古代社会中,农业作为主导性的经济部门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从长远来看,工商业的规模受制于农业的剩余率,但前者的存在又从流通、技术和资金等各方面为后者发展提供助力。商鞅所倡行的重农抑商着眼于既定生产力状况下农业与商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其效果是双重的,在确保一定时期农业发展的同时,窒息了其他经济部门在更长历史阶段中的自发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商鞅变法堪称中国封建社会僵化的产业模式之始作俑者。
桑弘羊的财经政策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实施的。汉武帝为了维持疆域的完整和中华帝国的威势,与匈奴打了10年的仗,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也耗尽了积蓄,新辟财政来源成了当务之急。其时朝廷的对策思路主要有两条:1、加重对工商业的征税;2、实行官营工商业政策。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实行“算缗”,“缗”是一种货币单位,每千钱为一缗,“算缗”就是按缗计算的纳税办法,20钱为一算。当时规定,商人按营业额(囤积商品按商品价额),贷款者按贷款额,每2缗纳税一算;手工业者按产品销售额,每4缗纳税一算,交通运输每辆车纳税一算,商人加倍,船长5丈以上纳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没收其财产。政府鼓励民间举报,举报者可以得到没收财产的一半。在杨可的主持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大都被告发,官府查抄的“财物以亿(10万)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史记》卷三○《平准书》)。后者的措施包括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具体做法就是政府直接参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如设立盐官、铁官,统一收购和销售食盐和铁器;政府通过征税或购买某些地区的土特产,运到价高的地方出售,朝廷所需物品则到价低的地方去买;在京师和一些城市经营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即买之”(《史记》卷三○《平准书》)。上述改革有的在桑弘羊上任以前就已实行(如“算缗”),大部分则是他到任后颁行(如平准)或强化推广的(如盐铁官营和均输)。史称,桑弘羊的经济谋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民不加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卷三○《平准书》),但这笔财富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政府依靠特权直接参与市场过程得来的,从物质形态上看,官营使商业利润从民间商人手中被剥夺到官府腰包里,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掠夺性干预扰乱或扭曲了市场的正常机制(传递价格信息、调节供求关系)。一旦经济行为的主体无法通过市场使自己的投入获得与社会效益近似的收益,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就被扼杀了。
相比之下,刘晏的改革具有较多的市场色彩。也就是说,同样是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不是单纯依靠提高税收,或直接由官府参与争利,而能借助于民间经营的积极性。如在漕运方面,他的办法是由官府出钱雇工,分段运输,“不发丁男,不劳郡县”(《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这样既确保了漕粮的及时运达,又大大节省了运输费用。在盐政方面,他规定盐户生产的盐由官府收购后可以转售给商人,至于商人把盐运到何处销售,官府不加限制,只在那些商人不愿去或到不了的边远地区,才设立常平盐,“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为了及时了解和平衡全国的物价,刘晏还在各道设立巡院,用高价招募快足,沿途遍布驿站,专门递送情报,这样,“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贵贱之优。”(《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显然,刘晏的成功是由于向商人提供了获利空间,但基于财政需要的改革目标决定了市场只能是负担买单的“侍女”,而凌驾其上的那把“悬剑”倒是培育出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毒瘤——官商勾结。
王安石因着列宁的一句“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丽受到正统历史学家的肯定。不过他的新政名目虽多,推行也久,大部分还是前人改革套路的袭用(如均输法、市易法等),最重要的举措要算青苗法和免役法。前者是在青黄不接时,将各路常平、广惠仓的粮食或现钱贷给民户(如贷粮食,按时价折成现钱),预先规定归还的粮食数(按前10年中丰收时的粮价计算),实际归还时可由民户自己决定还钱或还粮。青苗钱每年贷放两次,一次在正月30日前,随夏税归还;另一次在5月30日前,随秋税归还。利率每次2分。后者又叫雇役法或募役法,就是允许过去承担各种差役的民户不再服役,但必须按户等高下交免役钱,还有过去不当差的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等,也要交钱,称为助役钱。为了防备灾荒时役钱征收不足数,平时多收二成,名曰免役宽剩钱。从实际贯彻的情况来看,青苗法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如规定2分取息,年息4分,有些地方是3分取息,年息6分,借贷中的折钱计算也是暗中剥削,因为借时粮价往往很高,而还时按丰收年景的低价,叠床架屋,甚至出现“取利约近一倍”(《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四《奏为乞将米折青苗钱状》)的现象,再加上经办官吏的营私舞弊,所以有学者指出:“青苗法并不是薄息贷款,也不是‘公家无所利其入’,而是一种封建国家经营的高利贷,从中可以获得很大的财政利益。”(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至于免役法,明摆着是扩大了征收范围,更何况多征的宽剩钱实际高达四五成。王安石曾表示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书》),但实施的新法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解民间之困流于高调,官府的钱袋倒鼓了起来,其秘密就在于国家把原来属于兼并势力或高利贷者的暴利占为已有了。
最后来看张居正的改革。为相期间,张居正在财政方面的主要作为是在万历六年至八年清丈了土地,九年在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十年奏请免除了万历七年以前的各地积欠钱粮100余万银两。免除积欠固然于民有利,清丈土地也能制约赋税转嫁,值得深究的是一条鞭法的实际后果。史家有言:“所谓‘一条鞭法’,实际是将两税以来历久增加的各项正杂税、职贡尽数合并滚入,绝不会比原有税额减少。国家不吃亏,这是一条雷打不动的基本原则。而所谓‘折色以米值为断’,各地折算时往往又高出一般市价……结果农民赋税负担较前必有增无减。”(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203~204页)不仅如此,一条鞭法不具备应有的制度效力,因为没过多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旧税杂项又恢复了,如南米、里甲、均徭等,“种种不经,难以枚举”(范濂:《云间据目抄》)。形象地说,一条鞭法只是对电脑的一次桌面整理,旧的苛捐杂税被打包了,新的又不断生出来。这样的改革不仅徒有虚名,还给后人以障眼法搜括财富新添了愚民的伎俩。
通过上述聚焦,可以发现一个不争的史实:从劳动力刚性管理到产业结构凝固化,从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到官府支配下的商人运作,从农村金融的控制到税收改制的虚置,中国古代几次大的经济改革所呈现的演进轨迹是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步步加深,正是这样的管制使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市场的交换行为和一定规模,但在本质上是一种前市场经济,或者如程念祺所说,是由“看得见的手”操纵的“财政市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盛洪写过《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题目类似谈敏所著《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一文,对先秦思想家的一些精彩论述颇感自豪,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那时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自由经济思想,如《老子》第17章中说:“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之预(誉)之;其次,畏之侮之”。孔子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西汉的司马迁把政府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问题在于,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并没有转变为实际的经济体制。论及桑弘羊的历史作为,一般的说法是他在汉武帝要“变更制度”的当儿,改革了汉初以来的财政经济政策。众所周知,汉初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经济上比较放任,让人民休养生息,因而取得了“文、景之治”。把这样的制度改掉了,国家财政虽然可以充实,社会经济的演进路径却已转向。如果将先秦时期的自由经济思想比喻为“健康基因”,那么桑弘羊的改革无疑是这种“基因”受到“扼制”的契机。这样一种路径依赖具有两个特征:其一,由于中国古代历次经济改革中政府的干预力度是累加的(如管仲的劳动力管制思想在商鞅变法中得到强化),要想维护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就意味着改革成本的递增,这在低效率的专制经济中越来越难以实现。其二,政府权力的扩大,使人们的自主经济理性得不到正常的培育。习惯于、寄希望于用行政限制、优惠扶植等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一旦成为社会的思维定式,改革的动机和结果就可能出现背离,因为这种改革的短期效益是以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既然中国古代的经济改革具有阻碍、窒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特性,我们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眼下的市场取向改革任重而道远。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盛洪论文; 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平准书论文; 桑弘羊论文; 一条鞭法论文; 西汉论文; 东汉论文; 汉书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