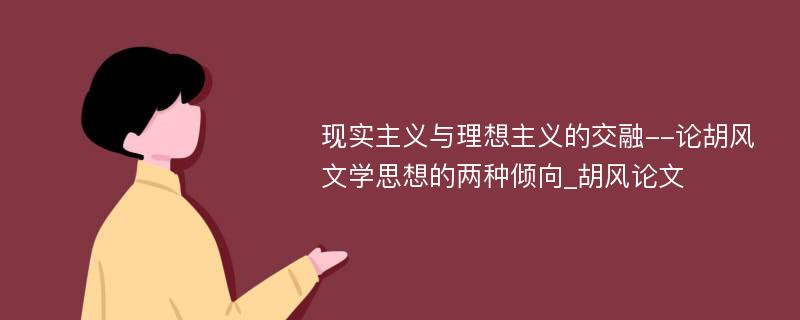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融化合——简论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两种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理想主义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倾向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1-022X(2008)02-0147-04
胡风文学理论一开始就坚持文艺的社会功用性,注重文艺的社会意义与时代内涵,反对脱离社会现实,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胡风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倾向,也体现在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上。他强调: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反映生活的。怎样说是反映生活的呢?那意思是,文艺的内容是从实际生活取来,它的内容以及表现那内容的形式都是被实际生活决定的”[1](第2卷,P293)。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社会里产生的作品,只能反映该社会生活特定的风貌、特定的色彩和特定的性格。他同时指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并不是说文艺像一面镜子,平面地没有差别地反映生活的一切细节。能够说出生活里的进步的趋势,能够说出在万花缭乱的生活里面看到或感觉到的贯穿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脉络者,才是有真实性的作品。所以,文艺并不是生活的复写,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东西须得是作家从生活里提炼出来,和作家的主观活动起了化学作用以后的结果。文艺不是生活的奴隶,不是向眼前的生活屈服,它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把生活向前推进的力量。”[1](第2卷,P318) 他由此提出:文艺作品的价值应由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的强弱来决定,这种对于文艺的理解就是现实主义(realism)。
胡风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倾向,集中体现为致力解决文艺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1930年代,胡风不满“左联”中“主观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倾向,深刻分析了两者的危害性,给予强烈批评。他指出:客观主义的症结在于对生活现象的屈服,既不能提炼生活,也不能推动生活,使读者无法从文艺作品得到力量。“有的作品较冷静地描写了一段污秽的或平庸的生活,有的作品平面地叙述了一件事故的经过……但这些不过是生活现象的留声机片,失掉了和广大的人生脉搏的关联;既没有作者的向着人生远景的情热,又不能涌出息息动人的生活的真情。”对主观主义,胡风指出:“公式主义是一种态度,一种看法,这态度或看法是从一个固定的抽象的观念引申出来的,不顾实际生活的千变万化的情形,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把这个固定的看法套将上去。”[1](第2卷,P323) 他认为标语口号作品就是主观主义鲜活的例证,这类作品失去了生活内容的真实,只演绎抽象的观念,结果把生活弄成了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既没有贯注作者的情愫,更不能产生强大的艺术力量。再比如,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争对文艺创作的需要,胡风极力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这一工作,一方面要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的热情里涌动着生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1](第2卷,P498) 建国以后,胡风忧心文艺领域“左”的倾向日益严重,写出“三十万言书”,详细论述了阻碍文艺繁荣的主要障碍,所提出的“五把刀子”理论句句切中实际、击中要害。可见,胡风不盲从权威,也不搬弄高深的理论,往往立足文学实践,结合自身创作体会,一点一滴总结经验,最终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单靠理论推导赚取噱头、哗众取宠。
在文艺批评方面,现实主义倾向也体现得非常充分。胡风曾专门指出:“文艺批评的对象是具体的作品,具体的文艺现象。”[1](第3卷,P196) 强调文艺批评的任务是“在活的过程上说明文艺世界里的已经衰老的,正要衰老的,开始成长的,含苞待放的,各种生命的性质和它们的社会基础。”[1](第3卷,P199) 因此,他要求批评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被生活经验所培养出来的敏锐的感应能力,要有坚贞的人生愿望,以及从人生愿望所产生的勇敢的突出气魄。批评家,我们所要求的批评家,得是认真的生活者,积极的战斗者。”[1](第3卷,P196) 认真的生活者,积极的战斗者,首先必须从实践的立场出发,直面文艺现实,直面文艺作品。所以,他认为批评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是公式主义;批评家不是手艺师傅,也不是作文教师,对于作品形式的表现成败的指摘,应当基于生活的实践立场,是为了作品内容的思想分析上的要求,决不能脱离作品和文学实践,进行凭空评判。
现实主义倾向在胡风涉及编辑的观点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他非常重视对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他曾在《七月》上声明决不拉成名作家的稿子。在他的激励培养下,丘东平、路翎、艾青、田间等一批文学新人迅速崛起。再比如,在如何编辑稿件等问题上,他提出“编辑者能做的只是拿住主要的方向、基本的态度,至于内容上部分的缺陷,甚至部分的错误,那是不必干涉的、作者的责任。如果一一改正了,那就成了编者个人杂志,将弄得没有生命了。事实上,有一部分稿子,编者是在付印之前清楚地知道那缺陷、那错误的,却故意地留下‘空隙’,作为批评家和读者的批判精神活动的余地。没有特别设法起批评活动,那倒是我们工作上的弱点。”[1](第5卷,P267) 在这一观点指导下,胡风所办的《七月》、《希望》采取用编辑态度和具体作品去诱发作者的方针,不仅在期刊界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稳定读者群,也逐步扩大了影响,成为国统区知名的进步文学期刊。
胡风与同时代文艺理论家不一样,他本人就是知名诗人,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在其文艺思想中,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诗人的激情,诗化的语言和诗性的思维,加之师承鲁迅,继承了“五四”人本主义传统。因此,他虽力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却能充分运用诗人特有的艺术直觉、艺术想像力,大胆探索创新,使其文艺思想充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在文艺创作问题上,胡风坚持文艺“为人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提出了理想化的目标。在他看来,文学艺术须正视现实生活,但不能局限于反映现实生活,而要追求人生,因为“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就没有存在价值”[1](第2卷,P3)。他所说的人生并非是抽象的,既包含了有关历史(社会)的内容,也包含了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矛盾中给人的灵魂打上烙印的东西。“现实主义的任务就是写出人的灵魂,通过写出人的灵魂写出那灵魂后面的历史。而集中表现一个人的灵魂的,是他的人生态度,是他的人生。”[2](P14) 胡风认为:文艺创作只有“写人生”,才能发掘、揭露出人在特定命运中的灵魂,让人感受到“病态社会”的“病态”和“不幸的人们”的“不幸”,进而加以评判和改造,否定旧的人生,促进新的人生的生长,重塑有理想并能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人,最终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斗的人生。所以,胡风把文艺反映的现实进一步拓展,上升到关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灵魂高度。与批判现实主义相比,他更追求生活的深刻与人的灵魂深刻的统一,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启蒙”姿态,但这显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不适应、不合拍,其理想色彩不言而喻。
胡风对文艺作品的标准,提出了不少切合实际、新颖独到的见解,有些也明显带有理想色彩。比如,胡风反复强调,要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实现创造主体和创造对象的“相生相克”。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上,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在诗的创造过程上,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1](第3卷,P79)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历史,深入现实的人生内容,深入人的灵魂,达到思想力与艺术力的统一。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内涵较含混,跟一般创作中作家的主观不是一回事。在他看来,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作家必须在创作中具有对人生、对历史真正的热情,具有在生活和艺术中“受难的精神”,不能仅靠某种政治认识或政治思想,但这些要求都局限在主观范围内,未能说清主观究竟怎样在同客观的结合、燃烧、相生相克中得到发扬,因此,具体创作实践中,这一标准较难操作实施,就连胡风自己创作的诗歌,也与之存在差距,更别说按此找出完美的作品了。
胡风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理想主义倾向。他明确指出:文艺批评也要追求人生,“它在文艺作品的世界和现实人生的世界中间跋涉,探寻,从实际的生活来理解具体的作品,解明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种文艺现象对于现世的人生斗争所能给予的意义。”[1](第2卷,P4) 他甚至提出: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胡风提出:文艺批评的任务,就是从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创作过程所达到的生活内容和形象的统一里面,探求他和生活的接触方法、把握生活真理的真实程度,是社会学评价与美学评价的统一。而作为批评家,必须是认真的生活者、积极的战斗者,不仅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敏锐的感应能力,还要有坚贞的人生愿望,以及从人生愿望所产生的勇敢的气魄;同时,“他的被正确的认识所武装、所培养、所完成的世界感,非得能够理解而且拥抱一代的精神生活的奔流和冲激不可。他要透过法则的世界去游历精神和世界,或者更正确地说,他要游历被法则世界所统驭的精神世界的人生的大洋,指示出这个大洋的每一个波头在法则世界里的来根去迹。”[1](第3卷,P197) 这些诗性化的要求,有些符合文艺实际,有些却与现实不适应,若完全按其所言开展批评,不仅现实条件不容许,难以拿出合格的批评文章,更难以在短期内培养出合格的批评家。
胡风的理想主义倾向,在解放后有关文艺建设的建议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尤其在《三十万言书》中,他在系统整理理论和多年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出格”的建议,有的已超出文艺的范畴。比如,撤销所谓“国家刊物”、“领导刊物”或“机关刊物”,以劳动合作单位的方式创立群众刊物、群众文艺团体,保证作家创作活动完全自由,绝对禁止匿名批评,废除强迫学习制度,废除作家等级制度,逐渐废除作家供给制和薪金制,刊物实现企业化或半企业化,作家协会的党支部和各刊物的党支部是平行的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等等[1](第6卷,P408-425)。这些建议中尽管不乏真知灼见,富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前瞻性,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但多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适应,与党的文艺政策方向不完全符合,根本无法实施,只能是一张美丽的蓝图,而随后发生的“胡风事件”又彻底撕碎了这张蓝图。
胡风文艺思想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倾向并非二元对立、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统一于现实主义理论中,并造就了其“异质”性。它们使现实主义超出方法范畴,成为坚持文艺本质的必要条件,处理作品与生活、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的思路,也成为文艺担当文化启蒙、战斗责任的理论支撑,解决文艺与政治难题的唯一途径。
现实主义倾向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外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胡风始终把视角放在文艺实践上,遵循文艺发展规律,更加注重文艺创作中的“写真实”问题。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依旧是文学同生活的关系问题;无论什么样作品,其内容应是对社会现实种种矛盾表现、根源和前途的提炼、升华。但他并不局限于生活现实,把生活现实的内容与人生的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统一于历史内容之中,强调追求历史内容的真实和深刻。他认为,作家无论面对怎样的生活,根本任务都是从中发掘真正属于历史的内容;作品无论描写怎样的生活,最主要的是它能否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从不同角度反映出现实的历史内容。因此,现实主义的任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映生活,而是透过生活现象,把人生的东西揭示出来,把生活里真正属于历史的东西揭示出来,把历史前进的潮流揭示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尽到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
理想主义倾向深化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彰显出文艺创作的个性特征和精神特质。胡风坚持文艺创作“为人生”的目标,注重发挥文艺作品的精神启蒙作用,使现实主义在“方法”、“道路”等意义基础上,增添了“态度”、“精神”等内涵。他强调:文艺作品必须写出人的灵魂,通过写出人的灵魂写出灵魂后面的历史,并由此提出“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等一系列新观点。这些观点继承了五四以来“尊个性、张精神”的个性解放传统,突出文艺创作的个性特点、作家的独立人格,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把文艺事业作为革命事业的同时,强调文艺有其特性规律,突出作家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着力探讨创作过程中主客观之间的复杂关系,坚决维护文艺创作的精神活动本质、自由精神特质。于是,胡风提倡的现实主义,不仅要描写现实生活,也要描写“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状态,活人的精神斗争”;必须以人为本,以对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感应”、“感受”、“感动”、“感激”为起点,靠用脑,靠学识、才能和技巧,更靠感情、意志、人格乃至生命,这样才能完成作家和对象活的生命运动,真正创作出“为人生”的作品。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融合,强化了现实主义的理性批判色彩,使之呈现出激进性、战斗性。基于现实主义,胡风发扬五四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专注苦难的现实生活,对封建主义保持一贯的批判与怀疑态度,致力于揭露“精神奴役创伤”,“改造国民性”,一直到解放后,仍不遗余力地批判封建主义残余,同时对创作中的主观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始终持警惕和批判态度。批判时,注重从文艺实践和作品出发,善于在对具体问题的争辩中展开观点,在论点的交锋中逐步建构理论,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鄙视用“吓人”的理论空洞说教,有时不惜四面出击、反抗权威。同时,胡风珍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情怀,使理想主义倾向融入情感性气质,成为理论的品质。正基于此,他不仅在理论上敢于超前,标新立异,从不人云亦云,在言辞上也充满了战斗的激情、辩论的睿智、突进的气势,处处体现出蔑视权威的气概、个人主义的热情和冲动,个别地方甚至表现出了固执和偏激。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相互作用,凸现了现实主义“主观体验”色彩,使之更加复杂、丰富。胡风没有完全遵从现实主义,走回批判现实主义旧路,也没有遵从理想主义,走上浪漫主义道路,而是在两者的作用下,以重作家体验为切入点,将创作主客观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把“思想启蒙”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实现了由文学—生活向作家—生活视角的转变,既囊括了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新因素,又凸现了创作主体地位,使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复杂。比如,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风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也不提倡自由主义、唯艺术论,他将此问题纳入现实主义中,强调只有现实主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的角度,是比政治的角度更高的角度。文艺要适应政治的直接要求,不能简单将文艺政治化,关键在于遵循现实主义的法则,追求历史内容的深广,即通过热烈、饱满、主动的主观精神,透过政治去把握深广的历史内容,进一步深入历史前进的潮流。这样,胡风把人们经常从政治角度认识的问题,硬转到文艺领域,拉回创作主观的范围,使现实主义的概念更为模糊。再比如,胡风根据多年的创作经验,从形式与内容辩证关系出发,强调民族形式属于现实主义问题。他认为:发展民族形式,就是发展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即“首先是对新的生活的历史内容的把握,然后是相应的新的形式的创造”,根本上就是发展现实主义;因此,“民族形式”的创造取决于“时代的内容”,必须在世界文学经验与民族文学经验的结合中产生,将文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统一起来。这既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相差甚远,也使得现实主义更为复杂,并造成了轻视民族传统形式的“瑕疵”。
总之,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倾向一直贯穿胡风文艺思想之中,伴随其发展、完善。这两者的交融化合,造就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异质性”、独特性,使之在现代文论史上自成一家。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两者,胡风文艺思想与政治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错位、龃龉,为后来的“胡风事件”埋下了“祸根”。不管怎样,这两种倾向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认真研究,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胡风文艺思想,全面总结经验得失。这将有利于我们将胡风文艺思想借鉴、运用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2007-09-24
标签:胡风论文; 文艺论文; 理想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