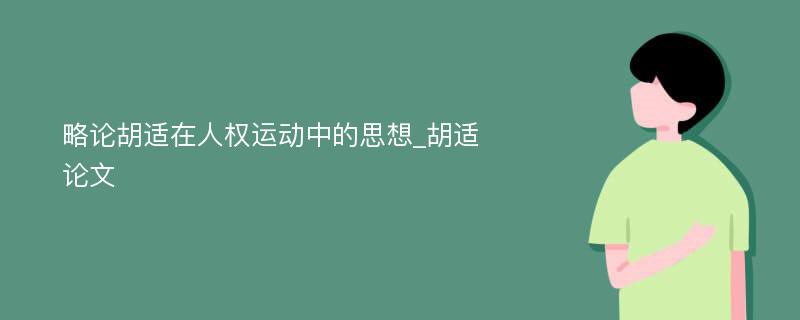
简述人权运动时期的胡适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人权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政治家。他在以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驰骋于20世纪中国文坛的同时,也在政治领域中留下了复杂多变的人生轨迹。具体分析胡适的政治活动,探讨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有助于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把握。
一
人权运动是兴起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崇尚思想自由、向往人权和宪政为基调,参加者大都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在1929年至1931年人权运动期间,胡适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表明了自己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政治态度,其思想主张包括:
在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基础上,呼吁切实保障人权,实行民主政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在“训政”的名义下确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是少数人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人权、民主、自由仍然没有丝毫保障,正如人们所抱怨的,“非国民党的人民,一有组织,即为反动,一有团结,即为叛逆”,[①]一幅万马齐喑的悲凉景象。胡适在人权运动期间的政治言论,是针对国民党的统治状况有感而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感到“时局是真沉闷”,终于“忍无可忍,便出来说话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②]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也就成为胡适话题中首当其冲的内容。
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布了一个《保障人权命令》,标榜说:“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和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③]在完善了一党专制体制,对人民的权利、自由进行了种种剥夺和限制之后唱此高调,完全是一种贼喊捉贼的欺骗伎俩,对此,胡适的揭露一针见血。他在1929年4月出版的《新月》杂志第2卷2期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可见,“命令”对人权的保障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④]除反击《保障人权命令》的虚伪,胡适还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黑暗,对“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⑤]的社会现状表示了极大愤慨。
鉴于专制独裁体制对民主的践踏和人权的剥夺,胡适大声疾呼保障人权,要使国民的身体、自由、财产都得到切切实实的保障。为达到上述目的,胡适还提出了保障人权须从制定宪法入手的思路,认为“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⑥]在宪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一个真正民主、民治的政府,从而使平民政治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
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人治”,提倡“法治”和“专家政治”。
依法行政,是欧美式政治制度的重要特色,也是人权运动时期胡适政治民主化的基本构想。心怀理想,眼望现实,胡适对国民党在“训政”名义下实行的“一党专制”政策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种愚弄老百姓的“训政”于国家、于人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实际上,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在对国民党的“党治”和“人治”深表遗憾的同时,胡适对资产阶级“法治”表现出热切的向往,并将法治视为争取人权的先决条件和杜绝一切“人治”不良现象的重要保证。他说:“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主席……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⑦]
胡适对蒋介石、汪精卫等新军阀政客嗤之以鼻,认为我们国家“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军人领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了”,大呼“全国无领袖”。[⑧]他把政治人才的缺乏视为中国政治紊乱的原因之一,提出要改革政治、改革行政,必须建立专家政治,指出:“民生国计是最复杂的问题,利弊不是一人一时看得出的,故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⑨]中国政治才有出路,表达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欲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
谴责国民党在思想上的专制政策,主张思想言论的绝对自由。
思想开放,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权运动期间,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与国民党当局分歧明显,矛盾尖锐。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公开指出,由于国民党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所以“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斥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同时,他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五条最低限度的改革要求,其中包括“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⑩]
批评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奉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
胡适否认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导致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认为中国落后的“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胡适所认为的中国革命的真正对象。而要打倒这五大仇敌,只须“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以此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二
应该承认,曾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胡适,其政治主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同反动统治阶级相对立的,最起码是不一致的。人权运动时期,胡适立足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既不满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抨击。但是在对国共双方的左右开弓中,胡适的力量并非平均使用,而是有其侧重点的。他的侧重点不在反共、反人民、反对马克思主义方面,而是指向国民党方面。他的人权、法治、思想自由、专家政治等主张,绝大部分是与揭露和批评国民党独裁统治紧密相联的,是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作为对立物而提出的。也正因为如此,胡适的言行惹起了黑暗势力的恼怒。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五六个省党部呈请反动政府,要端掉他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明令对其通缉严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发布命令,称“查胡适近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足以警告处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在1930年底密令将刊载胡适等人文章的几期《新月》杂志强行没收焚毁。
但是在革命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胡适的言行和胆识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他的《人权与约法》在《新月》杂志刊出之后,立刻有读者致书于胡适,说:“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而敢言。前日看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辞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①①]还有的读者赞扬他,“许多和你在那个时代共同呐喊的人,现在都颓唐了,腐化了,鼓吹白话文的,自己也用起文言文来了,骂军阀政客的,现在倒捧起军阀来了。惟你还站在那里呐喊,我觉得这是可贵的态度”。[①②]蔡元培读过胡适的这些文章后也称赞说:“振聩发聋,不胜佩服”。[①③]的确,在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决不使一人漏网”的白色恐怖下,并不是人人都有胡适那样的识见和胆量的。
当然,由于长年留学国外,囿于书斋,缺乏对中国社会真实、深刻的了解,加以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在论及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时,胡适的主张与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也是不一致的,此期间也确有一些反共言论,但从总体来看,不占主导地位,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言论相比,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人权运动期间胡适把主要锋芒指向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还应该看到,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既不表明胡适同国民党有什么特殊怨恨,更不意味着其与共产党有什么好感和同情,它是由国共两党当时所处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
三
人权运动开展的1929年至1931年间,正是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并逐步统一全国的时期。由于蒋介石实行“清党”,共产党的力量受到极大摧残。其所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虽然点燃了工农革命的星星之火,到1930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许多块农村根据地仍是地方性的红色政权,革命力量尚不足以控制全国政权。而此时的国民党却是掌握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的执政党,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政风和民气。胡适参加人权运动是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有感而发的。国共双方在当时所处的这种不同历史地位,使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共产党领导的局部的工农民主专政在他的视野里不占主要地位。其理想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与当政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诸多方面,归纳起来基本有三: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追求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政治的矛盾冲突。胡适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十分仰慕美国的民主政治,把其视为最理想的政治追求。然而回国后他所面对的中国现实却与自己的理想相去太远。北洋军阀政权搞得中国满目疮痍,国民党的专制体制也没有丝毫民主的味道,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胡适感到深深失望。随着失望而来的,则是不满与愤慨,为实现自己所向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本能地向专制政治发起攻击,而这一制度的代表者国民党,便成为他攻击的实际目标。
第二、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与一党专政的不可调和。胡适是一位旧学功底和西学修养皆备的学者,他身上既遗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吾侪不出,予苍生何”的基因,也深受西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决断天下的社会参与意识的影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要求。然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却把一切非国民党人士排斥于政权之外。这样,胡适及其人权派的满腹经纶无处施展,便对现政权产生了由衷的不满。抨击执政者的不学无术,视自己为专家,鼓吹专家政治,就是这种情绪的渲泄。
第三、两种文化观的差异。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尤其大肆尊孔复古,鼓吹恢复儒家“道统”,奉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而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不仅以砸碎孔家店为己任,而且滋生了全盘西化的倾向。资产阶级新文化与腐朽的封建旧文化的差异,使胡适在是非标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同国民党政权格格不入。对于国民党的文化复古政策,胡适大不以为然,不仅觉得没有必要,而且认为中国“处处都保持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①④]文化观的不同,成为导致胡适与国民党冲突的原因之一。
胡适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其终极目的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人权运动时期胡适思想的核心所在。应该承认,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中已失去了它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体趋向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在同步发展。当西方某些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时候,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里挣扎。在当时,用民族民主革命的方法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在中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胡适试图以改良主义途径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在消除中国革命的障碍方面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胡适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还应该看到,当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时候,胡适大声疾呼“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等口号,在政治上揭露并孤立了国民党,客观上对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多少也起了一些有益的作用。
注释:
①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见《新月》第3卷,第10期。
② 《新月月刊敬告读者》,见《新月》第2卷,第6、7期合订本。
③ 《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4月23日。
④ ⑤⑥⑦ 胡适《人权与约法》,见《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1月初版。
⑧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见《独立评论》18号。
⑨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见《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1月初版。
⑩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1月版。
①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上)。
①② ①③ 龙冠海《致胡适》,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
①④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3,第486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标签:胡适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新月论文; 国民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