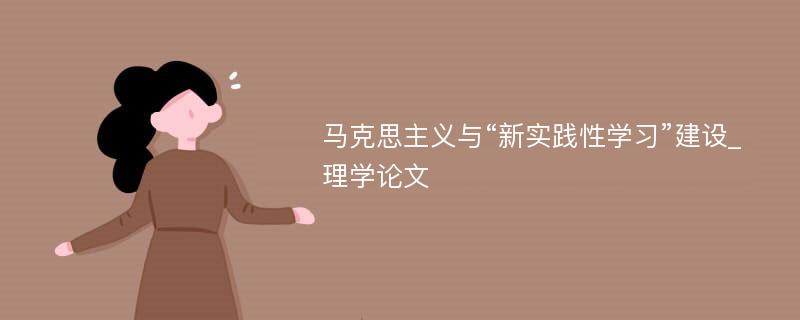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与构建“新实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1-0028-07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实学的对接点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哲学家多把“新宋学”作为构建现代中国哲学的起点。
冯友兰借助柏拉图的“共相”与“殊相”理论以及美国新实在论思想,按照程、朱的“理一分殊”哲学架构,创立了“新理学”体系;贺麟以西方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读陆、王心学,提出了“新心学”;唐君毅综合“中西古今”之学,以“道德自我”为基石,按照“依本成末”的理论架构,提出了“九境哲学”;牟宗三则通过消融康德哲学与改造陆、王心学,创立了庞大的“新心学”思想体系。这些哲学大师虽然在哲学创新上有重要贡献,令世人敬仰,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实际,构建出的新哲学往往远离社会需求,而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热衷于中国哲学中的“理学”和“心学”,並将它们视为中国哲学的精华,而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实学传统却不感兴趣。
实际上,在宋明儒学中,除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外,还客观地存在着一个以张载、王廷相和王夫之为代表的实学流派。所谓实学,主要是指北宋以降的“实体达用之学”,实学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科技实学”、“考据实学”、“史学经世”、“明经致用”和“启蒙实学”等。从本质上,它是一种“崇实黜虚”的学术思潮,既不同于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也不同于宋明理学家的“理本论”和“心本论”。宋明儒学不是“理学”与“心学”的“两足並行”,而是“理学”、“心学”和“实学”的“三足鼎立”。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宋明理学居于主流地位和“理学研究范式”的深远影响,多把实学淹没在“理学”或“心学”体系之中,鲜为人知。明清之际,“实学”在同“理学”、“心学”特别是理学末流的辩论中,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思潮。
中国古代实学如何才能由“旧实学”转化为现代的“新实学”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并作出了榜样。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P534)这就是说,在哲学创新上,要使中国古代实学由“旧实学”转化为“新实学”,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外,还必须与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相结合,也就是如何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实学相结合的对接点和生长点。
应当指出,20世纪在中西文化结合的社会思潮中,中国古代实学从不同层面对毛泽东产生过或隐或显的影响。“实事求是”、“实践论”、“明经致用”和“史学经世”是中国古代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实学传统最为密切的四个对接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古代实学走向现代化的四个重要生长点。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注重借鉴和吸收实学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充实自己的思想,并用以服务于他对现实社会的改造。毛泽东既不同于书斋学者的治学方法,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的学风。他立足于现实中国,面向风云变幻的世界,融合中西文化,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实学文化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实学的优秀传统,创造出了当代中国的“新实学”,从而为中国革命和现代中国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二、“实事求是”论与中国实学的“实事求是之学”
“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这一思想路线和优良学风的形成,除了他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外,也是与他吸取中国实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之学”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古代实学中,“实事求是之学”只是一种注重事实、讲求实用、不说空话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实事求是”一语是在汉代正式提出的,至北宋实学思潮形成后,“实事求是”才成为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中叶以后特别是乾嘉学派提倡的“实事求是之学”,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乃是注重实证、反对空谈性命的考据之学。如果说清代惠栋、戴震以及王鸣盛、钱大昕、阮元、阎若璩等人主要以自己的考据之学彰显了“实事求是之学”的话,那么实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则在哲学思想和“经世致用”上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更深广的社会意义。黄宗羲针对空谈义理的理学末流,指出:“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道,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生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建功立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2](P220)王夫之“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之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章沿革,皆极意研究。”[3](P73)他批评理学末流者成天“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辩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若此者,“于身心何益哉!于伦物何舆邪!于政教何舆也!……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势而误人之国家。”[4](P1348)顾炎武十分痛恨那些“游谈无根,置四海之困穷于不顾,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腐儒,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完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5](P310)他十分注重“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之学”,先后研究过吏治、财赋、典章制度;他治学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为写作《天下郡国病利书》,不但遍读史书,而且遍访各地,历时24年。颜元对理学末流的空谈之风批判说:程朱理学“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功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王阳明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物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可谓迷魂之第一洪涛水母矣!”[6](P257)为此,他和李塨、王源等人在清初学术界公开标帜“实学”,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的宋明理学末流相对立。黄、王、顾、颜等人提倡的“实事求是之学”,在明清之际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和经世理念,在中国社会政治和学术领域中,曾发挥过持久的重要的历史影响。
毛泽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时,就在塾师指导下阅读过顾炎武的《日知录》,他曾以顾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与同学互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他进一步接触到清初几位实学大师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内心共鸣。在他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公开标举清初实学家顾炎武“喜乘马”,颜习斋“学击剑之术”,李塨“文而兼武”,肯定三人是“三育(德、智、体)并重”的师表,认为三人“皆可师者也”。在《讲堂录》中,他还表彰了顾氏“留心当世之故”、“经世要务,一一讲究”,“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的实学精神。曾国藩的“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一段日记,也被毛泽东抄录于《讲堂录》中。岳麓书院大庭门梁上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和曾国藩的“实事求是”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他自觉地将顾炎武的“修己治人之实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
由于受到中国实学传统中“实事求是之学”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十分注重实际,大力倡导求实学风。他曾针对当时一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空虚”风气,主张“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7](P363)他认为开展实地调查是接近实际的一个好办法,主张“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7](P401)他还多次与蔡和森等人以“游学”方式,深入湖南各地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向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求学问道。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8](P63)五四运动后当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实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之学”不只是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而被加以强调,而是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批判地继承了这一实学传统,并从世界观高度对它作出了重新解释和创造性转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毛泽东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以便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不仅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为制定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从世界观的高度阐明了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9](P21)“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0](P115)他认为,是否开展调查研究,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般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路线”问题,而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对革命工作的指导。因此,共产党人一定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反对党内一些人以“本本主义”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0](P111-112)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哲学上对教条主义和孔孟之道又作了一次系统清算。他说:“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11](P145)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反复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又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传统实学中的“实事求是之学”作了重新诠释和现代转换。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2](P801)毛泽东不但吸取了“实事求是之学”这一实学命题的合理成分,同时还赋予它以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哲学意义,使其获得了现代性的转换。“实事求是”不仅代表着一种崇尚事实、反对空谈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更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通过中国古代实学这一优秀民族形式,对“实事求是之学”经过创造性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创造了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及现在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求真务实”之学,都是立足于辩证唯物论世界观,从实际出发,强调一个“实”字,批判一个“虚”字,把中国“旧实学”变成了“新实学”,从而完成了中国“旧实学”在世界观上的现代转换。
三、《实践论》与中国实学的知行观
毛泽东于1937年7月撰写的《实践论》,固然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概括,同时它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实学中的知行学说的一次科学总结。他不但善于使用中国人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如以中国人的“知和行的关系”表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等)和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如“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知识里手”等),形象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且更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学说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为了论证“知”源于“行”的道理,他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13](P42)以及王廷相的“行得一事即知一事”[14](P478)的思想,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思想联系。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中国人的老话,至少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二中,朱熹就讲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从上述两个例子,透露出《实践论》同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实学之间的某些思想渊源的文化信息。
毛泽东的《实践论》虽然吸取了中国古代实学知行观中的某些合理思想,但他是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批判中国哲学中的各种知行学说,第一次对人类认识总规律作出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毛泽东认为,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即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0](P296-297)把这种“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中国古代实学的各种知行学说相比较,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古代实学知行学说的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从具有片面的道德修养型的知行概念向完全的科学认识论型的知行概念的飞跃;二是从片面真理的知行关系论向具有完全科学真理的知行关系论的飞跃;三是从非科学的多元真理标准论向科学的一元真理标准论的飞跃。正是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指导下而完成的这一巨大的理论飞跃,才使中国古代实学的知行观转向现代“新实学”的知行观,完成了“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与革命”,具有划时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5](P190)
四、“有的放矢”论与中国实学的“明经致用”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他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领袖人物。他的“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取向,同他继承与弘扬中国古代实学传统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明经致用”是中国实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中国实学思潮的兴起,宋代湖湘学派最重“明经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胡安国将《春秋》一书视为“经世大典”,试图通过以义理解读《春秋》,达到“康济时艰”的目的。胡宏鄙薄功名利禄,一生以立身行道为志,要求“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16](P131)张栻也发扬“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十分注重治学与致用的统一,颇“留心经济之学。”晚清曾国藩追慕王船山、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认真研读过顾炎武和魏源的著作,留心于当世之务,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17](P12),被人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清朝的“中兴名臣”。
中国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明经致用”传统,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毛泽东,通过老师杨昌济从清代实学家那里获得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由此他对那些有志于以学问贡献社会的实学大家产生了崇敬之情。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抄录了王船山、顾炎武、魏源、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的不少名言警句,有些地方他还作出了肯定性评论。如他抄录了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的语录,把“圣贤”释为既有高尚“品德”又能成就“大功大名”的“德业俱全者”。[7](P589)他还明确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将“德业俱全”的“圣贤”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人格。[7](P589)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自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做一名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发扬光大“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特别是“明经致用”思想,要求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加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力求做到“精通”,而“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2](P815)即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将其作为招牌到处炫耀。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P534)以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同时,他对于那些“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提出了批评,指出:我们“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12](P797)毛泽东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实际的革命运动的科学态度,形象地称之为“有的放矢”。他说:“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这是“无的放矢”,[12](P799)是毛泽东所反对的。毛泽东所提倡的“有的放矢”,“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进一步解释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12](P801)他反复向全党阐述“有的放矢”的道理,指出:“‘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12](P819)“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12](P820)毛泽东的“有的放矢”论,既是对中国实学中的“明经致用”优良传统的传承,也是对中国“经世致用”实学的一种理论超越。
五、“古为今用”论与中国实学的“史学经世”
“史学经世”论是中国古代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明清之际,倡“史学经世”论已成为经世实学思潮中的一股劲流。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龚自珍、魏源是这一时期“史学经世”论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将治史与经世联系在一起,指出:“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18](P93)黄宗羲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2](P316)王船山对“史学经世”释曰:“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4](P135)龚自珍、魏源等人,在晚清新的政治形势下更加强调“史学经世”论,大力提倡“尊史”之说。魏源出于经世救国需要,突破“重古略今”的治史模式,尤重“现代史”著述(如魏源编纂的《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夏燮的《中西纪事》等),是道、咸年间“史学经世”论的一个新特点。
毛泽东从青少年开始,读史兴趣长久不衰,“史学经世”论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对历史就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得益于六年私塾期间所读史书如《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纲鉴易知录》等,而且也得益于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期间“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毛泽东酷爱史书,从未停留在对历史知识的单纯了解上,而是注重对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早在1915年9月,他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7](P22)“观往迹”是为了“制今宜者”。所以,读史不能只关注一般的历史过程,而应将其重点放在探寻“公理公例”即探寻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大趋势或客观规律上。在近现代,能够自觉地继承这一“史学经世”传统,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以为现实服务者,毛泽东可谓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毛泽东注重“观往迹制今宜”、注重探求“公理公例”的“史学经世”论,虽然受到中国实学传统的影响,但是他在继承“史学经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和发展了这一历史传统。毛泽东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对历史古籍的学习、钻研,不同于书斋中历史学者,总是赋予史书以政治生命力,使其为革命斗争服务。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P533)将掌握历史知识、掌握革命理论以及对实际运动的了解,皆视为革命政党指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第一人。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和强调历史知识对于指导现实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一是通过学习历史可以“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P633)他认为没有对历史的了解,对国情的了解是不完整的,也是不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的。他尖锐地批评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起,忘记了。”[12](P797)这是一种“割断历史”的严重错误,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P534)他号召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以为“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提供“帮助”。二是发扬中国实学家“鉴往所以训今”的思想,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指导当前革命运动提供历史借鉴。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既要注重古代,也要注重现代,而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刚刚过去的历史进行总结,尤为重要。通过从学习和研究党史开始的延安整风,进一步清算了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以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一次成功典范。三是毛泽东对历史功能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为指导当前实际运动提供某些历史借鉴的层面。他认为正确地看待和总结历史,特别是批判地继承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为新社会的文化建设,为提高全体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为推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939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我们应该“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1](P533-P534)四是在研究方法论上,毛泽东提出了对于历史遗产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要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历史文化遗产区分为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并将批判性地继承历史遗产与新的文化建设和人民民族自信心的提高联系起来,从而把对历史作用及其价值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更为浓厚。他在继续坚持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的同时,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充实和发展。1956年8月,他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发表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指出:“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我们不能“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19](P747)但是我们重视历史,目的是为了今天,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毛泽东的“古为今用”这一表述,是毛泽东有关历史应为现实服务思想的最高概括。同时,毛泽东在何为糟粕、何为精华以及如何对待糟粕与精华的问题上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60年,他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20](P189-190)这段话中,毛泽东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封建时代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了封建的和反封建的区分,指出封建主义的东西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带有统治阶级的影响,对它们都要做进一步具体分析,都要批判地加以利用;同时,他还提出对遗产要“充分地利用”。这些观点的提出,为“古为今用”添加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总之,毛泽东的历史价值观,既是对于中国古代实学家提倡的“史学经世”的实学文化的继承,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古代“史学经世”思想的一种现代性的诠释。
六、结论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实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吸纳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切合理成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接点,主要的应是中国古代实学特别是明清实学,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中国古代实学的现代化,即由“旧实学”转变为“新实学”,虽然应容纳古今中外哲学的一切积极思维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是最为重要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实学基本上同属于“外王之学”,在唯实性和实践性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从20世纪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实学相结合,创建新实学思想体系,一直是现代中国哲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时代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构建现代“新实学”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古代实学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和弘扬者。
[收稿日期]2009-9-10
标签:理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实践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知行论文; 顾炎武论文; 心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