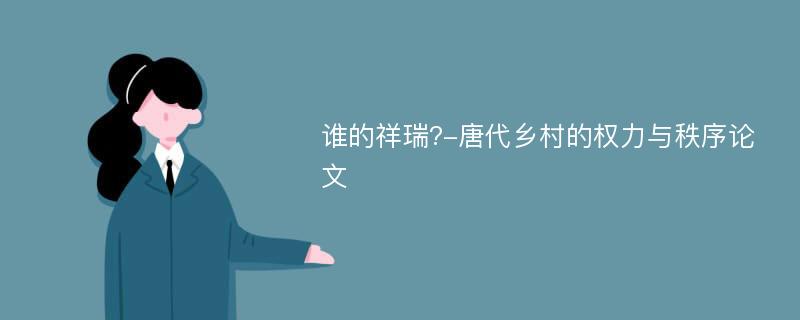
谁的祥瑞?
——唐代乡村的权力与秩序
孙英刚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7)
摘 要: 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氛围里,祥瑞是唐代政治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衡量和验证皇权统治正当性的重要指标。但是祥瑞并非是浮在上层的装饰品,它通过乡闾百姓、地方官员上报中央,再由中央对地方官民进行肯定和旌表。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互动,为中央权威深入基层,引导舆论、干预地方风俗与秩序,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机制。反过来,乡闾百姓和地方宗族通过(主动的)参与“制造”祥瑞,获得自身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甚至进入国家和地方权力体系,也深刻影响了地方的权力与秩序。在特定情况下,唐代一直存在着谁之祥瑞的讨论:是国家祥瑞、地方长官德政的感应,还是百姓孝感?这种讨论反映了中央、地方、百姓之间复杂的权力与秩序结构。
关键词: 祥瑞;隋唐;乡村;风俗
拟判是唐代一种常见的司法文书文体,科举考试通过者在吏部铨选时,被要求根据特定案例(判目)发表判决意见(判词),拟判的水平将决定候选人是否获得正式任官的资格。作为律令制社会的一种官文书文体,拟判反映了当时唐代官方的政治、司法理念和思想。如《全唐文》中收入刘宪(655-711)和李希言两人关于同一判目所做的判词,这一判目是:“楚州申殷贤丧亲,负土成坟。甘露降树,芝草生庐,青鸾镇集,白鹤翱翔。县令张德以为孝感,刺史欲飒庙。乡人梁静告:国家祥瑞。”[1]2364刘宪是武则天到中宗、睿宗时期的大臣,李希言生活时代与刘宪相同,开元中任太子詹事。基本可以推断,这道拟判是某一年吏部铨选的考题。《全唐文》中还收录了两道《对坟树有甘露判》,应该都是当时参加铨选的进士留下的答卷。刘宪年十五举进士,这道铨选拟判的出题时间大约在670年之后,代表的是唐代前期的情形。祥瑞事务成为吏部铨选考题,也说明这一问题在当时的政治运作中非常重要,事关地方风俗与国家权力等各个层面。
安仁古镇建设紧凑却不失条理,整洁中蕴含着气节。整个小镇坐落于大邑县,周边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安人古镇的建筑以青砖黛瓦为主,以沉稳的朱红色点缀,院内种植寓意吉祥的柚子树,点缀石桌石凳,布局简单大方,足显“安”“仁”之意(见图2)。
吏部铨选题目基本意思是:楚州一个孝子申殷贤,负土成坟,甘露、芝草、青鸾、白鹤等祥瑞出现。县令张德认为这是申殷贤孝顺所感应,楚州刺史计划为此立庙,但是孝子的一个叫梁静的乡人上告,说这些是“国家祥瑞”——不是申殷贤“孝感”所致,本文稍后还会谈到地方家庭和宗族因为祥瑞在地方权力结构中获得优势地位。大概梁静的上告,也是唐代经常出现的情况——乡里之间不同家庭和家族的竞争和嫉妒,让同乡之人难以接受对方因祥瑞而获得官方旌表,所以这一拟判为我们展开讨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一 国家祥瑞还是匹夫之感:中央权力与乡里社会秩序
刘宪和李希言在各自判词中,言论出奇地一致。刘宪认为,“率土莫非王臣,含灵皆用天道;通论则归于有国,析理则存乎其人;以匹夫之感,皆为王者之瑞”,而且认为“虽祯祥骤委,谅神理无欺;而谤议是兴,为乡人所恶”。最后判定,“梁静须正刑书,刺史不烦疑惑”。刘宪认为(1) 有关这一拟判的讨论,参看田野《从孝亲相关拟判看唐代司法过程中的观念冲突》,《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田野认为,在有关祥瑞的案件判决中,往往不利于原告,可见在政治和司法上,唐朝基本不支持对祥瑞事务提出异议。 ,率土莫非王臣,“匹夫之感”,也就皆为“王者之瑞”[1]2364。李希言认为,“瑞允彰于周德,孝因感于殷贤”[1]3679,观点与刘宪类似,只是不如刘宪判词果决。另两道阙名判词态度也是完全一致,一道云:“所感虽因孝致,论孝亦感皇风;旌以门闾,实将无愧;告以祥瑞,良亦有疑。”另一道认为:“翼县检巡非谬,州端勘亦不虚”,“眷彼门闾,固须旌表”。[1]10116
对两组临床相关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愈合时间、髋关节功能Harris评分、住院时间)、骨折复位丢失率、并发症发生率实行观察和记录。
在是“国家祥瑞”还是“匹夫之感”争论中,反映的是祥瑞上报在唐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皇权、地方官员、百姓之间,通过祥瑞呈报、勘验、旌表连在一起,从而使皇权下达县乡,直达百姓中间,宣扬道德理念,干预乡村秩序。从这个角度讲,祥瑞思想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不仅仅在于给皇权提供合法性论述的理论,而且是它深入到社会基层,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制度、社会舆论上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秩序,甚至成为政治传统的一部分。
祥瑞不仅仅是申明君主天命的政治武器,而且也常常作为地方官员治理有方、乡里百姓德行优异的证明。对应在唐朝的行政运作中,存在着三个层次。《新唐书》记:“凡景云、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苍乌、朱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2]1194具体名物见《唐六典》所载开元《礼部式》。[3]114关于祥瑞的上报,唐朝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唐会要》卷28《祥瑞上》引《仪制令》云:
再以2017年江苏高考作文题为例,材料共三句话,最后一句其实提供了四种立意方向:“车来车往,见证着时代的发展。”、“车来车往,承载了世间的真情。”、“车来车往,折射出观念的变迁。”、“车来车往,蕴含着人生的哲理。”这四句话基本涵盖了有关“车”的各种立意,考生很难逃脱也无须逃脱这四种立意。于是,有老师批评江苏高考作文题几乎没有给考生留下立意空间。其实不然,这四句话只是提示了立意方向和思考角度,并不等于立意本身。换言之,它提示考生可以从“时代”、“情感”、“观念”、“哲理”等角度中具体选择一个,进行具有个人特色的详细阐释,而至于选择哪一个角度或确定什么立意,考生仍有很大的自主权。
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其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史官不实对者,黜官三等。[4]618
我们通过例子具体看看唐代处理祥瑞的行政程序。载初元年(690),西京万年县出现了山涌。武则天在这年称帝。西京留守武攸望上表汇报这次山涌——将其描述为大瑞之一的庆山:
臣于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万年县令郑国忠状,称去六月十四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臣谨差户曹参军孙履直对山中百姓检问得状……伏请宣付史馆,颁示朝廷。无任凫藻之至,谨遣某官绘图奉进。[1]2241
东方宇轩接着讲:“我又与几位师父商议,觉得白天的六试,游于艺,轻于武,特别是,未能考较出你们对阵法的修习。我们总归是饭后无事,趁着这月明星稀,摆一个七绝逍遥阵,来对一对你们的天地人三才阵如何?无论你们能不能冲出七绝阵,都没有关系,就当替我们这些老家伙松一松筋骨如何?”他话音一落,其他九人跟着纷纷点头,那架势,就是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劳作一天的大人,要孩子来敲背的敲背,按腿的按腿……
地方精英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研究关注的话题。在唐代,地方宗族势力往上连接政府,其成员进入政府担任官员,往下则作为乡里事务的主导者,是乡村秩序重要的一环。有的家族通过上报祥瑞,获得优势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道德楷模,甚至在宗教信仰上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唐代乡村权力结构的重要层面。
以上是大瑞情况,更多地跟中央政治有关。但是唐代还存在着大量中瑞、下瑞,乃至部分上瑞,更多是跟地方和乡里百姓有关。唐代社会基本秩序,基本仍不脱君臣、父子理念。往上就是君臣,往下就是父子。于公是君臣,于私是父子。取忠臣于孝子之门的理念,也是基于忠孝相通。君臣父子,是最根本秩序。既是乡村秩序的核心内容,也是统治秩序的核心内容。皇帝同时也是臣民的君父。将皇权渗透进乡村百姓中间,除了税赋徭役之外,风俗教化也是重要一环。唐代大量祥瑞事件,也能看到皇权深入乡村的情形。
何大爷像往常一样把大半个炕让了出来,可我们谁也没动,既不上炕,也不走,仿佛不知道这姑娘的底细不甘心似的。何大爷似乎看出来了,嘿嘿一笑:“这丫头是从县里来看我的。”
唐朝对祥瑞管理是制度性的,上报祥瑞是地方官员职责。比如《旧唐书·职官三》记载地方留守、都督、刺史的职责,其中就有:“符瑞尤异,亦以上闻。……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精诚感通,志行闻于乡者,亦具以申奏,表其门闾。”[5]1919符瑞和百姓德行优异是连在一起,“精诚感通”大多数情况就是祥瑞——因为百姓德感所致。《唐六典》讲得更加清楚:
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间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有精诚致应者,则加优赏焉。[3]77
因为按照唐礼部式规定,白兔是中瑞。地方官员有上报的责任。王弘义向瓜园主人求瓜不成,就说瓜园中有祥瑞白兔,于是县官派人捕捉,把瓜园破坏殆尽。
在文献中可发现大量唐朝中央政府对孝子旌表门闾、墓闾的记载。“门”指家门,“闾”是指里巷大门。旌表门闾,一般的是指在家门和(或)里巷大门前树立双阙。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孝”判断标准,确实符合上述官方规定三个标准,尤其是常有祥瑞的出现。比如沧州清池的许法慎,孝顺母亲,母亲去世后坟茔“有甘露、嘉禾、灵芝、木连理、白兔之祥”,“天宝中,表异其闾”[2]5590。开元二十五年(737),尉氏县人杨思贞“庐于墓三十八载,有芝草、白兔、甘露等瑞”,于是朝廷“赐粟帛,旌表门闾”[7]181。先天二年(713),东陵人唐君祐母侧“有芝草三茎生焉”,“敕旌表门闾”[7]180。开元十四年宋州单父人刘九江,三代同居,“有慈乌巢于庭户”,乡里荣之,名其乡曰“邕睦乡”、里曰“同居里”,获得朝廷旌表其门的嘉奖;同一年,定州鼓城人彭思义“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有嘉禾生及白兔驯扰”,也“旌表其门”[7]181。大历四年(769),“睦州司士参军许利川居母丧,以孝闻,有芝草八茎及连理树一株产于墓庐,诏旌表其门”;大历六年,“邛州依政县百姓樊漪居父母丧,负土成坟,庐于墓侧。有兔鸽驯扰、木连理、慈竹,旌表门闾”[7]183。
从模拟结果来看,ARIMA(3,1,6)模型和 ARIMA(3,2,6)模型的拟合效果差距不大,但是 ARIMA(3,2,6)模型的模拟效果更好。
林攒,泉州莆田人。贞元初,仕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攒闻,弃官还。及母亡,水浆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冢,庐其右,有白乌来,甘露降。观察使李若初遣官属验实,会露晞,里人失色,攒哭曰:“天所降露,祸我邪?”俄而露复集,乌亦回翔。诏作二阙于母墓前,又表其闾,蠲傜役,时号“阙下林家”。[2]5590
嘉禾为瑞,闻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兹祥。放勋获之于前,叔虞得之于后。孤今纠合,复逢灵贶。出自兴平,来因善乐。休徵伟兆,何其美欤!顾循虚薄,未堪当此。呈形之处,须表天休。送嘉禾人兴平孔善乐,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应。[1]17
在这些纷繁记载中,我们看到,大量祥瑞都是嘉禾、芝草、木连理、白兔这样的下瑞或中瑞,极少数是甘露这样上瑞。与国家大事、君主天命直接相关的大瑞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也反映了这些祥瑞的乡村和地方属性。尤其像嘉禾这样的祥瑞,直接跟农业生产有关。治国务本,不违农时,就有嘉禾而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模式转换与发展方向——以上海市黄浦区“海燕博客”为例 ……………………………………… 肖存良(4·68)
在唐代,上报祥瑞是百姓责任,隐匿不报甚至是违法行为。关于隐瑞,阙名《对赤乌巢门判》云:“乙丧亲之后,家有赤乌巢门,白兔游墓,人告不报官司。”[1]10115李龟年《对同衅不缌义居芝草判》云:“又虞乙家五从义居,园中禾生两穗,庭中产芝草,盖形紫色,邻人告隐瑞,州不断罪,亦不上闻。”[1]3335当然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员并不会责罚隐瑞不报的人,利用隐瑞控告乡里邻居的,反而会受到谴责。但这些情况存在,说明上报祥瑞,在唐代基层社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操作。不论是乡闾百姓,还是地方官员,都有强烈动机,加入到上报祥瑞的队伍中去。获得旌表的人家,除了得到官方认可荣誉之外,还获得了经济上的好处,获得粟帛直接赏赐,并且获得“同籍悉免课役”的特权。甚至获得政治上的资本,踏上仕途,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
二 地方官员的角色
百姓上报祥瑞后,地方长官刺史、观察使等要派属官前往验实,以防伪诈。唐代确实有百姓故意制造祥瑞的案例。比如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地方官员勘验属实,朝廷旌表其门闾。后来发现该孝子每次痛哭,都散饼于地,群鸟纷纷啄食,所以汇集。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也获得朝廷旌表。后来发现其实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于狗案,狗子置猫案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8]105林攒的例子也很有趣:
唐朝一方面是以忠孝作为治国的重要理念,通过对乡里百姓的旌表,树立道德楷模,达到立名教、厚风俗、兴教化目的。《册府元龟》卷59《帝王部·兴教化》详细记载了唐朝诸帝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门闾的诏书,仅太宗贞观年间,就有贞观元年、贞观三年、四年、六年、十三年、十七年,下诏褒奖孝子顺孙、义夫节妇。[7]94贞观十五年五月,并州百姓希望太宗巡幸并州故地。太宗回复,希望“父老宜约勒乡党,教导后生。亲疏子弟,务在忠孝。必使风俗敦厚,异于他方,副朕此怀,光示远迩,使旌表门闾,荣宠家国,书名竹帛”[7]394。另一方面,唐朝仍笼罩在天人感应的政治思想氛围里,验证百姓是否“忠”“孝”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是否有“感应”——也就是祥瑞是否出现。唐玄宗《令郡县采奏孝弟诰》云:“间者抱戴、赤雀、白狼之瑞,接武荐臻,此皆皇帝圣敬之符,孝友之感也。…其天下有至孝友弟,行著乡闾堪旌表者,郡县长官采听闻奏,庶孝子顺孙,沐于元化也。”[1]410
这是指在通读的基础上,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联系上下文对课文中关键句子或暗含着深刻内涵的部分,进行反复揣摩体味地读。在潜心悟读中,学生在脑海中再现课文所描述事物或情境,领悟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哲理或情感。
甘露是上瑞,意义颇为重大。当观察使李若初遣官属验实时,“会露晞”,里人吓得失色,还好最后结局不错。林攒家族也因此获得了乡里优势地位。其实可以揣测,大部分出现祥瑞的家族,并非是普通人家,至少在出现祥瑞并得到官方认可之后,其家族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必然处于优势地位,不论在道德、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处在制高点上。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会成为统治阶层在乡村的代表,甚至成为统治阶级一部分。
取忠臣于孝子之门,在唐代确实有很多此类例子。比如参与推翻武则天政变的五大臣之一的崔玄暐,“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毁,甘露降庭树”[2]4317。玄宗时宰相张九龄,“迁中书侍郎,以母丧解,毁不胜哀,有紫芝产坐侧,白鸠、白雀巢家树。”[2]4428最典型的是杨炎家族,“父丧,庐墓侧,号慕不废声,有紫芝、白雀之祥,诏表其闾。炎三世以孝行闻,至门树六阙,古所未有。”杨炎三代都获得旌表,所以门前有六阙,被认为“古所未有”。这无疑是杨炎家族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资本。
对唐代地方官员而言,发现并上报祥瑞是自己的职责,比如天宝年间,“临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状如天尊像,太守张景夫拔柱以献”[5]1372。祥瑞出现,也同时是地方官员治理有方的反映,在唐代政治思想氛围下,这往往作为官员政绩的佐证,甚至成为良吏形象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要指出,这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套路,而确实存在于当时政治操作中。即便到了唐中后期,神文色彩褪去,但相关政治习惯还在延续。
上报祥瑞是唐代普通百姓获得官位爵位的有效途径。比如蒲州安邑人张志宽,因孝为乡里所称,后为里正。母亲去世后,“有乌巢于庐前树上,志宽哭临,乌辄悲鸣”,唐高祖“闻之,遣使就第吊,授员外散骑常侍,赐物三百段,表其门闾”。[7]176高祖授予张志宽员外散骑常侍,也就让其从普通百姓跻身官员队伍。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又比如高宗时宋州人程袁师丧母,“常有白狼、黄蛇驯墓左,每哭,群鸟鸣翔”,宋州刺史“状诸朝”,高宗“诏吏敦驾。既至,不愿仕,授儒林郎,还之”。[2]5581程袁师被授儒林郎,和张志宽被授予员外散骑常侍,都是因孝招致祥瑞。还有更多的情况并非匹夫之感,而涉及君主的天命,比如李渊《献嘉禾教》云:
令狐熙为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在职数年,风教大洽,称为良二千石。…在州获白乌、白麞、嘉麦,甘露降于庭前柳树。”[9]1385像令狐熙这样的例子很多,出现的诸多祥瑞,在正史书写中基本作为其治理地方成绩的证据。又比如唐高祖时期,岐州刺史梁彥光“甚有惠政,嘉禾连理,出于州境”。[9]1675罗珦为庐州刺史,“修学官,政教简易,有芝草、白雀。淮南节度使杜佑上治状,赐金紫服。”[2]5628罗珦在州治理有方,出现芝草、白雀等祥瑞,节度使上报朝廷,朝廷赐其紫金服。这一点跟百姓因孝致祥瑞,地方长官上报,朝廷旌表的程序有类似的地方。武则天父亲武士彟也以这样方式被描述为良吏:
六是国际界河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中哈霍尔果斯河友谊联合引水枢纽工程年内顺利完工并通过了中哈双方的联合验收。完成了霍尔果斯河流域冰湖处置研究、苏木拜河引水工程改造技术方案设计和乌勒昆乌拉斯图河水资源管理等各项前期踏勘、会晤及联合考察工作。《兵团国际河流防洪工程建设规划》通过了中咨公司组织的审查。严格按照中哈就乌勒昆乌拉斯图河水资源管理达成的共识,通过精心管理和科学调度,实现了乌勒昆乌拉斯图河全年不断流,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唐武士彟,贞观中为荆州都督。初届任时,有白狼、嘉禾出于境内。至是,太宗手敕曰:“公比洁冬冰,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暨,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嘉禾生于垅亩,其感应如此。”[7]2342
不但获得朝廷和皇帝的嘉奖,民间也往往把祥瑞和地方长官的德政联系起来,加以颂扬。比如豆卢勣“为渭州刺史,德泽流行,多至祥瑞”,“鸟鼠山,俗呼为‘高武陇’,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绝壁千寻,由来乏水。诸羌苦之。勣马足所践,忽飞泉涌出。有白乌翔止厅前,乳子而后去。又白狼见于襄武,民为之谣曰:‘我有丹阳,山出玉浆;济我民夷,神乌来翔。’百姓因号其泉为‘玉浆泉’。”[7]2341
州县出现祥瑞,不但对长官有利,属官也与有荣焉,尤其是直接有关的属官。独孤及在一篇墓志中重点描写了主人公李诚在担任河南府司录时的事迹:“自御史为河南府司录,持正不阿故也。宰美周月,收案大猾,除其根株,然后布政。及期而美阳无讼,乃有涸泉涌流,白雀驯于庭。”[1]3979李翰称颂大理评事朱自勉在嘉兴屯田的功绩云:“自赞皇为郡无凶年,自朱公为屯无下岁。……有白雀集于高丰屯廪,盖大穰之徵也。”[1]4375李翰把白雀的出现,作为屯田导致丰收征兆,这在唐代不少见,毕竟以农为本,很多乡村上报祥瑞,比如嘉禾等,也都有这样的意涵。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祥瑞出现,也让官民之间产生“争利”的情况,比如《全唐文》收录阙名《对芝草白兔由刺史善政判》:
岳州人王怀俊,幼丧二亲,庐于墓侧,负土成坟。至孝潜通,屡呈祥瑞,其地内生芝草兼白兔。刺史元利济仁明训俗,善绩著闻。廉察使以为由刺史录奏,怀俊不伏。[1]10114
岳州百姓王怀俊父母墓地出现了芝草和白兔的祥瑞,廉察使认为这是因为岳州刺史元利济“仁明训俗,善绩著闻”而导致。但是王怀俊不伏,认为是自己孝感所致。判词云:“昔闻让善,今见争功,贪天之诚,颇同于往责;无伐之愿,亦隳于前事。但论孝则义归光国,于师则不许让仁,与其抑俊而扬济,未若舍贵而褒下。任虽通广,孝实因心,许与一介之人,岂累六条之政?”[1]10114判词认为应该舍贵而褒下,“任虽通广,孝实因心”,所以应该按照规定褒奖王怀俊。另外判词也再次提到了孝虽出自个人,但是最终也归于国家的观点。
朝廷、地方官、百姓围绕祥瑞展开的互动,是皇权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乡村风俗,巩固符合正教秩序的过程。但是有关制度也会被恶劣地方官所滥用。比如《旧唐书》记载的酷吏王弘义:
弘义常于乡里傍舍求瓜,主吝之,弘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官命人捕逐,斯须园苗尽矣。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5]4847
可见唐代对孝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其中一个标准符合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有精诚致应”出现祥瑞的,尤其可以嘉奖。敦煌《开元户部格残卷》(S.1344)录证圣元年(695)四月九日敕对符合官方嘉奖标准的孝、义之家给出了严格标准:“孝、义之家,事须旌表。苟有虚滥,不可裒称。其孝必须生前纯至,色养过人;殁后孝思,哀毁遗礼;神明通感,贤愚共伤。其义必须累代同居,一门邕穆,尊卑有序,财食无私,远近钦永,州闾推伏。州县亲加按验,知状迹殊尤,使覆同者,准《令》申奏。其得旌表者,孝门复孝子之身,义门复终旌表时同籍人身。仍令所管长官以下及乡村等,每加访察。其孝、义人,如中间有声实乖违,不依格文者,随事举正。若容隐不言,或检覆失实,并妄有申请者,里正、村正、坊正及同检人等,各决定杖六十,所由官与下考。”[6]276其中明确将有“生前纯至、色养过人”,“殁后孝思,哀毁遗礼”,“神明通感,贤愚共伤”视为衡量“孝”的三标准。
三 地方宗族的参与
西京留守武攸望接到属县万年县令郑国忠状,称县界出现庆山;武攸望派遣户曹参军孙履直勘验确认,然后上报朝廷,并且派遣属官绘图奉进。上报仅仅是事情的开始,之后朝廷要做出裁决,重要的祥瑞要宣付史馆、颁示朝廷,中央各官署、地方各州长官还要上表祝贺。整个宣传是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达到全体参与的效果。在上面例子中,武则天就颁示中外,于是“四方毕贺”,[5]4883《全唐文》还收录有当时崔融为泾州刺史所撰写的贺庆山表。[1]2206
《册府元龟》卷681《牧守部·感瑞》专门对此话题进行了总结:“夫政平讼理,民无愁怨,至和浃洽,瑞物来格,斯盖肇自人心,契于神道者矣。自汉室而下,重牧守之任,循良间作,德让宣洽,协气斯兆,嘉瑞荐降,至于服猛鸷之性不为物害,弭螟蟊之灾无入郡境,膏雨随应,夭疠自消,枯木发荣,灵泉沸涌,美利浃於萌庶,休徵表于图牒,著之曩纪,形于谣颂,自非仁化之渊,塞诚心之合,亦何以通至诚之感,臻无方应者焉。”[7]2339正史中良吏、循吏的书写,往往就有感瑞的内容。
研究地铁施工对沿线高层建筑物沉降变形方面的影响,利用建筑物沉降变形曲线图和建筑物整体沉降曲线图对建筑物的沉降规律进行分析,同时模拟出建筑物整体沉降趋势[3-4],对建筑物的沉降变形进行预测,为地铁施工和建筑物变形监测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选取最大、最小沉降量,平均沉降量,平均沉降速率作为评价指标,对建筑物的沉降量进行评价[5-6]。
临床中早发现、早诊断乳腺癌疾病有助于提升治愈率,降低死亡率。早期乳腺癌疾病目前只是存在25%的发现率,所以,予以早期乳腺癌患者实施有效的超声检查不但是判断重点,也属于超声诊断的临床难点[1]。乳腺癌早期症状存在较小病灶,检查中经常不能触及到肿块,存在不典型的病变声像学特征,临床漏诊率和误诊率都比较高。超声造影属于全新且先进的超声医学领域技术,虽然在乳腺癌诊断超声造影表现得到显著改善,但不能有效研究早期乳腺癌疾病。报道在2016年8月—2018年10月期间收治的60例乳腺癌患者中使用超声弹性成像检查、超声造影检查的临床应用价值。
李渊从太原起兵占领关中,尚未称帝,所以他下达的命令称“教”。根据此教内容,应该是当时兴平地方一个叫孔善乐的百姓,给李渊进献了嘉禾。作为回报,李渊下令授予孔善乐从五品下朝散大夫,“以旌嘉应”。我们不知道获得文散官的百姓孔善乐以后事迹,但是可以揣测,这会使他在兴平地方社会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同时,进献祥瑞百姓,也因此跟政权合法性绑定,并成为中央权威在地方社会的主动宣传和维护者。这一点,在敦煌阴氏家族身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当然很可能的原因,是敦煌保存下来的材料丰富,提供了更多历史信息,而其他地区的情况因为信息湮灭而不得而知。
阴氏家族是敦煌地方豪族,在敦煌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上百年。其中主要阴稠和阴祖两大支系,都是在武则天时期崛起。而其崛起主要原因,就是上报祥瑞。从普通百姓,跻身官员队伍,成为当地豪族,都源于其通过上报祥瑞。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五色鸟”条和“白狼”条,分别记载了阴稠之孙阴嗣监和阴祖之子阴守忠“发现”并上报。其中“五色鸟”条云:
右,大周天授二年(691)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觜赤足。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五色具备,头上有冠,性甚驯善。刺史李无亏表奏称:“谨检《瑞应图》曰:‘代乐鸟者,天下有〔道〕则见也。’止于武孝通园内,又阴嗣鉴得之。臣以为,阴者母道,鉴者明也……”[10]61
像安德森这样的育种项目一直在寻找小麦新品种,以满足种植者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环境变化的需求。2011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气温上升已经导致小麦产量下降。而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趋势只会变得更糟,温度每上升1华氏度就会导致小麦产量下降5%。
百姓阴嗣鉴在平康乡武孝通园发现了“五色鸟”,合州官员百姓都前往观看,刺史李无亏上报朝廷,认为五色鸟出现在武孝通园内,由阴嗣鉴发现,证明武则天作为圣母神皇统治的合法性。[11]整个程序符合唐代上报祥瑞一般程序。而阴嗣鉴应该就是敦煌文献P.2625《敦煌名族志》中的“阴嗣监”[12,13]。《沙洲都督府图经》并没有交代百姓阴嗣监上报祥瑞后的结局。《资治通鉴》记载,垂拱四年上报“宝图”的雍州永安县百姓唐同泰,被武则天擢为游击将军[14]6448,相信阴嗣监也会得到来自朝廷的赏赐拔擢。
不过从后代文献中看,阴嗣监居然官居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的高位。阴嗣监子孙一直到10世纪仍在敦煌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号称“安西都护之贵派”,自认“门承都护,阀阅晖联”[15]194,261,已经俨然世代豪族。从普通百姓到北庭副大都护,阴嗣监的仕途,最重要的起跳,应该就是他上报五色鸟祥瑞。
《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武周初年敦煌所谓五色鸟、庆云、蒲昌海五色、白狼等“四祥瑞” 中,“五色鸟”是阴稠之孙阴嗣鉴“发现”,而“白狼”则是由阴祖之子阴守忠“发现”。《沙州都督府图经》“白狼”条云:
剖宫产术后疼痛还可能使原本和谐的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我院曾经有1位产科医生为患者完成了1例高难度的剖宫产手术,当时患者病情危重,很多医院都不愿接收,这位医生顺利完成了手术,可最后却换来了患者的投诉。原因正是术后产妇疼痛难忍,医生未能及时妥善处理术后疼痛。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白狼频到守忠庄边,见小儿畜生不伤,其色如雪者。” 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云:‘王者仁智明悊即至, 动准法度则见。’ 又云:‘周宣王时白狼见, 犬戎服者。’ 天显陛下仁智明悊, 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又见于阴守忠庄边者,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于陛下也。”
阴守忠如阴嗣监一样,在上报祥瑞后一飞冲天,步入仕途,后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其发迹应该归功于这只“白狼”。甚至有学者认为,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莫高窟第321 窟的两尊动物原塑塑像就是阴守忠上报的祥瑞白狼。[16]祥瑞白狼塑像出现,展示了敦煌阴氏,特别是阴祖、阴守忠家族在唐代崛起的发家史,足见献祥瑞是唐代敦煌阴氏家族从当地一般百姓向敦煌大族转变的一种特殊途径。
阴氏在崛起之后,不但拥有了政治资源,而且也在信仰世界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敦煌佛教重要资助者,他们也在信仰活动中占据了更多的信仰资本。莫高窟重要的北大像,就是阴祖和禅师灵隐所造[17]136,其他多个洞窟也是阴氏家族资助开凿。[18,19]
在上报祥瑞中起到桥梁作用是沙州刺史李无亏。[20]上报祥瑞是刺史职责,他上报五色鸟、白狼等祥瑞,一方面往上为武则天的政治宣传增砖添瓦,另一方面往下助推了一个沙洲家族从普通百姓崛起为绵延数百年的地方豪族,可谓中古时期特殊的政治风景。其实在沙洲百姓阴守忠献白狼祥瑞的同时,魏州也同时上报发现了白狼。我们在崔融《为魏州成使君贺白狼表》里读到:
臣某言:某月日得所部魏县申称,得令孟神符牒称,某日得佐吏长寿乡单守中状称:隆周、长寿两乡界有白狼见。臣等尝恐是虚,未敢即申,因处分诸乡,若有见者,辄令系取。某日长寿乡致仕前游击将军上柱国朱佛儿,于长寿乡界内逢白狼,驯狎无惧人意,遂以绳络头系得随送者。……谨寻令式,唯合申台。……谨冒死遣官奉表称贺以闻。其白狼既非常兽,臣未敢即放之山野,见令佛儿养饲,伏听进止。[1]2207
可见当时在武则天即位的背景下,各州纷纷上报祥瑞,沙州和魏州都报告发现了白狼。只是可惜史料缺憾,我们不知道魏州发现白狼的朱佛儿家族,是否因为这次进献祥瑞改变了家族命运。
四 余论
祥瑞与中央地方关系、宗族权力结构、地方文化传统紧密相关,也因此在地方政治、社会、信仰秩序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是观察中古时期地方社会一个很好的角度。祥瑞并非仅仅浮在政治上层装饰物,在唐代,祥瑞思想反映在皇权、地方官员、百姓三方的互动中,至少呈现出三个层次,第一,祥瑞出现象征着皇权的合法性,或者说其受命于天的证据;第二,祥瑞是对地方官员治理有方的认可;第三,祥瑞是百姓忠孝节义的感应。君臣父子,是最根本的秩序。忠孝之道,是维护秩序的根本精神。既是乡村秩序的核心内容,也是统治秩序的核心内容。皇权通过上报祥瑞干预乡村的道德教化,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就干预了地方权力结构,影响到乡村宗族的起落。归根结底,上报祥瑞是符合唐朝时期思想状况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是皇权下县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董 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王 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刘 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张 鷟.朝野佥载[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9]魏 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李玉珉.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壁画初探[J].美术史研究集刊,16(2004):70-71.
[12]马 德.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J].敦煌学辑刊,1997(1):90-95.
[13]张清涛.武则天时代的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浅议[J].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25-430.
[14]司马光,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5]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16]张景峰.莫高窟祥瑞白狼塑像考察[J].敦煌研究,2013(5):31-39.
[17]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18]王仲荦.敦煌石室出《沙洲都督府图经》残卷考释[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1):1-20.
[19]杨学勇.敦煌阴氏与佛教的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6(3):165-174.
[20]王团战.大周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J].考古与文物,2004(1):20-26.
Whose Auspices :The Power and Order of Rural Society in the Tang Dynasty
SUN Ying-gang
(School of Humanistic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7,China )
Absrtact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ory of interaction of Heaven and Man, auspices remained an important agenda of politic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act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political legitimacy. However, auspices were not only used by upper ruling class for political propaganda or adornment, but also acted as a mechanism for controlling the local society. It was officially regulated that certain auspices were reported by local peopl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firmed their reports and launched a movement to praise those who delivered reports. This mechanism provided significant chances for the royal authorities to penetrate into the local society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local elite families gained power and resources by creating and reporting auspices. Some of these local elite families even gained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rural power structure and then deeply influenced the power and order in local places.Under certain cirumstances,the discussion about whose auspices always exited in the Tang Dynasty:are they state′s?are they the induction of the local governor′s morality or the filial piety of the people?This discusstom reflected the complex power and order structure among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local government and ordinary people.
Key words :auspice; Sui-Tang; rural society; custom
收稿日期: 2019-05-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研究”(18ZDA17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转轮王信仰与中古政治研究”(18AZS008)
作者简介: 孙英刚(1979-),男,河南禹州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佛教史研究。
DOI: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9.06.003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 2019) 06-0026-07
(责任编辑 贾发义)
标签:祥瑞论文; 隋唐论文; 乡村论文; 风俗论文;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