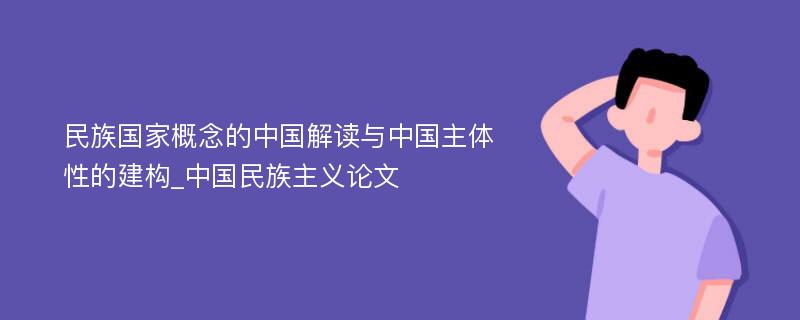
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式阐释与中国主体性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中国论文,观念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趋势成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这一趋势掩映下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却并没有被全然削弱,划分世界政治版图的基本单位依然是民族国家,而对民众最具有政治号召力与道德感召力的也还是民族国家。当然,在世界一体化格局下的民族国家本身也会发生某些变化,诸如吉登斯所称的那样,其国家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具有普遍性,但笔者认为,在民族国家构型逐渐趋同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对自身传统的强调与维护也同样会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和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她的政治与文化社会传统成为有别于其他大国的重要特征,基于此,建立在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式阐释就成为建构中国主体性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准备。
民族国家观念在近现代的简要流变
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最初起源于欧洲,在那个时期,民族的成型是与当时国家的建构同步的,而之后相当数量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则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种欧洲中心观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①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结构有着这种独特的能力,故而在现当代的世界历史中始终是行动的主角,并成为绝大部分国际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
在16世纪之前,欧洲的国家观念依然笼罩在帝国统治的理想之中。历史上所曾经有过的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基督教世界所代表的普世性理念超越了当时欧洲的任何“民族”,它们比任何“民族”都庞大而且伟大。而到了16、17世纪,随着基督教世界理念的逐渐破灭以及作为政治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实性瓦解,欧洲各国开始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民族与语言成为维系民众的最重要的力量,“民族诸象征的华丽甲胄为表达、代表和加强民族的定义范围服务,并且通过共享的历史记忆、神话、价值观等共同形象把民族内部所有成员团结起来”。②而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与传播是与现代宗教本身的衰落趋势同步进行的,“自从18世纪以来,关于历史超自然宗教的怀疑主义的兴盛(尤其是在知识阶级和中等阶级里),也许已经造成一种对宗教情感与崇拜的不自然‘真空’,这个‘真空’看来最好是用近旁的民族主义神灵和热烈的民族主义仪式去填补,而不必用遥远的世界主义神灵和模糊空泛的人道主义去填补。”③随着近代国际法体系的出现,各国之间的边界开始明晰,各自的主权范围也得以确定,民族国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不是国家,民族的分布范畴并不一定会与国家的疆域范围相重合,纵观整个国际格局,单一民族国家在历史语境中往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国家结构的多民族形态反而构成了国际政治的现实场景,而所谓的“多民族国家”是“以多个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是不同民族之间经过相互交往,从而产生政治上联合的产物”,④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将国家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加以整合并形成彼此间的有利互动,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中国”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观念建设
中国历史传统向来以王朝为其叙述对象,而对于制度特征及内部意识问题往往并不在意。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君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争其甘苦;狙公赋茅,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⑤可以说,在遭受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前的中国语境中,民族国家的观念是没有土壤的,而中国传统上的“天下观”与“王朝观”仍然是关于政体的主导性观念形态。
在清朝入关之后,清朝皇帝开始以整个中华的统治者自居,其对于大清的认识也逐渐地具有了“国家”的性质,⑥并且也通过这一时期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的巩固而使清朝的疆域成为之后建设民族国家的基本范围,如谭其骧先生所称的:“我们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⑦这种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历史上变动的政权边界以民族国家的疆域方式加以定义,从而将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范畴往前推,进而型塑出一种时间轴上的民族国家话语叙述方式,反映出西方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范式对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型塑力量。
清末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观念冲击的过程中也逐步在一般意义上接纳了这种民族国家观念,但其间也伴随着中国对这一民族国家观念的再解释过程。作为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中国有着丰富的政治资源与政治实践,这种历史背景使当时处于清朝这一历史语境下的中国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往往处于中西波荡的两难之中。正如柯文(Paul A.Cohen)所言,“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这些局外人的观点,直到不久之前,往往不是夸大西方的角色,就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错误地解释这个角色,从而歪曲了中国历史。”⑧这种感觉同样存在于中国学者中间。而如今更好地在这一西方人所塑造的民族国家观念与中国自身政治历史特征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摆渡,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力量的侵入,在面对这种外来攻势时,清廷对国家的定位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一方面,作为以满洲贵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清廷,始终不愿意为了全中国的利益而放弃其小集团的特权,仍然希望能够维系一个满洲皇帝统领下的庞大帝国,但在另一方面,在近代国家法所裹挟之下的清政府又不得不接受西方话语下的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活动主体的游戏规则。故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表述方式。这种观念超越了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观、“华夷尊卑”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华夷之辨”观念,而具有了新的内容。梁启超在其《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曾称:“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特不知我民族自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⑨而在1903年之后,梁启超受到了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对当时革命党所提出的“排满方能建国”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⑩最后认为,如果中国要建设民族国家的话,就必须“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1)否则就违背了建设民族国家的初衷。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在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观念的认识是存在着一个渐进的过程的,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观念的解读又往往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相关联,“概而言之,从中国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以血统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这两种思想资源出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了‘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国家这两种思想资源出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于‘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的主张。”(12)尽管梁启超的立宪主张并没有被历史所接纳,但之后的历史发展道路所选择的是却还是他的主张——致力于建设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从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所宣布的:“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3)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再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相关规定,中国一直在努力建设具有自身历史特色与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从历史的时间轴来看,“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中国历史观中的“华夷”观的一种超越,而中国政府力图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努力一直没有改变。西方舆论在2008年曾经对中国内部的汉藏、汉维冲突事件多有指责,但却忽视了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政府促进民族和谐的一贯努力,而想当然地将这些问题放在西欧和北美这些公民社会已经取代民族社会成为社会主要构成形式的国家场域中加以观察,无疑会产生偏颇武断的结论。中国自身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始终伴随着西方国家观念与中国自身社会特征的相互调适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主体性的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中国话语
近现代世界格局的几次变动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基本格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冲击,但对处于特定地区与特定环境下的国家的影响则相当深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凡尔赛体系的建立,欧洲版图日渐碎化,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及标志着美苏冷战的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民族独立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伴而行,民族国家数量继续增加,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苏联和东欧地区政治版图继续分化,这种状况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以及苏联式的民族区域治理结构为基础,因而苏联民族结构与国家结构本身出现的解体也让我们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反思。作为有着众多国内民族的大国,中国也开始直接面对西方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双重冲击,而如何用自己的话语方式去型塑自己新的民族国家体系并在当代世界格局中表达自己的意愿与立场,就成为发展中的中国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马克思曾指出:“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14)这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之时的国际背景而言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欧洲地区邦国林立,彼此间壁垒森严,如果没有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社会空间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后盾,欧洲的崛起是不可能的,而在这之后所经历的诸多单一民族国家实践,其结果喜忧参半,新的国家建立了,但却并未带来和平,这就说明单一民族国家并非是国家建设的一条必然道路。正如王希恩先生所言,“当代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已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无直接的关系。从整体来看,当代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主要动因已不是对束缚自身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冲击,而在于民族意识中的消极因素所引发的民族利己主义对民族利益的非份追逐或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对异族的无理排拒”,(15)在这种情况下所型塑的民族国家往往成为新一轮苦难与战乱的开始。
作为研究者,“历史学家一般来说很关注民族身份认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忽略同一过程中其他的身份认同或替代性的(常常是新生的)民族叙述结构被压制和遮掩的事实。一方面,民族已被揭示为一种不稳定和偶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历史却在不断地巩固着民族的神秘性,换句话说,就是巩固民族史一脉相承的主体这一可疑的论断。社会历史学家等有时在实践中怀疑这种论断,但他们尚未能对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提出理论上的挑战”。(16)
除此之外,民族学、政治学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也都有自己的声音并力图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之道。有学者认为,民族学研究偏重于从“民族”的角度来界定民族国家,因而往往会强调民族国家的民族属性,并进而把民族国家解释为单一民族国家,这种解释有将民族国家现象简单化之嫌,同时又会产生否定民族国家存在的结论。政治学研究则偏重于从“国家”的角度审视民族国家,故而其民族国家的概念涵摄范围较广。(17)而如果我们将两者合起来看的话,就可以对民族国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当今民族成员流动非常频繁的时代,理想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意义就此终结,从一般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或者平常所称的“国家”、“祖国”)仍然是能够号召起全体国民一致情感的唯一单位,这种感召力往往通过对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以及伟大人物的集体记忆、统一的价值观以及相关的象征符号等的认同而得到强化。这种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自己能切切实实感受到的背后的依靠力量。
如果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立以前,不管是汉唐还是元明清,从总体状况来说,中国都是具有王朝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在其境内共同居处,一起孕育了光辉璀璨的中华盛世,而其间蒙元与清朝的大一统不仅使蒙古与后金—清政权摆脱了原有的区域化的“内部朝圣”现象,而且使其政治朝圣行为更多地转向中原核心地区(元朝为大都,清代为北京与承德),从而初步构建起一个整体性的中华民族概念。(18)而在建立民族国家之后,中国则转变为具有民族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在这一向民族国家体制转变及发展过程中,在国家认同与整合方面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曾提出过关于国家整合问题的五种危机,即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行政贯彻危机(penetration crisis)、参与危机(participation crisis)以及分配危机(distribution crisis),(19)中国在这一转型中的危机就是这五种危机的叠加。清末中国社会对于满洲统治的认同缺失、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建设中华民国主体认同方面的合法性缺失(表现为缺乏广泛的国际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边缘地区与农村地区行政管理方面的薄弱以及现阶段在民族政治参与及社会资源分配方面所出现的某些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民族国家的认同与整合。
但在另一方面,正如阎学通先生所言,“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内生的,它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其传统文化以及整个政治哲学思想是其民族国家的内生基础。而中国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是从外面借鉴来的,但中国又不能全盘效仿西方……因此,我们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也摆脱不了这个模式,即借鉴外部思想和模式,然后与中国特有的基础相结合,这是我们的方法和必然路径”。(20)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建设民族国家并努力融入国家社会的过程中,对自身传统与资源的挖掘与再诠释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中国的复兴所依靠的不仅仅是经济力量,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软力量(soft power)更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决定性力量。而这种软力量的有效发挥又取决于良好的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多民族国家维护自己政治稳定、领土完整,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严格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人民主权原则行事,在多元主义的框架下协调民族之间的利益分歧和文化差异,通过制度化的权利分享机制夯实不同民族建立互信的感情基础,使少数民族自愿选择合作共存的道路,在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内实现民族的发展繁荣。”(21)而在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在作为软力量源泉的教育领域增强对国家历史与民族共有的荣辱经历的进一步教育,要努力建设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并形成新的文化观念传统,使之趋于持久稳定,同时加大对中国历史过程中的边疆意识与民族现象的研究力度,进而努力形成在这方面可以进行国际对话的中国话语体系,唯此,方能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确立起真正的中国主体性。
民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所带给我们的遗产,这一问题在当今新的国际环境下更会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历史经验中既有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当然不能忽视,但仅凭历史经验并不能全面解决当代所产生的新形势与新问题。“我们再三强调历史与现代民族密不可分。民族(及由其衍生的民族主义领袖和以民族的名义行事的民族国家)获得作为历史主体的特权和主权。没有主体,现代历史将毫无意义;主体在变,但不会消失。我们自己的历史实践表明: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王权、国家、阶级、个人、身份认同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参照系总是民族。我们从来不怀疑我们所学的历史就是中国、印度、日本或法国的历史。民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暗示专业与通俗的历史:它才是历史的支配主体。民族参照空间从来就没有无辜地沉默着,它为所有‘自己’的历史争夺疆土、人口和文化。”(22)在这个基本由西方所创设的规则罗织起来的国际社会中,学术研究中的中西规则分野也强化了东西方在各个语境下的对立局面,如果脱离开萨义德“东方主义”概念下的阿拉伯世界的“东方”,那么,作为亚洲的东方则具有更为明确的比较意义,而作为东亚大国的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展现出自身的地位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葛兆光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按照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说法,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标志,是‘从天下到万国’。从以自我中心想象天下的‘华夷观’中走出来、打消了盲目自大的近代中国,却逐渐养成了以西方为背景审视自身的习惯,‘中’和‘西’(或者‘东’和‘西’),中国一方面习惯把自己看成‘东方’的代表,一方面开始把‘西方’作为认识自我的唯一镜子,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梁漱溟,无论是‘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还是‘中国文化本体论’,中国始终都在西方这个尺度中被观看的,美丑妍媸,都来自那一面镜子。”(23)民族国家作为当今世界国际格局基本单位的事实已经无法动摇,但是,这种国家形态是否必然要按照西方的标准设定,则仍然是值得加以讨论的。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号召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在这段时期对建设一个怎样的民族国家始终在摇摆不定,而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对于自身主体性的强调。如果说中国已历经了从“天下”走向“万国”的阶段,那么,从“万国”走向“中国自身”就成为新阶段的任务。
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下,我们除了需要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之外,还需要从思想文化及政治观念层面为“中华民族”实体化建设作出努力。在这方面,中国自身独特的法律体系及边疆观都能够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撑与基础。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使一定疆域内的民众凝聚为一个国家,并形成其国家组织形态的最为强大的纽带。(24)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法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效地保障了中华文化与文明国家的绵延不绝,而且在当代也依然形成了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中国之为一种历史—文化命运共同体和一种政治共同体,悉数笼统于一种主权拟制的空间结构之下,而且正在努力形诸一种普遍主义的汉语文明法制安排之中。迄而至今,应当说这一过程尚未最终完结,但却基本成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特定文化内涵。”(25)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对疆域的大一统意识也有效地抵挡着国家分裂与民族分立的倾向,成为值得继承与发扬的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而多民族“和而不同”的和谐态势也正体现着这种悠久历史传统,在现阶段也都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如果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发展战略来看,全球化实际上正应该是中国式的现代化。(26)总之,在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可动摇的今天,作为一个有自身传统的大国,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自身定位决定了其必须要型构一个有自身特点与传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在与世界各国实现平等共处的基础上维护本国的最高利益。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说的:“其它的古老文化消亡了,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变革。中国始终显出变革和成长的能力。今天中国要迎接一个新的世纪,而你们的这个世纪正是中国振兴之时”,(27)我们努力期待着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体性在这个世纪中的巍然确立。
注释:
①卜正民、施恩德:《导论:亚洲的民族和身份认同》,卜正民、施恩德主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②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③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236页。
④高永久等编著:《民族政治学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⑤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1936年版原始页码,新版未作改动)。
⑥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⑦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第3期。
⑧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页。
⑨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35页。
⑩(11)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三,第74、76页。
(12)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
(13)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2页。
(15)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243页。
(16)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17)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18)袁剑:《故乡的离愁,民族的“朝圣”——兼读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民族报》2010年6月11日。
(19)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1966,pp.62-67.
(20)范勇鹏、李彩艳:《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加强民族国家建构——阎学通教授专访》,《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1期。
(21)王建娥:《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多民族国家化解民族矛盾、解决分离窘境的一个思路》,《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22)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28页。
(23)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序言”。
(24)参见卡尔·门格尔:《法律的“有机的”起源》,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25)许章润:《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载许章润主编:《历史法学》第一卷《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5-48页,此处为第30页。
(26)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27)牟卫民主编:《隔岸观潮——外国政要眼中的中国》,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标签: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主体性论文; 饮冰室合集论文; 政治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梁启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