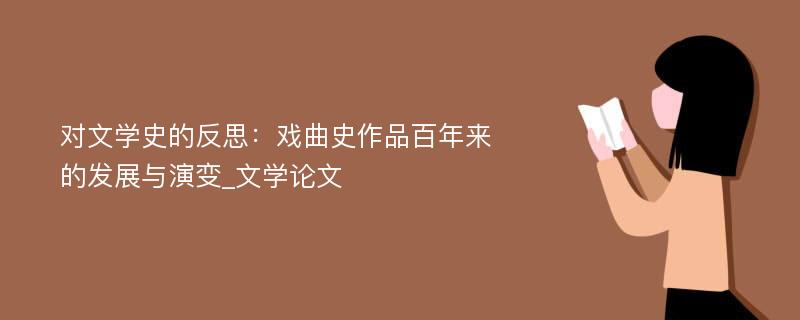
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百年来戏曲史著述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史学论文,戏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曲史著述是戏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是戏曲史研究所产生的诸多成果中的一种。
关于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在戏曲形成之初便已开始,戏曲研究的起步与戏曲创作实践的兴盛几乎同时。戏曲文学与单纯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样式不同,戏曲成品的展示实际上是通过作为一度创作的文学剧本和作为二度创作的舞台表现来共同承担的,其审美价值也是由文学剧本和舞台表现共同实现的。所以,戏曲研究的对象一开始就涉及文学创作和舞台表现两个系统的内容。例如在南戏形成以后,杂剧高度繁荣的元代和明代初年,便出现了研究有关戏曲剧本创作的著作,如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钟嗣成的《录鬼簿》、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和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等,还有研究有关舞台艺术的著作,如燕南芝庵的《唱论》、夏庭芝的《青楼集》等。《录鬼簿》、《录鬼簿续编》记录了作家的生平事迹、作品名目以及概括了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中原音韵》总结了北曲的用韵规则及曲辞写作规律;《太和正音谱》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北曲曲谱;《唱论》探讨演唱技法及演唱的表现特征;《青楼集》记录了戏曲演员的生活片段和艺术特长。明代以后,以“曲品”、“剧品”的形式出现的品评作家作品的著作和以“曲谱”名称出现的探讨曲辞的语言格式、音韵规则,规定音乐调式以指导填词和度曲的著作层出不穷。同时,属于戏曲舞台艺术研究的著作也在不断出现,例如明代沈宠绥的《弦索辨讹》和《度曲须知》都是规范戏曲演唱中念字的格律、技巧和方法的。清代黄旛绰的《梨园原》则是研究戏曲的表演艺术的。另外还有一类,是既探讨戏曲文学剧本创作的具有规律性的问题,又研究具体的戏曲艺术技巧的综合性论著,如何良俊的《曲论》、王骥德的《曲律》、李渔的《李笠翁曲话》等等。这些丰富的戏曲历史研究著作,就是本世纪以来戏曲史著作诞生的材料资源所在和学术传统的渊源所在。
中国古代戏曲与在文学史上占主流位置的诗文相比,总体上说,长期处在被“鄙弃不复道”的境地。当然,具体说来,元、明、清三代情况有所不同。元代戏曲创作者大都是或“门第卑微”,或沉溺下僚,或不屑仕进之人,而明代却有王公贵族、达官显宦或文坛名人士参与戏曲创作,官方主持编辑的《永乐大典》也收有戏曲剧本。入清后,情况又发生变化,官方对戏曲的贬抑、排斥加强,乾隆年间编的《四库全书》不再收入戏曲剧本。以上这些情况,纵见相异,但戏曲在文坛上没有获得过与正统文学平起平坐的位置,这一点又是相同的。清代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朴学”的出现,较之前代有显著的开拓,但朴学家大都是轻视乃至鄙视戏曲的。因此,深入地研究戏曲和戏曲史一直到清末才出现转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历代零散的、以笔记形式出现的戏曲研究著作成为本世纪初戏曲史著作诞生的基石。
这些古代的戏曲和戏曲史研究著作提供给近代戏曲史著作撰著的养料,除了用以再现戏曲历史面貌的原始史料外,学术思考方面的启示起码有两点:一是戏曲史著作的选票范围;二是如何认识和展示戏曲中的各个重要组成因素和创作环节之间的关系。
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为标志的戏曲史著作在本世纪初诞生,无疑受西方文学史撰著观念、方法和模式的影响,与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的产生互相呼应。如果说,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形式建构上与西方已有的文学史著作的模式可以一定程度并轨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古代戏曲特有的复杂的构造形式,戏曲史研究者在营造戏曲史著述的框架时,很难直接地从西方戏剧史著作中找到依傍。我们通常所见的西方戏剧史著作那种以剧院演出为中心的结构形式和研究视点,与我国古代戏曲研究立足于曲学的学术传统不一致。几百年来,戏曲艺术实践的发展过程和林林总总的戏曲史研究著作向近代戏曲史撰著者提出了在结构戏曲史著述时需要解决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其一,以什么为主线来描述戏曲发展演变的历史,探讨戏曲发展演变的规律。百年来,戏曲史著述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表明,戏曲史著作中对描述和研究的主线的选择和确定,受学术传统的引导和制约,也受材料留存条件的限制,更受戏曲自身创作环节变化的影响。此外,还受研究者自身条件和治学特点的影响和制约。例如本世纪初,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注重史料,爬罗剔抉,钩沉稽索。并在史的叙述中抖露观点,见出史家风格。他以作家、作品为主线,也见出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样是选择作家作品为主线的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则更多继承传统曲话、曲论的成分,所作评论也多从传统曲学视点出发,这同他本人是一位曲学家这个特点密不可分。而本世纪90年代初,马少波等主编的剧种史《中国京剧史》以戏曲班社和演员为主线,则是由京剧自身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的。
其二,如何处理和揭示戏曲艺术中诸种艺术因素之间和诸种创作环节之间的关系。在戏曲历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作品,大多是在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作品。这类戏曲作品实际上是依仗于各个创作环节的共同工作完成的,它们的长久流传,不被历史淹没也是借助于各个创作环节为媒介得以实现的。从创作主体说,包括剧作家、导演(广义上的)、曲师、乐师、演员等,从创作成果看,除了文学剧本外,还涉及音乐、舞台美术、表演等方面。前人大量的戏曲史研究著作中,最多的是关于作家作品品评的著作。在作品品评中,又多从两个视角探讨问题,一是品评文词,辨音析句,二是斟审音律。可以说,前人评论戏曲作家作品的视角是承袭传统的诗文品评路数而来,尤其与诗词品评的思路一脉相承。另一类戏曲研究著作是探讨关于戏曲舞台艺术创作中若干分支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它们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之间,以及它们与戏曲文学作品之间,大体上是分离的。我们现在是在文学专史的范围里讨论问题,也就是说,是从戏曲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即使仅就文学剧本看,剧作家只要是以剧本的体裁进行创作,就不仅要按照叙事文学创作的常规,考虑人物、情节的文学表现,还必然受到作为舞台表现手段的诸种具体形式的限制,诸如戏剧代言体的叙事角度,唱词、说白、人物上下场、人物的舞台动作、舞台调度等叙事方式等。即使没有付诸演出的文学剧本,剧作家在创作时也必定会溶进对舞台表现的考虑,如李渔所说:“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闲情偶寄·宾白第四·词别繁减》)尽管不是每个剧作家对舞台表现的熟悉和关注都达到李渔的程度,但剧本文学中,包含着与戏曲其它艺术因素的种种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其三,就文学剧本而言,建立起以剧和曲结合的研究视点。长期以为,以曲为中心的研究框架,不利于揭示戏曲艺术的特性和本质,这一偏向,在本世纪不同时期出现的戏曲史著作中,逐步得以矫正。仅就最初诞生的几部戏曲史著作看,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到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在研究视角上,即处于由“曲”到“剧”的逐渐变化过程中。
一百年来,戏曲史著作的发展变化,正是围绕在上述几个问题上的进展所表现出来。具体说来,本世纪以来的戏曲史著作是沿着以下几条线索逐步发展变化的,这些变化应该说是研究者戏剧观念逐渐完善的结果。
一、史著容纳的戏曲艺术成份逐步增加。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写于1912年)是最早出现的戏曲断代史。王国维对戏曲的概念作了界定:“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戏曲考原》),戏曲“必合言语、动作、歌舞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宋元戏曲史》)。这一概括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戏曲艺术的特征,表现出对戏曲包括多种艺术因素的综合性特点的清楚认识。但是,王国维的这种认识没有贯彻在他的著作中,他在选择描述对象时,他的视野大体局限在作家作品,局限在一般文学评论,而没有更多地作“以歌舞演故事”中涉及的诸种艺术因素的考察。以后出现的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出版)、卢前的《明清戏曲史》(1935年出版)都沿袭了这种研究范围。60年代初出版的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中便增加了声腔流变、戏曲扮演等剧本文学以外的内容,80年代初出版的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更是把属于戏曲舞台艺术部分的音乐、舞台美术、表演的历史发展情况,分门别类进行介绍,把它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进行研究。史著包容的戏曲构成成分的增多,看似是一种表面现象,但这种选择反映的却是对戏曲这种艺术样式认识的深化,也区分了“场上之曲”与“案头文学”的差异。
二、研究重心由曲向剧转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勾勒戏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显示出“史学”本色的同时,在评论戏曲作家作品时,视点多限于“文章”、“辞句”,大体继承的是古典诗词批评的传统。当然,王国维在评论剧本时,尽管注意力主要在“文章”,但已经有了剧的观念,这从他关于杂剧的悲剧问题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但这种观念在他的评论中没有系统化,在他的戏曲史著作中,没有依据剧的观念形成一种批评框架。从戏曲史著述的实际情况看,区别于散曲评论角度的戏剧的评论视角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把在场上演出适宜与否,作为评价文学剧本的标准之一。这在古时曲学家的曲话著作中已有体现,继承了曲学传统的吴梅在评论戏曲剧本的高下优劣时,有时就用这一标准,例如评《长生殿》和《桃花扇》“仅论文学,似孔胜于洪,不知排场布置,宫调分配,昉思远驾东塘之上”,“《桃花扇》有佳词而无佳调;深惜云亭不谙度声。二百年来词场不祧者,独有稗畦而已”(《中国戏曲概论》)。吴梅对阮大铖、李渔的剧本的高度评价也出于这样的标准。这种视角从一个方面纠正了只重曲文的文学价值,以曲文的优劣为唯一的标准来评判剧作水平的偏颇。其二是以前苏联、欧洲的话剧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戏剧冲突、人物性格冲突等方面剖析剧作,这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的差异,纠正了重曲不重剧的偏差。这种理论依据在80年代以后出版的戏曲史著作中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
三、逐渐重视戏曲文学与其他艺术成分的关系。这一问题与上述两个问题相关联。当研究者以整体考察剧本中的形象塑造和意义表达代替曲辞片段的把玩品评,当大量有关古代戏曲的文物被发现,其重要性又日渐被认识,研究者们自然会注意戏曲文学剧本特有的体制是由文学和舞台表现多方面的叙述需要共同铸就的。以元杂剧断代史为例来说,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到李春祥的《元杂剧史稿》(1989年出版)、李修生的《元杂剧史》(1996年出版),对元杂剧剧本文学体制与舞台艺术因素关系的论述,便渐趋明晰和完善。
以上所述犹如戏曲史著述发展变化的三个轴心,第一点立足于对戏曲历史的展示还原,第二点是关于戏曲创作成果评价的视点和标尺问题,第三点着眼于对戏曲本体的认知。在第二点上存在的问题最为明显。问题有两重,其一是曲和剧两种评价尺度之间关系的处理,其二是引进的西方话剧理论与中国古典戏曲这一研究对象对接时有效和无效部分的分辨。如果说,百年来戏曲史著述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最见研究者的卓识和最具学术意义,那么,今后超越的基点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