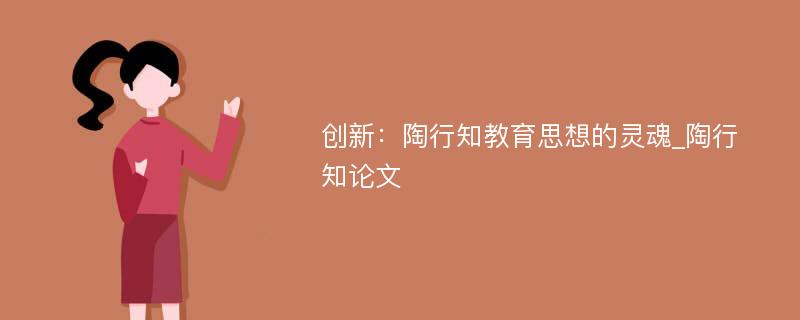
创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灵魂论文,行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2)03-0042-05
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钱,贯串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
一、教育观念和教育方针的创新
传统教育奉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思想,把教育看作是升官、发财的途径。陶行知旗帜鲜明地指出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1](P.362)中国的教育由戊戌变法进行了部分变革,开始废八股兴学堂。“五四”前后又进行了改革,结果是丢弃了“老八股”,取而代之的却是效仿德、日、美的“洋八股”。陶先生指出中国的新学办了三十年,只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他大声疾呼“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何能求其进步”[2](PP.93-94)?
陶行知的教育观与传统的教育观截然不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使人民大众受教育。他说教育不应是玩具,也不应是装饰品,更不应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不是“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的“小众”教育,“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3](P.338)陶先生指出“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3](P.393)陶先生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适国内外之势,提出受教育者应达这样的目标:“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五个方面用现在的话可以概括为“体、劳、智、美、德”。总结以后的诸多论述,可把他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大众服务,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人们做自己的主人,培养德、智、体、美、劳诸方面谐调发展,具有自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真善美的活人”。这充分体现了陶先生“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
1.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陶行知认为,教育不应象“老八股”、“洋八股”那样用来麻醉、欺骗广大青年,不应是生产“伪知识阶级”和培养特权的工具。他认为教育应为救国救民之用,发展教育是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必由之路,是国家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根本大计之所在。早在他创办乡村教育时就指出,教育“担负改造生活的新使命”,并深信“教育能够叫中国的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他强调:“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2](P.651)陶行知的观点,用今天的话表述就是教育要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2.教育与社会生活和劳动的关系
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实践人为地割裂开来,其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使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这种教育,陶行知一方面强烈地反对,并号召要革书呆子的命;另一方面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的口号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社会生活和劳动,从现实生活出发,联系现实生活实际,为改造和提高现实生活服务。提出学校要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要仅仅局限于学校,而应面向社会。
他曾讽刺脱离生活的旧教育是“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水已尽,山将穷;老鼠钻进牛角筒。”[4](P.123)并强烈地意识到,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的旧教育是非常可怕和令人担忧的。鉴于此,他指出教育与生活和劳动不能脱离,它们应紧密相联,提出“生活即教育”。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5](P.2)
3.教育的培养目标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他说:“我们要在必有事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中心。研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2](P.503)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他重申要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学生。他号召学生每天做如下“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3](P.464)陶行知提出这“四问”颇具独特见解。
二、教育内容的创新
教育内容是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教育方针、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载体。陶行知认为,教育内容的创新应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实际情况来确定,其主要表现为:
智育,陶行知极注重科学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一直只把“四书”、“五经”等先贤的遗文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圣贤的文章不乏精辟之处,如果把它们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就会忽视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此,陶行知要求青年必须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提出:“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他认为科学基础知识是一把钥匙,而“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他主张要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前沿性的、技能职业性的科学知识,他说“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最重要的知识技能,无过于自学科学。没有真正可以驾驭自然势力的科学,则农业文明必然破产,工业文明建不起来。”[5](P.292)在教育实践中他正是这么做的,南京高师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就给他们开设有介绍科学常识的课,既有遗传学,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说到孟得尔的杂交实验。另外还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史、心理学等课程,并强调要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具体反映,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教学用书,是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智育的重要媒介。当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很少以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大都含有封建流毒的思想。它们的通病是以文字做中心,空空洞洞毫无内容缺乏实用性。比方甲家书馆的教科书是“小小猪,快快跑,小小猪,快快跑。”乙家书馆是“小小猪,小小猪。快快跑,快快跑。”他认为“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身体。”[5](P.294)对于这种教科书陶行知坚决反对使用,他亲自着手研究教科书,并且组织一批教师去编写教科书。他认为辨别书的好坏就要:“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5](P.300)并指出应根据实际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比如他在回国不久推行平民教育时,为达到使平民识字明理的目的,他亲自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使五十多万人受教育。在上海搞普及科学教育运动时,他为儿童组织编写一百种的《科学丛书》,并组织编写了《大众科学丛书》,还亲自撰写了天文学的科普读物。这些活动旨在“要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3](P.513)。
德育,是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认为,封建教育只重视念书做文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至于气节品行教育丝毫不讲究。因此,他主张在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应注重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他指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做恶愈大。”[3](P.471)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德育主要之点就在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
他提倡讲求“公德”和“私德”,强调良好公德能使集体、国家兴旺发达,不顾公德的结果是“多数人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利益,则这个集体的基础必然动摇,并且一定要衰败下去”。“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因为“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要求学生必然有一种高贵的品德成绩表现出来,既要讲“公德”又要讲“私德”。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是针对封建教育只重视“学而优则仕”和以“文章定功名”的强烈抨击和讽刺,是对旧教育的德育进行的一种全新创造。
体育,传统教育从不提倡体育,教育者“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成了“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乃至当大学毕业时“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5](P.733)陶行知对此极为关注,在注重德育、智育的同时,把体育提高到等同于德智二育的基础地位。指出只有身体好,才有德智的存在。否则,虽具有良好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这种学识道德,不能用以树不世之业,为人类创造莫大之幸福。在他看来,体育是德育、智育的物质基础。显然陶行知始终把体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为此,陶行知积极倡导对体育进行革新,早在南京高师任教务主任时,就重视学校的早操,并在学校设置了体操、兵操、拳术等课程。在创办晓庄师范后,陶行知把体育具体落实到教学活动中。还请人来校传授体育技能。在育才学校期间,更是重视体育,而且体育课比前期更为规范,开展了以田径、球类、游戏等自然活动为主的“自然体育”,取代了以前以刀枪棍棒为主要内容的“兵式体育”。同时还强调把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也列为体育课内容,扩大了学校体育课程的范围。
三、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法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陶行知认为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种种弊端,其主要表现是教学领域中存在“重教太过”、“教学分离”等主观主义痼疾。这种主观主义的特征是教学过程被演化成简单的告诉与被告诉的过程。教师只知道自己做自己的教授,不管学生能否接受,只知道反复地一味灌输和强化作业。人们也习惯于把教师所干的事称为“教书”,把教师教书的法子称为“教授法”,似乎教员是专门教书本知识,此外无别的可教。学生在校内也似乎除受教外,无别的功课可学,于是乎出现了“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来却又像教校”。他尖锐地指出这是教与学的分离,并呼吁“教学二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两者分离是违背教学规律的,其弊端最终表现为“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2](PP.87-88)
陶行知指出教学方法必须革新,用新的教学方法取代旧的教学方法。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5](PP.41-42)。同时他指出中国应同欧美国家一样,要废除注入式、填鸭式的教授法,取而代之的应是“教学做合一”法。陶行知明确阐明“教学做合一”法的含义,在撰写《教学做合一》一文时,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来定。后来又进一步阐述“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5](P.42)
陶行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做”的环节,认为“做”是首位的,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教与学之所以能统一,就是统一在“做”上,只有“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是学生。”“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否则,“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5](P.42)
陶行知还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动精神,反对灌输的教学方法。他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强调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他明确指出“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教给学生”,[3](P.444)教师要在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上更进一步,使学生“不得不愤,不得不悱”。关于培养学生自动精神,陶先生曾精辟地论述“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在自动上培养自动,才是正确的培养。若目的为了自动,而却用了被动的方法,那只能产生被动,而不能产生自动”。[3](PP.444-445)培养自动精神则能使教育的收效事半功倍,因此,陶先生要求,要特别注意把自动力的培养贯彻于全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
传统教育用会考来确定学生是否毕业,会考成为衡量学生学业的惟一标准,这种教育制度不仅扼杀了学生的生机,束缚了青年的思想,而且使学校成了会考筹备处,学校必须教的课都是要会考的,不会考的课则“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学校中的音乐课、图画课、体操课、家事课等等课内外的活动都被取消了。陶行知尖锐地揭示出这种制度是“变相的科举”,“大规模地消灭民族的生存力”。因为,学校“所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生命赶掉了,这真是杀人的会考,用会考在杀人”。[5](P.676)为此,他大声疾呼要停止这种毁灭人生活力的单纯性文字之会考,对学生应采用新的评价方式。
陶行知主张以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建立和发动能培养生活力的创造的“考成”,并阐明“考成”要以生活的实质为内容,不能象会考那样“纸上空谈”,要注重学生的身体强健状况,手脑并用的程度以及改造物质和社会环境的程度。陶行知深信这种着眼于实际生活,重视培养人的实践力、创造力的“考成”,较之会考制度引发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创新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背景下,总结并借鉴他成功的教育理论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主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