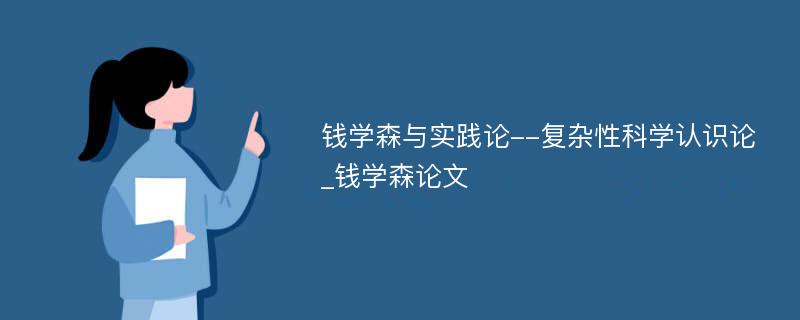
钱学森与《实践论》——再谈复杂性科学的认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认识论论文,再谈论文,性科学论文,钱学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0)01-0065-06
钱学森视毛泽东的《实践论》为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哲学基础。本文通过考察钱学森对《实践论》的评价、运用、发挥,以深入了解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和哲学立场,进一步探讨复杂性科学的认识论。
一、从认识论上超越还原论科学
钱学森于1955年回归祖国后,通过系统的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那时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他一直自觉坚持这一哲学取向。1970年代末从国防科技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钱学森的全部精力都投放于学术研究,重点是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以及作为这一时期学术研究总纲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由于相关的理论成果基本上已形诸文字发表,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是如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研的。
以1978年那篇里程碑式的作品[1]为起点,到1987年形成复杂巨系统概念之前,钱学森的系统科学研究主要有三项工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理论,梳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通过综合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既有理论成果建立系统学。在此过程中,他不断讲到科学研究要以辩证唯物论为哲学指导,并归结为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实事求是,防止主观主义和空谈;二是克服机械唯物论,避免死心眼。就钱学森此时期的著述看,这两方面的指导作用都集中体现于科学方法论的探索,强调把握整体性,以系统方法解决问题,而没有涉及认识论,未提到《实践论》和《矛盾论》。
回顾400年来还原论科学的发展历程,科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开创新学科的著作,感兴趣的是方法论探索一般不涉足认识论问题。还原论有多方面的含义,核心是定量描述的还原论,即相信(假定)对象有一组可以精确测量的特性,描述它们的一组特征量(变量和常量)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形式(特别是方程)把这种关系表示出来,建立量化模型,从而把实在的对象转变为数学的和逻辑的问题来处理[2]。一种理论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要看两点:一是它在逻辑上是否自洽;二是它能否经受住实验室中可控性实验的检验,而无须接受一般社会实践的检验,故不必涉及认识论的探讨。那些走上公理化、形式化描述道路的学科尤其如此。这种被钱学森称之为“科学推理方法”[3]25的方法论取向,通过教材、论文、专著、课堂教学、师徒传承等方式而深入科学家的思想观念,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常识,一种人人都自发遵循的惯例,也就成为一种盲目性。钱学森也不例外,不仅在当年从事力学和工程控制论研究时如此,在1978到1987年从事系统科学研究也如此。
直到今天,多数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仍然坚持这一方法论。系统科学的主要分支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工程等,尽管跟还原论的自然科学比较具有显著特点,如明确使用系统概念、强调从整体上认识和解决问题,但方法论基本上还是科学推理方法那一套,主要是定量描述的还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这些从理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产生出来的系统理论,基本依靠逻辑推理来解决问题,无须考虑实践经验的作用。但方法论与认识论不能截然分开,不讨论认识论的科学著作不等于它没有认识论。实际上,跟方法论上的还原论相适应的是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把认识看作人脑对客观事物径直的、静态的、被动的简单反映。由于所处理的对象属于简单性范畴(用钱学森的语言讲,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工程等处理的是简单系统,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处理的是简单巨系统),认识运动的辩证性不明显,基于形式逻辑的科学推理方法足以解决问题。
当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进展到超出简单系统和简单巨系统,面对真正的复杂性问题(钱学森称为“开放复杂巨系统”)时,由于对象系统没有良好的结构,或者找不到一组可以精确测量的特征量来描述系统,或者特征量之间没有明确的数学关系(无法建立量化模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主要靠逻辑推理加实验室可控性实验的那套方法不再有效了。在处理这样的系统问题时,认识运动的辩证特征十分明显,迫使系统科学界开始向重视运用实践经验的方向转变,从认识论上思考问题成为必要的了。跟世界系统科学界大体同步(见参考文献2),钱学森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最先使他觉察到单纯逻辑推理方法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是大系统理论。1985年,控制论专家涂序彦提出大系统控制需要直接引用一些经验知识,还要利用专家系统。钱学森对此表示“非常赞成”,进而引申说:“在解决大系统的系统工程问题时,要注意利用不能称之为‘科学’的人的知识和经验”,并判定为“这在控制论中是一个突破”[1]300。他还注意到灰色系统理论“也有经验判断的因素”(同上)。由此启动了从认识论上超越还原论科学的思考历程。
1970年代以后兴起的软科学研究也对钱学森的思想转变起了推动作用。粗略地说,所谓硬科学指的是单靠逻辑推理就能够基本解决问题的学科,所谓软科学就是那些单靠逻辑推理不行、还需要利用实践经验才能解决问题的学科。钱学森迅速把握了科学发展中的这一新动向,在1986年指出:软科学研究有三个要素,一是信息、情报、资料,二是收集专家意见(经验性判断),三是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计算,即数值试验(被称为人类的第四种实践形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路径解决问题[1]389。三年后正式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其基本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已表述得比较清楚了。
关键性的转变发生在1987年。在这之前,对于钱学森来说,复杂仅仅是一个一般术语,复杂系统还不是必要的科学概念,他用以对付复杂性的基本概念是巨系统。通过对人体系统、思维系统、社会系统等持续多年的具体探索,钱学森在1984年萌发了一个新想法:“复杂一词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术语,而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科学概念,仅有巨系统概念可能尚不足以对付复杂性”[4]229。又经过三年思考,钱学森对复杂性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到巨系统包括简单巨系统和复杂巨系统两类,二者性质迥异,研究方法必然有原则的不同;二是认识到处理复杂系统问题需要深入探讨科学与经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已故的王寿云将军是钱学森的重要助手,这一年他在总结钱学森学术思想的新发展时写道:“钱学森认为,处理复杂行为系统的定量方法学,是科学理论、经验和专家判断力的结合。这种定量方法学,是半经验半理论的。”[1]增订版说明王寿云在这里正面谈论的仍然是方法学,但探讨认识论的色彩已很明显。
1990年代,当钱学森在复杂性研究中走出对科学推理方法普遍适用的盲目性之后,即以过来人身份对这种方法论作出鞭辟入里的剖析。他指出,科学推理方法所讲的逻辑实际上指的仅仅是一阶逻辑,面对简单系统和简单巨系统问题,由于“一阶逻辑,比较成熟有把握,所以敢于用它‘深加工’,从公理、定义得到可以信赖的定理,中间不需要再与事实核对”[3]436。几百年来科学的发展是如此,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系统科学的发展大体也如此。1990年代,钱学森在认识上发生重要转变之后,曾多次指出,处理简单系统的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工程等,处理简单巨系统的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它们的方法论本质上仍然是还原论。自然,1980年至1987年期间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系统学的努力,使用的方法本质上也是科学推理方法,寄希望于用一阶逻辑进行深加工,中间不需要再与事实核对,因而无须考虑理论与经验、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不必涉及认识论问题。相反,人们一旦面对真正的复杂性问题时,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一阶逻辑不够用了,需要的是高阶逻辑,在处理复杂性问题的认识过程中必须反复跟经验事实核对。
传统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还不止于此。钱学森反复引用爱因斯坦的观点强调,应用科学推理方法的前提是人在实践中认识到许多事实,积累许多经验,经过大脑加工形成科学设想,然后才是逻辑推理问题。“……逻辑推理问题,有点科学知识的人都会做。但是关键的那个部分,即从事实到设想,这个过程是最难的”[3]25。明确了关键是从经验事实上升为科学设想,就使钱学森将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跟认识论联系起来了。
二、把《实践论》作为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的认识论
浏览钱学森近30年来的著作容易看到,对于科学研究中的新观点、新说法,他总喜欢问一问: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常常作出这样的评判:这个说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个结论有违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钱学森常常直截了当地质疑道:“……讲到哲学,怎么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5]204,“似乎还没有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问题”[5]244,批评他们“没有对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加以评驳”[5]236,一再提醒他们“请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5]203。特别是对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他一向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审视,力求使之建立在正确的哲学基础上。看得出,钱学森力求建设一个自觉而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研集体。
在区分了两类巨系统之后,钱学森用了大约两年时间对复杂巨系统概念和定性定量相结合方法作进一步的加工提炼,最终定格于开放复杂巨系统这一“整个系统科学的核心概念”[3]61,得出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定性定量相结合是惟一可行的方法”[3]27这个论断。在系统科学发展史上,这一进步确实是里程碑式的。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据何在?如何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深化和发展这些科学新思想?钱学森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思考的结果产生了《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一文(1989),明确承认这些新认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启发的”[3]194。按照钱学森确立的科研原则,既然断定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开辟了一个很大的科学新领域,作为一种新的基础科学,当然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这篇文章在钱学森的系统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看成他关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指导思想的宣言书。此后不久,他在一封信中把科学方法论中的定性定量问题跟认识论联系起来,写道:“其实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来说,一切认识都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总是从定量上升到定性”[5]206。他由此开始从认识论上系统地探讨如何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和建立复杂巨系统学,表现就是这之后的文章、讲演、书信中大量谈论实践与理论、经验与科学、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等认识论问题,并很快追溯到《实践论》的指导作用,跟前此的文章、讲演、书信形成鲜明对比。就目前已公布的信件来看,从1991年至1997年,钱学森在给他的六大将的大量信件中至少15封信明确提到《实践论》,3封信提到《矛盾论》,1封信提到“毛泽东的《认识论》”,反复引用毛泽东的观点来讨论如何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以及建立相关的科学理论的问题。
钱学森如何评价《实践论》对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的指导作用呢?这可以从他的下述言论中清晰而准确地看出来:
“我想,从定性到定量实际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3]404(1990);
“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建筑在《实践论》的基础之上的”[3]421(1991);
“我们之所以能搞出metasynthesis(也指出metanalysis之不足)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矛盾论》”[5]217(1991)(前后两个英文词分别是综合集成和跨域分析);
“近日来我在读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有些感受”[2]420。谈了两点感受,一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实践论》的具体化”,二是“要完善提高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要引用《矛盾论》”(1991)(同上);
他在评价圣菲学派的工作时说:“当然,美国人没有毛泽东的《认识论》!”[3]450(1993)。
钱学森对毛泽东认识论是何等的欣赏、尊重、信任,在这些言论中可谓溢于言表,无须更多地引用了。那么,在关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研究中,钱学森从《实践论》中究竟得到哪些启示和指导呢?笔者认为至少体现于以下几点:
1.传统的科学推理方法把科学认识的获得基本上归结于逻辑思维,不提实践在认识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践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第一性观点,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来揭示认识运动的特点、机制、规律。对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钱学森完全坚持这一哲学认识论立场。他列举了五条“集成法和研讨厅的理论根据”,第一条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认识源于人的实践,先有感性认识,然后加工综合上升到理性认识”[5]230。在现代科学至今尚未建立起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的情况下,如何研究这类对象,建立相应的科学理论呢?钱学森首先从认识论上寻找出路,指出“人认识问题只能从具体事例入手,而从解决一个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开始”,“每一个问题都要根据实践经验,通过具体工作,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方法来入手”;将来问题解决得好,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认识,再进行论理概括。他还特别指明:这一套认识“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嘛!”[3]538。
2.传统的科学推理方法不讲认识活动的过程性,仿佛科学新认识的形成是一蹴而就的。传统的科学推理方法是静态的,不讲认识的动态性。关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钱学森最初讲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1989),没有体现出认识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在这一点上跟传统方法无异。《实践论》则把认识活动当作过程,有方向性,有起点和终点,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之间有衔接转换问题,因而是一个动态的运动演变过程。钱学森于1990年代初期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改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指明应用综合集成法解决问题过程中认识活动的起点、终点、方向性,“实际是综合集成定性认识达到整体定量认识的方法”[3]400,这就跟《实践论》一致了。钱学森很看重关于综合集成方法论提法上的这一改变,视之为学习毛泽东认识论的成果之一。
3.传统的科学推理方法把认识看成一种线性系统,没有飞跃,没有质变,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以至于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都是线性的积累。《实践论》则把认识活动视为一种非线性动态系统,不仅有量变、还有质变,不仅有连续变化、还有飞跃(间断),首先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然后是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飞跃,认识的两次飞跃论是《实践论》最精彩的核心内容。钱学森在自觉运用《实践论》指导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的过程中,着力最多的也是如何把两次飞跃具体化,特别是第一次飞跃,即如何从关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局部定性认识(专家经验、统计资料和数据、其它点滴知识等)上升到对系统整体的定量认识。所谓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就是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设计出来的,既是一个方法论命题,也是一个认识论命题。
4.传统科学推理方法的线性观还表现为看不到认识运动中的循环往复,不考虑理性认识还需要回到实践接受检验。在这方面,钱学森不仅秉承《实践论》,而且还引用陈云“变换、比较、反复”的说法,强调应用综合集成法解决问题时,认识运动具有反复性和曲折性,并把这一认识具体体现在关于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操作程序的设计中。对于一项具体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任务,认识运动的循环往复是有限的,所谓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要求反复到所有专家对数学模型不再有意见为止,即把他们的经验和判断都综合集成起来了。对于人类认识运动的总体来说,钱学森坚持毛泽东“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说法,他曾经借评论老子的一个命题来论证这一点,并对天人合一观作出独特的阐释[5]237。
在时下的中国学术界中,避免提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似乎是与时俱进之举。但钱学森逆潮流而动,宣称“我们的优势在于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原则,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开路。对我们搞这样的复杂巨系统工作,这尤其重要!”[4]233对于一切把“我们的优势”丢弃的做法,他感到很痛心,并以自己的言行努力抗拒之。
三、研究思维科学也需要《实践论》的指导
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钱学森把认识论作为思维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学科。《关于思维科学》一书是以80年代前期的研究成果汇集而成的,其中并未提及从认识论高度考察思维科学研究,没有提到《实践论》对思维研究的指导作用。有了上面的分析,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因为那时的钱学森尚未建立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把思维运动仅仅看成巨系统;尚未把复杂性当成一个科学概念,思想深处相信有了巨系统概念,运用传统的科学推理方法,足以解决思维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无须作认识论上的考察,用不着《实践论》。广而言之,那个时期的钱学森相信地理、生命、人体、思维、经济、社会等系统都可以如此对待。应该说,这实际上是科学界的共识。
一旦形成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确立起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方法论原则,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也立即发生相应的转变,明白了思维科学研究也不能仅仅使用科学推理方法。在探索新的科学方法论的同时,必须从认识论上审视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自觉运用毛泽东的《实践论》。事实上,第一节提到的有关《实践论》的15封信大部分都涉及思维研究。钱学森对《实践论》在思维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的评价,从以下引用的几段话中看得很清楚。
1.当判明思维运动属于开放复杂巨系统之后,钱学森明确指出:“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怎么能搞思维科学的工作?”针对某些一时还讲不清楚的问题,如“区别定性和感性认识与模糊”的问题,钱学森告诫他的学生和合作者:“恐怕要再仔细读读毛泽东的《实践论》”[5]212(1991)。
2.当谈到W.Clancey有关思维运动的观点时,钱学森在肯定Clancey强调智能体(实即人脑·实践)的作用的同时,指出“他似又坠入经验主义哲学,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再次强调“我们要搞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科学”[5]241(1996)。
3.在拜读某些学者的有关作品后,钱学森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似乎没有从思维创造上讲清社会思维的意义。人是怎么认识客观事物的?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讲得最清楚:是一个辩证综合过程。”[5]245(1996)
那么,钱学森的思维科学研究从《实践论》中究竟得到哪些启示和指导呢?他如何应用《实践论》阐释思维运动的特征、机制、规律呢?由于钱学森的有关论述既精深新颖,又比较零散,而笔者对思维科学未作专门研究,自觉对这些零金碎玉并未吃透,难以给出系统而深入的回答。这里拟谈以下几点,以就教于行家里手:
1.灵感思维与实践。灵感思维一向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钱学森则坚持以唯物论来“解释灵感的来源,来源于社会实践”[5]232。他还从另一角度考察灵感与实践经验的关系,试图揭示灵感出现的机理,指出“醒梦”“才是灵感思维的来源,即人的大脑处于局部工作状态,在醒觉时思维受全部知识经验影响,思想不解放,出不了灵感。”[5]206
2.社会思维与实践。钱学森认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工程“就是以人-机结合的方法搞社会思维。由此实践再上升为理论,即社会思维学”[5]209。
3.形象思维与实践。在各种思维形式中,钱学森思考最多的是形象思维,新见迭出,此处只能列举几点。(a)“研究形象思维要靠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辅以中国古代哲学之精华。”[5]237(b)“形象思维过程实是与人的实践经验有关的,还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人的实践经验积沉于人的大脑,把某一形象(心象)与其将产生的结果作为规律,一旦人在以后某时某刻又得以形象(心象),则‘归纳’为规律所决定的结果,即概念。我自己反思,我们的形象思维就是这么回事!”“专家系统的基础看来也是形象(心象)的‘归纳’,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5]214(c)“我想形象思维实是:对要处理的问题有了一个感性认识,但仍是一堆乱麻,理不出头绪。这时如在大脑中在积存的事物形象去搜索对证,一旦‘对上号’了,就恍然大悟。此即形象(直感)思维之真谛。”[5]220
4.创造性思维与实践。关于思维形式的分类,钱学森后来不再提灵感思维和社会思维,代之以创造性思维,并断言创造性思维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综合统一,申明“我们就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思维学中的几种思维统一起来了”[3]436。他反复强调创造性工作不能只运用逻辑思维,重要的是形象思维。“对一时还没有搞清的问题,只有零碎概念,那抽象(逻辑)思维是无法下手的。这时要根据《实践论》,把感性认识的点点滴滴用一个软件把它‘缝’起来,……这个方法是每一步都离不开实践经验的‘形象’的,因此称形象(直感)思维。”[3]436他还指出:“A.Einstein早就说过,不能只靠抽象(逻辑)思维,还必须用形象(直感)思维,毛泽东同志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也是这个意思。美国圣菲(Santa Fe)学派就说得更多些。”[5]224。为揭示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机理,钱学森吸收了一个新概念,即“泛化”或“泛化思维”,提出一些别具韵味的见解。如说:“‘泛化’是大成智慧的组成部分。‘泛化’是大跨度的跳跃,不是‘嵌入’。”[5]238又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既讲实践,又讲‘泛化’,而且知道‘泛化’只是一个启发猜想,尚待科学验证。但‘泛化’的猜想是重要的,人是metasynthesis!”[5]237
5.逻辑思维与实践。一般来说,实践经验指未经逻辑加工的知识信息,逻辑思维是在高于实践经验的层次上作信息加工的,似乎与实践没有直接关系。但钱学森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一,逻辑推理的前提是非逻辑思维的猜想、直感的产物,而猜想和直感与实践经验难分难解,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就没有产生猜想和直感的实在基础。钱学森曾分别引用爱因斯坦、冯·卡门、盖尔曼的说法和他自己的经验来论证这一点。其二,信息高新技术的发展“将导致人-机结合的感受”[5]241,“发展了人-机结合的逻辑思维”[5]239,这样的逻辑思维跟这样的实践感受密不可分。其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感性认识的规律要嵌入理论体系”,欲走好这一步,“重在找路子,所以泛化就很有用了”[5]238,而这种泛化同样离不开实践经验。
应当说,钱学森的上述观点有许多属于一家之言,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他注意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意象概念,试图从认识论上考察意与象的关系,揭示其特定的含义。他认为,“意”是理性认识,“象”是感性认识,并断言“这是注入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思想”[5]222。揭示从意到象的演变为综合集成过程,确是一个新创见。但笔者认为,“意象”中的象并非感性认识,感性认识阶段的象是表象或印象,“意象”中的象则是意识化或意念化了的表象,已属于理性认识。但即使如此,他的说法至少提出了新问题,提供了考察思维现象的新角度,颇有学术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钱学森的这些零金碎玉式的论述,中国思维科学界至今未给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
四、在复杂性研究中丰富实践论
《实践论》有一句话很受钱学森赏识,他不止一次引用过。仿造其结构和语势,我们可以说:《实践论》并没有结束对认识论的探索,而是开辟了认识论发展的新道路。如何评价《实践论》对认识论的贡献呢?借用科学家的语言讲,笔者认为《实践论》给出的是关于认识之辩证运动的一级近似,从而开辟了给出二级近似的道路。用钱学森的说法,就是要把《实践论》具体化。钱学森的复杂性研究不仅以《实践论》为指导,而且在深化和发展《实践论》方面有许多独到的体会。
钱学森区分了实践感知和感性认识,认为思维是人脑接受实践感受后的结果,“从实践感知到感性认识是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感性认识的规律要嵌入理论体系。这一步要选出可以嵌入的已知理论体系,如果都不合适,那就要修改已有的理论体系了。”[5]238把嵌入和泛化作为一对矛盾概念,这是钱学森的首创,可能具有认识论意义,需要深入研究。
更有价值的贡献可能是关于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的论述。哲学认识论只讲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对范畴,不讲定性认识和定量认识。钱学森把后者引入认识论,论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以及相互转化,这是他对认识论的一个独到贡献。对于这一点,笔者有专文阐释[6],此处不再论及。
从知行统一的基本观点出发,《实践论》断言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中第二次飞跃更为重要。如果单就科学和学术研究来看,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认识活动的成败得失在此一举。作为一级近似,《实践论》没有详细探讨这个飞跃的机理、规律、原理,但给出一个简洁而重要的表述,即对感性材料的“改造制作”。流行的哲学认识论著作很少关注第一次飞跃的机理、规律、原理问题,没有深刻领会“改造制作”四个字的重大含义。钱学森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认识论的生长点,并且注意到毛泽东1957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不好就要犯错误。”[3]493钱学森由此引申说:“我想‘要制作得好’就是在‘微观’层次的处理之上,还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大道理的宏观调控。”(同上)20多年来,钱学森花很大力气研究思维科学,从不同角度讨论灵感、直觉、泛化、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等等,目的之一就是从思维科学上揭示人脑对感性材料进行“改造制作”的机理、规律、原理,并获得虽然初步但相当丰富的成果。当然,他的工作还属于思维科学层次,但对于从哲学认识论层次上揭示“改造制作”的机理、规律、原理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和新思路,有待哲学家提炼。
(注:《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中《关于观念和方法问题》一文下注的日期可能有误。按笔者的笔记,1987年12月29日,系统学大讨论班由王寿云讲《建立作战模拟的经验性理论基础》,钱翁发言跟此文对不上号。据内容来看,使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应该在1989年以后,1987年尚无此概念,1988年席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反映钱翁最新观点的《社会系统的研究方法》一文也没有这个概念。笔者猜想,此文或许是钱老1989年在小讨论班上的讲话。)
标签:钱学森论文; 实践论论文; 科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思维科学论文; 复杂性科学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定性研究论文; 矛盾论论文; 感性认识论文; 系统科学论文; 系统论论文; 推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