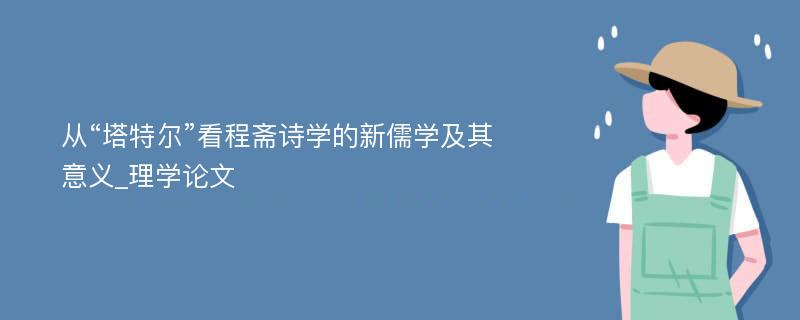
从“透脱”看诚斋诗学的理学义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理学论文,透脱论文,看诚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万里在南宋诗坛上卓然自成一家,开创了所谓的“诚斋体”。论者一般仅从诗学角度对之分析论列,未尝注意到他与理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当然,也有研究者已触及此点,但未作深入探究,故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此作一探讨,以求得对杨万里诗学及“诚斋体”的进一步把握。
其实早在杨万里生时及其身后,其诗风特色与理学境界的联系已为人所提及。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器》提到诚斋的《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即称:“张紫岩(张浚)见之曰:‘廷秀(杨万里字)胸襟透脱矣。’”(甲编卷四)张浚是从理学家的角度来欣赏这首诗的,他从诗的意境中看出了诗人的人格境界,故发为此论。而这一论断也启发我们去进一步探究杨万里的诗境与理学的亲缘关系。
诚斋的理学渊源
探讨这一关系,当从杨万里与理学的渊源入手。万里幼受庭训,得父亲杨芾之启蒙,立志向学,后又转益多师,其中以王庭珪对他的影响为大。这一为学经历培养了他向慕圣贤、持节耿介的人品。绍兴二十四年(1154)登进士第后,调永州零陵县丞,时张浚因主战而谪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求见而未果,后“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浚入相,荐之朝”(《宋史》本传),从此他与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服膺终身。又据《鹤林玉露》载,万里之得见张浚,乃经浚之子栻的介绍,得见后,“因跪请教,公(浚)曰:‘元符贵人,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至(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诚斋得此语,终身厉清直之操”(甲编卷一)。张栻也是一位理学家,与万里也深相契合,乾道六年(1170)张栻上书孝宗,论任用外戚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不当,被外放出知袁州,万里抗疏留栻,并致书左相虞允文规正其失,为公论所许。万里在理学思想上也颇得张栻之惠,栻辞世后为之作传、祭悼,赞为“名世之学,王佐之才”(《张钦夫画像赞》,《诚斋集》卷九八)①。
考理学之传,由二程的洛学至朱熹的闽学,其间的过渡桥梁为胡宏、张栻的湖湘之学。洛学之南传由程门弟子杨时(龟山)、谢良佐(上蔡)等人始。谢良佐较多地继承了程颢的思想,在知应城县任上与胡安国相识,安国向良佐问学,是为洛学南传湖湘之桥梁。安国还与程门之游酢、杨时等有密切交往,绍兴年间安国去官归隐于衡山,著书讲学,由此而创湖湘学派。这一学派是以胡氏学人为主体的一个学术群体,其中以安国季子胡宏的成就为冠,世称五峰先生,其代表作为《知言》,全祖望评曰:“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胡宏对理学的核心命题“性与天道”有开拓性的阐发,从而奠定了湖湘之学的理论体系。继五峰而卓然树立的张栻,他从学胡宏于碧泉书堂,使湖湘学统承传不坠。其后湖湘之学虽延绵至宋末,但其主导地位却渐由闽学所取代。后一统系则由杨时开启。杨时南归时,程颢目送道:“吾道南矣。”杨时复从程颐学,与游酢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由龟山杨时而豫章罗从彦,而延平李侗,延平传至朱熹,遂成就一代闽学之盛。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学统在张栻与朱熹之前在性理之学方面多有声气相通之处,至朱熹则有所修正,并影响到张栻,二人虽标榜其学统各有所自,但与前辈异趣者也不在少数。考察杨万里的思想特色以及其诗学与理学之关系,当从理学南传这一大背景着眼,寻绎出其间的传承同异的内在联系。
“兴”:诚斋诗学的理学底蕴
杨万里诗学以善变为其特色,经过持续不断的探索,终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诚斋体”。诚斋诗学中首先值得我们探讨的是他对“兴”的重视,他从传统诗教中拈出“兴”来表述其诗歌发生论,并推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焉?天也,斯之为兴。(《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卷六七)
诚斋标举此境为“天”,即诗人触物生感,不能已于言而必形诸诗的天然化生,以相对于“赋”与“赓和”的人为造作,故称后二者“人而已矣”。诚斋在自述其学诗经历时曾描述其屏弃模拟而达于独造后的状态:“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诚斋荆溪集序》,卷八○)这种状态正是诚斋所云“兴”的化境。
诚斋所述之“兴”正是理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表现。理学的核心命题是其天理论,天理作为形而上的终极存在为儒家的价值体系提供了本体论的支点,其理论渊源则是《周易》(包括《易传》)及《礼记》中的《中庸》,二者将心性论与宇宙论贯通,从而使道德伦理获得了形而上的品格。
儒家自孔子以来,一直在探索一条道德的主体自觉之路,由孔子之“仁”至孟子之“性善”就昭示了这一求索轨迹,至北宋濂洛诸子方结出“天理”之果。理和天、道、心、性被完全打通,“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命犹天道也”(《伊川先生语》,《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②卷二一下)。这些范畴共同指向了那个形而上的本体。而这一本体与形而下之范畴原本合而不二,即理气、道器、体用本为一体,正如程颐所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河南程氏文集》③卷八)只是由于情识气质的干扰才导致离析歧异,故必须通过修身养性使之复归为一,是即“天人合一”。据理学家们的描述,这是一种超越了刻意造作的自然无为,主体进入了绝对自由的行动天地。
这一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至《中庸》则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程颢极推许这一境界,其说集中表述于《定性书》中:“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以有为为应迹”,“以明觉为自然”,“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文集》卷二)。显然,其旨趣颇近于庄禅之逍遥任运。伊川的思想风范虽与明道有间,但在追求这一境界上与明道实无二致。伊川称“不动心”有两个层阶:“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后者乃是以外在的道德规范制心的结果,而前者的“造道”则是自我作古:“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遗书》卷二一下)
此种自由化境的获得缘于人屏弃了“私欲”“人情”之后与“大化流行”的天道的冥合。据《中庸》所论,天道“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故伊川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遗书》卷一八)。主体合于天道,也就获得了它的这一品性,入于自由而无碍:“圣人之神,与天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遗书》卷二)。这种自由又与自我作古相关联:“得而后动与虑而后动异。得在己,如自使手举物,无不以。”(同上。)“大而化之”,只是理与己一。……至若化者,则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遗书》卷一五)二程揭出天道之核心为“仁”,故天人合一之关键在识仁,如明道所云:“学者先须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遗书》卷二上)人与大化流行相合,言动举止也就皆合自然了。
为深入理解此“天人合一”之境,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分梳辨析。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是将心性与天道贯通的第一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至《中庸》则其义更为明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易传》更上升至宇宙论的高度来阐发心性。儒学经过这样的拓展,遂能经由天道这一关节点通向老庄,乃至在后来与佛禅相沟通。如前所述,儒家的这一求索,目的在于找到一条融合道德与自然的途径,使道德实践由理的外铄转为心的自发,冯友兰曾将两者分别称为“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笔者经多年的沉潜思索,认识到二者之合始终是貌合神离的,因为二者的致思进路各异,不同的思想逻辑难以妙合无间。
当我们追问形而上之道是什么时,理学内在的悖论就显现出来了。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从宇宙论的角度将本体概括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图说》)。其说源出《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关于无极与太极的关系,理学中人有过不少的争论,但从文本本身来解读,则“而”字显然有先后承续之意味,然则“无极”应是高于“太极”的范畴。如果说“一”是太极,则“无”当为道,它是超越一切存有、对待的本体,《庄子》中曾以“浑沌”的隐喻名之。所谓“天人合一”即是向这一本体的复归,如《老子》所云:“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二十八章)此一本体后来还通于佛性真如,故僧肇云:“以知涅槃之道,存乎妙契,妙契之致,本乎冥一,然则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涅槃无名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但周敦颐又将此本体释为“诚”,至二程又将之推向了“仁”,于是形而上之体愈益向形而下之器坠落,由仁而礼、智、信,乃至君臣父子、三纲五常,都被纳入了道、理的范畴。须知这些德目是与具体的理则联系在一起的。二程称“天理”二字是他们体贴出来的,此中实逗漏出他们的良苦用意。如果说“天”所表征的是本体的话,那么“理”自然地会将人的思路引向伦理规范的理则,由此而导引出二程在体道方面的微妙差异。
《中庸》曾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自二程揭橥其理以来,理学家们围绕它进行的争辩,历久靡衰。《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实通于道家之“无”,它是本体在人身上的内化,作为本体,它就是庄子所云“物之初”(《庄子·田子方》),即世界起始的那个“无”。理学家名之为“性”,内化为人性则为“中”,后来禅宗赋予它以佛性论的意义,所指更为显豁,即“父母未生时”的“本来面目”(《古尊宿语录》卷二九载清远语录),是相对意识生起前的本心、真我,它对应于宇宙起始前的混沌未分,那么如何体认此本体、本心呢?庄子提出当超越一般的认知而实行“心斋”,所谓“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庄子·庚桑楚》)。正如当代学人所指出的:“在知性体验破产之处,恰是‘道体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李孺义《“无”的意义》第五章,第75页);“形而上学乃是知解理性的极限”(同上第三章,第56页)。禅宗变换各种花样所要达致的也正是这种对执着于“常知”的破除,禅家谓之“截断众流”。反观理论家之论,则缺乏庄禅在逻辑上的这种一贯性,而是陷入了某种悖论,即既主得道的自然之境,又倡思虑积学的修养之途,走的是认知之路。程颐反复申述达致中和的途径是学和思:“君子之学,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遗书》卷二五)。伊川强调的是通过学与思达于体道,相比之下,明道则较重直觉体悟,因而更偏向于冲融淡远、潇洒逸如的人生境界,与庄禅更多契合,同伊川之庄敬严毅则有间。二程之间的这种同异在其后的理学家中间导致了不同的学术和人格风范。如果要追溯“诚斋体”的理学之源,当于此中去寻绎。
二程之后,理学家多有出入佛老者,他们往往借打坐、静修的方式来体悟“未发”之“中”。如龟山尝从常总禅师问道,常总谓:“本然之性,不与恶对。”(《朱子语类》卷一○一)按佛家将善分为有漏善与无漏善,前者为区分善恶之善,后者不以善恶论,乃不著相之善,龟山承常总之论,亦以善恶相对前之本体为性。龟山之道传罗从彦,再传李延平,其禅味愈来愈浓厚,黄宗羲云:“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宋元学案》卷三九《豫章学案》案语)
但是,静只是体道的—个方面,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动的一面。按动静之合原本是理学家据《易传》、《中庸》而引出的通识共则。周敦颐谓:“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通书·圣》);“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动静》)。二程教人不能陷于枯木死灰,当于动静语默间参悟。朱熹为纠偏静之失,提出“静以直内,义以方外”(《宋元学案》卷三九《豫章学案》黄宗羲案语引)。然则,体道之途当是动静内外的结合,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回环互动的进程,人持本寂之心投身世事,以心体之“定”应对物事之“变”,复从万物之变动不居中体认本体之寂然不动,促进对心体的持守。
杨万里作为服膺理学的诗人,其思想受二程以来理学诸子的影响,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思想除散见于诗文作品外,还集中表述于一些专论中,《庸言》及《诚斋易传》就是其代表性述作。如同其他理学家一样,诚斋亦重“已发”“未发”之论,如《庸言》卷一二释“中”与“和”曰:“不观之天地乎?阳气潜萌、万物归根之谓中,分至启闲、序则不愆之谓和。观吾心见天地,观天地见吾心。”(《诚斋集》卷九二)据此,则诚斋乃将物、我、心、性都加以贯通,观心与观天地形成一互动的过程。诚斋还据《易》理勾画出一幅天地万物化生变易的图景:“太极,气之元;天地,气之辨;阴阳,气之妙;五行,气之显。元故无象,辨则有象;妙故无物,显则有物。人者,气之秀也;性者,人之太极也;心者,人之天地也;动静者,人之阴阳也;喜怒哀乐者,人之五行也。”(同上)诚斋在此指出,通过观“象”之“辨”、“物”之“显”乃可达于对本体的把握,同时与主体相契合而了悟其心性。诚斋还点出:“人者,天地之心也。君子者,天地之心之师也。有天地而无人,无天地也。有人而无君子之学,有天地而无心也。”(同上)这种“心主万物”的观点来自张栻,它表明天地万物因人的存在、人心的映照才有意义,它是价值的载体、心性的表征而非认知的对象,因而诚斋之观物实为明心见性之手段,心与物是一体贯通的。
诚斋诗学所主之“兴”就是这种通过“观物”、“观化”而达致的心物交融,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是对人与世界的原初本然状态的复归。有当代学者曾以现象学的还原来阐释它,如彭锋在《诗可以兴》中称“对原初形式的追求构成人的生存的内在目的和动力”(第十一章,第356页),审美活动就具有这样的功能,而“在中国美学中……审美作为向人的本然的生存状态的还原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同上,第368页)。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是物我交融的体验,主体通过直觉观照(庄子称“心斋”,佛家谓“般若”)直面客体的大千世界,领悟到它与主体生命的契合,引起内心愉悦感奋之类的种种体验,这就是兴的状态。具体而言,主体从万物之动体认到本体之寂,无论山河大地、草木虫鱼,抑或人事周旋、洒扫劳作,主体都可由之悟道而通向那原初之无,复从本体了悟心性,感受到与万物浑然一体的仁者情怀,主体与大化同生共运,心灵获致解脱而臻自由无碍之境,这既是一种洒脱的人格境界,更是一种快意的审美体验。
诚斋诗学以“兴”为最高境界,其哲理的底蕴即如上述。诚斋的特色在于将“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化为以“兴”为标的的诗歌创作境界,理学家讲体认天道,固然与审美活动相通,但其心性修养是多元的,并不限此一途,他们还讲格物致知,将天道落实为仁义礼智之类的理则,如此则对天道之悟下落为积学思虑,更多地成为认知活动,与审美就拉开了距离,更不要说将审美转化为文学艺术了。如程颐就对为文从艺持否定态度,指出“为文害道”、“玩物丧志”,甚至指杜诗中的句子为“闲言语”。伊川曾云:“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遗书》卷二五)伊川在此将内外截然对立起来,而将为文从艺视为驰心外骛,不免胶柱鼓瑟,也有悖于理学宗旨。而诚斋则大大发扬了外向悟道的一面,所谓“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将朗朗乾坤的万千气象尽收笔底,成就了一代诗人的业绩。这种境界实渊源于他的理学修养。
由“生”而“乐”:诚斋诗学的理学境界
诚斋笔下的诗世界是一个生机活跃、万象氤氲的大千世界,“诚斋体”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活”。这一特色也可从理学思想中找到其源头活水。
中国传统思想走着一条三教合一之路,虽殊途而同归,却同中有异处。在体道悟性方面也表现出这样的特色。儒家早就有从客体中悟道之说,但客观事物多为道德的喻体,他们往往是从“比德”的视角去观山观水的。庄子将大自然的运行变化称为“物化”(《庄子·齐物论》),从中悟道则为“观化”(《庄子·至乐》)。禅宗将观物悟道更推衍至花样翻新,乃至篇咏迭出,演化成禅诗的一大景观。唐代宗密称:“心境互依,空而似有故也。且心不孤起,托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现。心空即境谢,境灭即心空。未有无境之心,曾无无心之境。”(《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故在禅家眼中,“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草木国土,皆能成佛”,“山河大地,悉现法身”。尽管禅家触目所见也是风光无限,生机跃然,但他们由“色空不二”所悟出的是妙有中的真空,是归于解脱的涅槃,此即见色明空,循相证性。相比于禅家之空、道家之无,理学家们由客体万象所悟到的是本体之诚或仁,本体带有更多的道德色彩,其表征为“生”,即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诚斋体的特色。
“生”作为儒家哲学的基本内涵,也是理学家所着力阐扬的一个观念。此说最早由《易传》揭出:“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此一义理经宋儒的彰显,遂成为理学家论道的理论基石。宋儒大力发明“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的观念,如欧阳修提出了“天地以生物为心”(《易童子问》卷一,《欧阳文忠公集》卷七六)的命题,张载也称:“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横渠易说·上经·复》)因此理学家们在观物中多着意于自然界的生命意趣,如程颐提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遗书》卷三)张九成述及此事时谓其不愿除草乃“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横浦心传录》)
“生”和“仁”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天地之道既然为生,也就是对生命的成全,这是最大的仁。程颢云:“‘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遗书》卷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与仁是一体贯通的,故程颢又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遗书》卷一一)明道在理学家中素以宽厚豁达的仁者风范见称,其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即以仁者之心体万物之仁,天人之际只是一个生生之理。在理学家那里,体道识仁每每表现为对生命与自然的礼赞与欣赏。天道之“生”由此而化为道德境界之“仁”,进而转化为审美境界之“乐”。美学家宗白华就曾指出,宇宙本身蕴含生命的律动,这种生命节奏与人的心灵节律是同构的,故主体在直觉观照中去体悟这种节律运动,即能进入一种审美境界。它既是对道的体认,又是对美的感悟。艺术就是天人互动交感的产物。叶嘉莹也提出,人心与外物的生命共感乃是审美与艺术的基础,她指出“在宇宙间,冥冥中常似有一‘大生命’之存在”,举凡“鸟鸣、花放、草长、莺飞”或“云行、水流、露凝、霜陨”,莫不是生命的表现,“我”与“物”之中均有此生命的存在,“因此,我们常可自此纷纭歧异的‘物’之中,获致一种生命的共感”(《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迦陵论诗丛稿》)。这就是诚斋所标举的“兴”,它是诗乃至一切艺术之源。
如果说,在诚斋之前,理学家也偶尔涉笔成趣,以诗歌来表述此一境界的话,那么至诚斋,则将这一境界化为一蔚为大观的诗歌天地。一部《诚斋集》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囊括天地万象的诗世界。大至山水风云,小至花草虫鱼,还有芸芸众生的事态物象,都被诗人摄入笔下,展现出活跃的生机,其诗歌主题主要表现为游心于山水风月、徜徉于天地人寰的种种意兴和情趣,带有随机生发、触目成趣的特色。钱锺书先生称“诚斋善写生”时描述其诗“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谈艺录》第118页)。最能体现诚斋体特色的是其七绝,诗人捕捉住某个瞬间场景,简笔勾勒,顿成妙谛。由于他冥搜万象,触处生春,因而姜夔在致诚斋的赠诗中称:“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白石道人诗集》卷下)
正因为诗人与万物发生一种生命的共感,故诗人是以宾友万象的态度去观照、体验世界的,世界在他的眼里并非是一个冷漠的客体,而是活泼泼的生灵,他能与之产生情感的交流、心灵的默契。所以诚斋诗中多以拟人笔法去模写物象,赋予万物以生命和灵性。这就是诚斋体诗的魅力所在。现录数诗,以窥豹一斑:
诸峰知我厌泥行,卷尽痴云放嫩晴。
不分竹梢含露雨,时将残点滴寒声。(《宿小沙溪》,卷八,《荆溪集》)
画舫鸣钲野寺钟,暮声惊破翠烟重。
好风不解藏天巧,雕碎孤云作数峰。(《雨后晚步郡圃》,卷九,《荆溪集》)
天欲游人不踏尘,一年一换翠茸茵。
东风犹自嫌萧索,更遣飞花绣好春。(《春草》,卷一二,《荆溪集》)
雨罢风回花柳晴,忽然数点打窗声。
游蜂误入船窗里,飞来飞去总是情。(《舟过望亭》,卷一三,《西归集》)
蝴蝶新生未解飞,须拳粉湿睡花枝。
后来借得风光力,不记如痴似醉时。(《道傍小憩观物化》,卷一三,《西归集》)
此类例子在《诚斋集》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中散发出的生命意趣构成了诚斋体的一大特色。这种生命意趣又通向了“乐”的终极境界。
如前所述,人通过审美活动达致一种原初体验,即对宇宙本体的领悟和向人性本原的复归。当代学人彭锋指出:“乐是审美还原的剩余者。但这种乐不同于一般的乐,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称之为‘无利害的快感’,我们称之为无所原由的愉悦。这种无所原由的快感是主体在彻底还原之后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因而是人生在世的基本情感。”(《诗可以兴》第十二章,第375页)主体在回归原初状态之后,摆脱了一切系缚,进入了洒脱自在、逍遥任运之境,精神升华至与天道性体合一的浑融状态,不再有烦恼忧患而一任其进退行止。庄子称此为“逍遥游”,是“至乐”、“天乐”,即“游心于物之初”而“得是至美至乐”(《庄子·田子方》)。禅家称此为“禅悦”。儒家同样以此至乐之境为鹄的,孔子最欣赏的是颜回,称许他虽处穷困而“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同上)云云。孟子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儒家之倡“乐感文化”最初来源于其“乐教”,《礼记·乐记》称“乐由中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后遂为理学家推阐为“天人合一”的终极境界,为他们所大力弘扬,津津乐道。
理学家所追求的乐境虽与庄禅同一归趣,是复归性之原初的结果,但佛、道、儒三家所拟议的“性”各具内涵特质,儒家所努力还原的性体是仁、诚,故更具道德伦理色彩。仁者与物同体,主体融入了天地宇宙的大化流行,一切循天理而动,自由无碍,触目是生机盎然的景象,主体感受到摆脱尘俗系绊、获致精神满足的愉悦体验,理学家即以“乐”字概之。北宋诸子中,邵雍对这种乐境曾不遗余力地予以阐扬,名其居处曰“安乐窝”,并将这种精神人格发为篇咏。二程中大程子对此境尤心向往之,他从学于周敦颐之后每教人“寻孔颜乐处”,且云:“某自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遗书》卷三)明道的《偶成》诗表述的正是这一境界:“云淡风清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文集》卷三)邵雍应是理学家中致力于吟咏的诗人,其诗多为吟风弄月之什,诗中表现的正是由“以物观物”而达于“天人合一”的逍遥之乐。
杨万里之诗遥承邵雍、程颢等人的人格风范和思想传统,在发掘生活的乐趣方面又大大地有所拓展。从广义上说,上文所述诚斋体的那种生机活泼的诗境,就是理学家所标举的“乐”。与此相联系的则是诚斋诗中那种诙谐幽默的风趣,这一特点尤为诚斋体所独具。诗人以豁达的心胸直面人生,放眼天地,自然会感到天趣洋溢,无处不有赏心乐事。试举几例以观:
上巳春阴政未开,寒窗愁坐冷于灰。
冻蝇触纸飞还落,仰面翻身起不来。(《上巳》,卷九,《荆溪集》)
稚子相看只笑渠,老夫亦复小卢胡。
一鸦飞立钩栏角,子细看来还有须。(《鸦》,卷一一,《荆溪集》)
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
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稚子弄冰》,卷一一,《荆溪集》)
天随楸枰作稻畦,啼乌振鹭当枯棋。
不论胜负端何似,黑子终多白子稀。(《晚望》,卷一二,《荆溪集》)
野菊荒苔各铸钱,金黄铜绿各争妍。
天公支与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戏笔》,卷一四,《西归集》)
即此数例就可见诚斋诗之谐趣横生。诗人以敏锐的眼光从生活中捕捉诗料,一经入诗,便成妙谛,或天真烂漫,或诙谐成趣,甚至以诗自嘲,让人忍俊不禁。宜乎清人吕留良等要在《宋诗钞》中称“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这种诙谐映照出的正是诗人那“透脱”的胸襟。
余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与诚斋诗学
以上我们论述了诚斋诗学与理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诚斋诗学的理学底蕴。上述论析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梳理,这一领域还大有开掘的余地。理学作为兴起于宋代的一种新的儒学思潮,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对士大夫的心性立身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必然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惜乎前人对此的关注较少,理学家出于对文的偏见而鲜有谈艺论文,文人则沉潜艺事而不大留意心性。当然,此类问题也并非无人论及,在此我们可以举出南宋的罗大经,其所著笔记《鹤林玉露》中就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罗大经以《鹤林玉露》一书名世,但他本人却名不见经传,其生平事迹也少为人知,值得注意的是,他与杨万里及其后人有过交往。罗、杨同为吉州吉水人,罗在十多岁时曾随父拜谒过杨万里,亲闻万里诵其《月下传杯》诗(《鹤林玉露》乙编卷四)。该书对杨氏家人每有生动的记述,如“诚斋夫人”条即详叙其德行,还多次记载万里长子杨东山对罗大经施以教诲及罗父与杨东山唱酬事。罗显然比杨万里年幼两辈。由于罗、杨的这层关系,我们从该书的议论中可以获得深入理解杨万里的若干启示,当是不言而喻的。
《鹤林玉露》有别于其他宋人笔记的地方是其有关理学的论述。罗氏在众多的理学家中虽非突出之士,但他对理学的理解却能得其要领,多中肯精辟之论,尤其对理学与诗学关系的论析能发人深思,有醒人耳目之效,其于推阐诚斋诗学诚功不可没。
在论理学思想方面,罗氏在“无极太极”、“无思无为”、“活处观理”、“忧乐”、“观山水”诸条目中的议论都醒豁而切中肯綮。如其论“活处观理”引《诗》及孔孟之语,再引程颢“观我生,观其生”及“复见其天地之心”,谓“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乙编卷三)。再如论“观山水”曰:“大抵登山临水,足以触发道机,开豁心志,为益不少。”(丙编卷三)。又其论“忧乐”则云:“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古曰无闷,曰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石之乐。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望花随柳之乐。学道而至于乐,方是真有所得。大概于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丧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丙编卷二)上引议论都关涉理学的基本观念,肯节所在,一经罗氏点明,即凸显而出,它们与诗学问题也密切相关,笔者从中受启导良多,已见于上文的论述。
罗氏的贡献更在于揭示出诗学与理学关联的联结点在于人格境界。上引程颢语中已及于此点,在此更可引“春风花草”一条:
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什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乙编卷二)
所谓“玲珑活络”就是本文开头所引张浚语“透脱”,它是主体摆脱系缚、超越尘累之后与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以此心境观物,方能感悟万物适性、天地融和的一派生意,诗人才能写出如此活色生香的意境。因此“透脱”既是理学修养的鹄的,又是诗歌创作成功的关键。诚斋本人就曾说过:“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卷四,《江湖集》)诗人之胸次透脱,始有万象毕来、应接不暇的诗思,是之谓“兴”。而从诗歌接受的角度言,“兴”又被视为诗歌作品对读者精神人格的激发,读者通过诗篇去领悟创作者的人格境界,并受其熏陶感染。由二程至朱熹对此均有发挥。对兴的重视与理学家标举圣贤气象是一脉相承的。罗氏论诗突出人格的价值意义,以此将诗学与理学贯通,对我们把握诚斋诗学颇多启导,在中国诗学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有必要指出,诚斋诗学也存在先天的不足。由于一味强调诗之兴,而其内涵又主要关涉山水自然、闲情琐事,故诚斋诗的主题过于单一,风格流为率易滑俗;又由于过分耽于逸乐,对家国之忧难免有所轻忽(不是说没有忧患国事之作)。《鹤林玉露》中有一条记载是耐人寻味的:诚斋年未七十即行退休,过了十六年清闲日子,宁宗庆元初与朱熹同被召,朱熹出而诚斋“独不出。文公与公书云:‘更不能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思,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甲编卷四)朱熹出于对朋友的责善之道而说的这番话,让我们领略到诚斋诗学中的偏失,也逗漏出诚斋更多的是沿袭程颢以来的传统,而与承续程颐一路的朱熹之学疏离有间。
要之,“透脱”作为诚斋诗学的一个关键词,既涵括了其诗歌的由兴而生、乐的创作过程中的精神境界,又指诗歌接受中所感受到的诗人的主体人格,是我们把握诚斋诗学时所不可轻易放过的。
注释:
①以下引《诚斋集》仅注卷数。
②以下引此简称《遗书》。所引二程语均出自《二程集》,不再标出。
③以下简称《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