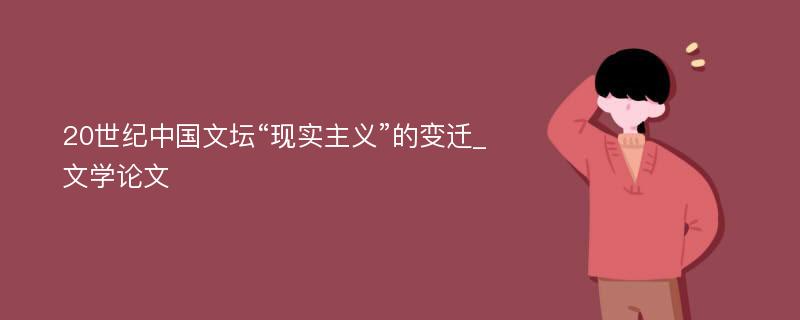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但人们对“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把握,其差异是令人吃惊的。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蕴藏着人们接受这一概念时所受到的主观选择的影响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折射着人们不同的文学趣味和审美标准。探寻造成这一差异的历史过程,有助于理清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发展的基本线索。
一、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来源
“现实主义”一词在中国文坛上的流行,是1933年之后的事。此前人们在表达“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时,通常用的是“写实主义”一词(注:陈鸣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一书,对历年所发表的创作及理论文章均有详细的目录索引,但查阅该书,早年人们所写的有关文学理论的评介文章中,并不见用“现实主义”一词。虽然不能因此绝对地说此前尚无“现实主义”这一术语, 但至少可以说是绝少使用。 1933年4月1日,静华(瞿秋白)在《现代》2卷6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介绍了马、恩有关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等论述。11月1日, 周扬在《现代》4卷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此后“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才流行开来。)。从总体而言,“文学革命”时期,人们在以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来作为新文学创建的重要一翼时,是以19世纪后期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为参照系的。陈独秀明确指出,欧洲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古典主义”进化到“理想主义”再到“写实主义”的过程,而“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注: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答张永言》,《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 年版,第16~17页。)在此,陈独秀是将“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来看待的。这一被陈独秀视为文学发展方向的“写实主义”趋近于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后者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创作特征:1.在创作的方式上,遵循写实手法、典型化方法及真实原则。2.在创作的内容上,注重社会阴暗面的题材选择和批判现实的主题立意。3.在创作的态度上,作家以人道主义作为评判生活的价值依据并持一种启蒙大众的精英心态。由于“文学革命”是为着引发“思想革命”,达到启蒙反封建的目的,因此“文学革命”时期人们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关注的不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而是其特殊的创作内容及创作态度。这在当时的批评和创作中都体现出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就是与“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相对立的,虽然提及“写实”的方式,但重在文学内容“新鲜立诚”的效果和境界。如若仅就写作的方式而言,“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采用的倒是写实手法,甚至也是照着真实写的,但“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之所以要批判它,原因在于那种男女恩怨的素材范围及其对青年的麻醉作用。李大钊认为此类作品“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注: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茅盾指出, 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思想上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谴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重印本,第386页。)。当年鲁迅、周作人等之所以注重译介东欧弱小国家的作家作品,则是因为这些作品关注且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鲁迅曾说,自己的创作全仰仗着过去所看的百十篇外国小说,又说,创作的目的是为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转引自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小说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从其注重揭露社会阴暗面及以个人主义、 人道主义为准的来批判封建礼教的创作实践看,鲁迅的创作在以外国小说作借鉴时,侧重的确是“批判现实主义”特殊的创作内容及创作态度。这样一种侧重,是由当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尤其是其创作内容及创作态度,成了这一时期人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判别什么是“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志。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隘化
“革命文学”的兴起,使得“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接受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人们译介引进了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年11月1日,周扬在《现代》4 卷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第一次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更明确的规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如果说“文学革命”时期人们是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以其所体现出来的创作特征作为参照来把握其精神实质的话,那么,“革命文学”时期人们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则是在引进一种“创作方法”的名义下,对文学创作提出特殊的社会性的要求。作为一种创作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注重的也就不是具体的创作手法及方式,而是创作的内容及创作的态度。其精神实质,较之先前的“批判现实主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批判现实主义”在创作的内容上是普泛性地关注“被侮辱与被迫害的”小人物,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具体化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尽管作家评判生活、启蒙大众的精英姿态并没有改变,但“批判现实主义”是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评判的准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以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这一历史的必然规律作为评判现实的依据,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过程中把握现实,以展现光明前景来鼓舞人民的斗志;虽然同样是关注劳动人民,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心已不是劳动人民值得同情与怜悯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状态,而是他们的觉悟、反抗及其“火热的斗争生活”。在此,“现实主义”已由一种文学形态,具体化为一种创作方法及要求,在内涵上呈现出“隘化”的特征。
这种发展态势,在中国30年代“左联”的创作要求及创作实践中充分地体现出来。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在有关决议中,就对创作的内容(写什么)及创作的态度(怎样写)都作了严格的限制:“第一,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1)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2)作家必须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3 )作家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第二,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注: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卷一》,第421页。)
“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质性的不同,在于前者所秉持的是一种民间的立场,而后者则是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扬即撰文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注: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载苏联《红旗》1952年第12期,1953年1月11 日《人民日报》转载。),中国文联也在决议中,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发展新中国文艺的基本准则。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又进一步地具体化,对写的内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创作不仅要展现无产阶级“火热的斗争生活”,而且要讴歌劳动人民建设新国家和新生活的丰功伟绩。对现实的描写,要同“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作家,必须肩负教育人民的使命。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有着内在的契合,因此,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对其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
三、“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转化
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了来自民间的非议,“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新的接受语境中发生了转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作家在发展中把握现实并展现光明前景来鼓舞人民,从而完成教育人民的任务。这就为作家在反映生活时过多地主观介入、以理想代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又常有紧密配合现实任务的匆忙,往往导致创作中的概念化和公式化。早在30年代,即有人颇为幽默地嘲笑了“左联”一些革命作品的这种弊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基本方针,其对文艺创作在内容、态度及方式上的带有政治要求的简单限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50年代后期,一些作家、理论家就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及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认为社会主义精神就活生生地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具体的真实。他提出应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刘绍棠也指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不是首先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于现实的生活真实,而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去反映和描写生活,同时这种描写又要结合着‘任务’,这就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既然当前的生活真实不算做是真实,而必须去发展地描写,结合着任务去描写,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饰生活和漠视生活的本来面目了。”(注:刘绍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
要求带着教育人民的任务去创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导致公式化和概念化,要克服这种偏向,秦兆阳、刘绍棠等人认为须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地写”。刘绍棠说:“我们几年来的文学创作,也使我们看到了教条主义的恶果,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生活内容的贫乏,艺术感染力的淡薄……这一切,归算起来,都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离开了现实主义古典大师的光辉传统……历史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来都是最真实最广阔地反映生活,从来都是深深关怀着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命运,从来都是用生活中所提供出来的问题教育人民的。他们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讴歌人民,但是他们也不避讳人民身上的缺点和不幸,他们全面地、深刻地描绘生活的真实,让人民如实地看见自己的遭遇和力量。”(注:刘绍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 )刘绍棠所说的“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及“现实主义古典大师的光辉传统”,指的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文学大师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及传统,可见在这一时期,这些人是在用“现实主义”来调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面“现实主义”大旗依然还是来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但应当注意的是,他们已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不同,注重的不是“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批判现实的态度,而是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原则。于此,人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就发生了由重创作内容和创作态度到向重创作方式的转化。李何林在提出他的“写真实”论时,将这一思想倾向表达得最为集中鲜明。他说:“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相一致的作品”,因为“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致的,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注:《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文艺报》1960年第1期。 )
四、“两结合”——“现实主义”的泛化
50年代后期,文学界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泛化。1958年,毛主席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1960年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两结合”取代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大会确定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最好的创作方法”。这一方法的提出,主要的目的在于为中国作家如何以文学为政治服务指出具体的途径。把“革命的理想主义”溶入写作中,自然就有利于作家“在发展中把握现实”,从而更好地展现光明前景来鼓舞教育人民。“两结合”的方法无疑是对写作态度的一种强调,唯其如此,一些权威阐释者才偏重于浪漫主义的作用方面来谈论“两结合”。周扬即说:“(“两结合”)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没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于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注: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理论家在阐释“两结合”时,泛化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接受理解过程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变更。周扬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注: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在从“全部文学历史”的高度来论证“两结合”时,当时的阐释文章大都受了高尔基观点的影响。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高尔基以为,“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成为当时人们论证“两结合”合理且必然的一个有力证据。在此基础上,郭沫若进一步发挥道:“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文艺活动的本质就是现实主义。但从文艺活动是形象思维,它是允许想象,并允许夸大的,真正的伟大作家,他必须根据现实的材料来加以综合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过程,你尽可以说它是虚构,因而文学活动的本质也应该是浪漫主义。”(注: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这就不是在文学形态和创作方法的层面上,而是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来考察“现实主义”,此前被视为文学形态或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于此也就被拔高为“文学活动的本质”。
这一泛化所引起的概念混乱,在建国后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几乎在所有的权威教科书中,都是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发展概括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几个历史阶段。诸“主义”在逻辑关系及地位上,是平等的。但在谈论“创作方法”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则又被从中拔高出来,成为贯穿古今中外文学史的两种基本的文学创作方式。教科书中的逻辑混乱表明,虽然“现实主义”已被上升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本质”,但其内涵特征,则又源自作为一种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这实质上是将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特殊的创作内容、创作态度及创作方式,当作贯穿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典范。
五、“现实主义重构”论——“现实主义”的神化
在近百年的接受过程中,对“现实主义”,人们有不同的取舍及侧重,其内涵已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宽泛,在逻辑层次上也不尽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家们尽管对什么是“现实主义”各执一词,但他们都是把“现实主义”当做文学的典范来看待的。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一直都纠缠着一种“现实主义崇拜”情结,只是到了世纪末,才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1995年,《时代》杂志刊发了一组批评家的文章,不仅将“现实主义”视为文学发展的正统与主流,而且以为只有“现实主义”,才是“拯救”文学的济世良方。在他们看来,在即将迈进21世纪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学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并迈上一个新台阶,必须“弘扬现实主义精神”、“重构现实主义”。(注:参看《时代》杂志1995年5、6期李广鼎、王光东、孔范今等人关于“重构现实主义”的文章。)这一“现实主义重构论”,是神化“现实主义”的集中体现。
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看,人们在提倡“现实主义”时,无论是注重创作内容、创作态度还是创作方式,均有着历史的针对性及进步性,并且在创作实践中都显出了实绩。例如:“文学革命”时期人们在提倡“现实主义”时,那种关注不合理现实的创作内容、以人道主义为依据来批判现实的创作态度,与其时启蒙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就有着内在的契合,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都是遵循这一途径,才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充分发挥出巨大的现实作用并达到相当的艺术成就的;50年代后期人们在张扬“现实主义”时所侧重的写实手法和写实原则,对克服当时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及假、大、空等弊端,确实有着积极的作用;而在90年代出现的“以笔为旗”的倡导,就其实质而言,是在提倡一种文学必须引导民众、确立价值规范的创作态度。这对一度泛滥的宣扬价值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游戏写作,有着当头棒喝的作用。这些实质差异但效果相同的“现实主义”,适应着20世纪中国需要文学服务于现实社会斗争的历史诉求,相应地,“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不仅事实上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而且在观念上亦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正统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正道。与现实国情的契合及相应的创作成就,是“现实主义”被神化的历史根源。
“现实主义的泛化”,则是“现实主义”被神化的理论基础。当“现实主义”不再是一种文学形态和创作方法,被上升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一层面上而被视为“文学活动的本质”时,它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就有了广泛的适应性,可以将一切反映及批判了现实生活、采用了写实手法的文学作品,都纳入自己的旗下,以众多的“现实主义杰作”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及典范性。这样,“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红楼梦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等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层出不穷了。而新时期以来诸多的新兴文学现象,也被削足适履地归入“批判的战斗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纪实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莫名其妙、五花八门的“现实主义”之中。(注:参看张学正:《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现实主义”,被混淆为符合文学活动的本质、贯穿古今中外文学史,统摄众多文学现象的神奇的东西。
这就形成了人们文学价值观上的一种偏向:以为只有(只要)采用写实手法、遵循写实原则,运用了典型化方法的作品,才是(就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有在作品中批判现实、指出解救方向和途径的作品,才是有力度、有深度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甚至以为只有符合这样一种范式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才是关注、反映、批判现实生活的,才体现出“文学活动的本质”及“正道”。这种思想观念在当今的一系列批评现象中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许多批评家虽然激赏“新写实小说”原汁原味的细节描写,但又遗憾其未能再现典型环境、塑造出典型的人物;所谓“情感零度介入”的低调叙述本是“新写实小说”最具特色的叙述方式,但许多批评家却认为这种“中性写作”未能显出作家的价值立场及文学所应发挥的“指方向”的价值导向作用,因而在总体评价上或鄙夷地以为“新写实”小说“流于自然主义”,或“宽容”地认为“新写实”小说可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有益补充”。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评价也是如此,从所谓强调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出发,一些批评家以为“冲击波”小说对现实表现了过多的认可,因而最终难逃“瞒和骗之嫌”,将“冲击波”小说视为向权力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和献媚。这些批评家提出:“目下我最欣赏也认为最需要的则是19世纪形成巨大流派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这种批判的现实主义已经感到久违了,作家们不知干什么去了。”(注:参看《钟山》1997年第1期“近期小说笔谈”邵建之文。 )现实主义的“重构论”者亦强调,“完善人类生存的特殊责任感、对于人类的宽厚的爱心、对于人类生存现实的独特关注与表现”;强调“爱的激情、批判精神和理想精神”。(注:参看《时代》杂志1995 年5、6 期李广鼎、王光东、孔范今等人关于“重构现实主义”的文章。)不难看出,这里的“现实主义精神”,参照的仍是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以一种既成的文学形态当做永恒不变的典范来要求规范活水涌泉般的新兴文学现象,使相当多的批评家们未能正确把握评判新兴文学现象的价值。就学理而言,这是一种当代的刻舟求剑之举,从现实效应看,已显现出了负面的影响。
六、结论:走出“现实主义”模式的规范
“现实主义”的神化,是在历史的接受过程中形成的。将“现实主义”视为“文学活动的本质”,以为“现实主义”文学才是文学的正道及典范,其实质就是将一种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神圣化和永恒化。事实上,并非只有“现实主义”这样一种文学形态,才是关注、反映、批判现实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形态,源自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独特的生存处境及精神状态,各种不同的文学形态,都以各自不同的层面、态度及方式,关注、反映、批判着现实。因此,文学才显出了历史的具体性及独创性,从而产生独特的艺术魅力及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如果我们能够公允地对待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话,那么,也就不应将“现实主义”作为永恒且最高的典范来要求新兴的文学创作。当代文坛上的“新写实”小说,作家们已不再用某种舶来的价值观念来剪裁点化评判现实,体现出了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忠实于自我生命体验的真诚;也不移植西方现代表现方式和新潮表现手法来“形式创新”,那些前所未有的精细的细节描写,“原生态”地展现了当今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现实,那种不加主观评判、“情感零度介入”、“低调叙述”,简单中寄寓着丰富、宁静中潜涌着骚动。目前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深切细腻地展现了在世纪末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期,中国农村及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真实状况,揭示了这个时期国家、集体与个人,“官”与“民”之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的特殊国情。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带着几分被迫和几分主动,出于几分无奈和几分奋发,靠着彼此间的相互谅解和共同做出的牺牲,走出了一条新路。
以“现实主义”的范式来鄙夷“新写实”小说及“冲击波”小说,以为其“流于自然主义”、“可疑”或是“肤浅”,固然反映出神化现实主义的倾向,但将这些新兴的文学现象纳入“现实主义”的框架中,视其为“新的现实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同样也是神化现实主义的表现。事实上,“新写实”小说及“冲击波”小说,正是作家们以自己的眼光和方式来表现现实生活的产物,由此,二者在关注现实的层面、态度及表现方式上,也就呈现出难以用“现实主义”范式规范衡量的独特风貌。新兴文学形态的出现,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以属于自身的历史具体性、独创性及感人魅力,走向世界,融入历史。
因此,走出神化“现实主义”的误区,自觉而积极地扶持新兴的文学形态,是文学批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用“现实主义”模式框定的新兴创作,显现出当代中国作家正以属于自己的眼光和胸襟观察把握现实人生,以独创的方式表现自己深切的人生体验。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不能用既往的范式来评论当代中国的文学。
标签:文学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现代论文; 红旗论文; 刘绍棠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