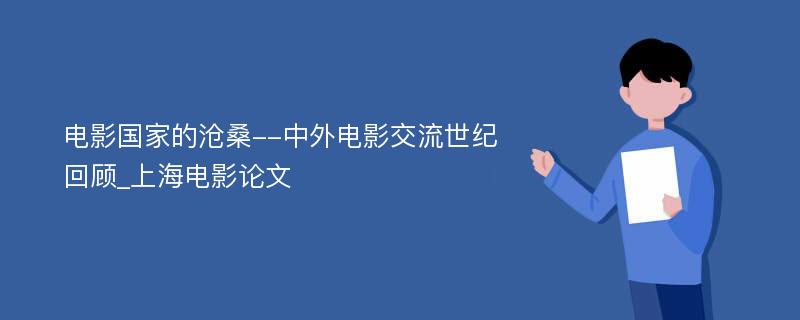
电影国门沧桑录——中外电影交流世纪回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国门论文,沧桑论文,中外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改革开放给中国电影带来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将曾经洞开而后濒临闭关的电影国门重新向世界开放。为了描述这一历史性转折态势,有必要对中外电影交流的进程做一番世纪回望。
20世纪前半叶:电影国门不设防
电影是一门建立在光学、化学、机械、电力等现代工业基础上的新兴艺术,当“西洋影戏”作为舶来品传到中国时,中国社会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电影前辈郑君里辩证地指出:“从经济意义上说,欧美电影(包括电影院的设立)流入中国,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之一般的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并没有两样。”他同时强调,“影片底输入给当时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国民众带来一种进步的世界性的观感”。① 中国电影是从放映外国电影开始起步的,早在1911年,美国驻汕头领事C·L·威廉姆斯在一份题为《中国需要的电影》中提到,“几乎中国每一个港口城市都以拥有一家电影院为荣”。② 上海是最早开放的重要口岸,也是西洋影戏登陆中国的首站,中外电影交流的众多个“第一次”便发生在上海。举其要者有:1897年7月,美国放映商雍松携片来沪,假座天华茶园、同庆茶园等处第一次公开售票放映电影;1915年9月,上海观众第一次见识卓别林主演的默片,他最初的汉译名叫做“哑波林”,音译意译配合绝妙,凸现其哑剧表演的天分;1929年2月,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首次公映进入中国的第一部美国有声片《飞行将军》。
早期涉足电影行业的中国人多有海外背景。如商务印书馆领头拍电影的鲍庆甲和叶向荣,前者曾赴美国考察,后者留学美国,接受电影新事物顺理成章。再如两位科班出身的导演,洪深于1920年由哈佛大学转到波士顿研习演艺与戏剧;孙瑜于1925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专程赴纽约,攻读电影编导及摄影、剪辑、化妆、洗印等课程。孙瑜回忆说:“二十年代,我看了美国‘银幕之父’格里菲斯的《残花泪》、《赖婚》等申诉世间不平的电影,看了影艺大师卓别林用笑声和眼泪演出的一幕幕悲喜剧之后,我就下定决心学习电影艺术。”③ 他俩学成回国后分别效力于“明星”、“联华”两家公司,成为民族电影的领军人物。
夏衍曾为中国电影下过“先天不足”的论断,当初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和从事左翼电影的同志们一起抓紧补课。夏衍晚年时披露:“第一个把外国电影剧本,美国的、苏联的、日本的翻译过来的是我,这些我过去没有讲过。再如一些电影术语,把close- up翻译为‘特写’,还有淡出淡入、溶出溶入,都是外国电影上有的名词,我把它们翻译了过来。”他还谈及美国电影对自己的影响:“30年代初,我们开始搞电影,也是从看外国电影学起的,当时看的电影大多数是美国的。没有书,没有学校,就是到上海大戏院去看,手里拿个小手电,边看电影,边计算时间,几英尺几英尺地计算。就这样,学了点电影的手法和技巧。”④ 在30年代,尽管美国电影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中国电影工作者也还是有机会接触其他国家的电影。1931年4月,上海百星大戏院第一次公映苏联影片《亚洲风云》;1936年9月,郑君里在自家寓所邀请一位苏联影人上门讲授《剧作在电影所起的作用》,沪上影剧界三十多位知名人士出席听讲,表现出对电影理论强烈的求知欲。
再来看中外电影人之间的交往。1929年底,好莱坞影星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夫妇乘豪华邮轮抵达上海,在沪期间出席了明星影片公司的茶话会,与中国同行叙谈影艺,胡蝶称“这次茶会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1936年春,卓别林夫妇到远东地区蜜月旅行途经上海,与梅兰芳、胡蝶等会面,还去新光大戏院观看马连良演的京剧《法门寺》。在电影制作方面,1931年洪深赴美国洽购有声电影拍摄器材,回国时雇来15名美国技师,协助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有声电影。另一则佳话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中外合拍片《世界儿女》,于1941年秋在“孤岛”面世,该片由流亡到上海的奥地利籍犹太导演弗莱克夫妇执导,编剧是费穆,双方以电影为武器,共同发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呼声。
在旧中国,中外电影交流呈现严重不对称。尤其美国影片大批量在华上映,而中国影片在美上映仅有零散的记录。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每年对华输出影片的数额与好莱坞年产量非常接近,换句话说,中国这块市场实际上已成为好莱坞小小的后院,占海外市场份额1%即800万美元左右。鲁迅看过不少美国电影,对其负面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收入的《“立此存照”(三)》中,鲁迅愤慨地指出:“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非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在鲁迅给予舆论谴责的同时,上海大光明影院还发生过洪深登台抵制哈罗德·劳埃德主演的《不怕死》的轰动事件,在各界人士声援下,这部引发中国民众公愤的辱华片被迫撤了下来。
20世纪前半叶中美电影交往的主要区域在上海,这段历史已引起两国学者深入研究的兴趣。如玛丽·坎珀在《上海繁华梦:1949年前中国最大城市中的美国电影》一文中指出:“30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美商或外商影院(中国大陆的电影史对此有误解);好莱坞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垄断存在于发行制度中,而不在于是否拥有影院。1933年的统计显示,上海37家影院中有19家主要放映美国片;30年代上海上映的影片约有85%是美国片。”⑤ 抗战胜利后,日寇侵华期间对美国电影的禁令不复存在。好莱坞八大公司于1946年联合组成影业公会来垄断西片放映市场,甚至规定上海各家影院的营业方针需征得该公会同意。据影业公会发行分会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9年5月不足四年间,经上海进口的美国电影多达1896部。1946年上海映出故事片383部,美国片就有352部;峰值出现在当年7月份,上映的199部影片中美国片占了142部。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名符其实成了一座电影不设防的城市。然而,从总体上看,上海观众以市民阶层为主体,他们对美国电影的观影兴趣低于知识阶层,20年代末即有“智识阶级中人,无不乐观西洋片,而唾弃国产”之说。⑥ 原因在于当时放映的均是英语原版拷贝,有些添加了中文字幕,有些需额外付费接受影院提供的“译意风”服务。当时米高梅公司曾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两项“战后计划”:其一是在中国乡村小镇推广16毫米普及型拷贝;其二是提供汉语配音的《泰山到纽约》。不料中国观众对《泰山到纽约》汉语配音版并不买账,致使米高梅放弃了这项推广计划。这个事例提示我们,旧上海的电影院分为西片、国片两大系统,观看国片的观众和观看西片(主要是美国片)的观众并不叠合。无独有偶,类似情形也在日本出现过,美国商务部通商局的内部通报记述日本存在着“下层社会喜欢看国产片,上流社会喜欢看外国电影”的现象。⑦ 当时上海电影市场主导运营方式是票房分账,中国放映商与美国发行商的分成比例一般为六四开。由于经济恶化通货膨胀越演越烈,电影票价赶不上物价飞涨,美国片商的赢利大大缩水,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大幅度减少对华输出影片。1948年数量为272部,1949年上半年骤降为1部,市场占有率随之跌落,预示着好莱坞好景不长了。
20世纪中期:电影国门留条缝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电影交往因政治原因很快出现历史拐点。1950年7月,文化部发布《国外影片输入》等行政法规,削弱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影响。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1月11日,上海市影院工会和影院同业公会发表声明,率先拒映美国影片,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配合开展一场声势不小的消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好莱坞电影就此被逐出中国大陆。1951年初,上海市军管会对好莱坞八大公司在沪设立的发行机构实行军事管制。同年4月,政务院第81次会议批准文化部工作报告,指出:“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有害影片已基本肃清,这是电影市场上的空前变化,是文化战线一个巨大胜利。”⑧
新中国对外电影交流存在着两个路径。一个路径通向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老大哥。建国初期,上海、长春两地的翻译片工作者加班加点,译配了一大批苏联影片,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影响了中国一代青年人。据统计,在“十七年”期间我国引进的857部外国影片中,苏联影片有421部,比例高达49%左右。1954年6月,由王阑西局长带队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苏联,用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深入考察苏联电影事业,回国后制定了全盘苏化的建设计划。1955年,中共中央给文化部下达批示:“应积极筹备将北京电影学校改为北京电影学院,聘请苏联专家系统地、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掌握现代电影艺术与技术的创作人员。”⑨ 但是,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1960年是个转折点,颇富戏剧性的是“长影”和莫斯科电影厂合拍的《风从东方来》3月份公映,讲述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设水电站的故事;不料到了7月,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签订的所有合同,随即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电影系统亦如此,不仅苏联专家撤走了,从苏联进口的电影胶片也停止供货了。此后,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论战,《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发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社论。在此背景下,1963年初文化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京举办“第一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电影座谈会”,出席者达226人,将《雁南飞》、《第41》等多部“苏修”影片列为反面教材进行剖析。
另一个路径通往西欧国家。1954年,周总理在出席日内瓦和平会议期间,分别宴请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定居瑞士的卓别林,并招待贵宾观看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称赞说“从来没见过这样一部非凡的影片”。与此同时,我国开始译制少量西方进步影片,如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时》,法国的《没有留下地址》等。1956年4月,受法国半官方电影机构邀请,又派出由蔡楚生带队的电影代表团参访法国,一路上顺访西欧诸国考察电影业,为时达半年之久。此行收获之一是与法国签订合拍儿童片《风筝》协议,两年后该片问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合拍片。1956年11月,法国著名电影史家萨杜尔访华,他为“长影”主创人员做学术报告时称:“中国电影是世界电影发展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要把中国电影发展情况写进我的《电影通史》里去。”
1957年9月,我国作为东道主首次举办规模较大的“亚洲电影周”,遍邀亚洲15个国家派来电影代表团出席,在国内十个大城市展映各国的故事片和纪录片,还发表了《参加“亚洲电影周”各国电影代表团联合公报》,堪称电影界一大盛事。可惜这样的势头未能保持下去,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演变,电影国门渐渐呈现收拢的态势。1963年3月,周总理在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并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选映苏联影片〈运虎记〉》报告上,以相当严峻的行文做了五条批示,前三条为“我提议:以后从外国进口片子,第一,要减少数量,留出拷贝洗印我们自己的片子;第二,要注意质量,不仅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不要,连低级趣味的也不要;第三,一切进口片子都要经过中宣部指定的专门小组(包括外办)审定后才许译制”。⑩ 周总理这段批示透露出当年对外反帝反修、对内抓阶级斗争的时代印迹。1964年5月14日,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电影代表团,这是毛泽东外事活动中唯一一次单独接待来自电影界的外宾,也为“文革”时期我国进口阿尔巴尼亚电影做了铺垫。
众所周知,在“文革”浩劫中电影界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对外交流处于停顿状态。1968年9月,周总理在与交响乐伴唱《红灯记》演出人员座谈时指出:我们现在很难拿出有艺术性的影片,外国朋友要我们送几部片子给他们,我们拿不出来。这种情况已经两年了,再继续下去不应该了。但周总理显然力不从心,此时别说外国朋友顾不上,本国观众早就陷于“电影荒”了。在这个非常时期,电影国门基本上只留出一道门缝,特别放行来自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罗马尼亚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出产的影片。当年民间有几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语虽调侃,倒也是实情,描述了当时银幕上鲜见的异国风情对民众看乏“老三战”、“样板戏”影片的调剂作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为庆祝朝鲜国庆献映的《卖花姑娘》,因国内观众长期看不到苦情悲剧片而备受欢迎,人人争睹为快,将蓄积已久的审美泪花慷慨地洒向那位朝鲜姑娘。除此之外,国内观众偶有机会接触某些涉及国际政治的批判电影。如1971年2月,国务院遵照周总理指示,将三部日本反动影片《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战》、《啊!海军》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内部发行,组织工农兵观众愤起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9·13事件”发生后,周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国内形势出现了一定转机。1972年10月,周总理向“中影”公司负责人详细了解外国电影进口情况,指示可以多进口一些外国电影,对业务部门摘编《国外参考影讯》也很感兴趣。后来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还在病榻上嘱咐秘书致电“中影”公司,关心这本内刊的印行。1973年元月,周总理与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在半个月之内连续两次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代表,他在讲话中提出:“发展电影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但也要进口一点外国的片子作参考,以便超过他们。”然而,江青带头在会上频频发难,致使周总理中途退场。1974年1月,江青授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反华影片〈中国〉》,用“文革”语言上纲上线,将通过外交途径由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委派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打成“反华分子”,借机攻击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总理,构成一桩涉外政治事件,在海内外造成了负面影响。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同意外交部《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上海社科院一位年轻的文学博士最近撰文反思:“感谢安东尼奥尼,他为我们留下了1972年的‘中国’印象。我们曾经真实地经历过,却没有诚实地记录过,也没有认真地打量过,更没有清醒地思考过,而他的《中国》则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11)
改革开放新时期:电影国门有序开
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国策的指引下,中国电影业开始迈上振兴之旅。在中外电影交往方面,电影国门再次打开。具体来看,对外开放是从三个方面有序展开的,即学术交流、合作制片与电影市场开放。
1979年5月,张暖忻、李陀在《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专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文章开门见山,用排比句连连发问“在分析我们的电影语言为什么落后于形势的时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常常被人忽略)提出问题:我们对近年来世界电影艺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吗?我们应该不应该向世界电影艺术学习、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电影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完全同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割裂开来,采取一种闭关自守的姿态,这是正确的吗?”笔锋直陈国产电影与世界电影潮流的巨大落差,透出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1980年3月,“中国世界电影学会”宣告成立,集聚起一批承担外国电影研究、评论、翻译和教学工作的同仁。1982年2月,由意大利外交部、意中友协、意大利国家电影资料馆等八个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在意大利都灵、米兰、罗马三个城市举行,共展映135部中国影片,其中20—40年代出品的有33部,吸引欧美一百五十余位电影学者、评论家出席。这次影展的规模和影响力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受到高度评价,意大利评论家卡拉西奇甚至提出:“意大利引以自豪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在中国上海诞生的!”当年年底,《中国电影回顾展》又移师法国,再一次取得成功。国际交流是双向的,从1984年开始,中国电影资料馆连续举办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西班牙、加拿大等七个国家的电影回顾展,累计达十余届次,展映的影片超过300部,大大开阔了中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视野。
中国电影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国际电影节。1985年第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由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受到高度关注与好评,海内外影坛随之掀起第五代导演冲击波。1988年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摘得最佳影片金熊奖,叩开了中国电影通向世界的大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特为此举行庆功会,主管领导致词中强调:“《红高粱》在著名国际电影节获大奖,其功绩与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同样重要,都是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12) 不过,在国际舞台上也有不谐和音掺杂出现。最强烈的一次是1999年4月,张艺谋致函戛纳电影节主席雅阁布:“我决定将《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撤回,不参加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因为我觉得您对这两部影片有很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治宣传’一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偏见。”(13) 中国电影这次毅然对戛纳说“不”!
1984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北京电影学院在京举办“国际电影研讨会”,邀请今村昌平、马丁·斯科塞斯等著名导演参加,这是我国电影界首次举办国际学术活动。随后数年间,中国电影家协会又接连举办四期“国际电影讲习班”,邀请美国教授来华讲学。此外,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发起的“中日电影文学研讨会”,为中日两国电影剧作家提供了每年一度相互切磋剧艺的平台。1993年10月7日,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隆重开幕,引来全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的164部影片参展参赛,“金爵奖”评委阵容显赫,由谢晋、大岛渚、奥利弗·斯通等名导组成。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经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确立的中国唯一的A类国际电影节,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目前已成功举办11届,在世界影坛正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中外合拍片领域,我国于1979年成立了第一个涉外电影企业“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迄今为止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及港台地区的制片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累计完成合拍片约560部。合作方式从开头阶段的浅层劳务协拍发展到深度合作,共同投资出品了多部大制作如《末代皇帝》、《霸王别姬》、《宝葫芦的秘密》、《木乃伊·3》等。2004年,浙江横店集团与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共同组建“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此举乃新形势下国企、民企与外企携手合作的先声,显示了中国电影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的姿态。
这里来回顾一下电影市场对外开放的轨迹。电影是视听艺术,域外电影进入中国大陆客观上受到国民审美心理的制约。新时期伊始,长年闭关锁国造成的禁锢和“极左”思潮的余绪,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观众对外国电影产生抵触。1979年曾爆出新闻事件,《大众电影》封底因刊登英国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男女主角接吻的剧照,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位读者写信责问编辑部:“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这张剧照以及这位读者的观点,引来全国各地雪片一样的讨论信,仅短短两个月,《大众电影》便收到一万一千二百多封来信来稿。然而,赞同该读者观点的不足三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电影》为这张剧照所担的风险,折射出中国电影对外开放是人心所向。
1979年5月,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一行来华访问,会见了文化部和电影局领导。瓦伦蒂在会谈中主动提出由美国出资,在北京、上海建造现代化影院,其前提是必须全年全部放映美国片,片目可由中方挑选,票房收入按比例分账。这一设想在当时显然超出中国所能接受的限度,因而未达成任何协议。“中影”公司仍旧对外国影片实行买断发行权的方式,每年用于进口片的经费约100万美元,进口数量约30部,平均每部进口片分摊到3万美元,如此低廉的价格决定了当时只能引进一些低成本的外国影片。到了1994年1月,中国入世的步伐渐行渐近,主管部门授权“中影”公司每年引进海外10部分账大片,其标准为“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分账制体现“利润均沾,风险共担”的规则,是世界电影发行业通行的。当年11月,第一部海外大片《亡命天涯》在京、津、沪等六大城市上映,首周票房即达一千多万元。1998年引进的《泰坦尼克号》,票房收入更高达3.6亿元,几乎与100部国产片等值,业内人士惊呼“狼真的来了!”此后,第二家国字号华夏电影发行公司成立,旨在形成竞争机制,打破“中影”公司独家垄断进口影片的局面。具体做法是把分账大片作为激励,哪家公司国产片发行得好,哪家获得分账大片的额度就越多,但这种做法在市场意义上似乎形成了悖论。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加入WTO长达13年的谈判达成协议,正式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前任局长刘建中曾参与入世谈判,他回顾说:“从市场和双边贸易的层面来看,中美电影交流的最大问题是不平衡。从1995—2001年七年间,我们共进口美国影片134部,其中分账影片61部;而美国几乎没有进口过一部中国影片在主流院线进行商业发行放映。”(14) 目前,好莱坞出品越来越多推行全球同步上映,一来为打击盗版,二则利用媒体力量将首映活动搞成吸引全球注意力的轰动事件,唤起人们的观影冲动。2003年,《黑客帝国3》首次在中国实现全球同步上映,从输入层面而言,中国市场已经同好莱坞“无缝对接”了。
新世纪:中国电影走出国门
据统计,1905—2005年这一百年间,我国共摄制了七千二百多部故事片。其中摄于1947年的《假凤虚凰》,由导演黄佐临亲自译成英语配音版,成为第一部走出国门在欧美国家上映的中国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到了1957年5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向西方国家的电影公司出售我国影片发行权、委托代理我国影片发行权、交换影片发行权、交换新闻影片素材等四个合同(草案)。1958年3月,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影片输出输入工作跃进会”,夏衍等领导到会讲话,要求拍摄一些“在国外发行毫无障碍的影片”。1959年7月,夏衍在全国电影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讲话时提到:“我们的电影要和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能够相称,要在国际上站得住脚。我们要考虑外国观众的爱好,当然绝不是说要降低影片的政治思想内容去迎合他们的趣味,而是要考虑我们影片的题材样式,要研究提高影片的艺术、技术质量,去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这个问题今天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5) 然而,受制于当时国际国内大环境,中国电影对外输出基本上务虚居多,实际成效进展缓慢。季洪时任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她长期分管全国电影经济计划,出版过一本不可多得的《季洪电影经济文选》,全书收入84篇文章,却没有一篇涉及中国电影出口创收,显露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电影内向型的局限。
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中国作为电影大国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身处21世纪全球化潮流,中国电影人肩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国形象与中华文明的使命。多次在海外举行过个人影展的谢晋导演清醒地指出:“一种是走向全世界的电影市场,拥有全球的观众,现在全世界电影行业能做到这种走向世界的,可以说只有美国;另一种是走向国外学术性电影院、大学,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文化交流,这个我们现在做到了。”中国电影对外输出在市场意义上的真正突破,是由张艺谋团队实现的。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以2100万美元向米拉麦克斯公司售出在北美、拉美、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非洲发行的版权,美方安排在2031块银幕上映,连续两周蝉联票房冠军,总票房达3525万美元,被美国媒体评价为“中国最成功的一次文化出口”。《英雄》在法国上映也备受欢迎,创出了375个拷贝的新纪录。
21世纪是中西文化交融、竞争、共存的时代。季羡林先生多年前就提出:“讲文化交流,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入超严重。”为缩小这一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巨大差距,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电影作为“软实力”的重要一支,同样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作为政府行为,国家电影局于1996年创办“北京放映”推介活动,每年金秋邀集国际买家聚会京城,至今已举办了12届,为国产影片开拓海外发行渠道搭建交互平台。近年还组建了“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向制片单位提供免费印制外文字幕拷贝、印发海报宣传品、租用电影节展台等优惠措施,着力推动国产电影走出国门。
在刚刚闭幕的第17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长影”厂翻译片前辈袁乃晨荣获终身成就奖,这位老艺术家九旬高龄壮心不已,放言要到好莱坞等地去开设译制片厂,将更多的华语“翻版片”译成全世界不同语种的拷贝,让中国电影走向全球。袁老这番豪言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既是中国电影人的心愿,也是中国电影人的担当,让我们为之共同努力!
注释:
① 引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5页。
② 引自韩骏伟《国际电影与电视节目贸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③ 孙瑜《银海泛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④ 夏衍《劫后影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⑤ 玛丽·坎珀《上海繁华梦:1949年前中国最大城市中的美国电影》,载《电影艺术》1999年第2期。
⑥ 黄转陶《摄制古装片之我见》,载《电影月报》1928年第2期。
⑦ 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⑧ 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⑨ 同⑧,第403页。
⑩ 同⑧,第501—502页。
(11) 陈占彪《批判“反华”影片〈中国〉始末》,载《世纪》2008年第5期。
(12) 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05页。
(13) 同(12),第1033页。
(14) 《刘建中局长答记者问》,2001年12月《中国电影报》。
(15) 同⑧,第456—4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