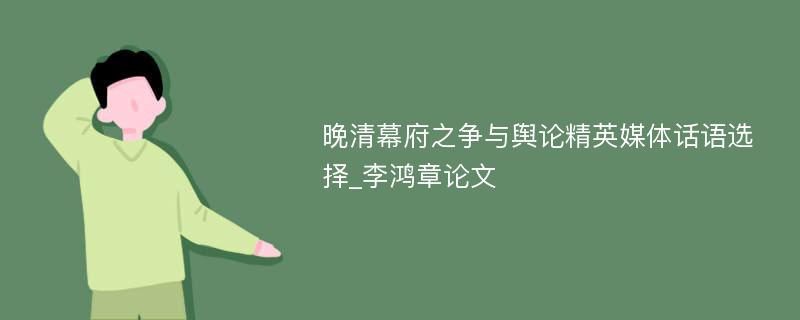
晚清幕府纷争与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府论文,晚清论文,纷争论文,媒介论文,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1-0062-09
内战与外战交织下的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分水岭,战败引发了朝野上下普遍的舆论探讨。其时社会舆论在政统、道统层面展开了大讨论,救亡压力下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成为舆论的焦点。学习之后的社会变革当然要牵涉到社会资源及权力的重新分配。面对救亡舆论下社会变革的合法性阐释,救亡图存压力下各个军政利益集团运用媒介为本集团牟利,展开政治宣传,维新舆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媒介意见的汇总。维新舆论媒介的建构离不开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或直接或间接与幕府有联系,特别是与幕府的社会定位及价值取向有关系。晚清政治变革涉及道统与政统两难抉择的社会语境,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侧重探讨借助报刊进行文人论政的思想策略,即首先是经世,其次才是学理论证上的合法性。但政治上的应变不能以牺牲学理上的价值取向作代价,这是作为舆论精英的幕宾与幕府关系的底线。下文从精英人物与军政利益集团的关系探讨近代舆论转向的社会语境,并分析中外舆论精英在晚清幕府利益冲突中扮演的角色。①
一、甲午战争前后幕府兴衰与幕宾的言论立场
甲午战争期间,政治舆论动员背后有派系纷争。李鸿章、翁同龢或谋和或主战,两者之争尚有狭隘的政客私利。而作为舆论精英,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举措及舆论动员意在为近代中国寻找出路。除康梁这一派外,维新舆论中媒介建构力量,部分源自幕府中知识人物,尤以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为代表。甲午战前,王仁堪以状元外放镇江知府,他对梁鼎芬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1]无论就地缘关系还是政治资本而言,李、张幕府在众多的军政利益集团中都有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法战争以后的晚清政局。
(一)甲午战争李鸿章及其幕府的衰败与舆论精英的舆论评判
甲午战争改变了晚清政治格局中李、张幕府的政治地位,对李鸿章冲击尤大。正如梁启超云:“中国维新之萌孽,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2]可以说,李鸿章幕府式微,始自甲午战争。面对甲午战争,李鸿章常囿于个人政治得失,扮演不了引导舆论的舆论精英的角色,其原委如梁启超所揭示:“李鸿章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制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3]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后虽未能左右国内舆论的导向,但他本人很注意国际形象,亦常接受外报刊专访。甲午败绩使得李鸿章声名狼藉并受罚,但《纽约时报》1894年8月6日的报道《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带罪领军》[4]仍称道李鸿章政治形象,说他“以‘清国伟大政治家’的盛名享誉于世,目前在公众面前仍保持着很卓越的名声”。[5]谈及李鸿章个人形象时,该报道称:“李在两三年前得过一次麻痹症……虽然李康复后的身体不如先前那么壮实,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机旺盛的老人,一点没有书生文弱的形象。”[6]甲午辱国,李鸿章在西方新闻媒介话语表述中仍以良好的形象呈现,可见其颇有外交手腕及政治派头。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幕府中幕宾多有重视报刊舆论的人物,如伍廷芳(1882-1895年入李鸿章幕府)早年有办报经验,1858年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颇受英国文化氛围影响,常为《时务报》撰稿,是近代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再如严复、宋恕等作为李鸿章幕府中的舆论精英,在言论阵地上举足轻重。曾留英的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提出“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7]认为这是西方富强的奥秘所在。反观李鸿章幕府的政治形象,严复在《直报》及友朋书信中称北洋的人际关系网络建构在亲缘、亲信基础上,这导致其指挥晚清政局失灵,海战中受日本巨创,无可避免。[8]相比之下,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教习宋恕后在《经世报》上发表言论,支持李鸿章。严复、宋恕等对幕主的选择,既与其在幕府中的经济地位及文化身份定位有关联,亦与幕府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其时,受舆论谴责的李鸿章利益集团内部亦危机四起。王修植等对李鸿章代表的北洋水师及其学堂颇多不满。总体上看来,随着中国海军节节败退,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派系中王修植、严复等掌握的《国闻报》针对北洋军政利益集团腐败所发出的舆论呼声,表明救亡压力下李鸿章幕府内部离心力加大,也反映了严复等舆论精英的政治抉择。
(二)甲午战后张之洞及其幕府的崛起与舆论精英的舆论支持
甲午战争的封疆大吏中能与李鸿章抗衡的就是张之洞,“之洞于交涉之事,著著(处处)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9]李鸿章在第一次会见传教士李提摩太时,就称:“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10]“《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他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11]甲午战后,张之洞军政利益集团在舆论场域上有其经营方向并有自己的特色。张之洞钟情国学,其幕宾亦多精研朴学的人物,成为舆论动员中主张保存民族特质的重要舆论精英。如著名国学人物陈衍(1898-1902年、1904-1906年,两度入张之洞幕府)曾为湖北官报局的总纂。后成为国粹派代表人物的章太炎于1898年入张之洞幕府,在张之洞授意下创办《正学报》并为之鼓吹。汪康年曾于1890-1894年入张之洞幕府,后执意离鄂往沪办报,得到张之洞谅解并资助。吴樵致汪康年信称:“闻南皮为公筹四十金,湘中四十,报馆廿馀,公为富人矣,甚羡甚羡。”[12]叶瀚致汪康年信亦称:“今年吾兄来鄂,奉帅委兼办译书局事,采买译述,实兼两局。”[13]汪康年在上海办报,也还在张之洞幕中兼差,领取丰厚的薪水。张之洞的幕宾邹代钧致信汪康年亦称:“香帅又予公四十金,甚善甚慰。淮阴多多益善之说,可为公诵之。”[14]张之洞在经济上支持汪康年显然有其控制舆论的目的。与汪康年相比,梁鼎芬的情况有所不应。梁鼎芬素喜时政,好发清流高论。中法战争期间,他以清流身份抨击李鸿章,与清流四君子之一张之洞相呼应,主张对法作战。后遭慈禧太后打击,虽辞职还乡,但其清流的身份得到士林确认,同时也为张之洞欣赏。1886年4月,张之洞聘梁鼎芬主持惠州的丰湖书院,后又支持他参与创办广雅书院,并任院长。梁鼎芬曾促成汪康年创办《时务报》,自己还作为张之洞幕府的代言人对《时务报》遥控。张之洞、梁鼎芬等的行迹表明,晚清幕府之间的派系纷争,大多为政治变局中争夺更多的发言权,从而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
总体上看来,甲午战争前后,在政统上与幕主合拍或分歧的舆论精英,在学理上本着传承中国传统的“立言”的人文角色看待报刊,投身舆论场域,利用报刊发表对时局的高见。即政治上可以应变乃至投机,但有其学理取向上的底线,两者冲突时,常放弃前者而回归学理上的价值取向。李、张幕府中文化精英在政统、道统上抉择两难,对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格局变迁及社会舆论趋向颇有影响。
二、甲午战争前后李、张纷争与中外舆论精英的媒介话语选择
面对甲午战争,朝廷要员就主战或主和,分成两派,此为帝党、后党之争的前兆。就对外主战或主和问题,幕主及其幕宾亦有各自的政治抉择。期间,掌握北洋军队的李鸿章主和,张之洞则主张对日决一死战。针对李鸿章、张之洞及其幕府间的矛盾及政治舆论上的分歧,中外舆论精英往往根据时局变迁而有所抉择。《万国公报》负责人为李提摩太,他多周旋李、张军政利益集团之间,面对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出路,提出代表西方殖民利益的“新政策”。而李提摩太对舆论界的影响,离不开李鸿章及其幕府的大力支持。李提摩太称其通过李鸿章和几个私人朋友,1890年7月获得了一项任命,成为《时报》(Shin Pao)的中文报纸的主笔。[15]他说:“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我写了一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一份特刊号,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事实证明,这种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16]李提摩太就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定位发表诸多时评。李称1890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太子——来到远东地区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中国的官员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几个礼拜的时间里,我在《时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王室成员之间相互访问的情况,指出这种互访极为有利于和平和善意的达成,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以同样的方式出国访问”。[17]后李鸿章出访欧美,与此不无关联。
以日本及欧美政治变革为参照系,李提摩太在报刊上发表的诸多时评及政论亦引起张之洞及其军政利益集团的注意。李提摩太称:“我还发表了一些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为此,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到报社向我表示感谢。不同地区的中国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18]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前后,李提摩太受张之洞三次会见。与此同时,李提摩太自豪地称:中日战争期间,“我们”的出版物《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番,“对它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就必须重印。”[19]此期间,报刊传播对国人而言,仍属新鲜事物,李提摩太亦在译著《泰西新史揽要》中夹杂地传播西方报刊思想。② 李鸿章积极推荐李提摩太以“教民”、“养民”、“安民”、“新民”为旨趣的“匡华新策”,1895年2月9日他致电清廷:“上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纷识其忠于为华,来电:‘有妙法救目前,亦救将来,请酬银百万。但发一确电允给,即详细告知,不成不取’云。应否姑允所请?不成不取,似无妨碍。候电示。”[20]《新政策》枚举中国急要办的九件事,第六件,即为办报:“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傅兰雅、美人李佳白总管报事,派中国熟悉中西情势之人为之主笔。”[21]可见,李提摩太等“匡华新策”,有控制中国社会舆论之野心。鉴于此,张之洞对李提摩太之游说,评价不高。③ 这显然有别于李鸿章对李提摩太扶持的态度。
鉴于李鸿章与张之洞政见分歧、幕府权势纷争,除李提摩太等周旋其间,兜售代表西方利权所谓新政策之外,国内一些精英人物也奔走其间。针对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败迹,以李鸿章幕府腐败为参照,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致信同乡兼学术知音陈宝琛,对张之洞及其军政利益集团颇有赞誉。[22]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被誉为晚清“清流派四君子”,彼此奥援。严复此信目的就是准备投靠张之洞军政利益集团。随着甲午战败成定局,严复对李氏集团加大剖析力度:“今日东事愈不可收拾,北洋之意气愈益发舒。於戏,可胜痛哉!”[23]随着时局的变化,严复下决心请陈宝琛在张之洞面前予以引见。[24]严复的努力并无实质性的结果,但表明甲午中国战败给掌权派北洋集团带来了巨大政治风险,李鸿章幕宾多离心离德,幕府面临分裂的危险。
但李鸿章精于宦海浮游,其所谓“外交能力”受列强垂青。1895年3月23日他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遭国内舆论痛诋。但时局很快有了变化,俄联合法、德,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鉴于日、俄对华态度的变化,李鸿章一贯主张联俄制日的外交思想受重用,他遂得以东山再起。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了大量主权,换取所谓中、俄共同防日。与此同时,奉命联络邦交的李鸿章受英、德、法、美等国的重视。是年8月28日,他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在美国获得“国宾礼遇”。[25]次日,《纽约时报》连篇累牍地发表词以万计的“新闻特稿”,并配有李鸿章“出使美国风采像”。[26]9月3日《纽约时报》又刊发《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该报道开头就称“李总督前天向纽约记者们发出邀请,预定昨天上午八时半在华尔道夫饭店接受记者采访”。[27]报道对李鸿章个人形象及政治形象作了刻画:“当他出现在记者们面前时,精神爽朗、面容生动、活泼。”[28]“回答问题时,他态度非常坦诚、谦虚,好像他只是世界上一个很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大清政府权势赫赫的人物。要知道,他是代表整个清国说话,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东方这个伟大的国家。”[29]采访结束时,李鸿章“向记者们优雅地鞠了一躬”。[30]可见,李鸿章在新闻媒体面前非常重视自己的个人形象及清帝国政治形象,并老于此道。但《中俄密约》签订后,中国政局随之动摇,列强以在华强租海港及强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掀起了瓜分中国狂潮。压力下中华民族进行社会改革,势不能免。与改革相契合的维新舆论建构亦成大势所趋。
三、维新变法与李张幕府中舆论精英的舆论转向
晚清舆论精英对舆论变迁的影响或轻或重,甲午战后的维新舆论动员涉及舆论精英在中西文化交融互释下的政统、道统的抉择。1898年维新运动期间,报刊由1895年的15家激增到64家,[31]是对维新舆论进行媒介建构的重要工具,充当了维新舆论动员的角色。
甲午战后舆论转向涉及舆论精英之间复杂交错的人脉资源。维新舆论动员中汪康年沪上办报成功,对张之洞、李鸿章幕府影响极大。一些知识分子离幕后,多仿效汪氏筹划办报。如吴德潇、吴樵父子曾在张之洞利益集团中当差,吴德潇同汪康年一样,曾列《时务报》五个发起人之一。吴樵在京师为主持译书事宜,致汪康年书信多称“吾鄂同志”,[32]也替汪筹办报纸出谋划策;[33]后因未受张之洞重用,遂往湖南;曾筹划《民听报》并征求汪康年、梁启超的意见。[34]再如,叶瀚曾为张之洞的幕宾,一度想办报,见吴樵致汪康年信:“浩吾(叶瀚)近颇恍惚,不知何故?又欲为元魁报。”[35]针对《时务报》的人事纠葛,叶瀚称:“卓如(梁启超)若去,正大可忧,公(汪康年)何妨调铁樵主笔。”[36]叶瀚对报刊舆论颇为热心,后离幕往沪筹办《蒙学报》并任主编。叶瀚主持的蒙学报馆与汪康年任经理的时务报馆有亲缘关系,[37]这与他们在张之洞幕府中的同事之情,密切相关。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亦多舆论精英,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时论,反省中国历史发展的堕性力量,常以西学为参照。典型事例就是李鸿章、李经方等往日本媾和,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的重要智囊严复在《直报》(1895年3月13日至14日)刊发《辟韩》,从道统、政统层面反思中华民族的惨败。严复称:“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他提出“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质疑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其时,朝野上下仍在纠缠主和、主战之争,严复则从道统层面对君臣依附关系作了极其深刻的反省,提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38]“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39]严复对君臣之伦进行的学理解构,并没有引发太大的关注。时过境迁,《马关条约》签订后,维新变法成为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辟韩》又作为经典性批判意见而被重新发现,于1897年4月12日被上海《时务报》第23册全文转载。两相比较,天津《直报》刊载《辟韩》原文有:“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时务报》转载时,将后半句改为“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40]将“六经”改为“古书”,可见梁启超及《时务报》在维新舆论建构中对待中国经典文献的态度。在朝野对甲午战败的后果彻底反省之际,《时务报》上的《辟韩》重刊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41]是年就任陕西学政的叶尔恺于5月21日致汪康年信,称:“《辟韩》一篇,尤与鄙人夙论相合,甚佩甚佩。特都中大位诸君未必留意耳。政府诸人招权纳贿,尤其昔年,钻营奔竞之习,日益加工,此其政教使然,无足异矣。”[42]将《辟韩》与晚清政教腐败相联系,可见《辟韩》用意及当时政要结合社会语境对其进行别具匠心的文本解读。晚清名流孙宝瑄对《辟韩》质疑君统的合法性颇有感喟,1897年10月12日就《辟韩》赋诗,见次日日记:“晚,录昨所为《辟韩》诗二首”,其中有“圣推殷受罪周昌,百代高文撼肺肠。堪笑宗风起闽洛,为言赤县有臣纲”。[43]《辟韩》以“观我生室主人来稿”,转载于《时务报》。孙诗中有“起闽洛”,可见正是借《时务报》背后的人际脉络及严复的文笔,他才有可能知道“观我生室主人”是严复。是年,《湘报》的发起者谭嗣同于4月25日致汪康年信亦称:“《时务报》二十三册《韩辟》一首,好极好极!究系何人所作?自置‘观我生室主人’,意者其为严又陵乎?”[44]总之,志趣相投的舆论圈内的人才能推测出作者,此亦可见严复作为李鸿章幕府中杰出的舆论精英其社会影响之大。
面对严复等在维新舆论媒介的建构中对传统的政统、道统的学理批判,严于君臣之伦的张之洞,对汪康年等掌控下的《时务报》刊登的《辟韩》,“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幕宾屠守仁作《〈辟韩〉驳论》进行反击。1897年6月6日,作为张之洞的传话人叶瀚致汪康年信,称:“顷念劬来传南皮帅意云:《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属布告合行奉闻。”[45]所谓“文犯时忌”,比照严复所称近代中国问题在于“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46]即可见一斑。严复从论证君臣作为人,皆有平等权利,但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此显系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而已。严复之论,有解构极权专制的道统之旨趣。叶瀚信中的念劬即钱恂,曾入幕府为张之洞帮办洋务,1893年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武备学堂提调,常扮演张之洞幕府代言人。颇感压力的严复在家书中云:“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出名也,《时务报》已照来谕交代矣。”[47]在他看来,此文为张之洞自撰,不过托他人之名而已。1897年6月20日,《时务报》第30册中“时务报馆文编”果然刊载《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称严复“以挫于倭之忿恨,有慕于欧洲之富强,直欲去人伦,无君主,下而等于民主之国,亦已误矣”。同时警告时务报馆:“虽报馆之例,有闻必录,误则从而更正之。窃以于众事犹可,抑亦他报馆不问义理,但聘快笔者所优为,恐非诸君子创《时务报》之深心所宜然也。”待《〈辟韩〉驳论》刊出后,张之洞特发牌示:“示谕两湖江汉、经心书院诸生知。上海《时务报》,前经本督部堂饬发院生阅看,以广见闻,但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纯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近日惟屠梅君侍御驳《辟韩》一篇最好,正大谨严,与本督部堂意见相合,诸生务须细看,奉为准绳。切切特谕。”[48]在道统这一根本的学理选择上,严、张两人显然不同,始至交恶。而一度想投身张之洞幕府的梁启超,时任《时务报》的主笔,早在1896年10月前后即写信给严复,表示要转载严著《原强》。缘此,严复有《原强修订稿》。随着张之洞授意对《辟韩》进行批判,《时务报》未再转载《原强》。此足见张之洞对《时务报》时评之影响,亦可见他在政统的舆论引导上的卫道士身份。
李、张军政利益集团中舆论精英在报刊发表时评的价值取向,多与其时舆论转向关联。甲午战后的舆论由宣传洋务转向鼓吹维新变法,与变法合拍的维新舆论面临媒介建构。戊戌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政治舆论媒介建构上的转向,关联着朝廷政要及舆论精英的政治抉择。章太炎曾书李鸿章,自称:“幼诵六籍,训诂通而已。然于举业,则固绝意不为。年十七,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于深山乔木间,冥志覃思,然后学有途径,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盖自三子以后,得四人焉,曰盖次公、诸葛孔明、羊叔子、黄太冲。”④ 针对1897年西方以租借方式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章太炎主张与日本结盟。反观李鸿章幕府重用英美外籍人员,而日本籍较少,章太炎称:“夫省饩得材而可以利结日人之心,则是政治饬而合从成也。”[49]他甚至提出:“自甲午而前,则谓之修好;自甲午而后,则谓之乞哀。虽然,苟有益也,虽乞哀何损。”[50]李鸿章幕府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军政利益集团,其在外交政策上代表后党,主张联俄;章太炎书生政论,主张联日,上书当然不为李鸿章所取。两个月后,章太炎另作他计,往武昌投靠张之洞,成为其幕宾,助张之洞办《正学报》。章太炎著《正学报·例言》,分“译报”、“议论”两部分。《例言》将《正学报》与邸钞相区别:“昔陈文恭令人阅邸钞,欲其明习时政、通晓格令也。今则外患迭乘,全球震荡,虽殊洲隔壤,一话一言皆与支那相感触,非寻常案牍所可伦比。若劳神簿领,转昧大势,譬鹪鹩巢苇,纵极坚致,风至则折,复何取焉?故以选译东西各报为主,于邸钞则从略。”[51]可见,章太炎等注意到邸钞以通晓格令的形式,由上向下单向度传播。鉴于此,章太炎办《正学报》以译报方式“通中外”。具体而言,兼有国学人物及舆论精英双重身份的章太炎即在政治舆论的媒介建构中主张联日制俄。
章太炎主持的《正学报》除强调中外信息沟通外,还强调救亡图存下报刊的教化功能。就这一点而言,报刊评论不可忽视,“译报自事实外,多录论议,其亦陈佹诗之意欤。”⑤ 以西报为参照,《正学报》还试图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时事日棘,则词无蕴藉;中外相轧,则语多中伤:西报利病,略尽此矣。由前之说,敢怒观者,而有益救弊,闳识之士,固不欲护美疢、远恶石也。由后之说,乃足以混淆是非,变乱缁素。……今于西报偏激之词,无所指驳,其蜚语中人,荧惑观听者,则必加之案语,力为纠正。”⑥ 论及《正学报》时评要求,章太炎称:“报章录事,史之余裔,旁罗众家,亦其宜也。”[52]针对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章太炎在《正学报缘起》中称:“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武昌,天下中枢也,其地为衢国,声闻四达,于中古则称周南,惟苍姬之王,尝斡运之以为风始。冀就其疆域,求所以正心术、止流说者,使人人知古今之故,得以涵泳圣涯,化其颛蒙而成其恳侧,于事为便。惟夫上说下教,古者职之掸人,而今为报章之属。”[53]文中所谓武昌为两湖之交通中枢,正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其幕府的扎根之地。在章太炎等看来,中国诸多问题皆由“学不正”而致,“今为是报,益使孤陋者不囿于见闻以阻新政,而颖异之士,亦由是可以无遁于邪也。”[54]总之,国学人物章太炎主持的《正学报》办报旨趣在于“新政”,也即试图从政统方面对晚清政治进行学理的探讨的同时,尤强调维新舆论的引导。章太炎与张之洞,皆属国故派重要人物。针对张之洞著《劝学篇》有所谓“忠爱”之议,作为幕宾的章太炎发表议论却称:“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55]张、章分歧可见。道不同,不相谋,道统上的歧见,促使近代著名报人章太炎离开张之洞幕府。可见,面对中西文化会通语境中的政治变革,作为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与作为国学精英的章太炎出于谋生的需要,可能一时迎合或批判某个幕主的言论立场,但在道统这一根本学理上他们仍然坚持自我。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学理最终决定了他们与幕府等利益集团关系上的离合。
甲午战后的中国面临政治舆论转向,舆论精英多相机而动,类似章太炎等奔走幕府间并在言论阵地颇有影响的国学人物,尚有很多,诸如前文述及的宋恕。就学缘关系而言,宋恕与章太炎同师俞樾,[56]属江浙文化精英。1897年,宋恕在林乐知寓所结识蔡尔康,蔡尔康遂将宋恕上李鸿章书,交《万国公报》[57]发表。再加上印行《六斋卑议》,宋恕由此声名大振。1899年9月23日宋恕致梁启超信称自己早些时候怀疑康有为与清流人物张之洞、黄体芳相互勾结之后,说:“余杭经学文章,今日江浙实无其敌,君于不通已极之岸贾,尚以大度登其大谬之《驳〈辟韩〉》,而不肯登余杭之作,仆时则益疑君非正人。”[58]余杭指章太炎,前文述及《辟韩》是严复所作,《驳〈辟韩〉》可能是张之洞授意屠守仁所为。作为舆论精英的宋恕在维新运动中基本支持幕主李鸿章,其反对张之洞及其幕府是顺理成章的。鉴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强学会拒绝李鸿章却接受张之洞的资助,再加上他对康有为倡导今文经学的不满,宋恕遂拒绝入会。而与宋恕同门的章太炎,因对康有为所谓“孔子改制”的今文经学做法颇有意见,且被康门弟子殴打并逐出《时务报》报馆,后又被张之洞亲信梁鼎芬之流赶出幕府。同病相怜的师兄弟遂共编《经世报》,欲与《时务报》一逐高低。宋恕亦注意结交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中一些舆论精英,他写信给李鸿章所代表的北洋派系中重要骨干及《国闻报》创始人王修植,鼓励他要“明佛道”并倡导变法,以便在维新舆论媒介建构中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
总体而言,作为幕府等军政利益集团代表的舆论精英在维新变革的社会舆论动员中积极利用报刊等陈说自己的高见。只不过有留学经历的幕宾多以西方当下的政治制度为借鉴,而有国学背景的幕宾多以本土历史经验为参照。无论是李鸿章幕府代表严复、宋恕、王修植,还是张之洞幕府代表章太炎、汪康年、叶瀚,他们的论说在舆论中的价值取向,有意或无意地促进了甲午战后政治舆论的转向。
四、结语
幕府是古代中国官僚制度的补充,多与中央集权相呼应,某种意义上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幕府常为专制政权弱化下社会秩序的维系与运转提供支持。幕府肇始于战国,两汉至五代,召幕兴盛。宋代以后各朝,注重中央集权,幕府式微。明清之际,中央政权在统治秩序上失范,幕府势力复兴。晚清李鸿章、张之洞幕府属军政利益集团,众多知识分子投身其间。[59]随着政局的变迁,处在权力场域中的知识分子与李、张的联系也或强或弱。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政治舆论发生转向。舆论精英不仅仅参与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亦参与维新变法的运动。其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是传播者政治言论的出发点及归宿。中国文化精英被迫审视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地位,认识到大国地位及形象的取得还须参与世界意义上的民族竞争,社会舆论发生转向。即中国首先要面对世界,在世界格局变迁的政治语境中进行自我身份的定位。就价值观而言,一直与天朝大国相匹配的传统的政统、道统意识也要自我反省。中华民族自我反省意识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往往与时代精英及舆论精英的变革思维所达到的深度基本一致。他们在政统、道统上抉择的本身足以表明媒介意义上的舆论精英面对保国、保种、保教等既有的救世框架的反思,也表明了他们面对西方的政统的冲击,试图从舆论动员层面对变革本土传统的道统做些努力。中国社会舆论呈现多样化,已不仅仅是包括幕主、幕宾在内的舆论精英全权掌控舆论的时代。近代意义上的报刊使得普通知识分子亦广泛参与社会矛盾评判并形成舆论。出身幕府的诸多舆论精英的作用在于舆论引导中常根据本军政利益集团核心人物的意见,发掘媒介沟通、协调社会各种意见的功能。
晚清幕府在社会舆论中的价值取向,亦与幕主、幕宾的学养大体一致。⑦ 幕宾占领言论阵地,从事舆论的媒介建构,或以近代意义上报刊这一新媒介为言论工具,表达自己对政局独立的评判;或是幕主给他们的职业定位即从事信息传播,诸如张之洞对幕宾章太炎就是这样职业定位。而汪康年任《时务报》经理的同时,仍在张之洞幕府代表的军政利益集团中兼职。维新运动期间,居两湖地区的张之洞借《时务报》对维新舆论予以遥控。后光绪下令改《时务报》为官报,张之洞终站出来维护汪康年,也可见张之洞幕府在晚清舆论中扮演的角色。相比较而言,幕宾以业余兼职的身份从事报业,与幕主分歧的诸多知识分子对张之洞、李鸿章亦有看法,本着传承中国传统的“立言”的人文角色看待报刊,投身舆论场域,利用报刊发表对时局的高见,与幕宾受幕主指派而成职业化报人显然不同。后者作为舆论精英,显然要为本幕府说话,也即在舆论场域中是本幕府的喉舌。
探究甲午战后中国历史可见,晚清幕府吸引力蕴含着幕宾谋生的经济利益诉求,作为知识分子的幕宾,多为近代幕府的舆论精英或文化灵魂。但这并不代表幕宾与幕主始终在政统、道统上保持一致。作为舆论精英的知识分子在面临政治与学理抉择两难时,学术良知往往决定他们放弃谋生需要而投靠某个利益集团的逐利动机,从而坚持学术个性上的自我。他们常以办报为职志,传承中国文人论政的基本言路。从中可解读学人与幕府离合关系最终取决于各自的学术立场。时过境迁,幕府早已成历史陈迹,幕宾谋生的经济利益诉求亦不复存在。但在中西文化会通的语境中面对社会转型中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利用传媒协调社会变革中政统、道统的内在紧张,这一课题仍值得探索。
收稿日期:2009-09-14
注释:
① 从个人与幕府关系出发解读严复著《辟韩》的旨趣,王宪明已有成果,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刘桂生在《戌变法史述论稿》序言中称:“严复在李鸿章、张之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严著解读密码”,这一提示性研究思路无疑具有启发性;笔者亦曾发表《严复与晚清幕府》,见《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
② “英人既有举官之权,若不知国事何能措理,若不观新闻纸何能知国事,则新闻纸者,诚民间所不可少者也。”见《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③ 张之洞致总署、天津李中堂电称:“查该教士屡向洞言,亦与致北洋电同,既奉旨一试,当即约该教士来宁详问,语多闪烁,除最谬之语驳斥不论外,大意言此时惟有恳英助中国方能支持。”在张之洞看来,李提摩太等所言,“皆系悬揣之词,总归于以利益与英,则英可助中国胁和。”参见《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④ 1898年2月章太炎称:“戊戌正月上是书,其三月,威海割界英吉利,已亥十月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3页。
⑤ 佹:乖戾。《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0页。
⑥ 疢:疾病。缁素:黑白。《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0-61页。
⑦ 李鸿章重西学洋务,其幕宾多重视英、美为代表的西学;张之洞重国学经世,其幕宾多偏好日本为代表的“东学”。李、张都不排斥对外学习,两者在以洋务促社会变革方面并无区别。
标签:李鸿章论文; 张之洞论文; 章太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幕府论文; 晚清论文; 甲午年论文; 严复论文; 时务报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万国公报论文; 北洋水师论文; 幕府论文; 精英集团论文; 媒介经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