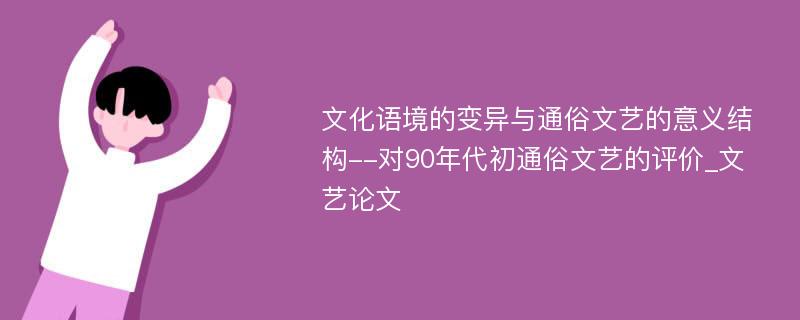
文化语境与通俗文艺意义结构的变异——90年代初期通俗文艺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文艺论文,语境论文,初期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关于文化市场
文化市场的形成和通俗文艺的兴起,构成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就一般意义而言,把文艺走向商品化视为灾难,认为文化市场只能产生毫无个性、粗劣低下的产品多少是过于简单化的断言。
文化市场总是存在着两种驱力的互相制约:为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讲究划一、模式化制作的驱力,和为不断地吸引公众的注意追求创新、独异的驱力。文化市场的规律就是在划一与个性化,程式与创新之间冲突和摇摆。就消费大众而言,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冲动:迎合时尚的冲动和追求个性化的冲动。这使得文化市场在其运作过程中受到双重机制的制约:一种是审美规律的潜在制约,另一种是市场规律的显在制约。脱离历史情境,抽象地谈论文化市场的优劣,很难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商品化是社会进步和文艺自身具有积极意义的变革的表现。在欧洲,大约十八世纪前后,伴随着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兴起,文艺经历着从宫廷的文艺到商品的文艺,由服务于宫廷和教会到服务于读者大众的转变。在此之前,一些有才华的文艺家为宫廷或教会所收容,这些艺术家从宫廷或教会那里领取津贴,并按照宫廷的意旨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了与民间艺术迥异的、体现宫廷趣味的高雅文艺,法国古典主义文艺就是由这样一些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艺术的商品化与市民阶层反封建,反教会,要求平等和自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将艺术视为商品这一观念本身,相对于把艺术视为贵族阶层的专利而言就富有挑战意味。正如利奥塔所说“叙事(通俗)文化重获尊严,它已表现在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各种启蒙思想体系之中,譬如狂飙突进运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法国历史学派。叙事不再是合法化过程中偶然的失误。在知识困境中转向叙事求助的明显趋势,是与资产阶级要求从传统权威下争取解放的潮流同时发生的”。①
这使得欧洲文艺走向商品化的进程从总体趋向来说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明清通俗小说最初两个流派(神魔小说和讲史演义)的形成,首先应归根于集市井气和铜臭于一身的书坊老板。书坊主以牟利为目的,但客观上无疑促进了通俗小说的传播和发展。尚友堂主人刻印《拍案惊奇》其驱动力正如凌蒙初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是眼红冯梦龙“三言”的“行世颇捷”。冯梦龙撰写“三言”,也是“因贾人之请”。通俗小说作为商品的属性,也离不开商品供求法则的规律,它调节着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当供不应求时,书坊就采取种种措施刺激作者满足读者的需要。如明末魏忠贤败亡后,人们渴望读到揭露魏党劣迹的作品,书坊觅人撰写并赶印《警世阴阳梦》。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曾以清新的风格和情节的曲折受到欢迎。但,当这类题材过滥而为读者所厌烦后,书坊也便停止收购此类书稿,迫使作者改变题材,于是,时事小说兴起。②
2.“自主的”文艺
新时期初,走向商品化的文艺也同样面临着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相近的文化背景:文艺由“四人帮”文化专制时代为政治服务,文艺家必须按照“领导出思想,群众出智慧,作者出技巧”的创作模式去形象地演绎特定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到转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适合大众的文化需求而创作。在当代中国,商业化文艺即隐含着将对文艺的裁决权转向读者大众手中。阿多尔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论及世界范围的通俗文艺的勃兴的缘由“轻松的艺术总是伴随着自主这个影子。它反映出社会上没有严肃认真的信念。这种轻松的艺术是缺乏真实的社会前提的作品。”③在当代中国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新时期以来,文化市场、通俗文艺的迅速勃兴,隐含的是对“文革”时期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强烈反拨。新时期初以“软性”为基本特征(强调抒情性),个性化阅读和传唱以及表演方式的革新(如流行歌曲演唱中的手拿话筒,吸气唱法、在舞台上边走边唱),都是对“文革”文艺政治化、公式化、群体化的反叛。在当时,谈论娱乐和消遣本身就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以至于一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庸的娱乐性作品如香港喜剧故事片《三笑》在当时都引起观众的情绪上的激动。新时期初围绕着邓丽君的歌曲、李谷一的《三峡传说》、娱乐片《庐山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公众是否有权利自由选择消遣娱乐方式的论争。
在新时期初,通俗文艺与严肃文艺有着相近的精神内涵。当张洁、舒婷叙述爱情故事仍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时,港台言情小说大规模的爱情叙事,无疑有助于确立爱情在个体生活领域中的位置。对新时期初的大陆年青读者来说,早期传入的琼瑶、三毛等港台作品不仅提供了理想的爱情模式,还提供了由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理想状态:拥有工业文明带来的一切物质成果,也保留了农业社会的诗意(精神的、语言的)和温情,对痛感文化专制时代物质贫困、精神匮乏,正步入商业化社会的大陆青年来说这类作品无疑具有某种文化模仿的意义。在人物性格结构方式上,新时期初严肃文艺与同时期流行的通俗文艺也有相近的特点,即在善与恶、忠与奸、美与丑、崇高与卑下……这些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进行叙事。
新时期初期,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在精神内涵上表现出来的若干相近特征,表明当代文艺在挣脱了“文革”文艺以后,不约而同地向人类母题回归的趋向。美国学者简·派·汤姆金斯在分析了斯托夫人的通俗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后得出结论“19世纪的通俗小说,代表了从妇女的观点重新组织文化的努力;这些作品无论在智力的复杂程度上,雄心上和机智上都很杰出。”④通俗文艺这种“重新组织文化的努力”其特点不是通过个体的创造性行为,而是通过群体性的表达来实现。当代中国通俗文艺的兴起也可作如是观,它表达的是新兴的市民阶层在文化上的要求和牟求话语权利的欲望。
在当代通俗文艺中,最基本的两大主题,是爱的主题(母爱,情爱)和惩恶扬善的主题。在当代商业社会,这两类题材如此兴盛,表明在旧有的理想大厦倒塌以后,市民阶层试图以他们所能接受的社会和人生模式填塞空缺的理想,这种理想的社会和人生总是体现为强烈的世俗化的特点,不仅是市民形象如此,历史人物也在被市民观念所整合。新时期汗牛充栋般的人物传记,都共同对各种历史名人进行世俗化的处理(如《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尽量淡化其意识形态性。不仅共产党人在历史年代的英勇业迹是这些传记文学的基本内容,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日业绩也同样是传记文学的表现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俗文化也成为市民阶层的狂欢节。在摇滚乐、迪斯科以及其他流行音乐中,在各种体育竞赛中,市民阶层渲泄着被压抑的情绪,在想象中获得自由的欣悦。这一切如同巴赫金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谈到中世纪市民阶层的狂欢节时所说的,狂欢节不同于仪式典礼,它不是由某个特权阶级来组织,而是依据市民阶层自己的规则,“狂欢节不是一个为人们所观看的场景;人们就生活在其中,所有人都参加进来,因为狂欢节的概念囊括了所有人”。“在狂欢节期间,生活只从属于它的法则,……它的自由的法则”。它是“特殊形式的生活”,一种现实的杂语现象,是社会组织的一道裂缝。通过狂欢节市民摆脱了诸如“永恒的”,“不可变动的”,“绝对的”,等一切“阴郁范畴”,而“面对着世界快乐和自由的笑的一面,连同其未完成的和开放的性质,连同变化和新生的快乐”。⑤
市民阶层通过通俗文艺塑造着理想的人格偶象。1993年3月,南京市有关部门举行“当代青年心目中十大青年偶象”评选活动,其中九位是港台歌星。《北京青年报》的读者评选了1992年10大当红人物,依次是:巩俐、葛优、施拉普纳、王朔、奥运明星、张艺谋、陈章良、侯跃华、崔健、张淳和吕丽萍。⑥青年偶象由雷锋、陈景润到向各种明星的转化,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表明公众理想的人格楷模由政治型、知识型向经济娱乐型的转变。这种转化的过程是公众由接受政治权威塑造的理想人格,到接受精英知识分子塑造的理想人格,再到按照市民阶层自身的文化要求塑造自身理想的人格形象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通俗文艺将商业化目的和人的主体性要求同时接纳其中,使这时期通俗文艺成为最具有蕴育性,也最具有活力的艺术样式。崔健的摇滚乐可以视为国内生产的通俗文艺的优秀代表。《一无所有》不仅是对物质匮乏的痛切感受,更是精神匮乏的愤懑。《一块红布》则表明与一个时代的断然诀别。崔健将市民阶层在商品观念席卷一切的大背景下,急于自我拯救又无路可寻的焦虑与惊心动魄的摇滚乐节奏达到了完美的融合,现实感和历史感也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柯林伍德曾将娱乐型艺术与纯粹的艺术(他指的是表现型艺术)作了这样的区分“如果一件制造品的设计意在激起一种情感,并且不想使这种情感释放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之中,而要作为本身有价值的某种东西加以享受,那么,这种制造品的功能就在于娱乐和消遣”。⑦如果这种区分娱乐型文艺与纯文艺的标准成立的话,那么,新时期初、中期众多的通俗文艺显然不属于柯林伍德所说的那种纯粹的娱乐型艺术。它们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事务”紧密相连,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3.文化语境与通俗文艺的转型
这种情形到了九十年代前后有了明显的改变。市民阶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由社会的边缘化状态进入社会结构的权力中心,被合法化的通俗文艺在现代科技的装备下,在公众文化生活中的主导的位置日益稳固。早期的通俗文艺的那种生气勃勃的景象也在消褪,人为的轰动则越来越明显。无论是被称为“后摇滚”,还是“留学生文学”“汪国真热”,“王朔热”均不同程度地表明这一点。
出现这种局面无疑与被阿多诺称为“文化工业”的生产和销售系统的文化市场的作用力密切相关。以文化工业⑧为生产方式的文化市场具有极强的再生产能力。一种文化消费样式一旦被文化市场所认可,就会迅速遍及全国,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而且各种仿作(包括被其它艺术样式改编)也会成批地出现,直到彻底地耗尽读者的热情为止。阿多尔诺对此的评价是,在“文化工业”时代,任何“达到个性化的最终努力,最终都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⑨
新时期初期,曾给大陆人清新之感的港台文艺(包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流行歌曲)已蜕化为对固定的爱情模式、音乐旋律的自我转述。崔健也已陷入自身的重复。而新的文化热点总是以批量生产方式被推向市场。《北京人在纽约》赢得读者以后,同类题材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渥太华的中国女人》、《中国姑娘在东京》、《巴黎不是梦》,等“留学生文学”达10余种之多。《红太阳》音带上市一举成功后,数十种“文革”和建国前十七年歌曲音带先后被推向市场。
90年代通俗文艺常常是形式的轰动盖过内容本身,文化市场触目可见的是轰轰烈烈的广告宣传攻势(包括出版社与报刊联手进行的图书促销,和流行歌手演唱会为增加票房收入进行的广告宣传)与并无多少创新的文艺活动之间的强烈反差。追求形式本身的震惊效果成为时尚:各种文艺晚会上令人眩目的布景和灯光,夸张的宣传和充斥于文艺作品中的刺激性的描写(这类作品大量地陈列在摊头文艺中),被称为“后摇滚”的夸张的动作,怪异的妆饰(如“黑豹”乐队全部是1.90米的个头,一律黑发披肩)均属此列。一些探索性文艺也热衷于此。(如1990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高悬避孕套,枪击行为等),桑塔格在评价一些模仿黑色幽默作家的剧本时说,这些“作品的毛病不在于怪异,性变异,或类似事物,而在于虚伪而浮浅地使用这种素材。变态的情景未得到真正的剖析。毋宁说,这种场面被用来作为震惊观众的常规手段……艺术中唯一真正惊人的,是形式上的惊人之举,……(是)对观众发起一种真正的感官上的进攻。”⑩
通俗文艺活力的消褪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源于时代的剧烈的变动。80年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拉开了富贫之间的差距,阶层化日趋明显。新时期初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乐观、轻松的气氛逐渐丧失,而代之以生存境遇的危机感,和把握现实的无力感。经历了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这种情绪被进一步强化了,这形成90年代独有的文化现象:致富的欲望和热情势头不减,非理性主义情绪也普遍弥漫,一方面,以构筑发财梦的为主要内容的海外文学,一时成为最畅销的品种,另一方面以表达无奈、无聊感为基本特征的灰色文化和怀旧题材盛行一时。
《红太阳》音带的流行则典型地表达了90年代的情绪意向。1992年元旦至春节,《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音带借助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契机,在音像市场迅速走红,一时间,《红太阳》旋律遍及大江南北。《红太阳》音带中选收的“文革”时期广为流传的歌曲,如今配上新式的轻摇滚旋律,采用电子合成乐器和民乐器,整卷音带融成一气呵成的轻摇滚大联唱。这种加上新型包装的“旧曲新唱”使老年人怀旧,中年人熟悉,青年人新奇,立刻受到广泛的欢迎。人们从《红太阳》的旋律中咀嚼着一度被遗忘的历史,那是一个荒谬却也充满激情和理想、一个极度贫穷却怡然自得、一个封闭却也没有失落感的时代。今天当人们告别荒谬、贫穷和封闭后,他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同时告别的理想(尽管是愚昧的)、怡然自得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认人眷恋。
在另一些文艺类别中(如众多的相声小品),则是以幽默、调侃、粗鄙化的对白和表演来掩饰这种无聊和无奈。摇滚乐中“后崔健”以嘲弄和玩世的态度取代了崔健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参予感:
我们生活的地方,/象一个垃圾场/人们象虫子一样/你争我抢/吃的是良心/拉的是思想……/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个屠宰场/只要你知道肮脏/你已够斤够两。《垃圾场》
我就在大地方,/我就在小角落。/这里面没有什么谁比谁厉害,/我就那么兴奋,/我就那么嚎啕,/这里面没有什么谁比谁学问,/我如今就是我,/你现在就是你……/哦——/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实际上没什么》。
中国通俗文艺本来有着丰厚的传统,传统的通俗文艺大致在唐宋以后伴随着商业化的发达而逐渐成熟。其思想倾向以惩恶扬善为主调,包括保障个体生存权,以及在不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前提下个性的一定程度的实现(主要是情欲、功名的满足),即使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也总是夹杂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五四以后,当一批接受西学的作家开始用现代意识和表达技巧改造传统严肃文艺时,一批通俗文艺家也在试图对通俗文艺进行变革。通俗文艺开始以某种新的姿态出现,惩恶扬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才子佳人模式有了新一层的含义,批判现实的意味有所增强。封建意识则被稀释了,这些被人们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以及后来的新武侠小说在当时赢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后来,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通俗文艺发展的势头被遏止。新中国成立后,这类文艺大都被作为封建文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很长时间里,通俗文艺失去了其生成、发展的社会条件。
新时期以后,市民阶层的迅速扩大、现代化传播媒介的日趋完备与通俗文艺的贫乏构成巨大反差,市民阶层急切渴求文化上的满足。起初,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只能顺应着改革开放所能提供的条件选择适合市民阶层品味的艺术。然而,在当时,所谓选择实际几乎无可选择,他们只能通过其情感记忆,从建国17年中抉取一些具有抒情味的歌曲,这就是《洪湖水浪打浪》等一批文革前流行歌曲再度流行的原因。这些歌曲的流行与其说是表达人们对前17年的眷恋情绪,不如说是反映了文化选择上的窘态。再者就是发掘传统艺术。文革中被斥之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遭禁闭的传统戏曲重新登上舞台。这些传统艺术从整体上说并不是严格意义的通俗文艺,它需要欣赏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接受背景和审美经验,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既缺乏欣赏西方艺术的修养,也缺乏传统艺术的熏陶,大多数市民对传统艺术感到相当隔膜,另外,隔膜也源于传统艺术所表现的生活与当代社会的距离感。当代通俗文艺只是在域外通俗文艺涌入后才开始步入正轨。域外的影响首先来自港台。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星的音带的涌入,给市民阶层以相当持久的震撼力和审美愉悦,大陆的市民阶层只是从这时方才意识到通俗文艺应有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魔力。
这些最初引进的外来文艺大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它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大陆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也较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假象,因为,上述作品的流行,与政府管理部门和知识分子引导密切相关,(我们当然也不可忽视这些通俗文艺反映的生活,表达的情绪与大陆有相同的或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无疑是其流行的一个原因)。
和严肃文艺一样,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一种通俗文艺式样的流行,总是顺应着其自身的生成规律,它构成通俗文艺自身日日常新,不间断地演变,受众也在这种不断翻新的艺术熏陶下,不知不觉地沿着既成的艺术趣味的背景去选择、塑造新的艺术家。但是,新时期通俗文艺发展由于缺乏历史的继承性,其文化传统是中断的;就受众方面来说,他们缺乏正常的通俗文艺的熏陶。他们的文化饥渴,其深层是一种精神饥渴。所谓“精神饥渴”,指闲暇时间无可打发的一种状态。精神饥渴感源于被束缚的心理及至生理在突然解除束缚后产生的情感满足需要。在正常生成的文化环境下,这种情感满足需要更多地是通过被社会所接受的,自然生成的文化形式来排遣,但是,对于缺乏这种自然生成的文化背景的当代市民阶层,他们尚不习惯于把这种情感需求通过艺术的方式加以排遣,而只能寻求满足情感需要的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当文化政策趋于宽松以后,大量的粗劣的通俗文艺便占据着文化市场。形成了一段时期里通俗文艺的行进过程不是走向雅化,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走向劣化。它与文艺正常发展规律相悖,却符合市民阶层的心理趋向。通俗文艺的正常生成规律被打断后,在历史某一阶段必然形成强烈反弹。
4.假性的“缝合”
有评论文章认为,90年代通俗文艺“已经由性/暴力对伦理价值的冲击,转向了驯良而温和的感伤的絮语”“商业性/伦理价值间第一次消解了其冲突和对立,它们成功地缝合在一起了(11)”。
这篇文章敏锐地把握了90年代打上商业化烙印的通俗文学精神内涵上的若干特点,但在对90年代文艺的基本判断上仍然有误差。新时期初与90年代通俗文艺在精神内涵上的区别不在于前者追求破坏,后者追求认同;前者表现“冲突和对立”,后者意在“缝合”。实际上两个时期的文艺所表达的对现实的基本态度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前者旨在通过对现实的积极的反抗去消除现实的不合理,后者则承认这种不合理的不可改变性而主张逃避。
这种弱者式哲学不过是牟取话语权利的另一种方式。这时期通俗文艺实际上勾划了与现实状态相对立的另一种的人生图景,这种人生图景隐晦表达的仍然是对现实的拒斥。一种犬儒式的消极的反抗。
以汪国真的诗为例。在精神内涵上,汪国真既抛弃了朦胧诗叛逆的、充满悲剧色彩的精神人格,也不取一些“第三代”诗人把现实视为无意义的“他者”的冷漠态度,强调进取是汪诗的基本格调。在艺术上,汪国真彻底摈弃了“朦胧诗”以来诗歌的“试验性”和“先锋性”回到浪漫主义审美经验上,清除一切可能给阅读带来阻遏的语言和审美方面的障碍,甚至清除一切“陌生化”的意象和语言组合,以口语化的语言,顺向连续性的思维方式,缀之以人们熟悉的象征意象和平浅哲理,使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迅速地体味诗的意旨,并在与既定的阅读经验的似曾相识的感受中寻觅乐趣。
《渴望》试图通过刘慧芳形象的塑造,确立市民社会理想的道德价值体系,即集真善美于一身和无私奉献。在剧中,刘慧芳被想象性地寄托了一种理想化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为痛感商品时代日益冷漠的人际关系的市民社会提供安慰之源。但是,《渴望》又让刘慧芳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碰壁,让这个好人“倒霉倒到家”。刘慧芳性格的完美性与她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遇到阻隔和尴尬构成深刻的矛盾,使这个形象实际丧失了在现实中的可摹仿性。它提供了人们面对历史与必然的一种方法,至少是一种可以自我说服的逃避方法。其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于虽然那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它可以把历史与必然所呈现的真正的矛盾蒙蔽住,让人们相信一切都还好。《渴望》有意让刘慧芳“倒霉”,强化了自我说服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对形象的乌托邦色彩的错误的认识产生冲突,而消解了形象的意义。
与《渴望》不同,《编辑部的故事》摆出否定既定话语体系的姿态。《编》剧选择的都是一些人们普遍关切的社会性话题,如假冒伪劣产品问题,夫妻离异问题,保姆的职业道德问题,这些话题本身包含了可能产生的对社会的否定力量。《编》剧经常对正统观念,政治化人物(如牛大姐)、流行的政治语言给予十分辛辣的嘲讽,揭露其空洞、背时和虚假。但,《编》剧中的这些社会话题最终并不引向对社会机制的怀疑和反抗,以否定既存的社会话语的合法性,也并不是借助于这种社会性话语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法律手段、思想教育等),而是通过矛盾的自行解决的方式(如制造伪劣产品厂家的良心发现,闹离婚的夫妻言归于好等)。这意味着《编》剧也并不承认现存的社会性话语的权威性,而是将这套话语“搁置”起来,用既不是与现存的社会性话语相对抗,也不是与之相认同的第三种话语——市民话语统摄全剧。但是,在《编》剧中,市民话语本身也并无稳定的、统一的内涵,并无统一的、稳定的价值标准,因此,《编》剧一方面将剧中所有的人都驱赶到“俗人”的行列,又对“俗人”加以戏谑和嘲讽。《编》剧的风格特点正是戏谑和嘲讽,它指向一切意义结构,包括自身。拉康认为,故事源于“匮乏”,“故事中必定有某种事物丧失或者不在,这样叙述才能展开”。《编》剧匮乏的就是统一的话语,这也形成《编》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杂语化。《编》剧通过将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交错和杂糅,以及这两种东西的最终转换,赋予了这部作品真正的魅力。
《北京人在纽约》塑造了一个呼应着新时期初乔厂长(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式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英雄——王启明,但两者在精神品格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王启明身上聚合着各种欲望(发财的冲动,维护自尊的冲动、性的欲动)。唯独没有乔厂长把个人价值实现与民族现代化的宏伟叙事相联结的冲动。这正显示了市场经济时代与新时期初的深刻差别。确定性追求的丧失,使王启明使用着各种话语:既能够熟练地使用北京市井鄙俗的话语,也能够调侃地使用“文革”语汇,具有商人兼赌徒的心理和头脑,又有着曾经作为一个大提琴手的艺术家的情趣。既能够迅速顺应最现代性的西方商业社会的文化情境,又深深留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既能潇洒地选择成功之路,又潇洒地承受失败的厄运。王启明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化混杂的象征。
注释:
① 利奥塔《后现代:关于知识的报告》,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P31
② 参见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上海文论》,1991年第4期
③ 《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1年7月版,P127
④ 简·派·汤姆金斯《感伤的力量——〈汤姆叔叔的小屋〉与文学史的策略》,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10月版,P477—478
⑤ 参见[美]凯特林娜·克拉克 迈克尔·霍奎金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P358-388
⑥ 《你还是想王朔》,《工人日报》,1993.2.24
⑦ [英]罗宾·乔治·柯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P80
⑧ “文化工业”的概念是由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一节中提出的。指晚期资本主义商业文化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的大众娱乐文化体系。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文化垄断下,一切大众文化都变成了同一的、标准化的商品的混合体,它是以一种满足公众需要、“个性化”的姿态,完成操纵与控制大众文化需求的文化生产程序。因此,文化工业在本质上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启蒙辩证法》,P158
⑨ 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P101
⑩ 张颐武《后新时期小说:转型时期的表征》,《生命游戏的水圜》(理论批评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
(11) 参见黎慧《欲望·代码·升华——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上海文论》,19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