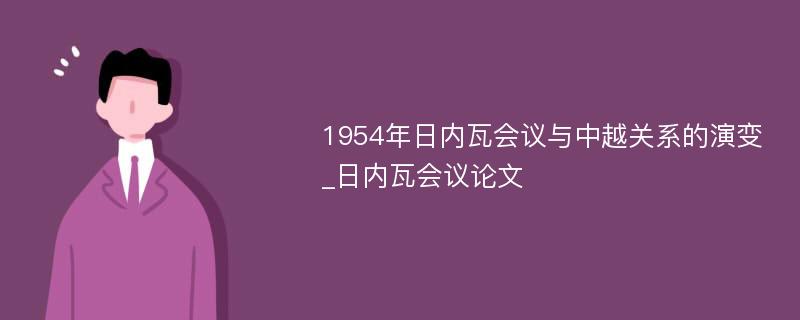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中越关系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内瓦论文,中越论文,关系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3)04-0014-13
1954年4月至7月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其对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以及中越关系的走向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此次会议的文献资料,问世最早的当属中国方面于1954年出版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①。之后,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②、《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③相继出版。但所有这些资料,其内容多为代表提案、发言和会议公报等当时即已公开的文件,有关中苏越等国在日内瓦会议中决策过程等内容的重要文件并没有予以披露。在日内瓦会议后,法国及英国方面也相继出版了此次会议的相关文件集及白皮书④。美国方面,负责出版美国官方文件的美国政府出版社也先后于1960年和1971年出版了美国国务院⑤及五角大楼⑥的相关解密文件。1981年,美国国务院又解密出版了《美国对外关系——日内瓦会议卷》⑦,不但涵盖了各国早已公开的文件,而且又增加了一大批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相关文件。其中,尤属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及国务院政策设计室的解密文件,最为引人注目。至此,美国方面已基本解密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全部文件。
在冷战期间,由于资料的相对匮乏,学者研究的著述较少。西方学者的著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69年出版的罗伯特·兰德尔的《日内瓦1954》⑧与菲利普·德维利埃、让·拉库蒂尔合著的《战争的结束:印度支那1954》⑨。同一时期,由于受各种原因的限制,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一直未予公开,相关研究也基本没有进展。冷战结束后,中国方面的资料公布、整理情况出现了重大进展,一大批有价值的档案相继解密。其中,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下卷)与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均有章节专门涉及该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于2004年至2008年分批分次陆续公开了1949~1965年间的81751件外交档案。其中有许多档案涉及日内瓦会议。在这些档案公布后不久,外交部档案馆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档案编辑成册,予以出版。⑩这些档案材料的公开和汇编出版,全面、系统地公布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中方档案材料,进一步便利了本选题的研究。
同一时期,伴随着前苏联、越南等国档案文件的陆续解密,涉及本选题的一批外文档案材料被公诸于众。其中,由前苏联解密、并被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翻译成英文公布的系列档案文件,成为研究当代中越关系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在档案材料不断解密的基础上,海内外对于日内瓦会议的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11)海内外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日内瓦会议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据笔者目力所及,学者们很少对涉及日内瓦会议的地缘政治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因此,本文不揣浅薄,拟以上述重要档案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地缘政治学的相关理论,阐述各国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地缘政治考量及由此而引发的中越关系的嬗变。
一、日内瓦会议前各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与中国会议策略的制订
1953年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整个国际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54年1月,四国外长会议决定,4月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苏、美、法、英四国达成一致后,中国、越南等相关国家也先后表示愿意参加,并开始为此次会议的召开进行积极的准备。但是,由于各相关国家各自地缘处境及地缘观的差异,各国对印度支那和平的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考虑,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预期。
(一)各国的地缘政治考量
对美国而言,东南亚地区是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正如对当时美国政策制订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所说,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对我们安全的威胁,每次都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眼看要被一个单独的强国所统治。”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防止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被一个大国单独统治,并“防止旧世界几个实力中心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利益。”(12)对于美国而言,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地区正处于这一重要的边缘地带。这一地区不但是连接东西世界的重要枢纽,而且是美国等“海上势力”进入欧亚大陆与“陆上势力”抗衡的重要通道。因此,在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控制与影响力之后,美国必须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渗透,防止共产主义中国“服从苏联的指挥,向其邻国入侵”(13)。基于上述考虑,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放弃了之前对中国实行的“拉拢”与“试探性”政策,开始谋求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地区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蔓延”。
相比美国对印支地区的明确态度,英国对该地区的态度则较为复杂。一方面,出于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固有恐惧和对稳定东南亚地区局势、保证英国远东特别是香港、马来亚等地区利益的期盼,英国非常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遏制中国及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渗透。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意过多地刺激中国,从而影响其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担心中共收复香港局面的出现。因此,虽然英国早已于1952年就与美国、法国达成协议,“一旦红色中国入侵东南亚,将导致三国的某种报复行动,这种报复行动不一定局限于遭侵略的地区”(14),但当美国于1954年正式提出“联合行动”的概念,计划直接干涉印支,并对中国进行报复时,英国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相对于英国的矛盾心态,法国的远东政策则比较单一。二战的打击使法国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欧洲都已经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已经无力像英美一样关心“共产主义的渗透与入侵”,也无力在欧洲捍卫资本主义的地位。因此,在深陷于印度支那的战争泥潭时,法国显得更加精疲力尽。它既无力依靠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支持继续战斗下去,更无力联合美英等国对中国或是苏联发起进攻。它所能做的,是通过和平方式尽快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以减少法国在这一区域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最大程度地保留法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并减少其对法国其他殖民地的“骨牌效应”。
1953年3月,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在经历了短暂的权力博弈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新的权力核心。赫鲁晓夫上台后,他对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及未来世界走向都提出了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观点。首先,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在目前国际形势中,没有任何争端是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的。”(15)再者,在革命与战争的关系上,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一定同战争联系在一起……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16)。基于其对苏联地缘政治环境及世界格局的不同考虑,苏联开始迅速改变了斯大林时代所一直坚持的地缘政治思维与策略,强调通过谈判解决美苏分歧,谋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与此同时,由于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在亚洲并没有太多的现实利益。因此,苏联延续了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倚重中共,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对于日内瓦会议的态度大致包括以下两点:一是积极谋求缓和国际局势,防止美国势力借机渗透。二是积极斡旋,利用英美法等国的矛盾,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国地位的实现。(17)
自1945年法国重新占领越南以来,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就一直在领导越南人民进行反抗法国侵略的斗争,并在斗争中积极谋求印度支那和平的实现。因此,在得知日内瓦会议将讨论印支和平问题,并将允许越南民主共和国参会的消息后,越方积极响应,并开始积极地为赴会进行准备。1954年2月26日,越南驻苏联大使阮隆朋即请求苏联指示越南应对日内瓦会议应该采取的行动方针。3月26日,越南又要求苏联向越方提供一些对印支形势的分析材料,以供越南参考。(18)虽然越南热切地希望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但越方大部分领导人对于越南形势的认识却并不清楚,对美国干涉越南革命可能性的认识也非常不足,加之越方一贯具有骄傲轻敌的思想,因此,越南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并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谈判中去,而是积极地准备进一步的革命战争。对于即将来临的日内瓦会议,他们希望通过参加会议而获得更多国家的关注与支持,但又不希望在会议中对法国有任何的妥协。可以说,对于日内瓦会议,他们的态度是犹豫不定的。
(二)中国的地缘政治考虑及会议策略的制订
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面临中国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积极地转变地缘政治思维,并据此制订了日内瓦会议的详细方案。
1、中国外交策略的转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一直坚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在外交中坚决贯彻国际主义原则至上的理念,积极对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及地区进行援助与指导。但是,从1953年开始,这种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对美国外交策略的估计迫使中共改变其外交政策。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战斗。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牺牲与物力消耗。因此,当探知了美国准备直接插手东南亚事务,并不惜与中国交战的外交策略后,中国急欲早日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防止美国以此为借口直接插手印支问题,再出现类似于朝鲜战争的中美兵戎相见。
另一方面,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是近百年来中国人的两大梦想。在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了第一个梦想后,中共即开始着手进行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努力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1953年1月,新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开始。所有这些的实施,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因此,中共中央急切地希望能够早日结束在朝鲜与印度支那的战争局面,使新中国的周边出现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
基于上述考虑,中共中央改变了之前一直坚持的国际主义至上的原则,暂时将民族利益置顶,积极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谋求实现中国的大国地位、恢复印支地区的和平并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2、中国有关日内瓦会议方案的制订
日内瓦会议前,各国有关此次会议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在开赴日内瓦之前,中国代表团根据对各国态度的判断及中国的利益诉求制订了详细的方针和政策。
(1)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恢复印支和平是日内瓦会议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代表团的考虑是,“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即使达不成任何协议,“也要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不致完全中断,形成边谈边打局面,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和法美间的矛盾,而有利于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局势的开展。”(19)
(2)打破对华封锁与禁运,促进与各国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正面临着43个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及禁运,这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无疑是相悖的。因此,中国代表团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则是积极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对华禁运及制裁的联盟中找到并打开缺口,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范围,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20)
(3)利用英美等国的矛盾,防止美国势力进入印支。中国方面意识到,中国在印支地区最危险的敌人是美国,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也来自美国。因此,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即做出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积极利用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促成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将美国势力堵在印支地区之外。
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与中越两国的分歧
1954年4月26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其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是会议的焦点之一。如前所述,中国与越南都非常希望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但是,由于两国对于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并不相同,因此,两国很快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并由此改变了中越关系的走向,亦影响了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一)三国还是一国——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分歧之一
在此次会议中,有关柬埔寨和老挝问题的讨论是会议的焦点之一,也是造成中越两国矛盾的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则源于一个复杂的历史概念:“印度支那联邦”。在历史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是三个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国家。近代以来,由于法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柬埔寨和越南先后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并于1887年被强行合并组成了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1893年,老挝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后,也被并入了“印度支那联邦”。因此,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并不存在,它实际上只是法国殖民者为便于统治三国人民而拼凑起来的一个殖民地联合体。但是,三国的一些革命力量在反抗法国侵略,谋求民族独立的同时却继承了所谓“印度支那联邦”的衣钵。例如,成立于1930年,以越南人为主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单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该党统属的范围并不限于单个国家而是整个的印度支那地区。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正式更名为越南劳动党。但即使在更名后,其党的纲领仍然是积极寻求“在三国民族自愿的原则上,进一步实现独立、自由、富强的越南、寮国(老挝)、高棉(柬埔寨)联邦。”(21)
基于越南劳动党的三国关系定位,劳动党中央积极地谋求革命力量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同时发展,并向两国派出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参与当地革命。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时,老挝抗战部队的1.8万人中有越南军队1.4万人,柬埔寨抗战部队的3000人中有1000多人为越南军队。(22)对于越南向老挝及柬埔寨派出军队一事,英、法、美等国早已掌握了准确的情报。而且,1953年12月,越盟自己的广播电台曾播放过越南志愿部队进入老挝作战的消息。因此,在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当天,法国外长皮杜尔即提出:“一切进入该国的越盟正规军及非正规军均应撤出”(23)。
在英法等国看来,老挝、柬埔寨问题与越南问题截然不同。越南问题是因法国的殖民战争而起,法国撤出军队即可解决越南问题。老挝、柬埔寨问题是因为“寮棉境内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只要越方军队撤退,寮棉问题即可解决。”(24)因此,在随后的会议中,英法等国代表一直坚持这一观点,并强硬地主张柬埔寨、老挝问题应与越南问题分开来处理。对于英法的这一主张,越南代表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既不愿承认在柬埔寨、老挝存在越南军队,也不愿将柬埔寨、老挝问题与越南问题分开处理。一时之间会议陷入僵局。
对于印度支那地区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之初也并不十分清楚。“因为这三个国家当时是一个共产党,是印度支那共产党,总书记是胡志明,所以大家认为都归胡志明管。”(25)因此,中国在一开始全力支持越南关于印度支那联邦的构想。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国代表团越南组在向苏联提供的参考文件中即指出:“在印度支那三国建立起统一的政府之后,他们有权进行磋商,根据三国人民的意愿组建一个印度支那联邦”。(26)在会议召开之后,中国代表团依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支持越南代表团的提案:不承认两国存在越南军队,同时反对将柬埔寨、老挝问题与越南问题分开处理。(27)
但是,在经过认真调查和周密思考后,周恩来逐渐发现,“印度支那三个成员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是非常显明而严格的。这种界限在法国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三国人民当中也是如此看待的。”因此,“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印度支那三国。(28)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日趋强硬:6月11日,会议主席、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会议发言中特别强调:“老、柬两国被越盟侵略正如捷克之被希特勒侵略”,“除非我们缩小分歧不再迟延,否则我们的任务就要失败”。(29)6月12日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当天,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法国政局混乱,法国代表团团长皮杜尔立即离开日内瓦返回了巴黎,美国则企图利用法国政局混乱之时中断会议,日内瓦会议面临夭折的危险。(30)
基于对印度支那地区三国关系新的认识,同时出于挽救会议危局的考虑,中国开始改变其在日内瓦会议中对越南志愿军及三国关系定位的态度,与苏联及越南代表共同谋求越南志愿军的撤出及三国问题的分别讨论。6月13日,中、苏、越三方代表商谈决定:“三国应相约互相尊重独立、统一和国内制度。……关于高棉和柬国问题,坚持必须予以具体讨论……争取双方司令部首席代表在此地并在当地直接谈判高、寮的停火问题。”(31)6月15日,周恩来在与苏、越代表团紧急磋商对策时进一步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我方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应按已定方针有所让步,以使会议继续下去,求得达成协议的途径。”因此,“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求得补偿。”(32)对此,莫洛托夫立即表示赞同,范文同经过反复考虑后也表示同意。按照中苏越三国的商定,周恩来于6月16日中午与艾登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不仅承认有越南人民军部队在老挝活动,而且表示,在老挝的越南人民军也是外国军队,也会撤退。”(33)同时,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像印度那样的东南亚型的国家,我们愿意同它们和平共处,这样对法国、英国也是有利的。(34)通过周恩来的讲述,艾登开始相信,“中国在柬埔寨和老挝并没有野心。这两个国家会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部武装力量存在于其领土之上的中立国家。”(35)因此,听完周恩来的新方案后,艾登连声表示: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英国的要求也正是这些。(36)当天下午,周恩来与范文同分别就军事及政治议题进行发言。虽然二人都没有明确提出自老挝和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的问题,但由于周恩来在会前已向艾登通报了中苏越三国的态度变化,与会各方也都已经知道。因此,会议气氛大为缓和,会谈破裂的危险也终于过去了。
6月18日,范文同更加明确地表示:“过去曾有越南人的志愿军在柬埔寨和老挝作战,但这些军队已经撤出该两国。如果现在还有这些部队自然也应撤出。”(37)在范文同对该问题明确表态后,有关老挝、柬埔寨问题的最大障碍已经得到解决。6月19日,与会各方对此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军事代表开始就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进行直接谈判。
有关越南在柬埔寨、老挝有无军队的问题是日内瓦会议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越南代表团最终放弃了其一直坚持的“印度支那”梦想,并且明确承认越南在两国存在军队,这些军队同样应该撤出。实际上,越南并不愿意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也没有放弃他们“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仍然表示他们与老挝、柬埔寨具有特殊关系,并多次向两国提出主权要求。(38)全国解放后,越南就快速控制了老挝并于1978年派兵大举入侵柬埔寨。因此,越南对这一结果是从来没有认同的,只是“受到中国逼迫,越南才接受了解决方案”(39)。
(二)南北划线还是就地集结——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分歧之二
早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苏联就已经形成了关于越南南北划线的方案。1954年1月29日四国外长会议期间,苏联即命其驻法大使提出了解决印支问题的方案:“于北纬16度线划一条临时停战线。法国撤出河内与东京三角洲。越盟停止其在西贡地区和柬埔寨的所有活动。三个月内召开政治会谈以解决所有问题。”(40)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提出沿北纬16度线划定临时停战线的材料。是年3月,苏联方面再次建议:“如果不能就建立有越盟加入的联合政府方案达成协议,解决方案可以是以北纬16度线划界”,因为“这一安排可保证中国南部边界的安全”。(41)出于保证中国南部边疆安全及防止美国势力入侵印支等多方面考虑,中国方面对于这一方案亦积极予以回应。3月2日,周恩来在其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指出:“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42)3月6日下午,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拜访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时亦提到,16度划线的提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十分有利,一旦被正式提出即应接受。”(43)
目前尚无史料表明,中苏是共同磋商还是各自单独形成了此项方案。但至少可以断定:到1954年3月2日前,中苏已就以北纬16度线南北划线达成了共识。对于中苏两国的方案,越南一时之间难以接受。3月5日,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会谈中即指出:“在越南没有确定的前线,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划分十分困难”。(44)3月13日,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在有关日内瓦会议的讨论中,对停战问题仍然争论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指出:“停战问题很复杂,我们打了那么多年,学会打了,但是没有学会停。在怎么停的问题上,要充分听取中国顾问的意见。”(45)
由于资料的限制,至今仍然无法获知越南方面此后态度的发展。但从胡志明的话语及日内瓦会议前中苏越三国就此事达成共识的结果来看,越南最后接受了北纬16度划线的建议。但是,越南大部分领导人特别是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并没有从内心中真正理解和接受16度划线的建议。特别是当奠边府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日内瓦之后,范文同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反复。范文同认为,越南问题应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候普选的方案为主,因为这样可以一举统一全越南,只有当对方不同意普选时,再考虑南北划线。(46)对于范文同的上述主张,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本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周恩来看来,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在印度支那追求的目标是划线而治,固定现状。(47)若就地停战,那么尚在敌人手中的红河三角洲、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便无调整的可能。越盟应该首先站稳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不然南越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被敌人挤掉了,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又未能在交换中得到加强,这样的结果对越盟是不利的。(48)因此,周恩来仍然极力推动越南南北划线的实现。
5月14日,周恩来会见前来拜访的艾登时,就划线问题征询英国方面的意见时,获知英国确有划定军事分界线的打算(49)。6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在越南的地区调整问题上,把南北划成两个大区的大调整,对我有利(50)。6月23日,周恩来在与法国新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在瑞士伯尔尼会面时,又向其询问法国对于越南停战方式的态度(51)。在获得了中共中央的明确支持及获知了英法等国对停战方式的态度后,周恩来又建议范文同积极主动地更改越方的划线方针,以求得和平协议的达成。但是,范文同对周恩来的建议并不赞同。他对形势的估计明显偏于乐观,认为“着急的应该是法国人”,在谈判方针上倾向于拖,主张“等一等看看情况发展再说”。在划线问题上亦要价过高,提出将停火线划在北纬13度线与北纬14度线之间,这样的要求已经超出了战场控制程度,与法国提出的北纬18度线方案也相去甚远。对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多次通过中共中央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转发电报阐明看法,但是他们对形势的严峻程度同样缺乏足够的认识。(52)为抓住转瞬即逝的和平机会,周恩来决定直飞广州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商谈谈判情形和划区问题,以求得意见的一致,并使日内瓦谈判获得进展。(53)
7月3日~5日,周恩来偕罗贵波等同胡志明等越方领导在广西柳州举行了8次会谈,围绕恢复印度支那三国和平等问题特别是南北划线及老挝集结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周恩来从越法双方的力量对比、美国干涉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战争国际化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越南战场的形势,特别是说服越南同志: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计较,因为法国方面已经给我们交了底:他们只要求给他们留点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越南的困境。周恩来给越南同志说:“只要法国军队撤出,越南不还是越南人的吗?”(54)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多次劝说,越方领导人终于勉强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最终,中越双方形成了关于划区问题的最后底线:(一)在越南,准备在十六度线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二)在老挝,要求是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有一块地区。如果不行再议。(三)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55)
在中越双方达成共识后,越南劳动党中央立即以“七·五文件”的形式通告在日内瓦的范文同,要求他“收到文件后请即邀请苏中代表团会商,如无基本不同意见,请即按此文件所定的方针进行谈判”。(56)但是,接到党内指示的范文同并没有按照指示行事。在其接到指示后到12日周恩来返回日内瓦的7天时间里,范文同依然坚持原有的13度、14度划线的主张,并消极地拖延会议的进程。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7月12日回到日内瓦的当晚,即分别拜访了莫洛托夫、范文同,向他们说明中国、越南和苏联三国党中央所商定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一致意见:主动、积极、迅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57)为了说服范文同,周恩来与之交谈至深夜12时,向他详细介绍了与胡志明会谈的情况和得出的共识,并告诫范文同:“要以法方为主要的对象,提出的条件要考虑对方接受的可能性。……为了达成协议,只要不是改变基本要点,在谈判中可以接受与方案稍微有出入的变通办法。”(58)经过周恩来的耐心说服,范文同最终接受了16度划线的方案,并决定第二天即向孟戴斯·弗朗斯提出。7月13日,周恩来紧急约见了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在与孟戴斯·弗朗斯的会谈中,周恩来指出,“如法方能前进一步,越南愿走更大的一步来迎接法方的让步”(59)。在随后与艾登的会谈中,周恩来向其介绍了中越柳州会谈情况,商谈在越南划分集结区问题(60)。
在周恩来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之后,范文同也与孟戴斯进行了会谈,并向孟戴斯提出了以北纬16度线划界的新方案。(61)但是,在范文同提出了这一新方案后,法国并没有像中苏越三国所想象的那样“前进一步”。相反,法国仍然坚持北纬18度的原有方案。为了推动谈判的进程,中国代表团积极进行斡旋。一方面,努力与苏、越代表团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并最终形成了新的折衷方案:“越南可以将九号公路让与法国,并且同意将分界线划在这条公路的北面。”(62)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向英、法代表团施压,并向法国代表团申明:“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再作让步,即分界线通过第九号公路以北约十公里,照顾到地形。如果对方再不接受,我们也只能买回家的车票了。”(63)经过各国代表特别是中国代表团的不断努力,法越双方最终以此方案为基础达成一致。双方协议以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的六滨河为越南的军事分界线。
由此可知,在划界问题的谈判中,周恩来多方交涉,不断努力,在划界问题上占据了主动。而越南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范文同则多次被动接受周恩来的意见,其主张也经历了以下变化:主张就地集结或袋形集结——以13度线或14度线为界——以16度线为界——以大约17度线为界。也就是说,在划界问题上范文同一直处于被说服被教育的被动境地。这就难免会使越南产生“中国日益催迫越南让步”(64)的印象。
三、日内瓦会议后中越关系的嬗变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最终结束。会议结束后,越南代表团及劳动党内部对会议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而且对未来越南的前途充满了憧憬。毕竟两年后整个越南都将是越南劳动党的了。但是,由于此后形势的急转直下:东南亚条约组织随后建立,越南亦被分成为南北两部分。此后,越南劳动党对会议的结果及中国在此次会议上的表现开始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并由此严重影响了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54年7月21日凌晨3时30分,双方代表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日内瓦会议最终顺利结束。对于这个结果,南越代表陈文杜当即表示了强烈的抗议。陈文杜指出:“它严重抗议法国和越盟最高司令部仓促缔结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很多规定是严重损害越南人民的将来的。它并进一步对下一事实严重地提出抗议,即停战协定是将一些领土归于越盟,而其中有些仍然在越南部队占领之下,并且还是对保卫越南使之不受越盟更大侵略的基本地区。”(65)诚如陈文杜所言:通过日内瓦协议的签署,越南民主共和国获得了本不属于其占领区的大量领土,大约1200万的人口(南方有约900万人口),而且拥有了在政治及经济上都至关重要的首都河内。另外,日内瓦会议的签署等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从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结束了其只存在于森林中的“幽灵国家”的历史,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更为重要的是,日内瓦会议的签署使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使美国干涉印度支那革命的企图失去了其道义上的合理性。因此,越南方面对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当时较为满意。在日内瓦会议有关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签订后,范文同即向记者表示:“会议的结果是对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贡献,这些结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国际上一切分歧都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来得到解决的。”(66)如果说范文同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很难代表其真正的想法,范文同发给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密码电报应该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情。在这份电报中,范文同同样表达了其喜悦的心情:“协议已经签订,这是我们的胜利……总的说来这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和平事业的巨大胜利。”范文同还特别建议越南劳动党中央“应致电苏共中央与莫洛托夫同志和中共中央与周恩来同志,感谢他们协助我们进行斗争,争取到外交胜利”(67)。除范文同之外,越南劳动党中央亦曾多次对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提出赞扬,并就中国及苏联在会议中对越南的帮助表示感谢。
但是,此后事态并没有按照原先中、苏、越所设想的那样向前发展。1954年9月,就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国即纠集英国、法国等八国组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以防止来自中国的“侵略”,同时保护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三国。1955年,吴庭艳又在西贡操纵公民投票,废除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共和国(即“南越”),并随之宣布“北方根本不具备自由选举的条件”,因此不接受全国普选。至此,日内瓦会议所达成的有关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已经被破坏殆尽。此后,越南已经无法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进行普选,而是在长时间内被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同时,越南做出妥协,撤出大量军队所换来的柬埔寨和老挝的和平与中立也无法得以实现。在这种形势下,中越两国都开始重新审视日内瓦协议的成败。越南对日内瓦会议的态度、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中的表现也开始有了相反的评价。
由于资料的限制,笔者无法得知中国开始对日内瓦会议评价转变态度的具体时间。但是,至迟在1968年左右,中国领导人开始多次就其在日内瓦会议中的错误向越南道歉。1968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与越南代表春水(Xuan Thuy)进行谈话时即指出:“当毛泽东同志最后一次会见胡志明主席时(68),他(对胡主席)说,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或许是错误的。”(69)是年10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与越南谈判代表黎德寿(Le Duc Tho)进行谈话时亦指出:“日内瓦协议达成后,我们将部队从南方撤到北方,那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70)同日,在会见来访的范文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日内瓦会议晚开一年,形势就会好一些,北方的军队就可以攻占(南方)并且打败(敌人)……我想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71)1971年,当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亦提到:“在这一问题上我当时想得不够充分,我们需要更冷静的头脑。毛主席已经多次向我们的越南朋友提到这件事。我们的越南朋友不怪我们,但我们当时本来可以做得更多。”(72)
相比中国领导人,越南劳动党内对日内瓦会议态度的变化则更早。这是因为,越盟内部在很早就有一种骄傲轻敌的思想。1950年前后,当时“越南领土的大部分,包括各战略要冲、公路港口,大中城市、物产基地等都在法国殖民军手中,中越边境越方一侧也完全由法军控制。”(73)在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同越南建立联系,越南没有任何国际地位,也得不到外援(74)。即使在这种形势下,越盟就曾多次开会研究中国解放军大军南下的形势,积极准备转入总反攻(75)。因此,可以想见,当越盟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并以胜利者的姿态与战败方法国进行谈判时,他们那种别样的心情。因此,参会的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在得到奠边府胜利的消息后立即更改了其原本同意的南北划线方针,主张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候普选,一举统一整个越南。在此期间,虽然胡志明表现出了对中苏两国妥协意见的理解,并在党内高调批评了那些“只见法国不见美国,偏于作战,轻视外交”和“企图乱打,打到底”的“左倾”错误思想(76),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胡志明主席(对这一协议)不是完全满意。对胡主席来说,让他放弃南方是非常困难的。”(77)实际上,不唯范文同与胡志明,几乎整个越南劳动党都有这种胜利在即的思想。因此,当周恩来力劝越南劳动党放弃南方的根据地,并撤出其在老挝、柬埔寨的军队时,他们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至于最后他们同意妥协,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周恩来所言,“只要法国军队撤出,越南不还是越南人的吗?”(78)而另外一个原因,就只能是“因为苏联和中国同时(向越南)施压,才出现了后来的结果。”(79)根据当时在越南南方领导游击队的黎笋后来回忆,当他听到要游击队撤出南方的消息后,“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80)从后来黎笋要求留在越南南方继续领导革命和多次就此事向中国问责的历史看,上述话语所反映的应当是他当时的真实感受。
之后,伴随着越南的南北分治成为事实和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国,原先被越南视为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全部化为泡影。对越南而言,日内瓦会议已经不能再被视为一种成功,或是有条件的成功,而只能是一种完全的失败。而所有这些失败的原因,只是由于越南“听了中国的建议”。(81)此后,越南开始建议中共承认其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错误,并对其提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逐渐地,在越南劳动党内再也听不到有关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中帮助越南的言论,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对印度支那三国革命的打压与背叛。在此之后,日内瓦会议逐渐成为阴谋与阻碍革命的代名词(82),亦成为越南不听从中国建议的一个重要借口(83),中越关系亦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对日内瓦会议及之后越南的历史进行认真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日内瓦会议不能称之为完全的失败,而应该被称之为一种历史性的成功。即使美国后来直接出兵南越,并对越南进行野蛮轰炸,但其军队却一直没有越过日内瓦协议所划订的北纬17度线进入北方。而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也正是凭借着北方这个巩固的后方和前进的基地,最终统一了全国。
如果从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通行原则来分析中国当时的行为,中国的举动亦无可厚非。日内瓦会议召开时,中国刚从朝鲜战争中抽出身来,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的越南劳动党,牺牲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做出让步,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亦符合正常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但是,由于当时中越之间并没有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而是基于国际主义原则建立起了一种负责与被负责的党际与国家关系。在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关系范式中,国家利益原则在实际上被抛弃,而代之以意识形态同质性下的国际主义原则。即一党及一国对具有意识形态同质性的另外的党和国家的支援与帮助。这种帮助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和国际主义的至上性,国家间的援助都无法谈及国家利益,而只能责之以道德层面的责任感。因此,当一国在国际交往中没有尽其心力援助自己的盟国,而是更多地顾及自身的国家利益时,就难免使责任一方产生一种强烈的道德愧疚感,并使被帮助的国家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从而获得对责任一方口诛笔伐的道德武器。正因为这个原因,当中国革命胜利后越南要求援助时,中国只能“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84),而不应有任何的推托。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中国于日内瓦会议之上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主义为原则处理印度支那事务时,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根据以情况处理问题了。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苏之间也曾发生过与日内瓦会议相类似的事件。1945年8月抗战结束之际,斯大林曾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斯大林当时可能更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用战争来完成解放国家的任务,因此需要转而采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生气。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所设想的和平民主没有出路,共产党仍旧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这一干预耿耿于怀,并从道德层面给予斯大林严厉的批评,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85)。而与中越之间故事更为相似的是,斯大林后来也曾就此事多次向中国共产党道歉和表示愧疚(86)。
四、结论
1953年前后,世界形势风云突变。世界各国开始因为各自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或是因为自身地缘政治思维的改变,而希望在印度支那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基于对美国入侵东南亚及中美发生新一轮冲突的地缘政治预期,中国力争通过日内瓦会议在印度支那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并以此来达到东南亚不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会成为美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中国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充分考量,迫切希望通过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迎来一个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正是基于以上诸多考量,中国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纵横捭阖,多方游说,积极在英、法、苏、越等国代表团之间进行斡旋,并劝说越南代表团放弃眼前利益,从而换取越南革命的长远利益。
经过与会各方特别是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印度支那的和平终于得以实现,中国也因之实现了此次赴会的目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美国入侵印度支那及中美再战的地缘政治威胁;另一方面,使中国得到了相对较长时间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中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主义为首要目标,从而使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失去了盟友越南的信任,并同时失去了其在指导越南革命中的正当性。从此,中国再也无法理直气壮地对越南革命及建设事务进行指导。同时,越南也将其原本就因两国复杂的历史纠葛和长期的政治不对称所造成的不信任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所谓“背叛”累加,从而更加不信任中国。同时,由于中国对越南的处理方式,越南之后在中越之间的交往中开始自行其是。此后,中越关系中中国与越南的定位全面反转,中国在中越关系发展中逐渐变得被动,而越南则开始更多地在私下或是公开场合拒不接受中国的建议与指导,中越关系由此出现了重大的嬗变。
注释:
①《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③《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④法国外交部出版的文件为:Ministe re des Affaires e trange res,Confe rence de Gene ve sur l'Indochine,8 mai-21 juillet 1954,Paris:Impr.Nationale,1955.英国方面的文件(白皮书)有二:A.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Discussion of Korea and Indo-China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April 27-June 15,1954.B.Fur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Discussion of Indo-China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June 16-July 21,1954.
⑤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for 1954,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Dwight D.Eisenhower,1954,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
⑥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1945-1967,12 volumes,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
⑦U S State Departmen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16,The Geneva conference,Washington D.C.,1981.
⑧Robert F.Randle,Geneva 1954: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ese Wa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⑨Philippe Devillers and Jean Lacouture,End of a War:Indochina,1954,Frederick A.Praeger,1969.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11)海外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Zhai Qiang,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The China Quarterly,No.129(Mar.,1992),103-122.此外还有Ilya V.Gaiduk,Confronting Vietnam: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1954-1963,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中国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蔡佳禾:《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百周年纪念》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有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钱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12)[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4~85页。
(13)Dean Acheson,United States Position on China,August 1949,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No.3573,pp.XVI-XVII.
(14)FRUS,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Indochina,1952,Volume XIII,Part 1(1952-1954),p.15.
(15)《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
(16)《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2页。
(17)Ilya V.Gaiduk,Confronting Vietnam: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p.16.
(18)Kirill Novikov-Nguyen Long Bang,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6,1954,AVP RF,f.079,op.9,p.6,d.5,1.pp.26,35.
(19)金冲及:《周恩来传》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20)CFMA,Record No.206-Y0054,2 March 1954,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of CWIHP.
(21)《越南劳动党纲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22)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213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260页。
(25)中央电视台《见证亲历》栏目组:《时代风云》,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26)CFMA,Record No.206-00055-04(1); original Record No.206-C0008.April 4,1954,CWIHP.
(27)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129、132、13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368页。
(28)金冲及:《周恩来传》第三册,第1126~1127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165页。
(30)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第118页。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167页。
(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83~384页。
(33)钱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第353页。
(34)金冲及:《周恩来传》第三册,第1127~1128页。
(35)AVPRF f.06,op.13a,d.25,II.8.Published in Bulletin #16 by CWIHP.August 10 2007.
(36)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第121页。
(37)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委员会:《日内瓦会议资料汇编》,1954年,第114页。
(38)郭明:《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39)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30 years,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9,pp.24-25.
(40)FRUS,1952-1954.Indochina Volume XIII,Part 1,p.1009.
(41)Tahourdin memorandum,March 19,1954,Public Record Office,Foreign Office:371 112048.
(4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页。
(43)AVPRF f.6,op.13 a,d.25,II.7.Published in Bulletin#16 by CWIHP.
(44)Ilya V.Gaiduk,Confronting Vietnam: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p.19.
(45)钱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第49~50页。
(46)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第116页。
(47)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页。
(48)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第116页。
(4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67页。
(5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77页。
(51)金冲及:《周恩来传》第三册,第1129页。
(52)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第126页。
(5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175页。
(54)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页。
(5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94~395页。
(56)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第129页。
(5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97页。
(5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190页。
(5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233页。
(6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98页。
(6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233页。
(62)AVPRF f.06,op.13a,d.25,II.8.Published in Bulletin #16 by CWIHP.
(6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257页。
(64)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30 Years,pp.24~25.
(65)《第八次(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54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1集 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198页。
(66)《范文同副总理答苏联〈真理报〉记者问》(1954年7月23日),《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第127页。
(67)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第135~136页。
(68)没有说明时间,但应该在1968年的冬春,当胡志明在北京接受治疗时。(原引文注解)
(69)"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Chen Yi,and Xuan Thuy"(7 May 1968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No.22,1998,p.132.
(70)"Conversation between Chen Yi and Le Due Tho"(17 October 1968),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No.22,1998,p.137.
(71)"Conversation between Mao Zedong and Pham Van Dong",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No.22,1998,pp.139-140.
(72)Memcon,Kissinger and Zhou,9 July1971,4:35-11:20 PM,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box 1033,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p.21.
(73)谢益显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74)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忆毛泽东和援越抗法》,《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5)文庄口述,盖晨、郭一峰记录整理:《风雨同舟话越南——出使越南经历访谈录(二)》,《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2期。
(76)《在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1954年7月15日),《胡志明选集》第二卷,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337页。
(77)"Converstaion between Mao Zedong and Pham Van Dong",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No.22,1998,pp.139-140.
(78)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430页。
(79)"Converstaion between Le Duc Tho and Ieng Sary"(7 September 1971),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No.22,1998,p.178.
(80)Le Duan.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People's Army Library,Hanoi.CWIHP Bulletin Nos 12/13.
(81)"Conversation between Chen Yi and Le Duc Tho" (17 October 1968),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No.22,1998,p.137.
(82)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对于尼克松的此次访问,西哈努克回忆道:“我和我的北越朋友,以及当时和我同在河内的民族解放阵线与巴特寮的朋友们,都一致认为,谁也不用想拿某种新的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来欺骗我们了。”见诺罗敦·西哈努克口述,W.G.贝却敌整理:《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王俊铭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5页。
(83)1968年10月17日,黎德寿就曾对陈毅说:我们在日内瓦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越南)听了你们(中国)的建议。”因此,越南不想在有关越美会谈问题上听命于中国。1971年9月7日,黎德寿与柬埔寨红色高棉领袖英萨利谈话时亦指出:中国同志“已经承认他们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错误……我们应该在思想上独立”。见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No.22,1998,p.137,178.
(84)《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年1月27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85)此处借用了杨奎松的对比事例。详见杨奎松:《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86)叶书宗:《斯大林反思中国革命问题》,《世纪》2007年第1期。
标签:日内瓦会议论文; 柬越战争论文; 越南共产党论文; 越军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柬埔寨战争论文; 越南论文; 英军论文; 中越论文; 越南总理论文; 周恩来论文; 印度支那论文; 范文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