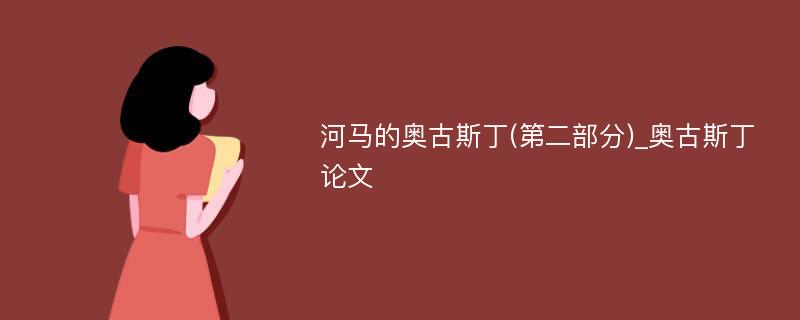
希波的奥古斯丁〔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古斯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罪与自由意志
这是奥古斯丁最著名,也是最具影响的理论。所谓影响,并不仅指接受或继承,更多地指,在建构不同理论时,某一先行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此后成为不可或阙的思维视野。
在《论自由意志》中奥古斯丁对本问题进行了集中系统的讨论。此外,在以下诸书中亦有较完备的阐释:《论基督的恩典与原罪》 ( DeGratia Christi etpeccato originali)、《论恩典与自由意志致瓦伦提努》(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 ad Valentinum)、 《论堕落与恩典》(De correptione
et
Gratia )、 《神学手册》(Enchiridian)。奥古斯丁的理论, 大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自由意志的性质、罪的根源与性质、人类的处境、理性与意志、上帝的预知与预定。
奥古斯丁的两大前提是:上帝存在;一切存在皆来自上帝,而一切来自上帝的皆是善。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上文已经说明,这是一个依存于柏拉图主义存在等级说的论证。人类理性是世上最高存在,而真理(智慧)高于理性,故真理必为超越性的至高至存,即上帝。上帝,至善,绝对永恒真理,智慧,这些都是同义语。
上帝是创世主,一切存在来自上帝,这本是信仰前提。一切善或好的事物皆来自上帝,这本来也是信仰内容。奥古斯丁为此提出一个论证。我们说一切可变之物是“可变的”,同样,凡是可接受形式之物皆是“可形成的”。一切可变之物皆是可形成之物。任何事物皆不能由本身给自己形式,因为它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自己,而只有在接受形式(形成)以后它才有形式。一切事物皆需从别处接受形式。身体和灵魂皆从不变永恒的绝对形式那里接受形式,那就是上帝的道。(De liberoarbitrio,2.17)
所谓善,便是指存在之物得以存在,以其存在完成宇宙整体,宇宙存在是善,存在比虚无为好,存在本身是善。一切存在之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有形式,一旦失去形式,便即灭亡。其形式有生灭变化,故一切存在皆倾向于无(消亡)。因此,一切存在之物之存在,皆依存上帝所赋予的形式,故一切善皆来自上帝。(Ibid.,2.17; 1.16.)
既然一切存在之物来自上帝,而一切来自上帝的皆是善,故自由意志也是来自上帝的一种善。然而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被滥用,既被滥用,还能够称为善么?能够。譬诸人的器官四肢,本是生命不可或阙的善,但却可以被滥用,为非作歹,然而它们本身仍是善。
有三种不同等级的善。美德之类,如正义、勇敢、坚忍、谨慎,属于上善。这些善,不可能被滥用去为恶。谁也不能以正义去做非正义之事。而没有这些善,人类不可能正当地生活。肉体之美,属于下善,没有这些,人类也可以正当生活。精神的能力,如理性、自由意志,属于中善。没有这些,人类不可能正当生活;但有了这些,人类却可以滥用它们去为恶。(Ibid.,2.19)虽然上善的规律依存于永恒真理, 但具体的美德属于个人,而非普遍,如甲的勇敢不是乙的勇敢。惟有真理、智慧为永住不变的普遍之善。
何谓幸福?幸福便是自由意志朝向永恒之善运动的结果,这样的人类存在便是幸福。何谓罪?罪便是自由意志背离永恒之善,朝向私己的下善。例如一个人骄傲,以上帝自居;窥探干涉他人的私事;耽湎于感官享乐。这样的存在是不幸,是死亡。(Ibid.,2.19)
上帝是全知,预知一切,而人有自由意志,按照自己的愿意去行动。这是否矛盾?并不矛盾。上帝预知,故预先知道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意志,作出自己的抉择,并对这抉择的后果负责。预知的知,是“知道”,不是“决定”。人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且必须为此负责,这一切皆是上帝的预知,而且是上帝的创造。(Ibid.3.3)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公义(正义)的秩序,上帝将人置于这个秩序之内。人的行为,出于人的自由意志之抉择。如果人抉择了善,最终将得到永福。如果抉择了恶,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自由的灵魂是上帝所创造的完美世界的组成部分。人犯罪,不是上帝的决定,而是人滥用自由的结果。如果人犯罪不受惩罚,将破坏完美世界的秩序。而犯罪受到应得的惩罚,则说明世界秩序的完美。既然自由意志可以被滥用,何必创造它?只创造正确的完美的世界岂不更好?这种想法是对上帝意志的过分推敲。上帝创造的秩序自然完美。中善(理性、意志)是人正当地生活的必要条件。自由的灵魂是完美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Ibid.,3.9)
关于本性(实体)的缺陷(不完美),奥古斯丁依据柏拉图主义提出一种解释。当我们对一种本性,观察到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与它的完美本性相比较。对其缺陷的谴责,蕴涵对其完美本性的颂扬。世界就其受造本性而言,本来完美。缺陷只是未完成状态。(Ibid.,3.14)从这个观点来看待恶与罪的问题,则知上帝创造的世界就其本性而言实为完美,恶是善的阙如,不是实体。罪是人滥用或误用自由意志的结果。既然罪不是上帝所造,而是人自主做出来的事,故应由人自负其责。罪是对宇宙完美的破坏,对上帝的背离。“一切罪皆包涵在这一类之下:即背离真正永恒的神圣之事而转向变动不居之事。这些事物原本被恰如其分地置于自身应有的位置,通过其特有之美来完成宇宙的整体;然而那堕落失调的人性却甘为奴仆而追逐这些本由神律定为受人支配的东西。”(Ibid.,1.16)
神律,或永恒法,规定何为正义,何为幸福。真自由乃是遵从永恒法,导向幸福。而自由意志则是一种中善,可以被误用。换句话说,正确运用自由意志,方是自由。罪是一种特殊的误用自由意志,即背离神圣,不顾永福,而耽溺于现世的快乐。现世快乐既包括物欲,也包括精神的欲,如权力欲,自大欲,自比上帝式的傲慢。背离神圣而转向物,实即转向虚无,转向灭亡。因为一切物皆是生灭之物。与神圣或绝对存在相比,受造的存在可以说是非存在或虚无。“至于现世之事,在产生之前并不存在;既经产生,便处于消逝的过程中;一旦逝去,便不复存在。故现世之事在出现之前并不存在,逝去之后亦不存在。既然其始而存在与趋于消逝无异,又岂可视为常在?”(Ibid.,3.7 )故人背离神圣而转向生灭之物,实即趋于死亡。人犯罪是对宇宙完美的破坏,是对上帝的背叛,自应受到公义上帝的惩罚。
奥古斯丁关心的是人的具体处境,依据圣经,即蒙罪堕落的亚当及其后代的具体抉择处境。本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赐给人理性、知识、自由、永生。然而在魔鬼诱惑下,人类背叛了永恒神圣,不信上帝的用心和目的, 为了恶的目的而利用园中的善树。 (De Genesiad Litteram 11.5)从此人类失去永生、知识和不犯罪的能力。 这便是人类在历史中的具体处境。
最初上帝创造人类,本赋予其理性、自由与智慧。人有理性,可以理解上帝的诫命,故理性是人类正当生活的必要条件。然而既经理解,乃有违命而犯罪的可能。故罪以理性为条件。“当人开始能够理解诫命之时,亦即开始可能犯罪之时。”(De libero arbitrio 3.24)理解诫命仅是进行抉择的必要条件,抉择本身则由意志或智慧作出。理性的理解,意志的抉择,既是犯罪也是信仰和永福的条件。
蒙罪之前, 上帝赐给人类的自由意志既包涵犯罪的能力( posse peccare),也包涵不犯罪的能力(Posse non peccare), 却不包涵不可能犯罪(non posse peccare)的完全恩赐。( De correptione et Gratia 12)既经蒙罪之后,人的本性已经堕落,意志仍然自由, 却只有在罪中抉择的自由,而已经失去智慧即不犯罪的能力。于此可知,奥古斯丁所谓的自由意志,乃指罪前与罪后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意志。并不如论者所言,在反对摩尼派时主张人有不犯罪的自由,在反对皮拉鸠派时又主张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J.Ball, "Libre arbitre et liberte dans S.Augustin",L'Annee Theologique,6 (1945),pp.368—882.G.Vrankan,Der Gottliche Konkuro zum freien Willensakt des Menschen beim hl.Augustinus,Rome: Herder,1948.)只是在写作《论自由意志》时,意在驳斥摩尼派, 尚未强调不犯罪的自由,以后加以更正和强调而已。
原罪的结果是:有死、无知、邪欲。所谓邪欲(libido),乃指人背离神圣之事的物欲,并不特指两性的情欲。但奥古斯丁以为情欲是人类受制于邪欲的最明显表现,彷佛人在性行为中最不顾一切地将注意力由造物主转向受造物。(De Gratia Christi et peccato originali 2.34)
原罪的原因是人滥用自由意志。“要么意志是罪的第一因,要么罪便没有第一因。罪不可能归于别人,只能归于犯罪者;也不能归于犯罪者,除非他意愿之。”(De libero arbitrio 3.17)既然自由意志有犯罪的可能,上帝为什么还要赐给人自由意志呢?因为人本身是一种善,当他按本性意愿时,他能够达致正确的生活;故自由意志是人完成其本性之善的必要条件,因此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人犯罪必受上帝惩罚,可知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并非为使人犯罪。这里奥古斯丁提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亚当是由于愚蠢才背离上帝呢,还是由于背离上帝而变得愚蠢(失去智慧的恩赐)的呢?回答实为两难。如果说亚当是由于愚蠢而背离上帝,则在犯罪以前已经变得愚蠢,而教义认为亚当原有智慧的恩赐;如果说亚当是在背离上帝之后变得愚蠢,则他是在智慧中犯的罪。两者皆不通。奥古斯丁的解决方式是提出,在由智慧转入愚蠢的过程中,有一临界状态,其时意志既非智慧又非愚蠢,犹如非睡非醒之际。亚当犯罪,便在此时。然而此事近于神秘,人类在此世不可能充分理解之,因为人的理解以或是或否为限度。(Ibid.,3.24)
人类堕落之后,从此失去了永生、知识、不犯罪的能力,这便是蒙罪后人类的处境。原罪由亚当传给后代的方式,按早期教父德尔图良的学说乃是亚当的灵魂传给后代,故罪性的遗传与气质的遗传相彷佛。这是基于斯多亚派灵魂观的一种解说。奥古斯丁则主张,在每个人出生时,上帝单独创造其灵魂。此说更符合肉体复活等教义,却更难说明罪性的遗传。
奥古斯丁解释上帝预知与人类犯罪的关系,略近于波依修斯。知道一件事发生,不是该事件发生的因。比如记忆中知道某事发生,并不是该事件的因。同样,预知某事发生也不是该事件的因。预知与犯罪不可能相矛盾,因为无因果关系。(Ibid.,3.3)
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可以说是其自由意志论和恩典论的逻辑后果。既然蒙罪的人只有抉择犯罪的自由,而走向得救的第一步却不是犯罪,这一步如何走法?奥古斯丁认为人本身无力走这一步(反皮拉鸠派)。蒙罪的、扭曲的意志不可能倾向上帝。只有上帝的恩典在人心中工作,改变人心的倾向,使人的自由意志与之合作,方能朝着称义走出第一步。在既信之后所行的善功,也是恩典的工作以及人与之合作的结果。既然使人得救的恩典根本不靠人的功劳,所以由谁来领受白得的恩宠只能由上帝来决定,即预定。人类的得救纯然是上帝仁慈的结果。全人类由于本性的堕落而受到惩罚乃是理所当然之事,是上帝的公义。上帝从受谴的全体中拣选出固定数目的人令其进入天国,乃是上帝的仁慈和自由。未被拣选者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而是由于自身的罪而永留在受谴的团体中。(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 17.)
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在当时便引起争议。 哈德鲁门图(Hadrumentum)的僧侣一向宗仰奥氏,然而却坚主得救的第一步应归功于人。此种史称的半皮拉鸠派,实为温和的奥古斯丁主义者。在高卢南部,尤以马赛,反对预定论尤烈。代表人物有约翰·卡西安、莱兰的万桑等。 公元529年的奥兰治宗教会议结束了半皮拉鸠派的争论, 然而会议本身亦仅采纳奥氏学说的温和形式。会议明确肯定了人的原罪为本性的蒙垢,既经蒙罪之后,人的自由意志便只能从事自然事物的正确判断,而对得救之事无能为力;故不仅补赎之事,而且信仰的第一步亦为恩典在人心中工作的结果。此即恩典先行说。然而会议否定了奥古斯丁的恩典不可抗拒说,亦即否定了预定论(永福和永罚皆已预定)。当时的奥古斯丁派神学家,如普罗斯培鲁(Prosperus Aquataniae )、 富尔根提乌(Fulgentius de Ruspe )等人皆主张恶不可能来自上帝(这也是奥古斯丁的前提之一),故上帝不可能预定永罚;恩典无所不在,坚忍者固由上帝的恩典而得救,上帝的其他子女亦不可能仅因预定而成为魔鬼的子女。
后来,奥古斯丁的恩典论在中世纪发展为对恩典进行繁复分类的教条,同时中世纪神学亦逐渐退到半皮拉鸠派的立场(恩典并非先行而与善功同时,既经蒙罪的人性之中仍有善根)。对此的反动,便引导出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预定论。这些神学自称师承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然而奥古斯丁主张恩典在人心中工作的一个不可或阙的过程乃是改变人心的倾向,令人的意志自由地与恩典合作。此种对人类自由的较多肯定,实较宗教改革派神学更为乐观亦更注重教会圣礼的功用。
奥古斯丁的原罪与自由意志学说,自亦难免某些逻辑的困难。诸如智慧与理性和意志的关系、临界状态的性质、恩典的工作与意志的关系等,皆需要更清晰的说明。恩典与意志的关系,颇有点象神之光与心智的关系。如果蒙罪的意志不可能倾向上帝,亦即不可能接受恩典的工作。此处似无合作的余地。只有改变了意志的性质,方能合作。奥古斯丁称恩典的工作为温和的暴力,亦即恩典不可抗拒。这似乎与人的自由意志无法调和。既然自由没有意义,那么信仰与自由合作又有什么意义呢?预定论的要旨在于强调上帝的权力。神的全知全能和计划,与有限的受造物无关,不可臆测,只能全心信仰。历史上,此种学说在提升信仰质量方面曾起作用,然而与上帝创造的自由意志可以与恩典自由合作的教义却难以调和。
奥古斯丁原罪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参与塑造西方的人性论。西方文化的人性观,既非主性善,亦非主性恶,而是说由天赋的善,通过理性和意志的抉择而变恶。这个恶,不是天赋的恶,而是人的罪,必须由人负责。而复原善,不在人力之内,只能信靠创世主在基督之内的救赎。也就是说,人性中的善,并不可靠。人必须努力,但人的努力没有必然的确定性。在此种观念结构的背景中,西方没有产生浪漫的性善伦理和内圣外王之类的政治哲学。反之,种种防范人性、限制权力的学说和制度应运而生。西方的伦理学说,也大抵强调人格的张力而非内在的和谐。此与西方文化性格颇有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张力、不安、求索的文化,一种权利、个人主义的文化,一种理性化而又超越理性的文化,一种进取、扩张而又内省、悔罪的文化。
历史哲学
公元410年,罗马陷落,异教作者指责基督教为亡城之根源。 此一争论已提出历史的意义问题。基督教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为何?基督教宣扬的永福带来的历史后果为何?奥古斯丁对挑战的回应,是在基督教世界观的构架内,解决历史意义的问题。他指出,世上有两种爱,形成两种城(国)。爱自我,形成地上之城,至于蔑视上帝;爱上帝,形成上帝之城,至于蔑视自我。地上之城荣耀自我,上帝之城荣耀主耶稣。地上之城的君主受制于统治欲,上帝之城的君主与臣民在圣爱中互相服务。(De civitate Dei 14.28.)这两种爱,两种城, 在性质上不可调和;然而自从人类蒙垢起直至世界末日止,这两个城在现世相混杂而不可分;直到最后审判将二者分开,地上之城终将受到永罚,上帝之城得到永福。(Ibid.,1.35.)罗马是地上之城,其一度强盛, 是由于上帝给了它统治世上之权,以便弘扬福音。这个历史使命一旦完成之后,罗马便因其自身的罪(如崇拜偶像等)而衰亡。地上的帝国率皆如此。现世的有形教会是良莠不齐的团体,中选者也并非全然无罪。 (Sermo88.19.)公教会之神圣,不在于其全体成员无罪, 而在于其终将在末日达到神圣。逐步建立起上帝之国,乃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真正目的,惟有上帝的旨意和设计方给历史以普遍的意义。一切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之若干瞬间而已。人类历史是神的奥秘在时间中的表现,神的仁爱不断运作,以期救赎那被罪扰乱的理性的受造物。
与古典希腊罗马的实证历史观念不同,奥古斯丁提供了一种以终极意义为基础的目的论历史观,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结语
奥古斯丁首先是神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他并不通晓希腊文,受的是拉丁文修辞学教育,不精谙希腊哲学。不仅他的教育条件,而且时代条件亦不成熟,尚不足以改建希腊哲学体系。此时的基督教文化处于奠基阶段,基本教义,如三一与位格问题,尚处在纷争之中,正统权威尚未确立。奥古斯丁的正统立场,自然使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护教”之上。他的主要著作,皆有为而发,澄清观点,反驳诸如摩尼派、皮拉鸠派、多纳图派、异教思想及新学院(园)怀疑派等。他与希腊哲学的关系,与其说改造之,毋宁说利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某些观念,重塑了基督教神学。他的最大成就是三一神学、原罪论、预定论,以及道理念论和光照学说。哲学方面也有伟大建树,却属于片段光芒,未成体系。对其哲学思想的理解,如果脱离他的神学体系,亦易致误导。比如他的“存在主义”。奥古斯丁着眼于人的处境,即亚当在自由中的抉择以及人类在罪中的抉择。抉择,也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似乎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命题。然而亚当抉择的结果是罪,人类的抉择可能导致信,皆不是人的本质。按照奥古斯丁神学,人的本质,以及万物的本质,皆来自上帝道中的理念,皆为上帝创世计划所预定。世上的一切,于存在之先,已有本质。因此他的命题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思想确实提供了希腊智力主义所阙如的东西,即以内在经验为认知的前设条件。但这里却是以神学信仰的方式,而非以哲学命题建构的形式提出。在他的著作中,俯仰皆引证圣经权威,与“纯哲学”大相径庭。此与经院哲学不同。他的哲学贡献,是实践而非理论建构。
然而奥古斯丁毕竟是一个深邃伟大的思想家,他在各方面的思维创造,皆值得反复深入的研讨。即使在今天,他的思想对人类关于未来的思考,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