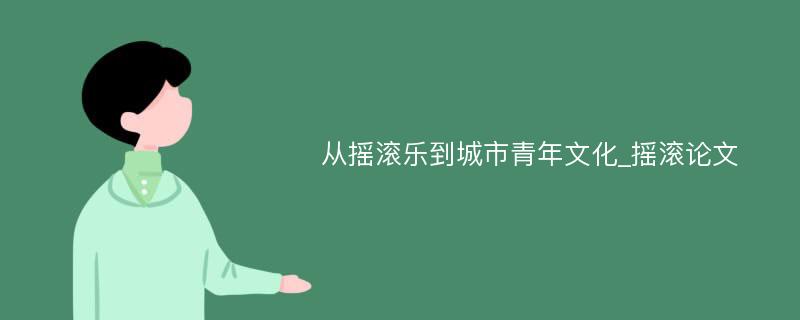
从摇滚到都市青年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摇滚论文,青年论文,文化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6年,崔健粉墨登场,以他在一个“伟大进军”的时代中“一无所有”的宣言,宣告着中国摇滚纪元的到来。崔健所执着的,正是以摇滚的酷烈方式重新诠释红色的革命经典,以“出走”作为新一代的出场序曲,开始了反叛的“新长征”。他以这一份赤裸的告白构建的青春造型,在抗议与异端几乎都失去声音的时代背景中,在政治与经济微妙的、不平衡的艰难协调中,很快就被接纳为抗议者的姿态——他真的就像一个反叛者,而他那一身破旧的军装无疑就是要“以革命的名义”来消解革命,清算政治禁闭留在个人记忆深处的悲痛与滑稽。一时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牢骚(崔健《不是我不明白》),成为一代人在青春觉醒时的箴言;而“一无所有”,也就成为八十年代末最为赤裸与热忱的青春爱情表白。的确,是崔健率先在一个禁闭的空间中,为懵懂的年轻人带来了另类的声音,来宣告一代新人类的闪亮出场。
摇滚第二代就没有崔健这样幸运了。当然,他们依然保留着这样一种反叛的姿态——只是,当他们在90年代出道的时候,商业热潮已淡薄了那份政治创痛,而这种姿态就会略显得有点尴尬:他们似乎是那位名叫堂·吉诃德的骑士的后代,与风车做着认真的搏斗;他们在拔出武器认真地准备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时,才于蓦然回首中发现“敌人”已经无踪迹可寻。于是,聪明一点的在文化创痛中更在意的是对自己的内省,是对都市中的个人的内心瞬息微妙变化的捕捉——当然,这样的内省也不乏直指人心的痛楚。你只要认真地去聆听张楚在“新音乐的春天”中那无声的抽泣,你就可以在认识他们的时候深刻地把悲悯指向自身:出现在磁带封面中的张楚只是以背对着我们,他的正面只飘渺地出现在镜子之中;这一处境象成功地诠释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一无奈与悲凉的命题:只有深刻浸润在孤独中的人才可以在对镜自视的刹那领悟孤独是可耻的,知道“生命像鲜花一样绽放,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必须恋爱”的无奈(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知道“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行人还很坚强”的空虚(张楚《爱情》);张楚说自己就像一只“苍蝇”,即使明了自己无路可逃的宿命,但还要“飞在被拍死在飞往纱窗的路上”(张楚《苍蝇》)——而我以为,这种自贬正是孤独中醒悟自己的虚弱之后最深刻的痛楚。
不够聪明的第二代摇滚人就没有适时地调整自己的位置: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嘶哑着嗓子跟想像中铁板一块的文化做一种无畏的争斗——其实就只是打在一堆松软的腐土上。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学来的牢骚与怨言都已经不再有太多的意义、也不大有市场的时候,他们也就乖巧地把愤怒虚化为一种没有明确所指的压抑:他们说自己“周围的环境一片凄凉”(《北极星·别再唠叨》),说自己“迷失在高楼大厦钢筋铁墙”(《指南针·我没有远方》);当然,没有具体所指的愤怒与压抑很容易就变得虚空,没有对手的战争也很容易就滑落为自我的私语与亵渎:当“我那充满欲望的心,空空荡荡”(许巍《路的尽头》)的时候,也就只能咏叹“就在我进入的瞬间,我真想死在你怀里”(许巍《在别处》)。生命终极之处的体验,也终将在这份赤裸的告白中,蜕化成“像野草疯狂生长”的欲望;在欲望“像苍蝇总是飞来飞去”的疲乏中(许巍《在别处》),生命也就沦落为凄惶无助的自渎。
而现在的情况则是我们的摇滚青年越来越年少了。当一群中学生也开始成为乐迷们膜拜的新神之时,你就不得不感叹“这世界变化快”了。与他们的年龄同步减少的,是他们对社会与人的同情与悲悯。尽管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称崔健是自己成长的精神之父,尽管他们依然似乎维系了一种抗议者的姿态,但他们对这位教父与这样一种姿态本身好像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了。他们首先是在形式上开始摇滚的。最先开始摇滚的是他们的发式、着装,然后才是音乐与心灵。然而,与形式这枚硬币互为表里的总是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他们是在电子游戏的厮杀与搏斗中开始最初的精神游历的,他们是从漫画的造型(当然是美国人或日本人的)那里学会辨别真与伪的。于是,他们的青春愤怒就在戏谑与狂欢中变得更像是一场游戏,更像是一场无人喝彩的独舞。
他们也了然自己是一群迥然不同于崔健的个体组合。于是他们大多首先从形式上完成一次“告别的革命”:很多人减去了长发,把头发染成了灿烂的金黄色;他们大多也不再穿着奇装异服或者破衣烂衫,却穿着很普通、很常见的T恤与牛仔裤。这让他们显得更健康; 让他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宣称“这是我们的时代”(新裤子《我们的时代》)。他们的嗓音状似无赖,带着睡眠不足的懵懂;他们专辑封面的颜色,也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欢快,带着初尝禁果之后的新鲜体验。
摇滚,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以青春期的名义来宣泄内心无名的不满与愤懑(当然,你绝不能说只有在青春期才有摇滚);这些不满与愤懑也只是青春期的焦灼与成长的烦恼。然而,挂着“父之名”标记的社会,似乎一直是他们宣泄的标靶,他们几乎是没有太多借口就无缘无故地把社会作为自己的假想敌:这是因为他们听的摇滚乐大多都是在仇恨社会的;他们在学会形式的同时也学到了确立可攻击的敌人。而显然,要让他们承载如此厚重的社会批判,就显得有点言过其实了。于是他们在“清醒”了之后就开始追寻“最迷人的LUCIA ”(清醒《永远的一天》),以明亮的颜色与寂静的美丽来消解清醒之后的疲惫;他们踏着“大闹天宫”的快乐节拍,徜徉在“绿野仙踪”的迷醉里(麦田守望者《大闹天宫》、《绿野仙踪》)。当然,在他们的音乐作品中,音乐的因素更为动态,也更为复杂、多样——毕竟他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国外最流行的音乐形式他们学起来也是得心应手;但他们只是以一种近乎纯粹的音乐的方式来体验生命与社会——这是不是太过狭窄?他们的时代特色在于他们勇敢地要表达对物欲横流的不满,可他们自己又是在商业运作中学会生存的,这让他们又如何去实践自己的抗议?他们是城市中高消费的一族,但他们又言称抗拒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与此相悖论的是,他们赖以抗拒的标榜却是典型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种不能协调的、可能他们自己也不自知的矛盾就这么缠绕在他们的音乐形式与生存方式之中。而他们似乎并不需要太执着于其中的尴尬,他们只要讨巧地在专辑中虚晃一枪,端一些抗议与反叛的架子,然后就没心没肺地去享受形而下的快乐了。他们的愤怒是无名的,可他们的快乐也一样是没有来由的。赖以支撑着他们的音乐动力的,是他们简单的心智与原始的激情。PUNK是他们主要的音乐形式,但在其中他们似乎更注重了流行的因素;他们的歌词不再那么费解,只要你跟着节奏就可以感觉。说他们是“城市平民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好,其实他们就只是不再像我名之为“第二代”的摇滚乐手那样,以大尾巴狼的姿态摆出忧国忧民的架势,他们只是很坦诚地告诉你自己实在并没有什么深刻而尖锐的思想,既然快乐是他们的当下状态,那就在不违背摇滚的大前提下快乐好了,即使可能有点没心没肺地玷污了摇滚先辈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大好河山。
我很欣赏《中国火》的封面设计(尽管它只是套用了古老的关于铁屋子的象征):一个幼小、无助,略显得有点痴呆的婴儿,被围困在一个砖房里,而在一扇狭小的窗外,则有着动画一般的天空与梦想一般的云彩;这是一个精彩的象喻:这些“新鲜”的摇滚乐手们其实就像这个婴儿一样软弱无力,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他们的内心其实是那样脆弱,对外界充满着恐惧。我想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在外部因素面前,他们只能三缄其口、无话可说;而我怀疑的却是,他们真的有话要说么?即使他们有了言说的自由,那谁又能保证他们给我们的,不是一块啃得干干净净的鸡骨头呢?
摇滚总是最能蛊惑年轻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或愤怒的。
被蛊惑者或者会成为继续蛊惑别人的偶像,或者继续被别人蛊惑着:这二者的差距只在乎机缘与运气。当年轻的“花儿”一夜成名之后,又有多少更年轻的“花儿”蠢蠢欲动,希望下一次迎风绽放的是自己的青春!蛊惑者与被蛊惑者都自认为自己是都市的边缘人,是正统的另类——可你一定要在说出这个边缘、一定要确定另类的归属的时候,你一定要质疑这个边缘的位置;它很可能正是另一处网络的中心。
摇滚是出现在新时代的生存方式一种。摇滚部落的正规军与后备力量总是活跃在都市的边缘、都市的夜。他们的音乐也总泛滥着酒吧里颓败而幼稚的气息;他们的嗓音漂浮着在重金属的铿锵中撕裂的破碎。他们的青春是过度燃烧的;不同的是,有些人在过度燃烧中感觉到的是痛楚,而有一些人则是从中体验到了巨大的快乐。很难说摇滚是不是一定就要愤怒,是不是一定就要扮演叛逆的角色,热情地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快乐生活,似乎也没有什么错。但无论是快乐还是愤怒,选择了摇滚,似乎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对生活在社会中个人不断的自省,需要的是从日常的琐碎与无聊中提炼出对社会与人类的悲悯。毕竟,摇滚从它的起源之初,就有着一颗普照人心的跳动灵魂;仅有摇滚的音乐形式,仅有疯狂与空虚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状态,也许仍然背离着摇滚的初衷与终极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