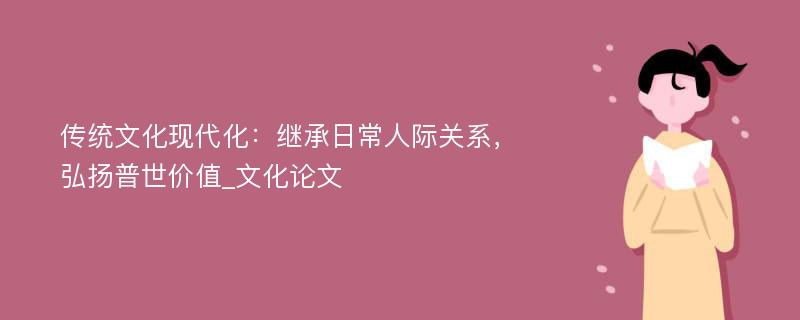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继承日常人伦,弘扬普世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伦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日常论文,价值论文,普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不能全部归咎于改革开放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落的?以1949年还是以1978年为起点?如果说是改革开放破坏了传统,那么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处于什么位置?难道文化大革命不算是对传统的破坏?
1949年以后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教科书中少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甚至明确反对传统文化,全国从上至下都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封建主义毒草,各条战线都在轰轰烈烈地对其加以消灭。多年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比比皆是的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殴打校长等现象,其对传统美德的破坏跟现在相比,谁更严重?
1949年是一个断裂——要建立一种新文化,要革一个文化的命——传统被破坏得天翻地覆、无以复加,这是一场巨变。对此,我们如果假装看不见甚至完全无知,是不行的。把现在的大陆人跟台湾人相比,这场巨变的影响就会看得非常明白。清华大学的校长向台湾客人赠送书法艺术品,竟念不出上面写的字。而我们去注意马英九的讲话,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对中国传统的弘扬,能让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差距就这么大。怎么来的?是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没断,在大陆却断掉了。
改革开放对传统有什么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系统的中央文件和一系列措施来宣布传统文化是毒草,没有发起政治运动反对传统文化,也没有谁一念到孔夫子就要打倒他,你能说它究竟破坏了什么传统美德吗?的确,人们开始重视物质,人性中的自利倾向得到极大的张扬,但这种自利完全是一种天性使然,为什么要把这一点看成是对传统的破坏呢?有的人臆想出一个1978年的断裂,事实却是:改革开放并未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也没有任何人要去故意破坏它。所以,1978年以后社会道德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尽管这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重视物质而轻精神,绝非中国一家,这是全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回顾一下“国学热”。有人认为“国学热”是从2004年开始的,这一年被叫做“中国文化保守年”,意思是从2004年开始提倡国学。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要重视国学了,而且势头更大。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毕全忠的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当时提的问题跟现在一样:中国社会太重物质而轻精神了,面临着精神文化危机,因此要用道统来挽救。这个提法在全国正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院长企图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大批判运动,说那些提倡国学的人妄图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替代马列主义。之后这股思潮就被打压下去,直至销声匿迹。十年后,即2004年,复兴国学再一次被大张旗鼓地提出。
现在,我们说要恢复传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这里面,我认为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之所以现在会出现道德真空,是因为过去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学到的主要是阶级斗争,把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当作道德来灌输,而缺乏规范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因而必须用别的东西去补充它。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之后,我们渐渐把道德往人性方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被重视,这样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是一件好事。第二,我们并不是在一个充分自由的空间里看文化和精神,然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要回归传统:完全回归传统也是不现实的,现实给我们划定了一个很大的界限,回归途中我们有着太多的限制。
二、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道德问题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被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价值观所伤害,因此中国的社会风气需要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到竞争与合作、利己和利他的平衡中去寻找。
其实,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利他主义是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流传下来的——文天祥、林则徐等人都用实际行为对之做过很好的诠释——不应该把它们归结为某一个党派的主张,更不要局限于某个党派在某个时段的主张。而且,这些概念应视具体背景而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提倡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利他主义,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金训华,他为了抢救被洪水冲走的集体财产(几根木材)而淹死了。如果我们真正以人为本的话,会把生命看得很重:抢救集体财产当然应该,但为什么要为此把命送掉?而那时毛主席的号召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文革”结束后,我们有一个拨乱反正,那种虚伪的、毫无人性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利他主义,是不应该要的。比方说劫机犯劫机,如果提倡乘客和乘务员跟劫机犯搏斗,谁不搏斗就是怕死鬼,会造成什么后果?那不就机毁人亡了吗?所以,现在我们提倡不要盲目地与劫机犯搏斗。中国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时代,后来提出应考虑个人的权利、利益,甚至要理直气壮地去追求,这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人类的共同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个人、利己、竞争的观念相对于那种非常虚伪、漠视人性的所谓“美德”而言,是一个进步。然而,挣脱“文革”极左思维,对竞争、个人、利己主义适当地肯定,这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举个例子,直到最近两三年,我们才开始强调小学生到外面不应该盲目地见义勇为:一个小孩子遇到匪徒,怎么去见义勇为?那是威胁到生命的事情!
出于这些考虑,当谈到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好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作参照物,首先想到这些好词可能代表着一些不合理的、偏执的东西;然后第二点我才说,我们现在对那种不合理的观点的纠正又过了头,有了偏差,存在极端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我们应该回过头来作一定的改变,但一定不能去歌颂那种极端的价值观。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意识形态现在仍然存在,一些当官的还在侵犯着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在拆迁、侵占土地问题上,用的全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公共利益这些词汇。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个人利益是绝对应该肯定的,这种个人权利应该受宪法保护。个人、利己、竞争不是天然的负面词汇,同样,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也不是天然的正面词汇,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用一些人类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如果是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权利,是联合国宪章肯定的政治文明的内容,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争取,而任何利用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名号来侵害他人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另一个层面,除了宪法和法律,我们还需要提倡道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然是不对的,但站在宪法的角度,我认为首先还是应当肯定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因此,有两个维度至少同样重要:一方面,那种物欲横流的价值观确实不应该有,我们应该讲求集体利益,讲求道德;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用虚伪的道德来禁锢人,更不能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号去侵害个人的合法权利。
三、中国现代化所需的价值观不能完全由传统获得
在当代中国,有人问:很有必要呼唤传统吗?这个问题其实隐含了一个倾向,就是已经把传统当作正面价值了。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传统,难道不应该作区分吗?
其实,中国近300年来,一直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复兴传统文化,这种力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文化形态的国家来说是很正常的。西方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基督教,有人说我们必须首先基督教化,然后才能很好地现代化。这在学理上表面也有一定的道理——学东西要学彻底,不学它背后的文化,就学不到这个制度。因此有人主张先基督教化,后现代化。这当然是一个很荒谬的想法,任何一个中国人凭直觉都不可能认为应该这么做。因为中国人之所以成其为中国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还是在起作用的,中国人中间有一些会成为基督徒,但要13亿中国人全变成基督徒,显而易见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300年来,中国人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复兴儒家文化。这件事情是一些大思想家和学者在做,但到了近代,就出现问题了。鸦片战争中,中国饱受欺凌,被西方帝国主义打得很惨,从那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国家必须要富强、人民要富裕,而且政治要民主,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应该讲究科学、理性这一套。很明显地,我们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中国必须现代化,但是跟现代化有关的东西,中国的传统并不能提供给我们。例如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等,都是起源于西方的,而不是中国本土文化中固有的,但它们又是我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吸收的。我们提出要弘扬中国文化,这是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而问题就鲜明地摆在面前了: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应该主要学习西方,还是主要弘扬传统文化?
主张复兴国学的人就是要证明:中国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也能够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谈到我们所追求的价值,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这些价值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已经有,我们干嘛要去学习西方呢?继承我们老祖宗的这些东西不就成了吗?所以300年来,尤其是近100多年来,中国真正有学问、有思想的人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的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能够给我们提供,否则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学西方,对不对?
中国那些真正要复兴传统的人—牟宗三、唐君毅等——下了很大的工夫,在20世纪30—50年代发表了各种宣言,试图证明现代化价值能够在儒家文化里面找到,但是最后全部失败了。因为那些价值观在儒家思想里面找不到,即使可以联系起来,也很牵强。他们找到的最关键、最重要的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西方不是要民主吗?但这句话跟现代的民主根本是两回事。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类,可能接近于民主,虽然比那些三纲五常要好得多,但也绝不是现代民主的东西。
四、可以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日常人伦和普世价值
现在,在海外用中文写作的最著名的学者余英时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弘扬,而不希望我们只学习西方。余先生在论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时,实际上将其分为政治文化和日常人伦两个部分。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都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核心其实是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与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想依靠自己的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化,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实践中行不通。与张、李不同,余先生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与区分:传统文化除了政治文化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孔夫子思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人伦,这一部分文化是有活力的、可以被继承的。
我觉得余先生这个话讲得非常好。政治上的道统我们是坚决不能要的,如果我们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日常人伦方面,会发现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道德文化,而且这一部分是永远不会丢失、永远有生命力的,是西方文化无法取代的。因为西方跟中国所讲的道理还是有差异的,比方说西方肯定不讲“温良恭俭让”,不讲“文质彬彬”。大哲学家罗素在西方是一个大讲道德的人,为什么他来到中国还十分欣赏中国的道德文化呢?因为西方虽然有很多东西很好,但道德是有独特性的,中国的“君子”概念跟西方的“gentleman”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能够给人们的日常伦理道德提供有用的东西,比如说讲求温柔敦厚、温良恭俭、邻里之间的亲睦,等等,去重视、弘扬这些,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去粗取精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总的来说,余英时先生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在学理上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在现实中也能够起正面作用。
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道统和传统。道统,主要指的是一个核心的政治文化,即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为妻纲等伦理道德,也就是从秦始皇以来一脉相承的为皇权、为专制服务的一大套完整的政治文化体系。尽管它也代表着一种道德文化,但这种道德同样也是为皇权、专制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道统并不是一件好事。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恢复一些传统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把道统和传统混为一谈,不应该用“道统”,不应该继承“道统”。
除了“温良恭俭”等日常伦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或者说吸纳更多的传统。比如孔夫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跟宪政民主中的一些理念就结合得非常好。其实,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对一些基本道理的表达几乎都是相同的,因而可以互通。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来解释宪法精神甚至联合国宪章都是可以的。像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可以古为今用。
每个民族的文化中既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好的东西之所以好,是因为它用非常精炼的语言,高水平地表达了普世价值。比方说西方有一个“金规则”,其实用英文表达,意思完全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实际上是最伟大的,它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它是我们东方独特的——独有的并不一定是有价值的,例如娶妾、裹小脚、打麻将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西方没有而我们独有的——而是因为它是全人类都一致认同的价值,而且我们应该为此而骄傲:你看,我们的孔夫子说得多么好,西方人的“金规则”跟我们的表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不应该刻意去强调它的独特性,这些值得我们骄傲的老祖宗的思想,恰恰是跟普世价值一致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