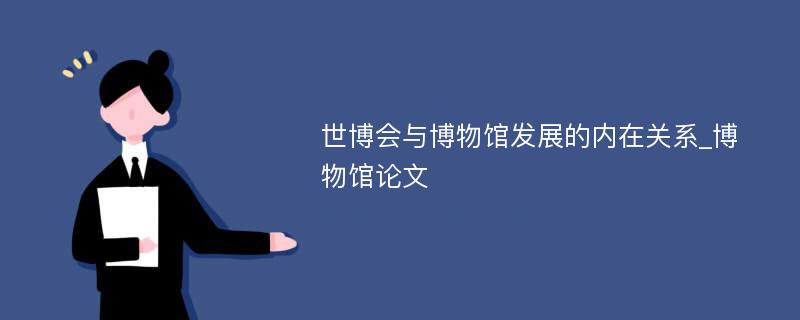
世界博览会与博物馆发展的内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物馆论文,关系论文,世界博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3-0108-12
毫无疑问,世界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博会)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国际性盛会,对举办城市乃至整个举办国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世博会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而言,一般学者可能关注的是世博会给城市留下的地标性建筑,诸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原子塔、美国西雅图的太空针塔、日本大阪的太阳之塔等,而对于博物馆学者则不然,他们更关注世博会对举办城市博物馆事业的推进。在此,我们以历史上世博会的筹办、世博会后展馆的利用、世博会展品为博物馆收藏以及博物馆专家参与世博会筹建等内容为研究视角,透过世博会推动博物馆发展的表象,考察世博会与博物馆发展之间的互动,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世博会对博物馆发展的推动
纵观历史上世博会对博物馆发展的推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博物馆的建设,增加博物馆的数量和种类;二是世博会的展示理念与技术被移植到博物馆中,使博物馆的陈列展示技术不断得到提高。关于第二个方面,我已有专论发表,[1]此不赘言。这里着重阐述第二个方面,即世博会如何通过增加博物馆的数量而推动博物馆发展。
(一)筹办世博会期间的博物馆建设
世博会是规模最大的商业展示盛会,为接纳来自世界各地数量巨大的参观人流,举办城市必须具备在连续数月内接待数以千百万计参观者的条件。为此,在世博会筹备阶段,主办方除了要在世博园区建造展馆之外,还要改善举办城市的基础设施,改进交通、住宿、餐饮、旅游等条件,提升接待能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参观浏览环境。世博会既是一项重大的商业经济活动,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大舞台,利用举办世博会传播民族文化,扩大国际影响力,这是主办方显示本国文化实力的极好机会。因此,以展示本民族艺术文化为主体的艺术宫也往往成为世博会展览中的重要项目。纵观世博会历史,世博会筹办期间建设艺术类博物馆受到许多举办城市的高度重视。这里参考哈维尔·蒙克鲁斯对世博会历史的分期,① 就不同历史时期世博会在筹办期间建设博物馆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分析比较。
在第一阶段“历史意义上的世博会”时期(1851—1930年),在筹办世博会期间建设博物馆的现象比较多见,第一阶段的20届世博会中,约有半数以上都在世博会期间建设了博物馆。譬如,1876年美国为纪念建国百年而在费城举办的“世纪的进步”世博会,世博会期间建设了艺术宫,世博会后留下成为费城美术馆。1893年的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在杰克逊公园开幕,会后场址由公园理事会管理,公众可以免费参观。不料后来发生了两次火灾,场址内一些主要建筑先后在大火中被烧毁。到1896年春,场址所剩下的展会设施都被拆除或搬迁,只有艺术宫例外,它被零售商菲尔德(Marshall Field)以高于15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转并到菲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Field Columbian Museum)名下,最终成为该世博会唯一留存在原址的建筑(现在是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之一部分)。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建设的圣路易斯艺术宫是该届世博会上耀眼的展馆之一,世博会后经过圣路易斯市民投票通过,该艺术宫留给圣路易斯城,转变为圣路易斯美术馆,连同世博会上展出过的雕塑和绘画作品,都成为该馆的永久性藏品。[2]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在旧金山举行,在博览会后的十个月内,为了拓宽旧金山的城市空间,几乎所有的博览会建筑都被拆除了,只有旧金山艺术宫被保存下来,成为该届国际博览会的历史见证。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诞生了以相互毗连的大王宫和小王宫为主体的博物馆群。小王宫现在主要收藏和展示19世纪法国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大王宫的一部分建筑现在则被巴黎“发现宫”永久使用。
除美国和法国之外,西班牙也在举办世博会期间建设了博物馆。1908年西班牙萨拉戈萨世博会建设了美学艺术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和医学馆,会后这三座馆被永久保留。1888年和1930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两次世博会,也都新建了博物馆。
在第二阶段“现代化时期的世博会”时期(1931—1988年),由于受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主办方对举办世博会的经济利益更加重视,并逐渐考虑到世博会对主办城市产生的持续效应。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筹办世博会同时建设博物馆现象有所减少,但是世博会后将展馆转变为博物馆的现象却明显增加。如1937年专为迎接巴黎国际博览会而兴建的著名建筑——夏洛特宫,现在已是包括法国建筑艺术博物馆、海洋博物馆、电影博物馆和人类博物馆、文化遗产博物馆等在内的博物馆群的核心建筑。1939—1940年的美国纽约世博会,会后将展馆中的科技馆作为博物馆的一种类型而保留,并一直对公众开放,而当年的另一展馆——昆斯艺术博物馆现在也依然存在。在筹办世博会同时建设的博物馆有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该馆是1937年巴黎市政府为举办国际博览会而建的永久性展馆。另外,1967年加拿大蒙特利世博会建设的艺术博物馆、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建设的世博美术馆(现为国际美术馆)和日本民间艺术博物馆,也都在世博会后被保留下来。
在第三阶段的“全球化与后现代时期的世博会”时期(1989—2010年),由于此阶段世博会的人文色彩日益浓重,主题性世博会已占居主导,加之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世博会规划产生的影响,因此,筹办世博会期间建设的博物馆不再是作为单纯的展览项目,而与世博会主题以及城市文化的未来发展紧密相连。如1998年葡萄牙里斯本世博会的主题是“海洋,未来的遗产”,主办城市建造了一座巨型海洋馆。按照先前的建设规划,海洋馆在世博会后留下。目前该馆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水族馆(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的定义,海洋馆属于博物馆之一种类型)。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的城市生活离不开博物馆,在迎接世博会的日子里,上海也把博物馆建设列为重要项目之一。正在筹建的各类博物馆以反映上海城市的历史文化内容为主,诸如位于江湾地区的上海文学馆、位于徐家汇地区的土山湾遗址博物馆、位于苏州河沿岸的上海近代民族工业专题博物馆等,另外还有与本届世博会内容直接有关的世博会历史博物馆和城市足迹馆等。上海的各类博物馆数量已达到一百多座,2010年世博会开幕之际,又有一批新博物馆将诞生。乘举办世博会东风展开博物馆的建设热潮,不仅为上海增添了一批富有特色的博物馆,而且也将使上海的博物馆数量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博物馆数量差距大为缩小。
(二)世博会后展馆的博物馆利用
早期的世博会几乎不考虑展馆的后续利用。1851年伦敦首届万国博览会(该博览会也被认为是首届世博会)在海德公园开幕,博览会结束后,作为唯一的展馆建筑——水晶宫便被拆除。② 正是由于水晶宫的设计便于建造与拆除,因而在众多的方案中胜出,为主办方所选中,这反映了主办方当时并没有对世博会展馆与世博会园区再利用的打算。总体上看,早期的世博会结束后展馆拆除或迁移,展品由原主收回,展会场地恢复原貌,是其惯例。即使有人不赞同,甚至是重要的政府领导人,也是无能为力的。譬如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之后,除了圣路易斯艺术宫之外,所有世博会展馆都被拆除或搬迁,没有留下纪念物。为此,当时的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只有一个遗憾,一个深深的遗憾:那些建筑和展品(指世博会展馆和展品——笔者注)未能被永久地保存,未能作为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永久纪念继续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3]
20世纪30年代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由于经受了世界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破坏,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有一些世博会出现严重的经济亏损,促使主办者为了弥补亏损而在世博会后的场馆利用上开动脑筋。当然,在世博场馆的后续利用方面,主办方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展馆多改为商务用途或其它文化消费设施等。但是战后世界各国出现的旅游热潮,使主办方看到博物馆不仅仅是一项文化事业,也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它能促进交通和消费,从而带动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价值。于是将有些场馆直接转为博物馆使用就成为在世博会后的一种选择。如1962年美国西雅图世博会,在负责景观的迪斯尼公司帮助之下,围绕着世博会中心展区建立了三个永久性建筑群:歌剧院、大剧院和美国科学馆。世博会后,科学馆转变为太平洋科学中心(属于科技类博物馆之一种),英国馆成为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分馆,加上被搬迁到世博会场址附近的弗兰克·盖瑞的设计博物馆,三者组成了博物馆群,与歌剧院、大剧院共同组成了文化娱乐中心。1967年加拿大蒙特特世博会,会后不仅留下了艺术博物馆,而且还将美国展馆改为环境展览馆,将法国展馆改为博物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受布伦兰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影响,世博会场馆的后续利用更受重视,国际展览局明确要求主办方在申办世博会时,其建设规划中必须有世博场馆的后续利用这一项内容。由于博物馆在当今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一些国家在设计规划世博会场馆时,就作出了在世博会后直接将一些展馆转变为博物馆的计划。如1993年韩国大田世博会后,将原各国的工业展馆整体保留,并将其变为永久性科普展馆(属于科普类博物馆之一种)。1998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世博会的会场设于城市内的布里斯班河南岸,世博会结束后,主办方将世博会场区改建为南岸公园,园内建有主题博物馆区,包括热带雨林保护区、蝴蝶和昆虫馆、昆士兰文化中心,很好地诠释了该届世博会“科技时代的休闲生活”这一主题。2008年西班牙萨拉戈萨世博会对展区以及展馆的后续利用也有规划:将展区转变为一个科学文化园区——水主题大都会公园。部分展馆将被再利用(如将河流生态系统的主题馆转变为水族馆,将水塔转变为选择性功能的博物馆),整个展区将改造成为一个集娱乐、休闲和文化科技用途于一体的城市区域。目前这一规划正在实施之中。
上述各国世博会展馆的博物馆再利用,在形式和方法手段上都因举办城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不同而各有差异,但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将部分世博会展馆转变为博物馆而再创辉煌,推动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可谓殊途同归。
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有会后将部分世博展馆转为博物馆利用的规划。上海世博会园区选在上海母亲河——黄浦江边,即位于南浦大桥与卢浦大桥之间的浦江两岸。这一区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江南造船厂(前身为距今140多年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内的一大批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筑等。按照上海的“申博”规划,[4]世博会园区占五分之一是旧工业建筑改造而成的展馆,如江南造船厂内的部分旧厂房将成为企业馆所在地,原上海南市发电厂的主厂房建筑也将被改造为世博会主题馆之一的“城市未来馆”。在世博会场馆建设的过程中,对那些具有历史价值和利用价值的工业建筑、船坞等遗址,我们将分别进行有效保护和改造,并利用旧工业建筑建设一些工业遗址博物馆。世博会结束后,不仅这些博物馆将被保留,世博会的部分新建展馆还将改建为博物馆。届时,上海世博会园区将会出现一个博物馆群,这是推进上海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世博会历史上的一大特色。
二、博物馆与世博会的互动
就博物馆方面看,世博会是博物馆发展的推进器。但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因为从某种角度说,建设博物馆也是举办世博会的需要。博物馆内容融入世博会展示之中,成为整个世博会之一部分,博物馆补充和丰富了世博会的内容。因此,世博会推进博物馆发展,不只是一种单向的促进,博物馆同时也为世博会增光添彩,相得益彰,两者呈现共同发展的面貌。
(一)博物馆为世博会增光添彩
历史上的世博会,不仅仅是展示科学技术的成果,人文艺术内容也纳入其中,成为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展示的国际盛会。从1855年法国世博会开始,人文艺术的内容出现在展会上,与科学技术的成果交相辉映。在1855年的世博会上,法国特意展出了为世博会而专门召集二千名艺术家创作的绘画作品,虽其初衷是为宣传法兰西民族的灿烂文化和艺术,但这一浪漫的创举,却对后来的世博会产生巨大影响,被纷纷效仿,由此改变了以往以工业发明新成果展览为主的世博会。以后,雕塑和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也纳入其中,展示民族文化成果的美术馆(或艺术宫)成为世博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艺术类博物馆作为收藏和展示艺术的主要机构,在世博会期间成为观众参观浏览、了解异国他乡民族历史风情与文化艺术的重要去处。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非常重视博物馆的建设,并且在这方面比以往的世博会有更大的突破。在筹建上海世博会的过程中,上海各界正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对上海的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整合,融入富有时代精神的内涵,建设各种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博物馆。
上海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上海开埠以来,根底深厚的本土文化以开放的胸怀面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勇于创新,从史前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到近现代的石库门文化,几千年来沉淀的地方本土文化,经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海派特色文化。如今的海派绘画、海派戏剧、海派电影艺术、海派文学、海派建筑、海派饮食、海派收藏等等,这些都是得天独厚的博物馆资源。
另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上海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七宝的皮影戏、崇明的扁担戏、南汇的锣鼓书、青浦的田歌、嘉定的竹刻、金山的农民画、三林的刺绣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浅显与世俗的特点,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却反映了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深层次的内涵,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将它们保护、传承和发扬,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市民的文化艺术生活,而且将为上海世博会的参观者提供一道充满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大餐。
根据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发展规划,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上海将有150座博物馆建成开放,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以海派文化与民间非物质遗产为主题的博物馆。为了办好世博会,上海加快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步伐,在短短的几年中,诞生了近百座博物馆,这是上海博物馆发展史上所没有的,也是世博会历史上所没有的。上海的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效增强上海世博会的文化含量。届时,“到上海去看博物馆”,将成为世博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博物馆专家参与世博会的筹建
博物馆具有展示的功能,因而历史上博物馆专家参与世博会的筹建并不鲜见。博物馆专家与其他参与世博会展示设计的人员(包括商业公司)共同筹建世博会,这是双方相互学习的极好机会。博物馆专家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奉献给世博会,为世博会提供智力支持,而参与世博会展示设计者或世博会组织筹备者将世博理念直接传入博物馆,双方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在一些发达国家,许多博物馆的展示设计早就由商业性展示设计公司承担了。委托商业公司承担,这就为博物馆移植和吸收世博会的先进展示理念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世博会展馆的设计往往是由许多商业设计公司参与承担的,而承担过世博会展示设计的商业公司设计师,在为博物馆展示设计时,自然而然地会把世博会展示设计理念应用到博物馆展示中来。如美国的工业产品包装与艺术设计师Walter Dorwin Teague(1883—1960)就是一位既参与世博会工业展品展示设计也参与博物馆展示设计的典型人物。他曾为工业界设计“机械艺术展示”(Machine Art Exhibition),在1933—1934年的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中,主持设计了福特公司的展馆,又在1939年的美国纽约世博会中,为参展商公司负责展馆设计,后来又为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美国工业艺术展示”(American Industrial Art Exhibition)的设计。人们从其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设计中,看到了他从世博会展示设计中带来的创意。另外,还有些曾是世博会举办城市主办组织的成员,在世博会后担任了博物馆的领导。如承办1934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的董事会成员Rufus Daws、Lenox Lohr和Allen D.Albert等,前两位在世博会结束后,先后担任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馆长,而后者则担任印第安纳Terre Haute美术馆馆长多年。他们参与世博会的经历和体验,在其各自的博物馆展示中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迹。
世博会是规模庞大的展示盛会,举办城市在筹备过程中,必然要组织和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其中有些展示设计本身也需要依靠博物馆专家们的帮助来完成,尤其是人文艺术类的展示。博物馆专家有机会参与世博会的筹备,既可直接与商业公司的展示设计师们交流,学习和吸收新的展示理念,同时也有了展现自己才华和睿智的机会。如1937年,担任斯密森机构(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执行秘书助理的古德先生(G.B.Goode)参与了美国芝加哥世博会筹备工作。斯密森是一个综合性研究机构,其下属有十多座博物馆,古德先生作为一名博物馆专家,当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世博会不是展示物体,而是展示理念”。此后,世博会的展示出现了这种趋势,即一种理念的展示。这种“展示理念”的思想一直影响到现在,并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由此可见,博物馆专家对世博会的智慧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组织筹备中,有两个展馆(世博会历史展示馆和城市足迹馆)的展示内容与设计,主要有上海博物馆界专家与高校、设计研究院、所等专业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团队来负责完成。各路专家汇聚一堂,相互切磋,探讨创意,建言献策,群策群力。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界专家借鉴世博会展示的历史经验,探索主题性展览,结合博物馆学专业知识,在主题演绎和展品设计上,注重体现世博精神,力求使世博会的展示理念与展示技术真正达到当代先进水平。
(三)博物馆收藏世博会展品
博物馆机构的性质、功能与使命,决定了它必定要承担收藏世博会展品的义务,从而注定了它在传播世博精神、延续世博会使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世博会的展示都有期限限制,一般每届为期半年。最辉煌的世博会也有闭幕的时候。所谓“永不落幕”的世博会,仅仅是人们对成功的世博会虽已闭幕但愿其精神长存、影响永续而表达出的一种美好愿望。而要弘扬世博精神,延续世博会的影响力,使之对一代代后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世博会展品的收藏、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
每一届世博会结束,都会留下大量的资料,除了世博会展品实物之外,还有大量的以文字记载为主的各种原始文件(如筹办规划、决议等)以及大量有关世博会各项活动的报道、或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和图像资料等。在所有的这些资料中,展品实物是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资料。文字记载和图像资料固然需要,但这些都是间接的物证,更重要的是直接物证。世博会展品是直接体现世博会的最珍贵资料,它对传播、延续世博精神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百五十多年来,世博会作为一个舞台,汇集了各时代人们创造发明的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许多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物,如电话、留声机、打字机、电视机、电脑、复印机、机器人……最早都是在世博会上与人们见面的,它们代表了当时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无论从历史的价值还是从科学技术的价值考虑,都值得博物馆收藏。今天,人们正是在博物馆中看到了这些人类文明的创造物,从中感受当年的世博精神,领略世博文化的魅力。
在世博会第一、二阶段的历史时期,筹办世博会期间专门建设的博物馆主要都是艺术类馆,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几乎没有。然而,在世博会的推动下,人们对世博会科学、工业的展品收藏热情,促成了欧洲各国在一届届世博会后兴起建设科学与工业类博物馆的热潮,一些世界著名的科学技术类博物馆由此而诞生。
最早收藏世博会展品的博物馆当属现在的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后,主办者阿尔伯特公爵利用举办博览会的盈余购买了5千英镑的展品,并于1852年建立了装饰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展示这些收藏品。③ 伦敦科学博物馆也是较早收藏世博会展品的科学博物馆。1909年,该馆收藏了1851年和1876年国际博览会的一些机械方面的展品,以及瓦特在1788年发明的蒸汽机和史蒂芬生在1829年发明的“喷射号火车头”等最重量级的科技展品,成为当时世界上收藏科技文物最多和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博物馆。
在首届伦敦万国博览会后的半个多世纪,欧美地区陆续举办了世博会,刺激了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博物馆的诞生。例如1862年在伦敦举办的世博会,促成了捷克布拉格市的波西亚工业博物馆的建立(后来改名为捷克国立技术博物馆),该馆的许多展品购自伦敦和巴黎世博会。又如1873年的世博会和1908年的奥地利博览会,导致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博物馆的创立。1876年美国费城“世纪的进步”世博会,促成了华盛顿斯密森机构下属的国立博物馆艺术与工业部的建立。该馆得益于世博会恩赐甚多。世博会后,来自30个国家的有关自然史、技术、工业方面的展品中,多达21节火车车厢的展品都捐赠给了博物馆,这些捐赠品为国立博物馆新建立的艺术与工业部奠定了基础。
在世界科学技术博物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德国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与世博会也有缘。该馆创始人米勒(O.Von Miller)是德国著名的电气工程师,他曾在德国负责举办过两次有关电力的国际博览会,即1882年的德国电力博览会以及随后在法兰克福的国际博览会。通过博览会,使他萌发了创办一个与众不同的科学博物馆的念头。他认为科学博物馆重点应该展示机器运作情形的实物或模型、科学演示以及观众能够参与的展示设备,以便有效阐释说明有关科学、工程学和工业的历史及其原理。[5]在一些政界、工业界和科学界名流的支持和赞助下,他组建了一个基金会,从各处收集展品,并参加世博会后展品的拍卖,从而购买了不少世博会展品。德意志博物馆收藏了许多由德国人发明的、在世界科技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物证,如1799年布兰德发明的反射望远镜,1866年西门子发明的第一部发电机,1866年本茨创造生产的第一辆汽车,1895—1896年间伦琴发明的X光发射管,以及1897年狄塞尔法发明的第一座狄塞尔引擎等等。
在世博会历史上,博物馆收藏世博会展品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由主办方出资直接购买世博会展品,建立博物馆,或将展品送到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典藏。如上述1851年英国伦敦的万国博览会,尽管世博会之后,很多展品物归原主由商家收回,但是还是有一些展品在拍卖中为主办方所购买,以此建立了装饰艺术博物馆(以后又成为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又如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后,部分由企业、个人提供的展品归还原主,还有许多展品,尤其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的工业展品则都送往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收藏,成为该馆第一代展品的基础。[6]31
其二,是由基金会或个人出资购买和收藏世博会展品,后来捐赠给博物馆。如上述的德意志博物馆创始人米勒,以基金会名义购买的世博会展品,成为德意志博物馆的永久性收藏。美国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中收藏的部分个人捐赠的世博会展品主要来自于两个人:菲尔德(Marshall Field)和冯格(Silas Fung)。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结束,零售商菲尔德出巨资收购了艺术宫,将其并入菲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该馆原来主要以收藏自然史藏品为特色,以后并入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个人收藏家冯格最初从收集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展品开始,世博会结束后,他购买了部分展品,以后又收集其他世博会展品充实其收藏,并建立了私人博物馆。到了晚年,他将私人博物馆的藏品全都捐赠给了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6]146-147
历史上世博会的许多重要展品,今天基本上只有在博物馆中才能看到,世博会的历史物证主要被保存在博物馆。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围绕着演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充分展示反映当今世界人们为追求“人与城市环境和谐”的美好愿望而创造发明的最新成果。展品是世博精神的直接体现,是世博历史最有力的物证。在世博会闭幕以后,世博会的精神与使命将通过博物馆所收藏、保存的世博会展品的展示而得到传播与延续。
2010年上海世博会场馆的后续利用规划中,已有将部分展馆转变为博物馆的计划,这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按照世博会惯例,世博会后展品物归原主,我们如果不积极主动征集,很多重要而珍贵的展品就可能消失。因此,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期间,我们一定要积极做好准备,确定博物馆需要的征集之物,一俟世博会闭幕,立即将它们收集起来,为博物馆提供藏品资源,同时也为传播与延续上海世博会精神与使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世博会与博物馆的内在关系
历史上世博会与博物馆的互动发展绝非偶然,有其共同存在的基础,那就是双方固有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具有共性的一面。世博会与博物馆虽属两个不同的行业,其社会功能和内容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以物品的展示服务于社会。正是由于这种“展示”的特征把世博会与博物馆连接起来,使两者之间产生重要的关联,使展览业与博物馆业成为最为相近的行业,这是两者的共性所决定的。世博会与博物馆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都以实物展示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
从信息传播角度看,世博会与博物馆一样,主要以实物为载体,通过对实物的展示,向社会公众传播知识和信息。博物馆陈列展示以实物为信息源,按照一定的设计理念,将实物(配合其它必要的辅助材料)组合在一定的空间系统中形成一定的形象体系,观众一般不必依赖语言或文字的解释手段就能理解展品,博物馆正是以这种特殊的“陈列语言”的方式,区别于以文字、言语和图片为主体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学校等机构的信息传播。但是博物馆的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在世博会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从博物馆展示技术的发展进程考察,我们发现近代博物馆陈列展示的理念与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留下了效仿世博会的痕迹。迄今,“一些博物馆、科学中心、航天中心……正在模仿运作最好的世博会展馆的一些做法”,“有些科学中心还通过有效地利用最新展示设备来吸引观众,例如IMAX电影系统、模拟器、虚拟现实和交互设备等”。[7]
世博会的展示理念与方法一直处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之中,从最初的动态展示到后来的互动式参与,又到现在的以强调观众“体验”为主的特征,即“解释和传播知识不再那么重要,关键要打动人,激发人们的想像”。[8]世博会展示中已越来越多地使用辅助手法(包括多媒体技术、图像、辅助模型和文字说明等)。尽管博物馆展示设计与博览会设计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展示设计中的一些基本理念与规律是相通的,这就为世博会增加博物馆展示内容提供了基础,而相似的信息传播形式又为博物馆展示融入世博会展示提供了条件。
(二)世博会和博物馆展示的都是人类创造物的精华
世博会既是世界经济贸易的盛会,也是世界各国文化、科技交流的盛会,这个盛会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博”与“精”,“博采众长,精髓汇集”是世博会的宗旨之一。各行各业的精华在会上展出,世界各国各民族间最优秀的事物、理念、技术、成果汇聚在一起,世博会提供这样一个舞台,使公众在短时间内就能够了解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科技的最新发展。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人类活动见证物的专门机构,由于博物馆的收藏空间有限,只能有选择地收藏那些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类活动见证物,它们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华,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的价值。博物馆向公众展示各国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文明的演进以及生态环境变迁的见证物,汇集了历史上的精华之物,供公众观赏、学习、研究,“博”和“精”也是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特色之一。
世博会展品与博物馆展品都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但是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实物都是历史遗留的精华,偏重于说明过去,记录着人类文明前进的足迹;而世博会展示的都是当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科技与文化的代表物,偏重于指向未来,预示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今天在世博会上的展品,就是明天博物馆里的藏品,正是从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了世博会与博物馆之间的前后连接,世博会为博物馆的藏品收藏提供了资源与机遇,而博物馆也成为传播世博精神、延续世博使命的重要场所。
(三)世博会与博物馆都是知识传播的课堂
世博会与博物馆同为实物展示之平台,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传播展品的知识和信息。博物馆通过藏品的展示,为社会公众服务,这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博物馆“既反映社会,又服务于社会”的主要形式。但博物馆展示的藏品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与价值,需要通过专家深入浅出的诠释,才能成为公众容易读懂的展品。
世博会是比博物馆展示规模更大的展览盛会,将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成果都囊括其中,集中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和信息。由于展出的许多先进科技对普通公众来说过于艰深枯燥,因此,世博会也肩负起对公众细述和解释的使命。世博会的各参展国在规划设计展览时,通过各种独特的创意和手段,力求将复杂而深奥的先进科技原理转化为一般人都能理解的知识,努力朝着使世博会成为“为成年人开设的科普常识大课”的目标前进。
如今的世博会以科学发展与人文发展为基线,融合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使之在成为向社会公众普及科学新技术的场所的同时,也是传播艺术理念的殿堂。通过展示技术,将展品所承载的深奥的科学原理和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知识,使一般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这是世博会和博物馆所承担的共同使命。世博会后部分展馆转变为博物馆(包括科学中心),这正是世博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和传播文化艺术理念使命的延续,体现了世博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四)世博会与博物馆都关注科学与文化
世博会虽然是从最初的商业集贸发展而来,但世博会不仅仅是一项重大的商业活动,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与文化活动,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本质上,世博会是人文精神的科技化、物化,也是科学技术的人文化”。[9]我们看到在世博会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以展示科学技术发展为主线到后来逐渐融入人文发展,进而科技与人文并重,形成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完成了世博会的转型。就大文化的角度而言,世博会展示的科技成果和理念属于人类科技文化的范畴,因而世博会的商业与经济活动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它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人文精神,积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
同时,世博会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大舞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民族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文化。与20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世博会相比较,现在的世博会更加关注人文发展,更多地重视人权、和平及国家间平等、文明的对话,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这些在战后的历届世博会主题中都得到明显的反映。
博物馆属于文化事业,对科学文化的关注自然是其分内之事。博物馆以其独有的藏品资源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而言,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文化精华的象征,是文化金字塔上的明珠。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将民族文化、民间艺术与民族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超越时空的表现手段,展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科学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如果说早期的博物馆偏重于藏品的收集、保护与研究,那么,现在的博物馆则更加关注社会对博物馆的需求,关注博物馆为社区服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博物馆协会一系列国际会议讨论的主题,充分反映了博物馆对社会和城市发展、对民族、生态、环境等问题的高度关注,预示了博物馆未来的发展趋势。
正是博物馆与世博会都共同关注科学与文化,因而两者展示的内容尽管在时代上有前后之不同,但其蕴含的科学文化内涵是一致的。徘徊于世博会与博物馆,人们在检阅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寻觅创新灵感,解读历史智慧,感悟艺术哲理,开拓新的知识,得到精神的升华。
总之,世博会举办的初衷并不是刻意推动博物馆建设,但是博物馆与世博会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促使世博会从筹办到结束乃至世博会展馆的后续利用,都与博物馆有着难解之缘,客观上起到了推进博物馆发展的作用。而博物馆也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方式,为世博会增辉添彩,回报世博会的“恩情”。
收稿日期:2009-06-15
注释:
① 哈维尔先生根据世博会对城市发展的关系,将世博会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历史意义上的世博会”、“现代化时期的世博会”和“全球化与后现代时期的世博会”。详见哈维尔·蒙克鲁斯·福拉加《世界博览会和城市规划》,于漫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9页。
② 虽然水晶宫设计者—英国园艺师帕克斯顿后来筹款在西德汉姆又重建水晶宫,但这并非是世博会主办者有意识的后续利用行为。
③ 该馆1857年改名为南肯星顿工业艺术博物馆,1899年,又改名为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标签:博物馆论文; 世博会论文; 展馆设计论文; 建筑文化论文; 国际文化论文; 上海世博会论文; 建筑设计论文; 展示设计论文; 科学论文; 上海博物馆论文; 上海论文; 建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