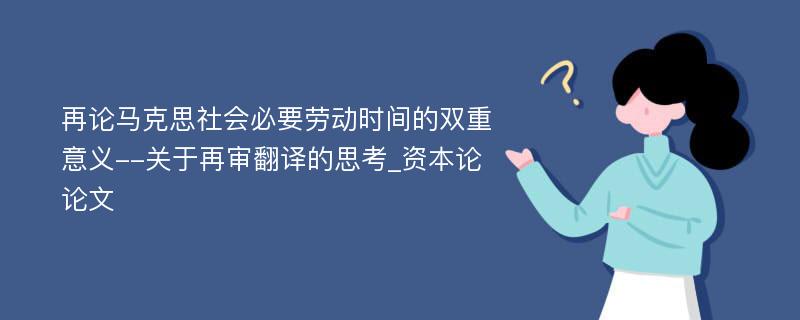
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重审译文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译文论文,含义论文,时间论文,社会必要劳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有关“双重含义”几处引发争议的重要译文欠妥(注:我在拙作《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层研究》(之一)(载《当代经济研究》1997(2)中曾指出《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版某些译文欠妥。 但它不全、不准确,而最大不足之处,是没有对照德文原文。)
1.决定价值(量)的使用价值(量)的前提, 不应是“某种”使用价值(总量),而应是“任一”使用价值(单量)。
《资本论》第一卷第52页(全集版)在接连两小段不算长的论述价值决定中,对它的使用价值前提一共使用了3 个限制词即“某种”(如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一定量”(如说“在英国……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和“单个”(如说“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单个的含义不会误解,而“某种”和“一定量”,则看读者如何主观理解了。韩凤来先生文章说,“请大家注意这里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提法。我们认为这里的‘某种’,主要是指同类商品的总量而言。”(注:韩凤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双重含义’之我见》,载《理论探讨》,1998(1),37页。)其他人也有类似见解。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呢?难道《资本论》第一卷价值决定的使用价值前提或载体,可以任意采用,没有内在同一性要求要遵循的吗?难道单位量、一定量、供求总量这样3个一看就知是彼此不同、 彼此排斥的数量关系,可以愉快地被集合到一起,用以限制同一个价值量关系?
我以为,不会是也不能是这样。对同一价值关系必须采用同一使用价值前提。《资本论》第一卷商品价值的使用价值量前提,严格的典型的规定是单个量,某些场合,也可以是一定量。但单量与一定量必须各自独立平行,不能混用,如果是对“单位商品”规定价值,其使用价值量的前提,就一定还是“单位”量,如果是对“一定量”商品规定价值,其使用价值量前提,就一定还是“一定量”。至于总量使用价值,在此处一定要排除,而留到《资本论》第三卷。
重要的问题在于全集版中译文不妥。在它译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时,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52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把制造“某种使用价值”说成价值决定的前提。但是,我国最早著名翻译《资本论》的两位学者郭大力、王亚南于1953 年和1963年在此处则译作生产“任一个”(注:马克思: 《资本论》,中文2版,第1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或“任何一个”(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2版,第1卷,1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任何一个”当然属于个量,而不属于总量。而郭、王译文是准确的。请看德文原文和曾当作世界语英文译文。
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lich notwendige Arbeitszeit istArbeitszeit,erheischt,um irgendeinen Gebrauchswert mit denvorhandenen gesellschaftlich-normalen produktions-bedingungenund dem gesellschaftlichen Durchschnittsgrad von Geschick undIntensitat der Arbeit darzustellen.”(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原版,第2卷,53页,柏林,1962。)
英文译文为:“The labonr-time socially necessary is that required to produce an article under the normal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with the average degree of skill and intensity prevalent at the time.”(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卷,39页,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73。)
德文中“irgendeinen Gebrauchswert”和英文中“anarticle”,中译文分别应为“任何一个使用价值”和“任何一个物品”。都与总量规定无关。
说到“一定量”那本是对一个分量的泛称,是为了表述某种灵活的数量关系的需要而使用的。它包括个量,也可是比个量更大的量。但不是总量。例如,马克思说:“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的交换价值”如何如何。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的“一夸特”就是“一定量”的举例。马克思又说“我说一码麻布值2磅咖啡,麻布的交换价值就 在咖啡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 而且是在这种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上表现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这里“2 磅”就代表一定量了。但无论如何,不能用全部咖啡的量来表现一码麻布的交换价值。马克思说:“一切商品都按一定量的金和一定量商品含有等量劳动时间的比例用金来衡量自己的交换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此处“一定量”表示多少,根据金和麻布双方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在等式两头,可能出现多种数量关系,但不可能两头都是各自的全部产量。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会在保持“劳动时间相等”的原则下,能恰好用金的全部产量来衡量麻布的全部产量的交换价值?
可见,经过对译文校正之后看出,《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第一章讲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本不包含第三卷第37章所说的“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容。还是个量与总量两种含义。
2.《资本论》第三卷(全集中文1974年本)第716 页关于价值规律所指的对象和内含译文有误。
全集本此处有这样一段译文。当把社会必要劳动概念从农业引入“社会内部的一切分工”时,马克思说,这是“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如果这种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比例量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
这又是一段引起不同理解的译文。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第二含义”只“影响”价值“实现”(“出售”)。相反则有些人由此获得证据,认为价值规律总是关于总产品的规律,而按社会不同需要量分配社会总劳动时间,正是价值规律的内含和要求。到底如何判断,还得看德文原文和英文译文中中间的那句话。
德文原文在讲了如果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各类商品就会按照它们的价值售卖之后,这样写的:“Es ist in der Tat das Gesetz desWerts,wie es sich geltend macht, nicht in bezug auf dieeinzelnen Waren oder Artikel, sondern auf die jedesmaligenGesamtprodukte der besondren,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verselbstandigten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sspharen”.(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原版,第25卷,648页,柏林, 1964。)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Wie es sich geltend macht”。 中译文应为“好象会自我运行的力量”,另一个是“in bezug auf”,意为“关于”、“论及”。都是用来形容限制、描述前面价值规律的。德文这一段译为中文应该是:“事实上这就是那个好象会自我运行的力量的价值规律,但它所论及的并非关于个别商品,而总是关于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下面就接着讲价值规律对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
可见,这里完全找不到什么“价值规律所影响的”这样的模模糊糊的词句;而是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就是关于总产品的规律,其内含更侧重按社会需求的比例分配的社会总劳动时间。此即“第二含义”必要劳动价值论的主张的由来。
英译文有两种,稍为复杂一点。其一为前面讲了的莫斯科版,谈到价值规律时是这样:“It is indeed the effect of the law of Value,not with reference to individual Commodities or article……”(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5卷,620页,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effect是多义词,有作用、影响、要旨、意义等多重含义,而译作“影响”,远不及译作“作用”、“要旨”更为适当,“With feference to”也是“关于”、“论及”之意, 全无“影响”含义在其中。英文芝加哥版,谈到价值规律时, 又是这样写的:“ It is indeed the law of Value,enforcing itself,not
with reference to individual Commodities……”(该书第745页)。 这里除 with reference to
与莫斯科版相同外,
不同的地方是用enforcing itself,不用effect,前者意为“一直在坚持自己要求的”,是现在进行时分词,用来限制“the law of Value”的。可见,英译文也不能为总劳动时间只“影响”价值的实现找到根据,反而也是直接把总劳动时间合理配置规定为价值规律的内含。
中国历来有两个由郭大力、王亚南提供的中译本。都无“价值规律所影响的”文句,1953年版本,意简而明,在“售卖”之后就译为:“事实上,这就是价值法则。不过这里说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是特殊的因分工而独立化的社会各生产部门各个特殊场合的总生产物(第830 页)。1963年版本,则显更完整:“事实上那就是那个一直在发生作用的价值规律,不过这里有关的,并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在每一个特殊场合的总产品”(第746页)。与德文原文很接近。郭、王既是翻译家,又是研究家, 因此他们的中译本比较准确是自然的。
因此,如果要对过去几种中译文本表示有所赞同的话,当然是郭、王1963年的译文。
至于所谓“实现”(出售)问题,当然是以价值已经形成为前提,而这一形成又是与社会分工中总量必要劳动相连,自不待言的。还有,这个价值在生产领域中还只是“潜在价值”或“个别价值”。而在交换中通过社会接触和市场竞争,才能转化为“现实价值”或“社会价值”、“市场价值”。商品按照来“售卖”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实现论”实际上主张总劳动只有具体一重性,而无具体与抽象两重性。这些,我在其他论文中已作了论证,此处不必多说。
3.《资本论》第三卷(中文全集本)第717 页关于单个商品价值规律与总产品价值规律的关系的译文和理解问题。
全集本译到“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规律的关系时,是“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每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
这里似乎又为某些人士提供了一个论据,证明“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市场价格形式用来“表现”或实现“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整个价值规律”的。价值规律第一含义唯一论,也就由此得到加强。
这又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刚才上面引用第716页, 那里说价值规律“总是”指“总产品”及其总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规律,怎么翻过一页,这个总劳动时间又变成“第一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整个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我们现在试图按一定顺序加以剖析之。
(1)从原著字面理解, 说“第二含义”必要劳动时间是“整个”价值规律的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肯定不妥。既然是“整个”价值规律,就已达完整或完善的地步,就没有再“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和必要了。难道“整体”还会向自己的局部(个别)发展不成?所以这纯属方的圆的这类形容词语的矛盾。
(2)必须另辟蹊径给予新的理解。其方式就是:第一, 再思考本句话的3个关键词——整个价值规律、发展、表现的真正含义;第二, 对照前引第716页的有关论述,从中找到正确理解第717页那句话的全部含义的佐证。
(3)就3个关键词分别理解如下。
①“整个价值规律”。德文原文为“Wertgesetzes uberhaupt”(柏林版第649页1964年),英译为“Law of value in generial ”(芝加哥版第746页)。此处uberhaupt和in general,都有“整个”和“一般”两层意思。而历来中译本既有译为“一般”的(郭、王1953年版本),也有译为“总的”的(郭、王1963年版本)。全集中文本译为“整个”则与郭、王1963年版本相近。可见,采取“整个”和“一般”都是可以的,只看我们如何联系上下文加以选择。
②“发展”。这个词很重要,不能轻易看漏。发展,那一定有两个对象物,一个在发展之前存在,是被发展之物,一个在发展之后存在,是发展物本身。据我们判断,发展之前之物应该是单个商品,发展之后之物应该是部门生产总产品。这两个对象物在原著中不是没有说明白,就是没有写进去,这就需要我们来做补充工作了。
③“表现”。它一定不能用来说明“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与“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或者单个商品价值规律与总产品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因为都是劳动时间对劳动时间,价值规律对价值规律,是同质的东西,不能相互表现。也不能交叉表现,说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用来“表现”单个商品价值规律的(注:韩凤来认为:“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是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韩凤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之我见》,载《理论探讨》,1998(1),37页。丛松日认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表述,前者是一般,是本质,后者是‘个别’,是表现形式……。价值决定必须而且只有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来具体体现”,或说“通过个别表现出来”(丛松日:《社会必要总劳动的核心问题:资源合理配置》,载《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2),77~78页 ),丛文所说‘个别’、‘表现’,从前后文来看,不过是指等到资本主义社会到来,推出一个生产价格来表演而已。这又似乎离题远了。)。因为,从马克思理论体系来看,价值才是劳动(时间)的社会形式表现,不能颠倒过来说,劳动时间是价值表现形式。表现,只能是指部门内总产品、总劳动、总价值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是指总产品总价值规律的劳动内含,可以和应该用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现。
(4)连结3个关键词,可以看出,第717页这句话的全部内含, 能够通过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给予理解。一种是,保留“整个价值规律”这个译法不变,但在“发展”之前插入单个商品价值规律,“发展”之后插入总产品价值规律,于是全句意思就是这样:社会总劳动时间可以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以其生产各类产品能恰好满足社会需要为必要的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在其由单个产品价值规律发展到总产品价值规律时关于其劳动时间内含的表现形式。另一种理解方式是,把整个价值规律改译为一般价值规律或任何一个商品价值规律,说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以其生产各类产品能恰好满足社会需要为必要的数量界限,不过是一般或任一个别商品价值规律在其进一步发展为总产品价值规律时关于其劳动时间内含的表现形式。
(5)就上述第二种理解而论,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价值规律何以被视同“任一商品”价值规律。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某个“个别”是指“任何个别”、“一切个别”,“这个个别”与“其他个别”“并无差别”,那末,这个个别就具有“一般性”(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文版,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马克思在这里是指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时间,但如果我们向两头扩展,一头扩到商品,另一头扩到价值,那末,我们就可以说,当我们面对的是彼此并无差别的个别商品,当我们为生产此一个别商品所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是彼此并无差别的个别劳动时间,则投入此种个别商品上的此种个别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个别价值就具有彼此无差别的一般价值的性质。
(6)对照《资本论》中文版第三卷第716页。事实上,第717 页的说活不过是第716页的说法的稍加改换而已。因为第716页说,“事实上价值规律”不仅要求在每一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要求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用在各类不同总产品上。这就是说,价值规律在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含上,不仅要有第一含义的,而且要有第二含义的。而第717页上那句话经过我们改动之后,是说, 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不过是单个商品价值规律发展成总产品价值规律时关于劳动时间内含的表现形式。至于所说单个商品价值规律究竟是出于我们的第一理解,指被马克思省掉经过我们补入才有的,还是出于我们的第二程理解,就是指那个“一般价值规律”,或与“一般价值规律”同义,是无关紧要的。两者都能说得通。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第717页上的那句话不过是抓住侧重点把第716页上那句话倒过头来写。把从价值到劳动,说出价值规律对劳动时间的要求,变成从劳动到价值,说出总劳动时间对价值规律内含的意义、作用,同时又把第716 页上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递进关系,改写成两个价值规律的发展关系。这样,两页两处所说的话形式不同,实质相同,都把两种互有内在联系但又各有特殊内含和要求的概念分别开来,又都把第二含义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
很明显,发展成以第二含义必要劳动为基础的价值规律会拥有自己的,不依赖于以第一含义必要劳动为基础的价值规律的独立存在权,就象单细胞发展成生物有机体,低等动物发展成为高等动物之后,这个有机体,这个高等动物会拥有自己的更强的生命力一样(虽然生命本质是相通的)。
以上是我对《资本论》中文版第三卷第717页那句话的再思考。
不可否认,无论说总产品是单个商品的“发展”也好,还是说单个商品是作总产品的“平均样品”也好,在供求平衡状态下,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量及其决定的价值量,可以通过乘法和除法互推,即由单个商品价值乘算出总产品价值,也可以相反,由总产品价值除算出单个商品价值。但不能由此推论,说两种含义“并无二致”、“无根本性差别”(注:高红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提法浅议》,载《当代经济研究》,1998( 3),60页。)。在供求失衡的状态下,总产品社会必要劳动对实际价值决定的支配作用就凸显了。此时,单个商品“第一含义”必要劳动价值就不能以其原本形式存在,而需要修正,通过折扣、贬值或加成、升值,使其被缩小了或放大了。比如说,假定麻布这个生产部门所有的生产者的生产条件都是中等的或平均的,就这一点说,单个商品“第一含义”必要劳动和价值总是一样的,但麻布生产总量超过社会需求一倍或落后一半,麻布总量的总价值仍然依照按比例应该分配的社会劳动量来计算,其价值量也不变,但用除法算出的“平均样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却会因为除法中分母(部门实际生产量)的变动,而减少一半或提升一倍。因此市场价格波动中心——市场价值也就决定性地向低处或高处转移。确认这个变动过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
二、《资本论》第三卷对供求约束价值论的肯定和对供求决定价值论的批判
“第二含义”必要劳动价值论主张生产恰好满足社会需要的总产品所费的劳动量,决定价值,而生产与需要的关系在市场上表现为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当社会用于购买的劳动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一定时,生产单位商品的市场价值就与供给量成反比例。这就立即进入经济学有剧烈争议的领域,成为难点所在。供求关系到底与价值是个什么关系,是决定还是不决定。
我认为,供求关系当作基础、当作力量源泉、当作决定因素,是不能作用于价值的,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供求关系当作约束条件,引起生产所费劳动量的变动,是可以作用于价值的。这也是马克思经济的重要观点,后一点往往被后人忽视。分述如下:
1.供求关系对市场价值的约束作用。
我曾说过,光是《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就至少有6 处指明了供求关系变动如何引致商品价值量的变动(注:姜启渭:《价值决定与供求关系论纲》,载《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8(4),49页。 )。现在不妨列举如后,供读者一同鉴别:
(1)“如果需求非常强烈, 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 200、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 2 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请注意,后面“商品”一词之后,省去了“的个别价值”几个字。
(2)“这里撇开市场商品过剩的情况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总是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很明显,此处市场价格乃指与市场价值一致,是市场价值的单纯的货币表现的市场价格。
(3)“只要需求稍占优势, 那末市场价格就会由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1版,第25卷,20 0、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对市场价格要说的话,仍如例(2)。
(4 )“但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个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204、206、206、207、213、 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种说法,就等于说,如果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市场价值就会同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相一致。
(5)“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一种需要, 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的需要。……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是由两端中的一端来调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0、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如果需求增加, ……,还可以在这个或那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引起市场价值本身的提高,因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产品在这个期间内必须在较坏的条件下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由以上六例已经确切证明,如果供求关系变动了,引发生产商品所费的总劳动量和起调节作用的单位商品劳动量出现了变动(这是一个中间项,只有通过它,不能越过它),那末,商品市场价值也跟着个别价值的变动而发生变动。在这里,引起价值量变动的唯一根据当然是劳动量,而不是使用价值或效用。但供求关系若不发生变动,劳动量也变动不起来。因此,作为间接约束条件,供求关系对市场价值的重要作用,不能否认。
2.庸俗经济学供求价值论错在何处。
庸俗经济学习惯于从表面看问题,断定供求关系本身是价值决定的力量源泉。萨伊、马尔萨斯、加尼尔、贝利、《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匿名作者以及后来的洛利亚,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资本论》中文版第三卷第十章中对匿名作者供求价值论的批判,是该书该该章唯一点名的批判,也是有典型性的批判,值得专门对待。其批判的要点是:
(1)循环论证。 他们一般都持有“价格由供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这种混乱观点”,而同时“还要加上:需求决定供给,反过来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产”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204、206、206、207 、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是平列地看待原动力与反作用力,王亚南先生称之为“无端循环,不可究诘”,可谓打中要害。
(2)推论轻率失据。匿名作者曾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 说随着工资、利润、地租的变动带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变动,这种需求的变动又带来供给的变动,当供给的变动与“那种就新生产费用来说代表有效需求”达到“一致”时,商品就“具有新的自然价格”,“所以”结论是“自然价格取决于一种供求关系,正象市场价格取决于另一种供求关系一样,可见,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样依存于供求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204、206、 206 、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212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是自相矛盾的。前面既然承认是生产费用的变化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后面为何又作出相反的结论,说自然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所以,马克思对之批判说,“这正好会证明我们这位思想家想要证明的事情的反面;就是说,这会证明,生产费用的变化,无论如何不是由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而是相反,生产费用的变化调节着供求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 、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违反概念同一性原则, “无差别”的供求关系被用来说明“有差别的”价值量关系。
匿名作者承认,“当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有两个不同的‘自然价格’时,供求关系在每一个场合都能够互相一致,并且必须一致,以便商品在两个不同场合都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售。”他是通过这一点来证明自然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马克思批评说,“既然在这两个场合,供求关系没有差别,而‘自然价格’本身的量有差别,那就很明显,‘自然价格’的决定同供求关系无关,因此也极小可能由供求来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0、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 页脚注、215、2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已经失去效力的东西不能用来对任何事物作出任何说明。
如果说供求不一致,是使商品具有不同价值的原因,那末,“一致”时又作如何解释呢?马克思说:“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无从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212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从以上批判来看,马克思是很重视一般逻辑学的一般规则的,因此批判是有说服力的。因而,不必要为此一供求价值论“正名”。
我认为,对所谓供求关系价值论的批评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要有关著作还没来得及读完,许多理论矛盾和难点,还未理出头绪来,不区分供求关系在价值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就匆匆忙忙,择取其中某一哪怕是很重要的观点,来否定一切,这不利于我们收集一切有用的供求理论,为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服务。
三、指导资源合理配置的不是价格“晴雨表”而是价格的“平均数”
资源合理配置问题,是今天经济学界最为关心的热点。
此次讨论中各方也都认为“第二含义”必要劳动价值论的实际意义,在于依靠它来合理配置资源。然而,通过何种具体形式,却意见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通过“第二含义”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市场价值,另一种认为通过日常市场价格的晴雨表。
何者更为正确,请先从晴雨表论评议起。
丛松日先生曾在我们前引的《社会必要总劳动的核心问题:资源合理配置》论文中这样写道,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国内国际统一市场的形成,“市场成为主宰商品生产经营的主导者,商品的市场价格成了商品生产经营的晴雨表”,指导人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每个商品生产者总是根据市场价格这个晴雨表反映出来市场供求行情来配置资源,调节生产。市场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引起生产规模扩大或资本流入这个部门;而当商品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下跌,引起生产规模缩小或资本流向其他部门。”为证明所论并非无据,丛文特别引证了《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第394页关于市场价格晴雨表, 起着帮助“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的作用的论述,和《资本论》中文版第三卷第213页关于市场价格会引导“供求’, “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的论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历来公认的道理。
但是,中国古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价格晴雨表论,只是对经济现象的描绘,而若停止在现象上,以现象为行动指南,只会使市场行为更加“无规则”,更加“任意”化,而使供求更加“不平衡”,结果是误导资源配置。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首先,价格晴雨表所提示的信息变化得太快,以致根本无法据以决策和实施决策。因为,市场价格变动是以时以日为单位来计算,所谓“早晚时价不同”,而生产资源再配置是以月、以季、以年为单位计算的。这个时间差距的矛盾使得纵使神仙也难以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及时调整生产,以每家每户每个成年人都会感知蔬菜市场价格为例(我本人曾有幸参与两年的蔬菜生产),那里固然也有价格比较稳定的品种,但是大多数时令新鲜蔬菜,对供求关系变动都十分敏感,其价格可说无时不在变动。而这些蔬菜的生产所费的时间(包括劳作时间和自然生长的时间)则比这更长。它们中最长的为一年以上,一般地为半年到一个季度,最短的如小白菜也得两个月。这就是说,当某一品种蔬菜还处在同一个生产周期之中,其市场价格已经变动了几十次,几百次。如果真要按照市场价格晴雨表来调节生产,那末,第一次配置也许还可以做到,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及第一百次调节,就根本无法实际进行。因为耕地已经被第一次配置所占用,无资源可供再配置。所以,按市场价格晴雨表合理配置资源,纯属一句空话。
假定我们的蔬菜生产者是一位虔诚的晴雨表论信奉者,他宁愿每一次都根据晴雨表的变化而重新配置资源,他第一次种下白菜,但还不到收获季节,市场上白菜价格令人遗憾地下落了,而萝卜的市场价格出乎人们预料相反上升,于是他不是拔苗助长,而是拔苗改种,但这一改种萝卜种子刚下地不久,白菜的市场价格忽地又上升了,于是不等萝卜种苗出土,他又转身刨掉萝卜种子,又改成白菜种子,他这样反复追踪晴雨表之后,不是丰收满园,而是一无所获。好心来配置,痛心来收获,结果是大浪费。
假如我们这位蔬菜生产者是一位在多次吃亏之后还肯思考问题、总结教训的人,面对从晴雨表带来的多次痛苦,他不再轻举妄动,宁愿观望等待下去,要看出一个究竟来,于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从弄潮儿变成观潮派,什么合理配置资源,由你张三李四去作贡献吧,他少奉献陪了。从蔬菜市场转到股票市场,人们会发现最终总有一批灰心丧气的人士,带着诅咒,退出股市,他们则是价格晴雨表牺牲品的极端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 204 、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 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这样说,是不是说,市场价格晴雨表就没有用了呢?也不是。
“表”,还是要看,现象还是要抓。问题是要透过“表”的现象,深入一步抓住它们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平均数规律,而价格的平均数规律,也就是市场价值规律。按平均数、按市场价值指导我们投资行为,这又确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有意告诉我们投资者朋友的。马克思说,商品供求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销,这个平均数就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间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版,第25卷,20 0、204、206、206、207、213、213、214页脚注、214页脚注、215、2 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马克思这里的分析,可以说,完全适合我们今天对市场理论的需求。
按价格平均数指导投资行为,这与“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又有何关系?
诚然,平均数不过是日常价格的平均,从这里不过表明,通过平均数可以捕捉到市场价值,或者说,市场价值可以通过平均数来显现,但是,显现市场价值是一回事,并不等于决定它。人的容貌可以通过摄影来显现,但某甲的尊容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则必须追寻到其血亲的遗传基因上来。市场价值的基因就是“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个“分摊”除法并非“偶然的情况”,而是普遍的适用。在“供求平衡”时有效,供求不平衡时同样有效。在后一种情况下,单位商品价值量就是用实际生产出来的部门商品总量来除(“分摊”)“第二含义”总价值所得之商。实际生产总量与按比例应该生产出来的总量(在一定社会一定生产力水平之下,应该分配的劳动量和社会总需要的产品量,也都是客观存在的比较稳定的量,不是“无法具体确定的因素”(注:丛松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核心问题:资源合理配置》,载《宁夏大学学报》,1998(2),79页。)。 当代西方社会统计学家已用大量统计数据证明,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会有不同的食衣住用消费结构相对应,如恩格尔系数理论。)之间的差距比例大小,决定市场价值的加成、升值或折扣、贬值。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论述两种含义必要劳动的关系时已有说明,在拙作《价值决定与供求关系论纲》一文第九点内更有专门论述。此处不拟重复。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加大调节资源配置的力度,或改换资源配置方向,才能得到“合理”的结果。
总之,要真正做到合理配置资源,就必须回到“第二含义”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论上来。
标签:资本论论文;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产品价值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市场规律论文; 价值规律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