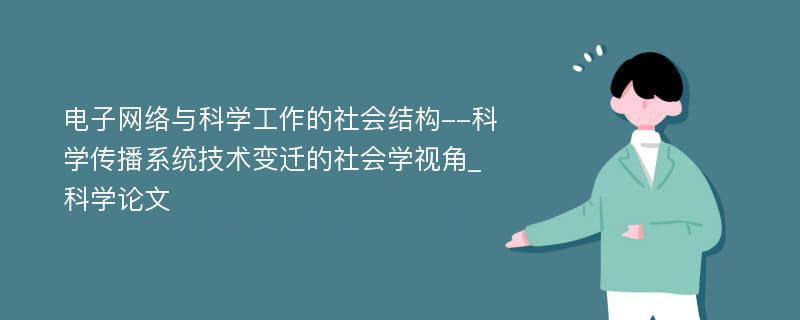
电子网络与科学工作的社会结构——对科学交流系统技术变迁的社会学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社会学论文,透视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年,以Internet为代表的电子信息网络风靡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数量一直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呈爆炸式增长。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也吸引了多学科的研究兴趣。(1) 对科学和技术社会学来说,电子网络的兴起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作为人类交流技术的又一次重大革命,它为技术社会学家考察技术变迁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案例;另一方面,由于科学家群体从一开始就是使用网络最多的用户,以及交流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电子网络被科学家采纳和使用的状况及其对科学家工作方式和科学交流体制的影响程度,也开始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重视。许多人已经注意到,科技界日益增加的上网人数和用网频率正在引起科学活动方式(特别是交流方式)的重大变化,但迄今为止,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科学家群体对网络技术的采用仍很不平衡。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两方面的情况是十分有益的,它将使我们在考察和估价一项技术创新的社会作用时,避免单向性的思维和简单化的结论。在本文中,我们将简要评述技术社会学和职业社会学的有关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就电子网络对科学活动方式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1 职业组织中的技术变迁
关于技术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目前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典型立场和观点:一是技术决定论,二是社会决定论。按照技术决定论,技术的后果与影响是内在于技术之中的,因而一种机器(技术)一旦被发明出来,它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就只是个时间问题。正如埃吕尔( J.Ellul )指出的,“在技术与它的使用之间不存在什么差别。(在技术面前)个体面临着一种唯一的选择,或者按照技术规则所要求的去使用技术,或者根本就不使用技术。”(2)因为一旦技术(系统 )被使用,它们就需要高度的一致性,而不管使用者的意图如何。社会决定论则认为,社会的运行有其内在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现有的常规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支配。按照这种观点,所有的技术变迁都会被置于常规秩序中加以权衡,因此,新技术要么不被采纳,要么经过改造以适应现有的社会结构。(3)
极端的技术决定论和极端的社会决定论由于各自的理论缺陷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以致于它们常常不得不汲取对方的某些观点而使自己的立场更加“温和”。许多人已认识到,技术和社会结构从性质上看既有“柔性”的一面又有“刚性”的一面:柔性或可塑性意味着允许技术与社会结构互相决定(支持或约束)对方的发展,刚性则规定了这种相互决定的限度。从目前有关研究的文献看,两种决定论的分歧尽管依然存在,但争论已主要不是诉诸思辩推理,而是将问题转变为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具体假说。如果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在技术变迁中是重要的决定因素,那就应看到,相同的技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使用情况是不同的(或者,相同技术被采用的形式是不同的);相反,如果技术自主地发挥作用,则可预期该技术将以相同的方式被用于不同的工作环境中。近年来的经验研究表明,技术革新尽管无疑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但其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要受到新技术植根其中的社会因素的制约。
比如,诺伯(D.Noble)在一项调查中发现,美国自动化工具机的开发深受少数大的用户(特别是空军)的实践和利益以及管理人员试图控制其功能的兴趣的影响。他还发现,在食品零售业中,超市系统内部的关系,零售商、供货商、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共同影响了美国肉类加工的中心化和结帐扫描的电脑化。(4)托马斯(R.Thomas )在其近作《机器不能做什么》一书中则认为,如果既有的社会关系体系抵制一项新技术,该技术就很可能被改造以适应这些社会关系。他十分强调工程技术人员的价值体系对技术采纳过程的社会选择作用,认为尽管这种价值体系是由经济理性加以引导的,但这种理性本身却深受决策者的社会背景的影响。(5)在对电脑技术的社会研究中, 人们尤其看到了技术发展的社会选择性。由于电脑技术具有更大的弹性,社会因素有可能在它与各种工作体系结合的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卡劳恩(C.J.Calhoun)在“微机革命”一文中考察了办公电脑化由于妨碍既有的地位体系而受到的抵制,发现高级管理人员会抵制那些影响他们的地位或其秘书部门地位的技术变迁。(6)在探讨电脑对组织的影响时,科林(R.Kling)也认为社会环境能极大地影响到一项技术的哪些方面被开发、如何使用该技术以及使用该技术会带来什么后果。比如,电脑技术在一种情况下可降低资源利用的不平等,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会提高组织的精英控制水平。(7)
上述研究结果推动了职业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work andprofessions)对不同工作体系中技术变化情况的研究。在这个领域, 传统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技术因素对职业群体的影响方面,认为一个组织所做工作的类型、所使用的工具和技术的性质以及原材料的具体种类,决定着组织成员之间任务关联的互动被社会地构造的方式。(8)而新的研究兴趣则表明,工作群体的社会结构可以影响该群体所采纳和使用的技术形式。这种侧重上的差别也反映在目前对电子网络的社会影响的研究中。许多人一开始就已注意到,电子网络技术的采用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比如导致了更多的分散化,降低了一个组织或群体中的地位差别,减少了对共地域的合作生产工人的需要,提高了组织的整体效率等。但也有人认为,这些人所提供的证据大多只具有相关性而不具有因果必然性,并且他们很少关注不同工作体系中电子网络技术使用情况的差别。赖斯(R.Rice)等人在对美国一所大学的教师群体使用电子网络情况的调查中就发现,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运筹学等学科领域的教师是使用电子网络最多的群体,而哲学人文学科对网络的使用则明显较少。据他们推测,学科际合作的程度和应用取向的水平可能是影响不同学科领域使用电子网络的重要因素。(9)
赖斯等人的工作已涉及到电子网络技术在科学中的不同工作群体和学科组织中的应用问题, 提出了把科学作为一种工作活动(workactivity)和置于有组织的和常规性的背景中的一组任务,并研究它与技术变迁的社会互动的可能性。正如福柯斯(S.Fuchs)在概括他的研究方法时所说的,“科学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组织加以探讨,其技术和社会结构决定着科学家群体做研究的方式。”(10)如此,通过检测电子网络技术被科学工作群体采纳和使用的差别,人们就可以对两组重要因素加以比较,即电子网络技术适应科学工作单位现有惯例的程度(或它瓦解科学工作系统整体各组成成份的多少),以及该技术对科学工作系统中现有交流关系和地位结构的影响。这显然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分析视角,它可以使技术社会学和职业社会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在考察电子网络技术与科学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下面将提到,沃尔什(J.Walsh )等人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
2 不同学科对CMC的使用情况:一个研究范例
1991年1月至1992年10月,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社会学家沃尔什和吉尔吉亚大学社会学研究生贝马(T.Bayma)就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使用电脑媒介交流网络(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的情况进行了一项社会学调查。(11)调查以他们所在的两所研究型大学中四个学科的教师名录为抽样框,采取滚雪球抽样(随机开始)方法抽出67位科学家(其中分别有数学家15人、化学家15人、粒子物理学家18人、实验生物学家19人)进行开放式访谈。访谈内容不仅包括被访者使用电脑网络的情况,还包括他们的研究工作、研究群体和所属学科的性质等。然后,两位调查者又用档案和文献资料核查了个案访谈数据,补充了关于各学科性质的更充分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科学家采纳和使用CMC的人数、 频度、选择偏好、体制化水平及其它相关问题。
沃尔什和贝马的研究假设是:不同科学工作群体的社会结构和各个学科的不同组织方式,可能会影响到科学家采用CMC的形式。 通过调查,两位研究者发现,科学中的每个领域都有相对特殊的职业组织和工作方式,它们对CMC与科学工作的结合产生了显著影响。 让我们先概括一下这次调查的结果,然后再看他们如何对调查结果进行社会学解释。
沃尔什和贝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学科在采用CMC 方面存在明显差别。首先,科学家对采纳和使用CMC的必要性有不同认识, 不同学科的上网人数和用网频度存在差异。在所调查的四个学科中,数学家已开始普遍使用CMC进行一种近似于“面对面的”讨论、交流和合作, 许多人“已简直记不起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类似地,粒子物理学家也认为,入网是其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一项成功的研究需要高效率地使用CMC。在物理学家的工作中,CMC既被广泛用于传递重要的信息(比如“机器出毛病了”),也被作为发布不太紧迫的信息(如会议日程)的常规手段。相反,没有一位化学家认为要使工作有成绩就必须上网。占化学家群体很大比重的工业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大多既不使用电子邮件也不进入BITNET或Internet,他们最典型的回答是,“事实上,我根本就不与网络打交道”。不过,物理化学家和理论化学家似乎较多地使用网络,他们的态度也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类似。 实验生物学家一般把CMC视为与电话、传真等一样的交流手段,只是在相对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网络。沃尔什和贝马根据使用CMC 的次数将科学家用户分为两类:一是“中等用户”(moderate users),每天用网约两次;二是“高频用户”(heavy users),每天用网约十次。他们发现, 大部分被调查的物理学家是中等用户;数学家中有一半中等用户和一半高频用户;化学家约有一半人用网,其中大部分为一天一次或低于一次,小部分为中等用户,只有一个高频用户;在生物学中,有1/4的人用网,其中约有一半人用网频率为一天一次或低于一次,其他人则介于中等和频繁之间。
其次,在选择具体网络手段时,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有不同偏好。数学家最普遍使用的是E-mail,所有被访者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这一手段发送或接收邮件。此外,也有人使用mailing list , newsletters ,public bulletin boards(比如Internet新闻系统中的Sci.math), 寻求帮助或给他人提供帮助。在物理学中,除普遍采用电子邮件、邮件名录、业务通讯外,
预印件也由物理学家通过网络实现了电子化, preprints bulletin boards已成为大多数人工作圈的一部分。 化学家在电脑网络中使用较多的是CA database,其中存有1967 年以来各国化学家发表论文的英文摘要。除物理化学家和理论化学家外,其他人很少使用电子邮件或预印件公告栏。生物学家使用较多的网络资源是有关核酸顺序和蛋白质的贮存信息,这种信息可以从Internet的Gen Bank获得。此外,他们还使用Medine或类似在线的文献参考数据库,约半数被访者提及互联网或所在大学图书馆的电子参考服务系统。多数生物学家不使用电子邮件,对公告栏的使用也很有限,仅限于分发和交换电脑使用的信息,而很少用于交换实质性信息。
再次,CMC在不同学科中的体制化程度也有所不同。 由于网络技术的特殊性能,各个学科(作为一个共同体而言)一般都倾向于鼓励对网络的使用。一旦某种技术应用被认为是可行的,体制性的动力就会促使其常规化和标准化。尽管如此,调查仍然发现在CMC体制化程度上, 各学科之间存在不同特点。CMC在数学中的应用已比较规范, 最初遇到的数学符号传送上的困难也已基本解决。目前美国数学会(AMS )采纳一种叫TeX的文字处理语言作为通用标准,得到数学界的认同。 在物理学中,美国物理学会(APS)为鼓励人们使用网络, 已允许向其刊物提交电子稿件,甚至通过免掉排版费给以鼓励。自1991年,《物理学评论》开始为供稿者提供其电子邮件地址。1991年的APS会员名录用11 页纸的篇幅介绍E-mail的使用方法,而同年为生物学家出版的FASEB 名录却没有这项服务。此外,预印件公告栏也在洛斯阿拉莫斯建立起来,为订阅者提供所有新撰写论文的摘要或全文。这项服务得到广泛响应,到1992年底已有5000名订阅者,每月至少收到1000篇新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个替代性刊物。与数学和物理学不同,许多被访问的化学家抱怨通过Internet传送化学论文(特别是图片)有版式方面的技术困难,但没有人提到使用TeX。由于化学家普遍使用化学文摘,美国化学会(ACS)也着手建立了CA数据库。约半数的被访者认为CA库很有用,可使他们在做课题或写论文时参考更多已有研究文献。但也有一些人宁愿在图书馆查阅CA,认为上网不如看论文那样有明显效果,且费用也较昂贵。在生物学领域,基因库和蛋白质数据库也已成为基因表达、确定基因顺序和合成新型基因的重要工具。《遗传学》、《生物化学杂志》、《分子生物学杂志》目前都要求将基因排序数据和结晶学数据存入已建立的电子数据库,并许诺作者的资料在论文出版后一两年内不公开。尽管如此,与化学一样,保密问题仍然困扰着生物学对CMC的体制化努力。 《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称,一个为虫类生物学家建立的信息系统WCS (WormCommunity System)没有得到有效使用,只有1/4的目标实验室鉴约,大多数使用者不提供自己的非正式资料,研究共同体也没有做出相应努力使其成为相关非正式知识的存储机构。
沃尔什和贝马认为,四个学科在使用CMC 上的上述差别可简单表述为:数学和物理学倾向于使用CMC的非正式交流功能, 而化学和生物学则大多局限于使用其正式信息(已刊登出来或已申请专利)。他们将这种差别归因于各个学科的不同组织环境和社会结构,认为如果一个研究群体规模庞大且高度相关,或者规模虽小但地域分散,那么CMC 就会被采用以满足其结构要求;在中等规模且相关性不大的研究群体中,传统的交流方式(如面对面交流、普通邮件、电话、传真等)会与CMC 一样发挥作用。此外,各学科与社会的关联程度特别是市场化程度,会影响到对CMC的技术选择:那些较少受市场化干扰的学科将欢迎CMC的信息社会化方式,而那些与商业和市场关系密切的学科则会选择能保持其对信息的所有权的交流方式。具体说,以下几种社会因素将对CMC 的使用产生影响:
第一,研究领域的规模 相对而言,数学和粒子物理学是较为独立的小领域,而化学和实验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却十分广泛。比如AMS 有会员27000名,而ACS则拥有会员140000名。由于非正式交流更适合在小群体中进行,因而数学家和粒子物理学家比化学家和实验生物学家更多地使用网络(尤其是E-mail)进行非正式交流。
第二,重要信息源和各研究单位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 数学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学科,且每个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都很少。在数学中,研究共同体通常由一些地域上分离的个人或小合作者群体组成,重要信息源(有类似思想的同行)十分分散。据沃尔什和贝马给出的统计数据,数学论文的平均作者数比其它学科要少,但机构/作者比却最高;合作论文中当地合作者很少,而跨国合作者居多。(12)因此对数学家来说,“交往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频繁的交往(如参加学术会议、安排访问性职位)才能改善知识传递。在一定程度上,CMC 受到数学家欢迎正是由于它可以帮助那些远离数学中心的人,使那些没有交谈对象的数学家摆脱孤立。
物理学,尤其是粒子实验物理学,需要耗资巨大、建造周期很长的大型精密设备,以及大量研究人员、组织人员的分工合作。其研究典型地属于哈格斯特龙(W.Hagstrom)所说的teamwork, 即一种有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的大规模合作研究结构。并且,这种合作具有“交互性的互赖性”(reciprocal interdependence),即研究项目参加者所分担的工作具有高度相关性,研究结果需要随时反馈,个别合作者的行为会直接、迅速地影响到该群体中的其他人。交互性互赖的组织要求有方便、直接、价格便宜的交流环节加以协调,因而CMC 一经采纳便很快成为合作实验协调系统的核心部分。
化学和实验生物学都是高度异质性的学科,有许多分支领域和大量研究机构(小组),研究工作分散进行,研究群体之间不大需要分享数据信息和紧密协作,重要信息源基本上限于实验室之内,远距离合作较为少见。与物理学不同,这两个学科中的研究合作只具有“接续性的互赖性”(sequentical interdependence), 即一个小组的工作结果是下一个小组的工作起点;或“合伙性的互赖性”(pooledinterdependence),即每个小组分头完成项目的不同部分, 它们各自的工作进度将对最终工作汇总产生影响。这种低度相关减轻了组织协调的压力,组织者只需通过“标准化”或“时间表”就可满足互赖性需求。换言之,CMC并不是不可缺少的交流和协调手段, 研究者可能在没有其他人信息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他们也可能去查寻外部信息,但大多是出于文献调研的需要。
第三,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 化学和实验生物学的商品化程度要远高于数学和物理学,其投入(如实验设备和材料)和产出(科研成果及其转化的产品)都更倾向市场化。各种商业性广告以及原料或仪器生产厂家已进入研究活动圈,专利权、信息所有权及其中巨大的金钱回报,导致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信息共享和网络使用上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产生不同认识。许多被调查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担心他们的成果被剽窃或被无偿占有,工业科学家在保密问题上由于体制性迫力而更加谨慎。商业性因素使预印件文件(preprints culture )和其他非正式交流方式一直未在这两个学科中占据主要地位,科学家对CMC 提供的非正式手段的电子等价物也不大接受,而是更希望与CA库或基因库那样的正式信息系统建立联系。
沃尔什和贝马的讨论还涉及论文出版周期和稿件采用率对科学家寻求替代交流途径的影响。他们发现,出版物滞后程度最严重的数学(论文出版平均间隔为20个月左右),以及稿件采用率最高的物理学,是各种替代交流(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的需求者,因而也是CMC 的积极实践者。
3 电子网络对现代科学交流系统的作用
电子网络应用于科学工作的意义在于,它为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开辟了一条通往新信息源和潜在合作者的通道。事实上,网络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正是来自它所引发的一场真正的交流革命。从互联网产生和发展的短暂历史看,它最初虽带有较强的军事目的,但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的交流服务的。作为一种广泛的、公开的和对大多数人有效的交流方式,电子网络可以比任何已有的交流技术都更快、更经济、更直观和更准确地把一个思想或信息传播开来。前述沃尔什和贝马的研究工作尽管突出了各学科应用CMC的特殊性,但它也表明, 这种新兴的交流媒介已经对科学家的交流方式产生了普遍影响。
科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公共知识,科学交流是科学活动的核心部分之一。科学交流系统通过种种方式(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把分散的发明、发现、研究成果等汇集到一起,实现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换,使个别科学家的贡献转化成为公众所有的知识财富。可以说,没有科学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就不会有科学中的专业一致和科学共同体的出现。为了实现有效交流,现代科学成功地发展出了自己的正式媒介系统(学术会议、定期出版物、图书馆等),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各种非正式渠道(私人通信、访问讲学、暑期研讨班、论文预印本等)。 齐曼(J.Ziman)曾经用实验室代表个别科学发现,以图书馆代表科学交流,认为实验室若是没有图书馆,就好象是一只剥去了大脑皮层的猫,以此比喻交流在科学事业中的重要地位。(13)。今天看来,齐曼的比喻无疑仍然生动,不过多少有些过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科学知识和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现代科学精心建立的交流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图书馆的扩容压力,以及浩瀚繁杂的文献海洋给人们查找所需信息带来的困难,已引起了大大小小的创新努力。从科学实践看,目前人们解决信息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即建立专业化的科学信息服务系统以提高原有正式交流媒介的容量和效率,以及寻找更加多样化的非正式交流方式。显然,电子网络的出现为这两种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使多年来人们期望的科学交流系统的重建有了新的可能。
的确,电子网络作为一种新型交流媒介尽管仍不尽成熟,但已表现出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优势。它的信息容量几乎是无限的,它对信息的传播既迅速又准确,通过它发布和接收信息完全不受时空限制。更为重要的是,电子网络潜在着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科学交流方式的兼容,既可为保存科学成果提供一种世界性档案,又可作为私人联系和非正式讨论的更经济和更有效的替代途径。随着更先进的技术的出现,曾经局限电子网络应用的技术障碍也逐步得到克服。比如前述图片和文本传送中的技术问题,由于像BITNET那样的以传播文本信息为基础的网络,以及像Mosaic那样的图像分辨技术的出现而得以解决。如果仅仅从技术上看,我们似乎可以乐观地预测,电子网络最终将取代现有的科学交流系统,并完全改变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
强调新兴交流技术的革命性质,并预言某种交流手段的出现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前述更广泛的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变种。60年代广泛流行的“麦克卢汉主义”,可能是试图将交流手段的决定性作用理论化的第一次认真的努力。在《认知媒介》一书中,加拿大哲学家麦克卢汉(M.Mcluhan )写道:“当任何一种新技术手段在社会环境中出现时,它会在这个环境中一直传播下去,直至渗透到每一个社会机构。”(14)这位“电子时代的预言家”认为,社会生活比之于被传递的信息内容,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递手段的性质和特点。他由此对电影、无线电、电视、电话、电报等电子手段的社会作用给予了乐观的估计,认为以它们为核心的大众交流媒介将取代过去五百年盛行的印刷术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正如米哈依洛夫指出的,交流方式的变迁史并没有为这种决定论提供支持性的证据。文字的产生并没有消除口头交流的需要,印刷术革命没有取消私人通信,电子媒介不仅没有完全替代图书的功能,反而使图书的作用更加有效,使之传播得更为广泛。”“看来,每个科学发展时期都给科学交流系统带来自己的变化。科学交流系统的重要特点在于,以往的方法和手段没有为新方法和新手段所取代,而只是为新方法和新手段所补充。”(15)按照米氏的观点,科学交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结构对于外界影响的反应异常稳定,不将整个系统破坏,便无法取缔任何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稳定性和保守性是现代科学交流系统的基本发展规律。
在一定意义上,前述沃尔什和贝马的研究结果已部分证实了米哈依洛夫的有关假设。他们的调查显示,电子网络对科学交流系统的作用有以下三种具体的代表形式:(1 )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原有的交流方式。比如在数学中,作为纸和笔的电子等价物,CMC 已经承担了原有交往安排(如旅行)的大部分功能。数学家仍然旅行,但其作用范围已被窄化且重点发生了转移。基于工具性交流的考虑,他们更喜欢访问同行的网址,并向同行提供自己的网址。(2)与原有交流方法和手段并存。 化学文摘是化学界普遍使用的参考工具,一些化学家已主要从网络的CA库获得所需信息,另一些人却继续去图书馆查阅CA期刊。在生物学领域,电子邮件、传真、数字电话等手段的作用似乎是并列的,不管它们是否以网络为媒。(3)对原有交流媒介加以改造。在这方面, 物理学界对预印件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沃尔什和贝马所做的研究的意义当然远不限于此,他们的社会学视角使他们有可能把一项技术变迁与其社会环境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电子公告栏较低的声噪比,未经专家同行评议的电子预印件并未影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广泛使用这些网络技术,但却被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视为重要缺陷;CMC的信息社会化特征对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来说是真正的问题, 而对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来说却是网络合用的基础和最主要的优越性。我们从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评价一项新技术(比如电子网络)的实际作用,只有与特定职业组织(比如科学)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对于科学交流系统而言,更可能的情况是:即使网络技术今后持续改进,并因此而使科学交流实践发生重大变化,仍不会出现各学科都能充分利用网络各项功能的情况,也不会从根本上瓦解各学科已建立的科学交流体制。手段的多样性和形式的可变性将是当代科学交流系统的基本特征。正如交流理论家伽尔维(W.D.Garvey)指出的,“科学交流系统的创新者,尤其是那些完全按照其它学科的模型设计一个学科的交流系统的人,很可能被大多数学科中的科学交流过程的总体相似性所误导。这些相似性掩盖了学科之间的重要差别,为一个学科设计的交流创新可能被证明不适合甚至有害于另一个学科。”(16)
4 结语
最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莫过于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吵吵嚷嚷的”(clamorour)社会反应。甚至, 有些技术(比如克隆技术)在其实际影响尚未表现出来之前就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应接不暇的技术变迁显然加强了奥格本式的忧郁:人们几乎没有机会仔细体验一项新技术的滋味,更新的技术(或原有技术的升级)又已经扑面而来。无所适从的感受不仅困扰着普通人,也困扰着那些创造技术的人。因此,我们的时代尤其需要“学者式的冷静”,以在变化中调整步调和建构秩序。
电子网络作为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之一,其潜在价值已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政府部门的政策多是为了推进网络建设和鼓励人们“科学地”使用网络,对网络如何与各种工作体系结合,以及网络使用所产生实际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则需要学术界做具体的调查研究。本文提到了沃尔什和贝马关于网络在科学中运用情况的研究报告,但应该指出,他们的调查是在美国背景下进行的,且调查范围不大(只限于两所大学中的四个自然科学学科),所使用的滚雪球抽样方法也有局限性,因而其结论的普遍性是有待检验的。比如,他们没有强调网络可得性(涉及科学家购置电脑和使用网络的费用,国家或地区网络设施的总体状况和建设进程,政府对网络运行的监控和管理策略等对科学界实际用网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可能是我国许多科技人员尚未用网或用网效率不高的社会原因之一。鉴于此,我们目前正在设计一项针对中国科技人员用网状况的社会学调查,试图对更广泛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有关该项调查的情况和研究结果,我们将另文报道。
注释:
(1)详细分析可参见:L.Sproull & S.Kiesler,Connections.Cambridge,MA:MIT Press,1991.
(2)J.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Random House,1964,P.68.
(3)J.Ellis,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86.
(4)R.Thomas,What Machines Can't Do.Berkeley,CA: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4.
(5)R.Thomas,What Machines Can't Do.Berkeley,CA: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4.
(6)R.Thomas,What Machines Can't Do.Berkeley,CA: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4.
(7)R.Thomas,What Machines Can't Do.Berkeley,CA: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4.
(8)S.Fuchs,The Professional Quest for Truth.Albany,NY:SUNY Press,1992,P.112,P.7.
(9) R.Rice,"Network Analysis and Computer- MediatedCommunication Systems",in S.Wasserman & J.Galaskiewicz (eds),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Thousand Oaks,CA:Sage,1994,PP.167—203.
(10)S.Fuchs,The Professional Quest for Truth. Albany,NY:SUNY Press,1992,P.112,P.7.
(11) 本节概述的调查结果均引自J.Walsh & T. Bayma,"Computer Networks and Scientific Work", Social Studiesof Science,Vol.26(1996),PP.661—703.该文所指的“网络”或“CMC网络” 不包括那些以电脑为基础的网络(Computer-basednetworks),如数字电话系统或传真通讯系统。
(12) 本节概述的调查结果均引自J.Walsh & T.
Bayma,"Computer Networks and Scientific Work", Social Studiesof Science,Vol.26(1996),PP.661—703.该文所指的“网络”或“CMC网络” 不包括那些以电脑为基础的网络(Computer-basednetworks),如数字电话系统或传真通讯系统。表1和表2。
(13)J.Ziman,Public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67,P.102.
(14) M.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4,PP.161—162.
(15)米哈依洛夫等著:《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徐新民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16) W.Garvey,Communication:The Essence of Science.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4,P.298.
标签:科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cmc论文; 社会学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电子论文; 数学论文; 非正式论文;
